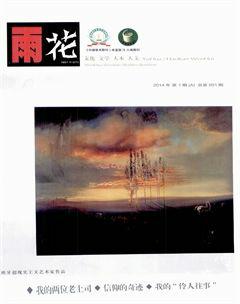梦见
●张 樯
梦见
●张 樯
妈妈这是怎么了?妈妈的这一反应,让我忽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妈妈早已去世了。她不能再对我的呼唤作出任何回答了。
我居然梦见了S国的总统。
我们前往S国,参加一场世界级的汽车大赛。
宽阔的比赛现场,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车手和五颜六色的赛车。然而,等了很久,比赛却一直未能进行。不知多少时候过去,一位来自总统办公室的金发小姐,跑来抱歉地通知大家:“大赛推迟了,因为眼下我们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
可以想象我们的反应。大家吵闹着争辩着,乱作一团,聚集在赛场不愿离去。
忽然我们看见总统现身于人群。我们曾经无数次在电视在报纸在各种媒介上见过他,还是惯有的严峻神情,那招牌式的有些摇晃的步态。人群归于寂静。
我恰巧站在他的身边,他的话听得清清楚楚,没有遗漏一个字:“你们知道吗?我国的森林正遭受严重的虫害。”他将手中的一枚显然刚刚摘下的果实掰开,我们看到一只蠕动的虫子。
他也不管我们的反应,话音刚落,他就迈开那招牌式摇晃的步态,向着远处茂密的森林走去……
我悄然对身旁的一个S国人说:“你们真是幸运,选择了一个高贵、正真的人,他将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
久别的妈妈
我又一次回到家里。我不常回家,往往间隔三五年才回家一次。因此我的归来,吸引了不少邻居,制造了一场小小的轰动。
在我家那狭小的客厅里,挤满了闻讯赶来的人,有熟悉的,也有陌生的。他们皆与我嘘寒问暖,笑脸相迎。有两个阿姨从人群中走出来,还亲切地拉住我的手,叫起我的小名。但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她们是谁,我在哪里见过她们。忽然,一阵熟悉的饭香飘了进来。我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从家里的厨房飘来的。谁这么早就开始张罗欢迎我的饭菜了?我赶忙穿过人群,跑到厨房一探究竟。
却是妈妈。这时候也只有妈妈才会想到做饭。我看见她独自在锅台忙碌,看见我走来,头也没抬。
“妈妈,在做什么菜?”我叫了一声。妈妈好像没有听见,仍围着锅台忙碌。
“妈妈,在做什么菜?”这次我抬高了声音。
妈妈没有抬头,仍旧自顾自忙活。
妈妈这是怎么了?妈妈的这一反应,让我忽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妈妈早已去世了。她不能再对我的呼唤作出任何回答了。
然而,确信面前忙碌着的就是久别的妈妈。她因为我的到来,也从另一个地方赶来了。意识到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泪珠从我的眼中滚落,我不由分说,紧紧地抱住了妈妈,生怕她会突然离开。
刺杀希特勒
这个梦,缘于一本关于二战的书。做梦的那天晚上,我恰好读到诺曼底登陆那一段。书中记载,这场被丘吉尔喻为“有史以来最困难、最复杂的作战”发起后的第10个小时亦即翌日6时,才被希特勒全部获悉……我的梦就从这里开始。
在希特勒的办公室,一名高级军官伦斯德正向希
总统
特勒禀告军情,显然希特勒已经相信盟军正式登陆的消息。这真是出乎希的神算之外,在此之前希特勒、伦斯德甚至在德军中颇有远见的隆美尔元帅都不会相信这是事实。因此,这使希特勒极为沮丧和暴躁,只见他在血红的纳粹旗帜下不停地踱着方步,仿佛再也不会停下来。那一撮醒目的黑胡须也急切地跟着抽搐起来,乌黑发亮的大皮靴掀起一阵响亮而恐怖的声音。偌大的办公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伦斯德将军这时垂立一旁,大气也不敢出。而我就站在他们的对面——我想我此刻该是希特勒麾下的一名侍卫官。很快希特勒停了下来,并恢复了一贯的镇定,也许是一夜的酣睡发挥了作用,他的脸上开始泛起少有的红光。仿佛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他和伦斯德开始谈起另外的话题。我听见伦斯德问元帅何时将称帝,他轻蔑地将胡子一撇,冷笑道:“不就是爱德华一世二世吗?我不感兴趣。”他的手用力地朝空中挥去,仿佛要将空中的什么劈为两半。“我只要征服世界!”话音刚落,他便哈哈大笑起来,好似全世界在这一瞬间已经被他牢牢地握在了掌心。伦斯德也跟着笑了起来。满屋子回荡着他们肆无忌惮的笑声。我感觉墙上那面巨大的纳粹旗也在朝我呲牙咧嘴地笑着。
这时候希特勒压根儿也不想如何去对付盟军了,或者说他已经彻底淡忘了盟军登陆诺曼底的消息,这会儿他只想乐一乐。你猜他想到了什么?只见他用力地将手一挥,命令道:“喝酒去!”听见这一命令,我在想全世界的男人,大凡在得意或者绝望时,无一例外地都会想到喝酒,即使希特勒大人也不例外。命令一旦下达,希的党卫军司令部成员全都赶来了,伦斯德司令,G集团军布莱斯柯斯上将,甚至沉着的隆美尔元帅也来了。一群人簇拥着希特勒,浩浩荡荡开出司令部。
我也夹杂在队伍中间。我们来到大街上,前方不远处,颇负盛名的柏林大酒店在等待我们。开阔空旷的大街上,鹰隼般威严的党卫军排着整齐的队伍,侍立两旁。希特勒连看也不看一眼,自顾自走在队伍最前面,我们也看也不看一眼,跟随希特勒乌黑的大皮靴,在坚硬的路面上敲打出巨大的声响。渐渐的,司令部远了,党卫军的队伍远了,巍峨的柏林大酒店赫然耸立面前。希特勒的大皮靴开始停了下来,并毫不犹豫地迈向酒店门柱的台阶。待我们的人马全都开进富丽堂皇的大厅时,我忽然发现迎接的人群中,闪过一个熟悉的面孔。那不是丘吉尔吗?那一刻,我看见他正望着我,并给我一个明显不过的暗示。是时候了!我对自己说。然后我不假思索地,悄悄掏出藏在衣袋里的勃朗宁手枪,靠近希特勒……
旺角
我必须在夜里12时前赶到罗湖关,否则一旦闭关,我就回不去了。我一看手表,怎么也不敢相信,时间已接近11时半,可我还人在旺角。如果我抓紧这最后的时机,尽快坐上地铁,兴许还来得及,还能在口岸关闭前到达。
这个时间,旺角一如既往,还是人潮涌动,灯火熠熠。我拨开闹哄哄的人群,一阵小跑,拼命寻找地铁口。这是我极为熟悉的路径,曾无数次从这里来回。我走进一幢大房子,有一条长长的走廊,我试图穿过,我意识到,现在我必须抄近路,才能赢得时间。然而,穿过这条长长的走廊,我却爬上了一座半山。环顾四周,人也愈来愈少,周围一片漆黑,很是荒凉。这是我从未来过的地方,我忽然发觉我可能已经迷路,心中不由一阵发虚。
深感庆幸的是,很快我就听到了巨大的轰鸣声,是火车进站的声音。那么可以断定,车站就在附近,或许就在山下。
我试着往山下望去,却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火车的轰鸣声却愈加真切和清晰。
我变得大胆起来,又往下探了两步,却感觉脚下一阵松动。就像在许多电影中重复的一个镜头:我连人带泥土、石块一同缓缓掉了下去。
凌士宁
我的朋友中,凌士宁属于手头拮据的一个,数年来,他的日子过得总是紧紧巴巴,也养成了精打细算的习惯,他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获知亚马逊买100送20图书之类的打折信息。有时候他宁愿走好长一段路,也不换乘另一班车,原因是能够省下区区5角钱的车费。
那天黄昏,我们约好要去一处地方吃饭。他还没有下班,我在他上班的大厦附近等了一阵,还不见他来,只好先行一步,让他随后跟来。
去餐厅的那一段路并不算长,却遍布泥泞,也许是刚刚下了一场雨的缘故。我走得小心翼翼,生怕随时都会绊倒。走着走着,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路上散落着一枚枚闪闪发亮的硬币。我俯下身来捡了几枚,就又往前走去。接下来,在一处水洼旁,我还看见几张票据,上面写满好多的零。奇怪的是,我竟没有捡,只看了看,就跨了过去。
一会儿,在某个车站站牌下,凌士宁追了上来。我赶忙告诉他一路上的发现,还炫耀道,今天真是鸿运当头,有捡不完的钱,还看到一张张写满零的支票。
凌睁着一双特大的眼睛,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该奇怪的倒是我,难道你跟在我的身后,就一点没有发现?
凌说,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认定一定是我拿走了全部。
我说,我只是捡了几枚硬币,说着从口袋里掏出来给他看。
凌不相信,执意要我将那几张写满零的支票也拿出来给他看看。
我一再说没有。凌突然目露凶光,一改往日温和的个性,把我狠命按到在地,翻遍我所有的口袋,抓了一把硬币,扬长而去。
买碟
同事张万极年长我许多,竟也与我有相同爱好,喜欢看碟搜碟。见到我,二话不说,总是向我借碟。鉴于借出的碟,十有八九总是有去无回,我常常索性顺水推舟,改借为送,也好做个人情。对老张也不例外,我前前后后已不知送他多少次碟了。有一次我部门的同事刘小姐专门托我买了一堆碟,恰巧被他看到,当场截获。起初他假意说只是看看片名,看着看着就不肯还我了。我再三强调,这是我为刘小姐买的,且她已经付款。然后告诉他,如果实在喜欢,可先拿去,我再买来,还与刘小姐。我的意思再清楚不过,这次我不再奉送,若是喜欢,拿钱来,我的碟也不是捡来的。狡黠如他,当然听懂了,但碟拿走了,却不肯付款,竟说下次给。七八张碟,也就区区几十元钱,他竟不愿掏自己腰包。想着还要自己贴钱再为同事再买,我当下就很是不爽。
随后在等电梯时或在职工食堂打饭,常常能遇见老张,他总不忘提醒,他还有碟钱未还我。也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已,从不见他有掏腰包的意思。我只好大度地表示,算了算了。
后来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竟是与老张一起去买碟。
我们要去很远的一个地方买碟。其实现实中也如此,因为当地严查,我们买碟常会去40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买,那里才有我们需要的盗版碟。不过,梦里显然要比现实中的那个地方更远,我们要翻越一座很高的山。我开了一辆车在前方带路,老张也开了一辆,在后面跟着。公路弯弯曲曲,车辆来来往往,我们转了很多弯道,开了很长的路,突然我听见身后一声巨响,老张连人带车一同翻到了沟里。
老张并没有丧命。我再次见到他时,他躺在病床上,眼睛半开半合,身上绑满一道道的绷带。我靠近他,表达了我的歉意,都怪我带的路,碟没买到,却……老张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张开一双凄楚的眼睛望着我。
那个梦之后,我每当见到老张,总是满含歉意。只是他浑然不觉。
雨夜
雨,大到不能再大,沉沉夜色中,像挂了厚厚的帘子。
在狭窄暗淡的屋中,我忙完手头的一切,已准备睡下,忽然接到电话,出大事了,我的同事T不想活了,现在正站在我们30多层的写字楼上,准备往下跳。而在跳下之前,他指名一定要见我一面。这是他在众人的劝告下提出的条件,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在深夜找到了我。
为什么是我?我和T仅仅是十分普通的同事,除了打打照面,平时根本没有多余的交往。那么,他为什么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独独想到了我?
不管怎样,我还是匆匆赶往现场——我们每天都进出的那幢写字大楼。
雨,真是大到不能再大。就像香港警匪片里的一个场景,亮闪闪的雨线中,人们齐刷刷地站在黑黝黝的楼下。见我跑来,全都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我。
我的上司L迎上来,很快我就从他的口中得知,原来T欲寻短见是因为他的妻子背叛了他,他一时想不开,就冲上了30多层写字楼的楼顶。那么,为什么会叫我来呢?L说他也不得而知,是T提出来的,也许你能够劝他下来。再说你上去一切不就真相大白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他,以及那些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的同事们是否怀疑我与这一切有什么瓜葛?真是天可怜见,我非但不认识他的妻子,也许甚至根本没有见过。会不会待我爬上楼顶,非但不能劝说T下来,反而会刺激已失控的他,冲上来一把撕碎了我。
我不知道是怎样爬上楼顶的,也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雨,大到不能再大,将夜色洗得透亮。见我走来,与T保持距离的一群人自动让开,让我通过。空旷的楼顶,就像一方舞台的中央,站立着T,散乱的头发和湿漉漉的衣服,使他像一头受伤的野兽,正等着我向他走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