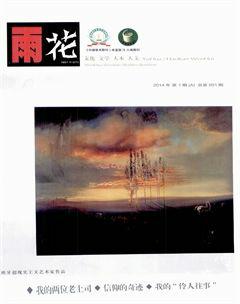老顾的手
●朱斌峰
老顾的手
●朱斌峰
老顾一手将细钢丝插入保险柜锁孔温柔地鼓捣着,一手左左右右地旋动锁钮,眼神凝在半空的虚点上。我,惊异地看见他的手竟像精密的齿轮,在严丝合缝地转动着。造物主真是神奇,竟然造出了那么一双灵巧的手。
整整九天,我一直在铜锁巷观察老顾,在这个世道,我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铜锁巷是银城的老街老巷,因地处国营锁厂旁而得名,它与小城的化工路、铁厂街、工人新村一样,都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生事物,如今已被时光腐蚀得破败不堪,知趣地躲在光鲜的大厦后,就像西风中的弃儿。我就站在巷内的一家小旅馆二楼,隔着残破的窗玻璃,俯视着对面的锁店。那间锁店门脸不大,是由沿街平房向前延伸的小披屋构成的,色调灰暗。屋墙上钉着木牌,上面横着“顾记锁店”四个毛笔字,宛若螃蟹似的。店内,一简易木桌上摆放着配制钥匙的小机器,靠墙的木架上躺着各式各样的锁具,木桌后每天都坐着老顾和他的儿子。锁店的生意冷清,很少有人在店前驻足,可顾氏父子总是专心致志地坐着,就像一对泥塑,被灰蒙蒙的光线淹没着,可我还是能看清那两张出自同一模具的脸。我很想看清老顾的手,可他的手总拢在袖管里,像只引人猜疑的小白鼠。
你甭费心思猜测我的身份,那不是你的活儿。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老顾是国营银城锁厂的下岗工人,他四十多岁,瘦干矮小,头发斑白,脸多皱纹。他没有老婆,只有一个傻儿子。我和他素不相识,没有半角钱关系,我只是奔着他的手艺而来的。
终于,我看见老顾站在黄昏中洗手了。他将黄色塑料盆搁在木桌上,白皙的手在一块瘦小的香肥皂上游走了片刻,就钻进了白色的泡沫里。然后,他把被泡沫包围的手慢慢放入冒着热气的盆里,眯着眼,一脸陶醉的模样。他的动作轻柔舒缓,就像在进行金盆洗手的仪式。半晌,他才把手从塑料盆里抽出,对着并不明亮的阳光细细擦拭起来,就像勤劳的工人擦洗自己的工具,就像乐手抚摸心爱的乐器。我怦然心动,快速下楼,走向顾记锁店。
我直直地站在店铺前,身影遮去夕阳的灰烬。老顾从光影中抬起头,笑了笑。
我威严地沉着脸,老顾又笑了笑,笑得很弱。
我哼了声:你会开锁么?
会的,会的。不管啥样的锁我都能打开。我以前是国营大锁厂的技师。老顾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就像风化的石头。
那你在公安机关备案了么?
备案?备啥案?老顾愣了愣。
凡是从事开锁职业的人员,都必须到公安机关备案。否则就有非法的嫌疑。
老顾有些慌了,双手作护卫桌上小机器状:你?你是公安局的?
我摇摇头。
那你……想干啥?
我是特高公司总经理毛总,我的保险柜钥匙弄丢了,急需打开取款。
哦,是这样呀!你是想让我帮你打开保险柜?老顾又笑了。
可是你没有公安机关的备案证明,我没法相信你,只有另找他人了。我摇摇头,又补上一句:这世道,什么样的人都有,不得不防呀。
老顾梗起脖子,脖子上的青筋跳了出来:你不信我?
老顾正如我意料的一样,是个固执的男人。我在心里发笑,嘴上却说:你没有证明,我怎么相信你?
你等着!老顾说着就钻进了店后幽暗的里屋。
我笑盈盈地看向仍端坐着的老顾之子小顾,那孩子十来岁,正一脸傻气地盯着我笑,就像观看马戏团里的动物。他的目光粘在我脸上,让我有些不自在。
片刻,老顾抱着一大叠证书从里屋走出,他将证书一本一本摊开给我看,那里面有银城锁厂的工会证、下岗证,也有先进工作者等荣誉证。老顾指指点点,言辞热烈:你看看!你看看!我在国营锁厂可是劳动模范、技术标兵!我这样的人你还不信?
我对着摆在面前的事实不停地颔首:嗯,不错不错!我们公司不从事锁具业务,否则,我一定会高薪聘请你!
老顾愈发激动,脖子上的青筋跳得更激烈了,就像打了一针鸡血。他喋喋不休地说起曾经的锁厂岁月,说他车、镗、钻、磨都能玩得转,说他曾作为岗位成材模范,戴着小红花跟以前的市长亲切地握过手,说着说着就哼起了歌儿:一把钥匙打开千家锁,小苗儿挂满露水珠啊,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我们干起工作劲头儿足——显然他已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我知道火候到了,突然说:我信你!那我公司的保险柜你能打开么?
小事一桩!我这就去帮你打开!老顾抄起小工具箱,向傻气的小顾嘱咐了几句,豪迈地挥挥手:走,咱们走!
我看天色尚未完全黑下来,就走到旁边的西瓜摊,磨磨蹭蹭地买了个西瓜,剖开递给小顾。老顾真诚地说:不好意思,让您破费了。小顾接过瓜就啃,不时张开满是红瓜瓤的嘴喊“瓜,瓜”,就像只青蛙。
我和老顾赶到特高公司时,正是恰如其分的好时光。那时,夜色就像黑色的液体让小城中毒般地微醺着,一些隐秘的事物正悄然绽放。这是个容易让人疏忽的时刻,我领着老顾坐着电梯直达大厦十楼,走向特高公司。我早就从手机短信得知:该公司的员工早已鸟兽散了,电子眼已被遮盖了,现在只有一个马仔在黑暗处等着我。那条信息言简意赅,上写:鸟飞,林静,月朦胧,颇像意象派诗人的佳作——这便是马仔发给我的,他的合法身份是这所大厦的保安。
当我昂首挺胸走进特高公司时,马仔站了起来,谦恭地喊:毛总。
我哼了哼,大摇大摆地领着老顾向总经理室走去,那里有一个绿色的保险柜,密封着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我点上一支烟,指指保险柜,对老顾说:老顾,就看你的手艺了!
老顾一进大厦就缩手缩脚起来,就像误入迷宫的孩子。当他茫然的目光落在保险柜上,眼儿倏地一亮,宛若猎人见到了猎物。我可以向你保证:他的眼光比我看到保险柜时还要亮。他扑了过去,把小工具箱打开,蹲下身将耳朵贴在保险柜上,就像聆听孕妇的肚子。
老顾全神贯注地诊听着保险柜,马仔紧张地看着门外,我抖落起几丝烟灰,整个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只有心跳声,就像安装了三颗定时炸弹。
老顾一手将细钢丝插入保险柜锁孔温柔地鼓捣着,一手左左右右地旋动锁钮,眼神凝在半空的虚点上。我,惊异地看见他的手竟像精密的齿轮,在严丝合缝地转动着。造物主真是神奇,竟然造出了那么一双灵巧的手。
大约过了三分钟,老顾突然高叫一声:开!保险柜的门晃了一下,敞开一条缝儿。老顾站起身,我毫无礼貌地扒开他,上前有条不紊地将保险柜里的十来万现金塞进包里,才弯腰对老顾说了声“谢谢”,随后抓起一叠钱放进老顾的小工具箱。那显然是一个败笔,老顾被那叠钱砸得迷惑起来;我赶紧拉起懵懵怔怔的他向外走去。
我们顺利地拿到了钱,计划执行得堪称完美。
我心里清楚,要不了多久,我会将老顾忘得一干二净,并衷心地希望老顾也能将我彻彻底底地忘掉,过多的记忆是种累赘甚至危险。
半年后,我不得不想起老顾,想起了他那张本已模糊的脸。
那天,我悠闲地踱在街上,打量着擦肩而过的行人。那些陌生的面孔让我感到安全而自在。我不喜欢与人相熟,不愿以任何明显的特征被他人记起。我只想混杂在人群中,如风过耳,如沙泻地。
我走了许久,才在一个街头阅报栏前站住,点支烟看起当日的《银城晚报》,我匆匆浏览着,那些文字跟我没半点关系,比天上的星星还远。忽然,我被第四版左下角的新闻吸引住了。那条新闻说的是,近日警方抓获一名惯犯顾某,据其供认,他已经入室盗窃六次。他作案极有规律,每月一次,每次所盗现金均为六百元,相当于小城政府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该惯偷入室后会顺手帮人家修理好滴水的水龙头、怠工的马桶以及坏掉的锁具,无物可修时就帮人家打扫打扫卫生,颇有按劳取酬的意思。看完新闻,我有些生气,这个惯偷显然坏了我们的行规——不按规矩出牌的人是可耻的。我吐了口烟,忽地觉得这个惯偷名字有些耳熟,既而一惊想起老顾来。我又逐字逐句地将新闻读了一遍,没有发现老顾供出特高事件的迹象,想了想,忍不住向铜锁巷寻去。
也许是天冷风急的缘故,铜锁巷比半年前更破败了。曾经的小旅馆墙上刷上了大大的“拆”字,墙下只有烤山芋的大伯把铁皮炉捣弄出淡淡的热气。偶尔驶过的车轮碾起飘飞的梧桐落叶,就像扣压下寄往春天的信件。令我惊讶的是,顾记锁店的门脸还开着,只不过木桌后只坐着傻气的小顾,显得人单影只。
我环顾四周无人,挺直身子向顾记锁店走去,想印证一下老顾的下落。我想:那个小顾肯定认不出只有一面之缘的我了,而且凭我的智商对付一个傻儿太绰绰有余了。
我越走越近,小顾直盯着我,嘴唇动了动,喊:锁……配钥匙。
停了片刻,他又喊。瓜……吃西瓜!
我吓得站住,意识到小顾认出我了。我的头型、着装都变了,他怎么还能认出我呢?
小顾站起,朝着我欢快地喊:瓜,瓜,瓜!就像高唱的青蛙。
我被他的喊声追击着,只得走过去,竖起中指“嘘”了声,示意他安静。
小顾停住叫嚷,一脸无邪的笑。
我问:那个……你爸呢?
他,玩捉迷藏……被,被警察,带走了。
我又问:你认得我?
他嬉笑:你,西瓜!
他仰起的小脸满是欢欣,让我心儿一动,脱口而出:我不是西瓜……我是你舅舅。
舅?小顾挠了挠后脑勺想了想,既而热情地喊起来:舅,舅!边喊边拉住我的手就往里屋拽。
我懊悔不已,我深知一些历史事件往往毁于细节,我不明白早已百炼成钢的自己怎么会一时疏忽,冒出个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舅”字来——也许是小顾那张不设防的脸让我麻痹大意了。说实话,我的确有个外甥,他和小顾年纪相仿,但一点儿也不弱智。除了寄玩具寄文具寄零食,我已经一年多没见着他了,干我们这一行的,与亲人而言还是相见不如怀念为好。
小顾那傻小子手劲儿不小,我被他强拉进里屋。里屋很暗,就像个黑洞。我很快就看清了屋内的摆设,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一张床、一桌两椅及其他生活物件,预估总价不超过三千元。这种家庭我们是不会光顾的,如若光顾的话,不仅将一无所获,而且会坏了自己在业界的名头。我犹豫了一下,拿出几张钞票递给小顾欲走。可小顾紧紧攥住我,一个劲地摇头,还往我身上蹭,就像一只猫。
我在心底叹了口气,就说:小顾,舅不走呢。
小顾这才松开我,说:舅,我饿。
我翻开碗柜,拿出鸡蛋煮了两碗面条,和小顾吸溜起来。我不会做饭,鸡蛋跟面条粘在一起呈坨状,可小顾吃得挺满意,边吃边朝我傻笑,可见做个傻瓜未必不是一种幸福。
吃过面条后,我关上店门,仰卧在床上百无聊赖地想事儿。我是该在这儿住下来,还是该编个谎拔腿就走呢?我干事一向干净利落,从没这么优柔寡断过。如在往常,这样的小事我用屁股就能决定的,可那会儿我竟然犹豫起来。小顾很快活,他不停地抱来玩具车、玩具枪递给我玩,可我是有真家伙的人,怎会对那些假的、少胳膊少腿的、疑似从垃圾堆里扒拉出来的玩意感兴趣呢?
小顾把他的宝贝献完后,见我仍僵硬地躺在床上,想了想,转身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塑料壳本儿,嬉笑地递给我。我随手翻了翻,那是某个年代流行的日记本,扉页上写着“大干红五月纪念”什么的,还盖了个银城锁厂的公章,里面插页都是样板戏《沙家浜》的彩照,那个阿庆嫂精神抖擞,但表情显得夸张。我翻着翻着,竟然在那泛黄的纸页上看见新鲜的字儿来。那是老顾近期的日记,字迹潦草,圈圈画画,可点划就像用细针扎出来的。我只看了两眼就不由得坐了起来,那些字儿在往我眼里钻。小顾为终于找到一个让我感兴趣的玩具快活着,咯咯地笑着。我在他透明的笑声中,读起一个老男人的心语。为便于你了解老顾,现将部分日记摘录如下:
“7月6日昨天锁店来了个人,他说他是特高公司总经理。我帮他打开了那家公司的保险柜,他给了我三千块钱劳务费。那钱厚沓沓的,我拿着它心里就发虚儿。今天我偷偷去特高公司附近打听,果然我上当了,那家伙根本不是狗屁总经理,是个小偷!他利用我打开保险柜,把那家公司准备给职工发工资的十几万卷跑了……我真后悔啊!我怎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呢?我可是国营锁厂的劳模啊!我该咋办?”
“7月8日想来想去,我还是不敢报案。一报案我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再说,那些钱我真的有急用,我拿它还掉了李二虎1200元、张春江1000元、田七600元的欠债,那都是我老婆治病时落下的,可是花了那么多钱,我老婆还是撇下我走了……那些债借了好几年了,就因为没钱一直没还。欠债不还,他们虽不说啥,可我哪有脸面找他们啊,平日想找个人说说话,都找不着人,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活着还有啥意思……对了,我还欠着章大个子600块,得想法儿还清。只要还清债务,我就有脸面有底气跟那些老工友喝喝酒了。”
“7月13日今个儿我真是鬼缠身了,竟然中了魔溜进了水云间小区2幢606室,偷了600元钱。我羞愧,害怕,后悔。可当我把偷来的钱还给章大个子时,心里的大石头一下子落地了,人一下子就轻松了,毕竟债全还清了……”
“8月13日又是13号!我又鬼缠身了,整天烦躁得紧,总觉得有事儿没做,就跟以前戒烟时一样。晚上,我忍不住还是溜进了水云间小区一户人家,又偷了600块……不过那户人家真有钱,银行卡、金首饰不算,光现金就有一万多。我拿它600块不就是九牛一毛嘛!”
“11月13日加上今天这次,我已经偷了5次钱了,每次都是13号,每次都是600块。我真是个天生的贱坯,竟然偷上瘾了。每次拿着一串钥匙、两个改锥打开水云间小区别人家的防盗门时,我就控制不住地兴奋,就忘了公安,忘了我是在偷东西,就像喝醉了酒,就像又回到了国营锁厂的岗位上……说实在的,我已经好久没干过正经活了,在国营锁厂那会儿,工友们都说我的手是天生的肉钥匙,这条巷子里哪户人家丢了钥匙打不开锁,我只要脱下布鞋,在锁芯锁簧部位啪啪几下,锁就开了。我不晓得除了配制钥匙开锁儿,我的手还能干啥?……哦,想起来了,13号就是以前国营锁厂发工资的日子。”
看完老顾的日记后,我顺手将那几页纸撕去,记日记真不是个好习惯。
其实,我对国营银城锁厂还是比较了解的。我认识的一个舞小姐就是该厂的下岗女工,她说:多年前,银城锁厂工人全员下岗时,曾聚集在政府大院前静坐,打出过“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翁”的标语,合唱过“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曲,可闹闹之后就没了动静,很多锁厂工人老老实实地去做摩的生意了,那种职业显然是不合法的,因为银城是文明城市,早已颁发了“禁摩令”。我这人没有职业歧视,可对缺乏职业操守和技能的人极为鄙视,比如对老顾就有恨铁不成钢的恨意。那个老顾太没有职业水准了,他怎么能每月按时去同一个小区活动呢?难道他跟他的儿子一样弱智?抑或他把人民警察看成与他儿子一样的人了?我义愤填膺走来走去,不小心踢了煤球炉一脚,痛得叫了起来。我这才发现煤球炉的垫脚架是三个锁子疙瘩,那是当年国营锁厂浇铸锁具时留下的废品。
我的表现让小顾吃惊,他仰起小脸看我:舅,你生气了?
我回过神来,笑笑:哦,我是替你爸担心呢。
小顾眼里的笑像风一样散去,他握住我的手,盯着我:舅,舅,我要,爸爸。
我不习惯被人抓得太紧,那让我紧张。我的手心冒出汗,一边抚摸小顾的头,一边慢慢将手抽出来。我想我该偷偷溜走了。
我被小顾看住了,他就像块磁铁吸在我身上,怎么也甩不掉,就连半夜小便他都形影不离地守候着我。他的韧性,他的警觉性,让我惊叹。如果小顾不是傻儿,那他长大后一定能成为优秀的狱警。我真想用蒙汗药撂倒他就走,可他的眼神让我不便出手。我想我可能沾染上小顾的傻气了,我的职业修养还没有练到家啊。我只好陪着小顾,给他煮鸡蛋面,给他买玩具,就像真舅舅一样——能快速进入角色是我的专长。
那天,我带着小顾去儿童游乐场。他可能是第一次去那种地方,兴奋得脸红得像富士苹果。他什么都敢尝试,我硬着头皮陪他坐过山车,在风驰电掣中恐惧得闭上眼并紧紧抱着他,可他却毫不畏惧,睁大眼睛开怀大笑。走下过山车后,我心有余悸,腿根发软,并为自己刚才那么拼命地抱着小顾而不好意思。我好久没跟人抱得那么紧了,当然除了一些女人外。而在划游船时,行走江湖多年却不会游泳的我,不慎失足落水,幸被小顾拉了上来。关于这个事故我不想多说,否则就会像电视肥皂剧那样过于煽情了。我只想说:小顾的手劲真大,他趴在船上用力向上拉我时,我吐着满嘴的水,耳边满是他急切的喊声,不知是“舅……舅”还是“救……救”。当我像落水狗般躺在船上喘匀气儿时,临时做了个决定:我得想办法把老顾从警察手里捞出来。我给自己的理由是:免得夜长梦多,让警察从老顾身上顺藤摸瓜找到我,这个理由并不充分,也难说服自己。我想了想,又给了自己第二个理由:只有把老顾救出来,我才能摆脱小顾的纠缠,还自己一个自由身——这个理由你觉得充分吗?
我带着小顾满小城转,找律师,请警察同志吃饭,交一定数额的罚金,然后去看守所看望老顾。我最讨厌干这些事,更不愿去看守所讨晦气。我的那个马仔也在狱中,可我从没去看望过他。我对天发誓,为了小顾那小子,我真的破戒了。
我拉着小顾走进看守所会客室时,老顾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嘴唇颤抖想说什么,我赶忙抢先高喊:姐夫,我带小顾来看你了。要不了几日,你就能出去了。
也许我的话说得太快,噎得老顾梗着脖子说不出话来。他脖子上的青筋就像蚯蚓一样爬起,最后还是隐去了。他不看我,只是一把抓住小顾的手。
小顾笑:爸,回家。
老顾真是没出息,眼泪哗地就下来了,滋润着他那张皱巴巴的脸。
我舔舔干涩的嘴唇,又说:姐夫,有我照顾小顾,你放心吧。
小顾用力地点头:舅,舅,烧蛋面条,带我,坐过山车。
老顾把脸沉了下来,不通人情地说:你们走吧。说着转过脸不再理睬我们。
我拉起小顾就走,那个地方连鸟都不愿久呆的。
几天后,老顾如期出来了。
那天早晨,隔壁豆腐店女孩一大早就朗读起小学课文《陈秉正的手》:手掌好像四方的,指头粗而短,而且每个指头都伸不直,里外都是茧皮,圆圆的指头肚子都像半个蚕茧上安了指甲,整个看来真像树枝做成的小耙子……我和小顾早早起了床,在女孩朗朗的读书声中,站在顾记锁店门前迎接老顾。
老顾低着头走得很慢,就像被铜锁巷的风拉扯着。
小顾跑上前,喊:爸!
我不便再称老顾为姐夫,只是清清嗓子问:那个谁,你恨我么?
老顾抬眼盯着我,摇了摇头,才开腔道:我没有告发你。
我仍执拗地问:你恨我么?
我只恨我自己,恨我的手!老顾说着举起右手,那只手小指已被整齐地切去了。
我悚然心惊,睁大眼睛:老顾,你的手指怎么了?
我把它切了。老顾平静地说:这样,它就不会作怪了。
我愣了愣,慌张地说:那,小顾就交给你了,我,我走了。
你我有缘,握个手吧。老顾慢慢伸出手来,就像伸出一只手铐。我没敢碰那只手,慌忙跑去。
跑到巷拐角处,我仍听见小顾傻气的声音在飘: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