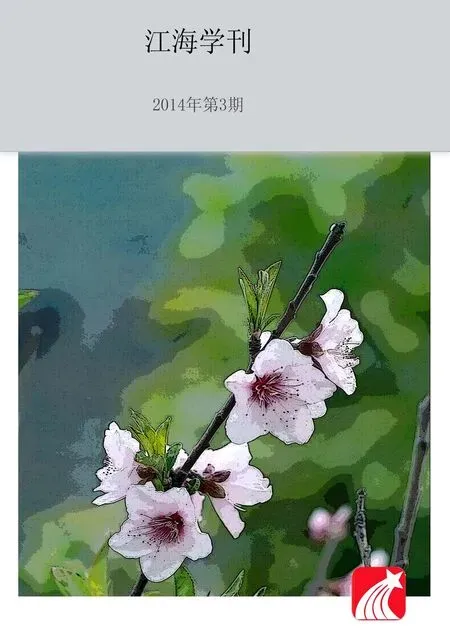实至而名自归
——对宋庆龄“国母”称呼来由的历史考察
罗福惠 李凤凤
围绕孙中山先生“国父”的尊称,已有多位学者作过多种角度的分析讨论,这类研究显然不乏历史文化意义。去年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宋庆龄诞生120周年,我们触类旁通,拟就宋庆龄的“国母”称号一事,表达如下三点意思:一是有关“国母”之实的言行概括;二是考察有关“国母”之名的出现和使用情况;三是对领袖光环下的女性应如何自我锻造的思考。
宋庆龄独特的功绩与贡献
宋庆龄自1915年10月25日与孙中山结婚后,就投身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主要做答复书信、翻译外文和电报等文字工作,成为一个“热情的小革命者”①。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主动担负起维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历史重任,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1925年5月爆发“五卅惨案”,宋庆龄随即发表谈话,声援民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她说“此次惨案,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的压迫”,号召“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②。此事为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对国内重大事件的首次公开表态,新闻记者称“夫人随先生奔走革命10余年,其精神与主张,当为关心此事者所欲知也”③。可见,公众对此前一直处于幕后的孙夫人缺乏了解,希望能借助五卅运动这类大事以窥其“精神与主张”,而宋庆龄不负众望,在20~40年代几个重要历史关节点的政治选择上都顺应了历史潮流,表现出远见卓识。
北伐前后,国民党内陆续出现了三民主义的修正派,宋庆龄积极维护孙中山的主张,与修正派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25年11月,宋庆龄通电谴责公开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西山会议”派,称“总理泉下有知,亦当痛苦”④。1927年,针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清共”和“分共”,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义正词严地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称“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是孙中山的信徒;党也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她严正声明“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⑤。抗日战争爆发,宋庆龄主张抗战到底,并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搭桥。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她发表声明,称国家处于日本入侵的危急关头,“内战必须停止”,“个人的不同政见都必须放弃”⑥,努力沟通南京与西安之间、国共两党之间的意见,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战后期国民党制造反共活动,宋庆龄对此一直密切关注并严厉谴责。1941年1月,宋庆龄和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就“皖南事变”联名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要求他们“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⑦。1944年2月,宋庆龄公开发表声明抨击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游击区的封锁政策,称“中国的一些反动分子正在准备(内战)以便消灭我们斗争中的民主部分,这一部分是陕北和敌后的游击区”⑧。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呼吁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1949年在中国政局大变动的情形下,宋庆龄坚持留在大陆,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
由此可见,在20~40年代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宋庆龄都站在革命、团结、进步的思想高地,尽最大努力推动中国走向光明,正如斯诺在致宋庆龄的信中所说:“在最复杂困难的时期,你始终坚持走正确的道路”,“你永远是在进步运动的主流而不误入漩涡”。⑨
宋庆龄在特定环境下所从事的维护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言行必然给她带来一定的危险。国民党右派始则施展种种反间,继则散布流言蜚语,恶意造谣中伤,甚至进行暴力威胁。如1927年7月15日,即宋庆龄发表抗议汪精卫“分共”声明的第二天,她的寓所就遭到何键所部军队的搜查⑩,此后她的“房子周围到处都有人监视,向她的仆人询问各种问题”。1929年5月,她在从苏联回国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期间,不断受到蒋介石等的拉拢,同时又受到戴季陶“应该遵守党纪”的警告,还有上海公安局杨虎之流“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宋庆龄自称——引者)装置秘密无线电,布置外国特务来对付我”的威胁,甚至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中。但宋庆龄依然坚定地表示“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不向威胁和恐吓屈服。
宋庆龄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赞扬。如《汉口民国日报》称赞“孙夫人宋庆龄同志,赞助总理革命事业,于三民主义,知之最审,行之尤力,秉正嫉邪,遂为反动派所深忌”。美国记者、作家文森特·希恩盛赞宋庆龄为“中国的圣女贞德”,称她有“罕见的精神力量,使她在严重的危险中镇定如常。她对孙中山的忠诚以及她作为孙夫人的责任感,使她能够永久经得起各种考验……死都不能吓倒她……贫困和流亡、自家亲属对她的忿怒、世界各地对她的污蔑也都不能使她的意志屈从于她认为错误的道路”。苏联《消息报》称“每当中国的革命经受危机的时候,宋庆龄同志始终站在革命的一边,如果有必要的话,她时刻都准备着独自一人奔向那鼓舞起义的中国人民和农民的目标”。
此外,宋庆龄还积极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和各种福利救济事业,作出了他人不可替代的贡献。
(一)领导妇女解放运动
早在1924年11月,宋庆龄随孙中山北上经过日本时就曾发表过关于妇女解放的演说,她说“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中国妇女应该参与公共事务,虽然“妇女无意于那类政治荣誉,但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1927年1月5日,宋庆龄被选举担任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主任,主持妇女党务训练班,她指出新时代的妇女不只有家庭的责任,还有社会的责任,“不仅是在家庭里面做一个贤母良妻”,还要“为国家做一个良好的国民革命的妇女”。为了有效地救护伤兵,她创办了妇女救护班,培养救护人员。1938年7月,宋庆龄担任“中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9月发动广东妇女为抗日将士及后方难民捐助寒衣,提出“一个广东妇女捐助一件寒衣”的口号,并带头向妇女团体抗敌协会捐款5000元。在她的号召下,广东妇女踊跃捐助。1940年4月她到重庆考察大后方的抗战局势和妇女工作,要求“妇女们都能够起来做坚持抗战的工作”。
宋庆龄积极倡导并领导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对世界各国和中国的妇女来说是一种伟大的精神鼓励力量”。
(二)参与“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落难者
宋庆龄一直关心和保护进步人士,“深盼全国人才,无论为国家主义派,为共产党,均能集中于同一战线之下”。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被捕,宋庆龄立即开展营救活动,得知邓已经遇害后,即于12月19日撰写《宋庆龄之宣言》,谴责“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而“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致于死”。1932年4月~8月,宋庆龄为营救牛兰夫妇,多次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并与其他中外名人发起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任委员会主席。经其努力,国民党司法当局同意牛兰夫妇到南京鼓楼医院就医。
1932年12月中上旬,宋庆龄与蔡元培、杨铨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担任同盟主席,积极奔走营救落难者。1932年12月,许德珩被北平警探非法拘捕,后经民盟营救,于12月19日释放。之后宋庆龄又为营救郑太仆、罗仁一积极努力。1933年,营救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余文化、陈藻英等人,并请律师营救在北平被判有期徒刑的侯外庐、马哲民两位教授。此外,她还于1933年5月25日,成立“丁梓保障委员会”,开展营救丁玲、潘梓年的工作。5月31日,又委托史良担任邓中夏的辩护律师。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特务杀害,宋庆龄于19日发表《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严厉斥责了国民党的暗杀行径,指出“这些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1936年11月,宋庆龄为营救沈钧儒等“七君子”多次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到1937年6月,又领衔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要求释放“七君子”,表示如果爱国有罪,则愿同服“爱国罪”,国民党政府终于在7月31日将“七君子”无罪释放。
(三)领导“保卫中国同盟”,为抗战提供援助
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在香港正式成立,宋庆龄任中央委员会主席,用国际声望和影响力积极寻求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如路易·艾黎所说的,“外国朋友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靠”,一些华侨也表示如果不是宋庆龄担任负责人,“我们就不汇钱来”。保盟一经成立,就得到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广泛支持。到1939年6月15日,在保盟成立的13个月中,收到各国捐款共为25万元港币(约为8万美元或1.6万英镑)。
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后,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资助医疗救济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建立和援助国际和平医院,为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大量医疗援助。1938年9月,宋庆龄着手筹建国际和平医院,决定将晋察冀边区五台山医院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共四所,分别位于陕西延安、山西岚县、河北阜平和苏北,并请白求恩大夫出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至1947年,国际和平医院增加了三倍,有总院八所,还将设立总院两所和分院四十余所,并有无数流动医疗队“把药品送给人民”。
而且,在宋庆龄的指示下,保盟向抗日根据地援助了大量物资和医疗用品。1938年底,为新四军购买了五万套军装所需的布匹和一批药品。1939年3月,宋庆龄将募得的五卡车药品和物资交给八路军以及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5月初保盟上海分会协助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给新四军医院带去大批紧急援助物品。当年夏,宋庆龄接受英国工业家约翰·桑尼克劳爵士捐赠的救护车,并派送这辆大型救护车和装载600箱医药用品的12辆卡车到延安和西北国际和平医院。1940年,保盟中央委员会每月拨款各1500元,订购大量棉背心、担架、绷带、纱布等,提供给西北医疗单位。从1943年到1944年,保盟共资助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等774581.3美元,171075603.54元法币。抗战胜利后,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为国际和平医院争取资金,在1947年陆续把捐款和物资赠送给华北八所国际和平医院和它们的四十所分院、白求恩医学院、药厂等地,在1948年又将300吨医疗用品分类运往解放区。
保盟为抗日根据地解了燃眉之急。因此,毛泽东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对宋庆龄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您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
第二,救济难民、儿童。宋庆龄在抗战中提出要特别注意战灾儿童,因此保盟成立后一年,即资助陕西三原建立孤儿院,收养儿童500名。1943~1945年,保盟共资助儿童工作551055.12美元,42216824.50元法币。抗战胜利后,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推行儿童福利工作,如1947年3月10日,中国福利基金会作为美国战灾儿童义养会在中国的代表,成立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义养会通过三十多个学校和儿童团体,帮助了五千余名战灾儿童。1947年,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创办三个儿童福利站和一个儿童剧团,“为邻近的孩子们提供文化、医疗和补充营养”,有五千儿童受益,并捐款给湖南省的四所孤儿院。1949年,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进行“小先生”制,推行儿童福利计划,受惠儿童达一万五千人。
此外,灾民、难民也是保盟救济的主要群体。1943年4月,黄河决堤,宋庆龄发起赈济河南灾民的国际足球义赛,所得门票收入125530元,汇交宝鸡豫灾赈济委员会,专用作赈济河南灾民。此外,保盟还募款5万美元救济河南灾民。1946年5月29日,她发起募集中国赈灾基金,号召募集资金救济难民。
鉴于宋庆龄对抗日根据地的帮助和在各项救济事业中的巨大成绩,董必武在1947年7月2日来函表示感谢,称“先生为全国儿童福利事业暨其他各种社会救济事业,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百折不挠,始终如一,此为民族谋福之伟大精神,实素为我全国同胞所崇”。
(四)深切关怀文化界进士人士
宋庆龄关心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处境,积极帮助有困难的进步文人。1936年3月22日,宋庆龄致函鲁迅问候其病情,并赠“糖食三种,茗一匣”,6月又致函催促鲁迅迅速就医,10月鲁迅逝世后,又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委员,亲自主持鲁迅丧事。
1944年湘桂战争后,旅居广西的文艺作家纷纷疏散,许多人贫病交加,陷入困境,宋庆龄发起募捐晚会以援助文艺作家。1944年9月29、30日,她亲自主持晚会,为贫病作家募得捐款80万元,由茅盾、郭沫若、老舍等三人代表全国文协接受。1946年3月,发起设立作家、艺术家“文化福利基金”,邀请中国歌舞剧社在上海义演,收入8000美元,全部作为文化福利基金,分配给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华音乐协会等十个进步文化团体,救济贫困文化人。1947年10月1日,她主持中秋游园会,募集文化福利基金,以救济苦难文人,后又指示中国福利基金会将一批救济物资直接送到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负责人侯外庐的家里,让协会负责将这些救济品分发给确实有困难的学者们。
宋庆龄对进步文人的关心和帮助使他们深为感动,终生难忘。1981年宋庆龄逝世之后,侯外庐先生在忆及1947年秋宋庆龄如何关心、帮助处于困境的学者、文化人时,所写纪念文章的标题就是《伟大的将士,伟大的母亲》。以此时侯外庐先生的学术地位之尊和年事之高,这样称呼宋庆龄,实是发自肺腑,令人感动。
国母——尊敬、反讽、诱惑的符号
从初步的史料检索来看,把母亲一类的称呼用之于宋庆龄,只比1924年7月26日广州市特别党部召开的青年党员大会的宣言称孙中山为“国父”晚半年。即1925年1月末,孙中山在北京病重,北京学生联合会、中华妇女协会、中俄协进会三团体致函宋庆龄表示慰问,称“夫人实吾民众之慈母,望殷勤守护,俾先生病早痊可”。此时的称誉还是“民众的慈母”。
一个多月之后,孙中山逝世,在国民党的有关宣传活动、国内民众团体和海外侨胞的纪念活动上,一些宣言、挽联、纪念文章中称孙中山为“国父”的渐多。到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尚在,从河南北伐前线下来的一批伤病官兵,因对生活、治疗情形不满而闹事,宋庆龄和邓演达前往安抚慰问,且发表了充满关怀与同情的讲话,伤病官兵受到感动,觉得“国母一片慈心,我们北伐军人,应遵守纪律”,事件得以平息。这虽然是出自当时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的现场亲历者的回忆文字,仍可说明“国母”之称当时已在国民革命军中流行。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于1927年8月22日从上海启程,秘密赴苏联。在苏联时,尽管宋庆龄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的欢迎,但是1928年春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态度是“听任蒋介石得逞”,希望宋庆龄、陈友仁等“回中国去同蒋介石合作”。而同年夏天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又确定了过左的方针政策,助长了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中共出席共产国际六大的代表陈宽,就在大会发言中排斥国民党左派,公言孙中山的学说“现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无论是蒋介石之流的右派,还是宋庆龄、邓演达这样的左派,这些人恰恰相反,他们应该是中国劳动群众无往不胜的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失败者”。应该说此时宋庆龄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故1928年她曾到德国和法国旅居。1929年5月15日宋庆龄从苏联回国,5月18日到6月1日参加了孙中山奉安大典的系列活动,同年9月21日遂赴欧洲,其中在德国居停时间最长,直到1931年7月接到母亲病逝确讯,宋庆龄才在8月上旬再度经莫斯科、西伯利亚回国。
在这段时间里,尽管宋庆龄仍在坚持革命活动(主要是和邓演达筹划反蒋活动),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显然左右皆不以为然。社会舆论既有宋庆龄“流落莫斯科”、“流落欧洲”的奚落,甚至不乏其婚姻和感情生活的谣诼。“国母”是不被提及了,即使是孙中山的奉安大典期间,《申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报道宋庆龄时,有时直呼其名,客气一点的也不过是称“孙夫人”、“孙总理夫人”。
“国母”的再度出现是宋庆龄已经归国,而且发生“九一八”事变之后,由此直到全国抗战前半期的1940年,“国母”频频见诸报刊舆论,不过多是一些影响不大、且政治立场各异的小报刊。1931年12月,蒋介石杀害了邓演达,宋庆龄公开发表宣言,宣称“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宣言发表之后,站在国民党右翼立场的王蕃立即发表《“国母”再醮了》的文章,不仅在“国母”二字上加了引号,表明自己的反讽态度,而且先以澄清谣言的方式重提谣言,“记得宁汉分裂时期,盛传‘国母’不甘寂寞,下嫁了‘美男子’陈友仁,又说勾上了洋顾问鲍罗廷”,“前此谣传,全非事实”,然后笔锋一转,称自己所说的“国母再醮”乃言“‘国母’已从‘国父’所手创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再嫁了邓演达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和中华革命党(即所谓第三党)”。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此文当然引起愤怒的反驳,《文艺新闻》上有短文说,宋庆龄的“个人宣言,我以为这是那些痛哭流涕着,正悔恸党破国亡,而又惭愤交集的国民党忠实同志们,都应三读的”,“照着封建的说法,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那么这话应该是称为‘国母’的所说的。要脸红的人留心一下‘国母’的‘教训’吧!”该作者赞同宋庆龄的立场和态度,但对“国父”、“国母”的称号好像有所保留。
1933年,因为宋庆龄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华年》杂志上发表不明作者的文章,把苏联的列宁夫人和宋庆龄称为两个“国母”,谈到当时列宁夫人“正在那里为苏俄的儿童争一些想像与智识的自由”,主张“新兴的文学家”为儿童“写成许多不违反革命理论而同时也无碍于儿童想像的健全发展的读物”,作者认为列宁夫人这个动议“大概可以通得过”,但宋庆龄“竭力为民众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党国当道未必完全赞同”,“前途究属如何”,“我们始终疑虑着”。作者把宋庆龄与列宁夫人并论,虽赞扬了宋庆龄的行动,但对行动的成效抱有疑虑,当然批判的矛头仍是针对“党国当道”。阿英(钱杏邨)的短文则介绍宋庆龄寓居上海的日常生活,称赞宋庆龄“对于世界潮流之演变仍极其注意,订阅英美日德各国杂志数十种”,又说“夫人以国母之尊,各方敦请宴叙者颇多”,但宋庆龄“对各方酬酢皆一概谢绝”,从正面树立宋庆龄好学沉思、关注大局、自奉简约、决不张扬的形象。
国外也有对宋庆龄“国母”之称的呼应和贬斥。1936年9月10日,由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著名科学家郎之万主持的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巴黎召开,宋庆龄是该会副主席,却因国民党政府的阻挠不能出席,遂由钱俊瑞代表。参加会议的法国共产党元老加香对钱俊瑞说,“假如宋庆龄这次能够亲自来到巴黎该多好呀!你们的国母不也就成了我们统一战线的法国的保姆了吗?”由此可见“国母”之名不仅传到了国外,也得到国际民主人士和左翼政治家的认可。日本人显然看出了这一点,故在1937年的日文某报的短评中,讽刺“中国左翼分子奉孙夫人为国母”,上海的《妇女生活》立即有义正词严的回应,文章说,“‘国母’,我记得当十余年前总理初逝世的时候,国人已曾这样的尊称她过,何尝是最近才有的称呼?不过这十余年来事实的表现,更够得上称‘国母’,那倒是事实。过去的‘民权保障运动’,历来的救亡工作,以及最近的‘救国入狱运动’”,“不正是孙夫人对民族国家的功绩吗?所以日文报上的论调,正相反的在中国反应出了国母称呼的恰当”,并且说,“在危急存亡的今日的中国,正需要若这样的国母!我们更需要爱戴这样的国母的国民!”这是当时难得的旗帜鲜明且理由充分地为国母正名的一篇文章。
国民党表面上尊重宋庆龄,从1929年3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宋庆龄为中央执行委员开始,不久又被国民党中常会选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在国民党“四大”后连任,但1942年国民党“五大”后降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但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形成之前,宋庆龄始终不肯住到南京,不出席国民党的会议,并公开宣称不与国民党合作,因此国民党也有意把孙中山与宋庆龄切割。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4月1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遵行,但对因上海沦陷而避居香港的宋庆龄一无提及。
1941年1月14日,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在还未获悉1月6日已发生皖南事变的情况下,即已联名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此宣言未能在大后方甚至香港公开。1月18日,在惊悉皖南事变之后,宋庆龄、陈友仁联名通电蒋介石,痛斥其倒行逆施,破坏抗战,要求“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延安的《新中华报》刊登了这篇通电。稍后延安方面又获知了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1月14日已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一事之后,《新中华报》又于2月9日刊发了电文内容,并冠以醒目标题《国母宋庆龄先生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停止剿共部署,发展抗日实力》,这可能是抗日根据地的报纸最早正式使用“国母”的称号。
不过1944年3月12日,在美国举行孙中山逝世19周年纪念活动之中,因香港沦陷而被迫住到重庆的宋庆龄,于是日晚在重庆国际广播电台对美国民众发表了题为《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的英文演说。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翌日刊登宋庆龄演说的中文稿,14日又就此事发表社论,称宋庆龄的演说“不仅帮助了美国人民对国父遗教的认识,也增进了中美人民间的友谊和团结。毫无疑问的,全国人民将为国父的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加紧奋斗”。社论中两次称孙中山为“国父”,而对宋庆龄只称“孙夫人”。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又把中国推入了内战。宋庆龄在1946年7月22日发表声明,强调“国民党必须通过联合政府、人民民主和土地改革来执行它的历史任务……自由批评必须代替腐化、恐怖和政治暗杀。国民党应该立即执行这些任务,否则就要担负掀起内战的责任”,呼吁美国人民阻止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所有的军事援助,并帮助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政府”。宋庆龄的声明得到了中共和绝大多数民主进步人士的赞赏,上海的《生活知识》杂志先以《内战声中,国母说话了》为题,支持宋庆龄“要求立即扑灭内战之火”的“声明”;继以《国母的呼喊在美国引起了大反响》为题,介绍数种美国新闻报刊对其政府对华政策的批评,还引用了美国著名评论家希德对宋庆龄的赞扬:“当孙夫人讲话的时候,让全世界洗耳恭听吧!全中国妇女中没有任何女人能得到中国数万万人民这样巨大的崇敬。”
由于宋庆龄在国内外都具有崇高的威望和巨大影响力,当然也有人忘不了对此加以利用,用国母的尊号劝导宋庆龄“回到中央”。王清流的《未被国人遗忘的国母宋庆龄》就是这种态度。当1947年冬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蔡廷锴等在香港筹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是宋庆龄提出的),希望宋庆龄南下担任领导时,宋庆龄并未离开上海。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成立,李济深任“民革”中央主席,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王清流之辈以为有了利用和拉拢的机会,遂撰成长文,名为叙述宋庆龄的“一页光辉革命史”,把宋庆龄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态度说成“她对现政府政治上有略微的格格不入,可是她深切地了解政府”,“李济深包围不了她”,“要利用她的人虽想尽种种方式向她采取攻势,而她始终没有被人利用”,所以“国人还在念念不忘怀想着这位有深远政治革新家尊称国母的宋庆龄”。文章最后点出了国民党方面的真实企图,要宋庆龄“体恤国艰及爱护民族,本着大革命家精神原则下放弃了小我,完成大我的革命精神,捐弃了成见,用迅速步伐回到中央,共参政局”,“因为人民还未遗忘着‘国母’,国母不要辜负了这尊称”。文中明显含有不回到国民党路线就不配称为“国母”的意思。果然,在两岸对峙的格局形成后,台湾社会舆论就把宋庆龄“雪藏”起来了。大陆上也不再使用“国母”称呼宋庆龄,但公认宋庆龄是中国20世纪的伟大女性。
综观宋庆龄“国母”称呼的出现和使用情况,可知“国母”只是一个符号、一种工具,不同党派、不同政治倾向的人用其表达不同的诉求。左翼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称国母,表达了对宋庆龄由衷的尊敬之情;而国民党右派一些人称“国母”,则极尽诬蔑嘲讽之能事,企图达到败坏其名声的目的。而宋庆龄不为所动,她说,“这样的谣言,以及另外一种性质更加恶劣的谣言,正在暗中传播开来,想要败坏我和我的家庭的名声,败坏我所献身的伟大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名声,但这将是徒劳的……我并不为此感到很不安,因为我是按良心行事。如果我的良心是清白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无关紧要”。还有一部分国民党右派分子想借“国母”之名行拉拢之实,美化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宋庆龄回到国民党政府,但他们却忘记了宋庆龄早就发布的声明,“我曾经明白表示过,在国民党未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前,我绝不参与这个党的任何工作”。
有其实而不居其名
“国父”、“国母”的称呼问题,可说属于历史学中的政治文化范畴。中国在君主王朝时代,常用“母仪天下”来赞誉正宫皇后,其主要职责是治理后宫、抚育皇子,在后宫发生龃龉和朝堂发生政争时,起到调和或缓解作用,但在后世历史学者看来,恐怕也只有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和明太祖的马皇后等极少几个女性近之。近代中国人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最早是把华盛顿称为美国国父,后来又用来称过土耳其的凯末尔、苏联的列宁,20世纪40年代曾介绍说印度人称甘地为国父,巴基斯坦人称真纳为国父,但对称为国母的外国女性了解极少,列宁夫人在苏联是否被尊为国母其实也大有问题。到20世纪后半期,世界各国使用国父、国母称呼的现象已难得一见了。在现代西方政治文化中,第一夫人的作用主要是树立国家领导人家庭和美的形象,在男女平等、家庭和谐方面为社会大众作出表率,并成为女性的榜样。但国母与第一夫人不同,第一夫人是国家领导人的妻子,一个人成为国家领导人,他的妻子自然成为第一夫人,而国母只是指开国领袖的妻子,第一夫人不可胜数,但世界上能得到国母称号的人并不多,大多都是昙花一现,而且会随着政权后继者对她的态度变化而改变。
回到20世纪前半期的政治文化语境,就容易理解,为何中国成为共和国后唯一的国母称号落到了宋庆龄的头上。的确,国母的出现要先有国父,但开国领袖的光环不是决定性的保障条件,根本还在领袖夫人的形象自塑。作为女性和母亲,她首先还是国家、民族和民众的女儿,要求她高度忠于祖国,始终和民族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当然她为国家和民众建功立业,不一定是指宏大的战略方针的决策和执行之功,更非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她应在关键的转折关头作出正确的抉择,维护民族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在各种政治力量的竞争中,她应有宽阔的胸襟和包容能力,起到“调和鼎鼐”的作用;她要成为女性的代表和楷模,为女性的解放努力,成为女性能力和人格提升的范型;她应有慈母一样的爱心,时时处处“亲民”,“人溺己溺”,为儿童、老弱、受难者和弱势群体提供切实的关爱和帮助;她还要有足够的知识、优雅的风度,能广泛得到国际认可。总之,只有这样的女性,才能为领袖的光环增色而不是相反。
客观地说,从国母的标准来看,宋庆龄在20世纪前半期指导妇女解放运动,参与“人权保障同盟”、“反帝大同盟”和长期领导“保卫中国同盟”,关爱儿童,救济灾民,帮助受难者和弱势群体,对内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对外展开多种形式的民间外交,为中国20世纪的进步事业作出了他人不可替代的贡献,符合国母的标准和要求,因此,她被称为“国母”是名副其实的。但宋庆龄一直非常低调、谦逊,如1925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八十八次会议,时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的何香凝主动提出辞去妇女部长一职,推荐由宋庆龄接任,她称赞宋庆龄“学问贯中西,阅历经验广”,由宋接任妇女部长,不仅“藉其声望,党务可发展”,而且“造福女界,正未有涯”。此提议获一致通过,但宋庆龄谦辞,称自己“德薄能鲜,焉能膺斯重职?且远居申江,难以就任”,请“另选高者,以充此席”。1933年4月23日她致函国民御侮自救会,要求辞去该会主席职务,称“因庆龄所任其他工作,已感时间精力穷于应付,万难再尸误事”,“此后仍当以会员一份子之地位”,“努力御侮工作”。1957年,毛泽东与宋庆龄自苏联归国时同坐一架飞机,毛泽东请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极力推辞说:“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而毛泽东坚持道:“你是国母,应该你坐。”宋庆龄一贯持有的低调、谦和的态度,使她对自己被称为“国母”一事也表示反对,她在1980年11月致函中共中央时就指出“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
近代国母尊号的“加冕”与传统社会的皇后不同,皇后需要举行特定仪式进行册封,而国母并未制度化,其称呼来自民间,并不需要任何政党或政府的决议或文件公之天下,是民众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认可后形成的一种尊敬和爱戴之情的外在表露,是一座无形的纪念碑。因此,国民党后来漠视宋庆龄与孙中山的革命伴侣关系,一些右翼文人对“国母”二字极尽轻佻、诬蔑之能事,或者如日本人挑拨离间地认为“国母”称呼是中国当时的“左翼分子”即民主进步人士提出和使用的,当时还有一些人极不以为然,这都反映出政治文化的复杂性。但宋庆龄“国母”之称呼来自于民众,更见其名副其实,这是她良好口碑的反映,她有其实而不居其名。虽然“国母”称呼到20世纪后半期不再使用,但这并不影响宋庆龄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定位。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中国民众的母亲。[本文受到华中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项目(项目号:2013YBZD10)资助]
②③《为“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6月9日。
④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故居管理处编:《宋庆龄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第224页。
⑦延安《新中华报》1941年2月9日。
⑧《宋庆龄呼吁取消对中国共产党的封锁》,《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4期。
⑩陈漱渝:《“中国的圣女贞德”——宋庆龄大革命时期在武汉》,《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