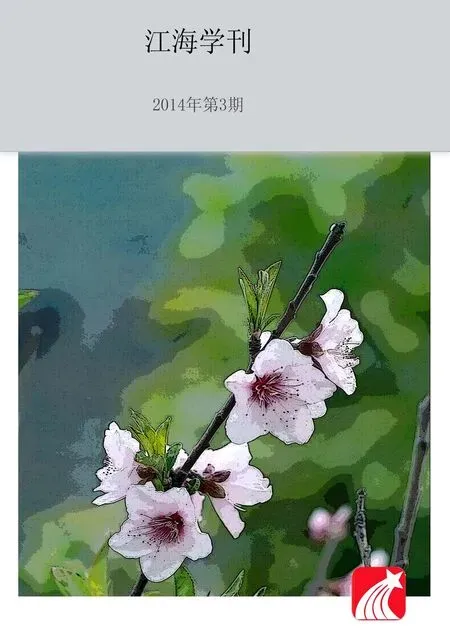艺术媒介与审美感兴
——论艺术创作发生的内在物性特征
张 晶 张佳音
感兴是传统的中国美学范畴,却有着丰富的现代美学理论价值;艺术媒介是一个带有西方美学色彩的范畴,在艺术哲学中被许多西方学者所论及。在我们看来,这二者在艺术创作领域中有内在的相通之处。
感兴源于中国的早期诗学,在后来的发展中意义得到了普遍性的升华。学界一般对感兴的理解与阐释是“触物以起情”,也即诗人受到外在事物的触发而兴发情感并产生创作冲动,因而,感兴与感物是难以明确区分的。魏晋时期著名文论家刘勰对兴的界说是:“兴者,起也。”①所起者何?正是诗人之情感。刘勰又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②也揭示出诗兴之发动是“感物吟志”的产物。笔者在这里要表述的观点是:感兴并非只是由物感而触发的诗人(或艺术家)的情感,而且是诗人(或艺术家)以其独特的艺术媒介感受外部世界,在与难以预期的事物邂逅触遇时兴发的艺术神思。这种艺术神思并非止于抽象的内在语言和情感波动,而是凭借内化的艺术媒介(也可称为媒介感),受到偶然的外物触遇感召,产生了诗人(或艺术家)的内在审美构形。
一
在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领域中,媒介的价值、媒介的功能尚未得到系统的研究和集中的揭示,而实际上,媒介之于艺术是至关重要的。离开了媒介,艺术本身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对于艺术品的物化表达来说,必须以媒介为工具方可实现;对于艺术创作的思维过程而言,同样是要借助媒介的内在化运行方可完成。只有这种内外的联通,艺术创作才能从理念走向实践。笔者在论述“艺术媒介”时曾这样表述:“艺术媒介是指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凭借特定的物质性材料,将内在的艺术构思外化为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品的符号体系。艺术创作远非克罗齐所宣称的‘直觉即表现’,而有一个由内及外、由观念到物化的过程,任何艺术作品都是物性的存在,艺术家的创作冲动、艺术构思和作品形成这一联结,其主要的依凭就在于艺术媒介。”③媒介具有物性的特征,这也是艺术品之所以成为客观存在的最根本的原因。如果艺术创作仍是停留在头脑中的观念形态,那么,无论你如何宣称你的作品是伟大的,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而只能徒然成为人们的笑柄。即便是将直觉推向审美活动的极端的克罗齐,其实也并不否认艺术创作中媒介的存在和作用,如其所言:“既承认个别艺术有分别与界限,就不免要问:哪种艺术是最强有力的呢?把几种艺术联合在一起,我们是否得到更强有力的效果呢?我们对此毫无所知,只知道在每个事例中,某某艺术的直觉品需要某种物理的媒介,某某其他艺术的直觉品需要它种物理的媒介,作再造的工具。”④克罗齐将以媒介进行艺术表现的阶段与内在的直觉阶段分割开了。他主张直觉的阶段是本能的审美,而通过媒介的“再造”则是“外射的实践活动”。因而,克罗齐虽然承认媒介的存在,但认为它只是“再造的工具”,而与内在的审美直觉是割裂的、分离的。
我们之所以将“艺术媒介”作为文艺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加以申说阐述,就是认为媒介是连通艺术家的内在运思与作品的物化表现的唯一通道。这可以视为诗(文学)与其他门类艺术的通则。对于媒介问题有深入阐述的一些杰出的美学家,如黑格尔、杜威、鲍桑葵、奥尔德里奇、古德曼等,都主张媒介是内在于艺术家的精神世界中,以其特定的媒介感觉来感受外在世界,兴发独特的审美情感,从而形成艺术的审美构形的。换言之,越是成熟的、卓越的艺术家,内在于心的媒介感觉越成为其产生创作冲动、审美运思的动力,在创作发生的感兴阶段,媒介就有着与生俱来的功能——这当然是对成熟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家而言。说到这里,可以明显看到,这是与克罗齐的观念截然相反的。
恰在此处,艺术媒介与审美感兴相遇了,而且彼此贯通了。感兴是诗人(或艺术家)偶遇外物的变化而唤起了内心的情感从而产生创作的冲动,同时也就进入了内在的审美构形。在诸多对感兴的界说中,笔者认为宋人李仲蒙“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⑤最能概括“感兴”说的审美本质,这其中的关键要素,一是感兴的偶然性,二是心与物的遇合性。言感兴者,皆可见之。魏晋时期的孙绰就说:“情历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则兴感。”⑥唐代诗人王昌龄所列诗歌创作“十八势”之第九“感兴势”:“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⑦宋代大诗人杨万里以“兴”法为诗之上:“大抵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庚和,不得已也。然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有触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⑧明代诗论家谢榛所说:“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苦索,不易得也。”⑨这些都是典型的感兴论。所谓“触”、“遇”、“适然”等,都有着明显的偶然性质。而这种偶然恰是诗人(或艺术家)与外物的遭逢之契机。感兴之所以在诗或其他艺术创作中起着重要的发动作用,成为创作的原动力,关键在于它不是事先立意,不是幽寻苦索,而是诗人以其敏锐的感受在外物的兴发下产生了淋漓澎湃的创作冲动,并由此进入了审美构形阶段。
二
从艺术创作的审美角度来说,感兴并非随便什么人都可产生,主体的艺术修养、艺术语言的谙熟和作为诗人(艺术家)的创作欲望,都是必备的条件。艺术媒介是内化在诗人的审美感受之中的,或者说,诗人是以其特殊的媒介感来感受和把握世界的。
再从物性的角度来看媒介的性质及功能。艺术品的物性是探讨艺术媒介的重要理论支点。海德格尔于此说道:“一切艺术品都有这种物的特性。如果它们没有这种物的特性将如何呢?或许我们会反对这种十分粗俗和肤浅的观点。托运处或者是博物馆的清洁女工,可能会按这种艺术品的观念来行事。但是,我们却必须把艺术品看作是人们体验和欣赏的东西。但是,极为自愿的审美体验也不能克服艺术品这种物的特性。建筑品中有石质的东西,木刻中有木质的东西,绘画中有色彩,语言作品中有言说,音乐作品中有声响。艺术品中,物的因素如此牢固地现身,使我们不得不反过来说,建筑艺术存在于石头中,木刻存在于木头中,绘画存在于色彩中,语言作品存在于言说中,音乐作品存在于音响中。”⑩艺术品的存在并不止于物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的客观存在却必须依凭于物性。所以海德格尔又说:“但是在艺术品中使别的什么敞开出来的唯一因素以及与别的什么因素结合起来的唯一因素,仍是艺术品的物性。这看起来,艺术品的物的因素仿佛是一屋基,其他的什么和本真的东西依此建立。艺术家凭他的手工所真正制造的不就是艺术品的物性吗?”物性与其物质性材料如音响、色彩、石头之类有直接关系,但并非完全是一回事。物性在我的理解中是艺术品的整体的客观性存在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说,媒介是具有无可怀疑的物性的。媒介是离不开材料的(如音响、语言、色彩、石头等),但不等同于材料。黑格尔谈及媒介时说:“艺术品既然要出现在感性实在里,它就获得了为感觉而存在的定性,所以这些感觉以及艺术作品所借以对象化的而且与这些感觉相对应的物质材料或媒介的定性就必然提供各门艺术分类的标准。”黑格尔以不同艺术门类的媒介提供了艺术分类的标准或者说是依据,并由此揭示艺术审美的感觉性质,这是颇为重要的观点。然而,黑格尔在这里并没有将材料和媒介加以区分,而20世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奥尔德里奇则明确指出媒介与材料的区别,把这个问题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即使基本的艺术材料(器具)也不是艺术的媒介。弦、颜料或石头,即使在被工匠为了艺术家的使用而准备好以后,也还不是艺术的媒介。不仅如此,甚至当艺术家在使用弦、颜料或石头时,或者在艺术家在完工的作品中赋予它们的最终样式中,它们也还不是媒介。在这种最终的状态中,基本的艺术材料已被艺术家制作成一种物质性事物——艺术作品——它有特殊的构思,以便让人们把它当作审美客体来领悟。当然,在创作的过程中,材料本身对于艺术家来说是物质性事物,而不是物理客体。艺术家并没有对它们进行观察。确切地说,艺术家首先是领悟每种材料要素——颜色、声音、结构——的特质,然后使这些材料和谐地结合起来,以构成一种合成的调子(composite tonality)。这就是艺术作品的成形的媒介,艺术家用这种媒介向领悟展示作品的内容。严格地说,艺术家没有制作媒介,而只是用媒介或者说用基本材料要素的调子的特质来创作,在这个基本意义上,这些特质就是艺术家的媒介。艺术家进行创作时就要考虑这些特质,直到将它们组合成某种样式(Pattern),某种把握了他想要向领悟性视觉展示的东西内容的样式。……在艺术家的创作经验中,每一种材料都被当成一种小的、基本的审美客体。因此,合成的审美客体并不是领悟主体和艺术作品之间的一种若有若无的障碍。审美客体就是在其种类外观下出现的按一定构思组合的物质性事物(艺术作品),这种外观是适合于领悟性知觉的。”奥尔德里奇这样一大段论述看起来有些夹缠不清,但其中的主要意思还是给人以深刻启示的。奥氏认为那些具体的材料如声音、颜料、色彩、石头等并非真正的“媒介”,而只是其中的要素,“媒介”是在不同的门类的创作中由材料构成的整体的样式或者说“调子”。材料并非媒介的全部,媒介还有非物质性材料的成分,那就是呈现为物质性外观的整体样式。其实,美国著名哲学家古德曼在其代表性著作《艺术语言》中所说的“符号系统”(symbol systems),或许可以更为明白地标示出媒介的这种性质,而与“艺术语言”这个概念相比,“媒介”更突出了它的物质性。
将媒介与材料作这样的区分是十分必要的,在艺术创作中,材料是媒介的物质要素,但媒介是将材料呈现为艺术品的物质化外观的整体样式,媒介是在诗人(艺术家)的内在艺术思维中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从大的方面说,不同的艺术门类有不同的媒介,不同的媒介恰是区分不同艺术门类的依据与标志。黑格尔谈到艺术分类的标准时指出:“分类的真正标准只能根据艺术作品的本质得出来,各门艺术都是由艺术总概念中所含的方面和因素展现出来的。在这方面头一个重要的观点是这个:艺术作品既要出现在感性实在里,它就获得了为感觉而存在的定性,所以这些感觉以及艺术作品所借以对象化的而且与这些感觉相对应的物质材料或媒介的定性就必然提供各门艺术分类的标准。”我们要接着说的意思是,不同门类的艺术,依媒介的不同形态而划分,同时,也依据不同的媒介而进行创作,在其观念化的内在艺术思维过程中,不同的媒介就是不同门类的艺术家所凭借的最基本的工具。诗人(或艺术家)对于外在世界的感受,他们所赖以发生创作冲动的审美情感,就远非一般性的情感,而是伴随着媒介而兴发的。为了区别于艺术创作中的物化阶段的媒介,我们可以称之为媒介感。这种内在于艺术家思维中的媒介,英国美学家鲍桑葵称为“感觉的媒介”,这种媒介感使艺术家在触遇外界事物时产生了强烈的兴奋,正如鲍桑葵所揭示的那样:“因为这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实。我们刚才看到,任何艺人都对自己的媒介感到特殊的愉快,而且赏识自己媒介的特殊能力。这种愉快和能力感当然并不仅仅在他实际进行操作时才有的。他的受魅惑的想象就生活在他的媒介的能力里;他靠媒介来思索,来感受;媒介是他的审美想象的特殊身体,而他的审美想象则是媒介的唯一灵魂。”鲍桑葵在这里所提出的思想,正是笔者对于媒介的基本观念。诗人(艺术家)在其产生创作冲动、进入审美想象的阶段,就是以媒介为动力因素的,或者说是凭着媒介把握了外界事物的触点,从而得到了空前兴奋的投入状态,作品的胚胎便油然而生!这里所说的媒介也就是内在的媒介感。诗人(或艺术家)是凭着媒介来感受外部世界的。
三
与之联系的是审美情感与媒介的相生相依的关系。艺术创作的发生,离不开审美情感的动力作用,而审美情感是由自然情感变异升华而来的。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如“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本》)、“诗缘情而绮靡”(陆机语)、“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勰语)等,都说明了情感对于创作的发生作用。而情感的审美化,是离不开媒介的功能的。正如鲍桑葵在反驳克罗齐的观点时所说:“但是我不由得觉得,他自始至终都忘掉,虽则情感是体现媒介所少不了的,然而体现的媒介也是情感所少不了的。”这对我们极富启示性。在艺术创作中,媒介的功用须有待于情感的发动,而审美情感的生成,更是离不开媒介的运动。进而言之,诗人(或艺术家)在与外物的触遇中兴发起灵感,进入创作状态,并且在神思方运中完成了审美构形,媒介是其所依凭的内在工具。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认为,那些杰出诗人的经典作品,并非只是强烈情感的迸发,而是凭着媒介形成了完整的结构,他说:“伟大的抒情诗人——歌德、荷尔德林、华兹华斯、雪莱——的作品所给予我们的并不是诗人生活的乱七八糟支离破碎的片断。它们并非只是强烈感情的瞬间突发,而是昭示着一种深刻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他又引用了歌德的相关论述清晰地表达了他的观点:“歌德写道:‘艺术并不打算在深度和广度上与自然竞争,它停留于自然现象的表面;但是它有着自己的深度,自己的力量。它借助于在这些表面现象中见出合规律性的性格、尽善尽美的和谐一致、登峰造极的美、雍容华贵的气氛、达到顶点的激情,从而将这些现象的最强烈的瞬间定形化。’这种对‘现象的最强烈的瞬间’的定形既不是对物理事物的摹仿也不只是强烈感情的流溢。它是对实在的再解释,不过不是靠概念而是靠直观,不是以思想为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卡西尔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即:艺术创作绝非只是强烈情感的流溢,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来完成内在的审美构形的。杜威则是从经验的角度具体地谈到了艺术家以媒介的眼光来把握对象,从而创造出内在的审美意象,他说:“画家并非带着空白的心灵,而是带着很久以前就注入到能力和爱好之中的经验的背景,或者带着一种由更晚近的经验形成的内心骚动来接近景观的。他有一颗期待的、耐心的、愿意受影响的心灵,但又不无视觉中的偏见和倾向。因此,线条与色彩凝结在此和谐而非彼和谐之上。这种特别的和谐方式并非专门是线条与色彩的结果,而是实际的景观在与注视者带入的东西相互作用后产生的应变量。某种微妙的与他作为一个活的生物的经验之流间的密切关系使得线条与色彩将自身安排成一种模式和节奏而不是另一种。成为观察的标志的激情性伴随着新形式的发展——这正是前面说到过的审美情感。但是,它并非独立于某种先在的、在艺术家经验中搅动的情感之外;这后一种情感通过与一种从属于具有审美性质材料的视觉形象的情感上融合而得到更新和再造。”杜威的论述特别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他在这里是以画家与外界事物的接触遇合而产生作品的审美构形的,线条、色彩是内在于画家的媒介感,通过这种内在的媒介感来对眼前呈现出来的对象进行修正,因此,杜威进一步阐明了这个思想:“如果他是一位艺术家——如果他是一位画家,有着一种由于训练而对媒介的尊重,他就要通过他的媒介的强制力量,对呈现给他的对象进行修正。”(同上)杜威在这里如此具体地描述了画家的媒介感在创作的原初发动阶段时的重要功能,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也是符合艺术创作的实际情况的。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感兴,是通过与外物的触遇而唤起诗人(或艺术家)的情感,这是在文论传统中的通常理解,这已经不需要更多的论证与诠释。但是,本文要阐明的观点是,感兴的获得和创作冲动的发生,本身便是凭借着内在的媒介感的。刘勰论“神思”时所说:“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诗人这个“神思”腾跃的过程就是以文学的内在媒介感来进行作品的构思的。“辞令”不是一般的语言,而是能够表现物象特征的辞语,也包括声律,后面所说的“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都说明了“神思”不是与语言媒介无关的空洞想象,而是以文学的媒介感来进行运思的过程。(关于文学的媒介特征,在下面一节加以论述)绘画亦是如此,画家在感受对象时就是以颜色、笔墨和构形等绘画的媒介感形成了内在的独特画面的。如南北朝时著名画家宗炳论山水画的创作时所言:“况乎身所盘桓,目所绸缪,以形写形,以色貌色也。”宗炳这里所说的是画家在晤对山水而进入山水画创作的内在构形阶段,画家身在山水之间,目与山水绸缪,以自己头脑中的形来写照山水之形,以自己头脑中的色来表现山水之色。前一个“形”、“色”,就是画家的内在媒介感。五代时大画家荆浩也在其论学山水画时说:“夫山水,乃画家十三科之首也。有山峦柯木水石云烟泉崖溪岸之类,皆天地自然造化。势有形格,有骨格,亦无定质,所以学者初入艰难。必要先知体用之理,方有规矩。其体者,乃描写形势骨格之法也。运于胸次,意在笔先。”荆浩认为,对于画家来说,“形势骨格之法”是属于媒介范畴的,“运于胸次”是画家在与山水晤对产生创作冲动时便以之进行。如此之论,在山水画论中最多,那是因为画家画山水多是与山水晤对而产生审美感兴的。如宋代画家董逌评山水画时便特重感兴,如其评李公麟画时所说:“伯时于画,天得也。常以笔墨为游戏,不立寸度,放情荡意,遇物则画,初不计其妍蚩得失。至其成功,则无毫发遗恨。此殆进技乎道,而天机自张者耶?”董逌多以“天机”论画,其实就是感兴。“凡赋形出象,发于生意,得之自然。”这也是说画家在“见于胸中”阶段,便以颜色、构图等内在的媒介感来运思了。而在董逌看来,它们都是遇物则画的“感兴”产物,即“天机自张”,得于造化。
四
这里要专门讨论一下诗(文学)的媒介特征,这样可以见出其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的不同之处,同时,也更能发现其与感兴之间的内在联系。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感兴论在诗学中是首当其冲的。发掘诗学中的感兴论与媒介的内在联系,这是当代的文艺美学可以深入一步的重要契机。在笔者的理解中,文艺美学之所以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了原来的文艺学那种以文学的社会功能为主的格局,而着力发掘艺术的内在审美属性。
媒介是以物性为其特征的,而文学的媒介是语言,与其他门类的那些有着看得见摸得到的物质属性相比,文学的媒介就显得虚化得多。但文学的媒介仍然是媒介,而且同样是具有物性的。文学的语言当之无愧地成为一种艺术的媒介,是因为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保存流传,也是因为它是通过媒介而创造出来的客观存在物。文学的艺术语言看上去与其他文字的语言并无二致,其实是以特殊的构造法创造出作为审美客体的作品。鲍桑葵专门论述过诗歌语言的媒介性质,他说:“在雪莱看来,诗好像对付的是一种完全合适的而且透明的媒介,这种媒介并没有自己的质地,因此几乎不成其为媒介,而是想象从虚无中创造出来为想象用的。而别的艺术所运用的媒介,由于是粗鄙的、物质的、而且具有其本身的质地,在他看来,毋宁说是表现的障碍,而不是表现的工具。对于这种见解的回答就是我们刚才提过的。使媒介具有体现情感的能力的,是媒介的那些质地;诗的媒介是响亮的语言,而响亮的语言也恰恰和其他的媒介一样有其种种特点和具体的能力。”鲍桑葵是坚决主张诗歌的语言也是一种具有物质性的媒介的,他认为语言本身并不缺乏作为媒介的属性。奥尔德里奇仍然从他区分媒介与材料为二物的观念出发,来谈论文学的媒介。他认为作品中的词和句等都还是文学的材料,如其说:“文学的材料从根本上说就是在最一般的情况中学会的具有各种静态和动态的词和句。”如何从文学的材料达到文学的媒介?下面的话也供我们领会他的意思所在:“一个熟练掌握语言的人,可以有意识地使语言脱离上述用法,可以通过语言本身的动态性媒介,而不是指称作为外部题材的事物的语言,来向想象性领悟展现事物。但是,这就说到了文学的内容和媒介。”“诗的媒介不仅包括属于语言静态方面的语言的音响度,而且还包括刚才作为语言普通用法的动态的伴随物而提到的各种情感、形象和意向。这些东西和词的音调性质一起,为诗人提供了作为诗人艺术的那种生动的语言描绘所必需的‘色彩’。就像画家运用他对颜料在各种调配中的性质所具有的领悟性眼光来加工颜料一样,文学艺术家也运用对这些要素以及语音形式的鉴赏力来处理他的语言材料。”媒介是和材料分不开的,但它们又不能等同。文学的媒介是运用材料而构成的动态性的整体结构。
语言(词语)作为诗的艺术媒介,其与感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或许有人要问:这二者之间难道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本文认为,在创作的发生阶段,感兴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感兴是触物而起,并非事先立意,这才是真正的审美发生。主“感兴”论者都认为真正的杰作佳什,是“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的产物,而且,“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我们所理解的审美感兴,并非一般性的触物以兴情,而是诗人(作家)以其独特的艺术媒介来感受世界,在头脑中已经凭借词语、声律等媒介因素构拟出意象化的整体。刘勰论“神思”时所说的“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以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就颇为值得我们深入理解,因为它深刻揭示了诗的“神思”与媒介的关系。《文心雕龙》中《比兴》篇的赞语尤为值得我们注意:“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之涣。”触物”即是指诗人感兴“触物以起情”的性质。“圆览”,一般的解释是“周密地观察”或“全面地观察”。笔者认为,“圆览”可以理解为浑融圆整的观览境界。感兴激发了诗人的主体意志,使本来如隔胡越的物象,在作品中合成为一个近如肝胆的意境整体。关于“拟容取心”有很多阐释,其中王元化先生的阐述较有深度:“对于《赞》中提出的‘拟容取心’,我在释义中作了这样的解释:‘容’指的是客体之容,刘勰有时又把它叫作‘名’或‘象’;实际上,这也是针对艺术形象所提供的现实表象这一方面。‘心’指的是客体之心,刘勰有时又把它叫作‘理’或叫作‘类’;实际上,这也就是针对艺术形象所提供的现实意义这一方面。‘拟容取心’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塑造艺术形象不仅要摹拟现实的表象,而且还要摄取现实的意义,通过现实表象的描绘,以达到现实意义的揭示。”笔者对元化先生充满了崇敬之情,但对“拟容取心”却有自己的理解,认为这个“心”并非客体之“心”或者“现实意义”,而是诗人的“触物圆览”之心,也即主体之心,因为“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正是强调了主体心灵的作用,即为《物色》篇中所说的“与心徘徊”。“断辞必敢”指出其语言作为感兴媒介的重要功用。宋代诗论家严羽反感于宋诗中那种堆砌故实、缺少情兴的做法,而最为推崇的便是盛唐诗人那种“兴趣”,其云:“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一种浑成圆融的审美境界,它的发生契机是诗人的审美感兴。诗人是凭借着长期艺术训练而获得的媒介感与外界事物相触遇,从而在头脑中产生了具有内在视像性质的画面,而这恰恰是已经用词语和韵律等媒介进行内在的构形了。鲍桑葵指出:“诗歌和其他艺术一样,也有一个物质的或者至少一个感觉的媒介,而这个媒介就是声音。可是这是有意义的声音,它把通过一个直接图案的形式表现的那些因素,和通过语言的意义来再现的那些因素,在它里面密不可分地联合起来,完全就像雕刻和绘画同时并在同一想象境界里处理形式图案和有意义形状一样。”鲍桑葵在这里强调的是,诗歌创作的媒介虽然不同于绘画、雕刻等物质性很强的东西,而是有意义的声音,但是这种媒介却是可以描绘内在的形式图案的,也即给人以画面感的。他认为这二者是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哈利泽夫强调了文学媒介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的不同之处,然而,他却认为文学媒介可以更好地表现内在的视觉形象,他说:“有别于绘画、雕塑、舞台和屏幕的画面,语言画面(词语描绘)是非物质性的。词语的艺术形象缺乏直观性,却能够生动如画地描绘虚构的现实,而诉诸于读者的视觉。文学作品的这一方面被称之为词语的塑像。较之于直接地、瞬间地转化为视觉接受,借助于词语的描绘,更加符合对所见之物加以回忆的规律。”哈利泽夫对于文学媒介的特点的阐述是颇为中肯的,对于前述鲍桑葵的观点是一个更为明确的补充,尤其是有力地说明了媒介在文学的内在运思中的不可缺少性。
作为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的诗人,对于艺术媒介的熟练运用和媒介感的内化,会激发审美感兴的强度,从而产生类似于“自我实现”的感觉,并促使天才杰作的诞生!诗人对于自己运用媒介的能力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兴奋感,杜甫所说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最为典型的。此时诗人进入一种高度的创造性状态,正如清人张实居所描述的那样:“古之名篇,如出水芙蓉,天然艳丽,不假雕饰,皆偶然得之,犹书家所谓偶然欲书者也。当其触物兴怀,情来神会,机括跃如,如兔起鹘落,稍纵则逝矣。有先一刻后一刻之妙,况他人乎?”这应该是诗人在灵感爆发时极为亢奋的状态,其实是诗人因其秉赋了炉火纯青的媒介感的缘故。
审美感兴与艺术媒介表面上是看似没什么联系的范畴,其实有内在的因缘,将这种内在的关系予以研究和揭示,对于理解艺术创作是可以向前大大推进一步的。感兴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话语,它揭示的是艺术创作发生的奥秘,但我们一般理解的感兴,就是与外物触而兴发的诗人情感,本文则将媒介的内化与感兴结合起来,从而说明了感兴是已经凭借媒介的功能而形成了作品的构形。在这个阶段上,卡西尔的论述是相当深刻的:“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但是这些运动的形式、韵律、节奏是不能与任何单一情感状态同日而语的。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的或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是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之间的持续摆动过程。使我们的情感富有审美形式,也就是把它们变为自由而积极的状态。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情感本身的力量已经成为一种构成力量(formative power)。”卡西尔揭示的是媒介的构形功能。而认识到感兴发生阶段所凭借的媒介功能,则使媒介的研究向内深化了许多。
③张晶:《艺术媒介论》,《文艺研究》2011年第12期。
④[意]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朱光潜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页。
⑤胡寅:《斐然集》卷一八《致李叔易书》,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6页。
⑥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全晋文》卷六一,中华书局影印本。
⑦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地卷》引,(台北)金枫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⑧杨万里:《答建康府大军库军门徐达书》,《诚斋集》卷六七,《四部丛刊》本。
⑨谢榛:《四溟诗话》卷二,载《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