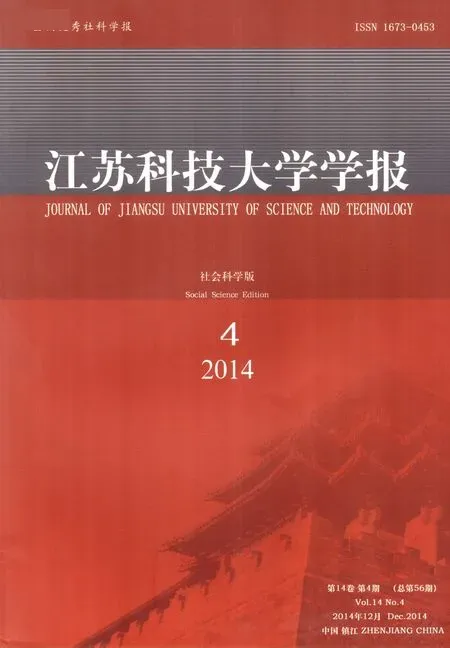以花为伴 与花共舞
——华兹华斯诗歌中花意象解读
孙晓明, 姜礼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以花为伴与花共舞
——华兹华斯诗歌中花意象解读
孙晓明, 姜礼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华兹华斯被称为“自然的歌手”,其自然诗中千姿百态的花意象尤为引人注目。华氏笔下的花意象具有主体性和神性两个特质,有抚慰心灵、愉悦心情、启迪智慧的功能。以花为伴、与花共舞的华兹华斯尽显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敬畏,充分显示出“一花一天堂”的意境。
华兹华斯; 花意象; 自然观
华兹华斯一生创作了大量歌咏自然的诗,藉此表达对自然的热爱与向往。自然诗中千姿百态的花意象是一种独特的现象,令人印象深刻,却并未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浓厚兴趣。罗俊容《论华兹华斯诗歌中的植物意象》一文是国内唯一一篇专门探讨华兹华斯诗歌中植物意象的文章。他认为华兹华斯诗歌中植物意象有三层象征意义,即“人类可居的理想家园”、“生命旅程的伴侣”以及“神性的直接体现”[1]。国外学者对华兹华斯诗歌中花意象的评论只是零星散落在对其具体诗作的分析中。因此,国内外学者都未对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花意象进行系统性研究。
华兹华斯笔下的花千姿百态,不仅具有人性的特质,而且有神性的光辉。它们带给人们的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心灵的慰藉、智慧的启迪。对华兹华斯笔下的花意象进行系统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和生态观。
一、灵性之花——敬畏之神
在诗歌中,华兹华斯往往借用人格化的处理,使花儿成为可以倾心交谈的主体性存在。《致雏菊》描述了诗人与雏菊的交谈,诗的开篇就是“广阔的世界上事物万千/但这儿没什么可做、可看。/可爱的雏菊啊,你的优点/使得我又同你交谈”[2]204。诗人眼中的雏菊不再是供人们观赏的客体,而是可以沟通交流的主体。在《永生的信息》中,华兹华斯倾听了三色堇的困惑与疑问,“我脚下的一株三色堇/也在把旧话重提:/到哪儿去了,那些幻异的光影?/如今在哪儿,往日的荣光与梦境”[3]261。华兹华斯与花的交流是双向的。他既与雏菊交谈,又聆听三色堇的细语。他自己也曾说过,“我与所看到的一切交流,它们不是远离我的无形本质,而是紧密相连”[4]。在他看来,人与自然万物血脉相连,可以进行心灵交流。
在华兹华斯的笔端,花儿都有灵性,有喜怒哀乐,有人一样的情感体验。在《瀑布与野蔷薇》一诗中,野蔷薇对瀑布说道,“叶子啊,如今已零落满地,/那时却引得红雀来栖身, /为我们唱出婉转的清音;/你那时没什么声息”[3]83。在这里,野蔷薇指责瀑布忘恩负义的行为,它享受过美丽的自己带来的“清音”,如今却嫌弃叶子尽落的自己阻挡了道路。这里的花不再是默默无言的被动客体,而是积极言说感受的主体。在《让雄心勃勃的诗人去攻占人心》中,华兹华斯写道:“烈风前瑟缩的/三月花朵,乐意在轻柔的南风中/吐出最珍奇的芬芳,因为这风儿/温和的气息轻呵着它们的心胸”[2]357。“乐意”一词形象地描绘出了花的感受与意愿,在三月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花香是出于对风儿的喜爱,出于对风儿“温和气息”的喜爱。诗人眼中的自然景象不再是客观的事实存在,而是花自我选择的结果。
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花是有形的存在,人们可以感知,可以与之交流;同时又是无形的存在,是上帝精神的体现。深受泛神论思想影响,华兹华斯相信上帝存在于自然万物中,并没有另外的超自然的主宰或精神力量。艾玛·梅森(Emma Mason)曾说过:“华兹华斯从来不是卫理公会教徒,只是从对人与上帝关系感兴趣到转变成泛神论者。”[5]在华兹华斯看来,上帝不再居于天国,而是居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王佐良先生在《英国文学论文集》中评论华兹华斯诗歌时也曾说过:“自然界最平凡最卑微之物都有灵魂,而且它们是同整个宇宙的大灵魂合为一体的。”[6]正因为如此,华兹华斯诗作中的花散发着神性的光辉。最能诠释华兹华斯诗歌中花意象具有神性特质的诗作当属《岩石上的樱草》。华兹华斯眼中的樱草不仅仅是植物性的存在,是“自然之链”的一个环节,更是神性的存在,是与神的世界(highest heaven)紧密相连:“它是自然之链的永恒环节,是从九天之外下凡。”[2]334紧接着诗人写道:“上帝把这一切筹划:寂寞的草就这样开着花,一年葬一次也不怕。”[2]335樱草的凋零与枯萎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遵从上帝的旨意,是上帝精神的体现。
华兹华斯在他的诗歌中赋予花以灵性与神性,是对文学视花意象为手段或工具习惯性思维的一次重要反拨。西方传统观念认为人是“万物的灵长”,并且这样的观念还在不断得到强化:《圣经》声称上帝创造了人并为人创造了世间万物;文艺复兴更是把人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强调科技发展要为人谋取福利,教育要注重人性,一切以人为中心;启蒙运动进一步提出人是有理性的,人能够理解世界甚至掌控世界。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影响下,文学作品中的花意象只是用来表达情感或营造氛围的手段或工具。情感或氛围是第一位的,而花意象本身则无足轻重。反观华兹华斯诗作中的花意象,人们看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信念。在华兹华斯的眼中,花作为有灵性主体是可以推心置腹交谈的对象。由此,诗人与花建立起了一种主体间的平等关系。吉尔伯特(K.E.Gilbert)在《美学史》(下卷)中写道:“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是那样的互相依存,以致我们难以在他的哲学中确定自然与人相比何者居首。”[7]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不是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华兹华斯由此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禁锢。而赋予花以神性,把普通自然景象提升到上帝精神的体现,则体现了华兹华斯对自然的崇拜之情。
二、烂漫之花——快乐之源
华兹华斯诗篇中那些烂漫绽放的花儿,能够给予人以心灵的慰藉、快乐的时光。在《水仙》中,华兹华斯描绘了成片的水仙花随风摇曳的动人景象:“连绵密布,似繁星万点/在银河上下闪烁明灭,/这一片水仙,沿着湖湾/排成延续无尽的行列;/一眼瞥见万朵千株,/摇颤着花冠,轻盈飘舞。”[3]107置身如此美景之中,华兹华斯不禁咏叹道,“有了这样愉快的伴侣”,“怎能不心旷神怡”[3]107。水仙成了有生命的主体、诗人的伴侣,给诗人带来了一段快乐时光。诗人完全陶醉于眼前的美景之中,正如诗中所说:“我凝望多时,却未曾想到/这美景给了我怎样的珍宝。”[3]107在这里,诗人心无杂念,全身心融入自然,享受自然之美。“水仙呵,便在心目中闪烁——那是我孤寂时分的乐园”[3]108,水仙已经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中,更存在于诗人心中,抚慰诗人那颗孤寂落寞的心。在感悟自然中,华兹华斯获得了心灵上的“欢情洋溢”。换言之,水仙在现实世界和回忆这两个层面都给诗人带来了慰藉与欢愉。在《致雏菊》中,华兹华斯也同样表达了花能够带给人快乐的观点:“请你(雏菊)就像你惯常那样地/让我的心重新充满欢喜。”[2]206华兹华斯认为,雏菊可以带给人以快乐,并请求它给予自己内心以欢愉。
诗人一边深情地歌颂花之美,感受花给人内心带来的欢愉,一边又流露出对人们破坏自然美景的不满与批判。《采硬果》描写了采硬果的经历,在诗的开篇诗人就表达了置身于花丛中以花为伴是何等令人欢欣鼓舞:“我也坐在树下/花丛里,同一朵朵花玩耍嬉戏;/厌倦于久久等待的人如有幸/突然地获得超过一切想象的/幸福时,他们也会有这种心情。”[2]91在华兹华斯看来,与花为伴给人的愉悦甚至可与经历了漫长等待后获得所希冀的幸福相媲美。但紧接着,他笔峰一转:“能活五个季度的紫罗兰会再/开花和谢去,但不为人眼所见。”[2]91年复一年,娇巧迷人的紫罗兰盛开又凋零,人们竟不曾注意。人们的目光只为代表利益的硬果而停留,而不屑于低头瞥一眼象征自然之美的紫罗兰,这何尝不是又一出悲剧。引人注目的是,这首诗多处描写了采硬果给自然带来的破坏,“没有枯叶的断枝挂在那儿,/显示粗野的蹂躏”,“随着断裂声/和无情糟蹋,罩在榛树荫里的/幽僻处所和满是苔藓的树丛/给丑化、玷污了”[2]91-92。毋庸置疑,华兹华斯对于人们为采硬果满足一己私欲而破坏自然的行为是持批评态度的。他在诗的最后呼吁:“所以亲爱的姑娘,怀着温柔的/心在这树荫下走吧;/用温柔的手轻抚吧——因为林中有个精灵。”[2]92华兹华斯认为自然给予人的是美的享受、丰硕的果实,人也应当对自然温柔以待。
华兹华斯投身自然的怀抱,在花海中寻求精神慰藉,与其对现实的失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兹华斯曾是法国大革命忠实的拥护者,并积极投身于这场革命,“认为英国理想形象是自由与民主,而法国大革命正是这一形象的延伸”[8]。但是革命带来的并不是起初所倡导的“平等、自由、博爱”,而是雅各宾派的独裁专政。吉伦特派中一些人被推上断头台,而这些人曾为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付出过心血,尤其是其中一些人还是华兹华斯曾经的战友和朋友。在政治理想破灭与丧失好友的双重打击下,华兹华斯的政治热情骤然退却,归隐之心悄然产生。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工厂数量急剧增加。在工厂里,人们机械地重复着相同动作,异化为机器的一个部分、一个零件。乡村自由自在的生活从此成为历史,当下只有枯燥乏味而又永无止境的工作。华兹华斯在《序曲》第一巻《引言—幼年与学童时代》中写道:“逃离那巨大的城市,不再是怅惘的游子/长日消磨——如今自由了,自由得/像鸟儿一样随意选择栖身之处。”[9]在华兹华斯眼中,城市就像个囚笼,束缚自由,压抑个性,令人怅惘。与此同时,蒸汽机的广泛运用导致了严重的空气污染,矿物资源的开采更是直接破坏了自然景观。华兹华斯并不愿意享受工业革命的成果,由于看到工业革命存在的问题,一直用批判的目光审视工业革命,正如迈尔斯(Frederic Myers)所说,“他是工业革命的观察者和批判者”[10]。湖区作为一方未曾受到污染的净土,草木繁茂,花儿烂漫,自然景观尚未受到人类的破坏。于是华兹华斯义无反顾地隐居到湖区,希望在自然中得到解脱,正如贝特(Jonathan Bate)在《大地之歌》中借用席勒的话所表达的那样:“在现代文明的压力下,我们都渴望能尽快的回归自然,去聆听遥远的土地的甜蜜的声音。”[11]诗人也的确在回归自然、融入自然和感悟自然中获得心灵的慰藉。
三、百态之花——智慧之泉
在华兹华斯诗作中,烂漫之花带给人的是视觉的盛宴与内心的欢愉,而百态之花带给人的则是智慧的启迪与深邃的感悟。“一花一世界”,在这些花的世界里,华兹华斯看到了花的美好品质、与人相似命运或相反的境遇。诗人深受启迪,从中获得了书本所不能给予的智慧:“对于我,最平淡的野花也能启发最深沉的思绪——眼泪所不能表达。”[3]273在华兹华斯诗作中,人们既能寻觅到泛神论思想的踪迹,也可以看到一个基督教徒的信仰。罗益民认为,华兹华斯“既是一个自然神论者, 但他更是一个基督教徒”[12]。对于信奉《圣经》的基督徒来说,智慧源于神的赐予。同时,泛神论者认为上帝就存在于宇宙万物中。深受这两种信仰的影响,华兹华斯相信自然能够赐予人们以智慧。
华兹华斯认为,比起书本,自然能给予人更多、更丰富的知识,而“啃书本”带来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烦恼”[3]241,因此他提出让“自然做你的师长”[3]241。《可怜的罗宾》描绘了罗宾——一种野生小天竺葵的俗名,在百花争艳的时候却只有“红红的梗子”,但是“尽管被忽视,却在温暖的山谷里/和赤裸的小山上努力尽着职责”[2]356。罗宾在被忽视的情况下依然努力绽放美丽,这正是华兹华斯所欣赏的品格。人何尝不应如此,尽己之责,不为赢得他人的目光,只为求得内心的安宁。在《致雏菊》中,华兹华斯对雏菊的优秀品质赞叹有加——谦虚自信、待人友好、性情温和,而且能够在艰难困苦中心平气和地坚持完成“使徒般的任务”。相比之下,人显得脆弱而犹疑,“一旦不顺当,就不太肯依靠他的回想—/或依靠他的理智”[2]202。于是华兹华斯尊雏菊为老师,虚心向其请教:“你(雏菊)可愿教他,教他怎样/在刮风时候找藏身地方,/在困难时候不丧失希望”[2]202。雏菊教给人们如何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在困难中仍心怀希望坚定地走下去。书本带给人的是枯燥的理论,而花带给人的是生活的智慧。
华兹华斯好像是自然之子,能够从寻常的花中思考感悟到生命的真谛。花开花落往往能引发诗人诸多感慨,这与中国古人的悲秋颇有相似之处。《小白屈菜》一诗描写了一种野花,在遇到“阴雨寒天”、下冰雹的日子及狂风肆虐的时候,就会闭拢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但是最近一次诗人看到它却“一任那风风雨雨欺凌侵害”,不是“出于自愿,出于勇敢”,而是“因为老了,只能听命运的安排”[3]253。小白屈菜的年老衰败与其中的无可奈何,使诗人对老年顿生感慨。每个年龄段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年轻的活力,年老的睿智。但诗人显然还是更偏爱年轻,“人呵,青春岁月里辉煌阔绰,/老了,只配讨一点余沥残羹”[3]254。此外,诗人在小白屈菜对命运的无力抗争中也看到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与不可违背性。“它已经疲惫不堪,救不了自己;/阳光露水也难使其生机重旺”[3]253,没有什么能够拯救行走在衰亡之路上的小白屈菜,这是自然的意志使然。人也不例外,衰老是一个无可逆转的过程。生命只有一次,年轻的岁月逝去便不再回来,珍惜当下也许是人们唯一的出路。
寻常的花儿不仅蕴含了生命的真谛,也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生活境界。华兹华斯对小白屈菜情有独钟,赞赏有加,甚至在《白屈菜》中直言不讳地宣称“为你唱赞歌我很应该,/我该唱我心中的所爱”[13]81。而诗人如此青睐小白屈菜,原因就在于小白屈菜很好地诠释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不管是身在荒原、树林,还是在巷道,它“都能够随遇而安,/不管炎凉而到处安然;/卑下之所,低微之位,/欣然自得,不以为愧”[13]80。面对荒凉的生存环境与无足轻重的地位,小白屈菜没有怨天尤人,反而泰然处之、怡然自得。诗人透过小白屈菜的豁达看到了一种生活的境界,即能以一颗平常心看待惨淡的际遇、坎坷的经历。无独有偶,明朝洪应明也认为,人生最高境界就是能够做到“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诗人祝福小白屈菜,即使身在海角天涯、万里之隔,也要以每日五十次的频率祝福它。这深切祝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华兹华斯对这种生活境界的珍视、渴求与学习的心理。
华兹华斯所处的时代,在物质上工业大发展,在精神上理性至上。技术迅猛发展进一步导致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盛行,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污染破坏;而对理性的过分强调则导致了人们情感的枯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受到卢梭“回归自然”思想的影响,华兹华斯把目光转向自然,转向花的世界。他笔下的花具有主体性,同时又笼罩着神性的光辉,能给人带来慰藉与快乐,也能引发感悟、启迪智慧。他诗作中的花意象召唤着人们被压抑的情感、激发起他们回归自然的欲望,正如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所说,“华兹华斯真正的出发点,是认为城市生活及其喧嚣已使人忘却自然”[14]。
[1] 罗俊容.论华兹华斯诗歌中的植物意象[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6):74-77.
[2] 威廉·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M].黄杲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3] 威廉·华兹华斯.华兹华斯诗选[M].杨德豫,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4] WORDSWORTH W.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William Wordsworth, 1806-1815[M].New York: Cosimo, 2008:52.
[5] MASON E.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William Wordsworth[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42.
[6] 王佐良.英国文学论文集[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79.
[7] 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美学史[M].夏乾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522.
[8] HARTMAN G.The Unremarkable Wordsworth[M].Twin citi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5.
[9] 威廉·华兹华斯.序曲或一位诗人的心灵成长[M].丁宏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1.
[10] MYERS H.Wordsworth[M].Charleston S.C.: Nabu Press,1901:6.
[11] BATE J.The song of the earth[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24.
[12] 罗益民.心灵湖畔的伊甸园——作为自然神论者的基督教徒华兹华斯[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 2): 77-80.
[13] 威廉·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M].谢耀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1.
[14] 奥尔格·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英国的自然主义[M].徐式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2.
(责任编辑: 吴言)
启事
本刊编委会四年一届的换届即将到来,诚邀海内外关注我刊发展、并有意愿为我刊赐稿、约稿、审稿的专家成为我刊特约编委。
TheFlowerImagesinWordsworth′sPoems
SUN Xiaoming, JIANG Lif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Jiangsu 211106, China)
In Wordsworth′s nature poetry, flower images are rich and noticeable, which not only poss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ivity and divinity, but also have an impact on soothing soul, lifting mood and inspiring wisdom.Wordsworth, immersed in the world of flowers, sees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and shows his love and reverence for nature.
William Wordsworth; flower image; view of nature
2014-06-05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2013SJD75003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教改课题“西方文学‘研究型’教学的新探索”
孙晓明(1990—),女,江苏连云港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I106.4
: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