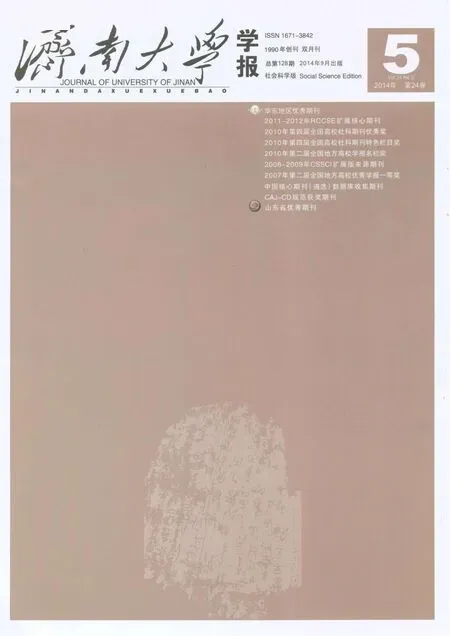秧歌与政治动员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根据地为中心
崔一楠,李群山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秧歌与政治动员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根据地为中心
崔一楠,李群山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对华北根据地的秧歌进行了改造,并利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积极推广,收到了较好的动员效果。改造后的秧歌不再是单纯的民间娱乐,而是农民接受政治教育、理解革命话语的渠道,是他们表达政治意愿的途径。这种新变化赋予了民间艺术特殊的时代使命,有利地促进了中共革命事业的发展。
秧歌;华北根据地;政治动员
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动员民众接受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政治工作的关键。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1](P513)成功的政治动员需要借助一切社会资源进行宣传,对于广大农民而言,秧歌这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中共如能很好地改造和利用,势必会发挥特殊的动员效果。本文尝试以秧歌为视角,透视中共如何利用民间艺术来传递自己的政治理念,农民又做出了何种回应。对于这一互动效应的考察,或许有利于我们从文化的角度理解中共革命的成功之道,体味战争年代下民俗艺术与政治动员的深切关联。
一、秧歌的功能转换
秧歌在中国北方乡村社会源远流长,原本是农夫在插秧时唱出的一种“自由腔调”,后来把其它通俗游艺的角色、故事和表演方式吸收过来,形成了既载歌载舞又写情叙事的表演形式。因此,秧歌是一个综合性的名称,既包括秧歌舞也包括秧歌剧。尽管与传统戏剧相比,秧歌的戏棚、舞台要小得多,行头和乐器也比较简单,但它的受欢迎程度却毫不逊色。作家贺雷曾描写过秧歌在河北乡村演出时的情形:“锣鼓一响,四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时间把一座戏台挤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的聚集起来,在乡下就有种魔力……秧歌对于农民比都市摩登小姐、公子哥儿们对电影还起劲。”[2](P18)时任晋察冀抗联宣传部部长的冯宿海也曾有过类似的评价:“秧歌在今天的乡村里,算是盛极一时了。真是随时皆舞,随处都舞;女的要舞,男的也要舞。”[3]秧歌呈现出了影响范围极广、民众参与度极高的特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秧歌的上述特点受到中共的重视,逐渐承载起政治动员的使命,成为宣传抗战的重要形式。1939年2月,《新华日报(华北版)》发出号召,要求文艺工作者抓住过旧历新年时农民“比平日略微不同”的心理状态,利用好秧歌的“聚众”功能,集中宣传党的政策和纲领。[4]在此之后,《抗敌报》《太岳日报》《大众日报》等主要报纸也有过类似的提法。到1940年时,华北各根据地利用秧歌为政治服务的呼声日益高涨,它被视为“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重要工具”,成为构建意识形态的主阵地之一。在此种精神的指引下,秧歌与政治的结合更加紧密,1942年1月,《晋察冀日报》刊登社论指出,类似于秧歌这样的文化娱乐活动能够坚定广大农民对革命的信心,“激发民族意识,提高对敌战斗情绪”。为此要求各级政府务必让专业人员深入乡村,组织农村秧歌队,充分发挥其政治动员功能。[5]为了使秧歌更好地反映战争形势,文艺工作者还想方设法把政治任务编排进秧歌中。比如1943年,太岳区的固隆村剧团在动员农民参军时就编演《参军去》,春耕时就演《互助好》,反对顽军进攻时即演《血染口子里》,“他们能做到如与中心工作不合时,就是他们最好的戏也不演,而另编适于中心工作的戏”[6](P205)。通过各边区政府有意识的组织和引导,秧歌在构建中共意识形态中的作用日益明显,逐渐成为行之有效的政治宣传手段和群众动员途径。
解放战争时期,秧歌在政治动员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其体现政治任务、服务政治任务的宣传随处可见。例如在太行区偏城县区村,该村党支部积极提倡利用秧歌来表扬八年抗战的英雄事迹、群众翻身、互助发家、拥军优抗等故事。[7]而太岳区党委则更强调秧歌与当时的华北形势相结合,希望“造成广大群众活动”,不仅要显示解放区内翻身后的新气象,还能“揭露蒋阎之卖国内战、残害人民罪行,启发人民对蒋阎之仇恨心,加强斗志”[8]。到了1948年,华北各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宣传《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要求,将相关的法令、文件编入秧歌,力求使广大农民都能了解《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内容,“作为今年复查土地改革平分土地的思想武器”[9]。由于现实的需要,加之多年斗争经验的积累,中共已经系统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融入秧歌之中,通过这样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达到教育民众、发动民众的目的,实现了秧歌由娱乐活动向政治动员工具的转变。
二、革命元素的不断植入
虽然中共极为重视秧歌的政治宣传、社会动员功能,但是传统秧歌的内容却与其政治理念相去甚远。一方面,传统秧歌是娱神的仪式,逢年过节,乡村民众会闹着秧歌去庙里“敬神”,具有浓厚的祭祀色彩;另一方面,它又是娱人的民间艺术,内容不外乎“讽刺官僚士绅”和“男女调情”。[10](P78)可见,旧式的秧歌根本无法满足中共政治宣传的需要,其必须对秧歌进行改造,增加“团结抗战”“参军报国”“反抗压迫”“生产斗争”等内容。
中共对传统秧歌的改造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起初是从利用旧形式开始的,文艺工作者剔除了秧歌中的“不健康”成分,在基本保留原有音乐、舞法、道具的前提下,增加了一些反映每年政治任务的内容,这种改造方式被称为“旧瓶装新酒”。之所以这样,为的是通俗易懂,便于接受。乡村民众长期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头脑中已经形成了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倾向性认识,他们理解和接受一种新观点往往是因为这个观点符合固有的价值观及审美倾向,或者对原有观念做了有限的修正,他们很难能一下子接受一种全新的观念。不过,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对“旧瓶装新酒”提出了批评,认为“我们今天的新秧歌也曾经配进去几个不连续的、独立的抗战歌子或小调,然而由于旧形式的僵化、音乐的不协调、舞法的过于简单,使这些内容和动作完全不一致,彼此无关系,成了两回事”[3]。但这种言论一出,便遭到了强烈的批评,更多的中共文艺工作者强调:“秧歌本质上到底不同了,它没有礼义廉耻、男女大防的臭东西……人物不是忠臣孝子、烈妇义仆,而是抗日的战士以及敌人汉奸等等”,“那些情节和表演方式是幼稚而简陋的,但它是今天边区人民思想意义的反映,它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要受群众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准所限制。”[11]从中不难看出,中共对秧歌的改造不是让秧歌如何具有观赏性,而是要塑造出符合其理念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改造后的新秧歌能为民众接受,并自觉成为他们的娱乐方式,即使新秧歌“幼稚而简陋”,那也是成功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的经验迅速扩展到华北各根据地,在“为工农大众服务”精神的号召下,中共文艺工作者深入华北乡村,编排出许多新秧歌。这时秧歌的形式和内容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衍生出“新瓶装新酒”的改造方式,即注重内容贴近群众生活的同时,对道具、舞法、音乐等也进行改造。如将具有引领功能的“伞头”改为镰刀斧头,“五色旗”改为红旗,“星位牌”改为标语牌或革命领袖的画像。秧歌的舞法“不单是轻快,而且刚健,节奏鲜明,表现人物特征”。此外,“新秧歌音乐,节奏强烈、活泼高亢,节拍简单齐一,满足了集团性群舞的需要”[12]。上述的变化构成了根据地一种新的文化语境,这种语境使中共逐渐成为民众拥戴、追随的核心对象,新秧歌的艺术形式反映了华北根据地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表达了农民去旧迎新的理想,建构起新的文化秩序。
抗战后期,华北秧歌又有了新的发展,农民成为改造主体,许多村庄建立了自己的秧歌队、剧团,他们除了演出延安传来的《兄妹开荒》《动员起来》《拥军花鼓》《小二黑结婚》等剧目外,更多的还自编自演密切配合斗争实际的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胶东地区的高街村。该村农民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协助下,以真实故事和个人经历为原型,创作了大型秧歌剧《穷人乐》。该剧抛弃了旧的脸谱、着装和道具,代之以贴近现实的装扮;舞台的主角不再是专业演员,换成了普通群众,因此广大农民更容易受到触动。《穷人乐》公演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村纷纷演出反映自己生活的新戏。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专门下发文件,给予《穷人乐》充分肯定,指出“这是我们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成就”,“实为我们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新方向和新方法”[13]。
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的新秧歌趋于成熟,其不再是“贴近生活”,而是“再现生活”。每次演出时,参演人员力求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与现实高度一致,演出的场所也很具随意性,大多不用专门舞台,只需广场或空地即可。此外,农民已经自觉地运用中共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去评判秧歌,如1947年涉县神头村上演秧歌剧,饰演“地主”的演员一出场,群众就大喊:“打回去,打回去!”后来“地主”表现得很和善,村民非要找编剧理论,要求其端正立场。类似的事例还发生在响堂铺,演到逃荒时,村民提出解放区没有这样的事,还质问剧团究竟和谁是一伙的。砦村演秧歌时,唱词中有几处说“八路军人少力量小”,村民们不让再唱下去,“要问一问为什么这样唱,是什么用意”[14]。
中共对秧歌的推广是与改造相辅相成的,主要依托各种节庆进行传播。特别是每逢新年之际,华北根据地都要召开会议,组织专门人员对秧歌演出的主题、方式做出详细规定,有些地区还开辟“宣传周”,巡演重点剧目。如1942年春节,太行根据地宣联会决定从专署至各县、区、村,普遍成立文娱动员委员会,指导各地秧歌的排练和公演。同年,晋绥抗联还特别要求儿童团发挥应有作用,组织少年儿童也参与秧歌演出。为了尽可能的扩大秧歌的政治动员效果,各级政府还大胆破除旧有的条框制约,寻求秧歌推广方式上的新突破。1946年冬,晋察冀边区下发文件,倡导大开门主义,要求各地的秧歌实现“个人创作”向“集体创作”的转变,真正将广大村民纳入其中,使秧歌成为“老百姓自己的东西”[15]。通过中共各地机关、文艺工作者及群众团体的不断努力,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胜利,改造后的秧歌在乡村中随处可见,村与村之间有的开展竞赛,评选模范团体;有的举行经验推广会,交流心得,形式丰富多样。华北根据地内掀起了一拨又一拨的热潮,形成了“人人可演戏,处处是舞台”[16](P67)的新文艺运动。
三、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融合
中共对戏剧的改造并不是简单的与旧有传统决裂,而是渗透和移植、改造和置换,实现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融合。这样的意图在左权县襄垣农村剧团创作的《李来成家庭》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该秧歌剧描写了李来成为家长的八口之家在县长耐心的教育帮助下,由一个矛盾重重的落后家庭变成一个团结和睦、积极生产的边区模范之家。李家原是奉行家长制的旧家庭,事无巨细都要由李来成一人决定。经过改造后的新家庭有了会议制度,家长决定事务之前必须征求全家人同意,这极大地促进了全家成员的团结。除此之外,剧中还倡导家庭生产活动实行精细分工,男女有别各尽其才,劳动力得到合理发挥,全家收人大增。该剧以形象的方式宣传了“抗日根据地里的家庭改造是把新民主主义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把一家一户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活动”[17](P269)的政治理念,它教育农民要学习李来成的“新式家庭”,从人力到物力,从生产到消费,都有效地组织起来,这样才能使传统的大家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李来成家庭》一经演出便受到了广泛好评,各个剧团争相上演,《解放日报》更是称其是“农民进步家庭中优秀的典型”。
从本质上看,《李来成家庭》并非号召农民对旧式家庭进行彻底革命,传统伦理格局在“模范家庭”中得到保留。剧中男性家长仍占据主导地位,婆婆还是副家长,依旧沿袭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所不同的是通过家庭会议,其他成员能对家长进行一定程度的制约;家庭内部财产分配更加合理;利用奖励来刺激每个家庭成员生产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极大地缓解了家庭矛盾,而家庭矛盾的缓解又反过来促进了家庭经济情况的改善,这在当时不失为既能发展经济又不引起过度震荡的好方式。此外,该剧中对“县长”的刻画也耐人寻味,他刚到李家时,李来成的女儿、三个儿子和儿媳们吵吵闹闹,相互埋怨着对方。而“县长”不仅要抓抗日、生产这样的大事,还得处理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他既是政治觉悟高、工作得力的地方官员,还是走家串户、跟农民打成一片的忠厚长者。在根据地创作的新戏剧中,这样的形象并不是孤立的,我们在很多剧本中都可以看到。对群众生活的体贴关心,不仅确立了政党的合法性,还把政治延伸到私人生活领域。在当时的华北乡村社会,并不存在公共与私人之间绝对的分治,两者始终处在一种互动的关系之中,而将公、私两个领域积极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中共的乡村干部。在戏里,他们既不是过去的旧官僚,但又多少带有传统社会所向往的“循吏”的身影。
除了家庭、生产等内容,改造二流子也是根据地戏剧经常涉及的主题。所谓二流子是指没有固定职业,把卖鸦片、盗窃、赌博等行为作为谋生手段的人。这些人破坏了社会风气,给根据地财政带来沉重负担,甚至有可能沦为汉奸、特务。[18](P94)然而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数量众多的二流子又是潜在的劳动力,他们可能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人力资源,而且二流子中的大多数属于农村穷苦农民,因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而逐渐堕落,他们的革命性可以通过动员得以释放。因此,中共对改造二流子十分重视,积极利用戏剧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其重新树立起劳动光荣的观念,诸如《钟万才起家》《刘二起家》《二流子转变》等剧目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些新戏剧多由农村剧团根据真人真事创作而成,并鼓励二流子自己演自己,一个又一个洗心革面的“转变典型”展现在舞台上。很多二流子都受到了触动,纷纷表示自己也要“学好”,剧团团员们都高兴的说:“演新戏就是办事啊!”[6](P119)新戏剧形成了一种热烈的氛围,使二流子们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于政治的规训,也来源于民间传统伦理。在中国乡村,劳动被视为一种美德,个人通过努力获得相应的生活资料,不仅受人尊重,而且从根本上维持了费孝通所谓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改造二流子固然是出于巩固根据地的需要,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是中共对民间伦理的继承和发扬,是让思想落后农民“学好”的一种方式。
四、民众角色的重新定位
经过一番改造和推广,华北根据地的秧歌逐渐与政治宣教契合,传统里娱人、娱神的秧歌转化为对思想和行为的规训。娱乐与规训原本具有完全不同的特质,通常是无法相容的,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新秧歌的锣鼓喧天中,娱乐与规训却和谐相融,规训成了娱乐的性质和职能,娱乐成了规训的载体和工具。更为重要的是,民众的角色也随着两者的相融而发生转变。
长期以来,乡村民众在秧歌面前,多是“看客”的身份,尽管他们会簇拥着演出队伍,从村头一直跟到村尾,表演时报以掌声、喝彩、欢笑,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是秧歌创作、表演的主体。至迟到1944年时,华北地区的新秧歌已有意识地大量吸收民众参与,他们不再是秧歌表演的围观者,更是文娱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例如1946年元宵节时,山西左权县五里墩村准备排练秧歌《翻身乐》,该村有146户,参加演出的竟然有122户,接近全村总户数的84%,其中五六十岁的老人有12个,中青年为208个,儿童53个,另有十余家合演。①参见《翻身乐在左权五里墩广场的演出》,山西省档案馆,A166-01-37-10。1947年,在平山县回舍镇的秧歌大会上,翻身后的农民从四面八方涌向会场,不管是四五十岁的老大爷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人人都穿着花花绿绿的新衣裳,手拿着红旗。“没化妆的人肩上都扛着锄头、蹶子,非常威武雄壮,全场人山人海,拥得水泄不通。”[19]
新秧歌弥合了艺术与农民之间的鸿沟,给他们提供了更多表演的机会。当舞台演出的内容不再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而是更容易引起共鸣的真人真事时,越来越多的农民被动员起来。这时的秧歌不再是单纯的文艺作品,而是他们现实生活的重现,是真实的情感宣泄。1946年,晋城某村演出广场秧歌剧,剧中一个觉悟不高的群众在翻身运动中,私下找地主拉关系,结果反被地主打出来,于是伤心地哭了。演到此时,观众在下面大喊:“哭什么!挨打我还说你不对,来吧,还是和咱们在一起,大家团结力量大!”[16](P40)秧歌充分发挥了它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在热烈情感的烘托下,中共的政治理念成功地主导了民众的思想,他们遵循这样的理念完成了社会身份的认同。而在这认同之外的人,将被视为他者,成为火热的公共生活的弃儿。秧歌剧中的情节激发了民众斗争的决心和勇气,甚至有些人难以抑制对敌人的仇恨,出现了过激的行为。鲁南某地在演出斗争张百万的剧目时,一位民兵被剧情带动,“端起枪瞄准台上的‘张百万’就要开枪,幸亏旁边的班长发现及时制止”[16](P150)。1947年,《一笔血债》在涉县杨家庄公演,当表演到佃户向地主诉苦,地主咒骂踢打时,观众的怒火被点燃了,像打雷般喊叫起来,此后竟然把本村的地主拖出来斗了好几天。[14](P20)在这样热血沸腾的氛围中,秧歌具有的“凝聚”与“释放”功能一次次得到展示,舞台不再是娱乐的场所,而是斗争的阵地,观众也不再是看客,而是中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五、结语
构建自身的意识形态,将其传递给民众,并最终获得社会大多数成员的认可,这是中共取得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长期以来,中共面对的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广大农民,受到历史传统、自然环境和文化素质的制约,政治情感较为冷漠、政治参与较为迟钝是这个群体的固有特征。1938年,聂荣臻在一份写给毛泽东的军事报告中,谈到当时的华北乡村由于文化闭塞,“对于社会改革表现隔膜与冷漠,富于农业社会所特有的保守观念”[20](P97)。要想把这个群体纳入革命体系之中,就必须利用多种方式唤醒他们的革命意识,让他们理解、认可中共的政治理念,从而自觉地投身到革命运动之中。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开发利用与乡村生活关系密切的文化资源就显得紧迫而重要,极具乡土气息的秧歌自然会成为中共政治动员的关键因素。中共利用秧歌来表达政治理念,这极易被文化水平较低、政治意识较为淡薄的农民所接受。他们会看到自己的行为也可以“入戏”,也可以被后人传唱,从而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而且“农民因此也感觉到了自己抗日行为的意义所在,意识到原来打打鬼子冷枪,摸伪军岗哨,支前抬伤员,生产公粮对整个民族和国家有如此大的意义”[21](P215)。
当承载着中共意识形态话语的秧歌活跃在华北根据地的大小村落时,农民不再是娱乐的围观者,而是政治的参与者。秧歌不但有效地培养了他们对中共的政治认同,而且让他们把这种认同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成为一种社会习性。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作为民间艺术的秧歌因具备了时代价值而在战争年代得到继承和发展。秧歌本有愉悦大众、传承文化、增进交流等社会功能,但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这些功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在华北根据地内,由于抗战的需要,中共没有抛弃乡村社会旧有的文化传统,而是在扬弃之后,植入革命元素,利用它来为政治动员服务。政治赋予了秧歌特殊的时代性,使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大地释放着别样的艺术影响力。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贺雷.河北定县的秧歌[J].剧学月刊,1937,(2).
[3]关于秧歌舞[N].晋察冀日报,1941-03-15.
[4]怎样过旧历新年[N].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02-13.
[5]广泛开展旧历新年的文化娱乐工作[N].晋察冀日报,1942-01-30.
[6]山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山西文艺史料(3)[G].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
[7]全区各地积极筹备春节娱乐[N].新华日报(太行版),1946-01-29.
[8]太岳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年关宣传娱乐工作的指示[N].新华日报(太岳版),1946-12-05.
[9]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春节宣传土地法大纲[N].新华日报(太岳版),1948-01-23.
[10]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M].北京:现代出版社,1947.
[11]关于秧歌舞种种[N].晋察冀日报,1941-04-03.
[12]用秧歌活跃目前宣传工作[N].晋察冀日报,1942-03-23.
[13]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的文艺运动[N].晋察冀日报,1945-02-25.
[14]卜克江.涉县春节文娱活动[J].北方杂志,1947,(3).
[15]晋察冀中央宣传部关于年关工作指示[N].晋察冀日报,1946-12-24.
[16]荒煤.农村新文艺运动的开展[M].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49.
[17]邓伟志,徐榕.家庭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8]牛建立.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二流子”改造[J].中共党史研究,2010,(2).
[19]晋冀农民庆翻身春节文娱空前活跃[N].晋察冀日报,1947 -02-16.
[20]聂荣臻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21]张鸣.乡村社会权利和文化结构的变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陈东霞
K26
A
1671-3842(2014)05-0048-05
10.3969/j.issn.1671-3842.2014.05.11
2014-04-14
崔一楠(1983—),男,辽宁锦州人,讲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