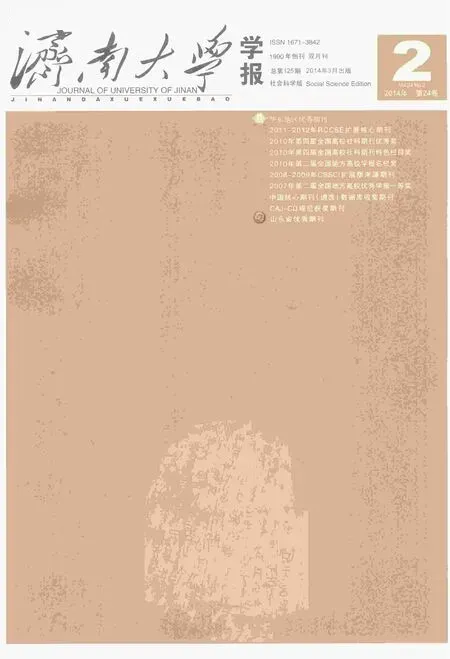叶嘉莹的中国身份认同
张春华
(山东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外学术交流呈现出立体交叉的形态和繁荣之势,国内学术界的眼界也日渐开阔。随着对西方文化、历史乃至社会现实等西方学术基础认识的深化,西方学术的神圣性、神秘性不再是吸引国内学者热衷于其的因素,西学的诸种不足也被国内学者认识。另外,虽说西海东海,心有同理,但中西文化、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指向功利性目的的西方学术研究开始趋于理性。一些学者开始向内求诸己,重视传统文化的研究,乃至出现了国学热。国学热兴起的同时,海外汉学家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开始吸引更多国内学者的关注,逐渐形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海外汉学热。不仅一批数量可观的海外汉学著作被译介到国内,而且有许多海外汉学家应邀来华进行学术交流,对我国的传统文化研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在这些汉学家中,有些曾生长于中国,出于诸种原因,现在侨居海外,成为海外华人的,如张光直、叶嘉莹、徐复观等,他们和中国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虽处异国,却不忘旧邦,可谓海外遗民。他们的经历、感情都非常复杂,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有着不同的认知。叶嘉莹先生是他们中的一员,本文仅就叶先生的文化身份认同一窥部分海外华人汉学家的身份意识。
一、叶嘉莹的“中国身份”
叶嘉莹先生现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依照当代地缘政治法则和国籍法,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加拿大才是其祖国。然而,无论叶先生还是许多国内学者,似乎都不这么看。在叶先生公诸于世的汉语著作中,以及她在国内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她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外国人”,而是认定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在大量讲座中,面对国内的听众和学子,她曾不止一次地用“我们、我们国家、我们的文化”等词,有些时候,“我们”一词确系学术套语之用,更多的情形中则是叶莹嘉自觉地将中国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属之地。
那些熟知叶先生的国内学者,似乎也并没有把她当作一个外国人来看,专访、介绍叶先生的报刊杂志所用的标题直接反映了这样的认识。比如《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的叶嘉莹教授访谈录,题目为:“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这是叶先生自己的诗句。书生无疑是指叶先生,“报国”中的“国”不是加拿大,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华人时刊》刊出了介绍叶嘉莹的文章,标题为“诗词报国叶嘉莹”,其中所报效的国家也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都表明国内民众对叶先生国别身份的认定并没有遵从国籍法的准则,而是不假思索地认定叶嘉莹就是和自己同籍的中国人。
毫无疑问,国内学界并非不知叶嘉莹先生的国籍,许多口头或文字的介绍也都明确指出她是加拿大学者。叶先生本人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她为什么将自己视为一个中国人,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而这种认同又被国内的多数人所认可?
问题的核心在于对“国家”的界定。简单而言,指称叶嘉莹先生的祖国为中国时,“中国”并非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中国”,而是指文化中国;无论叶嘉莹本人,还是其他人,在涉及到叶嘉莹的中国身份时,认同的都是一种文化身份、民族身份。
在中西方语境中,“身份”一词出现虽早,但它成为一个学术概念,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却是社会学兴起以后的事。人是具有社会性的物种,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系统之中,各个社会系统也都有由多种不同的结构构成。身份标志着一个人在系统中所占据的结构位置。这一位置决定了一个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属性,乃至精神归属。身份认同表明个人对自己在社会中的结构位置的认知、接纳和肯定。由于构成社会的结构多种多样,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个体也就处于各种结构之中,每个人也就拥有了复杂多样的身份。从身份的形成或者说来源看,大致可以划分为继得性和获得性两大类,前者指社会中的个体与生俱来的身份,如性别身份、亲属身份、地域身份等等;后者则是一种通过学习后天获得的身份。如职业身份、阶级身份、情境身份等。[1](P93)文化身份属于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它带有习得性。文化环境、教育背景都是一个人取得自己文化身份的重要因素。由于文化身份属于具有习得性的特点,它与身份持有者所受的文化教育就密不可分,对大部分人而言,成长前期的传统教育确定了他们的文化身份。叶嘉莹先生自小接受的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仅对传统文化对着深刻的理性认识和文化自觉,并且尤为擅长古典诗词创作,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有所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已融入她的生命之中,不仅接受,还以自己的努力和成就延续着传统,叶先生的中国身份也得之于此。
叶嘉莹先生祖上为蒙古旗人,和纳兰性德同一氏族,叶先生是否受这位著名的词人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她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和这位前代著名词人之间的亲族关系,在写作《论纳兰性德词》时,她曾创作了一首诗,其中有“我与纳兰同里籍”一句。[2]对一般人而言,有意攀附历史上的名人,多是为了满足一时的虚荣之念。但是,对于在诗词创作、批评,以及批评理论都卓有建树的叶嘉莹来说,这种比附绝非单纯的虚荣心可以解释,它表明一方面叶先生对自己种族身份的确认,另一方面则在潜意识中对自己延续前代成就的认可。诗词创作曾是历代文人墨客抒怀、酬答的方式,是一个读书人必有的文学素养。白话文推广以后,这种素养渐不被人重视,但历史上那些著名诗词作为宝贵的遗产仍受人喜爱,它们的作者也受人敬仰。叶嘉莹能创作出颇受时人好评的诗词,表明她拥有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有意识强调和纳兰同族这一事实,无疑是对自己汉语诗词创作能力的肯定。因此,可以推定,和种族身份相比,叶嘉莹更在意她的汉文化身份,这种身份和她的成长联系在一起,并伴其一生。
虽为蒙古裔满族人,叶嘉莹自幼年起接受的却是汉文化的教育。在她四岁的时候,父母已经开始教她认识汉字,习诵古诗。七岁时,姨母成了她的家庭教师,用《论语》作为她的开蒙读物。姨母不仅强调传统的背诵之功,而且重视传授做人的道理。童蒙时期的家庭教育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深植于叶嘉莹的内心,并伴随她一起成长,及至成年,当被问及影响自己最深的话时,她回答说是整部《论语》。“取得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成功化为了生活本身”,“把生活塑造成了与之一致的存在”,“因此在那个漫长的时间里儒家思想事实上就变成了真理和价值”。[3](P48)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其中不仅积淀着上千年的思想与情感,也是价值观、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文化的指导性文本。叶嘉莹将这部书视作影响自己最大的书,接受了其中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并将它们和自己融为一体。在成长过程中,她虽接受过西方教育,少年时曾习练英文,但无论语言技能,还是文化素养,都没有因此有大的改变。人到中年,叶先生家遭不测,也曾受洗,成为一位名义上的“基督徒”。1954年春天,和丈夫一起,叶嘉莹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曾做过儿童“主日学”的教师,也曾在姊妹会讲过圣经故事。但是,在自己的女儿小慧眼里,她并不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2],她内心却并未完全认同这一身份。个中原因,或许就在于基督徒的身份是一个生活在困苦中的人“被迫”认同,而中国人的身份是她的自觉认同。[4](P133)中年以后,她到美国做研究、教书,重新开始学习英文,一方面是生活所迫,一方面仍是为了向他者传授自己祖国的传统文化。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立场,面对异族文化,她秉承拿来主义的态度,将异国文化、理论化入对中国传统诗歌理论的解析之中。因此,西方文化的浸染并没能改变她的汉文化身份,反而使之得到强化。
由于自幼受汉文化教育,一生都在从事汉文化研究、传播工作,蒙古族身份也只具有人种学上的意义,从文化身份的角度看,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人”。历史原因和个人境遇又使她的汉文化身份和另一个身份——民族身份交织在一起,共同构筑成叶嘉莹的中国身份。
二、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的交汇
一个人认同了某种文化身份,也就是找到了文化归属,而活的文化总与承载者结合在一起,当这些承载者归属于同一族群和民族时,文化归属又和民族归属联系在一起。因此,萨里姆·阿布断言:“文化认同基本上是指民族性。”[5](P11)在他眼中,民族性是文化认同的基础。以此为基础,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之间具有了共通性。以此来描述叶嘉莹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十分帖切,在她心中,文化身份也就意味着民族身份。只是这里的民族既不是血缘意义上所属的蒙古族,也不是汉族,而是经过民族融合以后形成的中华民族。她的汉文化身份即表明了她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也就是说她是一个中国人。但是,叶嘉莹身上体现出的文化身份与民族身份的融合,虽然契合了萨里姆的判断,却并不能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这种融合有它自身的独特性,有其特定的历史情境。
人类历史上,民族和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同源性,民族性和文化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每个民族总会创造出自己民族特有的文化,而特定的文化也总和一定的民族联系在一起。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化和民族之间完全一致,不分彼此。毕竟一种文化完全可以由不同民族共享,同一民族也拥有不同类型的文化。但是,一旦涉及到身份认同,共享的因素就会被排除掉,留下那些最能反映民族性或文化特质的元素。它们被挑选出来,成为特定群体的身份标识,该群体中的个体凭借这些特殊的元素明确身份,表明归属,从而将自己和他族区别开来。由于那些反映民族性的元素都属于文化因素,或者掺杂进深厚的文化色彩,所以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认同永远交织在一起。文化身份却不一定和民族身份交叉融合,它可以完全独立于民族而存在。只有在形成、标识身份的文化与民族紧密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出现文化身份与民族身份的交织。标识叶嘉莹身份的文化因素恰恰如此,汉文化和中华民族是一体的,因此,她的文化身份与民族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二为一的。
前文已述,叶嘉莹认同的文化是汉文化,她获得的文化身份是汉文化身份。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文化不仅是汉族人的文化,它还不断涵化着周边其它民族的文化,比如满族,形成了一个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化圈。清代以后,人们更多用中华一词来指称这一文化圈及其成员。伴随着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夏文化圈再次摆脱其它强势文化的统治,中华民族成为生存于华夏文化圈内的各民族的正式称呼,成为一个国族与民族的统一体。虽然在百年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华夏文化吸纳了许多其它民族的文化,但汉文化仍旧是主体,这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源所在。
叶嘉莹的文化身份形成于早年,当时国家、民族、传统文化都处于生死存亡之中。自幼年起她便经历了这一切,她汉文化身份的形成是与汉文化的危机,以及中华民族的危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纵使不关心世事,但卢沟桥事变、何梅协定、亡国政府成立等都令她有“切肤之痛”。[6](P480-481)越是危机,越是图存的时刻,越能激起民族内部成员对自己身份的关注。民族磨难是叶嘉莹那一代人难以抹去的记忆,这样的磨难是她们认识到自己民族身份的清醒剂。她之所以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属于这一民族,固然与文化认同有关,更与她和这个民族一起经风历雨有关,那样的经历使她铭记自己的民族身份,即使离得再远也没有忘记。况且,这个身份背后还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在支撑着。
认同中既包含着归属,也包含着排异,对一种文化或民族的认同意味着对其它同一层次的文化或民族的排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身份认同可以交叉出现,却很少异质相融。叶嘉莹认同了自己的汉文化身份和中华民族身份,将自己当作一个中国人,最后却加入了其它国籍,以行为背离了她心理上的认同,其中缘由则在于那段难以回首的遭遇。经历了民族与文化危亡的叶嘉莹并未看到新文化的力量。抗战胜利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无知,认为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完全相悖于自己的价值观。抱残守缺的她跟随自己的丈夫离开了大陆,到了台湾。之后,她的先生却又被国民党怀疑私通共产党而遭牢狱之灾,此一变故使全家人都蒙受磨难,身心受到迫害的先生一心离开台湾,并鼓励她先行到美国就业,叶嘉莹因此才借机去美国,用她的话说,这些都不是她的选择。她选择的只有一样,那就中国古典诗词。无论何时何地,她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热爱没有变,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爱没有变,这是她的根。带着这样的根,即便生活于美国、加拿大,即便受洗于自认为有道理的基督教,都不能改变她对自己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的认同。在她心里,她仍然是一个中国人,因此,待得时机成熟,她就会迫不及待地回到中国,将一生所学回报自己心中的祖国。
三、身份意识对她学术研究的影响
叶嘉莹虽身居海外,内心则认同自己的汉文化身份,自然与她所受到的汉文化教育有关。同时,她又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中国是她的祖国。她秉持的汉文化身份与中国身份,不仅是一种纯粹的心理归属,情感依靠,而且是她做人的准则,进行学术研究的旨归。
在创作、研究过程中,叶嘉莹的汉文化身份和中华民族身份是其价值取向、理论取向的支点。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结合方面,叶嘉莹所取得的成绩成为一种典范。她将解释学、女性批评等西方现代理论引入到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中,却又不露痕迹,使二者水乳交融,发人所未见之论,丰富了古典文学的内涵。在回答如何将西方理论结合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提问时,她指出一个人要有学习中国的历史,拥有一个根源,这样才可以结合,否则,一个人看再多的西方著作,它们也是支离破碎、散漫无归的,需要一个中心将其贯串起来。[7](P224)这样的根源、中心就是本族的文化,叶嘉莹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身份,这样的民族感情才可以用它们来融化西方的文学理论,将之成功引入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
在叶嘉莹的学术著作中,《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是份量极重的一部。这部著作不仅是她的古典文学研究由批评赏析转向理论分析的标志,而且也是她对王国维文学批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叶嘉莹的早期文章追随自己的老师顾随一路,注重诗歌对人的兴发感动,间杂自己的主观情思,多赏析之作;在准备研究王国维的过程中,开始侧重客观析理;等到这部书完成以后,她的学术路径已经由感性赏析转向理性探讨。吸收西方理论之长,以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用的研究路径恰形成于此时。叶先生研究王国维的巨大成就,学界自有公论,她化通中西的研究方法也被大量研究者采纳。总之,王国维研究在叶嘉莹的学术之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追问她为什么会选择王国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会发现她的中国身份认同对其研究对象的选择以及研究方向的确立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叶嘉莹喜欢王国维源自少年时。天资聪慧的她自幼对中国古典诗词有极高的感悟能力,少年时读《人间词话》,已感到其中一些评词的语句“于我心有戚戚焉”。王国维的词也让身处困境的她产生强烈的共鸣。无疑,这些都是中年以后计划研究王国维的动因。如果留意王国维的身世和《人间词话》的学术立场,再来观照叶嘉莹的人生际遇以及这部研究著作的旨向,便会发现两人两书有诸多共通之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契合之处颇多。王国维遭逢乱世,正如殷周之际,旧道德旧文化四面危歌,行将解体。叶嘉莹前半生离乱不定,她看到了旧文化的解体,虽没有亲身经历新文化的确立,却由于漂泊海外,感受到异文化的冲击。两人身世两异,对自己旧文化的认同却相似,对异文化的态度也相同。王国维写《人间词话》之际,已是他从事文学批评的后期,从看重西学转向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然而,此时王氏笔下的批评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古典诗文评点,尽管他采用了传统的形式,却融入西学的理念,是“新观念与旧修养的结合”[6](P127)。这种结合体现了王氏在文学批评上的地位,他把“把西方新观念融入中国旧传统,为中国旧文学开拓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新的批评途径”[6](P127-128)。也就是说,《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对中西文学批评的一次超越,将新观念、西方理论融入传统批评模式,发展了评点式的传统文学批评模式。在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叶嘉莹也开始大量接触西方理论,还为此苦读英文,以补不足。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这部著作中我们很难见到叶嘉莹究竟受哪些西方批评理论的影响,已完全不是感悟式的批评,而重视客观材料,进行逻辑推理的理论探讨,是叶嘉莹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上做出的重大转折。方法虽转,背后的取旨却并未变,她的研究对象仍属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范围之内,其对王国维批评理论、批评观念的评析也旨在承扬传统。这表明在研究之始,她已经预设了价值前提,也预设了研究的方向。个中原因和王国维研究诗词批评一样——文化身份使然。王国维以新文化中的旧文化守望者自居,叶嘉莹则以异文化中汉文化的传承者自勉。明白自己的文化身份,也就明白自己在文化传统、文化发展中应扮演的角色。这样的人一旦有机会在文化创造的舞台上进行表演,就会按照自己的角色定位行事。王国维和叶嘉莹都明白他们的身份,所以才会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做出杰出的贡献,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
叶嘉莹做人的价值观是中国的,她的文化之根系于中国。因此,她的诗学批评和理论创作,最终都是以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为旨归,传承中国文化,发扬中国文化是她自觉的学术追求。和一些西方汉学家比较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一些置身中国文化传统之外并不认同中华民族身份的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时,也取得了杰出的成绩,但他们是抱着“他者”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他们感觉不到归属,无法体会文化中沉淀的深厚感情。一些清醒的西方汉学家也明白这一点。比如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就曾说过:“在学习和感受中国语言方面,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无论下多大功夫,也无法与最优秀的中国学者相并肩;我们唯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新问题的提出和对旧问题的新回答,这二者具有同等的价值。”[8](P6)叶嘉莹先生以自己取得的成就向世人证明,处于学术传统之内的位置,不仅可以提出新问题,还可以对旧问题做出新回答。并且,凭借着对传统的深切体悟,其问和答包含着更多的智慧,启发也更深广。
[1][美]艾伦·G·约翰逊.见树又见林——社会学与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叶嘉莹,祝晓风.“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叶嘉莹教授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3,(6).
[3]赵汀阳.学问中国[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4]黄平,罗红光,许宝强.当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5]《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文化认同性的变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6]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7]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8]斯蒂芬·欧文.初唐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