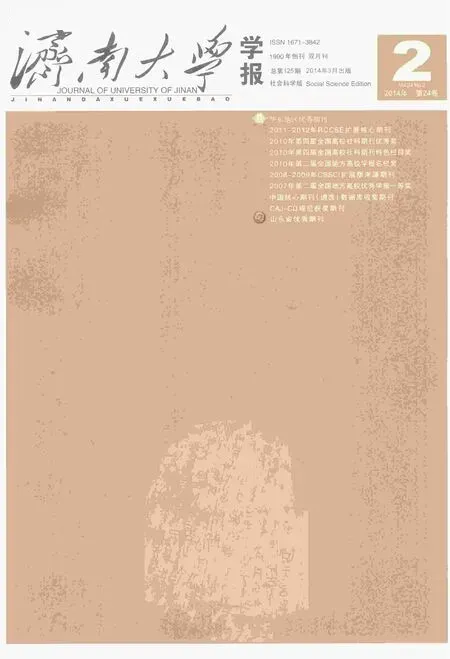孔子与官书制度(下)——孔子对书籍传播的历史贡献
刘光裕
(山东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经学传记是一家之学的集体著作——兼谈官书三特征与产生集体著作的必然关系
六经的经学都由经文与传记两部分组成。如《诗经》之305篇诗作,如《春秋》之鲁国十二公编年史,如《周易》之六十四卦象与卦辞、爻辞,这些都是经文,也称本经。传记是对经文的解释。举例如,《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此为经文。《公羊传》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为传记。再如,《诗经·周南》第一篇《关睢》,这诗作是经文。《毛诗》解释说:“《关睢》,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此为传记。对经文的解释,无论是口头还是文字,古人称“传”或“记”,也称“传记”。对经学来说,经文与传记都重要,两者缺一不可。经文如果没有传记,如《诗经》经文就是一部古代诗歌集,又如王安石称《春秋》经文为“断烂朝报”,就只有史料价值与文献价值,而不具有儒家意识形态的意义。东汉桓谭说:“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太平御览》卷610)从“王正月”到“大一统”,从《关睢》到“后妃之德”,说明经文的思想意义是由传记赋予的。经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都是通过传记对经文的解释而产生的。儒家经学以此为特征,区别于诸子,也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思想家的著作。经学的历史演变如汉学演变为宋学之类,最终取决于传记内容的演变;经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概取决于传记。经文虽为“周官之旧典”,可是孔子对经文的解释是民间著述,所以在西汉独尊儒术以前,经学一直是民间学说,儒家也与诸子一样是民间学派。
据汉以来文献记载,传记都由孔子弟子传于后世。如认为商瞿传《易传》①《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淄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子夏传《毛诗》②《汉书·艺文志》:“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又,《经典释文》:“徐整曰:‘子夏授高行之,高行之授薛仓之,薛仓之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夏传《公羊传》《谷梁传》③徐彦《公羊传疏》载《何休序》引载宏曰:“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于子平,平传于子地,地传于子敢,敢传于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应劭《风俗通》:“谷梁子名赤,子夏弟子。”,还有曾参传《孝经》等。商瞿、子夏、曾参都是孔子著名弟子。学界公认,传记归根结底源于孔子教授弟子时对经文的解释,没有孔子当年讲经,就没有传记。那么,这些传记的作者是谁呢?是否就是孔子?若不是孔子又是谁?如《易传》,自汉至魏晋的几乎所有著名学者都说是孔子作。④举例如:《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系辞》《说卦》《文言》。”《汉书·艺文志》:“孔氏为之《彖》《象》此外,魏晋以来大都认为,《左传》的作者为左丘明,《公羊传》的作者为公羊高,《谷梁传》的作者为谷梁赤作,《毛诗》的作者为子夏或毛弘或毛苌,如此等等。宋代欧阳修最早指出《易传》“非一人之言”(《〈易〉童子问》),否认《易传》为孔子作。大致从宋代开始,逐渐发现传记都不是某一个人的文字,于是产生了是否“伪作”的长期争执。总之,传记的作者问题由来已久,两千多年悬而未决。
凡书籍都有作者,讨论作者与作者问题是书籍史或出版史的份内之事。经学传记都是先秦古书。可是,后人所见传记都是汉代人整理并公诸于众后传下来的本子;它们在汉代以前传承了二三百年的本子(口传或文字),因为从未公诸于众的缘故,汉代就见不到了,汉代以后根本无法见到,无以为据。在我国书籍史上,汉代以前是漫长的官书时期。官书与汉以来书籍相较有三大特征,这就是:不准公众传播,作者不署名,书无定本。官书时期的学术著作受官书三特征的影响,凡经长期传承,最后不能不演变为无名氏集体著作。可以说,有官书三特征,必有无名氏集体著作。传记在官书时期传承了二三百年,不能不受官书三特征影响与制约。因此,讨论经学传记这类先秦古书的作者问题或著作权性质,首先要注意官书三特征与产生无名氏集体著作的必然关系。弄清了这个关系,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不然的话,只能再一次回到上千年悬而不决的争论中去,不会有什么结果。对传记来说是如此,其它先秦古书大致也是如此。不过,人们对官书三特征早已陌生,它与无名氏集体著作的关系又是诸多因素纠结在一起的复杂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且从作者不署名讲起。
秦汉以前,作者不署名作为一种历史传统,最初源于官书,后来又被经籍与子书所继承。余嘉锡《古书通例》有“古书不题撰人”一节,说之甚详。清初学者章学诚最早发现先秦作者不署名,他在《文史通义·为公篇》反复讲一个观点就是:“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他说“古人”不将作品(“文辞”)“据为己有”,意思就是作者不署名,此言不虚。不过,他认为不署名的原因是出于作者“为公”之心,无非是复古史观的臆测而已,并无事实根据。商周以来,政治上为君权至上;经济上是无所不包的国有制;文化上实行几无遗漏的全面垄断,就是史官文化。官书都是官府典籍。史官文化从垄断典籍的需要出发,将官书中作品一律规定为君王所有或国家“公有”,不许视为作者“己有”。如果允许将作品视为作者“己有”,等于将作品视为贵族私有,必将危害官书制度的巩固,所以是史官文化决不允许的。将官书中作品视为君王所有或官府“公有”,这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颇为一致,也与公田之外没有私田颇为相似,这些在西周是普通平常之事,并不奇怪。在出版学看来,作者署名的根据是什么?这根据就是将作品在名义上或精神上视为作者所有。官书中作品不许视为作者“己有”,说明作者没有署名的根据,也就是没有署名权。可见,官书作者不署名的真正原因不是别的,是因为自己没有署名权。如果作者是因“为公”而不署名,其中一个必要前提是作者享有署名权;而官书作者是因为自己没有署名权而不署名,所以与“为公”毫不相干。须知官书作者的身份是“王官”,他们撰写作品是奉王命,循职守;
《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魏晋易学名家王弼、韩康伯说:“其《彖》《象》等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见
《周易正义卷首》,《十三经注疏》本)他们孜孜不倦追求的是赏赐,是爵禄(因为作品不能公众传播,作者写作概不以名利为动机)。如前所说,官书作者是垄断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反对将作品视为君王所有或国家“公有”,这也是不将作品视为作者己有的观念得以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经籍与子书都不是官书,可是官书传统是书籍领域的唯一历史传统,人们只能继承这个传统,包括继承不将作品视为作者“己有”的传统观念,故而经籍与子书的作者也不署名。
先秦作者概不署名,说明先秦作者对作品没有署名权;没有署名权的根源在官书制度,不在作者方面。
在我国古代,作者署名萌生于战国后期,到汉代才渐渐成为社会习尚,大致以汉代为界,由作者不署名演变为作者署名。从历史过程看,作者在作品上署名,首先取决于社会观念将作品在名义上或精神上视为作者所有,简单说是将作品视为作者己有。自汉代开始建立了这样的社会观念,我国作者从此享有作品的署名权,因而都在作品上署名。与此同时,又逐渐形成了与这种社会观念相适应的道德准则,以维护作者署名的真实性不受损害。汉代以前因为一直未能建立这样的社会观念,所以作者概不署名。今天所说著作权,其核心就是作者对作品享有署名权;作者对作品的其它权益,都是在署名权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我国自汉代建立的将作品视为作者己有的社会观念,以及与此适应的道德准则,与今天所说著作权的核心——署名权完全一致,仅因为不是法律规定的权利,故称“著作权观念”,以示区别。
在我国书籍史上,汉代开始建立著作权观念是古代书籍文明的重大进步,具有里程碑意义。至今有人仍旧认为,先秦作者不署名是“为公”,汉以来作者将作品视为“己有”是道德退步,这是与书籍文明背道而驰的错误观点。无论在著作界还是读书界,著作权观念之有无,亦即作者署名与否,都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头等大事。例如,在没有著作权观念(作者不署名)的社会中,作者可以无条件地、任意地利用或使用他人作品,其中概不存在“窃为己有”与“篡改”之类问题,仅此便知著作权观念决非无足轻重。在漫长的官书时期,因为没有著作权观念(作者不署名),再加不向公众传播与书无定本,这些深刻影响了作者观念、读者观念以及著作方式,从而形成一种与汉以来截然不同的特殊著作环境,再通过作者及其著作活动,最终影响作品特别是学术著作的著作权性质。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其一,影响作者观念。作者不署名与不向公众传播这两项,决定作品不可能成为作者获取名利的工具,因而作者头脑里的名利观念也无从产生。作者不署名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是书籍尚未公众传播,在实现公众传播以前,作者不署名必将继续存在。鉴于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作者的责任观念、荣誉观念、道德观念等,无不源于将作品视为作者己有(作者署名),所以在建立著作权观念以前,作者的自我意识不可能完全自觉,与作者意识相互依存的读者自我意识也不可能完全自觉。由此可知在汉代以前作者与读者的区别是模糊不清的,两者间不存在像汉代以来那种泾渭分明的界限。
其二,影响读者观念。不将作品视为作者己有的社会观念决定读者头脑里的书籍作者,一概没有真假之别,与此相联系的“伪作”观念也就无从产生。因此,道德领域也不可能产生反对“剽窃”“篡改”之类旨在规范作者活动的道德准则。受作者不署名的影响,读者只关心作品本身,不知道也不关心作者是谁,对作者问题从来不闻不问。读书界产生伪作观念以及社会上重视作者问题的时间,只能在著作权观念产生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
其三,影响著作方式。不准公众传播的官书,都在相对固定的狭小范围内世代传承,如医书在医官范围世代传承、天文书在天官范围世代传承,如此等等。对官书来说,一是在相对固定的狭小范围内世代传承(不向公众传播),二是不将作品视为作者己有(作者不署名)。因此,凡有旧作可用,就不必另撰新作;凡撰新作,大都利用旧作,对旧作做修订改造的工作。总之,著作活动以修订旧作为常规,非必要不另著新篇。作者修订旧作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已有的单篇作品,做重新选择、编次的工作,《诗》《书》皆属此类;另一种是对旧作内容做增删、改造或吸收、整合的工作,学术著作大都属于此类。
由此可见,受官书三特征影响的作者观念、读者观念与著作方式,与汉代以来迥然有异,因而形成一种与汉代以来截然不同的特殊著作环境,时刻制约作者及其著作活动,从而影响作品特别是学术著作的著作权性质。
为何特别强调影响学术著作的著作权?所说学术著作,是与同为官书的典章文献相对而言。官书中的学术著作,著名者如《内经》《本草》《周髀》《九章》等,汉代称“方技”“数术”。这类著作与典章文献相比,后者常常被诸侯私自毁灭,前者一般不会。悉心传承这类著作,完全符合执政当局的利益。这类著作的传承者是专业技术官员。对这些技术官员来说,传承这类著作就是传承一家之学;这一家之学,又是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据,无不视若生命,或比生命更重。因此,这类著作与典章文献很难传于后世不一样,它们传承时间大都特别长,往往数百年或上千年传承而不佚失。此外,典章文献理应保持历史原样,不可随意修改。与此不同,学术著作在千百年或数百年传承过程中,为了适应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必须不断修订;若不修订,就不能与时俱进,将失去生命力。当年有能力修订这类著作的人,只有著作的传承者——专业技术官员。著作修订以后仍供他们自己使用(不用于公众传播),所以除偶尔需另著新篇外,大都以修订旧作为常规,对旧作做增删、改造或吸收、整合的工作。这样不断修订的结果,必将导致以下两个结果。
结果之一,导致有些作品成为古典名著。学术著作不断修订的过程,就是不断丰富、完善、提高的过程,也是不断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作品通过多次修订,积累成果,凝聚智慧,其中有些终于登上学术顶峰,像《周髀》《九章》《内经》《本草》等公诸于世时遂成古典名著。有些人不知古典名著的上述经历,不知它们是华夏先人千百年心血与智慧的结晶,常常以为它们是莫名其妙地突然降临的,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结果之二,导致它们必然成为无名氏集体著作。学术著作在长期传承过程中必须不断修订,已如前述。在修订著作时,官书时期特殊著作环境中一些因素,如作品无真伪之别,作文无名利之念,特别是没有著作权观念与定本观念,必然对作者及其著作活动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因为没有著作权观念,作者(修订者)可以无条件地、任意地使用或利用他人的作品。“无条件”,指无需征得他人同意,无需做任何说明;“任意”,指增、删、抄、改之类,悉听尊便。作者这样做,因为尚没有著作权观念,完全符合社会道德。作品经过这样多次修订后,作者不能是一人,必定是不同时代的许多人;作者概不署名,所以必然成为无名氏集体著作。其次,因为没有定本观念,凡修订,必定将旧作留存的文字,与修订者新增的文字,以及吸收整合其它作品的文字,这些不同时代、不同作品的文字都混合在一起,不加区分。修订一次,就混合一次;修订多次,就混合多次。最后,这类著作传承到汉代公诸于众时,作品中不免留下多次混合的痕迹,诸如观点前后矛盾,文字前后重复,全篇结构不统一,混用不同时代的专门词语等。公诸于世前多次修订留下的这类痕迹,用汉代以来“一人一作”的标准衡量,都是不可原谅的常识性错误,所以一旦被文献学家发现就惊呼“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殊不知官书时期的作品,因多次修订而成为“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是合乎规律的正常现象,这不是“伪作”的凭证,这是历经多次修订的可靠证据。
前面,从官书三特征形成的特殊著作环境,说明长期传承的学术著作因多次修订而必然成为无名氏集体著作。现在,再将这过程归纳为以下四点。
其一,在官书时期,书籍因为不能公众传播而无法成为社会传播工具,学术著作受此影响而不能流布于社会公众间,它们在相对固定的狭小范围内世代传承。其中,王官之学在畴官家族范围内世代传承,而私学中学说在师徒范围内世代传承。
其二,在相对固定的狭小范围内传承的学术著作(口说或文字),凡经长期传承,必须不断修订;若不修订,就不能与时俱进,将失去生命力。这类著作的修订者,就是著作的传承者。
其三,凡修订著作(口说或文字),以下四个因素必然影响并制约修订者(作者)及其著作活动:一,作品无真伪之别;二,作文无名利之念;三,没有著作权观念(作者不署名);四,没有定本观念(书无定本)。
其四,著作(口说或文字)经历这四个因素制约下多次修订,最后传承到汉代公诸于众时,必然成为无名氏集体著作,亦即“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这类作品的作者包括历代参加创作与修订的所有成员,所以是一个特殊的作者群体。这类作品的著作权属于这特殊的作者群体,概不属于任何个人。
在上面四点中,第一点、第三点是既定的客观因素,第四点是必然结果,导致这必然结果的关键是第二点,即凡经长期传承必须不断修订。
经学传记作为学术著作,既然在官书时期传承了二三百年,长期处于由官书三特征形成的特殊著作环境,最终不能不演变成为无名氏集体著作。这一点,只要在传记中找到不断修订的证据,亦即“不是一人一时之作”的证据,大致就能确定。可是,经学传记在汉魏以来似乎都有了作者,如认为《易传》的作者是孔子,认为《左》《公》《谷》的作者是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等。既然有了有名有姓的作者,而且作者是一人,都与我们所说无名氏集体著作有矛盾,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无法继续讨论下去。
实际上,汉魏以来,不只是经学传记都有了作者,其它先秦古书也都有了作者。既然先秦作者不署名,先秦古书为何到汉魏以来都有了有名有姓的作者呢?这些“作者”是怎样得到的呢?揭开这个谜,不能不涉及汉魏以来社会上针对先秦古书的“被作者”思潮。
传承到汉代的先秦古书,因为作者不署名的缘故,大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作者是何人,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可是,因为汉代开始建立了著作权观念,人们所见汉代以来书籍都有一人为作者,有些人以为先秦古书也是这样的“一人一作”,于是想方设法给不知作者的先秦古书包括传记、子书与官书都按上一个“作者”,这就是所谓“被作者”,详见拙作《简论官书三特征》。[1]“被作者”的出发点是为先秦古书找一个作者,然而置主客观条件于不顾,再加求功心切,因而采用猜测、比附之类幼稚办法给先秦古书硬按上一个所谓“作者”。具体方式不一,兹举两例。
例证之一,西汉还不知作者的《本草》,东汉开始有了作者。
《本草》是古老官书之一,《汉书》三次记“本草”,意思是药物学或药物学这一类作品,都不涉及作者是何人。①《汉书》三次记“本草”见:一,《郊祀志》“本草待诏”;二,《平帝纪》载征召“方术、本草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三,《楼护传》记楼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从这三次所记,西汉时“本草”的含义有二:一为药物学,如“本草待诏”;二为药物学这一类作品,如楼护所诵“本草”。“本草”的含义指称药物学一类作品,这类作品的作者必定有许多人,决不是一人。可是到东汉,郑玄就说《本草》是神农作;到晋代,皇甫谧又说是歧伯或伊尹作。郑玄或皇甫谧给《本草》按上的这个“作者”,未经考证,没有根据,无非是在权威崇拜心理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猜测而已。
例证之二,以书名中的人名为作者。
传记以书名中的姓氏为作者,子书以书名中的诸子为作者,都是以书名中的人名为作者。历史上的事实是,先有以人命书,然后才出现以书名中的人名为作者。先秦古书原来只有篇名,没有书名;它们的书名都是到汉代以后才有的,原因是它们要在公众间传播了,非有书名不可。汉代常见的命书方式是以人命书,像西汉刘向以子命书便是。我们从刘向校定的子书看,他以学派为准,把同一派的作品,包括疑似同一派的作品,都编入这一派的书中。②例如,刘向《晏子叙录》说:“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再如,刘向《列子叙录》说书中有些篇章,“不似一家之言”。由此可知刘向校子书,以学派为准,为了保存资料,“不敢遗失”,他将“疑后世辩士所为”或“不似一家之言”的作品,也编入这一派的书中。刘向校定的子书,其实是学派的文集,或学派的集体著作。他虽然以子命书,然而不认为子书是诸子一人所作,不认为书名中的诸子就是作者。由此可见,刘向以子命书,他没有把书名中的人名(诸子)与作者等同起来,也不认为子书是诸子一人的作品。刘向以后,经东汉到魏晋,以书名中人名为作者才流行起来,主要对象就是传记与子书,《左》《公》《谷》以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为作者皆为此类。用这种办法给传记或子书按一个“作者”,除了同样是一种猜测,另外还是一种不科学的比附。汉代人所撰作品若以人命书,以书名中人名为作者大致是对的,可是将这种办法,用于传记、子书这类先秦古书就不对。
“被作者”作为书籍领域一种错误思潮,兴起于汉魏间;大致官书在先,再及传记、子书;到唐代,《隋书·经籍志》将子书都录为某子“撰”③例如,《隋书·经籍志》称:“《老子道德经》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庄子》二十五卷,梁漆园吏庄周撰”等。,从此登峰造极,几成定论。现在看来,“被作者”是我国校雠学在幼稚阶段所犯最大错误,后果之严重,始料不及。“被作者”的要害不仅是弄错作者,更是篡改了先秦古书的著作权——将集体著作篡改为某“作者”的个人著作。这样篡改了著作权以后,只要在先秦古书中发现那个所谓“作者”死后才出现的人物、事件或词语之类(文献学这类发现并不难),这些就都成为有人篡改或作假的证据,该古书因此就变成了“伪作”。宋代以来,“被作者”的先秦古书都是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打成“伪作”,酿成千古冤案。清初以来,文献学家不断发现古书作者不署名,以及子书不是诸子一人所作等。这些新发现等于宣告“被作者”是一个伪命题,客观上是一个骗局。可是,古书辨伪者深信不疑,故而他们反对“伪作”的崇高热情只能事与愿违,实际上变成了抹黑先秦文化的一场欺世盗名的游戏。
从“被作者”的错误可知,讨论经学传记这类先秦古书的作者问题,要注意以下两点:其一,官书时期的学术著作因长期传承而不断修订,最终不能不演变为无名氏集体著作;其二,不可胡乱套用汉代以来的“一人一作”模式。“被作者”的错误,首先源于套用汉代以来的“一人一作”模式于先秦古书,不知先秦学术著作大都是无名氏集体著作。这个惨痛教训,是以诸多先秦古书被打成“伪作”为代价换来的,理当记取,不可忘记。
针对“被作者”之荒谬,余嘉锡《古书通例》指出:“传注称氏,诸子称子,皆明其为一家之学也。”[2](P184)他认为传记以姓氏命书,子书以诸子命书,都不是指称作者,都代表一家之学,他的看法是对的。为何代表一家之学,容后再说。下面,以《春秋》三传《左》《公》《谷》为例,主要引用四库馆臣的话,说明传记在公诸于世以前都经过多次修订。
《公羊传》,据说最初由孔子弟子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战国时齐人,生平不详。《四库全书总目》卷26“公羊传”条说:“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于两楹之间’二句,《谷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併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于公羊子。且併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高之明证(按:高,即公羊高)。”四库馆臣一再说《公羊传》“不尽出于公羊子”。换句话说,就是《公羊传》的作者不是一人,而是许多人。我们前面说过,官书时期的学术著作因长期传而必须不断修订,最后必然演变为无名氏集体著作,亦即“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公羊传》就是一个例证。
《谷梁传》,据说最初由孔子弟子子夏传给谷梁赤。谷梁赤,战国时鲁人,生平不详。《四库全书总目》卷26“谷梁传”条说:“《公羊传》‘定公即位’一条,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诂以为后师。此传‘定公即位’一条,亦称‘沈子曰’。公羊、谷梁既同师子夏,不应及见后师。又‘初献六羽’一条,称谷梁子曰。传既谷梁自作,不应自引己说。且此条又引‘尸子曰’。尸佼为商鞅之师,鞅既诛,佼逃于蜀。其人亦在谷梁后,不应预为引据。”四库馆臣发现“沈子曰”“尸子曰”都是谷梁赤以后的人,说明该作品在谷梁赤以后有人修订过。根据“谷梁子曰”这种语气,这话必定是谷梁赤以外的人留在作品中的。这些说明,《谷梁传》曾经一些人修订;究竟多少人修订,概不可知。《谷梁传》的作者包括历代参加创作与修订的所有人,故而它的作者是一个特殊的作者群体。谷梁赤或许是这作者群体中的一员,然而更多成员全然不知。由此看来,《谷梁传》不是谷梁赤或其他人的个人著作,它是无名氏集体著作。
《左氏传》,据说最早由左丘明传于后世。左丘明,春秋后期人,大致与孔子同时。四库馆臣发现,《左氏传》“哀公五年”载有“子思曰”一段话。子思(前489—前402),姓孔名伋,孔子之孙,比左丘明晚两代。“子思曰”这段话,必定是左丘明死后另有人加进去的。《左传》书中许多“君子曰”,有些学者以为是左丘明以外另有人加进去的。史学家顾颉刚认为,今本《左传》经过七种途径的“改造”①顾颉刚认为,今本《左传》是对《左氏》原书改造而成,改造之途径有七:一,本无年月日而勉强为之按插者;二,本为一时事,再分插入数年中者;三,将《国语》中之零碎记载加以修改并作一篇者;四,受西汉时代影响而加入者;五,受东汉时代影响而加入者;六,在杜预作《注》后加入者;七,《左传》本有而后人删之者。详见顾颉刚讲授、刘起釬笔记《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59-83页。。所谓“改造”就是修订,“改造”者为何人,概不可知。如果《左传》最初真的是左丘明作,它的历代修订者或“改造”者姓甚名谁,人数多少,都不知道。在《左传》的特殊作者群体中,左丘明只是一员而已,更多成员一无所知,所以《左传》为无名氏集体著作无疑。
从有关《左》《公》《谷》的以上考证,可知它们在长期传承过程中经过多次修订,最后到汉代公诸于众时遂成为无名氏集体著作。其它传记也与《春秋》三传一样,都是无名氏集体著作。
那么,为何认为这些传记都是一家之学的集体著作呢?这是因为传记在汉代公诸于众以前一直在师徒间世代传承;凡是世代师徒相传的学说,都是一家之学。
在官书时期,书籍因为不能公众传播而无法成为社会传播工具,故而私学中的学说不能不靠门弟子传于后世。而传记的“口耳相传”,足以证明它们在公诸于众以前一直在师徒范围内传承。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认为,“《诗》无所谓今古文,口授至汉,书于竹帛”。章学诚说,《易传》“自田何而上,未尝有书,则三家之《易》著于艺文,皆本于田何以上口耳之学也”①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田何而上,未尝有书”,意为《易传》从孔子弟子商瞿到西汉初年的田何,一直是口传。《春秋》三传中《公》《谷》在汉以前也是一直口传。学说的口耳相传,必定是师徒相传;不是师徒关系,无法口耳相传。经学传记多数靠口传,已如前述。此外,《左传》是少数录为文字者之一。东汉范升说,《左传》“出于丘明,师徒相传”②《后汉书》卷36《范升传》。。可见录为文字的《左传》,与“口授”的《公》《谷》一样也是“师徒相传”。
根据“师徒相传”这一点,可以判断传记的历代修订者的身份,不会超出同门师徒这个范畴,四库馆臣说是“传授之经师”也是对的。当年,一家师徒只传一种传记,《左》《公》《谷》《齐》《鲁》《韩》《毛》等分别在各自师徒关系中传承,通常是后学修订师辈传下的作品(口说或文字)。不过,像《谷梁传》的“尸子曰”,尸佼是法家,法家不可能成为儒家传记的修订者,所以“尸子曰”当为某谷梁后学所引。既然历代的修订者概出于同一师门,他们虽不是同时代人,然而遵循同一师说家法,故而可以判断传记的内容为一家之学。
归根结蒂说,传记最初源于孔子讲经。可是,孔子所讲经义,经弟子后学不断修订改造而传承到汉代时,早已不是孔子当年所讲原样,早已演变为数量很多而彼此相对独立的一家之学。对后代研究者来说,可以认知的不是孔子当年所讲原样,而是由此演变而来的一家之学。与传记的一家之学相比,古老官书如《周髀》《九章》《本草》《内经》都出于畴官的一家之学,它们因为传承时间特别长,在千百年传承中转辗于不同畴官之手,最终成为不同一家之学的综合体。传记的一家之学源于民间私学,传承时间相对较短,大都是单一的一家之学。
从著作权考察,传记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个人的著作,它们是一家之学的集体著作。从传记是集体著作看,以为它们是包括孔子在内的任何个人的著作,都与事实不符。欧阳修称《易传》“非一人之言”,其实所有传记都“非一人之言”,因为它们是集体著作。从传记是一家之学看,它们的作者都是一个特殊群体;具体一点说,是以一家之学为界限的、跨越不同时代的特殊群体。不同的经学传记,出于不同的作者群体。诚然,孔子不是传记的作者,然而是这些作者群体的始作俑者与关键人物。诚然,传记书名中的姓氏不是作者,然而可能是该作者群体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一个成员。这样说并不矛盾,事实就是如此。
孔子“述而不作”的原意——兼谈书籍尚未公众传播对作者行为的影响
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③《论语·述而》。“述”与“作”的含义,古今差异不小。在先秦,“述”的本义是遵循、训释、解释等意思。如《说文》:“述,循也。”礼《说文》:“作,起也。”《广雅·释诂》:“作,始也。”汉以后称“作”,多为“著作”之“作”,或“创作”之“作”,限于文字作品与精神产品。先秦称“作”不以精神产品为限。例如,《吕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所作,当矣。”可见在先秦,不论物质产品、精神产品还是社会制度,都可称“作”。
“述而不作”之“作”所指是什么?要注意“述”与“作”两者,都与“信而好古”联系在一起。孔子所“信”之“古”是什么?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④《论语·八佾》。“吾从周”表示他对西周礼乐制度的敬仰与崇拜。“信而好古”之“古”,就是西周礼乐制度。“述而不作”之“作”是礼乐制度之“作”,其中包括有关礼乐制度的精神产品。孔子“述而不作”的原意大致是,遵循、训释周公的礼乐制度,而不是自己另外创始什么制度。这样的意思,与“信而好古”一致,也与“吾从周”一致。如前所说,孔子对六经所做工作是利用原有篇籍而赋予新解释。这种工作称为“述而不作”,完全符合“述”“作”的原意。
到秦汉年间,“述”与“作”的含义有所变化。由河间王刘德整理问世的《乐记》说:“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乐记》诠释的“述”“作”,代表秦汉年间儒家学者的理解,与孔子原意有联系,又有区别。就联系而言,其一,《乐记》所讲“作”,仍旧是礼乐制度之“作”。其二,《乐记》所讲“述”,仍是遵循、训释、解释等意思;所讲“作”,仍是创始或兴起的意思。以上两点与孔子原意一致。就区别而言,其一,孔子“述而不作”,推崇的对象是西周的周公,不包括孔子自己;《乐记》中“作者之谓圣”的“作”,已经包括孔子在内。其二,孔子的“述”本是夫子自谓,《乐记》“述者之谓明”之“述”,已将孔子排除在外。如《乐记》孔疏说:“述”指“子夏、子游之属”。
现代社会称“作”,是“著作”之“作”或“创作”之“作”,与孔子所称“作”不一样,也与《乐记》所称“作”不一样。那么,假如从现代所称“作”考察,孔子有没有自己的“著作”或“创作”呢?下面,列举上世纪三位学者的看法,供参考。
其一,哲学史家冯友兰说:“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般儒者本来都是如此。不过孔子虽如此说,他自己实在是‘以述为作’。因其以述为作,所以他不只是儒者,他是儒家的创立人。”[3](P277)其二,历史学家范文澜说:“《论语》载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事实上述与作是分不开的。他讲解古书,绝不能不掺入自己的意见,这个意见正是作而非述。”[4]其三,文化史家柳诒徵说:“《易》《春秋》则述而兼作。世谓孔子‘述而不作’,盖未读《十翼》及《春秋》也。”[5](P236)
上面三位学者,或说“以述为作”,或说“述与作是分不开的”,或说“述而兼作”,都认为“述”与“作”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意思大致是,孔子的著作存在于他给弟子讲学,特别是口授弟子的经义之中;其中,“赞《易》,修《春秋》”则更多表现为他的著作。20世纪中国史学界,无论批孔还是尊孔都认为孔子有著作;否认孔子有著作者,大概只有编辑史与出版史。
孔子作为思想家与著作家,不能不向社会传布自己的思想与学说,这样必然碰到使用何种传播工具,怎样使用传播工具,以及利用何种传播方式等问题。这类问题如何解决,首先取决于客观的社会条件,而不是个人意愿。这是因为传播工具与传播方式任何时候都不属于个人而属于社会,它们必然由社会提供,人们只能在此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因此,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传播工具与传播方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必然影响并制约人们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方式。从官书时期的特定社会条件看,主要是书籍尚未公众传播,还有作者不署名,这两项必然对孔子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我们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孔子讲解经义,为何“口授”而不录为文字?古今学者一致认为,孔子给弟子所讲经义是“口授”,而没有录为文字。那么其中原因何在?《史记》《汉书》都说,孔子讲《春秋》经义,因为其中有批评时政的内容,“不可以书见”,故而口授。不过,孔子讲《诗》经义没有批评时政,同样不录为文字,可见批评时政并不是孔子不录为文字的主要原因。再进一步看,儒家传经,除经文有文字,传记大都口授到汉代才录为文字。不仅如此。在汉代以前,师徒间口授学说并非儒家独有。章学诚说:“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①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从“口耳之授”到“著之竹帛”的时间,大致以汉代为界。在先秦学术界,师徒间口授学说是一种普遍现象,其中必有深刻原因。民国前后一些学者认为,先秦学术盛行口授的原因是简牍繁重,使用不便。与纸书相比,简书繁重为不争的事实。可是,简牍另有两大优点:一是书写文字与绘制图画,无不可用;二是制作不难,价格不贵,贵族以外的布衣也用得起。在汉代,简牍繁重依然如故。可是,传记在汉代纷纷从口授录为文字,著于简牍,这个事实可以证明简牍繁重,并不是先秦学术盛行口授的主要原因。
离开了社会传播,孤立地讨论孔子为何口授经义而不录为文字,先秦学术为何盛行口授而不利用文字作品,这类问题无法解决,或许只能是个谜。
对思想家或著作家来说,他们的学说要向社会传播是既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可以变更的是传播的方式与渠道,或利用书籍(文字作品),或通过“口授”(口耳相传)。如果书籍(文字作品)可以将学说传布到社会公众间,若是这样再盛行“口授”(口耳相传),就完全违背常理,也完全违背常识。由此看来,口授之盛行必定与书籍的作用如何密切相关。以前,人们从不怀疑先秦书籍的作用,总以为它们与汉以后书籍的作用是一样的,其实大谬不然。从书籍的社会作用看,汉以前书籍与汉以后书籍有何不同?简单地说,后者是传播工具,前者不是。汉以前书籍为何不是传播工具?因为尚未公众传播。一般说,凡书籍都可以成为传播工具或媒介工具。但是,书籍只有公众传播才能成为传播工具,才能发挥传播工具的巨大作用;不向公众传播的书籍,不能成为传播工具,仅仅是一种记录文字的载体,这种不能成为传播工具的书籍作用是有限的。书籍的作用如何,首先取决于是否公众传播,这一点被人们完全忽略了。官书作为君王的政治工具,作为贵族特权等级的标志,从来不准公众传播,故而从来不是传播工具。受官书传统的影响,官书时期的书籍都不能成为传播工具,仅仅是记录文字的载体,这种书籍的作用是有限的。我国书籍到汉代才在公众间流通与传布,从而成为传播工具。所以,孔子从未见过成为传播工具的书籍,他头脑里对书籍作用的认知,与汉以来人们的认知相差甚远。从资料看,孔子作为思想家与教育家家从未正面谈论书籍的作用。他讲过“文献”对考证夏礼、殷礼的作用,这“文献”的含义除了典籍文字,还指贤者口传。①《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按:杨伯峻注:“《论语》的‘文献’包括历代的历史文献与当时的贤者两项。”考证古礼要靠口传资料,说明书籍的作用还不大。孔子以后的墨子,最早宣称书籍具有超越时间空间的巨大传播作用。墨子这些高论,汉代以前应者寥寥,原因也是书籍尚未成为传播工具,所以他的超前意识无法成为社会共识。
讨论孔子为何将经义“口授”弟子而不录为文字,以及先秦学术为何盛行“口授”而不利用书籍,首先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身处官书时期,必须面对书籍不能公众传播这个客观现实。不能公众传播的书籍无法成为传播工具,只是一种文字载体,它的作用是有限的。例如,早就录为文字的《左传》在先秦社会上一无所闻,说明录为文字对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等没有什么作用,可见当年书籍(文字作品)的作用很有限。所以对经学来说,除了防止记忆差错或其它原因不得不录为文字者,如经文等,将口授的经义都录为文字是不必要的。再从学者传播学说的要求看,因为受制于不能利用书籍作为传播工具,他们只能将学说传授给弟子,通过弟子再向社会扩散。在此情况下,老师“口授”弟子不只是一种教学方式,也是学说的传承方式。将学说向弟子“口授”(口耳相传)的作用,未必不如文字,有时优于文字。像解经的传记由老师口授弟子,不只比文字方便灵活,还有利于弟子后学的发挥创造。从学说传承的生命力看“口授”与录为文字,前者为《公》《谷》,后者为《左传》,前者如果不是比后者更具生命力,至少不比后者差。由此看来,孔子“口授”经义而不录为文字,以及先秦学术盛行“口授”,都是受制于书籍(文字作品)不能公众传播这个客观现实,无可奈何,不得不如此。
话得说回来,“口授”的作用仅限于师徒之间,不能超出门弟子这个范围。因此,当历史发展到书籍可以公众传播的时候,书籍作为传播工具的巨大作用得以发挥出来;与此相比,“口授”的局限性必然暴露无遗。在此情况下,要向社会传播学说的学者凭常识就能判断:必须弃“口授”而利用书籍(文字作品)。这就是一直“口授”的传记到汉代纷纷录为文字的原因所在。章学诚说:“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我国古代学术从先秦“口授”到汉代录为文字,幕后主导这场历史变革的最大因素,不是学者,不是政治家,而是书籍(文字作品)面向公众传播。
我们再从传播方式看“口授”与书籍(文字作品)的区别,前者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传播,后者是利用传播工具的间接传播。与直接传播相比,间接传播因为利用书籍或其它传播工具,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故而信息传播的范围广,速度快,效率高。所以,书籍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汉代以前书籍尚未公众传播这个客观现实,决定孔子或其他思想家向社会传布学说时,因为书籍不能成为传播工具而无法从事间接传播,只能主要利用面对面的直接传播,即口头宣传。直接传播的先决条件是要靠人,故而思想家必须依靠门下弟子,别无它法。总之,孔子与其他先秦思想家要将学说布于社会,传于后世,除了靠自己外,必须靠门弟子,因而门弟子数量越多越好。如果没有门弟子,学说难以布于社会,更无法传于后世。例如《春秋》传记之一《邹氏传》,据《汉书·艺文志》载它在西汉初年有书十一卷,可见已录为文字,然而因为“无师”很快就失传了。同为《春秋》传记的《公》《谷》并无文字,一直靠口传,然而代有师徒,数百年长盛不衰。与录为文字的《邹氏传》因“无师”而失传相比,《公》《谷》的长盛不衰可以证明,师徒关系对传承学说的作用,远比录为文字重要。在书籍尚未公众传播的社会上,思想家的学说必须靠师徒关系传于后世。有师有徒,学说才能传承,才能保持生命力;无师或无徒,学说就失传。因此,师徒关系成为思想家学说赖以传承并赖以发展之不可或缺的载体,世代“师徒相传”就是这样必然地产生的。在长期师徒相传的过程中,原为老师创立的学说(口说或文字)不能不被弟子后学修订改造,最终演变为一家之学;而一家之学的著作必定是集体著作。
总起来说,一,口授而不录为文字;二,世代“师徒相传”;三,一家之学;四,集体著作。这四者看似互不相干,实际上彼此联系,它们都是书籍尚未公众传播的产物。孔子与战国诸子及其弟子后学,他们在这四个问题上为何不约而同,十分一致?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生活在官书时期,必须接受书籍尚未公众传播这个共同因素的制约,故而必须如此,也只能如此。
到了汉代,因为书籍可以在公众间传播了,人们开始利用书籍作为传播工具从事间接传播,促使学术界纷纷放弃“口授”而利用书籍(文字作品),作者为文字作品甘愿倾注一生心血,以期自己随文字的传布而扬名于世。于是,师徒关系逐渐演变为以教与学的关系为主,它不再是思想家学说赖以传承并赖以发展之不可或缺的载体。书籍作为传播工具的巨大作用被人们认识并掌握以后,口授的作用相形见绌,望尘莫及。在此情况下,“口授”只是作为师徒间一种教学方式继续存在,学术界数百年“口耳相传”的历史就此结束了。书籍成为传播工具以后,一家之学迟早要突破门弟子的范围而融入社会,从而被公众掌握,一家之学很快演变为公众之学。新的一家之学仍将产生,然而像传记那种师徒相传二三百年的一家之学不能再有了,一家之学主宰我国学术的历史就此结束了。与此同时,无名氏集体著作也随一家之学一起走向历史的终结。鉴于公众传播必然要求作者署名,诞生有名有姓的大著作家、大科学家的时代从此来临。
凡此种种,都说明书籍(文字作品)公众传播与否,对人们思维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影响非常重要。
第二个问题,孔子与诸子作为思想家为何都开门办学?先秦私学中师徒为何结成一体,形成利益共同体?孔子一生开门授徒,门弟子三千。他先在鲁国一面办学,一面从政;五十五岁开始,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六十八岁返回鲁国,与弟子一起著书,至七十三岁去世。在此可注意两点,一,孔子著书已是晚年,离去世只有五六年;二,孔子著书,著于文字者只有经文,经义都口授弟子,并不录为文字。既然是晚年才著书,又不将经义录为文字,说明面对书籍不能公众传播这个客观现实,他不指望通过书籍作为媒介工具向社会传布学说,他主要通过包括周游列国在内的口头宣传(直接传播)扩大社会影响。孔子以后,战国诸子也都开门授徒,他们门弟子数量也都很多。例如,墨子、孟子的弟子常有“数百人”,道家田骈有“徒百人”,农家许行有“徒数十人”,等等。那么,孔子与其他先秦思想家为何都开门授徒办教育呢?这样不约而同,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共同受一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呢?在此,先将孔子与西汉扬雄作一比较。
扬雄(前53—18),西汉著名思想家,一生未为大官,立志“求文章成名于后世”,重要著作有《法言》《太玄》《方言》等。①《汉书》卷87下《扬雄传》:“雄三世不徙官。……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忽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矣,而桓谭以为绝伦。……雄以病免,复召为大夫,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钜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时人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闻雄死,谓桓谭曰:‘子尝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桓谭曰:‘必传,顾君及谭不及见也。……’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然篇籍具存。”将扬雄与孔子相比,至少有三点不同。第一,孔子开门授徒,有三千弟子;扬雄没有开门授徒,去世前只有一个弟子——侯芭相随。第二,孔子带领众多弟子从政,并周游列国;扬雄在长安闭门谢客,“人希至其门”。唐代诗人卢照邻说:“寂寂寥寥扬子居(按:“扬子”即扬雄),年年岁岁一床书。”(《长安古意》)第三,孔子到晚年才著书,孟子也是到晚年才著书;扬雄一辈子埋头著书,很早就立志“求文章成名于后世”。这三点说明,同为思想家的扬雄与孔子,他们所走道路并不一样。扬雄走的是著书扬名的道路。这里要提的问题是,孔子能否也像扬雄那样走著书扬名的道路呢?
扬雄所以能走著书扬名的道路,首先取决于西汉社会为他提供了两个客观条件。其一,书籍(文字作品)已经在公众间传播。这证据便是,扬雄死后四十多年,他的著作“大行”于世。其二,作者已经在作品上署名。这证据便是,扬雄头脑里产生了“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的著作动机。在扬雄以前,司马迁早已公开了自己著书扬名的观点。要是没有这两个客观条件,扬雄把文章做得再好也无法靠埋头著书而名扬全国。这两个客观条件,汉代以前概不存在。例如,战国末年流布到秦国的韩非《孤愤》《五蠹》抄本上,作者仍未署名。①《史记·韩非列传》:“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亦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所著之书也。’”从李斯告知秦王“此韩非所著之书”,可知作者没有署名。战国后期的书籍领域,在子书带领下悄悄发生许多变革,然而一直到战国末年,不向公众传播与作者不署名仍旧未见根本改观。因此,孔子或诸子如果也像扬雄那样埋头著书,所著书不能流布社会,湮没无闻,这样他们无法成为具有社会影响的思想家。
汉代以前的社会,因为书籍尚未公众传播与作者不署名的缘故,扬雄那种著书扬名的道路从来不存在,人们头脑里连这种想法也不可能有。孔子与诸子要做思想家,他们必须开门授徒办教育,而且门弟子数量越多越好,所以师徒关系成为思想家学说赖以传承并赖以发展之不可或缺的载体。于是,在私学师徒之间,不能不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特殊关系。一方面是弟子依赖老师子传授学说;另一方面又是老师依赖弟子传承学说,并发扬光大。这种相互依赖的特殊关系,促使师徒双方以传承师说为中心,抱成一团,结为一体,最终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孔门儒家的师徒关系是如此,诸子的师徒关系也是如此。
教育史最早发现先秦私学的师徒之间存在这样一种特殊关系。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说:战国年间,“学派林立,私学比春秋更为昌盛,儒墨法名农诸家都有私学。……各学派都有自己的信仰,以私学为中心,结成政治集团”[6](P162)。像孟子常常带领“数百”弟子“传食于诸侯”,②《孟子·滕文公下》:“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这样的师徒关系称为“集团”,或不为过。与儒家相比,墨家师徒更是组织严密。先秦私学中师徒双方,抱成一团,结为一体,这是事实。不过,既以传承师说为宗旨,或许称为“文化集团”更好些。师说,是将师徒双方联系在一起成为利益共同体的纽带;维护或强化师说的生命力,是这纽带继续发挥作用的关键。因此,师说在传承过程中,弟子后学必须不断修订。若不修订,因此师说失去生命力,无法成为联系的纽带,他们的利益共同体也将解体。明乎此,再看经学传记在师徒相传过程中演变为一家之学集体著作,也就不难理解了。
官书制度在西汉初年宣告结束,书籍从此开始面向公众传播,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利用书籍作为传播工具的人越来越多,汉代以前师徒间那种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特殊关系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故而两汉产生了有别于先秦私学的新型师徒关系。这件事再次提醒我们,传播方式特别是传播工具的变革,不只改变思维观念与行为方式,也改变人际关系。
[1]刘光裕.简论官书三持征——不准公众传播、作者不署名、书无定本[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2]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冯友兰.新原道[M]//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
[4]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M]//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5]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
[6]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