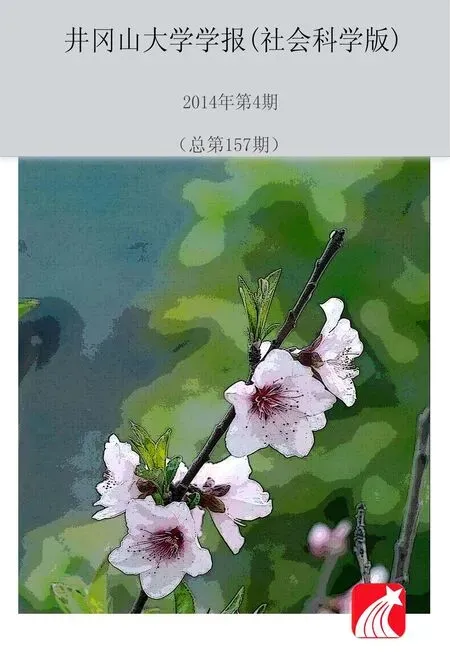论德里达“幽灵政治学”的伦理意蕴
荀泉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论德里达“幽灵政治学”的伦理意蕴
荀泉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
德里达的“幽灵政治学”以苏东剧变后的时代现实为背景,以马克思的异质性遗产为阐述主题,以祛除现实政治的苦难为宗旨,架构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体现着特定的伦理意蕴。马克思“幽灵”内蕴着政治伦理的追求,是复数的亡魂。德里达从马克思“幽灵”的政治伦理精神中提炼出了正义,作为我们应该秉持的价值法则,并认为“追求正义”,是我们建构理想生活的现实选择。
德里达;解构主义;马克思的幽灵;伦理意蕴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当中,探讨了与“幽灵”对话的时代价值,建构了被学界称为“幽灵政治学”的学说。“幽灵政治学”关涉到正义、人权、希望、理想、善恶、幸福、宽恕等人一生必然遭遇的道德问题,有着浓重的伦理意蕴,产生了巨大影响。“无论在哲学界还是文学界,现在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忽略雅克·德里达的作品。”[1](P89)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既是德里达心理空间的表现,同时也是对伦理空间的构建。《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完全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阐释了马克思批判精神的政治伦理价值。本文要探讨德里达“幽灵政治学”的伦理意蕴,就不得不涉及解构的策略。因为德里达对马克思政治伦理精神的考察,始终贯穿着其早期的解构理论和方法。
“幽灵政治学”介于解构与建构之间,以苏东剧变后的国际形势为背景,以如何继承马克思的异质性思想遗产为考察对象,以实现现实政治的公平正义为宗旨。伦理学的宗旨是关注人类的生存困境,实现有节制的理想生活。因此,德里达要彰显马克思政治伦理精神的时代意义,并非仅仅是为了在伦理意义上补充其解构策略,也是为了在“幽灵”的指令中,探寻生存的价值,以便让人们更好地回归生活的本真意义。
一、“幽灵”出场的伦理价值:学会生活
德里达在继承西方传统哲学观点的前提下,提出了“学会生活应该是指学会死亡——去承认,去接受生命有限这个绝对事实——没有正面的结果,没有死后的复活,或末日审判的赎罪,为自己或为他人。自柏拉图以来,这一直就是古老哲学的教诲:做哲学家就是学会如何死亡。”[1](P165)。在他看来,死亡既是我们终生的恐惧,又是我们无法挣脱的枷锁。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建立了一个幽灵的世界,这个世界相信鬼怪,注意到了“幽灵性的非空间的空间”,允许幽灵们说话。这在有的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让一个灵魂言说,这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3](P13)但他希望,后人能够从他的“幽灵政治学”获得学会生活的启示。
(一)向死亡学会生活是我们唯一的可能
建构理想生活,是每个人的期望。“某个人,您或者我,走上前来说:‘最终,我当然希望学会生活’”[3](P1)如何才能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人生价值,这既是每个人的理想追求,也是每个人面临的现实抉择。“但为什么是最终?”[3](P1)人生的尽头当然是死亡,这是非意味着人只有经历死亡才能学会生活?因为生活,就其涵义来说,是无法依靠个人的力量实现的。也就是说,个人无法历经死亡的全部过程,必须通过他者才能理解死亡,学会生活,“因此,只有向另一个人且是通过死亡来学。”[3](P1)理解死亡才能学会理解生活。惟有理解包括死亡在内的生存的全部涵义,才有希望摆脱欲望的枷锁。永恒的死亡在窥视着人类社会。死亡是人灵魂的最终家园,生命每天都在走向死亡,把每天都当成人生的终点,才能学会珍惜。生命不是等待明天的到来,而是让今天不留悔恨。因此,我们需要勇敢地面对死亡,把握当下。社会只是一出自编自导的舞台剧,每个人都处于被摆布的境地,谁也无法抗衡命运。冥冥之中,已经设定总的道路,正如每一颗星星都有自己的运行轨迹,无法改变。很多人必将会从我们的眼中消失,最后成为我们的记忆,就像有一天我也会从别人的眼中消失,成为记忆一样。必定有些人,死后还会回来。从死亡的维度反观生活,虽然悲观,但可以让我们学会珍惜眼前的一切。
与死亡亲密交流,固然是学会生活的唯一可能,但人是不可能历经死亡的国度再回来的,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与死亡妥协,以便进入生与死之间。“无论如何,只能向弥留之际的另一个人学。不论是在外部的边界还是在内部的边界,这都是一种在生与死之间的异常教学法。[3](P1)而鬼魂是沟通生死的使者,人们要了解死亡,必须借助鬼魂的力量,“所谓‘两者’之间,如生与死之间,发生的事,只有和某个鬼魂一起才能维护自身,只能和某个鬼魂交谈且只能谈论某个鬼魂。”[2](P2)德里达极其重视“幽灵”对死亡的描述,他认真地与他们交流。也许,固执的行为和无知的激情,本身就是狂妄愚蠢与自不量力的表现。虽然人们并没有想坠入二元对立温柔的怀抱,但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人们还是被一些冥冥的驱动力量所控制。对与错,爱与恨,君子与小人,文明与野蛮,美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一对对泾渭分明的概念占据着人们的头脑,控制着人们的价值判断,阴阳对立,非此即彼,死亡让人们意识到应该有第三条判断标准。既然,死亡不过是埋葬过去的记忆,那么就珍惜现在,忘却记忆。因为忘却不是胆怯,而是前行;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不是死亡,而是新生。因为一切终会过去,就连最可怕的阴影也将消失,崭新的黎明终会降临,一切终究会重头再来,这才是最应赞美的感人历程。有很多时候,是可以放弃,并决绝的离开的,但德里达没有放弃,他决定踏上荆棘之路,因为他始终抱着一种信念,这世上一定存在着善良,值得我们奋战到底。可是,该如何重拾过去的生活,又该如何继续呢?我们只能依靠记忆,“这种和幽灵的共存也是,或者说不仅是,而且也是一种记忆政治学、遗传政治学和生成政治学。”[3](P2)
(二)向“幽灵”学会生活是唯一可行的路径
德里达通过考察后得出结论:要学会更好地生活,只能求助于生死之间的“他者”,而介于生死之间的他者就是幽灵。召唤“幽灵”,是为了让正义出场。“如果我打算详尽地谈论鬼魂、遗传和生成或鬼魂的生成,也就是说,谈论某些既不在场、当下也无生命,某些既不会向我们呈现、也不会在我们的内部或外部呈现的其他东西,那就要借用正义之名。”[3](P2)作为正义使者的“幽灵”与灵魂有同质之处,既能带来可怕的景象,又能引起冤仇。传统观点认为,死亡只是肉体的朽坏,而作为人灵性存在的灵魂能够脱离肉体而四处游荡,成为幽灵。意志渴望永生,规避死亡。意志凭借生殖延续自己。死亡能消灭意识,但不能磨灭意志。死者的意志会凭借幽灵在黑夜展现。幽灵对内心强大的人不起作用,它要呈现必须凭借紧张的气氛。幽灵的重返人间,是因为放不下尘世的恩怨情仇。“倘若没有某种责任的原则,那么在所有的生命存在之外,在能分离生命存在的东西的范围之内,在那些尚未出生或已经死去的鬼魂——他们乃是战争、政治或其他各种暴力、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性别歧视或其他各样灾难的牺牲品”。[3](P2)幽灵不仅具有魔性,也具有灵性。幽灵利用人们内心的恐惧,对现实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幽灵在生前作了很多罪孽,这让它无法超脱,因此,幽灵渴望阳光,又躲避光明,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一些幽灵,也保有良知,抵挡暴力和专制,渴望给人类带来希望和光明。人类对于虚无,充满恐惧。幽灵带有虚无的色彩,它要煽动起仇恨情绪,才能激发人们采取行动。幽灵在虚无的世界中,并不能逍遥远行。它被情感羁绊着,而只能游荡在生死之间,既无法重新获得生命,也无法毁灭自己。
幽灵存在于生命之外,这让它关注正义。“如果过去的经验是可能的,且如果人们必须认真地对待它,那么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它也许不再是一个问题,并且我们在此可以称它为正义——就必须超越当下的生命,超越和我的生命或我们的生命一样的生命。”[3](P3)幽灵一直徘徊在尘世的边缘,不甘心舍弃原本属于它的利益,总能带来阴森森的气息。它实际上一直耿耿于怀于自己的处境,一直试图回到之前的地方,一直难以忘怀生前的遭遇。幽灵在风中乱舞,为的是诱惑世人进入另一个世界。幽灵要实现目的,就必须采用阴暗的手段,窥视和恐吓人们。幽灵既能引起恐惧和颤栗,又能平复创伤和仇恨,从而制造了一个奇幻的乐园。沉湎于生活泥潭的人们,需要幽灵造成的生活“断裂”,以反思存在的价值。幽灵消解人的本能欲望,复归精神存在。幽灵凭借悲悯与颤栗,使人的情感获得升华。幽灵如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直接感受它的存在,却无时无刻不受它的支配。幽灵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幽灵的正义追求,表明它不是虚无,而是实在的延续,“这个正义使生命超越了当下的生命或它在那里的实际存在,它的经验的或本体论的实在性:不是朝向死亡,而是朝向一种生命的延续,也就是说,一种生与死本身不过是一些踪迹和踪迹之踪迹的踪迹,一种其可能性将提前走向分裂或打乱生命存在以及任何实在性本身的同一性的残余。”[3](P4)“幽灵”非但不能被消灭,而且能够发挥潜在影响,它能内化为人的精神意识,支配人采取策略。幽灵将人的精神意识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而人则将幽灵看成自己灵魂深处的幻梦。
(三)向马克思“幽灵”学会生活是必要的现实选择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称共产主义是被围困的单数“幽灵”,这直接影响了“幽灵政治学”的思路与理论逻辑。“此时,是的,我已经发现,事实上是刚刚才回想起那个本来一直在我的记忆中徘徊的东西:《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个名词,不过这次是单数形式,这就是‘幽灵’:‘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3](P6)人们始终不能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显形”,无论是在巴黎公社运动中,还是在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人们根本看不见这个东西的血肉之躯,它不是一个物。在它两次显形的期间,这个东西是人所瞧不见的;当它再次出现的时候,也同样瞧不见。”[3](P8)马克思曾经称自己的作品为“污秽之书”,把自己的思想称为“幽灵”,这充分表明了马克思的谦虚精神和批判精神。彻底地批判自己,使马克思的思想不断向前发展。当然,这也如同德里达说明的马克思并不完全相信自己的学说,他并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作为批判传统和现实的“幽灵”,既是令资本主义颤栗的革命思想,又是指引大众采取暴力活动的行动指南。共产主义“幽灵”制造了紧张的社会氛围,引起了资本主义的恐惧反应,“在一种明显不同的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1848年就已经在那里讨论了一个幽灵,更确切地说是‘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旧欧洲的所有势力看来,这是一个可怕的幽灵,但是共产主义的幽灵在那时还是将要到来的。”[2](P37)
马克思的“幽灵”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存在诸多碎片。“这意味着可能有一撮,尽管不是一伙,一帮或一个社会,要不然就是一群与人或不与人共处的鬼魂,或某个有或没有头领的社团——而且是完完全全散居各处的一小撮。”[3](P5)马克思的“幽灵”从政治伦理精神中获得了现实存在,能随时变换形式,成为自己也不认识的东西,“它愿成为某个难以命名的‘东西’:既不是灵魂,也不是肉体,同时又亦此亦彼。”[3](P8)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并不进行物质生产,它要做的就是摧毁现存的一切制度,为物质生产创造更好的社会关系。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权力,严密控制意识形态,把社会的一切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中,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进行整体规划。社会权力无非来自暴力、财富或知识。共产主义革命主张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实现社会的严密控制,这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横征暴敛来说的。只有放弃心中的所有幻想,清醒认识自己和他者,而决心抵制放纵和贪婪的诱惑,才有希望挣脱资本剥削的附体梦魇,以节制清明之理性,建构以尊重多元和普遍关爱为内核的内心道德。共产主义不会很快到来,而是一个持续斗争的过程。“‘脱节’——不论它是当下的存在还是当下的时代——只能造成伤害和罪恶,它无疑就是罪恶的那种可能性。但是若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开启,那可能就仍然只有超越于善恶的最不幸之物的必然性。这(甚至)不是命中注定的必然性。”[3](P29)马克思的“幽灵”自始至终行进在路上,处于来临的状态。尽管,时空发生了变化,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仍在引导着人们学会更好地生活。
二、向马克思“幽灵”学会生活:追求正义
马克思思想及其共产主义革命出场的目的是摧毁不合理的旧制度,以便给人们找寻更美好的未来,可共产主义运动总是遭受挫折和磨难。无论任何时代,总会有一些被称为“时代良心”的人,这些人不理会主流意识形态,不迎合权威的价值理念。而德里达显然有这种傲骨。德里达不像那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那样,只是把“实现公有制”作为一种赚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而是把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作为自己学会生活的榜样。一直对马克思及其思想敬而远之的德里达却公开表达了对马克思批判精神的支持。这具有独特的价值。
断裂的年代需要英雄的出现,需要有人牺牲。德里达把自己比作哈姆雷特,决心负起改写历史走向的重担。“安息吧,安息吧,受难的灵魂!好,朋友们,我以满怀的热情,信赖着你们两位;要是在哈姆莱特的微弱的能力以内,能够有可以向你们表示他的友情之处,上帝在上,我一定不会有负你们。让我们一同进去;请你们记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守口如瓶。”[4](P33)时代虽然乌烟瘴气,但并非一潭死水,无可救药。断裂的时代也孕育着复活的希望,“这种断裂,这种‘日趋恶化’的失调不正是为宣告良善,或者至少是宣告公正所必需的吗?”[3](P23)断裂是新生活的条件。死亡会把被生活遮蔽了的“幽灵”呈现出来。只要能挣脱恐惧,就能坦然面对一切。在断裂的年代,德里达决心背负起拯救世界的重任。他要唤醒人们内心的良知,让完全的正义出场。世界上必有一种完全的正义值得我们奋斗到底的。“就政治正义而言,不存在任何纯粹的程序,并且也没有任何程序能够决定其实质性内容,从而,我们永远依赖于我们关于正义的实质性判断。”[5](P429)要实现完全的正义,就不能用传统的对立统一观点看待问题,就不能局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而要重视那些不在场的东西。“要正义,我们的原则就必须尊重不再或尚未存在的他者。我们的责任不能忽视不在场(缺席)的人,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6](P187)因此,马克思“幽灵”的最大价值就是号召人们持守正义。
马克思的幽灵需要政治伦理精神的依附。遮蔽的幽灵,总有呈现为政治伦理精神的机会。政治伦理精神总要展示为幽灵的指令,“幽灵是精神的肉体显圣,是它的现象躯体,也是一种救赎”。[7](P171)因此,政治伦理精神必须借助马克思的“幽灵”才能成全自己,“幽灵”必须发出指令,政治伦理精神才会有所附丽。正义是马克思政治伦理精神的内核。马克思的政治伦理精神作为死掉的正义,内蕴着正义的理想追求,是正义精神的彰显。但马克思幽灵中的“正义”又蕴涵三种特质:惩罚性、弥撒亚性和解构性。
(一)马克思幽灵中“正义”的惩罚性
马克思幽灵中的“正义”带有复仇色彩,既是惩恶扬善法则的展现,又是暴力革命内在逻辑的彰显。德里达凭借叙述《哈姆雷特》中“王子复仇”的经历,阐释了马克思“幽灵”中的“正义”的惩罚性。在他看来,复仇是哈姆雷特竭力拒斥的理性选择。在良知和本能的撕扯下,他无比纠结。叔父的谋杀行为证据确凿,母亲的背叛历历在目,爱人的软弱尽收眼底。世界本身就处于暗夜之中,复仇能够带来曙光吗?他在反复追问:倾力一战还是宽恕兼爱?父王的幽灵一再发出尖利的指令,王子的精神在每时每刻却处于崩溃的边缘。王子的爱恨交织就是父王幽灵在背后种下的蛊。如果不是父王被谋杀,母亲就不可能另结新欢。因此,王子对父亲极度仇恨。可叔叔的毒杀行为更令人不齿,尤其是叔叔霸占了自己的母亲,这让哈姆雷特简直痛不欲生。作为对母亲的报复,他必须杀死叔叔。最终他选择了毁灭自己。父王的冤仇终于得到昭雪,可没有带来黎明,而是仍旧处于无边的暗夜之中。人生只不过是痛苦的无限循环,而快乐只不过是痛苦的消极中断。理性的人不渴望快乐,只求解脱痛苦。可摆脱痛苦后带来的只是无聊。人之所以还能苟活于世,因为对残酷的生存图景心存幻想。德里达特意引用海德格尔的观点,来阐释复仇式正义与惩罚的密切结合。“我们总习惯于用正义(Recht)来翻译Dikē一词。在对此箴言的种种翻译中,甚至有用‘惩罚’来翻译‘正义’这个词。”[3](P24)复仇式的正义体现的善恶有报的观点。共产主义运动也表现出了“复仇式的正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封建势力强盛的德意志帝国,其理论潜移默化地继承了战争理念,“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8](P307)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对敌对的事物、敌对的人,从来都是坚决无情地予以打击的,它为了实现“正义”,表现出了空前的果敢,即使带来遍地血污也毫不在乎。它既损害了公民的基本人权,也背离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共产主义作为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但实现的途径是否只有暴力一种途径呢?徐志摩去英国途经莫斯科写的《欧游漫录》中这样评价苏俄的马列主义者:“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这种看法,也许对我们是有启示的。马克思思想及其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大手笔,“可怕,实在令人恐惧。不仅令《共产党宣言》的敌人恐惧,而且可能也令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自己恐惧。”[3](P101)因此,德里达是坚决反对使用暴力的,即使是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也是不应提倡暴力的。马克思早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作出了判断:无产阶级最后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尽管,如今共产主义又由现实退回到了“幽灵”状态,但保持信心和希望是我们的现实选择,失去正义精神的引领,我们将丧失自由意志,失掉生活的勇气。
(二)马克思幽灵中“正义”的弥撒亚性
德里达用“弥赛亚性”展示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理想追求,它是对美好生活充满期待的希望模式,它同情现存的一切,而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地摧毁。马克思“幽灵”中的“正义”,体现着拯救颓败世界的伦理向度,是一种弥撒亚的召唤。德里达声称,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瓦解,从而让马克思思想再次回归幽灵。共产主义是被“谋杀”的,谋杀它的就是倡导民主和人权的工业社会。共产主义一经诞生,就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驱赶。“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9](P778)马克思用弥撒亚的形式宣传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它有时采取的是一种弥撒亚式的或末世学的形式。”[3](P95)德里达声称,共产主义蕴含着诸种伦理精神,展现着丰富的在场性,“而且像民主本身一样,它区别于被理解为一种自身在场的丰富性,理解为一种实际与自身同一的在场的总体性的所有活着的在场者。”[3](P96)共产主义思想预示着美好的未来,“这些形象预示着最美好的东西,它的事件他必定会欢呼。”[3](P96)共产主义的领袖们以“弥撒亚”的召唤,领导人们摧毁现存的一切社会制度形式,建立了合作的公社制度。一如布道者的工作。在他看来,尽管马克思及其共产主义思想宣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但马克思自始至终是位虔诚的“教徒”。因此,共产主义沿袭了宗教的理想追求,“那宣言显示的是耶稣复活。是作为政党的宣言。”[3](P100)具有弥赛亚性的共产主义并非是“痴人说梦”,而是“改造世界”的现实努力,“如果幽灵只是幽灵而不是别的,并不多于无,是来自于无的无,那么我的书就不值得看第二眼了。”[10](P543),因此,共产主义始终以拯救世界为自己的使命,“这个荒漠将指向另一个深渊似的混沌的荒漠,如果说混沌能够首先描述在张开的豁口中——在等待或召唤我们在此由于对弥赛亚的号召,即另一个绝对的不可预知的具有独特性的和代表正义的到来者即将到来,一无所知而戏称的东西中的无限性、过度性和不相称性。”[3](P28)而实际上,马克思早年非常敬畏神灵,17岁时,还郑重写下如下字句:“宗教授予我们所有人向往的理想。它为全人类牺牲了自己。谁敢否认这一点?若我们选择的职业,能让我们把自己最好的给予人类,我们就不会在其重压下蹒跚行走,因为这是献给万物的牺牲。”[11](P16)但18岁之后,他放弃了基督教信仰。但无疑,《圣经》中上帝拯救罪人的壮举指明了马克思毕生的奋斗方向,使他在潜移默化中学着耶稣的行为样式,拯救颓败的世界。马克思的弥赛亚精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精神。马克思主义把拯救人类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马克思幽灵中“正义”的解构性
马克思幽灵中的“正义”,蕴含着对传统和现实的深刻批判,主张在破坏世界中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与解构的伦理宗旨异曲同工。德里达在马克思幽灵中的“正义”中,发现了马克思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德里达“从一种富有新意的角度对‘逻各斯中心论’的传统进行了解构。”[12]解构本身是一种摧毁正统和主流观点的策略,“解构总是在这一或那一时刻,影响着批评和批评——理论的洋洋自信,这就是说,影响着决断的权威,即事物的可被决断定夺的最终可能性;解构乃是对批评教条的解构。”[13](P205)它要求打破现在的等级秩序,打破私有财产制度,克服人自身的局限性,提升人的觉悟。共产主义社会不是对原始社会的简单复归,而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人人合作的“大同社会”。马克思这种平等思想具有后现代色彩,但与后现代思想又有异质性,“后现代思想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包容,是让不同的社群和团体发出声音”[14](P190)。实际上,私有制不是灾难的来源,灾难来自人性之恶。人性之恶不能消除,只能把矛盾对准社会制度。正义是解构的前提和宗旨,而不是心理体验。传统的政治形式:个人或集团假借大众的名义去欺压公民的利益,即少数人带动的多数人暴政,目标是欺压另一小群人。在政策的制定上,它是少数人决定的;然后通过武力和媒体优势,向大多数人宣传自己的主张,调动大多数人去打压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独裁就是一个人握有绝大多数权力。民主不是“为民做主”,而是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解构不仅要打破传统的等级思想,更要挑战传统的等级制度。“传统那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作为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经给人类带来诸多弊端,它已经难以适合时代的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以更好的切入现实。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开辟了新的思维空间,开启了人们思考当代政治问题的一个新的视角。”[15]完全正义的实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真实的实践与努力。在马克思的形体退场后,正义将成为维系人类保持信心的“许诺”。权力诱使人堕落,绝对的权力诱使人走向绝对的腐化之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要防止腐败。因而,正义的实现需要自由的政治机制,需要警惕斯大林那种专制政体,虽然德里达和马克思现在都蜚声世界,但他们都经受过巨大的挫折和磨难。这种磨难的经历使他们崇尚正义,批判现实。解构本身是一种批判权威的思潮,它关怀弱者,悲悯现实的苦难,这使它保持昂扬的斗志。而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也是通过批判现在的一切实现正义理想的。
三、“幽灵政治学”的伦理意蕴:建构希望
正义精神经过天使的感召定会再现人间。共产主义运动暂时偃旗息鼓,但它的成就无法抹杀,“西方评论家往往强调苏联的失败,但它的成就之巨大是谁也否认不了的。”[16]解读就是理解。德里达阐明了向马克思幽灵学会生活的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建构希望。
(一)在希望中建构伦理精神
不深切体会现实的苦难,就不能理解变革政治体制的重要性。暴力在步步紧逼,而正义在节节败退,如何避免迷惘?个人与外在世界始终存在冲突,必须建立伦理,将人从欲望的泥潭中挣脱出来。人生是在摇摆中进行的,如同西西弗推动巨石,是无聊的循环过程。人生追求幸福,良善只是手段。伦理追求公正和良善,而不是强权和利益。人之所以建构伦理,是期望通过伦理的善达到幸福。道德既是对苦难的怜悯,又是强者的胆识,还是个体和群体的和谐。伦理与道德是不同的范畴,伦理是我们的相处之道,道德是个人适应群体之德。不能用道德谴责取代制度制裁,因为道德只对相信它的人才起作用。对“恶人”来说,道德只是谋利的工具。伦理是为了公正而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是个人的妥协,是群体的虚伪。因此,不必对政治人物抱有道德期望,他们不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道德,必须用制度制约他们。德里达倡导马克思幽灵中的“正义”,但这种正义具有局限性,他要求超越,实现完全的正义。学会生活,关键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德里达呼吁人们团结起来,建立“新国际”。这是对人类生存灾难的“深切关怀”。“新国际”是没有机构组织的联盟,是“一种深刻变革”。“新国际”对每一位觉醒或即将觉醒的生命负责,同时为了阻止专制集团的蓄意干扰,它认真、严肃地辨识真伪,旨在能及时反馈公民利益,以便得以及时补充或改正错误观点,并在今后的行动中能做的更好。德里达有感于现实政治的乱象,迫切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呼吁创办责任、希望、关切的“新国际”。
(二)在正义中点燃生活希望
德里达积极建构鼓舞人心的希望,表现勇气,信仰,人的精神,推崇伦理精神和正义理念,提供有见地的观点,教给人们如何在纷乱的现代社会生活得坦然、快乐和健康,以行动的力量增进道德底蕴的建立。“我不会倡导任何跟马克思相反对的东西。”[17](P63)解构如同黎明前的曙光,能够照亮前进的道路。“德里达的解构是一种批判的进取精神,它在打破了我们长久的迷梦的同时,又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希望,其结果是涅槃后的重生。解构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在理论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启迪人们从不同维度深入思考现实和世界。而德里达的“幽灵”将继续指引我们找寻前进的道路。”[18]德里达的“幽灵政治学”深切关照现实的灾难和人的生存困境,力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平相处。追随真理和正义,我们才能不被世间繁华冲淡内心。他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榜样,而马克思“幽灵”的伦理精神就是面向时代和现实的必然选择。正义作为爱的使者,把恩典布满世界的每个角落,让尘世平安,让尘世有喜乐。完全的正义始终在路上,处于来临的状态。尽管马克思“幽灵”中的正义带有惩罚性色彩,但作为一个精神的“幽灵”,共产主义思想内蕴着对完全正义的渴求。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正义精神可以让我们战胜内心的恐惧,点燃生活的希望,勇敢地追求理想。坚持正义不能使我们获利,却能使我们内心坦然。尽管,马克思“幽灵”的借以显形的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共产主义思想内蕴的正义精神将继续成为维系人类生存希望的“许诺”。
[1]Jim Powell.Derrida for Beginners[M].New York:Writers and Readers Publishing,1997.
[2]张宁.解构之旅·中国印记——德里达专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英]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第9卷[M].朱生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5]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6][英]克里斯蒂娜·豪维尔斯.德里达[M].张颖,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7][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M].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法]雅克·德里达.《友爱的政治学》及其他[M].胡继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11]Karl Marx.Reflections of a Young Man on The Choice of a Profession.[M].Sally Ryan: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1985.
[12]张奎志.德里达“补充”概念的解构学意蕴[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13]V.B.Leitch.Deconstructive Criticism[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14]John B.Cobb Jr.Postmodernism and Public Policy[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
[15]荀泉.德里达“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述评[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16][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M].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7]Jacques Derrida.Positions,trans.Alan Bass[M].London:Athlone Press,1981.
[18]孙全胜.论“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形态[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On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Jacque Derrida's"Politics of Specter"
XUN Q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China)
Derrida's"politics of specter",backgrounded on the realities of Soviet-Eastern Europe collapses in early 1990s,is a theory aimed to elaborating Marx's legacy of heterogeneity and eradicating realistic political miseries.In bridging the ideals and the realities,it embodies certain ethical implications.Marx's"specter"is specters with pursuit of political ethics,from which Derrida distills the idea of justice that people should adhere to.Derrida believes"pursuit of justice"is the realistic choice through which we build an ideal life.
Derrida;deconstruction;Specters of Marx;Ethical Implication
B82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4.04.007
1674-8107(2014)04-0038-07
(责任编辑:吴凡明)
2013-12-20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科技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发展研究”(项目编号:08JA720004);江苏省道德哲学与中国道德发展研究基地项目“高技术道德哲学研究”(项目编号:2009-03-01)。
荀泉(1985-),本名孙全胜,男,山东临沂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