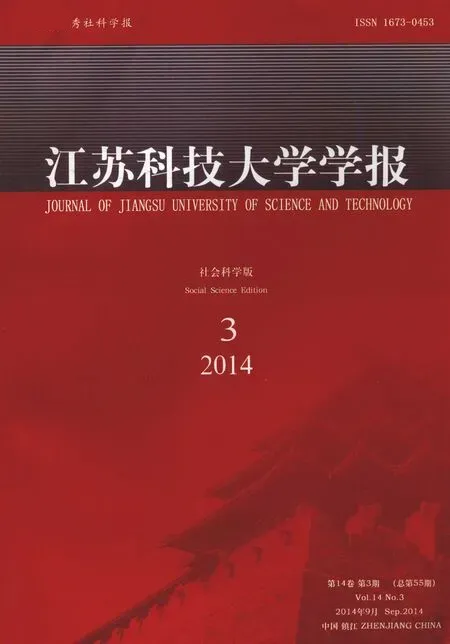论盖斯凯尔女性哥特小说中的幽灵、暴君和母亲
吴庆宏
(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镇江 212013)
论盖斯凯尔女性哥特小说中的幽灵、暴君和母亲
吴庆宏
(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镇江 212013)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以当时流行的哥特文体,创作了短篇小说《老保姆的故事》《克拉雷会苦行修女》和《灰发女郎》等作品,塑造了痛苦的幽灵、专制的暴君和焦虑的母亲几种不同的人物形象,表达了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思考。从女性哥特研究视角解读这些人物形象,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几部一直未引起评论家重视的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很大程度反映了盖斯凯尔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和对女性主义的坚持。
女性哥特,盖斯凯尔,女性主义
女性哥特(female Gothic)指的是美国女作家埃伦·莫尔斯(Ellen Mores)1974年在其著作《女文人》(Literary Women)中提出的概念,即“女作家以‘哥特’这种文学形式创作的作品”[1]90,是一种表达女性幻想、恐惧和对父权社会抗议的流派,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90年代英国女作家安·拉德克利夫创作的《尤道弗的秘密》。以创作长篇小说 《玛丽·巴顿》等著称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对这种文体从来都不陌生,她曾创作过十分优秀的短篇女性哥特小说。自从她的名字在2010年9月25日被绘上西敏寺诗人角的“哈伯德纪念彩绘花窗”后,她的作品再度受到广泛关注,而她的短篇小说却仍然鲜为人知,这方面的研究更是滞后。本文从女性哥特的视角解读她的短篇小说《老保姆的故事》《克拉雷会苦行修女》和《灰发女郎》中的人物形象,将女性主义理论与哥特小说研究相结合,发现她以较为隐秘的方式,巧妙地批判了女性在父权社会的从属地位,表达了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这几部一直未引起评论家重视的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很大程度反映了盖斯凯尔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和对女性主义的坚持。
一、幽灵:女性哥特中的受害者形象
从表面上看,女性哥特和男性哥特作品在叙述技巧、故事情节以及对超自然主义的恐惧与恐怖等手法的运用方面并无区别。但是,正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幽灵故事这种形式给女作家以特殊的自由:不仅能写怪异的故事和超自然的故事,而且能提供比在现实的文类中对男性的权力和性欲更为激烈的批判。”[2]57盖斯凯尔在她的短篇哥特小说中,通过塑造幽灵形象抨击了父权制二元对立的性别观,以述说无法言说的事实。
在《老保姆的故事》中,老保姆海斯特在冬夜听到了从常年上锁的东边厢房传出的阵阵琴声,而家里的琴早已破得无法弹奏。一天,她照看的小姑娘罗斯蒙德小姐突然失踪,原来遭到了幽灵的诱拐,差点冻死在雪地里。而海斯特看到的幽灵是“一个面色严厉而美丽的女子及其身后紧拽着她裙子的小女孩”。那女子名叫莫德,小女孩是她与父亲请到家里的外国乐师秘密结婚所生。自从她发现丈夫背着她和姐姐调情,姐妹反目成仇,不久丈夫就悄悄离开,销声匿迹了。姐姐葛蕾丝出于报复心理,向父亲揭发了妹妹和乐师的关系,以致莫德母女被赶出家门,冻死在冰天雪地中冤魂不散。毫无疑问,莫德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正如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指出的那样,“凭借双重标准的多种优势,男性利用其优越的社会和经济资源获得的权力介入到两个世界中,挑动疏远的两个女人相互为敌”[3]46。莫德和姐姐被自己爱的男人欺骗、玩弄和抛弃,还彼此互相妒忌,互相报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她那专制、暴虐、残忍的父亲,直接把她逼上了绝路。因为“传统上,男权制授予父亲对妻子和孩子的绝对拥有权,包括肉体摧残的权力,甚至还包括杀害和出卖的权力”[3]42。结果连带无辜的孩子一起死于非命。莫德和孩子的幽灵表达了对父权制的控诉和反抗。
《克拉雷会苦行修女》涉及三代人两对母女的生活。年老的布丽奇特因为丈夫早亡,女儿远走他乡杳无音讯,老主人夫妇过世后,她过着孤独凄苦的日子,整日精神恍惚,被人视为女巫。当打猎路过她门前的吉斯伯恩先生射杀了她唯一的慰藉小狗时,她愤怒地诅咒他将看到自己最爱的、也是唯一爱的人成为所有人讨厌和恐怖的对象。不久,吉斯伯恩的女儿露西就成了诅咒的牺牲品,被幽灵附体,以致恐惧的吉斯伯恩把她赶出家门,再也没几个人敢接近露西。当布丽奇特最后得知露西是她的外孙女时,毅然投身克拉雷会做苦行修女以身奉献,才使露西摆脱幽灵的纠缠。故事中的幽灵其实是露西母亲玛丽的化身,小说描写了露西与外婆布丽奇特首次会面的情况:
突然——一眨眼的功夫——幽灵出现了,就在露西身后,外形与露西相似得吓人,它跪了下来,姿势完全与布丽奇特一样,双手紧扣,似乎在顽皮地模仿布丽奇特双手紧扣忘我祈祷的样子。克拉克小姐惊呼起来——布丽奇特慢慢起身,眼睛死死盯着一边的幽灵:发出嘶嘶的喘息声,可怕的目光犹如磐石那样,毫无转移,然后冲向幽灵,却像我之前一样,只抓到一把空气。我们再也看不到它——它突然消失,就如同它突然出现一样,而布丽奇特还慢慢地继续张望,仿佛在注视渐渐褪去的影子。[4]
显然,布丽奇特看到的幽灵并不可怕,它让她想起自己的女儿玛丽。而此前吉斯伯恩看到的幽灵形象却是“邪恶的、令人生畏的”,让他想起了布丽奇特的诅咒。因为他欺骗、玩弄、利用了玛丽,迫使她投水自尽,他的心里有鬼。幽灵与诅咒都在向他讨回公道。
与前两篇小说不同,《灰发女郎》中描述的幽灵形象不是死去的鬼魅,而是活生生的人。一个原本年轻美丽的德国女子安娜,为了摆脱家人介绍给她的结婚对象而离家访友,邂逅法国男子杜赫勒先生并与之结婚,婚后即被丈夫禁锢于一个城堡内,与家人失去联系。一天夜晚,为了偷看被丈夫藏匿的娘家来信,她溜进丈夫的密室,却无意间发现丈夫是个暴徒、杀人犯。已经身怀有孕的安娜决定逃跑,她和乔装成男裁缝的女仆阿曼达扮作夫妻,四处躲避杜赫勒先生的追杀。为了逃避魔爪,她不得不用腐烂的胡桃壳染头发和脸庞,弄黑牙齿,甚至还磕掉一颗门牙。经过18个月的逃亡生涯,她的金发最后变成了灰发,红润的面庞也变成了死灰色,形容枯槁,被人称作灰发女郎。长期的恐惧使安娜身心憔悴,像漂泊不定的孤魂野鬼,整天怕见阳光,怕见人。她外表的变化折射出了她精神的崩溃,而这正是男性权力对女性身体控制和惩罚的结果。安娜的悲剧在于:她像许多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妇女一样,从小被教导把婚姻作为自己的职业,缺少女性自我意识,婚后成为丈夫的附属物,在丈夫的淫威之下,过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生活。
盖斯凯尔早就认识到,女性的屈从地位使她们在父权社会中集体失语,无处申诉自己的痛苦。她怀着深刻的同情与理解,试图借用幽灵——一种女性哥特式表达方式来表现女性内心深处的抗争,为她们鸣冤叫屈。
二、暴君:女性哥特中的强权者形象
除了幽灵,“暴君形象,是英国哥特小说常出现的人物形象类型之一。无疑,专横残暴、冷酷无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这类形象的共同性格特征”[5]131。
在盖斯凯尔笔下,《老保姆的故事》中的老福尼沃先生,“除了骄傲,最特别的就是喜欢音乐。他能弹奏几乎所有的乐器,但奇怪的是,音乐一点也没能使他的脾气缓和;他始终是个狂暴、严厉的老头,大家都说他的冷酷使他可怜的妻子心都碎了”[6]。作为一家之主,他得知小女儿私定终身后暴跳如雷,对她又骂又打,连她幼小的孩子也不放过。“然后,老主人召集所有家仆,用极其可怕的语言,赌咒发誓地告诉他们,他的女儿让他丢尽了脸,他已经把她和她的孩子赶出家门。如果有人胆敢伸手帮她,给她提供食物或住所的话,这个人将被他诅咒,灵魂永远升不了天。”[6]
在《克拉雷会苦行修女》中,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吉斯伯恩先生的形象与老福尼沃先生的形象如出一辙。他误把露西的幻影当作露西本人,不容露西争辩,大骂露西是骗子,不是他亲生的,甚至手持长鞭,一边指责露西,一边要抽打露西。对他来说,女儿只有服从于他,听命于他,才是他的天使,否则就是恶魔,必须得到惩戒。事实上,他从未真正爱过任何人,无论是妻子还是女儿,他爱的只有他自己。
《灰发女郎》中的暴君杜赫勒先生更为可怕,他表面上文质彬彬,追求安娜的时候对她大献殷勤,大加奉承,并不断送珠宝之类价值不菲的礼物,对安娜的父兄也毕恭毕敬。婚后,他立刻变了脸,郑重其事地向安娜宣布,不许她与娘家人多往来,让她必须听命于他。他把她作为笼中鸟囚禁于他的城堡中,安娜在给女儿的信中描述道:
“杜赫勒先生把我当作他珍爱的、收养的、宠爱的、放任的珍贵玩具或玩偶来对待,我很快发现自己或者似乎还有其他人,几乎无法改变这个男人的可怕意志,而我一开始认识他时,他看起来是那么柔弱无力,一点也不可能把他的意志强加给别人。我现在终于更多地了解了他那张脸,看到了某种高深莫测的情绪,由于某种我无法洞悉的原因,使他灰白的眼睛闪烁着暗淡的光,嘴唇上扬,精致的面颊有时变得惨白……我明白,杜赫勒先生以他自己的方式喜欢我——我敢说(因为他经常对我说过)——他为我的美貌而骄傲,但是他的妒忌和猜疑也很重,绝不会因我的愿望而改变,除非我的愿望与他的愿望一致。”[7]
当安娜发现他杀人的秘密而潜逃后,他终于露出狰狞的面目,一路追杀安娜,乃至误把和安娜同宿一间客栈、长得很像安娜的一位德国女士杀死在床上。后来,迫于生活压力,阿曼达冒险出卖杜赫勒送给安娜的一枚戒指,结果被杜赫勒先生发现,招来了杀身之祸。杜赫勒先生的所有恶行给安娜的心灵造成了严重创伤。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写道:“诚如特里威廉教授所指出的,实际上妇女是被关起来,在屋里被打来打去。”[8]590根据特里威廉所作的《英格兰史》,打老婆是男人的一种得到公认的权利;女儿拒不接受父母所选择的夫婿,就会被关起门来打而不会引起舆论的谴责。在父权社会中,家庭暴力的存在是男性霸权在婚姻家庭领域的集中体现。男性凭借他们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中的强权地位,在家中发号施令,作威作福。他们自私自利,任意欺辱女性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盖斯凯尔在父权文学传统所允许的范围内,利用哥特小说人物谱系特征,通过塑造一系列家庭专制的暴君形象,揭示了父权统治是造成女性可悲命运的根源。
三、母亲:女性哥特中的失语者形象
母女关系是女性主义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养育了几个女儿的盖斯凯尔关注的话题。“著名法国哲学家及女权主义理论家露丝·伊里加蕾在《思考差异》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弗洛伊德坚持认为女儿必须离开母亲才能进入欲望和父亲律法之所是有目的的,那就是建立一个男人自己的文化,而女孩为了成为女人则必须把自己交给文化,尤其是爱的文化,这个爱就是冥王哈得斯,为此她必须忘记童年和母亲。‘拐走珀耳塞福涅是父权制的原罪…… 它摧毁了母女关系这一最体现关爱和丰饶的纽带’。”[9]116
在《老保姆的故事》中,老保姆海斯特亲手抚育了罗斯蒙德小姐,犹如母亲般地疼爱这个孩子。看着她一天天长大,就怕她有个三长两短。在罗斯蒙德失踪一次之后,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她再也不敢离开罗斯蒙德。当幽灵再次来临时,海斯特死死抱着罗斯蒙德不放手。这里,幽灵对罗斯蒙德的引诱暗含着女孩长大后面临的婚姻诱惑,她迟早会挣脱母亲的怀抱,追随一个男人而离开自己的家。
母亲——特别是受到过男人欺骗和伤害的母亲,会出于对女儿的爱而试图保护女儿免遭与自己同样的厄运,而她的过度保护常常激起女儿的反抗。在《克拉雷会苦行修女》中,布丽奇特与女儿玛丽的关系就是如此。“她(玛丽)和她母亲太相像了,彼此很难达成一致。她们之间出现了疯狂的争吵,然后是更疯狂的和解。有时,她们在盛怒之下甚至要互相捅刀子;更多的时候,她们——特别是布丽奇特——更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布丽奇特对女儿的爱很深,超乎她女儿的想象,否则,我想她女儿不会厌倦在家的生活而请她的女主人为她找一份去海外做女佣的差使。”[4]玛丽怀揣梦想去了欧洲大陆,她说等自己安定后就回来接母亲。布丽奇特虽然不愿意让她走,但也没有办法阻止她。结果,玛丽步母亲的后尘被男人骗了。当她的女儿露西长大后,也将坠入爱河。这时,玛丽的幽灵附身于露西,不仅让露西看到她父亲的本质,还让爱露西的男人在她身上同时看到了天使与恶魔的影子望而却步。
同样,《灰发女郎》中的安娜坚决反对女儿厄休拉的婚事,她临终前给女儿留下了一封信,向女儿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最后告诉她:“你的爱人,你只知道他叫勒布伦,是个法国艺术家,而他昨天却告诉了我他的真名叫莫里斯普瓦西,因为嗜血的共和党人觉得这个姓氏太贵族化,才放弃了这个姓氏。”[7]她由此揭穿了勒布伦的父亲是被厄休拉的生父杜赫勒先生所杀的秘密,同时提醒女儿,其实她与当年的自己一样不了解结婚的对象,存在上当受骗的危险。
不少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社会中的母亲是软弱无能的失语者,她们没有自己的语言,只能处于沉默的被动状态中,无法向女儿传递自己的经验。她们若借用男性语言,结果往往会复制男性的价值体系,伤害母女之间的关系。《老保姆的故事》中的罗斯蒙德和福尼沃小姐、《克拉雷会苦行修女》中的露西和《灰发女郎》中的安娜都是自幼丧母,无法从母亲那里获得经验指导;玛丽的母亲布丽奇特也是失语的。伊里加蕾认为,母女关系所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母亲缺乏主体性造成的,而母亲主体性的缺失又导致女儿主体性的缺失。她强调女性主体性的建构,要求建立一个女性话语体系,提倡女性之间的积极沟通。盖斯凯尔笔下的安娜就试图通过书信向女儿讲述自己的经验,让女儿走进她的内心世界,看到她的感情和内心世界的痛苦,启发女儿对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进行思考,可见盖斯凯尔希望女性用笔书写和传承女性经验,进而逐步颠覆男权社会秩序。
过去,“即使那些非常欣赏盖斯凯尔作品的评论家,如埃德加·怀特、阿瑟·波拉德、玛格丽特·甘兹、安加斯·艾森,都把盖斯凯尔看作次要的传统的女性化的富有魅力的作家;似乎大家都认为盖斯凯尔作为妻子和母亲,生活很快乐,她毫无怨言地接受了传统文化所赋予她的性别角色”[10]183。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盖斯凯尔因为出身于唯一神教信徒家庭,父母亲友都比较开明,给予她良好的教育,她丈夫也很支持她的写作事业,她养育了四个女儿,靠自己的创作收入买了一栋房子,但是她更多地目睹了社会中各个阶层妇女的不幸婚姻生活以及她们在社会中的卑微地位,她为自己的女儿们担忧,更为无数的姐妹们不平,只是在男权社会女性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所说:“大多数成功的女作家经常把她们对女性的关注导向隐秘的或者最不明显的角落。为了使她们的文学作品能被阅读和欣赏,这些女性创造了隐蔽的手段,即藏在更容易看到的东西或者说作品的‘公开’内容之内或之后的方法,尽管她们主要关注的女性问题会被忽视。”[11]72“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女性写作与某种文学体裁之间的亲疏程度多取决于‘众多物质和意识形态因素——创作环境、出版业的变迁、批评界的反应、某些特定形式的性别关联’等极其复杂、变幻不定的合力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女作家的声音及其选择的载体只有在符合特定时代的主流性别观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认可,否则便会被认定缺乏‘女性气质’而招来指责。”[12]74所以,盖斯凯尔会以当时流行的哥特文体,借用父权社会建构的一套话语编码,如女巫、恶棍、幽灵、附体、关押、囚禁、怪异等,颠覆性别二元对立中所谓男性的理性和力量与女性的软弱和不可理喻,隐蔽地表达女性主义的思考,批判菲勒司逻各斯中心主义。
[1]MOERS E.Literary wome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90.
[2]WALLACE D.Uncanny stories:the ghost story as female gothic[J].Gothic studies,2004(6):57-68.
[3]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42-46.
[4]GASKELL E.The poor clare(1856)[M/OL][2013-05-12].http://ebooks.adelaide.edu.au/g/gaskell/elizabeth/poor/chapter1.html/
[5]李伟昉.黑色经典:英国哥特小说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31.
[6]GASKELL E.The old nurse′s story(1852)[M/OL].[2013-05-12].http://ebooks.adelaide.edu.au/g/gaskell/elizabeth/nurse/.
[7]GASKELL E.The grey woman(1861)[M/OL].[2013-05-12].http://ebooks.adelaide.edu.au/g/gaskell/elizabeth/grey/chapter1.html.
[8]WOOLF V.Selected works of virginia woolf[M].Hertfordshire: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2005:590.
[9]邱小轻.主体间性与母女关系的社会伦理建构[J].求索,2010(8):116-118.
[10]REDDY M.Gaskell′s“the grey woman”:a feminist palimpsest[J].The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1985(2):183-193.
[11]GILBERT S&GUBAR S.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72.
[12]林斌.西方女性哥特研究——兼论女权主义性别与体裁理论[J].外国语,2005(2):70-75.
(责任编辑:喻世华)
On Images of Ghosts,Tyrants and Mothers in Mrs.Gaskell′s Gothic Stories
WU Qing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Jiangsu 212013,China)
Elizabeth Gaskell,a British women writer in Victorian Age,created images like suffering ghosts,tyrannic men,and worrying mothers in her short Gothic stories The Old Nurse′s Story,The Poor Clare,and The Grey Woman in order to express her concern and reflections on women′s fate.After a study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stor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female Gothic,it is quite clear that the long neglected short stories by Elizabeth Gaskell actually show the author′s strong criticism on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great support of feminism.
female Gothic;Elizabeth Gaskell;feminism
I106.4
A
1673-0453(2014)03-0038-05
2014-03-03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1SJD750031)“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作品研究”的阶段成果
吴庆宏(1969—),女,江苏镇江人,江苏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