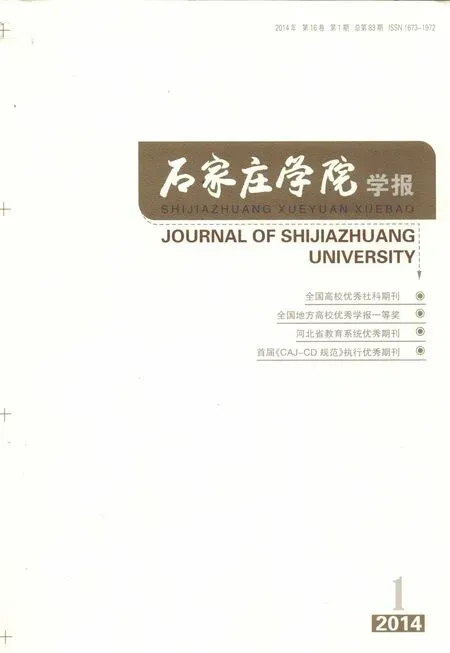现代中国乡愁的开拓与建构
——论《巨流河》对中国文学乡愁母题的创新
许玉庆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基础部,山东 济南 250200)
现代中国乡愁的开拓与建构
——论《巨流河》对中国文学乡愁母题的创新
许玉庆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基础部,山东 济南 250200)
乡愁是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学中人们赋予了她独特的美学特质。台湾学者齐邦媛的《巨流河》通过一家人在一个世纪中的漂泊、奋斗历程,创造了不同于以往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愁叙事,对现代民族国家、精神家园和现代人格进行了开拓创新,体现出鲜明的独创性特质。
现代乡愁;精神家园;民族国家;现代人格
在中外文学史上,乡愁是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学,对乡愁的书写从未中断过。“乡愁往往是自我放逐者或被放逐者对家园的铭心刻骨的思念,对于家园与国家富强、安危的期望,是身系国家命运的巨大的乡愁。或是由于战祸而失去家园、辗转流离、引起离散者对家国命运的无尽的焦灼和忧虑,是对可望而不可即的乡关何处的无奈的慨叹! ”[1]256在中国文学中,从先秦时代的《诗经》《离骚》到盛唐时期李杜的诗歌,到现代文学中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以及台湾作家白先勇、萧丽红的小说,乡愁以其独特的审美意蕴成为文学世界的重镇。自20世纪以来,乡愁更是成为台湾文学化不开的情结。百年的隔海相望,半个世纪的牵挂。故园之恋、亲人之思,成为萦绕在两岸儿女心头挥之不去的情思。余光中、白先勇、陈映真等笔下的乡愁,以各自独特的审美意味在台湾文学中流淌。当下文学中,这种故土之思、家园之恋已经大大超越了情感范畴,成为一种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著名台湾学者齐邦媛的自传文学《巨流河》①齐邦媛《巨流河》,生活·新知·读书三联出版社2011年版,文中未标注之文献均出于此。,自面世以来引起两岸三地出版界、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热议。细细读来,处处感受到该作品对传统乡愁书写的突破与建构。作家以独特的视角,通过一家人在一个世纪的漂泊、奋斗历程,创造了不同于以往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愁叙事,体现出鲜明的独创性特质。这一独创性集中体现为:现代乡愁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民族国家、对现代人的精神家园和现代人格的开拓与建构。
一、漂泊之痛: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与民族国家建构
故土之恋乃人之本性,却往往打上了民族、时代、个体的烙印。遥望乡愁的文学星空,农耕文明时代的乡愁主要体现为一种朴素的情感遥寄,像《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对亲人的思念和个人孤独的流露;再高一些层次的乡愁则是一种对形而上问题的思考,如《天净沙·秋思》中流淌着漂泊者的人生迷惘。故国家园是漂泊者曾经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是每个人情感之旅远航的起点。远行者对家园的回归以及回归不得的忧伤,成为文学反复咏唱的主题。正是这一复杂的情感,维系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家园的坚守和民族国家的凝聚力。齐邦媛的《巨流河》对这一情感进行了独特发掘和创新,通过对老一代知识分子齐世英、张伯苓、朱光潜以及年轻一代张大飞等人故国原乡的书写,传达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全新的乡愁内涵:将乡愁穿越传统体验内涵,化为现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也就是“将爱乡观念扩大到国家民族观念”。
首先,现代乡愁源自于其特有的中国现代文化语境。对于20世纪初那些身处民族国家危难中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乡愁无疑有着更为复杂的思想情感内涵。他们在异国他乡奔走焦灼,经历了太多以往任何时代漂泊者所不曾有过的辛酸苦难,承担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艰巨的民族重任。具体而言,他们的乡愁往往伴随着种种救国救民的梦想。教育救国是他们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为此他们身体力行,无怨无悔。面对民族危亡的现实处境,齐世英及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心怀壮志,去国怀乡,到异邦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应该提及的是,这与古代士人求取功名、撇家舍业的漂泊截然不同。这是一种情系家园、心系民族命运、建构现代中国文明的求道之旅。齐世英先后到过日本、德国、美国等地,以期探索拯救民族之道。“那十九岁男子,在广大的世界,纵情于书籍、思想,参与青年人的社团、活动……”现代性的焦虑让青年齐世英的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激情,对故土的思恋、对家人的眷顾与对理想的追求融为一体,悄悄地激活了其心中萌动的教育救国的种子。他企图以此来重新照亮那片冰冷的土地。“回去办教育,我美丽苍茫的故乡啊!我一定要拼命练好一身本事,用最理性的方式回去办教育……我今日所学所知,终有一天会让我报答你的养育之恩。”然而,这种梦想在现实中国又是一条怎样艰辛的征途!
其次,寻求教育救国对国民精神的重建是振兴民族国家力量之维。理想的具体实施在这一代人身上,主要体现为创办现代学校和传播现代思想。回到家乡后,齐世英在东北军将领郭松龄的帮助下创办了同泽中学,践行教育兴邦之梦。但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注定这是一条困境重重、荆棘丛生的路。最终因郭松龄军事失利、惨遭杀害,齐世英及同仁被迫逃离家园。可是,这一次次的失利并没有改变他的救国信念。当东三省沦陷后,齐世英奔忙于南京和北京之间:在北京筹建中山中学,为东北流亡学生提供生活和学习帮助,为沦陷的故乡培养后备建设人才;在南京收留东三省的流亡子弟,为他们提供饭菜,给他们以家的温暖;南京失陷后,他多方联络,借军车、房舍、船只,带领所有流亡学生从南京辗转武汉、湖南、桂林到达重庆。在迁徙、轰炸、没有校舍等困境中,齐世英为东北学子们硬是争取到了学习、成才的种种便利。
除了齐世英之外,书中还记述了像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武汉大学朱光潜等老一代学者形象,读后令人难以忘怀。他们力图通过现代教育为民族国家的未来打造精神支柱,寻求图强之路。“念国家极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这样的羞耻使他深受刺激,更因为看到怠惰无知的一般民众,既无纪律和敬业精神也不知国难当头,故思索唯一能振作民心的只有教育——教现代知识,教爱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使命感促使齐世英走遍欧美,促使张伯苓在功成名就后仍执意去美国求学。在此,乡愁之痛已经转化成为另一种思恋,化作一种振兴民族国家的动力。薪火相传,这种精神也通过他们传递给了年轻一代。齐邦媛在回忆张伯苓校长时写道:“他说的话,我们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数万学生都深深记得,在各自的领域传他的薪火,永恒不灭。 ”
创办现代教育的同时,齐世英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还采用了另一种形式来传播西方现代文化——出版发行书刊,以拓展国民的视野。齐世英投身于书刊编辑出版,将西方各种现代文化书刊引入中国。在抗战时期的重庆,齐世英主持《时与潮》杂志的编辑,向处于抗战中的全国人民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许多人说那是水深火热的战线后面的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家国之恋,成为齐世英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斩不断的情思。而教育救国则是他们无可替代的信仰,是乡愁的一种现代内涵。
第三,特殊的时代语境造就了现代知识者在逃离家园时秉持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当然由于世界观和地域性因素,我们不否认书中有个别观点值得商榷。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两岸中华儿女都在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繁荣默默奉献。这一理念应该是不同于政治派系角逐的,是一种拯救民族家国的信仰。这种信念不为外力所诱惑,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为之付出一生。体现在齐世英身上,他是一位有着强烈政治思想观的践行者,更是一位有着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民族战士。“我父亲和他年轻的朋友们忙着向老天爷求取时间(buying time)推动各种加强国力的现代化建设,因为他们知道日本军部正加紧侵略的步伐。”尽管政治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他们在推动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的问题上是相同的。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不可避免地要同既得利益者发生冲突,甚至可能导致自己陷入争斗的漩涡。这在无形之中成为人生的一个悖论。青年时代的齐世英就极力反对军阀混战,但为了消除这种军阀割据的现状,他又参与了郭松林反对张作霖的军事行动。“故乡沃野千里,农耕缺人,而青年官兵伤亡异乡,遗族处境悲惨,实在应停止征战,教育生息。”郭松龄兵变失利后,齐世英逃亡异国他乡,后来又加入国民党。但这一做法却不是为了投奔某个人,纯粹是为了信仰。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他冒着巨大的危险潜回东北腹地,去解救那些身陷困境的抗日同胞;到了台湾后,为了争取自由和国民尊严,他公然抵抗蒋介石的独裁,结果被开除“党籍”。“以这种方式离开了国民党,在我父亲那时可以说是一种解脱。”由此可以看出,其所践行的现代思想观念,更多的是对故乡、对民族前途独立思考的产物。
当故土沦陷、民族危亡之际,将个人生死系于整个民族的情感就是一种新的乡愁。在此,乡愁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现代性的思考。这一代人身逢乱世却不绝望不徘徊,而是以一己之身在漂泊的人生旅途上默默为故国家园焦虑、奉献,道出了现代知识者对乡愁的体认和独特认知。正如王德威所言:“乱世出英雄,但成败之外,又有几人终其一生能保有‘温和’与‘洁净’?这是《巨流河》反思历史与生命的基调。 ”[2]380
二、自己的园地:永恒的忧思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建构
在哲学层面上,乡愁是一种对人类精神家园的皈依。思乡总是伴有一定的寄托物,但是归根结底是一种精神的回归。在齐邦媛的乡愁里,既有着父辈情思的传承又有着自身的独特感悟。她继承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家国意识,力求以教育变革脚下的这片土地,将求学、办教育、建设现代文化作为其一生之目标,探索出一条现代知识女性所特有的人生之路。论及此,我们不得不回首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其中,不难发现一个这样的尴尬: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女性,虽然为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不断作出各种努力,但是很多理念却难以支撑起她们的精神世界,进而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其中不乏如冰心、林徽因等这样的新女性典范,但更多的知识女性却是在经历了启蒙的觉醒后,不得不面临着来自各个层面的压力,最终回归到家庭和传统中,继续过着此前鄙视过的生活。而齐邦媛却边咀嚼乡愁边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以个人的独特经历完成了个体精神家园的建构。
首先,独特的成长经历造就了齐邦媛特有的现代意识。一个人的成长与其生活的环境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齐邦媛而言更是如此。“我出生在多难的年代,终身在漂流中度过,没有可归的田园,只有歌声中的故乡。幼年听母亲幽怨地唱《苏武牧羊》,二十年后,到了万里外没有雪地冰天的亚热带台湾,在距北回归线只有百里的台中,她竟然在我儿子摇篮旁唱 ‘……苏武牧羊北海边……’”“我生长到二十岁之前,曾从辽河到长江,溯岷江到大渡河,抗战八年,我的故乡仍在歌声里。”书中详细讲述了作家儿时别离故土、颠沛流离的岁月。她出生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巨流河畔,从儿时起自己的命运就和故土、民族系于一体。尚未出生时,年轻有为的父亲就开始为拯救民族危亡而辗转于欧、美、日等国,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后来,作家追随父亲,跟着母亲离开了故土,踏上了漫漫漂泊之路。在北平、南京、天津、武汉、桂林、重庆、上海等地,齐邦媛阅尽了人间沧桑,遭遇到种种家国的灾难和不幸。“那些凄厉的哭喊声在许多无寐之夜震荡,成为我对国家民族,渐渐由文学的阅读扩及全人类悲悯的起点。”这一独特的人生经历深刻影响了齐邦媛世界观的建构,以至于她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着独特的理解。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民族的灾难、家庭的漂泊和个人的生活遭际成为现代知识者必不可少的体验。这种乡愁不同于传统的漂泊之痛,已经化为一种现代性的焦虑。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愁是齐邦媛成长为一名现代女性、一名有着独立意识的现代人的重要文化构成。
其次,现代人格建构的动力源自其所接受的现代文化教育。她从小接受到新式教育,铸就了现代人格的良好底蕴。在家中,其父受过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浸染,有着独立的现代人格诉求,因而在儿女教育方面注重培养他们的现代世界观。身为政府官员,齐世英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公私分明:“晚上回家他说,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务车上学,公务信纸有机关头衔的,我们也绝不可用。一则须知公私分明,再则小孩子不可以养成炫耀的心理。”因此,在重庆时学校尽管离家很近,齐邦媛还是坚持按照南开中学要求住校。生活上的严格要求,对齐邦媛现代人格的形成无疑有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在学业上,齐邦媛接受了南开中学的良好教育,后来又追从朱光潜、吴宓、胡适、钱穆等现代学术大师作专业训练和学术探究,为后来的学术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最敬爱的孟志荪老师和其他老师,无论学识和风度都是很好的典范。而在武汉大学,朱光潜老师不仅以高水准的授业,且在我感情困顿之时为我解惑,使我一生有一个不易撼动的目标。”特别是文学教育,对现代人格的启迪和引导是不容忽视的。“文学教育帮助我更客观、深层认识人间悲苦与活着的意义。”“文学能给人以温暖,让人理解并同情他人的痛苦,叫人学会容忍。”[3]和谐向上的家庭生活和厚重的学术氛围让齐邦媛对社会、人生具备了现代性的认知,给予了她在后来学术研究中战胜重重阻挠而奋力前行的勇气和力量。
一路走来,乡愁无时无刻不笼罩着她生活的角角落落。在浓浓的乡愁中,她将其与自我成长进行了有机结合。“这是一种涉及人的生存的乡愁,是人的精神飘零无依、栖居艰辛的乡愁了。”[1]258人生在乡愁这坛米酒中酿制发酵,自然会塑造出一个对故土家园有着深厚情感的别样人生境界。
第三,精神家园的建构体现为事业与人生的有机结合。在家庭和事业问题上,作为女儿、妻子、母亲、老师、学者等,齐邦媛都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将它们巧妙地融合而非尖锐地对立,展示了一名现代知识女性的独特人生境界:将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做了“不同而并立”而非冲突性的对待。两个世界分别给她带来了世俗的快乐和精神的慰藉。作为妻子,齐邦媛积极支持丈夫干好事业。从台大到台中、立农学院、东海大学、中兴大学,齐邦媛追随丈夫工作变迁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工作地点;作为一位贤淑的母亲,齐邦媛继承了传统女性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耐心细致地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给予他们良好的教育。“那时的我,带着三个男孩,大的九岁,小的五岁,白天要上课,晚上备课,改作业,活得和陀螺一样,如果有祷告的时间,只祷告不要撞车,因为汽车和火车似乎都在灾祸的边缘疾驶。”家庭琐事并没有将她改造成一名职业家庭主妇,更没有导致她放弃现代知识女性的本色。她像父亲一样热爱教育事业,关心学术界的变革,并以骄人的成绩赢得了世人的青睐。
个体精神家园的建构,带给齐邦媛的是种种难以言传的独特体验。这些是世俗生活所难以替代的。“这段苦读时间,我最大的世界是那扇大玻璃窗外的天空和变化万千的浮云;台湾的消息来自家信和七天前的《中央日报》航空版,开花城那间陋室是我一生住过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在职业生涯中,无论是在台中还是在台大,她都以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和崇高的敬业精神赢得了学生,赢得了同仁。教育振兴民族的理念在她身上得以传承。但与父亲不同的是,齐邦媛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而是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向海外译介台湾文学、传播中国文化中去。她编选了第一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和台湾普及教育国文教科书系,主持翻译西方文化经典,以文学作为媒介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平台。
齐邦媛通过自己的努力 “寻找到了自己的园子”。这“自己的园子”里开满了自己精心栽培的精神花朵,是其对现代人精神家园的独特思考和建构性尝试。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齐邦媛认为教书不仅是一份传播知识的工作,而且是一种自我心灵的皈依。“对我而言,教书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传递,我将所读、所思、所想与听我说话的人分享,教室聚散之外,另有深意。他们,都是我心灵的后裔。”对于学术理想,齐邦媛认为求学和学术研究是一种无以替代的幸福。“自从一月八日我坐在那窗口之后,人们从草坡上来总看见我俯首读书或打字,我自己最清楚地知道,每一日都是从妻职母职中偷身得来!”读书求学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精神小屋。如果一个人仅仅是把教书、写作当做一份职业,而不是视为现代人精神的天空,那么她的心灵后裔或家园是无从谈起的。在此,故土的思恋、家国的振兴则是这精神家园的最基本的色彩。“有了这种心灵安顿中生命展开的追求,传统的家园观念有了无比开阔的空间,‘乡愁’也有了生命再创造的喜悦。 ”[4]
三、现代乡愁美学:“双重的剥离”与现代人格的确立
乡愁是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又是一个发展的文学母题。古往今来,人们对乡愁的体验不断发掘出新的思想认知和情感体验,因而让这一文学母题常写常新。或是凄凉,或是心痛,或是幽怨,或是期待……这一文学母题的美学内涵不断得以丰富得以拓展。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农耕文明烛照下的“叶落归根”是一代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情感羁绊,自然也演绎出了一场场说不尽道不明的感人至深的人间悲喜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几千年来一直处于近似静止状态的农耕社会中,乡愁主要还是体现为一种单纯的思乡之情。在《诗经》《楚辞》《古诗》等诗词歌赋中,我们早已久违了这种情感。自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兴起,特别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侵入蔓延,乡愁内涵在一代代文学家的努力下拥有了更多的情感内涵。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形式的时空变化上,更体现在作家对乡愁的独特感知层面。《巨流河》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关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部作品发掘了现代乡愁的美学特质。
首先,现代乡愁在情感体验上是一种“双重的剥离”。现代乡愁不在于作家对其书写得多么深刻,多么动人,多么痛楚,而在于其独特的情感感知。一般情况而言,历史上任一地域的开拓者永远是一群孤苦无依的离乡人。乡愁在这些人身上是一种难以磨灭的煎熬,所以有人将乡愁比做“怀乡病”。但是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的加剧,乡愁则已经变成更多人情感的基本构成。在迁徙地生活很久之后,离乡者会发现自己在心灵上始终无法与脚下这片土地完整地融合。原乡成为离乡者内心深处一个难以解开的结。“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五十年在台湾,仍是个‘外省’人,像那艘永远回不了家的船(The Flying Dutchman),在海浪间望着回不去的土地。”其实,这不仅仅是属于齐邦媛的,而是漂泊者命定的困惑。同许多大陆漂泊到台湾的现代知识分子一样,齐邦媛们注定是一群永远回不了家的“外省人”。所以,台湾文学一度出现了大批外省人形象,成为文学史上难以抹去的记忆。这里不是自己心灵的家园,而那个心中怀念的家在现实中同样也不再属于自己。就像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无知》中所展示的那个难题:“曾经与我们那么亲近的‘故乡’正随着时间日渐疏远,而新的生活又因生疏而不能容留我们漂泊的灵魂。”[5]现代社会正以加速度的方式运转,因而人们往往来不及仔细品味远去的故乡,在生活的表层做着惯性的滑翔,内心念念不忘的是对故乡的眷恋。等着离乡者返回故园才发现,故土早已经面目全非了。这种“双重的陌生”感无疑增加了离乡者的前所未有过的孤独和困顿。
但是《巨流河》中这种“双重的剥离”,与其他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乡愁书写有着很大不同。这是一种“空间剥离而文化同质”的乡愁。因此无论是走到哪里,怀乡者尽管面临精神家园迷失的困境,但在情感和心理上依然能够执着于民族文化和梦想的建构。例如书中的东北流亡青年张大飞,怀着国仇家恨逃亡到关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齐世英一家,从而获得了“家”的温暖,并在与日寇的决战中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齐邦媛到达台湾后,倾心于自己所喜爱的教育和文化传播事业,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即便是到美国访学,齐邦媛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中时刻渴盼着的却是能够回到在台湾的“家”中。“而我多年来,当然也曾停下来自问:教学、评论、翻译、做交流工作,如此为人作嫁,忙碌半生,所为何来?但是每停下来,总是听到一些鼓声,远远近近的鼓声似在召我前去,或者那仍是我童年的愿望?在长沙抗日游行中,即使那巨大的鼓是由友伴背着的,但我仍以细瘦的右臂,敲击游行的大鼓……”台岛虽然不是自己儿时的故土,却是自己的居所、自己的家园,那里有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同胞、自己热爱的土地。所以说,齐邦媛一直在努力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
其次,现代乡愁蕴含着现代人格和现代情感的确立。以往的乡愁书写更多的是对乡土文化的依恋,很难突破传统美学的阈限。但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特别是现代人格意识的凸显,乡愁的美学内涵有了崭新的拓展。在《巨流河》中,齐世英、齐邦媛父女以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在乡愁之旅中。齐世英的一生就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探索与建构现代人格的一生。他在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同时,又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无论是早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主动去国离乡,还是后来因为战争、政治原因而离开大陆,浓重的乡愁非但没有让他像很多漂泊者那样沉郁落魄,反而激发了他寻求人格独立的动力。例如,他在年轻时加入国民党不是为了谋得高官厚禄,而是追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到了台湾后,他与蒋介石发生矛盾被开除党籍,同样是为了捍卫民主自由的理念。这一独立人格是以自我对外部世界的独特思考而形成的,不同于既往乡愁书写中思乡者对某一既有观念的坚守。现代人格的美学特质在张伯苓、朱光潜、钱穆等学者身上,同样有着不同的体现。张伯苓虽人过不惑之年,却依然坚持到美国读书研究现代教育,回国创办南开中学;朱光潜在战火中坚守讲坛,为国家建设培育英才。现代人格和现代情感在乡愁中释放着自己特有的温馨和力度。
齐邦媛以一家人漂泊的经历探究了现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辛酸,为现代乡愁书写作出了新的探索。书中处处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建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浓厚的家国意识,同根而生的“乡愁”实现了维系整个民族血脉的永不破灭的奇迹。正如齐邦媛在一次采访中所言:“我大半生都在台湾,但我早年生活在大陆,那里才是我的根。所以,在台湾,有时我会有没根的感觉。”[3]
[1]曾繁仁.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
[2]齐邦媛.巨流河[M].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出版社,2011.
[3]傅小平.《巨流河》是我一生的皈依[N].文学报,2011-07-07.
[5]黄万华.乡愁是一种美学 [J].广东社会科学,2007,(4):146-152.
[6]陈超.“乡愁”的当代阐释与意蕴嬗变[J].当代文坛,2011,(2):78.
(责任编辑 周亚红)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Modern Nostalgia:Innovation of the Chinese Nostalgia Theme in The Juliu River
XU Yu-qing
(Department of Basic Courses,Shan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Tourism,Jinan,Shandong 250200,China)
Nostalgia is an eternal literary theme.It is given some unique aesthetic qualities in different ethnic literature at different times.The Juliu River by Prof.Qi Bangyuan in Taiwan creates the nostalgia narrative,unlike the previous,by telling her family’s wandering and struggling in the last century.It reflects the important quality of originality that renews the modern nation state,spiritual home and modern personality.
modern nostalgia;spiritual home;nation state;modern personality
I206
:A
:1673-1972(2014)01-0076-06
2013-09-30
许玉庆(1972-),男,山东济南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