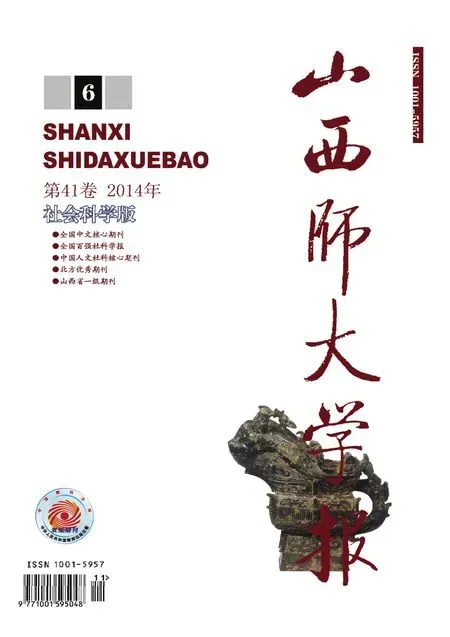明代情性思潮下的女性文学嬗变
刘 士 义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明代情性思潮萌芽于明初文人对“情”与“理”的哲学探讨,并发展为文学与哲学领域的人性启蒙运动。明人情性启蒙运动的实质在于通过对传统两性关系及女性文化的伦理改革,建立人性解放的法理与实践基础。然而,由于传统保守势力对伦理改革的强力排抵,情性启蒙运动的锋芒不得不转向了受宗法约束较为松懈的狭邪世界。情性启蒙运动的实绩反映在文学领域就突出地表现为由世情文学向女性文学及狭邪文学过渡的文学嬗变。
一、明代情性哲学的世俗化演变
笼统而论,一种思潮或文化的产生、发展与消亡,大而言之,与传统社会之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小而言之,与精英士族的鼓吹与揄扬、市民阶层之生活实践关系紧密。经过明初近百年的社会积淀,明中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大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受城市经济的发展与浮靡社会风气的影响,精英士族与市民阶层合力推动了启蒙思潮的发展。这一点足可以总结明代情性思潮产生与发展的革新轨迹。
明代中后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城市繁盛,刺激了商贾势力与市民阶层的强势增长。受新兴财势阶层的浮靡生活方式之影响,在市民社会中逐渐形成一种开放、自由、纵情、适性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逐渐侵袭至文人群体,进而影响到精英士族集团。另一方面,受社会浮靡风气的影响,明初统治者所推崇的宋元理学在精英士族中逐渐成式微之势。宋元理学的式微造成了精英士族的思想真空,因此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哲学体系来诠释与填补。对启蒙先哲来说,这是一场产生于哲学与思想界的破与立的持久革新,因此他们必须在儒学前贤的哲学命题中寻找破与立的哲学基础。在儒学精英看来,人之存世的生命、修养与价值莫不与“情”“性”“理”“欲”诸命题相关,因此对于诸者之哲学探讨亦成为儒学体系的基本命题,亦成为明中叶精英士族进行思想革新的重要领域。
对于“情”“性”“理”“欲”之命题,明初大儒如宋濂、方孝儒、吴与弼、胡居仁辈,皆沿袭宋元理学之旧调,总言之不外乎“性善情恶”、“灭情复性”、“心统性情,性体情用”诸论调,并未形诸思想革新、人性觉醒之风潮。明人情性启蒙运动实发韧于明代中期兴起的文坛革新运动与哲学领域的阳明心学启蒙思潮。明初,理学家陈献章曾高举异帜,鼓吹“心”“性”与“情”“理”,并由此开启了明代理学由“理”学向“心”学转变的滥觞。以此为端,陈氏亦将心学引入诗文评注之中,“诗之发,率情为之,是亦不可苟也,不可伪也”[1]10,“故七情之发,发而为诗,虽匹夫匹妇,胸中自有全经”[1]1。由此亦开启了明代情性思潮之哲学与文学两大启蒙先锋。
于此之后,启蒙者在哲学领域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理学革命。王守仁承继白沙心学,以心为体,奠定了“情性合理”的哲学基础,从而为阳明后学进行情性世俗化实践扫平了障碍。阳明心学从起始即保持了鲜明的革新性,从王守仁的“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到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再至泰州后学杨复的“要晓得情也是性”,乃至明后期阳明心学讲学思潮之繁盛,*参阅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与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学林出版社 2004)。都反映了明代情性哲学向世俗生活侵渗的趋势。与此同时,李梦阳在文学领域承续发力,正式将哲学之“情”“性”思想引入诗文领域:“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真诗乃在民间。”[2]102无论是王守仁的心学革命,还是李梦阳的“真诗乃在民间”诗论,其实都反映了明代情性哲学世俗化的渐变过程。
精英士族在填补精神领域所产生的思想真空时,迫切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为来践行启蒙运动的实绩。社会新兴集团亦需要一种行之有效的理论来证明浮靡生活的合理性。于是在这个问题上,明代精英士族与新兴财势阶层达成了统一认识。在继承以往儒学先哲对“情”“性”等哲学命题探讨的基础上,明代启蒙者的关注视野逐渐从对自我人格的修持敬养转向了对世俗伦理、男女情爱的文化鼓吹,并由此导致明代启蒙运动由形而上之“情”“性”哲学转向形而下之人伦事理与世俗情爱,从而弱化了明人变革两性关系的阻力,亦促进了情性思潮的蔓延与普及。明代情性启蒙运动的实质是将形而上之“情”“性”与“理”“欲”之概念从哲学层面拉向世俗社会,并与明代中后期所兴起的市民思想相融合,进而形诸人性解放思潮。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场启蒙运动亦是明代启蒙知识分子从世俗社会寻找情性变革依据的有效实践。当明代启蒙者的情性哲学走向僵化状态时,必然会向世俗社会寻求通融与变通的革新手段。
哲学与文学领域的“情”“性”世俗化演变,在明中叶以后逐渐有交合的趋势。这也反映了明初启蒙思潮已从散漫的个体呼号转向集体自觉的理论实践。李贽是明中后期启蒙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一生与王畿、王艮、耿氏兄弟(耿定向、耿定理)、焦竑诸理学家有着密切的交往。这些交往对李贽后期“离经叛道”思想之形成有着密切关系。在与程朱理学家的论辩中,李贽提出了“童心”说, 强调知识分子在创作中要“绝假还真”,独抒己见;在生活中,肯定自我欲望的合理性,“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3]361。在政治中,提倡人人平等,“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主。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3]16—17。童心说的实质,在于打破程朱理学关于人之“情”“性”的神圣性,促进哲学与文学之“性”“情”向世俗生活转变。
李贽是明中叶情性启蒙运动的中坚人物,其上承阳明心学之革新传统,下启明后期重情文学之盛行,集理学、文学、史学之大成,推动了明代情性启蒙运动的实绩。重情尚性,崇实致用,融事理于世俗人欲之中,可谓李贽对情性思潮的一大功绩。于此以后,明代文人多继承李贽的方式,继续把形而上之情性哲学推向世俗领域。明后期情性启蒙运动蔚然成风,中间所出现之人物,如公安三袁(宗道、宏道、中道)辈高举性灵说,均深受其影响。如王之祚在《花镜隽声跋》中所论:
《花镜》行世必有呼之为情句者,噫!实性书。臣忠、子孝、夫义、妇节,生于性,实天下大有情人。臣不情不忠,子不情不孝,夫不情不义,妇不情不节,人情合天性,人情即天性。情于君臣者,载情于夫妇,情于父子者兼载之,正言反言规言寓言总括于无邪,一言在通,人自领之耳。……故与天下谈性,莫先与天下谭情。[4]
王之祚所论之“性”多有形而上之哲学意味,而所论之“情”则更倾向于世俗社会的人伦事理。王氏这段论述在于打通形而上的哲学之“性”与形而下的世俗之“情”的逻辑关系。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各尽其职,与世俗之情有着密切关系。正因为有世俗之情,所以才会有社会的整体和谐。如此一来,王氏便把形而上之哲学性理转化为形而下之人情事故,即“人情合天性,人情即天性”。王之祚所言之“人情即天性”,实际上反映了人文启蒙者将哲学之天理(天性)物化为世俗社会之情爱的哲学尝试。王之祚之情性哲学的世俗化倾向,可以充分地代表明代中后期明代文人的情性世俗化路程。
然而即使如此,王之祚所论之情性仍然未能完全褪尽理学气息,而真正的情性复兴大旗的高举则有待于冯梦龙等辈。冯梦龙出生于明万历二年,此时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辈,皆以重情尚性之学说声名于世,且冯氏成长之苏州,亦是经济繁荣、人杰地灵、情性思潮至为发达的地区。这些条件都为冯氏提出情教思想并践以实行奠定了基础。冯梦龙继承了前代启蒙者的情性世俗化理论,提出了情教思想并将其理论化、系统化,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实践。在冯梦龙的情教体系中,情是万物之本原,几乎褪尽了理学“性”“心”及“理”的抽象概念,这一点较之阳明后学更加具有世俗性的实践意义,即如其在《情史》中所论: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相环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5]]3
如果说,阳明后学是通过立教、授业、讲学等方式自上而下地进行心学之传播的话,那么冯梦龙则是以世俗社会的生存经验为基础,进行情教理论的完善与总结。由此而论,冯梦龙实质充当了世俗社会之生存方式的代言人。世俗社会的生存经验,往往比文人的哲学命题更加直接与实际,正因如此,冯氏才绕过了文人式的辩难、授业、讲学等方式,而利用了更加直接、有力的世俗文学来进行情性启蒙运动。
二、情性思潮之两性、女性及狭邪
对人性与物欲的肯定,是明代人性启蒙运动的主要目的,但是如何将这种理论加以实践执行,则是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在启蒙者看来,人性与情欲是一个抽象的儒学命题,必须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才能充分地展现其实践意义。受明中叶情性思潮影响,传统的“情”“性”“理”“欲”等哲学命题逐渐世俗化为日常生活中的人伦事理。而在人伦事理的诸多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人情男女关系。那么,明代情性思潮所宣扬的人性启蒙之理想,就很容易地蜕变为对男女情爱关系的鼓吹。因为在所有的世俗情爱关系中,男女情爱关系最为基础,亦最为引人注目。
对于世俗情欲与男女情爱之关系,方鼻甫在《青楼韵语》中论道:“人情莫甚于男女。”[6]正如冯梦龙编纂《情史》而“事专男女”,独以男女情事为长,都充分地反映了这种情性蜕变之事实:
六经皆以情教也。《易》尊夫妇,《诗》有《关雎》,《书》序嫔虞之文,《礼》谨聘奔之别,《春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岂求以情始于男女,凡民之所必开者,圣人亦因而导之,俾勿作于凉,于是疏注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汪然有余乎![5]3
在冯氏看来,情之最根本者在于男女之情,因此圣人作六经,以阐发两性关系之微妙。由万物之“泛情”而类化为人类之“性情”,再由人之“性情”进而论证“两性相悦”的合理建构,冯梦龙建立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论证方法,同时亦确立了明代情教普世思潮的基本理论构建。从明初的情性启蒙到冯氏的情教体系之建立,明代情性思潮体现了一条系统的发展轨迹:情性(哲学架构)——泛情(理论建构)——两性(具体方式)。
然而,传统社会的两性关系是个复杂的社会体系,包括家庭体系与家庭外体系。家庭体系中的两性关系包括男性与嫡妻、妾室、侍婢、家妓等关系,而家庭外关系则包括通过狭邪、偷情、通奸等方式而维持的两性关系。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群体往往依附于男性群体而表现为显著的次等地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传统两性关系的建构又聚焦于对女性群体及其文化的革新上。例如冯梦龙在编纂《情史》时,虽则“事专男女”,然而绝大篇幅仍集中在女性群体上,从而无意识地将男女情事之记录蜕变为女性事迹之整理。在明代繁夥的女性传记作品中,女性传主被有意识地划分为妻妾、侍婢、妓女等身份。这也从侧面折射出明人对于女性文化革新的过渡途径。
夫妻关系是维系家庭伦理关系的基础,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然而对于如何建构夫妻双方之地位,传统女教文化与启蒙知识分子则有着较大的区别。传统的女教文化强调女性应该秉持恭顺体性、怀有内敛之德。班昭在《女诫》七篇中,特以“卑弱第一”为首篇,“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7]。基于这种理念,传统家庭关系形成了独特的女性分工:嫡妻的作用在于持家与传衍子嗣;妾室则是家庭夫妻关系的补充;而侍婢与家妓的职责则在于对男性物质与精神方面的服侍。
实际上,尽管启蒙者采取了谨慎而渐缓的态度,传统家庭两性关系的革新仍然遭到社会保守势力的强力阻扼。在启蒙思想传播方面,李贽最终因异端思想而死于囹圄,何心隐因妖言倡道而被诛杀,冯梦龙亦因传播世俗情爱思想被官员训戒。而在婚姻自主、情爱自由等实践方面,情性启蒙者更是遭受保守势力的强力排抵。钱谦益娶名妓柳如是被世人报以砖块瓦砾,龚鼎孳与顾媚结合亦被杭人目为妖人,吴三桂与陈圆圆的情爱纠葛更成为世人唾骂的口实。
在儒学精英所制定的伦理体系中,传统社会形成了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两性关系,以维系于君臣民庶、尊贵低贱的等级制度。那么,当明代情性启蒙者宣扬女性之才学、艺术等人性因质以及平等、情爱、独立之两性关系时,就必然与明代官方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冲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人性启蒙者所引领的女性文化重塑运动是在与整个传统伦理体系进行持久的对抗。这也注定了情性启蒙者在改革传统两性关系时遭受社会与制度强力扼杀的历史必然。因此在启蒙运动遭受强烈的社会阻扼时,启蒙者不得不选择一种灵活的变通方式——狭邪——来解决两性关系变革所带来的社会排抵。
在启蒙者看来,狭邪文化与乐户制度是儒家伦理体系与政权执行的一个体制性的伦理漏洞。在儒学精英所设定的两性伦理秩序中,并没有对家庭之外的两性关系进行制度上的规划,而此亦为启蒙者对狭邪与乐户文化进行两性文化实践提供了理论上的契机。不仅如此,以富商巨贾为代表的社会新兴势力之出现与其纵情狭邪之生活方式的推波助澜,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的伦理体系,亦助长了启蒙者的两性变革信心。明代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商贾的地位远低于官宦士子,至明代中后期,因户籍界限而造成的文化壁垒逐渐趋于消融,士民商贾等户属的交往更趋于一种自然状态。商贾势力与文人集团的密切交往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群体的生活方式,从而将新兴的享乐、情爱、恣情等生活方式浸渍到文人群体。
对于苦于探索新型两性关系却找不到合理伦理阐释的知识分子来讲,青楼无疑是一个最佳的爱情实践场所。对于明代文人的理想伴侣,明人徐石麒在《凤凰台上忆吹箫5意中美人》一词中,有着明确的展现:
一点常凝,频年不遇,依稀有个卿卿。要兼花比色,选玉评声。那更温柔心性,挑剔尽、词赋丹青。堪怜是,高怀独绝,于我多情。盈盈。时来醉眼,自不屑凡媛,舞榭歌亭。有风流万种,拟向他倾。待阙鸳鸯社里,消受我、雾帐云屏。何时幸,销魂真个,笑眼双青。[8]1804
这种文人式的理想美人与明代青楼名妓的形象颇为契合。不仅如此,狭邪女子亦投其所好,刻意将自我与生存环境文人化、脱俗化。*明人卫咏在《悦容篇》中,通篇讨论了闺阁女子的生活营造,通过对美人的情性、居室环境、室内陈设、才艺诗画,以及美人的仪态姿容、修饰妆扮,阐述了明人对女性美的理解和认识。书中所论之设计恰恰可以印证明代青楼文化之营建,详情可参阅笔者《青楼文化折射下的文人与文学》(《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另一方面,青楼女妓与士人亦保持了一种相对平等和自由的关系,从而为士妓交往营造了一种浪漫情愫。对文人士子来说,青楼世界是一块脱离传统伦理制约的自由之地。被传统女学所禁止的歌舞声乐、妩媚多情等女性因质,在青楼世界中得到了尽情地展现。
明代情性思潮是启蒙知识分子尝试改变两性文化的一种实践与努力。然而由于传统保守势力的强力阻扼,启蒙知识分子不得不把改革的视角从两性关系转移到对女性文化的塑造上。即便如此,启蒙者仍然无法突破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伦理制约,而再一次把改革的锋芒从夫妻关系转移到对狭邪文化的营建中来。与之相随,在情性思潮的不断发展与突破中,启蒙者利用文学所进行的种种尝试与实践亦促进了明代两性及女性文学的发生与发展。
三、世情文学、女性文学及青楼文学之嬗变
如果说阳明后学所进行的讲学活动,是自上而下的哲学启蒙的话,那么文人书商所开展的通俗文学之整理与出版等活动,则是自下而上的宣扬与鼓吹。满足城市生活的需求、反映市民的理想与价值,则成了启蒙者的实践基础。明代情性思潮直接促发了情性文学的发展,而情性文学的实绩则在于对人性及情感的重新审视。在对抗“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束缚中,对人性及情感的再审视很容易蜕变为对两性及女性文化的重新诠释。这种文化再诠释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集中地表现为以两性关系与女性文化为主题的文学革新思潮。由此而来,随着明代情性启蒙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富有人文启蒙性质的文学革新思潮,便呈现出其独特的发展脉胳。
明代中期,当启蒙知识分子将情性文化的旗帜转向世俗生活时,由此亦开启了明代情性文学风潮的滥觞。情性文学发韧于表现男女情爱、世俗生活的世情文学,其中包括反映“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世情小说,亦包括以男女情爱为主体的民歌、戏曲、笔记等内容。可以说,明代情性文学发源于诗歌领域,李梦阳的“真诗乃在民间”理论,实质是知识分子向民间汲取文学变革依据的有效尝试,表明了精英士人对世俗情爱关系的认同与接受。李梦阳将真诗与明代民歌相联系,正是发现了民歌所秉赋的真情精神与所包涵的世俗情欲内容。李开先在《市井艳词序》中所论:
正德初,尚《山坡羊》,嘉靖初尚《锁南枝》。……二词哗于市井,虽儿女子初学言者,亦知歌之。但淫艳亵狎,不堪入耳,其声则然矣。语意则直出肺肝,不加雕刻,俱男女相与之情,虽君臣友朋,亦多有托此者,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风出谣口,真诗直在民间。[9]142
在李开先看来,民歌是底层社会的心声,多以赤裸裸的男女情爱为主题,反映了世俗社会的情爱状态与心理诉求。这一点,冯梦龙在其民歌集《山歌》中有着明确的认识:“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10]317,因为山歌之绝假纯真,才会有“淫艳亵狎”之“私情谱”,正是这种歌颂男女情爱之“私情谱”,才会有“借男女之真情同、发名教之伪药”的情性启蒙实践。
世情文学对两性关系的关注还体现在小说与戏曲中。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开启了以描写男女情爱关系、世俗浮靡生活为主体的文学题材。在《金瓶梅》故事中,西门庆与诸多妻妾、姬侍、婢女,乃至乐籍女妓、游娼水户等关系,折射出明代知识分子对新兴两性关系的深刻思索。在《金瓶梅》的影响下,明代世情小说大量出现,均以描写男女情事为主体,阐发情爱自由、性爱至上等思想,这些都可以视为世情文学对情性思潮传播的一大实绩。另一方面,以《如意君传》、《绣榻野史》为代表的艳情文学挟裹了大量的淫秽描写,这些赤裸裸的性爱描写逐渐浸淫到世情小说中,以性爱代替情爱、以感官刺激为目的,极大地刺激了世人对情爱、性爱的生理欲望,从而对根深蒂固的伦理秩序产生了巨大冲击。
情性理论在戏曲中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徐渭较早地将哲学情爱思想拓展到戏曲领域。在徐渭看来,人生为情爱所驱使,而戏曲之本质则在于“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弥远”[11]1269。徐渭对戏曲之情爱思想的推崇,在汤显祖的戏剧理论与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完善与实践。在《牡丹亭》的故事架构中,汤显祖的主情理论正是以两性情爱为基础,而生发出“世总是情”的泛情论与“一往而深”的至情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9]142。明代后期活跃于剧坛的作家与理论家,多受其情性思想的影响。情性理论在戏曲领域的流播与发展,亦促生了大量的以男女情爱为题材的剧作,以孟称舜、吴炳和阮大铖为代表的风情剧作家,均有大量的以男女情爱为主题的戏曲实践。
然而,汤显祖的至情论却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以《牡丹亭》为例,至情论的实践主体有意忽略了两性关系中的男性因质,过多地聚焦于以杜丽娘为代表的女性群体上。这种“阴盛阳衰”的故事构建,恰恰折射出启蒙知识分子改造两性关系的历史局限。*在明人所编纂的以两性关系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往往成为情爱故事的主体,决定两性关系的发展。以冯梦龙《情史》为例,此书虽冠以《情史》之名,以宣扬两性情教为宗旨,但是实际上其内容仍不脱女性色彩,且在全书诸多类目之中,以女性冠名的篇目达三分之二以上。事实上,当明代启蒙者大张旗鼓地在民歌、戏曲领域发起情性启蒙思潮时,保守势力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对情性思潮进行苛责与抵制。在儒家精英分子看来,男性是维系社会与政权稳定的主导力量。他们认为,过分地强调男女情爱关系必然导致男性主体地位的丧失,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失衡。正是在这种文化高压下,另一些启蒙分子避开了情性变革中的男性阻力,集中于女性文化的重塑运动,而女性文化重塑运动的实绩则集中体现在女性文学领域。
明代启蒙者对女性文学的整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对女性诗歌、词作、文赋等文学作品的整理与辑录;其二,对女性传记类作品的搜辑与编纂。实际上,两者都可视为明代文人“女史”思维的一种文化展现。*这种“女史”思维在明人所编纂的书籍中,每每见诸卷端,诸如田艺蘅以《诗女史》命名其编纂的女性诗集,而《亘史钞》、《绿窗女史》、《情史》诸女性史料汇编直以“史”概括全书主旨。不仅如此,女性文学编纂者亦以“女史”自居,如梅鼎祚在《青泥莲花记》各卷之末均有“女史氏”之评语;冯梦龙在《情史》中自署“詹詹外史”,并且在所叙故事之后多附有“女史”之按语。史学思维的建构在于通过对某一特定文化的记忆与传承,还原历史风貌,以古证今,从而建立起一套可行的理论范式。因此而论,明代启蒙文人因整理女性文化而表现出的女性史观,正体现了明人重建女性文化的实践与努力。而明人对女性文学的大规模整理活动,实质上反映了启蒙者对女性之“才艺与妇德”、“身份与才华”、“情感与婚姻”等问题的深刻思索。
明人对女性之才艺、妇德与身份等因素的思索,可以从女性诗文集的编纂过程中略窥一斑。嘉靖年间,张之象辑录女性诗作,以妇德为范式编纂《彤管新编》,“庶垂百代之规式,附风劝之本”[12]。这些都表现出明代文人对女性才艺观的重新审视。郦琥在其所编《姑苏新刻彤管遗篇》论道:“学行并茂,置诸首选;文优于行,取次列后;学富行秽,续为一集;别以孽妾文妓终焉,先德行而后文艺也。”[13]879郦琥以“学行并茂”、“文优于行”、“学富行秽”为编排顺序,其目的在于强调女性才艺的同时,亦明显地流露出强烈的说教意味。嘉靖三十六年,田艺蘅编选《诗女史》,打破了以往以宫阁闺淑、命妇贞女、婢女娼妇为分类的编次体列,表现出作者强烈的妇女平等意识,“乾坤异成,男女适敌。虽内外各正,职有攸司,而言德交修,才无偏废”。[14]
嘉靖年间出现的文学启蒙思想,经过数十年的酝酿,在万历中后期已发展为两性文学启蒙的自觉。在此背景下,明代文人的女性诗文整理运动逐渐形成高潮。然而,由于传统保守势力对启蒙思想的抵制与扼杀,亦使女性文学的发展面临着强大的社会阻力。一方面是传统势力对女性文化的强力阻扼,一方面是奢靡纵欲之社会风俗的推波助澜,因此而造成启蒙文学主体由传统女性群体逐渐局限于狭邪女性,并由此而滋生了大量以狭邪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首先,在狭邪诗歌整理方面,明代社会出现了繁夥的名妓诗歌选本。万历年间,杨慎整理《丽情集》,多有狭邪女子诗篇辑录在内。稍后,相继有梅鼎祚《青泥莲花记》,朱元亮、张梦徵合编之《青楼韵语》,均以青楼诗词编选为目的,专门辑录历代名妓小传及诗词。此外,亦包括诸多女性诗集选本中的女妓作品,如《众香词5数集》中的大量女妓词人等。与狭邪诗词之整理活动相对,明人对青楼女子的关注亦体现在对青楼女子传记的整理上。从署名王世贞的《艳异编》、《续艳异编》和吴大震的《广艳异编》,到潘之恒的《亘史钞》,秦淮寓客的《绿窗女史》,再至冯梦龙的《情史》,都以汇编的方式记录了大量的女妓传记。然而无论是女妓诗歌整理,还是女妓传记辑录,都体现了明代启蒙知识分子在面对强大社会阻力时所表现出来的革新勇气。
明代情性复兴运动交织着启蒙者对两性关系、女性文化与狭邪文化的多重审视。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与纲领,这场运动自始至终表现出一种非系统、百花齐放的状态。正因如此,才会生发出明代“两性——女性——狭邪”文学创作的自由、自觉之人文启蒙精神。
[1] (明)陈献章,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 (明)李梦阳.诗集自序[A].蔡景康.明代文论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3] 张建业.李贽文集:第七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明)王之祚.花镜隽声[M].明天启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5] (明)冯梦龙.情史[M].杭州:渐江古籍出版社,2011.
[6] (明)方悟编.青楼韵语广集[M].明崇祯四年刊本,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
[7] (清)王相.闺阁女四书集注[M].光绪庚子年刊,江荟宝文堂藏本.
[8] (明)徐石麟.美人词[A].全明词[C].北京:中华书局,2004.
[9] 蔡景康.明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0] (明)冯梦龙编纂,刘瑞明注解.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注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1] (明)徐渭.徐渭集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 (明)张之象编选,魏留耘校刻.彤管新编[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十三册[C].济南:齐鲁书社,1997.
[13] 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4] (明)田艺蘅.诗女史[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21册[C].济南:齐鲁书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