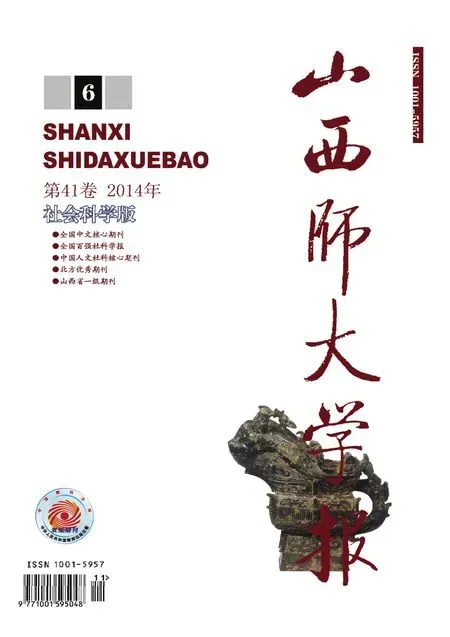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法律对孕妇人身权的保护
彭 炳 金
(天津师范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387)
中国古代法律非常重视对于孕妇生命权与身体健康权的保护,但是学术界对这一课题关注不够,至今还未见有人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就中国古代法律中对于孕妇生命健康权的保护问题做一梳理。
一、对孕妇生命权的保护
中国古代刑罚以笞、杖、徒、流、死五刑为主,对于孕妇执行死刑与笞、杖刑等会危及孕妇腹中胎儿的生命,所以,中国古代法律对于犯罪的孕妇执行死刑与笞、杖刑时有特殊的照顾,在中国古代很早就确立了孕妇不适用死刑的刑法原则。董仲舒《春秋繁露》记载,西周时期“法不刑有怀任新产,是月(正月)不杀。……法不刑有身怀任,是月不杀。”[1]192—194“任”通“妊”,这表明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确立了对于被判处死刑的怀孕妇女实行缓刑的法律原则。《后汉书》中有西汉末年对实行孕妇死刑缓刑的案例。“(王莽)于是遣甄丰奉玺绶,即拜帝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赐帝舅卫宝、宝弟玄爵关内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师。莽子宇,非莽隔绝卫氏,恐帝长大后见怨。宇即私遣人与宝等通书,教令帝母上书求入。语在《卫后传》,莽不听。宇与师吴章及妇兄吕宽议其故,章以为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惧之,章因推类说令归政于卫氏。宇即使宽夜持血洒莽第门,吏发觉之,莽执字送狱,饮药死。宇妻焉怀子,系狱,须产子已,杀之。”[2]4065《晋书》记载,曹魏时期,“毌丘俭诛,子甸、妻荀应坐死。其族兄顗、族父虞并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丐其命。诏听离婚,荀所生女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妻,亦坐死,以怀妊系狱。”[3]996在这两个案例中,王宇之妻与毌丘俭之女虽然被判处死刑,但是因为怀孕没有立即执行,而是等待产后执行。
北魏法律正式确立孕妇产后百日行刑制度,《魏书》记载,世祖拓跋焘即位,“诏司徒浩定律令。”规定,“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4]1490—1491《魏书5崔光传》记载,“(正始)四年,除中书舍人。永平元年(公元508年)秋,将诛元愉妾李氏,群官无敢言者。敕光为诏,光逡巡不作,奏曰:‘伏闻当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乱,诚合此罪。但外人窃云,李今怀妊,例待分产。……帝纳之。”[4]1874“例待分产”即《北魏律》“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的规定。北魏确立的孕妇产后百日行刑制度一直被后世法律所沿用。《唐律》规定,在孕妇未生产前执行死刑及产后一百日前执行死刑构成犯罪,分别应受徒刑二年和一年的处罚。“诸妇人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刑。若未产而决者,徒二年;产讫,限未满而决者,徒一年。失者,各减二等。”[5]338
《大明律》“妇人犯罪”条:“若犯死罪,听令隐婆入禁看视,亦听产后百日乃行刑。未产而决者,杖八十。产讫,限未满而决者,杖七十。其过限不决者,杖六十。失者各减三等。”[6]223《大明律集解附例》对犯死罪的孕妇实行产后百日行刑的原因做了解释,“妇人产后一百日血气方全,故凡孕妇罪必待产后百日拷决;虽死罪亦听稳婆入视,亦待产后百日乃刑。盖恐伤其胎与躯也。” 即对犯死罪的孕妇实行产后百日行刑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孕妇本人的健康权和保障胎儿的生命权。清代律学家沈之奇也说:“欲听其乳所生之子,至百日以后,乃可哺食续命。故未产而决者,杖八十:限未满而决者,亦杖七十,仅轻一等,意在生全其子,故特严其法耳。不然,罪本应死,法当行刑,岂必待其血气充足乎?既保其胎生于前,复全其子于产后,仁之至也。”[7]1047
二、对孕妇身体权、健康权的保护
(一)禁止对孕妇进行刑讯与执行笞杖刑。中国古代的笞、杖刑虽然是比宫刑、劓刑等肉刑较轻,但是对于孕妇施加笞杖刑仍会导致孕妇堕胎,损害孕妇身体健康和危及腹中胎儿的生命。因此,从唐代开始法律明文禁止对孕妇执行笞、杖刑和进行刑讯。《唐律》规定:“诸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若未产而拷、决者,杖一百;伤重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产后未满百日而拷决者,减一等。失者,各减二等。【疏】议曰: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及决杖笞,皆待产后一百日,然后拷、决。若未产而拷及决杖笞者,杖一百。”[5]570—571《宋刑统》完全沿用了《唐律》这一规定。元代法律规定:“诸孕妇有罪,产后百日决遣,临产之月,听令召保,产后二十日,复追入禁。无保及犯死罪者,产时令妇人入侍。”[8]2690这一规定被明清法律所沿用,《大明律》“妇人犯罪”条:“若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决者,依上保管,皆待产后一百日拷决。若未产而拷决因而堕胎者,官吏减凡斗伤罪三等;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产限未满而拷决者,减一等。”[6]222—223《大清律例》与此相同。清代律学家沈之奇认为,“怀孕不得拷决者,虑伤其胎也。”[7]110
另外,由于怀孕妇女腹中有胎儿,从西汉起法律规定孕妇在监禁期间不得加戴刑具,景帝后三年(前141年)诏:“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9]110颜师古注:“乳,产也。”根据这个诏令,怀孕未生产的孕妇犯罪经审讯应该关押入狱的,解除桎梏,可以不带刑具。《唐六典》:“凡死罪枷而杻,妇人及徒、流枷而不杻,官品及勋、散之阶第七已上锁而不枷。杖、笞与公坐徒及年八十、十岁、废疾、怀孕、侏儒之类,皆讼系以待断。”[10]188即孕妇与老幼、废疾及侏儒在监禁待审期间不得加戴枷、杻、锁等刑具。
明清法律规定,妇女(包括孕妇在内)犯罪,奸罪及死罪外一律不监禁。《大明律》“妇人犯罪”条:“凡妇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杂犯,责付本夫收管。如无夫者,责付有服亲属、邻里保管,随衙听候,不许一概监禁。违者,笞四十。”[7]222
(二)严惩斗殴致使孕妇堕胎与强迫孕妇堕胎的犯罪行为。用暴力致孕妇堕胎与用药物强迫孕妇堕胎,不仅侵犯了孕妇的健康权,同时也侵犯了胎儿的生命权。中国古代法律规定用暴力致孕妇堕胎与用药物强迫孕妇堕胎构成犯罪。
在睡虎地秦简《封诊式5出子》中有斗殴致孕妇流产的案例:“某里士五(伍)妻甲告曰:‘甲怀子六月矣,白昼与同里大女子丙斗,甲与丙相捽,丙偾庰甲。里人公士丁救,别丙、甲。甲到室即病复(腹)痛,自宵子变出。今甲裹把子来诣自告,告丙。’即令令史某往执丙。即诊婴儿男女、生发及保之状。有(又)令隶妾数字者,诊甲前血出及痈状。有(又)讯甲室人甲到室居处及复(腹)痛子出状。”[11]161某里士伍之妻甲已怀孕六个月,控告同里的大女子丙在昨天白昼斗殴中将自己摔倒,甲到家就患腹痛,昨夜胎儿流产。官府当即命令史某前往捉拿丙,随即检验婴儿性别、头发的生长和胎衣的情况。这表明在战国及秦朝,在斗殴中致孕妇流产就已经构成犯罪。
北魏宣武帝时期,刘晖娶孝文帝之女兰陵长公主为妻,“主严妒,晖尝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杀之;剖其孕子,节解,以草装实婢腹,裸以示晖。晖遂忿憾,疏薄公主。……正光初,晖又私淫张、陈二氏女。公主更不检忌。主姑陈留公主共将扇奖,与晖复致忿诤。晖推主坠床,手脚殴蹈,主遂伤胎。晖惧罪逃逸。灵太后召清河王怿决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宫,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为兵。主因伤致薨,太后亲临恸哭,举哀太极东堂。出葬城西,太后亲送数里,尽哀而还。后执晖于河内温县,幽于司州,将加死刑。会赦,免。”[12]1049
《唐律》规定,斗殴中致使孕妇堕胎者徒二年。“诸斗以兵刃斫射人,不著者,杖一百。若刃伤,及折人肋,眇其两目,堕人胎,徒二年。【注】堕胎者,谓辜内子死,乃坐。若辜外死者,从本殴伤论。”“【疏】议曰:……‘堕人胎’,谓在孕未生,因打而落者:各徒二年。注云‘堕胎者,谓在辜内子死,乃坐’,谓在母辜限之内而子死者。子虽伤而在母辜限外死者,或虽在辜内胎落而子未成形者,各从本殴伤法,无堕胎之罪。其有殴亲属、贵贱等胎落者,各从徒二年上为加减之法,皆须以母定罪,不据子作尊卑。”[4]385—386
《宋刑统》关于堕胎的处罚与《唐律》相同,南宋法律加重了堕胎罪的量刑,“堕胎者准律:‘未成形像,杖一百;堕胎者,徒三年。’”[13]33
元代对堕胎的量刑比唐宋有所减轻,由徒刑减为杖刑。《元史5刑法志》记载:“诸斗殴,……折二齿二指以上,及髡发,并刃伤、折人肋、眇人两目、堕人胎,(杖)七十七。…… 诸职官殴妻堕胎者,笞三十七,解职,期年后降先品一等,注边远一任,妻离之。[8]2672明清法律又将堕胎的刑罚改为徒刑,《大明律》:“折人肋,眇人两目,堕人胎,及刃伤人者,杖八十,徒二年。【注】:堕胎者,辜内子死,及胎九十日之外成形者,乃坐。其虽因殴者,若辜外子死,及胎九十日之内,未成形者,各从本殴伤法,不坐堕胎之罪。”[6]159—160《大清律例》对斗殴中导致孕妇堕胎的处罚与《大明律》相同。
元代法律禁止强迫怀孕的妓女堕胎,“诸倡女孕,勒令堕胎者,犯人坐罪,倡放为良。”[8]2644用药物强迫妓女堕胎构成犯罪,“至元十七年七月,中书省刑部呈:‘彰德路申,娼馆之家若有妊孕,勒令用药堕胎,陈告到官,将犯人断罪,娼女为良’。都省准呈。”[14]199
清代法律规定,奸夫与奸妇通奸怀孕后合谋用药堕胎致使奸妇死亡,奸夫以毒药杀人罪论处,知情卖药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妇人因奸有孕,畏人知觉,与奸夫商谋用药打胎,以致堕胎身死者,奸夫比照以毒药杀人。知情卖药者,至死减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若有服制名分,本罪重于流者,仍照本律,从重科断。如奸妇自倩他人买药,奸夫果不知情,止科奸罪。”[15]466
《大清律例》规定,“若用毒药杀人者,斩监候,或药而不死依谋杀已伤律,绞。”[15]453用毒药杀人属于故意杀人犯罪,奸夫合谋用药堕胎致使孕妇死亡应该属于过失杀人犯罪,按照《大清律例》,“过失杀伤人者,各准斗杀伤罪依律收赎,给付其被杀伤之家。”《大清律例》之所以规定作为过失犯罪的奸夫合谋用药堕胎致使孕妇死亡行为按照用毒药故意杀人罪量刑,是因为这一行为同时剥夺了孕妇与胎儿的生命权,即背负两条人命。
在清代司法实践中,奸妇虽然非因奸怀孕,奸夫协助奸妇堕胎致死也要以毒药杀人罪论处。乾隆三十九年,黄受林、薛其六与怀孕妓女孙氏嫖宿,黄受林、薛其六代为孙氏购买堕胎药,孙氏因打胎致死。刑部认为:“查例载,妇人因奸有孕,畏人知觉,与奸夫商谋用药打胎以致堕胎身死者,奸夫比照以毒药杀人,知情卖药者至死减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语。此案黄受林等与娼妇孙氏嫖宿,孙氏怀有身孕,虑难卖奸,邀商黄受林等欲行打胎,黄受林旋送孙氏至薛濮氏家。濮氏取药治用,将胎堕落,孙氏因而殒命。该抚虽称与诱奸良妇败节戕生者有间,但细核本条例义,既未区分良贱且系比照毒药杀人,知情卖药至死减流之例,尤不得以良贱论。今孙氏虽系娼妇,而黄受林之商同用药打胎毙命,自未便因系娼妇遂为末减,致使淫纵残忍之徒无所惩儆。黄受林应照例杖一百,流三千里,薛其六虽有奸宿并与谋打胎情事,其后黄受林转送孙氏至薛濮氏家用药堕胎之时并未在场,应与听从用药之薛濮氏均照为从减一等,各杖一百,徒三年。薛濮氏系妇人收赎余,均如所咨完结。”[16]1328
三、古代胎儿生命权观念与孕妇保护权观念
中国古代法律对于孕妇生命健康权的保护首先是由于孕妇是需要特殊保护的弱势人群,基于儒家的仁政传统与恤刑法律文化,汉代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指导思想,对于孕妇进行特殊保护是法律开始儒家化的具体体现。
中国古代对于孕妇生命权与身体健康权的保护与古代对胎儿享有生命权的认识有关。在中国古代许多人的观念中,胎儿是有生命的。如唐传奇《红线》中记载侠女红线辞别薛嵩时说:“某前世本男子,游学江湖间,读神农药书,救人灾患。时里有孕妇,忽患蛊症,某以莞花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三人,阴功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气禀贼星。所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使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至矣。况国家建极,庆且无疆,此辈背违天理,当尽弭患。昨往魏郡,以示报恩。今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在某一妇人,功亦不小,固可赎其前罪,还其本形。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常存。”[17]26—28红线为孕妇治疗蛊毒病因下错药而致使孕妇与腹中两个胎儿死亡,红线认为自己是“一举杀三人”,表明红线承认胎儿是有生命的。清代纪昀所著《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吴惠叔言,医者某生,素谨厚,一夜,有老媪持金钏一双就买堕胎药,医者大骇,峻拒之。次夕,又添持珠花两枝来,医者益骇,力挥去。越半载余,忽梦为冥司所拘,言有诉其杀人者。至则一披发女子,项勒红巾,泣陈乞药不与状。医者曰:‘药医活人,岂敢杀人以渔利。汝自以奸败,于我何有’?女子曰:‘我乞药时,孕未成形,倘得堕之,我可不死,是破一无知之血块,而全一待尽之命也。既不得药,不能不产,以致子遭扼杀,受诸痛苦,我亦见逼而就缢,是汝欲全一命,反戕两命矣。罪不归汝,反归谁乎’?”[18]467这位医生不肯卖堕胎药给老妇是因为他认为堕胎等于杀人,与医生救病治人的职业道德相悖。以上两部笔记小说中的故事都表明在古代民间有堕胎等于杀人的观念。
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左都御史詹徽奏民殴孕妇至死者,律当绞,其子乞代。大理卿邹俊议曰:‘子代父死,情可矜。然死妇系二人之命,犯人当二死之条,与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无辜之子。诏从俊议’。”[19]2288大理卿邹俊认为殴打孕妇致死实际上是杀死两条人命,属于重罪,故不能允许凶手儿子代替其父受死刑。
总之,中国古代的刑法对于孕妇生命权、身体权与健康权的保护还是比较完备的,体现了中国古代刑事立法的先进性与人道性的一面。
[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怀效锋.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7] 沈之奇.大清律辑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8] 宋濓,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9]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 李林甫,等.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1]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12]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 宋慈.杨奉琨译.洗冤集录校译[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0.
[14] 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15] 张荣铮,刘勇强.金懋初点校.大清律例[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16] 祝庆祺,鲍书芸,潘文舫,何维楷编.刑案汇览三编[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17] 李玫,袁郊撰,李宗为校点.纂异记甘泽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8] 纪昀.北原注译.阅微草堂笔记注译[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19]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