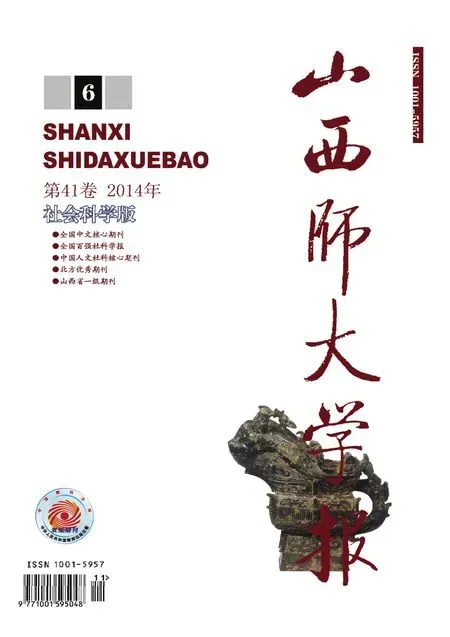汉族传统丧礼仪式的德育启示
张 鲲
(北方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银川 750021)
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具有持续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德性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德性在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德性体系的文化密码。传统是人们既有的解决各种人类问题的文化途径,它具有规范性,承载着德性的基本价值取向。“正是这种规范性的延传,将失去的一代与活着的一代连接在社会的根本结构之中。”[1]32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礼仪之邦,丧葬礼仪在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映着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宇宙观、价值观和心理特征。几千年来,传统丧葬仪式成为地域差异很大、幅员辽阔的疆土上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纽带,孕育着浓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熏陶着各个成员的个体品德,其中蕴含的德育理念和方法对当下社会个体品德培育与道德秩序的建构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德育应立足于个体的现实生活
人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由社会成员共享的意义和知识所构成的象征符号体系的“文化世界”之中,人正是通过文化去适应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并建构起关于世界与自我的观念。道德来源于社会生活,道德只有在群体生活之中才能彰显其价值与意义。关系群体生死存亡的丧葬仪式既可以强化和确认集体意识,获得组织的统一性,又能通过复杂的象征结构展现“不可言说”的信仰内蕴,维系族群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说,定期的仪式是信仰生命力延续的保证。丹尼尔·贝尔认为,人类需要依靠类似于宗教的崇拜来把握自己的文化,用仪式等象征系统体现诸如死亡、爱情、痛苦与悲剧这些人类永远面对的“不可理喻性问题”,解决人类的精神寄托、情感需求或文化传承。传统丧礼仪式之所以长期受到社会的认同,原因在于其一直秉承着人类共有的一些基本情感和道德。
从古至今,尽管丧葬礼仪已有所变化,但为父母举哀守孝依然传承不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亲情是人的天性,家庭情感生活是人最主要的自明性体验,家庭是社会伦理的基础。家庭作为人的心灵回归的港湾,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人们常常对家庭具有一种深深的眷恋感。家庭是个体一生牵挂的情愫,家庭不仅养育了自己,还是自己恒久的心灵安慰,家庭对个体的影响是持久的。孔子说:“爱亲谓之仁。”(《论语·学而》)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最重视家庭,中国人一生离不开家庭伦理观念,家庭是中国社会伦理的基础。在华夏子孙看来,“百善孝为先”,为父母尽孝是每个人不容置疑的应尽义务。《诗·小雅·蓼莪》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而且家庭还是人之信任感的最初来源,家庭和社会是集体情感和神圣感发生的源泉。在古代中国,“身”与“家”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吕氏春秋》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社会是所有信仰体系和膜拜体系的基础,社会生活之中孕育着某些恒久的、具有人性色彩的客观要素,这些要素是共有的价值体系和集体意识。建立在家庭伦理基础之上的孔孟原创儒学反映了人类最真实的情感,丧礼仪式维持了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奠定了古代以“礼”治国的理念与实践基础。传统丧葬仪式成功地将个人、家庭、宗族的意识,与国家的主流意识完美地融为一体,使之成为凝聚海内外华人情结的象征符号。
此外,传统丧葬仪式能够通过定期举行膜拜仪式来唤起人们共同的观念和情感,创建起个体信仰的心理倾向,从而加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汉族是世界上最注重丧祭礼仪的民族,黄帝时期就有“心丧”,尧舜时期已有三年之丧,到西周时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繁杂而严谨的丧礼仪式。南宋时朱熹在《书仪》基础上撰写了《朱子家礼》,这是一部简明适用的庶民之礼。《朱子家礼》在秉持正统儒家理念的同时,使礼从主要规范贵族生活走向坊间平民,而且随着《朱子家礼》的普及,民间丧祭文化的儒教色彩更加浓厚。《朱子家礼》不仅成为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儒家礼仪的蓝本,对东亚的朝鲜和日本也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丧礼仪式通过对丧事仪轨的细密安排,使“亲亲、尊尊、长长、幼幼”的观念扎根于家庭、宗族和国家的日常生活,使“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成为社会政治制度的根基,从而巩固了在“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伦秩序与政治制度。汉族丧礼仪式不像其他仪式那样,要么描述辉煌的仪典文化,要么记述个人或区域的公众交往,而是以现实生活中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聚合与安宁为视点,从国家和个人共同关注的人生重大事件出发,使儒家正统思想与乡民社会意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贯穿国家、宗族、家庭和个人“四体一位”的道德文化沟通模式,既使主流意识扎根于底层真实生活,又使国家意志得到支撑与凝聚。在此意义上,丧礼成了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密切联系的纽带。
二、德育应重视行为习惯的养成
习惯指由于反复实践而逐步养成的、并根植于心理之中自然而然的稳定的行为模式。《辞海》对“习惯”的解释是:“由于重复或多次练习而巩固下来的并变成需要的行动方式。”习惯对个体行动结构的建构作用历来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大戴礼记·保傅》:“少成若性,习贯之为常。”荀子说:“注措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荀子·荣辱》)古罗马西塞罗《论目的》说:“习惯是一种第二天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而具有的某些自然素质,随着持续的训练就形成某种习性或行为。他将人的德性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理性活动上的德性,即理智德性,可以由教导生成;欲望活动上的德性,即伦理德性,则需要通过习惯来养成”[2]61。黑格尔称习惯是人的“第二自然”,是“灵魂的一种直接的存在”。他说:“一个人做了这样或那样一件合乎伦理的事,还不能说他是有德的;只有当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他性格中的固定要素时,他才可以说是有德的。”恩格斯肯定了社会生产方式在习惯中的作用,他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变成了法律。”[3]211泰勒认为:“世界文明的发展遵循着一定的轨道。有很多事实能帮助我们追溯出这些轨道。我发现用‘残存’(survial)一词表述这类事实十分方便。这些事例就是进程、习俗、意见,等等。它们由习惯的力量带进了新的社会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社会的严肃事务融入到了后代的精神之中。”[4]15
丧礼仪式能通过“意义”系统来协调生命现象的活动与方向,引导文化心理沿着社会期待的方向形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者与死者之间是能够交流思想和感情的,丧礼仪式中的话语、情态、举止、器物,乃至汉字和人本身,在特有的文化心理“背景场”里都成为富有意义的系统。《礼记·礼运》云:“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丧事内容和文化心理是人的行动的“场域”,仪式仪节是既定的“惯习”,“场域”决定“惯习”并使之沿着感觉和意义的方向延展。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行动者有一种相对固定的“性情倾向”,但这并非结构主义所说的先验思维图式,而是在一定客观条件约束下形成的“惯习”,“惯习”始终是“理性行动”的基础。在他看来,惯习属于“心智结构”的范围,是一种“主观性的社会结构”,惯习“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或者是生物性的个体里)”[5]171。布迪厄言及的“性情倾向”正如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文化心理”,文化心理是沉淀在个体内心的心态,是个体思维和行为模式的持久效用的秉性系统,保持着特定文化传统的方向和秩序。以祭祀为例,家族祭祀是昭穆精神的体现,昭穆制的功能就是维系宗族与家庭的稳定。
社会生活通常会产生各种相互识别和相互认同的期望,这些期望既构成了生活规范的基础,又使理性成为必要。传统丧礼仪式可以调适人的情感和欲望,并促使人伦秩序的形成。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礼乐为特征的伦理型社会,儒家认为人的言行用礼仪来统率,就会得到礼仪和情性的满足;如果只用情性来统率,那么礼仪和情性都会失去。梁漱溟认为,“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而其道则在礼乐制度”[6]207。费孝通说:“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7]52著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与延续》中提出,社会既包括有秩序的社会关系和规范构成的“结构”,又包括由超越地位和身份等差异的“反结构”构成。社会结构充满着冲突和分裂,而社会结构之所以始终是完整的,仪式在其中起着社会平衡和稳定的作用。特纳首次提出了仪式“反结构”的功能,“交融并不会抹杀个体之间的差异,相反,它使之从毫无差异的统一状态回归到了自然状态”[8]331。特纳肯定了仪式对社会行动结构的调节。“我们可以最终看到,作为特殊的强调功能,仪式的展演在社会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在具体的族群中起到了调整其内部变化、适应外部环境的作用。就此而言,仪式的象征成为了社会行为的一种因素,一种社会活动领域的积极力量。”[9]20传统仪式以一种自然的教化方式在更为细微的层面培植了个体的德性与秩序感,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三、德育必须重视信念支撑体系的巩固
现代性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人之心灵世界的冲击,人的心灵依赖于信念的支撑,信念的根基是信赖感和意义感。“信”表示人对有关对象(事实、人物、观念、命题、理论等)的一种肯定心态。信念指“信”在情感和意志方面的强化。大卫·休谟深刻地洞察到,“信”与“不信”的差别不在于所指的内容,而在于理解的方式;信念能给予观念以更多的影响并使观念嵌入到个体心灵之中,成为人们一切行为的支配原则。在他看来,“信念”表达的首先是主观倾向和态度,“对象”、“内容”和“所信”反倒不紧要。任何层次和形态的“信”都建立在人的意义感体验之上,都蕴含着人的欲望、动机、兴趣、爱好、情感和意志。西美尔强调:“我们信仰某个人,虽然有悖于一切理论论证,而且种种现象看上去又是如此矛盾,可我们仍然矢志不渝,这是维系人类社会最可靠的纽带之一。”[10]15“信”植根于人性之中并且是人之生存、思考和行动的基础,“信”实质是个体的德性与某种超越信念之间的贯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良善均来源于天理、天道或天伦,“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而且,这种道德信念还得到了“情”和“文(仪式)”的支撑。
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伦理结构”是社会信念体系的实体支撑。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层结构,礼规范的是人伦关系,仪式是人伦关系的集体表象。在传统丧礼中,以死者为中心的包括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各个伦理实体的人都会聚在一起,每个人都能在共同体中找到自己的伦理关系,感受到对家庭、宗族、村落的归属感,生之信仰与死之情感都置于人生重大的死亡事件面前,价值、道德和信念此时此刻不再变得虚无飘渺,而成为个体真实的体验。人类一开始就从属于某个伦理实体,否则他就无法生存。人们共同的劳动、生活,共同的习俗,共享的痛苦和欢乐,构成了家庭、居住地、民族乃至人类整体的社会记忆,这些社会记忆不仅能勾起人们对共同体的依赖和眷恋之情,而且还能使人们从中汲取力量,树立信心,形成凝聚力。阿尔弗雷德·许茨认为,日常生活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的行动的领域,他把社会行动定义为有意义的经验。日常生活现实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性质,人们对它不怀疑,想当然如此,且在主观上共同享有。人们主观上的共同性是群体道德生活的结果。许茨说:“行动者的实际情景具有它自己的历史,它是他以前所有主观经验的积淀。”[11]120许茨认为,常识世界包含着人们共同拥有的意义结构,“这种意义结构来源于人类行动——我们自己的行动以及我们的同伴的行动,当代人的行动和前辈人的行动——并且一直是由人类行动规定的”[11]36。
以意义感为基本内容的“心灵秩序”是个体信念的精神支撑。在传统社会,人们生活在一个具有“共同体”性质的社会,而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个“共同体”分崩离析,导致个体失去了过去群体为其所提供的安全感和意义感的纽带。在现代社会,所有个体都处于总体社会的巨大张力之中,而且还处于不断地剧烈变化之中,情感结构和信任体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代生活的社会力量往往是一种导致不稳定的力量和从根本上进行摧毁的力量,它摧毁了人们从以前生活中获得的意义感”[12]137。而传统儒家文化的独特功能正是通过对个体心灵世界的修复来接续意义感的。儒家认为,人的精神可以超越生死,流芳百世,名传千古。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 儒家的精神不朽论,实质是给有限的生命赋予无限的道德理想,通过人之自省和终极关怀来实现道德信仰的内在超验。在儒家看来,道德理想对于人来说不应是虚无飘渺的,而是与自身血肉相联的、内在的,由人的心性所创造出来的。孟子认为, 人只要能自觉地发挥心性能思的力量, 就能“尽心知性”,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正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传统丧礼文化还能够通过仪式化、象征性和规范性的行为使人们的心灵在神圣的仪式空间有了着落,这对忙于奔波而身心疲惫的现代人来说尤为重要。“仪式是一种憩息,让您从惯常行为超脱出来,了解自己最深的内心需求,认清当前的生活阶段,并把其视作发展和变化的机遇。”[13]8马林诺夫斯基首次提出了仪式的情感抚慰功能,“这样看起来,不死的信仰,乃是深切的情感启示底结果而为宗教所具体化者;根本在情感,而不在原始的哲学”[14]33。
[1] (美)E.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 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英)道格拉斯.洁净与危险[M].黄剑波,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5] (法)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 陈来.梁漱溟选集——中国文化要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7]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 (英)维克多·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M].刘珩,石毅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9] Turner. The Forest of Symbol:Aspects of Ndembu Ritual.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10] (德)西美尔.宗教社会学[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1] (奥地利)阿尔弗雷德·许茨.社会实在问题[M].霍桂桓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2] Davis J E. 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 New Jersey :Transactions Publishers,2000.
[13] (德)辛格霍夫.我们为什么需要仪式[M].刘永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4] (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