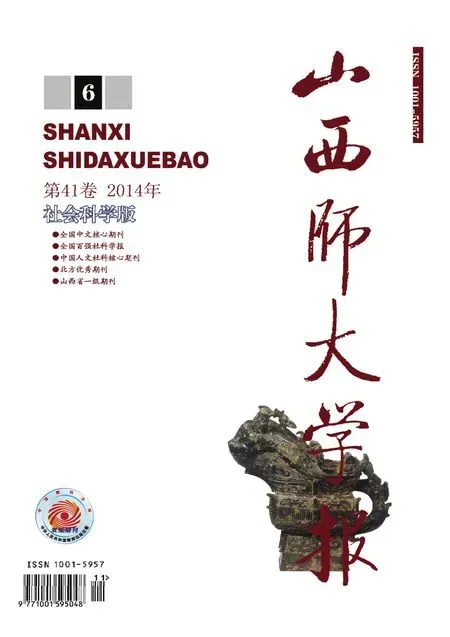从杰克·伦敦的日本书写看其种族主义思想的渐变性
吴华南,王丽耘
(上饶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是美国19与20世纪之交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短暂的40年生命曾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包含不少跨文化的书写文字。这些文字涉及美洲本土异质文化的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夏威夷土人以及美洲之外的日本、中国和朝鲜等异域他国的人物。它们不仅是上世纪转角异质文化大规模碰撞与交流肇始的生动记录,更是透视杰克·伦敦异域文化观的珍贵文献。在有关杰克·伦敦研究中,他那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一直是个令研究者头疼的话题,对其作品的细致梳理与文本细读将非常有助于消除悬置在此问题上的疑云。
但我国目前学界对伦敦的跨文化书写关注不多,除对其中国题材作品有过一些较深入的研究外,伦敦的其他跨文化书写至今仍是研究空白。这些研究领域的薄弱导致了对伦敦“种族主义”问题的简单判定,他的形象在我国呈现“无产阶级的作家”、“美国的高尔基”到“白人至上种族主义鼓吹者”的两极逆转。本文拟聚焦伦敦的日本书写文字,探究这些文字背后是否存在种族主义,伦敦是否可称为种族主义者以及他的种族主义是彻头彻尾的,还是呈现一定的变化等问题。
一、早期文学作品中的日本描画
伦敦最早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东方形象是亚洲的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1893年,17岁的伦敦首次成为签约水手远航海外,时长八个月,目的地即日本。当时,载着伦敦的索菲亚·萨瑟兰号在日本的小笠原群岛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在回航旧金山时又于途中停访日本横滨。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促成回国后的伦敦陆续创作了四部涉及日本的文学作品,即《酒井绪、和乃爱子与孝武》(Sakaicho, Hona Asi and Hakadaki, 1895)、《夜游东京湾》(A Night's Swim in Yeddo Bay, 1895)、《阿春》(O Haru, 1897)和《在东京湾》(In Yeddo Bay, 1903)。
伦敦创作生涯始于1893年,终于1916年。上述四部短篇约归于其创作生涯早期的作品。在这些短篇小说中,伦敦为美国公民勾勒了他眼中的日本底层劳动者形象:被不幸压垮的人力车夫、喜欢趁火打劫的舢板公及遭遇丈夫厌弃的名艺妓。这些人物在伦敦笔下不乏同情的描写,但有的作品不时流露创作者下意识的蔑视,作者带有一定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意识,这一事实不可否认。美国学者达尼埃尔教授是海外少数全面关注伦敦东方书写的西方学者,他近年提出“仔细考察伦敦的作品会发现他决不是种族主义黄祸创作的倡导者,……他以一种同情的笔调描画日本人们”[1]30。但问题在于同情的描画并不意味着种族偏见的缺席。
(一)明褒暗讽的日本形象
1895年,伦敦发表了其日本题材的处女作,其中,《夜游东京湾》较之《酒井绪、和乃爱子与孝武》的简单情节与单纯情绪更为复杂,值得分析。
全篇以头发花白、名叫查理的老年商船水手的叙述为线。故事开篇即是这位老年水手手举酒杯向听众不容分辩地赞美日本人的场景,他赞美日本人的聪慧、发奋、精力、学识、诚实、礼貌和好脾气,并从日本的发奋,查理转而谈到他们的急于西化,从而讲起了他午夜在横滨遭日本舢板公盘剥衣物以抵船资的惊险经历。当时,日本舢板公提议不名一文的查理以身上的衣物当抵船资,查理不依。他最终将衣服寄存在横滨码头的日本警局,只身跳海游回了美国邮轮。抵岸后他不按常规去水手舱就寝,又引来一场随后的海上寻人骚乱。不过,这次事件后,查理上岸虽每每遭到日本舢板公指指点点,但他们却没再向他要过摆渡费。
全文写得较为含蓄,没有过多的事件解释与心理描写,作者对日本(人)的态度较不明朗,文字背后的真义需要读者耐心细究。首先,文章开篇的褒扬更像是反话,后文老水手叙述的一系列遭遇使得开篇那不容置疑而又毫无保留的颂扬产生了绝妙的反讽效果,从中读者不难窥见作者对日本人的态度。其次,文中刻画的与查理起冲突的老少两位日本舢板公形象不得不说有些可鄙。老者在作者的描述中犹如博物馆里陈列的伤痕累累的盔甲:又老又瘦、奇高的个头、浑身打皱,晒黑的皮肤上各种各样大块的疤痕黑白相间,再加尖细如小孩的嗓音。当他在查理面前弯腰鞠躬延揽生意时,这位经验丰富的白人老水手也不禁感到一阵慌乱。而舢板上老头的副手则又是另一副模样,少年矮小早熟,高不过一捆烟草、圆胖结实,举止神情完全像个大人。他失去童真的可恶之样文中有细腻的细节,是他目光锐利地注视已烂醉如泥的水手,是他提醒老头先让客人掏钱再撑船,是他以犀利的目光上下打量这位付不出船资的美国水手并首先建议以衣相抵。再次,故事中围观起哄的日本舢板公群体被描画成可憎的趁火打劫者群像。他们第一时间聚拢,当看到美国水手掏遍口袋不名一文时,他们开心地狂笑,叽叽喳喳出主意、提忠告。当听到少年向水手要求衬衣时,他们一面乐滋滋地看水手的笑话,一面纷纷拍手以示赞同。没有一位日本舢板公愿意先摆渡再收费,美国水手怒不可遏,爬上身边一块大花岗岩石,“向着这群乌合之众激动地大说一通,而日本舢板公只管起哄与嘲笑,我说的话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2]。这里查理用的“motley mob”一词,同为各自国家底层民众的代表,美国水手称日本舢板公为“乌合之众”,这无疑是种族优越性在作怪。
(二)儿童版中露骨的种族宣扬
《夜游东京湾》的故事,八年后伦敦再次在美国儿童文学杂志《圣尼古拉斯》上讲述,题为《东京湾》。《圣尼古拉斯》是一份质量上乘的儿童读物,书中配有精美的插图。该刊注重思想导向,办刊宗旨定位于培养美国未来最优秀的青年男女。在此类刊物上发表作品,应该说作者的创作态度更为严肃认真,其中表露的思想也最接近作者本人的思考,因为其受众是国家的下一代。从这种意义上说,《东京湾》的文献研究价值巨大。
为适应儿童读物的需要,故事主人公被改为刚满16岁的稚气少年阿尔夫·戴维斯,且篇首增加了阿尔夫丢了钱包付不出饭钱被店老板叫嚣及日本民众围观的紧张情节。之后的故事脉络基本与《夜游东京湾》相似,旨在叙述身无分文的阿尔夫如何回到美国邮轮,不同之处在于细节描写及为儿童读者增添的事件说明与心理描写。而这些恰恰为我们考察伦敦的种族主义思想提供了绝佳的佐证。
《东京湾》中,作者称日本人为“短腿的人们”,而当他挑选的自认为面善的老舢板公也要求阿尔夫以衣抵费时,伦敦描写了阿尔夫的心理反应:“阿尔夫胸中燃起美国人的独立感。盎格鲁—撒克逊后裔与生俱来厌恶被人强迫。对阿尔夫来说,这样的交易简直是赤裸裸的抢劫。”[3]显然,在《夜游东京湾》中只以“我那时自己也极度固执,不愿屈服”一语带过的原因在《东京湾》中得到了清晰的阐述。
在16岁的阿尔夫眼中,这群围困他的舢板公来自社会底层,他们衣不蔽体,健壮、粗鲁、吵闹,并时有肢体冒犯,阿尔夫感到危险。但当有人胆敢强抢他戴在头上的帽子时,他还是予以了迅速回击。伦敦描写当时阿尔夫脑海中快速转动的念头是:“水手的骄傲不允许他让自己的帽子落在这群人手中。”[3]当帽子滚落最终被结实健壮的日本舢板公踩在赤足下时,阿尔夫感到“这是直接的挑战”[3]。而当阿尔夫最终勇敢地夺回帽子并用四面挥舞的拳头击退趁机向他涌来的人群时,伦敦这样解释这场化险为夷的冲突:“全世界深色人种已学会尊重白人的拳头,与其说是阿尔夫的好战帮助他赢得了胜利,还不如说是众多水手斗争的战果。”[3]这里美国水手是白人的象征而日本舢板公即是那所谓的深肤色人种,其中的种族主义是显见的。
阿尔夫退进海边警局时,伦敦描写跟随的日本艄公“变得安静、有序,犹如苍蝇聚在敞开的大门前”[3]。“苍蝇”这一动物形象无声地表明了美国水手(阿尔夫)或者说创作者(伦敦)对日本舢板公的恶劣印象。其时,阿尔夫注意到日本海署队长讲着一口“完美的英语”,而《夜游东京湾》里老年水手查理听到的是日本警长的“上等日语”,其中微妙的差异显示了主人公(或者说创作者)激增的民族自豪感。此外,《东京湾》中还增添了日本警长建议美国水手在户外将就一晚的细节,从而也让我们领略了阿尔夫的又一次心理活动:“舢板公已激起他的种族自豪感与坚毅不拔的精神,问题无论如何不可能那样解决:睡在外面岩石上即是认输。”[3]其中的种族意味还是非常强烈的。
(三)貌合神离的同情
早期伦敦日本题材的创作还有一部未公开发表的作品即《阿春》,该短篇中伦敦试图同情东方文化,但全篇被强调得有些变形的东西对立与差异,表明创作者虽主观意欲同情东方文化,却对其内涵与深意不得要领。过度强调异质文化之别易于导向冲突与隔膜,如此状态下给予“他者”的同情,恰似一份被架空的同情。
《阿春》以日本最底层的不幸女性——艺妓为描画对象,她是“所有艺妓中最好、最纯的;所有舞者中举世无双、最优雅的;所有女人中最具飘逸之美、最诱人的”[4]。这样的女人苦等恋人十年,可已被白人文化(至少是白人审美观)同化的恋人——丰臣却是人回心不回,短暂的新婚后即对日本人百般追奉的阿春又骂又打,甚至逼阿春重回艺馆舞蹈谋生。悲愤的阿春选择了先人武士的“切腹自杀”,在回馆首演时假戏真做,将自我灰飞烟灭。在这个悲情的故事里,作者给予了武士之后的阿春从长相、舞艺、才能、机智到性情等全方位的赞美。篇中叙述者甚至站在阿春一边,称丰臣之前10年在外朝夕相处的是“白种野人”,习惯的是“异邦恶魔的风俗”,学会的是“白鬼的招数”,带回的是“古怪的审美标准”。对丰臣而言,阿春不再是美丽的,他“狂热着迷于西方美人”[4]。
东西文化的冲突与碰撞是个深刻的话题,伦敦截取两种文化矛盾的审美观(对美女的不同评判标准)为聚焦点,契入角度原本不错,但小说展开中过多着力表层差异的对比(过于强化,有变形之嫌),而贯穿全文的那场阿春精神顿悟之旅(即神庙参拜)写得更是虚简与玄秘。这些均表明创作者与日本文化的隔膜,早期的伦敦在种族主义裹挟下虽有同情日本之念,但难成其实。
二、中后期非虚构作品中的日本思考
1904年,即完成儿童版《东京湾》创作的次年,伦敦受雇美国著名的《赫斯特报》,以日俄战争战地记者的身份前往日本,有了第二次与日本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同时也拉开了他日本题材创作的中后期阶段。
1904年1月7日,伦敦登上美国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在海上颠簸近三周后抵达日本东京,随后辗转朝鲜进入中国东北地区。 6月,由于阻力重重,伦敦最终无奈结束了其艰难的战地采访,撤离前线。近半年的实地接触促使伦敦写下了数十篇战地报道并传回了成百上千张珍贵的战时照片。加上撤离前创作的最后一篇政论文《黄祸》其中涉及不少有关日本的讨论。
上述材料不同于早期的文学创作,属于新闻报道、政论文,相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应归入非虚构作品一类。在非虚构作品中,作者的观点相对明了,因其多直接陈述。翻阅此批文献,读者仍能捕捉到伦敦思想中“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一些影子,但令人欣喜的是其中逐渐融入了更多理性思考的因子。近半年,伦敦亲历战场、辗转各地,与日、朝、中三国的普通军民有较多接触,他关于日本的思考不再停留在文学作品中的想象。伦敦在上述多篇文章中赞赏日本人的勇敢、冷静与胆识,肯定日本民族的集体爱国主义与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叹服日本民族学习西方现代化的惊人本领,预测日本民族终将承担唤醒中华睡狮的历史大任。
1906年,伦敦创作科幻短篇《空前的入侵》,文学虚构中夹杂一定的理性思索。文中伦敦就日本国家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所作的预测,实际上从未来两国的发展史来看也是基本应验了的。日本在日俄战争胜利后不满足于打败俄国、侵占朝鲜及中国东北的战绩,于1931年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但日本的强大与侵略最终并没有侵吞中国,中华民族在一片亡国的呼声中迎来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并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1909年12月,伦敦在《日落》杂志上发表政论文《当日本唤醒中国》,不仅重申前述观点,而且谈到了美日沟通的深远话题。伦敦指出美国人经常让日本人弄得昏头昏脑、惊诧不已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对日本历史与文明的无知。美国人是从自己的文化来创造日本人形象,并希望日本人以美国人可预知的方式行为举事,可事实并非如此。伦敦尖锐地批评道:“我们自认为对日本人有所了解,实际上却是一无所知。人类的一大缺点就是相信别人是以自己的模子造出的,我们白人的问题在于相信日本人和我们想法一致,观点相似,会因同样的事情而行动。”[5]361此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标明伦敦的思想已从中、朝、日等亚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异同思考迈向了各国彼此沟通对话的探讨。他呼吁西方跳出种族主义中心论的窠臼,平等对待东方各族。
此后六年多的时间里,伦敦孜孜以求的一个话题就是东西方交流可能性的探索,1915年8月他发表《部落语言》一文即为一证。文中伦敦多处谈及日本,他关注到在美日本移民的艰难处境,指出这些日本移民无法被美国民众接受为居住国公民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彼此间的文化误读。两国差异太大,除了日本人耐心、冷静而美国人急躁、草率这样的日常生活体现的性格差异外,还有其他很多显著的不同导致了两国人民的误解。故此,伦敦倡议创建“泛太平洋俱乐部”,为太平洋两岸存在巨大文化差异的各国提供相遇与相识的平台。伦敦写道:“泛太平洋俱乐部将是我们彼此相识相知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将了解彼此及彼此的爱好;同时,我们可继续邀请新朋友来此作客,这是一种突破泛泛之交走向彼此深入了解的好办法。为了大家的利益,让我们创建一个这样的俱乐部。”[6]126此时的伦敦不再强调白种人(美国)与黄种人(日本)的优劣,他承认彼此的差异,期待良好的交流成为可能。他渴望建构潜在的东西交流,他留下的文字表达出了对于东西方交流的期盼之情与乐观之识。在伦敦创作晚期,他的种族主义意识可谓极大地减弱,在理性思索与种族情感的交锋中,理性终于胜出。
1916年11月22日,是伦敦猝然离世的日子。人们发现他正在创作长篇小说《亚洲的眼》,虽然生命的消逝使读者无缘一睹作品真容,但我们从伦敦拟取的书名至少可以确定一点:直至生命的终点他都非常关注亚洲,关注东西方交流话题。
总而言之,伦敦日本书写中存在一定的种族主义意识,但他的这种“白人至上”种族意识并不是彻头彻尾的。早期日本题材的四部文学创作不乏伦敦对日本底层或弱势群体的同情,但其中也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伦敦“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烙印,有的作品还十分明显。时代的刻板印象在东西文化碰撞之初多少反映在了伦敦关于“他者”的描画中。日俄战争是伦敦日本观的转折点,这场战争的结果使包括伦敦在内的很多西方人开始对东方日本刮目相看;而几个月的战地采访也有助于伦敦更为客观、冷静地分析日本,从而他的日本思索中逐渐减少了露骨种族意识的渲染。生命晚期的伦敦,更是呼吁西方放弃种族成见,走向东西互识之境。严格说来,伦敦的种族主义意识总体呈现出了由强及弱的渐变态势。细致耙梳历史遗留的宝贵文献,有助于我们走近更加真实的杰克·伦敦。
[1] Daniel A Metraux. Jack London and the Yellow Peril. Education about Asia, Spring 2009,(1).
[2] Jack London. A Night's Swim in Yeddo Bay. Oakland High School literary magazine, Aegis, 27 May, 1895.
[3] Jack London. In Yeddo Bay. St.Nicholas Magazine, February, 1903.
[4] http://www.jacklondons.net/writings/ShortStories/o_haru.html.
[5] Jack London. If Japan wakens China.Jack London reports: war correspondence, sports articles, and miscellaneous writings. Hendricks, King, and Irving Shepard, eds.Garden City, NY:Doubleday, 1970.
[6] Jack London. The Language of the Tribe. MidPacific Magazine, August 1915. Reprinted in Daniel J. Wichlan ed., Jack London: The Unpublished and Uncollected Essays.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