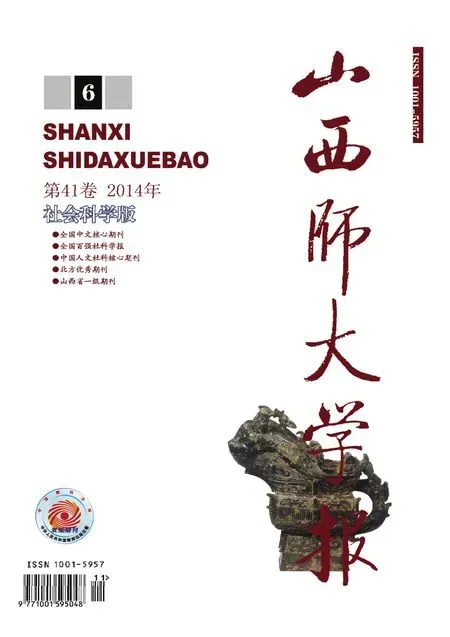创伤的叙事与叙事的创伤
——玛格丽特5阿特伍德创伤主题初探
王 韵 秋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作为北美知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直享有“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美名,并与玛格丽特·劳伦斯、爱丽丝·门罗并称为加拿大文学“三剑客”。2013年,73岁高龄的阿特伍德出版了反思现代性的新作《疯狂亚当》,至今,她仍旧活跃在文学的大舞台上。2013年末,她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虽然最后与奖项失之交臂,却仍不失为一位深度与广度兼备的作家。学界对于阿特伍德的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经过数十年发展,主要以其女性主义思想、加拿大民族文学、生态思想、幸存、权力政治、风格技巧以及互文性等为主,而关于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创伤角度解读则涉及甚少。从创伤这一新视角切入,不仅能丰富阿特伍德作品的阐释空间,而且能使研究进一步向纵深拓展。
一、创伤的叙事
关于创伤的研究最早起源于18世纪的神经病学。早在1766年,神经生理学者麦悌博士就通过一例在创伤后身体机能陆续出现问题最终死亡的伤患病例描绘了创伤与脊髓通路之间的关系,为之后精神分析辖域中的心理创伤这一概念奠定了生物神经学上的基础。此后的一百年间,很多临床医生都对这个主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伦敦外科医生赫伯特发现了创伤性癔症之后,对癔症与创伤之间的研究犹如雨后春笋般在精神病学的各个领域展开。弗洛伊德关于创伤的研究可谓伴随终生。尽管中间颇有曲折,但在其晚年的著作《摩西与一神教》中,他重拾幼年性创伤理论,认为“我们在幼年经验过而又遗忘的那些印象称为创伤”[1]68。与神经生理学所关注的科学性不同,创伤心理学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体验。而正是这种共同的体验性将文学与创伤心理学紧密联系,从而产生了创伤性叙事的倾向。9·11事件为创伤研究各个领域的融合提供了契机,并产生了一批如卡鲁斯、拉卡布拉、赫尔曼等理论家,发展和丰富了经典的创伤心理学研究,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野。这一时期的理论家们普遍认为,人类精神的创伤并非只存在于创伤事件的当时,而是出现在创伤事件之后,作为一种当时无法体会和理解的潜意识被一次次拉回意识领域,在其他时间和地点并在意识层面上被咀嚼和体会。正是这一点使创伤文学叙事扮演着创伤事件滞后的见证者和创伤后遗症的治疗者的双重角色。
正像从叙事的方式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精神健康与否一样,对于已经出现精神疾病的、尤其是创伤性后遗症的患者,叙事又是一条治疗的途径。创伤文学是一种叙事性的精神活动。它一方面是精心安排的文化审美,一方面也是人类精神中潜意识的投射。凯西·卡鲁斯认为,创伤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简单的精神创伤疾病,而在于伤口发出的声音,试图告知我们一个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的现实。现实已经被延迟了,它不仅仅与我们所知的相分离,也与我们语言和行为中的不可知相分离”[2]4。可见,创伤文学的意义也不仅仅是机械地反映社会的创伤事件,沉浸在一种创伤性的叙事之中,而是时刻提醒着人们曾经遭受过的创伤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创伤性行为,为修通过去与现在提供路径。
表现创伤的文学古来有之。从《荷马史诗》、《埃达》、《萨迦》等英雄史诗到《俄狄浦斯王》、《美狄亚》等古希腊悲剧;从《圣经·约伯记》到莎翁的四大悲剧,这些文学创作都是以人类的伤痛为主题,展现了人类从诞生起就必须面对的创伤现实。在英雄史诗中,伤痛是英雄的荣耀。在《圣经·约伯记》中,灵魂的叩击和肉体的伤痛同等重要。而在希腊神话之中,肉体的伤痛能够换取挣脱命运的意识。从文艺复兴开始,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人类从幻想神迹同在的白日梦中苏醒,开始直面人自身的悲剧。科技革命之后,人开始脱离上帝的控制,对自己创造物质的力量感到崇拜,错以为通过对物质的创造就可以消除人因为无法企及宇宙之力而产生的恐惧,但是这种创造并没有治愈人类与生俱来的创伤,而是起到了反效果:我们因此看到浪漫主义作品《弗兰肯斯坦》中创造背后的创伤及预言——人类一旦陷入以造物来弥补创伤的恶性循环之中,人的造物行为就失去了创造的真正意义。这个预言在现代化加速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得到了应验。在盲目的拜物中,人与自我产生了分离,并将自我客体化了,似乎只有在被客体化的对象物身上,人才能找到力比多上的满足。从此,人类开始全面进入弗洛姆所谓的“精神病理世界”。 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创伤文学。具体来讲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述症”文学,指的是文学叙事的创伤性。这类创伤文学在形式上呈现出“创伤后遗症”的特征。先锋派的一些作品,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巴塞莱姆的《白雪公主》等多属于这类。另一类是“述伤”文学,以刻画创伤现实为主要特征。托尼·莫里森的《宠儿》、派特·巴克的《幽灵路》都以描写殖民创伤经历、战争创伤现实为主。作为当代作家,阿特伍德的作品之中呈现出这二者的融合特征。就其风格来讲,阿特伍德的作品以多视角叙述、反讽、互文、剪切拼贴等现代、后现代技巧作为创伤的叙事形式。就其内容来说,阿特伍德保持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深度,以冷静的视角描述了战争、殖民、文化等多重创伤问题。
二、现代创伤叙事与《猫眼》中的叙事创伤
这是一个充满“恶意和侵犯的世界。这个世界中有国家暴力的军队和子弹,也有种族灭绝后的荒芜,有恐怖主义的炸弹,也有人际之间的痛打和诅咒,有日常勒索,也有不怀好意”[3] 4。这也是一个世纪的创伤与文学的叙事相互指涉的时代。现代派的兴起标志着“抑郁症”世纪的开始,一如弗洛伊德所说,在抑郁症患者那里“自我被视为那已被抛弃的客体,那些要加在客体上的一切报复的凶暴待遇都改施于自我了”[4]347。而“现代派本身往往成为自己所反对的对象”[5]34。这种抑郁症式的写作与敏感、容易受创的作家发生了融合,在弗吉尼亚5伍尔夫,普鲁斯特,卡夫卡等现代主义作家笔下,文学叙事也与创伤世纪的叙事发生了融合。他们的文学作品不再指向外部世界,而是将自己视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将一切压抑诉诸于自我,任凭受创的心灵在无始无终的意识流中流动。
由于加拿大的特殊性,阿特伍德的作品叙事风格横跨了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多重叙事边界,也因此融合了从狄更斯到卡夫卡的创伤叙事特色。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中,《猫眼》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特色颇浓的作品。而其意识流的叙事方式也让很多评论家将其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相提并论。如果说《追忆似水年华》是基于普鲁斯特本人的创伤性经验,那么《猫眼》的叙事风格和内容则基于小说主人公伊莱恩的创伤性经验。伊莱恩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50岁左右的故地重游让她迷失在时间与空间的迷宫之中。在伊莱恩的世界里“时间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维,就像空间之维一样……仿佛遗传透明的液态透明体,一个堆一个……有时这个浮出水面,有时那个浮出水面,有时什么也不见,没有一件事情是往而不返的”[6]1。时空的混乱不仅是小说的叙事特色,也是伊莱恩幼年创伤的症候表现。弗洛伊德认为,童年的创伤是人成年精神征候的原因。伊莱恩幼年时期曾两度被好友科迪莉亚置于死地,也因此造成了她精神上的创伤后遗症:分离和重复。这是一组创伤心理学上的用语,分离指的是“意识与记忆的正常联结过程的阻隔,即思想,感情,经历无法整合到意识流”[7]18。创伤造成的分离症状一方面造成了小说叙述者的混乱叙述,另一方面也让叙述者伊莱恩与受创的自己相分离。在曾经的遇害地——木桥要被拆除之时,伊莱恩隐约觉得“仿佛有某个无名然而至关重要的东西被埋在了那下面,或者是,桥上依然有个人,被错留在了上面,在那高高的半空中,无法落到地上来”[6]204。在创伤事件中,她丢失了记忆和自我,而创伤不仅仅止于遗忘。伊莱恩的另一个症状重复也始终折磨着她。弗洛伊德认为创伤始终是在重复中再现。深受创伤折磨的人“更乐意把被压抑的经验当作一种当前的经验来重复,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过去的部分来回忆”[8]13。幼年的创伤性事件实际上并没有离开伊莱恩,而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着强迫性的重复。这种重复性时而是“一个九岁儿童的声音”[6]392,时而以分离的形式闯入她的意识之中。由于创伤具有这种重复性,因此,当事人往往会采取防御措施,从而诱发了闪回和噩梦。闪回是片段性的,犹如一个个黑白画面不时入侵当事人,而噩梦则与创伤事件有关,因为意识层面对任何有关创伤的刺激都会产生回避,因此所有的创伤被压抑进潜意识,并在噩梦中呈现出来。
伊莱恩的噩梦一直伴随她到成年。当她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之后。她不知不觉将潜意识中的创伤和这种白日梦似的创作融合在一起,从而模糊了创伤的叙事和叙事的创伤的界限。但阿特伍德赋予伊莱恩的绘画行为两种含义:其一,绘画是伊莱恩经历幼年创伤后的文化创造产物;其二,绘画是伊莱恩治疗创伤的途径。就前者而言,由于画作的主要模特是幼年时期曾经歧视过伊莱恩的史密斯夫人,因此,以丑陋的史密斯夫人为主题的画作从本源上来说就是一种创伤性重复,伊莱恩只不过在创作中无意识地重复了这个噩梦。就后者来说,这种创造性途径又提供了治愈创伤的治疗方法,起到了叙事治疗的功能。因此,在小说结尾,伊莱恩经历了创伤性的意识流叙事之后恢复了时间的关系。在创造性的绘画和反思中,走出了创伤的阴影。了解到“以眼还眼只会导致更大的盲目”[6]422,她开始了真正的创作,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在交汇的时空中慢慢整理出时间的顺序,并畅想起自己与科迪莉亚的未来:“这就是我怀念的,科迪莉亚:不是某种已经逝去的,而是那种再不会重来的东西——两个老太太,就着一杯茶,在那里开心的咯咯大笑。”[6]438
三、后现代创伤叙事与《盲刺客》中的叙事创伤
当20世纪的现代主义正用“抑郁症”式的方式叙述着精神深处受创的潜意识时,当时间与空间的朦胧展现着形而上的探索之时,二次创伤再次袭来。二战与大屠杀带来的是整个文学世界的沉默。阿多诺在《棱镜》中直呼“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具有文化隐喻功能的诗歌在人类极端的暴力面前只能沦为“沉默的伤痛”。因此,20世纪 50年代大行其道的荒诞派丧失了诗性的隐喻,采用直喻和重复的手段展现了隐喻丧失后的世界。而在垮掉的一代中,精神不堪重负而分裂,因此,我们才看到《在路上》的疏狂漫游和沉思顿悟之间的悖谬。在同一时期的自白派诗歌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般心理痛苦,人生的孤独,不安的经验和异化的主题,而是经过痛苦过度后的淡漠,自我挣扎后的畸形分裂,发展到对自我的冷嘲和对一切的否定。它明显完成了与后现代主义的对接。”[9]454
后现代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后工业社会的语境之中,也是 “后创伤世界”的主要叙事方式之一。创伤的后遗症在此阶段日渐表露出来:信仰的失落、身份的混乱、社会矛盾的激化、道德标准的改变接踵而来。人类彻底进入了精神分裂的社会。在后现代那里,虚构和真相的界限被消解了,一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幻想和真实的混淆。一切矛头指向了自己,主体被自我消解了,也如日益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最终走向自杀的道路。现代人因此完成了从神经症到神经病的转化。
阿特伍德作品虽然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有 “那么一点点的后现代”[10]6。一方面,在她多视角叙述、反讽、互文、剪切、拼贴、多元化等后现代技巧背后呈现的是创伤世纪的精神分裂现症。另一方面,在症候的背后存在着阿特伍德作为一位创伤作家对创伤之后的心理重塑的洞见。以2000年的布克奖获奖作品《盲刺客》为例,这部小说 “通过杂糅了科幻小说、元小说、激情背后的浪漫以及被矫饰过的压抑之后的堕落,戏仿了小说本身及大众品味从而描绘出三四十年代被战争摧毁的一代人”[11]184。在这部小说中,叙述形式上的时空混乱、元小说式的自我解构和体裁上的剪切拼贴与主人公个人创伤和历史创伤的述症方式不谋而合。
从叙事方式来看,小说以“俄罗斯套娃”的形式展开层层叙述:(1)以女主人公爱丽丝为主的主要叙事。叙述者爱丽丝是一位82岁高龄的老者,她回忆了自己家族——蔡斯家族的起落、她和妹妹劳拉之间,以及她们与无产阶级代表亚历克斯之间的情感纠葛。(2)爱丽丝以劳拉之名出版的作品《盲刺客》的叙事。(3)爱丽丝杜撰的小说《盲刺客》中由男女主人公杜撰的科幻故事。(4)公共记忆的代表:报刊新闻,从公众视角解读了蔡斯家族和格里芬家族的纠纷。 当这四层叙述分别被拼凑在一起时,虚幻与现实的界限被彻底消弭了。但是纵观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叙事方式,在时空交错、记忆混乱、解构与建构并存的两极之中依旧依稀可循的线索就是劳拉之死。爱丽丝的个人记忆和公共记忆都是以劳拉之死为开篇:“大战结束后的第十天,我妹妹劳拉开车坠下了桥”[12]1,“上周圣克莱尔大街发生事故,死亡一人,验尸结果为意外死亡……劳拉·蔡斯小姐当场死亡。”[12]4创伤心理学家凯西·卡鲁斯指出创伤并非来自外界的第一次伤害,而是内部记忆对第一次创伤事件的重复。可见,整个故事是建立在创伤性的死亡事件之上。妹妹的幽灵以德里达所称的“不在场的在场”方式萦绕在爱丽丝的意识之中,并在爱丽丝的叙述方式上表现出来。这所呈现的是爱丽丝自我与本真的分裂。
从内容上来看,由于劳拉之死是爱丽丝潜意识作祟下的结果:在明知劳拉会自杀的前提条件下,爱丽丝托出了自己与亚历克斯的恋爱关系,导致劳拉不堪忍受,开车坠下大桥。因此,整个回忆的内容是在对妹妹的爱,和弑妹的愧疚这二者之间展开的。从爱丽丝的回忆内容上讲,创伤性记忆的要比美好的回忆多之又多:爱丽丝的母亲出身天主教家庭,她以虔诚修女的形象造福众人。虽然靠着其奉献的精神在小镇中享有美名,却也以爱与牺牲来要求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爱丽丝自出生以来就被母亲修女般的光辉形象所笼罩,因此无法摆脱“道德的十字架”。在父母的阴影之中负起了照顾妹妹劳拉的责任,并在这种压抑之下萌生过弑妹的念头。而爱丽丝的父亲参加过加拿大皇家军团,1915年就被送上了前线。在一度被认为死亡的情况下,父亲的归来为爱丽丝的家庭带来了希望。随后他继承了蔡斯家族的纽扣厂,但是日子却再也回不到战争爆发之前。战争摧毁了父亲,父亲也将战场上的创伤后遗症带回了家中。母亲为了弥补创伤选择牺牲自己,冒着危险怀孕,最终死于流产。之后,在战争和资本主义权贵阶层的联合冲击下,纽扣厂也面临倒闭的风险。在此情况下,父亲劝说爱丽丝嫁给自己不爱的富商理查德以免遭厄难。作为资本主义利益集团代表的理查德潜心策划了爱丽丝父亲之死的阴谋,夺取了纽扣厂。不仅如此,他一边对爱丽丝施加家庭暴力,一边将魔爪伸向了爱丽丝的妹妹劳拉……
这样看来,《盲刺客》在内容上更似一部主人公的创伤史。既有战争带来的代际创伤,又有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家庭暴力带来的创伤。这些创伤性事件由于创伤的延迟效果被爱丽丝重复回忆,并以症候性的表述方式表达出来。与其他创伤作家不一样的地方是,尽管在小说中呈现了创伤的症候,但是绝处逢生才是阿特伍德的精神。因此,爱丽丝积极寻求多种重塑心理的方式。在《盲刺客》中,叙述不仅是一种述症,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爱丽丝通过叙述潜入到自己的回忆最深处,发现“再也没有比理解死者更困难的事儿了。但是,也再没有比无视他们更危险的事了”[12]521。象征创伤症候的幽灵如果一直被遗忘,它始终会出来作祟,在幸存者心中种下怨恨和报复的种子。死者要以被哀悼的形式才能祛除其“幽灵效应”,重新将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爱丽丝决定将曾经的创伤叙述出来无疑已经是迈向了心理重塑的第一步。
综上所述,20世纪是创伤的世纪,20 世纪的文学叙述方式也具有创伤后遗症的特点。在创伤语境中诞生的阿特伍德作品一方面在叙事中表现出了时代性的创伤后遗症症状,另一方面也在作品内容中隐喻了时代本身的创伤。就创伤的表现形式讲,在阿特伍德具有现代主义特色和后现代主义特色的作品中,意识流、剪切拼贴、消解主体、多视角叙述等手法是一种创伤世纪的症候表述方式。而就其创伤叙事的内容来讲,她又通过现代与后现代的表述方式彰显了民族创伤、性别创伤、政治创伤和文化创伤等各种创伤范畴,并通过其中不断寻求救赎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其对创伤后身份重建的渴望。
[1] (奥)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M].李展开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
[2]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Larocco, Steve. Forgiveness: A Quiet Assault on the Malicious. Christopher R. Allers and Marieke Smit. Forgiveness in Perspective[C].New York: Rodopi BV., 2010.
[4]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 王洪岳.现代主义小说学[M].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6] (加)玛格丽特5阿特伍德.猫眼[M].杨昊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7] 赵冬梅.心理创伤的理论与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
[8] (奥)弗洛伊德文集:第四集[M].杨韶刚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9] 罗明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
[10] Nischik, Reingard.Flagpoles and Entrance Doors:Introduction. Nischik, Reingard. Margaret Atwood Works and Impact. USA: Camden House, 2000.
[11] Howells, Coral An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garet Atwood.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12] (加)玛格丽特5阿特伍德.盲刺客[M].韩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