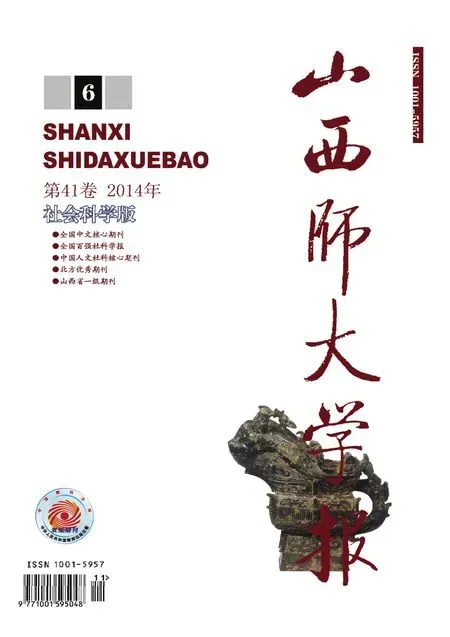语言变革与五四小说叙事“向内转”的实现
王 佳 琴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早在1903年,已经有人开始得益于西方理论看重现代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英国大文豪佐治宾哈维云:“小说之程度愈高,则写内面之事情愈多,写外面之生活愈少,故观其书中两者分量之比例,而书之价值,可得而定矣。”[1]“内外面事情”描写的比重与小说价值的大小是否必然具有如上关系可以进行辩证分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晚清以后中国小说在外国文艺思潮的催化之下逐渐重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则是事实,尤其是五四以后,小说描写的“向内转”成为新文学众所周知的重要特征。学界很多成果已经从小说叙事学的角度对“向内转”进行了描述,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因素使得这种叙事特征能够实现?下文拟从文学语言变革的角度伸入叙事学留下的间隙,重新阐释现代小说的这一问题。
一、不同语言受制下的不同“内面”
古代白话小说很少静态地描写心理,如其描写心理则必与“外面”相联系,“自忖”、“暗忖”的心理内容或表现人物的性格,或推动故事的进展。近代小说《老残游记》、《恨海》中出现了较大篇幅的心理描写,但章回小说使用的却是白话,是站在说书人的立场上讲故事的,因此即使是人物所思基本上也是围绕情节进行的。如《恨海》中棣华与未婚夫伯和走失后“万念交萦”,甚至写到梦境,内容不离对未婚夫行踪的忧虑和思念,由于这一走失对整个故事情节影响甚大,因此这种心理描写是对整体情节的加深。
文言小说似乎走得更远一些,在晚清域外小说的译介影响和小说地位抬高的背景之下,历来被鄙视的小说成了文人抒情的一片园地。甚至出现一边采用小说形式言情,一边又否认小说的矛盾做法,徐枕亚就声言:“余所言之情,实为当世兴高采烈之诸小说家所吐弃而不屑道者,此可以证余心之孤,而余书之所以不愿以言情小说名也。余著是书,意别有在,脑筋中实并未有‘小说’二字,深愿阅者勿以小说眼光误余之书。”[2]598“余心之孤”、“意别有在”之情似乎不宜在小说中道出,然后毕竟还是道了。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连人物都成“余”了,不掩自叙传的色彩,其中大段的自我解剖,使以往由“诗文”来承载的情感在“小道”之中得以抒发,极大地改写了小说的表现领域。从叙事学的角度考察,与“五四”时期郁达夫的主观抒情小说颇为同调。有学者认为:“《断鸿零雁记》正是郁达夫自叙传式小说的先驱。”[3]75“我们通常说,五四小说完成了中国小说由讲故事到表现(向内转)的现代性转化,但是,这个转化尽管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才成为主流,但它的发端却不能不追溯到民国初年的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4]239甚至在颇为挑剔的“五四”时人眼中,苏曼殊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其“所为小说,描写人生真处,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乎。”[5]尽管如此,本文仍想进一步探究的是,二者所使用的不同的文学语言(前者为文言,后者为现代白话),在其“向内转”的叙事转化过程中是否起到了作用,即文学语言在何种意义上、通过何种方式影响了小说的叙事转化,促成了现代小说某些叙事特征的形成。
同为描写“内面”,同为主观抒情,文言和白话所能达到的心理层次是不同的。“五四”文学革命大力批判文言及其所载之道,但是对传统文人来说他们只能运用这一书面语言来表达自身,《断鸿零雁记》中有真切的自我解剖:
余姊行后,忽忽又三日矣。此日大雪缤纷,余紧闭窗户,静坐思量,此时正余心与雪花交飞于茫茫天海间也。余思久之,遂起立徘徊,叹曰:“苍天,苍天!吾胡尽日怀抱百忧于中,不能至弥耶?学道无成,而生涯易尽,则后悔已迟耳。”余谛念彼妹,抗心高远,固是大善知识,然以眼波决之,则又儿女情长,殊堪畏怖;使吾身此时为幽燕老将,固亦不能提刚刀慧剑,驱此婴婴宛宛者于漠北。吾前此归家,为吾慈母;奚事一逢彼妹,遽加余以尔许缠绵婉恋,累余虱身于情网之中,负己负人,无有是处耶?磋乎!系于情者,难平尤怨,历古皆然。吾今胡能没溺家庭之恋,以闲愁自戕哉?佛言:“佛子离佛数千里,当念佛戒。”吾今而后,当以持戒为基础,其庶几乎。余轮转思维,忽觉断惑证真,删除艳思,喜慰无极。决心归觅师傅,冀重重忏悔耳。
(《断鸿零雁记》第十八章)
这样的内心解剖可谓真诚,即令支持白话文学的人也不能掩饰喜爱之情,张定璜曾回忆阅读苏曼殊等人作品时的感受,“如今看起来,我们所夸耀的‘白话的文学和文学的白话’时代以前的东西在形式上也许不惹人爱。不过我喜欢他们的真切。……我最感到趣味的是他们的作家写东西时都牢记着他们的自己,都是为他们自己而写东西,所以你读一篇作品,你同时认出一个人。”[6]这正是民初那类文言抒情小说带来的审美震撼。这里描写的是主人公三郎人生抉择的痛苦心理,对静子不能摆脱的情感带来的心理痛苦应当是十分真切的,但是怎样来表达这种痛苦,在文言系统内只能找到这样一些词语:“百忧”、“尤怨”、“儿女情长”、“家庭之恋”、“闲愁”、“艳思”。如此一来,读者只能将这种心理概括为类似“情网与佛门”等模糊的东西,更具体的内心煎熬则无法得知,只能借助主人公外在的身世和哀情故事去填补和感受。可以说文言“保存着我们最后的旧体的作风,最后的文言小说,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情波,最后的中国人祖先传来的人生观。”[6]与此不同的是,“五四”时期使用现代白话的郁达夫则采取了直接宣泄的方式抵达了人物心理的各个层次,包括文言无法概括的隐秘欲望、性心理等。如“我只要异性的温暖,不管她美与丑……”,心理描写不是靠叙述而是呼喊与倾诉,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那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7]325浸濡在传统文化里的文言没有为个体私密欲望的表达留下空间,包括词汇、语气、表达方式,“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五四”文学语言变革才成全了郁达夫和他的个人叙事,只要作者愿意,他可以随时把情绪、苦闷、欲望等一览无遗地表达出来。由此可见,同为主观抒情,使用文言还是白话直接制约着“内面”书写所能达到的深广度,正是“两种的语言,两样的感情,两个不同的世界!”[6]郁达夫的“此内面”非苏曼殊的“彼内面”,这是由白话所带来的现代小说表现内容方面的重要特征。
二、语言变革与抒情小说散文化的实现
文学语言不仅关系到小说的表现内容,而且关系到怎样表达的方式问题,这一点又影响到小说叙事的结构特征。以往我们多强调晚清抒情小说和五四抒情小说一个是开始,一个是完成,强调二者在叙事转型中的区别是程度不同,这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为什么会如此呢?苏曼殊的小说已经为小说注入了强烈的抒情因素,超越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但是为何只有到了“五四”之后,在郁达夫那里才真正实现了小说结构上的散文化?或者说是什么因素阻碍了苏曼殊小说实现以情感、情绪作为小说的结构主线?可以说,语言是重要的因素。
如前所述,苏曼殊小说中由文言的模糊、抽象概括所无法直接呈现的心理情感,必须借助于他的哀情故事框架,才能更好的体认。也就是说,除了那些大段的抒情和剖白之外,还有大量的故事叙述部分。这些叙述部分能否和抒情部分完美地统合在情绪之中,是实现小说结构散文化的重要条件。如郁达夫的《沉沦》,无非写了留学生的一些日常生活,谈不上曲折的情节,但是所有的外在生活都由其开头所言的“孤独”情绪所笼罩。用文言则很难保持叙述和抒情部分的一致。文言抒情的时候,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但叙事的时候,就舍弃了自我成了客观的历史叙事者,这正是由于使用文言时,同时不得不顺应其表达的方式所致。这一点也许由小说家自己说出来更令人信服。刘半农叙说自己曾经就小说“原质”之一的“文”这一重要问题,问业于一位当时颇负时名的小说家,答语曰:“作文言小说,近当取法于《聊斋》,远当取法于《史》《汉》。……则谓小说即是古文,非古文不能称小说可也。”[8]使用文言叙事时,或不知不觉、或非常自觉地取法《史》《汉》,将小说写成古文。《史》《汉》本来是历史著作,把持一种历史叙事者的立场,从而达到教化和文化整合的目的。无可否认,《史》《汉》笔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世的叙事文学,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叙事文学是以故事为主的,当创作的是一种主观抒情小说时,那种客观(其实不可能完全客观)的历史叙事者与自我抒情的叙事立场就不能完全接合。小说中的文言叙事部分如:
余莫审所适,怅然涕下。忽耳畔微闻犬吠声,余念是间殆有村落,遂循草径行。渐前,有古庙,就之,中悬渔灯,余入,蜷卧石上。俄闻户外足音,余整衣起,瞥见一童子匆匆入。余曰:“小子何之?”童子手持竹笼数事示余曰:“吾操业至劳,夜已深矣,吾犹匿颓垣败壁,或幽岩密菁间,类偷儿行径者,盖为此唧唧者耳,不亦大可哀耶?”
(《断鸿零雁记》第二章)
这里的叙事正体现了古文的高简,与抒情部分不可能统一在“情绪”之下。所以我们在阅读此类文言抒情小说时,有一种直感:小说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叙事的古文,一部分是抒情的古文。如此一来,要实现那种散文化的结构是不可能的。苏曼殊的文言小说已经在文言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实现了个人化的表达,但是终究不可能逾越文言的限度,正如萨丕尔所说,虽然“个人表达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语言尤其是最容易流动的媒介。然而这种自由一定有所限制,媒介一定会给它些阻力。”[9]198文言正是实现以个人情绪为结构的散文化叙事的阻力媒介。只有使用白话,打破文言客观化的历史叙事者的叙事语调,使得叙事部分同出于个人化立场,才能与抒情部分共同服务于“情绪”。有研究者认为,“郁达夫的小说至少有两个要素得效于那一时代的火热现实,即:以现代语取代古代语的‘白话’文学和选用稍稍上升为有利形式的叙事文。”[10]723—724从现代语取代古代语的“白话”语言角度认识郁达夫及其小说可谓一语中的。没有现代白话,就没有郁达夫对苏曼殊的超越,正是现代白话成就了自叙传抒情小说对心理的深层刻画,促成了叙事结构的转变。
理解了郁达夫小说借助白话实现了现代小说对心理的倾诉性描摹,同时就不难理解“五四”时期浅草社作家的小说创作。如果说郁达夫的情感倾诉还是一种理性层面的,那么还有一种心理描写则深入了无意识领域。需要强调的是,白话文学语言是这一领域得到释放和表达的必要条件。这类小说也是“内向”书写的一个重要方面,鲁迅曾将其概括为“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11]343这里的“魂灵”、“心灵的眼睛和喉舌”用更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无意识层面的人物瞬间感受、幻觉、印象等,借用林如稷《将过去》中的话来说就是:“觉得瞬息间有一种灵性的幻感窜入脑内,由这样而想捉住它,更想把它拿来压在纸上——不如此他终不快意。”法国作家杜雅尔丹谈到意识流时曾说:“在内容方面,它是那些存在于最靠近无意识的内心最深处的思想的表达;在性质方面,它是超越逻辑组织的言语,当深层思想产生和到来时,它就把它们再创造一番;在形式上,它应用切成句法最小单位的句子。”[12]121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基本可以认识这种内向的书写。以林如稷的《将过去》为例:
火车是如何的在颤抖……上……下……起……伏……倾……斜……
若水脑内如何的在颤抖……上……下……起……伏……倾……斜……
……
这是一条蛇,赤的,绛的,菜花色,灰白色,……圆长。蛆条……
蛇,载着迷惘,悲愁,含着似陈酒发酵的积郁……
去向那被蛇所认为仇人,人类中之一部分复仇。
曲行,匍匐……
……蠕动……潜行……在蠕动……
凄凄雨……
——去呢……
梦中的吃语,方锥的——有一个整的,……
复仇!复仇!
——站在房子下的人,哦——站在地壳下的人……
同臭虫一般大小……同天,狱的天一般厚薄……
腥恶……不是……生鸡蛋一般的腥恶……
以上是主人公若水在火车上的一段感受描写。从内容方面看,主人公这种“幻感”是个体的、当下的、瞬间的。如此复杂、细腻的现代人“无意识的内心最深处的思想”,用古雅的文言来表达根本无法奏效,只有用白话才可能追踪和表现。从形式方面看,瞬间的感受往往是超现实、超逻辑的,这就需要用“超越逻辑组织的言语”来表达,而白话打破了文言的文法成规,使这种表达成为可能。蛇,赤的,绛的,菜花色,灰白色,积郁,复仇,蠕动……潜行……在蠕动等多种事物、色彩、动作、心理叠加在一起,被“切成句法最小单位的句子”和特殊的标点符号形象呈现了人物瞬间的感受。这样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是现代白话所独有而为文言和旧白话所不及的。
正因此,“五四”文坛对旧白话小说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周作人说:“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旧小说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装不下新思想;正同旧诗旧词旧曲的形式,装不下诗的新思想一样。”[13]“形式”包括叙事、结构等诸多要素,但语言是首要的。“五四”以后的小说与古典小说所使用的语言之不同不仅体现在白话和文言之异,而且体现在旧白话和新白话的区分上。新白话和旧白话在经过小说体裁的“程序聚合”后,会凸显不同的审美特质,实现不同的文体功能,形成不同的审美质地。经过语言变革的现代白话使现代小说实现了不同于晚清文言小说的“内转”,表达了更为个体化的心理内容,并且实现了抒情小说叙事结构的散文化,是小说现代转型的重要方面。由此,从语言变革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学发展的某些内在规律。
[1] 璱斋.小说丛话[J].新小说,1903,(7).
[2] 徐枕亚.《雪鸿泪史》自序[A] .吴组缃,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6)[C].上海:上海书店,1991.
[3]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 钱玄同.致陈独秀信[J].新青年,1917,( 3).
[6] 张定璜.鲁迅先生[J].现代评论,1925,(7—8).
[7] 郁达夫.忏余独白 [A] .卢今,范桥编.郁达夫散文(下)[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8] 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J].新青年,1917,(3).
[9] (美)爱德华5萨丕尔.语言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0] (美)郜淑禧.郁达夫中短篇小说的结构和意义[A].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研究资料[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11]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5小说二集》导言[A] .吴福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2] 张怀久,蒋慰慧.追寻心灵的秘密——现代心理小说论稿[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2.
[13]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J].新青年,1918,(5).
——岭南历史文化名人图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