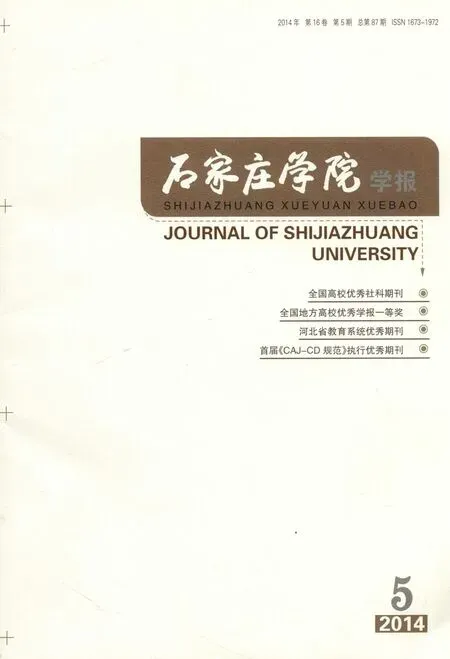知性与人情
——论周作人的饮食散文
何亦聪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知性与人情
——论周作人的饮食散文
何亦聪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饮食散文在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中占有一定比例,但与同时期或稍后的其他饮食散文作家相比,周作人的饮食散文创作有明显的特殊性。这既与其丰厚的学养有关,也与其复杂的思想背景有关。周作人饮食散文创作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充满知性,二是富有人情味。事实上,这两个特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作人散文的整体风貌。
周作人;饮食散文;知性;人情
无论从哪个方面考察,周作人在饮食散文作家队伍里似乎都是个异数。比如,在写作姿态上,其他作家谈吃,多数是“有意为之”,梁实秋有《雅舍谈吃》,汪曾祺有《五味集》,邓云乡有《云乡话食》,赵珩有《老饕漫笔》;而周作人的饮食散文虽也有十几万字之多,却显得零零星星,写作时间既不集中,文章风格亦不一致,而且相当一部分还是1949年以后发表在《亦报》报头的“豆腐块”,直到后来才由钟叔河收集起来编为一本 《知堂谈吃》,这多少显得有点像是“无意为之”的结果。再比如,在写作内容上,其他作家谈吃多是极尽渲染之能事,把人生的阅历、天南地北的吃食、酸甜苦辣的味道悉数融汇于短短几篇文章之中,引得读者食指大动之余不禁慨叹;而周作人却总是只捡几样乡野小吃淡淡描述几句,文章语气简素到不能再简素,从阅读效果上来说,很难引出读者的口水和食欲。因为这种种的不同,所以许多人在对现代饮食散文进行划分的时候,都有意识地突出了这种差异性,譬如有人将饮食散文分为“文人的”和“学者的”,认为梁实秋、汪曾祺、邓云乡等人的饮食散文是“文人的”,而周作人的饮食散文则是“学者的”;又比如有人将饮食散文分为“贵族的”和“平民的”,认为梁实秋、唐鲁孙、沈宏非等人的饮食散文是“贵族的”,而周作人、汪曾祺的饮食散文则是“平民的”。这些划分都不无根据,只是免不了有过于笼统和简单化的嫌疑。
与其划分类别,不如研究个案。文人谈吃,重点不在谈吃,而在文人;不在谈什么,而在怎么谈。换句话说,就是关键在于寻求其题外之旨,看到谈吃的背后是什么,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周作人饮食散文的特殊性,或许能有所得。事实上,周作人的饮食散文创作之所以显得像是“无意为之”,是因为他有一套自己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理念”,而谈茶谈酒谈点心,正如谈妇女谈儿童谈草木虫鱼一样,是他 “文化结构”很自然的一部分,也是他“文化理念”很自然的体现。他的这种“文化结构”较为复杂,可以从《我的杂学》里看出来,而他的文化理念,则可以用舒芜一篇论文的题目来概括——“向低处广处看”,因为是“向低处广处看”,所以必然要注意人世中的种种琐屑,包括油盐酱醋草木虫鱼,这就是周作人饮食散文特殊性的关键所在——其他任何饮食散文作家创作的背后,都不存在这样一套复杂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理念”。这种“文化结构”和“文化理念”反映到其饮食散文创作上,就体现为两点:一是充满知性,二是富有人情味。第一点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学者气”,第二点则容易被误认为是具有“平民性”。其实并非如此,这两点只是周作人“疾虚妄”与“重情理”的一贯态度罢了。
一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1]1这是周作人《知堂说》一文的开篇,“知”在周作人的思想体系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若单纯从这篇短小的文章看来,似乎源出于儒家,而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周作人最钦佩王充‘疾虚妄’的精神,自号‘知堂’,固然源出于孔夫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圣教’,但究其‘神’,还是王充的‘疾虚妄’。”[2]450“疾虚妄”这三个字,打中了周作人的“知”的概念的核心,正因为“疾虚妄”,痛恨一切虚伪的、矫饰的东西,所以才希望去知道,去了解,并强调“知”的重要。
但是,并不能就此认为周作人的“知”与儒家思想无关。“疾虚妄”是“知”的因由和根骨,那么其间的血肉和内容是什么?也就是说,知什么?这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19世纪40年代初,周作人写过一篇《汉文学的传统》,收在《药堂杂文》里面,其中引焦循《易余龠录》卷十二一则云:“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3]5这是很浅近明白的道理,但是在儒家思想中却向来未得到重视,所以周作人评论说:“此真是粹然儒者之言,意思至浅近,却亦以是就极深远,是我所谓常识,故亦即真理也。”[3]5常识即真理,这是周作人的一贯主张,倘若与儒家思想对照来看,可以看出两种相似的趋向:一是对形而上的、不可知的、玄虚神秘的食物的疏离,或周作人所谓“现世主义”的态度;二是对人生的、现世的、琐细常识的重视。孔子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4]40这句话周作人十分看重,他曾评论说:“鄙人岂敢高攀古人,不过少也贱则相同,因之未能求得一家之学,多务杂览,遂成为学艺界中打杂的人,亦不得已也。”[5]1这里,他自称“打杂的人”,看起来像是谦虚,实际却是非常自负,他是深以自己的多务杂览和常识丰富为傲人之资,并确信这些杂乱的知识都有价值,所以才能不顾当时舆论几乎一致的反对甚至谩骂指责,写草木虫鱼,写喝茶吃酒,写乡俗市声。
这就是周作人饮食散文背后的文化理念,这种文化理念体现在他的饮食散文创作上,就表现出一种知性的色彩,但是,在这里,“知性”有更为复杂的内涵。
首先,“知性”在周作人的创作中,是与“诗性”相对立的一个概念。他曾明确地说自己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6]628,而不是诗的,所以其中并不存在知性与诗性的统一,反而呈现出一种对诗性的有意的疏离,体现在写作风格上,就是不喜夸张,不喜渲染,不喜抒情。这一点,相对于绝大部分散文家对诗意的强调显得十分特殊,但是放进周作人的思想框架中去考察,就会发现这其实很自然——不过是 “疾虚妄”精神在文艺创作中的延续而已。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性格方面的因素,周作人说自己不是情热的人,这是实话,从他对喝酒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凡事过度就会难受,不必一定是喝酒至醉,即吃饭过饱也是如此。”[1]292-293这种态度显然与“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7]610的潇洒豪迈大有区别。所以,相对于其他作家,周作人在饮食散文创作中更加注重传达知识,描述时显得冷静、细致、严密,极少夸张、想像、抒情,如《谈酒》一文中,他描写饮酒风习云:“正当的喝法是用一种酒碗,浅而大,底有高足,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香槟杯。平常起码总是两碗,合一‘串筒’,价值似是六文一碗。串筒略如倒写的凸字,上下部如一与三之比,以洋铁为之,无盖无嘴,可倒而不可筛,据好酒家说酒以倒为正宗,筛出来的不大好吃。”[1]280寥寥几语,谈了酒碗又谈“串筒”,谈了价钱又谈形状,交代得清楚明白,非文章老手不能为。其他饮食散文作家在写作中多数更为注重传达情感和人生体验,而非琐细的常识,因此也就不具备这样的细致和严密,夸张、渲染自属寻常,有时甚至不免有穿凿之嫌。以梁实秋的《面条》一文为例,其中有段文字谈起诗人尹石公,说他称许李渔 《闲情偶寄》中的话:“味在汤里而面索然寡味,应该是汤在面里然后面才有味。”[8]145并据此道理试验:“第二天他果然市得小小蹄膀,细火焖烂,用那半锅稠汤下面,把汤耗干为度,蹄膀的精华乃全在面里。”[8]145下面而“把汤耗干为度”,闻所未闻,且蹄膀汤本就重浊油腻,以此下面而把汤耗干,结果恐怕只能是一锅油糊糊,所以这一段故事多半是为了附会李渔的道理穿凿而成,未必可信。
其次,其他饮食散文作家的创作中当然也包含许多知性的因素,但是就其内容而言,还是与周作人的饮食散文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其他饮食散文作家所传达的知识主要是烹饪的,关于吃的;那么周作人的饮食散文所传达的知识就主要是民俗的,关于人的。如汪曾祺谈“白肉火锅”云:“白肉火锅是东北菜。其特点是肉片极薄,是把大块肉冻实了,用刨子刨出来的,故入锅一涮就熟,很嫩。白肉火锅用海蛎子作锅底,加酸菜。”[9]134几句话就把白肉火锅的用料、特点说清楚了,要点很突出,且没有一句废话,读来干净爽脆。这是汪曾祺饮食散文的一贯特点,可称手笔不凡,但是其视野也就限定在了吃的方面,范围小,题目小,上来就直奔主题,才能这般利落。周作人则不同,他写文章绝不存在“直奔主题”这一说。以《谈油炸鬼》一文为例,其中写道:“乡间制麻花不曰店而曰摊,盖大抵简陋,只两高凳架木板,于其上和面搓条,傍一炉可烙烧饼,一油锅炸麻花,徒弟用长竹筷翻弄,择其黄熟者夹置铁丝笼中,有客来买时便用竹丝穿了打结递给他。做麻花的手执一小木棍,用以摊饼湿面,却时时空敲木板,的答有声调,此为麻花摊的一种特色,可以代呼声,告诉人家正在开淘有火热麻花吃也。 ”[1]424这哪里是在“谈油炸鬼”,简直活画出一幅情趣十足的风俗画,制麻花的器具、各色人物的动作以及前后过程都历历在目,在这里,重要的倒是民俗,而不是吃食了,且其语言优婉雅致,与汪曾祺语言的明白干脆也大异其趣。这,是周作人饮食散文的另一个特殊性之所在。
那么,能否将周作人饮食散文的“知性”特色等同于“学者气”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如果可以将“学者气”领会为学院派、学理性的话,其中就存在两种明显的差异。第一种差异在于,周作人并未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从知识结构上来说,他是个杂家,依照个人的兴趣杂览,“我平常没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就只喜欢涉猎闲书,这岂不便是道地的杂学,而且又是不中的举业,大概这一点是无可疑的”[1]574。 所以,周作人饮食散文的“知性”色彩也带有一种边缘性的杂家气,甚至可以说是野狐禅气息,这一点与“学者气”的散文是大为不同的。第二种差异在于,周作人的饮食散文虽充满知性,却并非以传达知识为根本目的的科学小品,他的目的在于人,其知性的背后有更为广大宽阔的人情作为底色,时时呈现出大关怀、大悲悯,这,才是其饮食散文创作最突出、最可贵的一个特点,也是接下来要论及的第二个主题。
二
上文已经谈到,周作人的散文知识丰富,不仅饮食散文如此,其他散文也是如此,其中包含着各种各样、各方各面的知识,数量之大,门类之广,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但是,如果纯粹从知识的角度看,其价值也不过是一种经验的累积而已,除了文笔优胜、选择精当外,并不比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强到哪里去。关键之处在于,事实上,周作人关于这些知识的种种努力,部分当然是出于兴趣,更大程度上却是为了构筑一个庞大的由各方面常识组成的“人学”体系,或者严格地说,是作为一个健全的人所理应具有的知识结构,这是与鲁迅“尊个性而张精神”[10]54所不同的另一种“立人”方案,可是历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也就是说,周作人的种种“常识”,都是奔向一个总目标去的,这个总目标即是“人”,包括饮食散文中的知识,也是其“人学”体系中之一小部分。
既然目的是人,那么其创作中就自然会流露出对人的关怀、理解和宽容,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点。中国自步入20世纪以来,就未有片刻宁静,人们既惊诧于西方的先进,又不满于自身的落后,因此各种文学作品中充斥着高调的呼声、愤怒的指责,以及对人性的严厉的审视,即使是恬淡平和如丰子恺,也在《吃瓜子》一文的结尾这样写道:“试看糖食店、南货店里的瓜子的畅销,试看茶楼、酒店、家庭中满地的瓜子壳,便可想见中国人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间,每年统计起来为数一定可惊。将来此道发展起来,恐怕是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呢。本来见瓜子害怕,写到这里,觉得更加害怕了。”[11]212将吃瓜子这样的小事情上升到国家危亡的高度,现在看来或许奇怪,但在那个时代却是种很平常的现象。周作人似乎总有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敏感,也许在当时他就敏锐地感觉到人们的情绪太急躁了,火气太旺盛了,中国缺少一种容忍的氛围,更加缺少一种对人性的理解和宽容,所以他才会在《北京的茶食》里写下这段有名的文字:“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12]5这种对待人们的日常享乐的态度显然远比丰子恺更富有人情味,因此也就更加深入人性,更加贴近人生。
重情理,有人情味,正是周作人思想与创作的另一大特点,与“疾虚妄”相呼应。周作人很欣赏李贽的一段话:“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13]21由此可见,饮食在周作人这里并不仅仅是吃吃喝喝,而是人伦物理之一部分,写饮食散文即是谈人伦物理,看似普通,实则非常重要。
以上种种,就构成了周作人饮食散文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可以用“表里不一”四个字来概括,似小而实大,似理而实“情”①这里的“情”之所以要加引号,是因为它不是普通的抒情,而是博大又微妙的人情。,似简淡而实丰腴,似琐细而实宽广。但是这种“表里不一”又不是刻意造作出来的,而是周作人自身思想性格复杂性的一种自然体现,这就容易让人感觉读周作人的散文仿佛隔着一层,有种疏离感,而一旦走进去,又发现其实里面妙境无穷。当然,谈到饮食散文,关键还是在“人情”两字上,下面试从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首先,周作人的饮食散文中充满了对下层人民生活的关注和体贴。这一点,如果找比较简单的证据,那么可以从文章的题目看出几分,如《腌菜》《锅块》《六谷糊》《臭豆腐》《馒头》《吃青椒》等,都是下层百姓的日常吃食,与梁实秋的《狮子头》《西施舌》《佛跳墙》《醋溜鱼》可以说是大有区别。但是重点还是在“体贴”两个字上,也即“理解之同情”,这才是体现其人情味的地方,如他在谈到乡下人吃酒的时候说:“中国智识阶级大都是城里人,他们只知道城里的吃酒法,结果他们的反应是两路,一是颓废派的赞成,一是清教徒的反对。颓废派也就算了,清教徒说话做文章,反对乡下人的奢侈的享乐,却不知他们的茶酒烟是一样,差不多只是副食物的性质,假如说酒吃不得,那么喝一碗涩的粗茶,抽一钟臭湾奇,岂不也是不对么。 ”[1]300-301这真是设身处地为乡下人说话了,若无深入其中的体察,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的。
周作人在1949年以后所写的饮食散文多有这样的议论,一方面是对乡民生活的由衷赞赏,另一方面是对“智识阶级”和城里人的讽刺轻蔑,上面的引文即是一例,又如他称赞锅块为“朴实可喜”[1]442,谈起“一块咸鱼,一碗大蒜煎豆腐”[1]367这种“穷措大的盛馔”[1]367也是津津有味,说到粽子时则写:“满口吃着粽子,却还不知做粽子的米是怎样的,这实在是城里人的一种耻辱。”[1]454而在他早期的饮食散文里,这个特点虽也有些端倪,却并不十分突出,特别是对“智识阶级”的嘲弄,更是少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显然这里面有解放以后受另一种普遍性价值观的影响,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周作人本来思想性格中就有某些与这种新价值观相契合的东西,到1949年以后,那些契合之处就被有意地凸显出来。那么,能否因此就认为周作人的晚期饮食散文具有鲜明的“平民性”和“平民立场”呢?周作人早年曾提倡“平民的文学”,但是从他以后所写的文章看来,似乎对此提法并不以为然,在《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的最后,他说:“从文艺来说,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凡人的超人化,因为凡人如不想化为超人,便要化为末人。”[6]75如此看来,他的立场并不是“平民的”。再具体看他的文章,不难发现,归根结底,周作人还是作为“智识阶级”之一员对平民的生活发议论,无论他自己承认与否,事实都是如此。“大关怀”也好,“大悲悯”也好,其姿态都是居高临下的,而非平等的,自始至终,周作人所坚持的立场都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6]34,这种立场必然与所谓 “平民立场”相冲突。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周作人这种立场的可贵之处,看到其中的宽和与真诚,这种立场既与解放后的强调“阶级性”而非“个人性”的立场不同,也与之前其他的许多作家不同。以梁实秋的《吃相》一文为例,其中描写了一些体力劳动者粗鲁饕餮却又豪爽痛快的吃相,然后似乎不无欣羡地说:“上面这两个景象,我久久不能忘,他们都是自食其力的人,心里坦荡荡的,饥来吃饭,取其充腹,管什么吃相!”[14]267这也是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但已经不是周作人式的悲悯和同情,而近于文人的矫情了。
其次,宏大的悲悯与微妙的人心,广博的知识与精细的观察,在周作人的饮食散文里得到了极其自然圆融的结合,这就使得其人情味渗透于行文的细节之中,真实可感。如《喝茶》文中描写学生吃“干丝”云:“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最为合式。因为一到即磬,次碗继至,不遑应酬,否则麻油三浇,旋即撤去,怒形于色,未免使客不欢而散,茶意都消了。”[1]268寥寥几笔,学生的盘算,堂倌的喜怒,都历历如画,仿佛就在眼前。又如描写酒保筛酒云:“唯酒保好于量酒之前先‘荡’串筒,荡后往往将清水之一部分留在筒内,客嫌酒淡,常起争执,故喝酒老手必先戒堂倌以勿荡串筒,并监视其量好放在温酒架上。”[1]269这本是市井小民之间勾心斗角的平常事,事情既是无趣,人物亦非特别,但是由周作人的笔娓娓写来,就满含人情和风趣。之所以能如此,一方面当然在于对人物微妙心理的敏锐把握;另一方面还在于,周作人看似平淡的描述语言的背后,充满了对人性的理解、同情和悲悯。因此,即使在描述委琐无聊的市侩行径时,他的语言也不是批判性和带有讽刺意味的,反而显得十分温厚体贴。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鲁迅的散文是“憎多于爱”,而周作人的散文是“爱多于憎”。
此外,对儿童和儿歌的留意,也是周作人饮食散文富有人情的一种体现。如《卖糖》一文中有这样的话:“绍兴如无夜糖,不知小人们当更如何寂寞,盖此与炙糕二者实是儿童的恩物,无论野孩子与大家子弟都是不可缺少者也。”[1]42这种对儿童天性有着深切的理解与体察,充满慈爱且纯出自然的文字,除了周作人和丰子恺,大概没有第三个人写得出了。有时候,温和慈爱也会一变而为诙谐风趣,如描写卖糖者“虚左手持一小锣,右手执木片如笏状,击之声镗镗然,此即卖糖之信号也,小儿闻之惊心动魄,殆不下于货郎之惊闺与唤娇娘焉”[1]428。这就略带一点点调侃的意味了,但是稍现即收,并不会过头进而显得油滑,底色仍然是温和慈爱的——这种平和而不过头的境界,则丰子恺亦不能及。
总之,目的是人,前提也是人,这不仅是读周作人的饮食散文,也是读他的任何文章都必须了解的一个关键点。因为目的是人,所以欲了解人,就必须了解与人有关的各种知识,包括饮食,这是知性;因为前提是人,而人有人之天性,除了保证基本生存之外,还想吃不求饱的点心,喝不求解渴的茶酒,所以食色种种,当然也应该予以重视,这是人情。鲁迅的思路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15]51,而周作人则似乎更趋向于去关心如何将“生存”提升为“生活”。早在1918年,周作人就在《人的文学》中对“人”进行了定义,他强调两点:一,人是“从动物”进化的;二,人是从动物“进化”的。第一点是生存层面的,第二点则是生活层面的。先生存,后生活,顺序当然如此,但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其能够“生存”,而在于其能够“生活”,重视有关“生活”的各种琐碎知识,理解有关“生活”的各种人之天性,有了这样的重视和理解,再进而塑造出懂得“生活”的健全的人——这,是周作人的思路,顺着这样的思路再来重读他的饮食散文或其他散文,一切就豁然开朗了。
[1]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卷九[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2]钱理群.周作人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3]周作人.药堂杂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王国轩,张燕婴,蓝旭,等.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周作人.药味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6]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卷三[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7]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8]梁实秋.雅舍谈吃[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9]汪曾祺.五味[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
[10]鲁迅.鲁迅全集:卷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1]丰子恺.丰子恺作品精选 [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12]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卷六[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13]李贽.焚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1.
[14]梁实秋.梁实秋名作欣赏 [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1.
[15]鲁迅.鲁迅全集:卷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责任编辑 周亚红)
On Zhou Zuoren’s Diet Essays:Intellectuality and Human Feelings
HE Yi-cong
(School of Arts,Shanxi University,Taiyuan,Shanxi 030006,China)
Diet essays hold a certain proportion among Zhou Zuoren’s works.However,his works obviously have their particularity compared with those of other writers in the same or latter era,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his profound academic accomplishment as well as his complicated ideological background.The feature of Zhou Zuoren’s essays on diet can be summed up as intellectuality and human feelings,which actually reflect the overall style of Zhou’s works from one side.
Zhou Zuoren;diet essay;intellectuality;human feelings
I207.6
:A
:1673-1972(2014)05-0082-05
2014-06-19
何亦聪(1985-),男,河南濮阳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