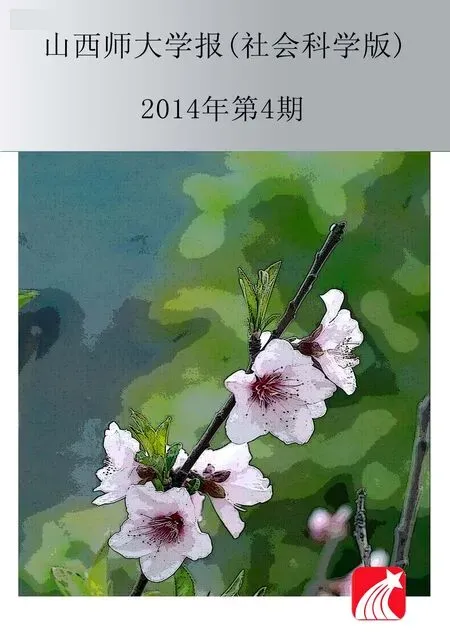“三改”与戏曲现代教育的确立
董 昕
(中国戏曲学院 科研与研究生工作处,北京 100073)
1951年5月5日,由周恩来签发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简称“五五指示”)面向全国发布,《指示》的中心内容是“改戏、改人、改制”,即俗称的“三改”。“三改”的提出迅速掀起了戏曲改革的高潮,各地纷纷展开了对戏曲剧目、戏曲工作者、戏曲制度等的全面改造。与以往不同,新中国的戏曲“三改”运动是一场由政府主导,有专门机构、政策、制度保障的,由新文艺工作者和戏曲艺术工作者共同参与的,涉及戏曲所有剧种的,从内到外、由上至下、史无前例的全覆盖式的戏曲现代化改革与改造工程。“三改”成功地将戏曲教育从传统推向了现代,顺利完成了对戏曲教育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使它快速地迈向了现代化的教育进程。
一、“改戏”与戏剧教育内容改革
“改戏”,重点是审定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并对其文学形象和舞台形象进行适当的修改。
1951年中央《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了戏曲改革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剧目审查的标准是“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戏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审定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对其中的不良内容和不良表演方法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修改。对旧有的或经过修改的好的剧目,应作为民族传统的剧目加以肯定,并继续发扬其中一切健康、进步、美丽的因素。”同时“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1]1328。
《指示》将戏曲改革工作定位为“改革旧有社会文化事业中的一项严重任务”[1]1328,它关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教育和影响广大人民的“重要武器”,因此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随着戏曲改革工作的开展,一方面不断有一些传统剧目被禁演。从1951年4月至1952年3月间,连续五次发出停演剧目的通告,先后有《大劈棺》等14出剧目被禁。另一方面,澄清舞台形象也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革除庸俗落后的表演方法,如跷工、走尸、淫荡猥亵的动作、恶俗的噱头、不科学的武功等;二是取消丑恶、野蛮、恐怖的舞台形象,如厉魂恶鬼、酷刑凶杀、狰狞的和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脸谱等;三是改革旧戏曲舞台陋习,如台上饮场、出台把戏、检场人出头露面等。总之,舞台上一切野蛮的、恐怖的、猥亵的、落后的、奴化的、侮辱自己民族的、反爱国主义的内容都在革除之列。[2]31经过一段时间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造工作,戏曲舞台呈现出一派全新的、健康的气象。
由于新中国的戏曲教育继承了戏曲传统教育中的成品(剧目)教学的理念和模式,因此通过审定和改编的戏曲剧目,以及按照“改戏”精神进行加工、创作、整理过的传统教学剧目,如京剧《新十三妹》、《新白蛇传》,川剧的《秋江》等都成为新中国戏曲教育的专业教学剧目。可以说,“改戏”工作的实施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新中国戏曲教育专业教学的内容与内涵,推进了专业教材的建设工作。
二、“改人”与艺人文化修养的提升
“改人”的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提上了日程。关于如何改造艺人,毛泽东曾在1944年《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提到两个原则:一是团结,二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延续这一精神,周恩来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我们应当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尊重他们方能改造他们”。尊重便是团结,改造便是批评教育,但尊重和团结是前提。
建国初期,秉着团结为主、批评教育为辅的精神,全国各主要城市以讲习班、文化识字班、艺人学校、戏曲座谈会、竞赛公演等方式对艺人进行了教育。据统计,截至1950年12月,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均举办了艺人讲习班或艺人学校一期至三期,参加学习的艺人约有五万人。[1]1319
1951年5月出台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对“改人”问题也尤为重视,它将戏曲艺人的作用提升到了“在娱乐与教育人民的事业上负有重大责任”的高度,要求戏曲艺人“应在政治、文化及业务上加强学习”,强调“改人”工作的重要性。
《指示》发布后,立即得到了戏曲界的响应。截至1951年底,接受过学习的艺人已经成倍增加:如“东北全区9000余艺人中有5600余人参加了文化学习,其中有很多人由文盲而粗通文字,约有8000余人参加了各地的艺人群众组织,成立了戏曲改进会、戏曲协会等,进行了业务与政治常识的学习。”[1]1338经过学习和改造,艺人们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这突出地体现在戏曲艺人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响应和支持上。1951年4月,刚刚成立不久的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就组织了部分师生赴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号召时,各地剧团班社的演员以及戏曲学校的专业师生更是争先恐后地举行义演,很多脱离舞台几十年的老艺人、老教师也纷纷登台演出。
首都戏曲教育界为捐献飞机,于1951年6月还组织了五场义演。如萧长华、郝寿臣、尚和玉、鲍吉祥、谭小培、张德俊、马德成、侯喜瑞、贯大元、雷喜福、谭富英、华慧麟、姜妙香、李桂春、方连元、宋富亭、梁连柱、范富喜等一大批老中青教师和相当一部分学生也参加了义演。田汉还特意为义演活动题写了一副对联:“学来粉墨春秋谈唐说宋,鼓舞风月儿女抗美援朝。”有“通天教主”之称的王瑶卿还担任了义演的舞台监督,五场义演的全部收入都上交了抗美援朝总会。[3]76豫剧演员常香玉更是领导全团在两个月时间通过大量的演出,募得3.6亿元(旧人民币)的捐款。可见,通过改造,戏曲艺人的思想觉悟有了较大的提高。
除了对戏曲艺人进行改造外,政府还格外注重对戏曲教育机构中的师生员工进行教育。建国前夕,政府在接管旧的戏曲教育机构的同时,也将原机构中的教师和学员一并接管。如1950年1月成立的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就是在被接管的原国民党青年军二〇八师四维剧校三分校的基础上建成的。学校成立伊始,其专业教师大多是从解放前的名艺人或旧科班、旧学校教习中聘请的,他们经过建国初期一系列对旧艺人尊重、团结、改造政策的影响,在思想情感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转变。如1950年开始在戏曲实验学校任教的李甫春先生回忆:“那会儿,我们脑袋里只有四个字,就是‘听党的话’。我们大家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都争着干活,在这种环境下出成绩也是理所当然的事。”[3]145再如1937年入荣春社科班学习,1947年在四维剧校任教,后随四维剧校一起迈入新中国新学校的汪荣汉先生也谈到:“解放以后,学校的条件越来越好。老师和同学生活有了保障,当时大家学习和排练的热情都很高。后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国家需要我们这些人去朝鲜慰问演出,我们自然责无旁贷,义不容辞。”[3]136
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作为新中国建成的第一所新型戏曲学校,在接收改造旧艺人的同时,其主要任务还是以新社会的思想理念和全新的社会关系为内容,通过教育改革实验来培养新社会所需要的戏曲人才,即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建设人才和新型的戏曲人才。何为新型戏曲人才?当时戏曲实验学校的老师是这样理解的:“有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没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有没有创造精神,这是衡量新型戏曲人才的重要标准。”[3]130在培养新型戏曲人才的具体做法方面,戏曲实验学校“主要通过政治课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参加一定的社会实践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让学生明白学戏、演戏不仅仅是为个人找一个有名有利的好职业,发挥个人才能,而且还要懂得个人的命运和前途总是同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联系在一起”[3]130。关于当时的教学内容,戏曲实验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苏移回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三改’政策的指导下,学校为我们安排了文化课。当时提出‘改人’,就是让戏曲演员对艺术要有正确的认识,对于旧的习俗要进行批评。……老校长史若虚亲自给我们上课,讲文艺是什么,戏剧是什么,它应当摆在什么位置,演出的意义是什么……”[3]156
“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拟定的《共同纲领》中对新中国教育任务的描述。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戏曲艺人通过参与这项教育改造工程,普遍从目不识丁到认识几百字,基本完成了从卖艺赚钱到为社会主义戏曲文化事业建设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转变。通过改造学习,他们无论是政治觉悟,还是文化修养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参加戏曲改革建设工作的积极性也随之高涨。这不仅为建国初期的戏曲改革工作奠定了基础,也为新中国戏曲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三、“改制”与戏曲现代教育的发展
“改制”是改革原有制度中那些不合理的部分,包括剧团体制、艺术体制、教育体制和剧场管理体制等多个方面。
就教育体制而言,随着1951年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实施,戏曲(中等)教育被列入了国民教育序列,戏曲教育机构被纳入了中等专业学校的范畴,同时国家还规定了戏曲学校的修业年限、招生条件等均参照中等技术学校的标准执行。
1952年3月31日,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指出:“各类各级中等技术学校,均应根据各业务部门的具体需要,明确规定其方针与任务,并逐步地与适当地实行专业化与单一化,务必学用一致,使所培养的人材确能适合各业务部门的需要。中等技术学校除给学生以专门的技术训练外,必须实施政治教育和基本的文化与科学知识教育。因此,各类各级中等技术学校的课程应包括普通课、技术课及实习,纠正与防止单学技术忽视政治、文化学习的偏向。普通课的科目以及普通课与技术课所占的比重,应根据学校的性质、学生程度和修业年限分别规定。”[4]146—147文件的第九条还特别指出,本指示对于艺术等中等专业学校同样适用。文件一经发布,各级各类戏曲学校纷纷响应。戏曲实验学校于1953年成立了教务科(不久后改为教导科),主要管理政治文化教学,还有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学校还提出要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相应开设了政治课和文化课。
除课程改革外,很多戏曲教育机构还在教风学风上加大整改力度,一方面废除了打骂制度,明确提出“不打、不骂、不损(讽刺挖苦)、不罚(体罚)”的口号,另一方面积极推行民主制,强调“尊师爱生”,这在戏曲教育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数百年来,“打戏”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学生与老师都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不打不骂学不出真本事。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戏曲学校却废除了这一制度,这对于以身体技能训练为主的新中国戏曲教育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戏曲实验学校的首任校长田汉先生对此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封建社会靠鞭子,资本主义社会靠饿肚子,社会主义社会靠自觉。”[5]52这些新型戏曲学校正是靠循循善诱、启发帮助、因势利导,靠政治思想工作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鼓励他们勤学苦练,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引导他们走上了又红又专的正确道路。
《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中还明确指出按专业化、单一化的原则调整学校,并提出将中等专业学校转归有关业务部门领导的必要性。根据这个指示,当时的中央教育部与中央各业务部门、大区及省市的业务部门和教育部门于1952年即着手整顿和调整中等专业学校。1953年,中央高等教育部与有关业务部门及教育部门更进一步将全国中等专业学校作了比较全面的调整。在工作进行的过程中,曾将许多条件十分不足的学校予以停办,并将大部分私立的技术学校改为公立,把原来那些多科综合的职业学校改组成具有明确培养目标的单科性的中等专业学校。到1953年9月,全国中等专业学校数由原来的794所调整为651所。
在院系调整的大背景下,1950年成立的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于1951年4月改属中国戏曲研究院,并更名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实验学校。1952年11月20日,根据教育部规定的中等技术学校以所在地命名的规定,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实验学校更名为北京戏曲实验学校。1953年,北京市接管了创办于1952年的北京私立艺培戏曲学校,并更名为北京市戏曲学校。为避免重复,北京戏曲实验学校于1954年再次更名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学校。同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撤销六大行政区委员会①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划分为六大行政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东北戏曲实验学校划归中国戏曲研究院领导,并入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实验学校,定名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实验学校沈阳分校。1955年1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戏曲实验学校归属文化部直接领导,正式命名为中国戏曲学校。不难看出,从该校成立至最终定名,几乎每一年改一次校名,其实变更的不止是名字,更是行政隶属,也就是管理体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建国初期戏曲现代教育建设和发展的整个历程。
总之,在戏曲制度的改革过程中,随着对不合理的旧制度的废止和改造,以及新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不仅使国家意志和理念通过法规的形式成为新社会戏曲人的行为准则,并形成文化的渗透,而且还使“改戏”与“改人”所取得的成果有了制度化的保障。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内,国家通过“改戏、改人、改制”三个方面完成了对戏曲教育的现代化改革与改造,所取得的成果及影响是史无前例的。“三改”的成功为社会主义戏曲现代教育的确立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5北京卷[Z].北京:中国ISBN出版中心,1999.
[2] 张庚.当代中国戏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3] 董德光.回顾——中国戏曲学院校史访谈录(1950—2005)[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4]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5] 史若虚.戏曲教育论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