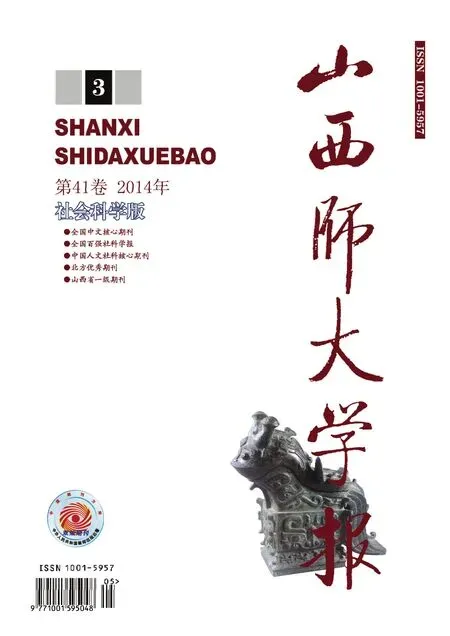从“极性”到“间性”
——20世纪西方文论的理论品格解析
延 永 刚
(牡丹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自从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出版之后,“后理论”便成为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这种现象既显示出人们对当前文学理论危机的一种担忧,也表现出人们对文学理论未来的一种期许。在这样一个前途尚未明朗的时期做出一些合理的反思工作应该是文学理论工作者的使命之一。然而,从一个纷繁复杂极富魅力的文学理论世界概括出几条规律来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冒险的工作,更不用说对文学理论的未来做出一些有见地的预测。然而冒险并不见得就没有价值,只是需要一些承受力。因此回顾一下艾布拉姆斯对文学要素进行描述的三角形结构,它里面各要素之间的超级不稳定性和三角形的超级稳定性形成一个反讽,这个反讽似乎正在启示人们,文学理论的一些奥秘可能深藏于此,带着这样的安慰,本文试图对文学理论做一次回顾和前瞻。
一、 文学理论的“极性”言说
极性(polarity),在物理学中指物体在相反部位或方向表现出来的固有的性质或力量。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可以引申为对事物和现象的判断向截然对立的两极聚拢。在文学理论兴盛的20世纪,各种理论在面对作者意图、读者接受和文本指涉等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时极性特征十分明显,它们打破了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学常识,显示出现代文学理论的战斗品质和质疑精神。
(一) 意图:从标准到死亡。传统理论认为,作者意图等同于作品意义,于是作者意图便成为作品阐释的主要工作甚至是唯一的追求,而达到复原作者意图的主要途径就是重建作品的原初语境。这时,历史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文献学方法和考证方法便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将作者意图作为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唯一标准统治人们思维长达千年之久,时至今日,仍然残留在许多人的潜意识里。因为这种观点可以避免文学阐释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带来的麻烦,但是同时也使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成为多此一举的事情,因为人们能够通过历史学的方法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比尔兹利和维姆萨特合著的《意图谬误》正是从这里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作者意图和人生经验是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对于我们理解作品无关痛痒,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成功,不应该是作者的意图或者构思,它难以找到,而且徒乱人意。”[1]231在这部著作里,作者从两个方面论证了作者意图的非必要性。首先,假设作者没有能够通过文本实现自己的意图,文本的含义偏离了作者的初衷,这时有关作者的任何观点都显得微不足道,因为作者所思所言与文本无关;其次,假设作者通过文本实现了自己的意图,那么,人们完全可以通过阐释文本来发掘文本意义,从而忽略作者所思所言。总之,无论哪种情况,得出的一致结论就是:作者意图无关紧要。而对于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态度则要比尔兹利和维姆萨特极端得多,他们沿着索绪尔的观点,即文学文本是自足的,文本的意义由语言系统锁定,而与意图无关,因此,文本意义的阐释必须以抛弃作者为起点。由此看来,由于反意图论的冲击,原本是作为坚固的文学常识的意图论变得漏洞百出,反意图论以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在和意图论者进行着斗争,然而,它本身却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处在无根的语言楼阁当中。
(二) 接受:从缺席到霸权。20世纪之前,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是印象主义批评,这种批评秉承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传统,谈心得、谈体会、谈感悟。虽然此时的文学接受还未成为理论中的一个备受关注的词汇,但它确实没有成为一个被人们忽视的因素,这可以从印象主义批评家阿纳托尔5法朗士的话中得到证明:“说实话,批评家们应该说,先生们,我将用莎士比亚和拉辛的作品来谈谈我自己。”[2]132
20世纪初期,科学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批评家们公开明确要摒弃读者和文学接受,他们将作品界定为一个自足的有机单位,一个稳定、封闭的系统。他们的信条是“诗歌不表意只存在”,主张对诗歌进行实验室的解剖,以提取潜在意义。这派理论继通过炮制出“意图谬误”后又抛出“情感幻觉”,将读者接受和作者意图一起逐出文学领地。
与之相反,在完全抛弃读者接受的另外一极,读者似乎一夜之间拥有了无限的自由,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通常称这一派理论为“极端阅读论”(通常也称之为读者反映批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文学理论家斯坦利5费什。费什坚决反对视文本为有形的空间独立物,认为没有发生在具体时间的具体阅读,文本将不复存在,从而揭发文本自主性、客观性的幻想。他将一切意义划归给读者,不再将文学定义为对象,而只是“阅读的收获”。为了更进一步清算意图论的余毒(指文本意图),他提出了“阐释社群”的概念,这个概念反对将读者和文本进行二分,反对文本的独立性,“因为‘阐释社群’不仅对读者的阅读活动负责,同时也对生自于阅读活动的文本负责,它是一种文本和读者同时出现的权威结构和系统”。[3]322这样,读者便不是一个总是在文本之后出现的某个实体,而是凌驾于文本之上,决定着文本和意义的诞生。在1980年出版的《教室里有文本吗?》一书中,汇集了10篇论文,体现了费什绝不走向妥协立场的全部历程,长期以来一直默默无闻的读者和接受活动经过“极端阅读论”的点拨,一下子成为了文学活动的中心,这种对文学边缘要素的极性言说虽然不好接受,但确实架构起了文学理论的问题场域,原本清晰的边界变得问题丛生。
(三) 文本:从指涉到互文。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西方文学追求的理想就是文学要精确地再现现实,当然,这个现实包括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源自人们一种古典的语言观:语言可以复制现实,语言具有指涉现实的功能。人们相信在主体与客体之间,语言是人们放心的可信赖的媒介,而不是障碍,就像福柯在《词与物》中所说:“一个大大的乌托邦,即语言是完全透明的,它对事物的命名也是完全无误的。”[4]101
这是理解文学和现实关系的一极,当然这一极,只有在现代文学理论对它构成极端威胁时才成立。若非如此,文学的“指涉”现实功能也许就是我们理解文学的全部观点。可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观彻底推毁了文学指涉现实的语言学根基。他们认为,符号的任意性蕴含了语言对现实的相对性和独立性,符号与对象的原始联系已经被打碎,解释只能不确定地在一个无限的“符指”过程中从一个符号滑向另一个符号,永远达不到源头。
现代语言观成为文学反指涉的前提后,文学理论家们一步步将文学与现实彻底割裂开来。雅各布逊将语言分为六要素:发信者、信息、收信者、语境、代码和载体,与之对应六种不同的功能:情感功能、诗歌功能、意动功能、指涉功能、元语言功能和交际功能。接着,他提出,在文学中,语言的诗歌功能起主导作用,指涉功能在此处不能与之相比,也就是说,文学所关注的只是信息本身,与指涉无关。巴特则从文学的叙事功能来确定文学指涉现实的不可能性。他指出,“文学叙事功能不在于再现现实,而只是给我们建构一个神秘莫测的戏剧场景,在这里只有语言的奇遇和语言的狂欢”。[5]153一句话,语言取代了现实,语言能够模仿的只能还是语言,因为我们面对的世界只是一个被阐释过的世界,初始的语言关系发生在表征与表征之间,而不是发生在词与物,文本与世界之间,在无头无尾、无穷无尽的表征队伍中,参照世界变成了一种神话,巴特将其称为“指涉幻象”。如果说雅各布逊和列维5施特劳斯以及巴赫金还给文本和世界留下一丝联系的话(这里的世界虽然是语言建构的),那么,到了“互文性”理论那里,文学完全变成一个封闭的语言牢笼,它和现实彻底断绝了联系,文学完全变成了一种文本间的自我指涉。
二、 文学理论的“间性”探索
“间性”(inter-sexuality)这一术语来自于生物学, 亦称为“雌雄同体性”,指的是某些雌雄异体生物兼有两性特征的现象。“间性”一词目前也被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所使用,指的则是一般意义上的关系或联系,体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文学理论的极性特征,使其具备“战斗性”的品格,然而处于两极之间的思想场仍然面对一些棘手问题,或者说根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思考文学的精英团队不仅不能清楚地阐释文学现象,反而更加左右为难;鉴赏文学的普罗大众捧着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或者被感动得痛哭流涕,或者猜想着小说人物和场景的原型。“过于极端的理论架构起了思想,同时也毒害着思想,或许人们是应该从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2]20可喜的是,处于极性理论之间,人们已经开始进行着可贵的探索。
(一) 意图的归来。意图论者和反意图论者各执一端,看起来势不两立,但是长时间的对峙过后两极论调都开始底气不足。经过反意图论的冲击,极端意图论者的天真之处已经暴露无疑,比如,过分地强调作者意图在文学研究和文本阐释中的唯一地位,会造成文本时代价值的贬值;过分地追求作品原初语境的重建,会导致文学研究的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然而,在反意图论内部,也有关于作者意图的重新认识,这似乎开始预示着“意图论”的东山再起。然而,问题也许没有那么简单,此时的意图已非彼时的意图。
重返作者意图需要克服两大难题:第一,意图论无法解释作品在作者之后的生命力——一部作品的全部意义绝不简单地等同作者及同代人首次接受的意义,而在于后世接受者对作品的阐释;第二,意图论无法保证作者笔下的词语表达他想说的东西,不能保证作品的意义一定能够吻合作者所欲传达之意,即在作品意义和作者意图之间没有一个必然的逻辑式。对于第一个困难,美国文学批评家赫施区分了文本的意思和意义的不同:意思,是文本在接受过程当中稳定不变的东西,它回答的问题是“文本说什么”,也就是说意思是单一的,而意义则让意思与具体情况发生关系,所以它是多变的、多元的、开放的,甚至可能是无限的,它回答的问题是“文本怎么样?”意思和意义的区分,解决了作者意图对作品意义的垄断,保证了作品的后世意义和生命力的延续,同时也保证了作者意图不被简单地忽视和去除。对于第二个困难,分析哲学的学者们最近又做出一个大胆的区分:意图非构思。他们认为意图论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简单地将作者意图等同于作者的构思。事实则是,作者意图不仅包括构思,还包括作者的“言外行为”,这些言外行为虽不在作者的计划当中,却可能蕴含在作品的细节处,但是它们仍然在作者的主意图之内。作者写作品时不可能考虑到词语的所有蕴含,但并不意味着那些细节与意图无关,也不意味着作者用这些词表达了他不想表达的东西。以上两种困难的解决虽然路向相反(缩小意图的内涵与扩大意图的外延)但是,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在意图论和反意图论双双陷入困境时,需要重新定位意图的当代含义,重新思考意图对于文学研究和文本阐释的重要价值。
(二) 隐性的读者。极性理论分别采取两个相对省事的办法,要么完全忽略读者,视其为“情感幻像”(先是文献学,后来是“新批评”学派、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有读者,或者视之为捣乱分子,将它排挤到一边;要么视读者为核心,用读者权威代替文本权威和作者权威。虽然两者避免了文学要素之间的复杂博弈,但是省事的办法未必是有效的办法,二者虽然势不两立,最终却殊途同归,在各自的极性言说中取消了读者。
接受理论的两极之间仍然是学者们探索问题的主要场域。和意图论与反意图论一样,文学范畴的裂解也许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意图论最终在第三条道路上选择了“意思”和“意义”以及“意图”与“构思”的划界。在接受理论中同样出现了“隐性读者”和“真实读者”的区分,两种读者的区分,其实就是尝试着解决极性理论留下的棘手问题:阅读到底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主动大于被动还是被动大于主动?读者在接受过程当中拥有多大程度的自由?文本又如何作用于读者?
伊瑟尔将隐性读者定义为“代表了文学文本产生效应所必须预备的所有条件,这些预备条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现实经验,而是来自于文本本身。因此,作为概念,隐形读者就植根于文本结构之中:它是人为的建构,绝不等同于现实中的任何读者”[6]27。表面上看,伊瑟尔好像在处理现实读者和理想读者的关系,实际上,他处理的乃是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因为伊瑟尔的隐性读者本质上是一种文本结构。他认为有两种库存,一种是读者库存,即读者头脑中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规范的集合,对应的是真实读者;一种是文本库存,即文本自身的一套规范,对应于隐性读者。并认为如果在两者之间如果没有最起码的交集,阅读便无法进行。关于库存的论说一方面意在告诉人们隐性读者与文本权利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探索极性理论架构起来又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尽管此种解决也只是其中的一种尝试。
(三) 虚构的真实。有关文学和现实的两种极性理论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人们长久以来的错误指涉观:要么是纤毫毕现,要么是什么都没有。建立在这样的指涉观上很容易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让人们无法取舍。因此,要想在两个极性理论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必须取消这样的“指涉观”,而要取消这样的指涉观必须重提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因为这种简化的指涉观恰恰是对《诗学》中模仿说的误读。既不管是弗莱还是利科,他们都在竭力为模仿正名,模仿不再被视作静态的拷贝或者复制的图像,而是一种认知活动,它赋予我们对时间的体验以形式。模仿是构型,是综合,是动态的实践。
在这种新的模仿论调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关于文学和现实关系的两种极性理论都犯了一个相同的错误:那就是忽略了文学语言指涉的特性。他们认为文学语言指涉遵从日常语言指涉的逻辑前提:指涉之可能性的逻辑条件是某物的存在,然后有可能出现谈论该物的真假命题,即有关于某物的指涉就必须先有该物。然而文学的虚构性特征使文学语言正好不能满足这个逻辑前提,文学中的人物、场景、细节都是虚构的,也许在生活中会找到原型,但是绝对不会完全等同,然而极性理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否定文学语言的指涉功能,进而断绝了文本和现实的关系。其实,按照新的指涉观和模仿论,人们应该在可能世界和虚拟世界来思考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文学作为虚拟世界,它有它自身的真实性,判断文学是否具有真实性,并不必然地取决于现实世界是否有所指,而只需要可能世界之事物与现实世界之事物不相矛盾即可。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诗人不是道出真实世界发生之事,而是依据情理和必然性道出可能发生之事。”[7]180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说:“如果这本书的书名表明‘理论’已经终结,我们可以坦然地回到前理论的天真时代,本书的作者将感到失望。”[8]3我想,伊格尔顿有两重含义:第一,面对极性理论对文学常识的冲击,人们似乎已经培养起来了怀疑一切的反思品格,不会再轻而易举地接受一些看似合理的现象,人们似乎成熟了许多。这是极性理论给我们带来的宝贵财富,也是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理论品格之一,这种品格张扬着笛卡尔以来的人的主体精神,怀疑一切,唯一不能怀疑的就是怀疑本身。第二,不能回到前理论的天真时代并不意味着天真毫无价值,极性理论打败了天真,但是天真不会束手就擒,天真自有其战斗方式,它屡次向人们招手,将来的文学理论不会漠视天真的魅惑。习惯了理论论战的20世纪,未来的文学理论将会在极性理论之间重新思考文学的一些核心范畴,当然,这些范畴也许会染上几分天真,但已经不会像我们首次接触它时那样坦然。
[1] 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 安托万5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M].吴泓渺,汪捷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 Fish.Stanley.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 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
[4] 米歇尔5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
[5] 罗兰·巴特随笔选[M].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6] Iser, Wolfgang. The Act of Reading.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
[7] 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8] 特里5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