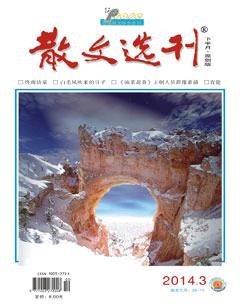爱的真谛
张晓帆

记忆时起,就看见我家堂屋的大相框正中贴着一幅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妙龄美女,大概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时代拍摄的。她着一身戎装,看样子也未施粉黛,可那飒爽的英姿,那如兰的气质,真是无人能及。母亲说,这照片上的女人叫兰荻,我就叫她兰姨吧,她曾是在我们这个镇上插队的上海知青,已回城多年了。
母亲非常珍爱这帧照片,许多年来曾几次翻拍。她尤喜凝视照片上的兰姨,尤其心情有大起大落时。母亲凝视兰姨时的目光我一直讀不懂。父亲却好像很敬畏这帧照片。许多年来,曾几次怯怯地说:“阿梅,我们把它拿下来放到影集里吧,把我们的全家福贴上去不是更好吗?”但每次都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不仅母亲反对,我也反对,因为我自小就爱这照片上的兰姨。我经常凝视着她的美丽出神。况且,她的名字我也喜欢,兰荻,既有一种如诗如画般的高雅,又仿佛蕴含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让人浮想联翩。
在我们镇上插过队的上海知青返城后,这些年中,绝大多数都曾经回来过,可是我始终没有等到兰姨。而回来的那些人,在与我父母聊天时,几乎把所有知青插队时和返城后的故事侃个遍,却从来也没有人提起过兰姨。从小到大,从父母看兰姨照片的目光与表情中,我心里隐隐有些感觉,她与我父母之间一定有一种微妙的关系。有几次,我曾见到过,母亲不在家时,我的父亲?在凄清的雨夜,曾泡着一杯浓茶,对着兰姨的照片,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而我的母亲竟也有些怪异,在兰姨的大幅照片旁边,贴满了她教小学这么多年来,在各种表彰大会上,接受颁奖的照片,仿佛在用另一种方式来与兰姨媲美。对我来说,兰姨和我父母的关系,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来愈想揭开这个谜底。
那年暑假,45岁的母亲做了胆囊切除手术,我到医院护理她。在医院的十天,是自我成年以来,我们母女独处的最长的日子了。母亲忙于教书育人,我忙于学业,加之做教师的母亲总是以对学生的严厉态度对待我,因此,一直以来我对她总是心存敬畏。而今,重病中的母亲显得十分的慈爱。我第一次感觉到母亲原来也是这样的温柔和脆弱,我们母女整日聊天。母亲讲我童年的趣事,讲她的故事。聊着聊着便聊到了兰姨,母亲突然说:“也不知兰荻她过得怎么样,身体好不好,她比我还大一岁呢,这辈子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缘和她再见一面了,我真的很想见见她呀,唉!”
“妈,兰姨她是你的朋友吗?”我乘机鼓足了勇气问道。
“是的,但她也是我的情敌!要不是那个年代,嫁给你爸爸的应该是她。”
“真的是这样啊,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禁不住失声喊道。
“我知道,你早就已经猜测到了,毕竟妈妈那时也正是你这样的年龄啊。你想听听我们的故事吗?”
我点点头,母亲打开记忆的闸门,往事就这样从她口中喷涌而出。
原来兰姨是1968年的上海知青。她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一开始就双双被关了牛棚。她是个独生女,下放时刚刚高中毕业。她是他们那一批知青中文化最高的一个。她来镇上半年的时候,镇上让大队选送一男一女两个社员去县医院学习医疗技术,以便回来后做大队的赤脚医生和接生员。大队书记便推荐镇中学毕业的父亲。但女社员一时还定不下来。那年月,我们当地的农村女孩,读到初中毕业的是凤毛麟角。而与兰姨同来插队的上海女知青,略有文化的都被安排了诸如小学教师、宣传队长等工作,只有她因为出身不好,才一直未被安排,而是和女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因为实在没有人选,书记一甩帽子,骂了一句娘道:“老子不管她黑的白的,只要认字,学到本事,能把村里妇女肚子里的娃鼓捣下来就行!”于是兰姨便打起行囊与父亲一起到县医院学习去了。半年后再回村时,他们已经成为一对如漆似胶的恋人。那时父亲和兰姨都是二十一岁。父亲向大队申请开证明,要与兰姨结婚。可是遭到了爷爷奶奶乃至本户族众人的一致反对。原因是父亲家是根红杆亮的贫农,而兰姨是个黑五类,何况,一个朴实的农家后生又怎能娶一个浑身散发着洋气的外路货上海阿拉做老婆呢?他们认为父亲一定是疯了,是被那个狐媚魇道的女人迷住了心窍。于是我的祖父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那就是赶快在我们当地寻一门亲,拴住父亲。于是镇中学毕业,做小学教师的母亲便成了最佳人选。母亲与父亲是上下届,早已暗恋父亲多年。而父亲良好的家庭出身和出众的相貌,也使得母亲家人十分赞同这门亲事。而父亲却坚决反对这门类似包办的婚事。他扬言非兰姨不娶,甚至以死相挟。可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原来,我母亲的叔叔当时是镇革委会副主任,在一个夜晚,他与父亲谈了一次话后,第二天父亲就答应与母亲订婚。许多年后母亲才知道,原来是他的叔叔威胁父亲说,如果他不同意婚事,他马上就把兰姨从大队的卫生所调到最偏远的打石场去做工。在那地方做工的,都是些很野蛮的男人。曾经有两个女知青在那里煮饭,可是没多久就不明不白吊死了一个。为了兰姨,我父亲才不得不同意了这门亲事。可是,兰姨后来还是调走了,是她自己自愿走的,她去了一个偏远的林场卫生所。第二年春天,二十岁的母亲和二十二岁的父亲举行了革命的婚礼。而就在婚礼的前几天,母亲才第一次见到了兰姨。
“正是那次见面,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兰荻这个不凡的女人。”母亲说。
“我对兰荻和你父亲的事有所耳闻,但我那时始终认为,那不过是因为年轻,不过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而已。可是当我与你父亲一起去见兰荻时,从他们的眼神中,我读懂了一切,我才知道,他们的爱是那样的坚贞与不可改变,他们都是因为爱对方而牺牲了自己的,而我的婚姻只是他们为爱而施舍给我的……”
“那么,你恨兰姨吗?”
“不,我非常感激她。没有她,我的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就像许多善良的中国人一样,有三间瓦房,两个儿女。做丈夫的呢是个典型的模范丈夫,包揽家里的一切重活,尽最大努力赚钱,让老婆孩子衣食无忧,他认为这是他的责任。而在心里,始终有一个痛点,埋藏着永难割舍的爱情。做妻子的呢,也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纺织井臼,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这是为人妻者该做的。可是,在每一个凄清的雨夜,身边丈夫辗转难眠时,她幽怨的泪水就会无声地滑落脸颊,因为他知道,这辈子,他不爱她,她没有赢得他的心。当老去的时候,怆然回首,才发现彼此都是戴着面具熬过了一生,这该是多么的悲哀啊。兰荻让我懂得了爱是一种心灵的契约,爱是一种包容和牺牲,最终我赢得了你父亲的心。”
“那你是怎样做的呢?这么多年来父亲一直对你那么好。”
“我首先央求我叔叔设法把兰荻调回了大队卫生所,因为那里不但环境好,工作轻松,每天还记最高工分。我娘家人都说我简直疯了,明知她和自己男人倾心相爱过,却还给他们创造在一起的机会,他们都指责得我不行。”
“就是啊,妈妈,我也认为你这是在冒险呢”
“不,我不这样认为,他们俩都是善良而又理智的人,虽然倾心相爱过,但是现实已经不可改变了,必须要面对,只有让他们在工作中重新建立正常的人际的关系,才能平复他们心中的波澜,才能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使他们渐渐坦然面对彼此,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大队卫生所和我们学校毗邻,除了他俩之外,还有一个会计和一个现金,他们一直相处得很好。我和你父亲就住在学校里,为了方便群众看病,兰荻住在卫生所,我们都是自己开伙。只要我们家里做点像样的饭菜,我就主动叫她过来一起吃,她也是那样,我还让你爸爸包揽了她的一切粗活和重活。后来我们相处得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了。你就是兰荻接生的,每次回上海探亲,她都给你带穿的和吃的,还给你织了很多件漂亮的小毛衣。后来,政治运动渐渐没那么严峻了,大队每年都有推荐知青上大学的名额,虽然也要考试,但是每年都有兩三个考上大学的,这是知青们最好的出路了。兰荻毕竟出身不好,不符合规定,按正常渠道推荐屡屡受挫。我又去央求我的叔叔,费了好一番周折,才给她挣得一个名额,她在那年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医学院。临走时,她几乎把一切能用的家当都留给了我们。我和你爸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为她践行。大家都喝了不少酒,她抽泣着拥抱着我说,我是她一生最敬佩和感激的人,她永世难忘。后来,她又对你父亲说,要好好对待梅姐,像梅姐这样的人,这世上有几个?你遇到她是你的幸运,要好好珍惜。最后她说,她到上海后,每隔一段时间,会写信报个平安给我们,她以前打扰我们太多了,我们应该有一份安乐平静的生活,她不应该过多介入,她将在远方永远默默远祝福我们……我们都哭了。”
“那后来呢?”
“兰荻每年都会写一封信给我们,最后一封信是她毕业那年写的,她说她去报名参加援藏医疗队了,不日就要出发。后来就再也没有了她的消息。”
“妈妈,你真是太伟大了,你能够这样坦然地和情敌相处,这么宽容地对待她。”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很多年后我听到的一首歌,叫做《爱的真谛》,我正是做到了这些。我想,你父亲正是被我的包容、忍耐和恩慈所打动,我最终赢得了他的心。”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不止息……”这正是母亲的爱的真谛。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