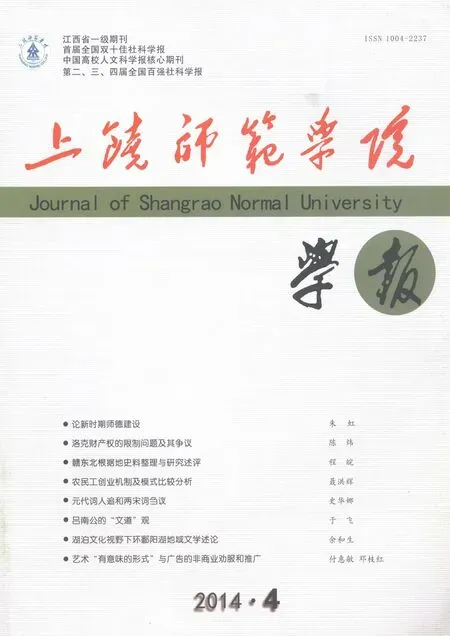吕南公的“文道”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吕南公(1047—1086),字次儒,号灌园,建昌南城(今属江西)人。出身贫苦,于书无所不读。治平末出游,治平末至熙宁间参加科举,屡试不第。后退而筑室灌园,不以进取为意,益务著书,借史笔褒贬善恶,以“衮斧”名其所居斋。元祐初,时朝廷立十科以取士,陈绎、曾肇等人举荐,廷臣议论欲命以官,然未及除授而卒,年仅40,《宋史》卷四四四有传,并有《灌园集》二十卷传世。
吕南公是北宋卓有成就的文论家,其文论思想主要集中在他对“文”、“道”以及“文道关系”的论述上,我们称之为“文道”观。吕南公的“文道”观不仅与当时的道学家、政治家之“文道”观迥然有异,即使在推崇古文创作的古文家中也要比欧阳修和曾巩进步,而更接近三苏父子的文论观点,尤其与苏轼更为接近。只是由于吕南公位卑言微,其“文道”主张影响有限,今日重新审视北宋中期各家文论,就不应忽略吕南公的文论思想。吕南公“文道”观的形成是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发展中形成的,因此有必要对唐宋古文运动,特别是北宋的古文发展情况作简要梳理。
唐代古文运动是在对抗齐梁时代占据文坛主流的骈文逐渐发展起来的,韩愈和柳宗元可谓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尤其是围绕着韩愈还形成了古文创作的作家群,如皇甫氵是、李翱等,不少古文作家都得到了韩愈的赏识和提携。古文运动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上的革新,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表现出的巨大变革,韩愈也十分重视这一点。因此,打着复古口号的古文运动,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革,更是以古文来复兴儒学。韩愈的古文理论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学古文的出发点应是学“古道”,“古道”是古文的内容,比形式更加重要;第二点指出“古道”是古圣贤人之道,最主要的就是指孔孟的仁义学说思想。韩愈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之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1](P111)朱刚在《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对比韩、柳、欧、苏古文四大家的文学与道论主张后指出韩愈的道论是一种文化价值之“善”,即以孔孟学说中的“仁义”为核心的“道”,是从先圣中继承下来的一种激发正义感的力量。吕南公对于“道”的认识,可以说是韩愈的异代知音。“吕南公《灌园集》卷十六《重修韩退之传》谓‘愈之于学,本仁义而守教者也’,他的理解是正确的”[2](P46)吕南公十分推重韩愈,这与宋代的古文大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是一致的,在继承韩愈的“文道”观上主要着眼于韩愈提倡的“古道”,吕南公对于儒家“仁义”观也有自己的论述:
某闻君子所学当博矣,而其要不出乎仁义。仁义之本存乎人之心,而充积之盛得以立天下之道,大之为王者,小之为匹夫,无加损焉。学之于仁义,岂不重哉?自古圣君贤臣,其所以相吁谟暇豫,天下于熙平,而儒生亦以隐约之身扶持此道,使不灭绝者,其事业可谓神明矣。然语其立政,皆不过广吾爱以立天下之爱,尽吾宜以底天下之宜,如斯而已耳。故夫仁义者,学士之心所当汲汲也。[3](卷2366,P207)
吕南公强调学习仁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自身的修养,同时也是“立政”的伦理基础,由韩愈而上,吕南公直接继承了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学精神。可以说,由韩愈所复兴的古道对于吕南公的影响主要在于“善”的方面,吕南公在《重修韩退之传》中对于韩愈的“文道”观把握得十分准确。
唐代古文运动的声势虽然浩大,但是在韩柳古文创作的高潮过后很快便归于沉寂。晚唐时期由于时代的原因,文人又逐渐向齐梁骈体文风靠拢,但是古文运动的影响却并未中断,而是成为潜流。直到宋初,为了与当时流行的五代以来那种浮艳轻丽的文风和片面追求辞藻音律的文坛倾向相抗衡,一些古文家重新扛起了古文运动的大旗,力图重建儒家的“道统”和“文统”。直到北宋中期形成了比唐代古文运动影响力更大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最终取得了古文运动的胜利,也改变了文坛的风气。吕南公的“文道”观正是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中产生的。吕南公生活的北宋中期,当时的主要文论已由宋初古文家不同的倾向主张而逐渐发展为道学家、政治家与古文家三种不同的“文道”观取向。吕南公明显属于古文家阵营。
北宋初期“道统”与“文统”的重建有赖于柳开、赵湘、穆修、田锡、王禹偁等作家的努力,同时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张毅认为“从柳开、赵湘、穆修等人身上,可以看出宋初古文家重建儒家道统和文统过程中的一种走向,即将儒家的道统由外在的仁义教化归结到内心的心性本体。……而且由于他们过分执着于道德理性,把心性的道德本体直接当作文学的本体,视道统与文统为一,把道德与文章等同起来,反对和排斥文学创作中非道德的情感因素,因此其‘文统’观也无益于当时的创作,只是后来开了理学家文论的先河。”[4](P36)这是宋初古文运动中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又与在北宋不断发展的“道学”相结合,形成了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道学家文论。为了克服这种偏执于道德理性而带来的思想方面的缺陷,使儒家的道统和文统的重建并有助于实际的文学创作活动,因此必须借重于道家的自然哲学和艺术精神,对道统和文统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这种文学思想倾向是通过田锡、王禹偁等人的理论和创作来表现的。“田锡和王禹偁在理论和创作中都肯定了情气,从而使他们的创作心体和文学思想远比柳开等人丰富,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4](P42)可以说他们开了古文家文论先河,对于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创作更有影响。从文学角度言,宋初的古文家中王禹偁的创作成就也要远远高于柳开等人。另有学者认为宋初古文运动思想除了道学家和古文家的文论,还有一种后来发展为政治家文论的倾向。
第三种政治家文论倾向的代表是孙复和石介。宋初,文与道的运动,可以看作是韩愈的重生,是韩愈精神的复现,在宋初的古文家心中又都存有一个“统”的观念,道学家要重建“道统”,古文家自然也有自己重建的“文统”。但是“道统”和“文统”的关系究竟如何,这里就产生了分歧。柳开等人的论调与后来道学家“文以载道”的论调没什么不同,实质是将“道统”与“文统”合二为一了,其结果就是取消了文的独立性,进而从道进入身心,讲究“心气”、“理性”等等,直到后来抛弃了“事功”。本来宋初的理学是讲究应用的,明道之后本就连带着要再言致用,这就开了政治家文论之门。所以胡瑗在湖州州学中分经义、治事为两端,范仲淹也已名儒而为名臣。孙复《答张洞(一作洞)书》说得很明白:
《诗》《书》《礼》《乐》《大易》《春秋》之文也,总而谓之经者也。以其终于孔子之手,尊而异之尔!斯圣人之文也。后人力薄,不克以嗣,但当左右名教,夹辅圣人而已。或则发列圣之微旨,或则名诸子之异端,或则发千古之未寤,或则正一时之所失,或则陈仁政之大经,或则斥功利之末术,或则扬贤人之声烈,或则写下民之愤叹,或则陈大人之去就,或则述国家之安危,必皆临事摭实,有感而作,为论为议,为书疏歌诗赞颂箴辞铭说之类,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孙明复小集》)
政治家的文论是尚用的,所以能够接触到一些现实,做到有感而发。这一点比古文家以道为幌子切实得多,也比后来的道学家空谈心性来得具体。孙复在这篇文中又说:“文者道之用也”,这其实也是“文以载道”的意思,但是他又说:“道者教之本也”,这就明显的偏于教化,成为政治家的主张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道学家与政治家文论主张的异同,虽然他们都强调“文以载道”,但是其“道”则根本不同:一个是内化于身心,一个是外用于事功。政治家的这种主张到了石介便说得更加明白,他在《怪说中》攻击西昆体的杨亿、刘筠等人所作皆是无用之文,主张言之有物。孙复和石介是政治家文论的先声。
吕南公明显带有继承宋初古文家的倾向,因为他对“道”的认识,既不像道学家那样局限在儒家之道中,也不像政治家那样宗经和讲求事功。他对“道”的态度与田锡、王禹偁较为接近,持有一种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对于儒道互补中道家的文论作用是接受的。
以上就是宋代初期的文论生态,北宋中期的各种主张大都已孕育其中,只是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毕竟宋初古文家的总体地位比不上居于馆阁的西昆体诸人,而创作实绩也并不十分突出,影响有限可以理解。真正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推向高潮的是一代文坛领袖欧阳修,他的理论和创作对古文的发展影响深远。
欧阳修无疑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最重要的人物,嘉祐二年贡举,他罢黜了务为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推崇平易畅达、议论恳切的文风,并“以西汉文词为宗师”,选拔了苏轼、苏辙兄弟和曾巩,彻底改变了整个文坛的风气,奠定了北宋的文学风格,甚至影响到元、明、清各代的文学发展。[5](P3~6)但是对于欧阳修个人的文论却一直存在着不小的争论:“理学家恨其离‘道’,而文学史家又嫌其过于道学化。”[6](P331)这也可以说明对于欧阳修的认识,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我们应该具体来看欧阳修的文学主张。欧阳修的文论主张最有影响的是两个口号:“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以及“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其一出自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其二出自苏轼《祭欧阳修文》的转述。郭绍虞先生认为欧阳修的“文道”观是重道而轻文的,更接近道学家的主张。因为此时道学家的文论主张已经与古文家泾渭分明了。道学家的文论已由最初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发展到程颢、程颐极端的“作文害道”之说。《二程遗书》卷二八程颐说:“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必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7](P181)二程认为溺于文则远于道,文辞愈华丽,作文愈专注则离道越远。这一点与欧阳修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所言颇为一致。但是祝尚书先生认为这是对欧阳修的误解,欧阳修并非溺“道”,而是摒弃了“道统论”,对于“道”的理解提出了新的解释。这种新的变化朱刚用道论的动态发展做了很好的解释,朱刚认为韩愈的道论以“善”为核心,而欧阳修承接韩愈所发展丰富的是一种“真”。是从“善”的文化价值推展到自然、人情之“真”,以“至理”的面目出现在文章中,因此能够平心静气地讲事实、说道理,文风平易自然、流畅婉转。[2](P194)所以说,以欧阳修对于古文革新运动的贡献,其必定有改造文风的文学思想基础,虽然表面上看其论“道”接近道学家一流,然而这里要注意的是“道”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包蕴着丰富的含义,甚至不同的人的言说中会有不同的含义。欧阳修为了夺取古文运动的胜利,并不明言“文”的重要性,而是通过改造“道”来进一步改造文风。道学家与古文家的根本区别在于,道学家以文为手段,以道为目的,虽然对于“文”这个手段认识有不同,但最终目的一致。而古文家则是以道为手段,以文为目的,通过不断地改造“道”来不断地完善“文”。论者多认为吕南公的文论比欧阳修和曾巩的文论要进步,就在于吕南公大胆的主张文的重要性。他在《上曾龙图书》中说:
盖十五而读书,二十而思义,以为文者言词之大美,以天地之化,四时之运,人物之成世,古今之无穷,其间变故幽显,治乱盛衰,贤愚勤戒,一切籍文而后经远。其所关系如此,虽古之人处之以力行之余事,然观书契以来,特立之士,未有不善于文者也。士无志于立则已,必有志焉,则文何可以卑浅?[3](卷2368,P240)
从中可见吕南公作为古文家对于文的重视,其后吕南公还表示要继承和发扬欧、曾等古文大家的古文传统。吕南公论“文”,并不是脱离“道”而谈。“在‘文道’关系上,他将道、言、文三者分开,并且否认以六经为作文发源的传统观念,认为百家才是作文的起点。”[8](P213)确保了文的独立性,同时“文”又与“道”和“言”有着紧密的联系。吕南公文论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对“文统”的改造上,不师六经而师百家。先来看吕南公对于道、言、文关系的论述。其《与汪秘校论文书》云:
盖所谓文者,所以序乎言者也。民之生,非病哑吃皆有言,而贤者独能成存于序,此文之所以称。古之人以为道在己而言及人,言而非其序,则不足以致道治人,是故不敢废文。尧舜以来,其文可得而见。然其辞致抑扬上下,与时而变,不袭一体。盖言以道为主,而文以言为主。当其所值时事不同,则其心气所到亦各成其言,以见于所序,要皆不违乎道而已。商之书,其文未尝似虞夏,而周之书,其文亦不似商书,此其大概。若条件而观之,则谟不类典,《五子之歌》不类《禹贡》,《盘庚》不类《说命》,《微子》又不类《伊训》,至于《泰誓》、《洪范》、《大诰》、《周官》、《吕刑》之文,皆不相类也。盖古人之于文,知由道以充其气,充气然后资之言,以了其心,则其序文之体自然尽善,而不在准仿。[3](卷2365,P201、202)
吕南公在文章中提出了“言以道为主,而文以言为主”的“文道”观,并在后面又说明了由道充气以资之言的创作方法。关于文与言的关系,吕南公在《读李文饶集》中进一步强调了文对于言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文不可以不工”的观点。文章说:
余独论立言,以为士必不得已与言,则文不可以不工。盖意有余而文不足,则如吃人之辩讼,心未始不虚,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无助于辞而已矣。噫,古今之人苟有所见,则必加思,加思必有得,有得矣,而不欲著之言以示世,殆非人情。然而伟谈剧论,不闻人人各有者,此非文不足故欤?[3](卷2370,P275、276)
吕南公所指出的“文不足”即是“文不工”,与前文所提到的关键词“序”是同一概念。吕南公不仅强调言之有物,即这个道,同时还强调言之有序,这样才能写出好文章。而吕南公的“道”更多地是指“为文之道”,虽然是以儒家的思想伦理为基础,但又不仅仅限于儒家的思想。吕南公在《与汪秘校论文书》中说:“于《庄》、《列》、六经、百家、十八代史,因文见道,沉酣而演绎之,私心自许。”又谓:“文学之事,虽使圣人复生,不得废吾所是,惟当勒成一书,俟之百世。”又曰:“尧舜以来,扬、马以前,与夫韩、柳之作,此某所谓文者,若乃场屋诡伪劫剽、穿凿猥冗之文,则某之所耻者。必若黄河、泰山,峻厚高简,浑灏奔注,与天地齐同,辐日月不能老之者,此某之所以究心。”吕南公有着自己的“文统”,即周秦西汉再加上韩柳的古文,最为吕南公推崇,而这些的源头或者说吕南公要学习的对象是百家文章以及史书,不仅限于儒家的六经,更为重要的是吕南公抬高了文学的地位,并有志于“成一家之言”。“惟当勒成一书,俟之百世”与《上曾龙图书》中言“一切籍文而后经远”的表述是相同的。吕南公的文论与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唯干著论,成一家言”有着共同的认识追求。但要注意其中的差别,即虽然二人都强调文章的重要,但是曹丕站在政治家的立场上来论述,文章终究是要为政治服务的;而吕南公的论文则是强调了文章的独立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仅体现在为政治服务方面,这是吕南公文论可贵的地方。
前面谈到了吕南公论文与言的关系,也在文中提到吕南公的主张是“因文见道”,这与道学家“文以载道”的论调固然大不相同,但究竟吕南公所言的“道”相比之前古文家的“道”有什么发展变化呢?吕南公对于道持一种包容和开放的态度,超出了儒家之“道”的范围,同时对于儒家的“道”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吕南公在《答李讲师书》中指出“道可以心行故也”,因为:
且夫道非出于圣人也,盖其用亦明于圣人耳,是故资道以作经。资道以作经,与圣人乎何有?而纷纷之徒乃欲拜经作道母,此其所以骇眙于经之所言欤?孔孟以前学者,不务传经以见道,鲜至于惑矣,由汉以后,传经之士相望,道益不明矣。[3](卷2368,P242)
吕南公针对当时解诂经书的风尚,指出道以心相传,并非靠着经书相传,同时也就否定了六经作为道之原始的地位,并且连圣人也并非道之原始。这个道,早在圣人之前便存在了,圣人的作用是“明道”,经也是资道而作,现在的解经风气完全将先后顺序颠倒了,可谓舍本逐末。既然道不以六经为源头,那么自然地文也不应以六经为宗师,所以吕南公提倡以心气来感受传承先圣所名之“道”,同时学习诸子百家各种类型的文章。吕南公所谓之“道”除了儒家的“道”外,还有更广的内涵,吕南公对于“道”的认识更接近于苏轼。吕南公在《上知郡郎中书》阐发了“道”的性质。
事未之无理,而物常各有分,安我之分而循乎理以对之,使凡事先不在我焉,则上自上而下自下,何求之有哉?道诚出此,而有至于不得不动,则亦可以逃名于妄耳矣。[3](卷2367,P227)
苏轼的“道”更加广阔,“作为自然万物的总体,是包罗万象之世界的根据。”[2](P148)物无常形而有常理,这就是苏轼的道,他对于道,实则是“莫之求而自至”。这是因为苏轼的道论,是典型的儒道互补士大夫人格的完美体现,因此朱刚在梳理过韩愈的“善”与欧阳修的“真”之后,认为他们的道论最终发展为苏轼的“美”,这个过程是一步步不断继承和发展,不断补充和完善的。他评价苏轼说:“他的‘道’已是造化中所蕴含着‘美’的‘无尽藏’,这种‘道’无处不在,所以处处皆春;再加上他的‘性命自得’的通达境界,远大的‘器识’和越来越深刻的对人生的反思,最终觉醒为主题‘性’的高扬,于是他的文风便不但有‘万斛泉源,随地涌出’的挥洒之妙,并且能以理性的思致为其精神,一步步脱落华饰,现出气骨。”[2](P194)吕南公在当时的文论中最与苏轼接近,如果他能见到苏轼,也许会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二人的相同不仅表现在对“道”的认识上,还表现在具体的喜好上面,如二人都对萧统的《文选》有所不满。
吕南公《复傅济道书》云:“萧统所集缪多而是少,如王俭、任日方之作,只以污人耳目”,[2](卷2366,P220)可见对萧统的态度。苏轼对于古代之文,最不满于《文选》,《答刘沔都曹书》云:“粱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漏于识者,莫统若也。”[9](P130)他们对于萧统批评的这种一致性,正反映了二人在“文”与“道”上认识的一致性。他们的“文论”都是与王安石所代表的政治家文论相对立的,共同反对王安石的“新学”,也是二人文论能够相一致的前提。苏轼在《答张文潜书》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10](P1427)
陶文鹏先生分析称:“苏轼看到了社会生活现象的多样性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性,因此他认为一个时代作家作品的风格应该是多种多样、千姿百态的,任何人都不能强制推行某一种风格。”[11](P61)用西哲罗素的话说:“须知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本源。”同样是出于对于“新学”以及其所造成的不良风气的批判,吕南公也主张文章风格的多样性。
刘向之文未尝似仲舒,而相如之文未尝似马迁,扬雄之文亦不效孟子也。张衡、左思等辈于道,如从管间窥豹,故其所作文赋紧持扬、马襟袖而不敢纵其握。自是文章世衰一世,几于童子之临模矣。由扬雄至元和千百年,而后韩、柳作,韩、柳之文未尝相似也,而前此中间寂寞无足称,岂其固无人?[3](卷2365,P202)
吕南公所认为的优秀的古文作家,其风格均不相同,即使同为古文家的韩愈和柳宗元为文也各有不同,而模拟仿佛的结果只能是使“文章世衰一世”。这可以说是吕南公针对政治家文论最重要的一点,而古文的长处就在于风格的各不相同。郭绍虞说:“我们看了苏轼黄茅白苇之喻,那就知道吕南公这种论调是有它时代的因素的,所以可以看作古文家文论和政治家文论的对立。”[7](P203)
吕南公作为古文家的“文道”观距离当时的道学家较远,并且是在与政治家的对立中所形成的。古文家中,按照韩愈到欧阳修再到苏轼这种由最初的“善”到“真”再到“美”的不断发展完善的动态过程[2](P5),吕南公的文论更接近求“美”。因此,吕南公的文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远绍韩愈、超越欧曾、比邻苏轼,在北宋“文道”关系的论述中占有重要一环,值得重视。
参考文献:
[1] 吴庚舜,董乃斌.唐代文学史(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2] 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 [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3]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4]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
[5] 曾枣庄. 文星璀璨的嘉佑二年贡举[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3~30.
[6] 祝尚书.重论欧阳修的文道观[A].祝尚书:宋代文学探讨集[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
[7]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 吴海,曾子鲁.江西文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9]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 孔凡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 陶文鹏.苏轼诗词艺术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