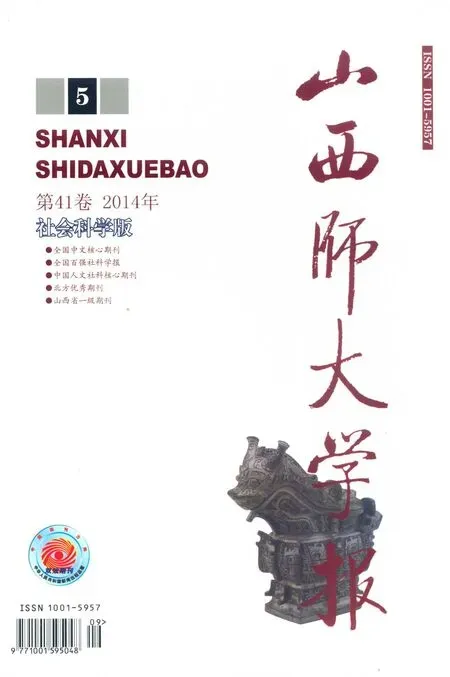论“体知”视域下中国古代的躯体化现象
史梦薇,赵李媛
(贵州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贵阳 550001)
躯体化是指一种体验和表述躯体不适与躯体症状的倾向,这类躯体不适和症状不能用病理发现来解释,但患者却将它们归咎于躯体疾病,并据此而寻求医学帮助。1982年,Kleinman在中国湖南长沙进行调查发现,焦虑症在门诊病人中相当普遍,但是大部分都被诊断为神经衰弱。他认为神经衰弱其实就是躯体化现象。由此,中国人的躯体化现象正式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中。最新调查表明,以躯体化症状为临床主诉的患者往往达到70%以上。[1][2]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人的躯体化报告率如此之高?Kleinman认为主要在于其文化没有突出主体的人的地位,以至于对事件和身体状态的前因后果的理解更多地归结为身体的,甚至是超自然的、神秘的因素。还有学者把精神病的污名化作为中国人高躯体化的因素。但是,上述研究无不是从西方文化话语出发来解读中国文化中的现象。无论是从自我、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还是精神病的污名化,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用这些西方概念解释中国文化中的现象势必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文化的差异性提示我们需要反思躯体化的文化适用性,更重要的是找出本土文化对这一现象的合理解释。
体知是“体之于身”的身体之知,与西方近代以意识为主的认识论有着很大区别。近年来随着哲学本土化的进展,“体知”逐渐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的研究热门,并且大多从哲学视角出发,强调个体身体的亲历性和在场感,将认知和身体的直接体验融为一体,又着重体知的关系性和实践性[3][4]。体知作为传统中国人重要的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其影响必然超越哲学范畴,深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躯体化产生于西方意识哲学,即以意识为主的认识论为基础衍生出的现象。相对应地,探究中国文化中的认识论——体知,是认识躯体化现象本土意义的必然路径。
一、体知的基础:兼容的身体
传统文化把元气看作是世界的本原,元气运动使阴阳分离而形成天地,天地阴阳交感生成“五行”,“五行”生成万物。《太平经合校》中对万物始于元气作了这样的解释:“夫物,始于元气。元气恍惚自然,其凝成天,名为一也;分而生阴而成地,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三统其生,长养万物。”这里不但指出自然万物始于元气,而且认为人也是秉天地之气而生。元气论把天、地与人联系在一起,不仅因为天地人都是由元气生成,而且天地人三者有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载体,即身体。身体不仅是生理层面的形躯,更是个人与天地乃至万物沟通交往的存在支点。传统身体观在论述身体形成、身体结构的基础上,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开放的身体。
(一)建构身体的要素
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及气是传统身体观的构成要素。阴阳作为古代宇宙观和社会观的动力元素,具有解释包括身体在内的世间万事万物生长衰变的功能。“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素问5四气调神》),“人生有形,不离阴阳”(《素问5阴阳应象大论》)。并且,躯体内部也可以划分阴阳,从而使这一抽象概念获得外在形体上的体现:“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藏府中阴阳,则藏者为阴,府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府皆为阳。”(《素问5金匮真言》)与阴阳概念一样,五行及天干地支也同样是身体的构成要素。古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加上《黄帝内经》中的论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这就论证了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的配对框架(《素问5阴阳应象大论》)。最后,气也是身体的本原。中医认为生命活动过程,全赖身体内气的消长变化及升降出入运动。气的盛衰聚散及运行正常与否,直接关系着人的生老病死。
(二)“形—气—心”三位一体的身体结构
在构筑身体之形后,先哲们又开始探讨身体的结构。总的来说,“形—气—心”的身体结构被各家思想学派所公认。杨儒宾充分肯定儒道两家对身体“形—气—心”结构的认可。首先,“形—气—心”的身体结构与天道是相通的,存在个人能领悟天道的可能。其次,气既通向心也通向身,所以身体与心灵是同质,只是拥有不同的形态。最后,身体与心灵存在对抗。因为心灵通过一定的方式能体悟到最高的规范,而身体必须通过转化与心灵达到一致。[5][6]
另外,还有中医的论述。中医把气看成是构成人体的基础物质,它不仅形成了人体的组织器官——五脏六腑,还塑造了人的情志——喜、怒、忧、悲、恐。并且,气的运动把身与心联系起来,将人体的各个器官组织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黄帝内经》以气作为事物的元本,认为人的身体为气转合而成,如“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5宝命全形论》)其中,气的盛衰虚实则演变成身体各器官,如“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腑。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脏之气,名曰传化之腑”(《素问5五脏别论》)。此外,气还生成人的情志。“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悲、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而且,五种主要的情感都对应着脏腑的器官。心脏对应喜悦、肝脏对应怒气、脾脏对应思虑、肾脏对应恐惧、肺脏对应忧愁,这种对应性使得器官与精神可以相互表征。最后,气成为连接身体与精神的中介。“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六节藏象论》)这样,通过气的运行把身体与精神有机的联系在一起,身体也形成了“形—气—心”的格局。
(三)对身体的界定—处在天地人网络中的开放的身体
儒家对身体的研究多为探讨其在社会、政治、个人修养等方面的准则,身体作为一个实践,关乎生存体验的载体,体现着儒家对生命、社会、自然的理解。杨儒宾认为,儒家身体应该包含意识、形躯、自然气化、社会属性四个特性,这些特性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的共同体。[7]9中医和道家对身体的认识在于更好地照顾身体,探寻养生之道,少有关于道德价值等考虑,“不含道德价值的意义上理解‘气’与身体,可说是道家和医家共有的进路”[8]。
虽然各家都有研究的侧重点,但是对身体的生成及结构的认识却是一致的。万事万物都起源于元气,元气的运动生成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气,而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以及气不仅形成了身体,具体来说是形成“形—气—心”的身体结构而且将其与五脏、情志的功能与属性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就从理论上使身体拥有与天地社会他人交融的功能,构成一个天人合一、内外相通的小宇宙,即“呼吸与天地相通,气脉与寒暑昼夜相运旋,所以谓人身小天地” (章潢,《图书编》)。
二、体知的体验性、关系性:躯体化的本土认知基础
体知注重个人的亲历和在场感,是一个不断把知识内在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把认知活动与个体生命体验融为一体的进程。与西方传统认知观不同,体知没有把认知独立于身体之外,而是以身体及其与环境的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这样,体知就把个人的认知从一个无关身体的心智活动扩展到依赖于身体的体验,即把需要学习的知识与自身的身体感官体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认知与技能全部内化为身体的一部分。
具体来说,体知是一种直接性的认知方式,直接性是相对于西方间接性的认知方式来说的。西方哲学借助科学研究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即是用立足于实证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探索世界万物。实证主义有两个基本假设:一个是主观与客观的分离,在实际研究中也就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分离;另一个就是主观对客观的把握,这是建立在感官证实基础上的结论能去除研究者的主观判断。这样,客观的观察成为取得认知唯一正确的方法,而其他方法获得的结果例如个人的体会、体验等,则被认为是主观的、不科学的。西方哲学实际上秉持的是一种透过客观的方法把握事物本质的间接性认知,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体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身体,而不是西方式的作为客体的意义。这种本体论的身体,消除了主客两分的界限,达到了身心合一、主客并存的状态。这样,通过身体进行认知就成为超越感官认证的间接性的直接之知。体知不需要观察、实验等西方传统实证方法得出结果,而是回到我们身体的本质体验。体知的直接性表现在通过身体体验、感悟而产生认知,而不是通过间接的感官证实。
与此同时,体知还有关系性的特征。体知的关系性对应着西方认知的还原性。西方还原论主张把高级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每一种现象都可看成是更低级、更基本的现象的集合体或组成物。还原论派生出来的方法论手段就是对研究对象不断进行分析,恢复其最原始的状态,化复杂为简单。西方的认知最终也需要找到最原始最根本的实体存在,而体知并不追求最基本的存在,相反它更注重关系性的认知,也就是更关注事物是如何互补共生的。
体知的直接性与关系性直接体现在国人躯体化现象中。首先,病人诉说身体不适表现了体知的直接性。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医是注重身体直观感受的。在中医典籍中,“证”是人在疾病过程中具有时间性的本质性的反映。证的本质是以症状和体征为依据分析归纳而成的一种病理性状态,是人体气血津液和脏腑经络等疾病状态在某时间的全身综合反应。然而,中医的器官实质上没有相对应的解剖物质实体,因此证的出现并不能找出相对应的生理病变。但是,中医可以通过这种以身体不适表现出来的证,治疗没有病变但是有身体症状的患者。因此病人的自我表述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中医判断病情的依据。所以,当病人向医生诉说病情时,并不需要积累根据相关现代医学知识,也不需要科学的医疗检查,而是直接诉说具体的身体不适感。
其次,身体症状的主诉体现了体知的关系性。根据传统身体的结构形—气—心,身体症状的出现,不只是形的问题,而且气或心也同样出现了问题。“形”既包括构成精、血、津液等物质,也包括以五脏为中心的组织器官。“心”即神、魂、魄、意、志,是精神心理性活动的统一。另外,又有气贯穿于形与心之间,形成了形—气—心三者一体的状态。中医在分析病症机制时,对形与神的病理关系有如下论述:若五脏发生病变,形体出现问题,就会引起相应情志变化。“伤形则神为之消”。(《景岳全书》)《灵枢·本神》曰:“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反过来,情志过激则会破坏机体内的平衡,导致躯体疾病的产生。而形、心的任何损伤,都会影响到气;气虚也同样损伤形与心。也就是说,气、形、心或是共同处于正常状态,或是一起出现问题。只要有其中一个出现问题,最终都会体现在身体症状上。
三、体知的实践性:躯体化报告率偏高的必然
体知既是一个认知的过程,也是一个行动的过程。传统西方认知是只与心智相关的活动;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于身体的体知就意味着不光是思辨,还是一种践行。杜维明先生认为体知从内涵上讲更注重“体”,而“体”是当动词使用的,即“体之于身”。体之于身深刻地揭示了自我由认知到行动的转化。与西方传统的静态思辨不同,体知具有设身处地地去想、去感受的意味,从而也具有了实践的意义。在传统文化中,知与行是合一,体知的过程同样也是知行不分的,这样的认知过程并不仅仅是心智的活动,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
身体不仅是古人理解传统文化生命观、社会观乃至宇宙观的载体,还是表达个人感受及对世界社会他人认知的方式。个体可以通过身体感知世界,身体体验是个人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从而形成了身体认知,即体知。那么,在这个大的文化环境下,各种躯体症状更多地是中国人认识到这样一个无所不包的身体后,对这种认知的实践。通过诉说身体不适可以表达许多与身体相关联的意义。第一,症状反映出肉眼看不到的器官或情志病变。在传统文化中,身与心相互表征。器官和情志是一一对应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基本情绪分别对应着心、肝、肺、脾、肾五种器官。患者陈述病情用器官或身体情况诉说的是躯体不适还是心理体验,这需要医生仔细观察和认真的体悟。第二,身体状态还可以反映出引起疾病的其他因素。中医的诊治遵循整体辨证的原则,整体辨证需要医家结合患者的病症、当前的状态等以及社会、自然环境等因素分析病因。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下,疾病的原因不再仅仅是生理病变,而且扩展到社会等更广阔的领域,病邪、环境等都成为导致人体疾病的重要因素。这样,身体症状与生理病变之间就没有了必然联系。
躯体化产生在西方身心二元论的基础上,个体的情绪不能正常地从言语和/或行为方面发泄时便被潜抑下来,而以“器官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躯体化症状,这是一种非常态的病症。传统中国几乎不存在躯体化这一症状,而躯体化在我国出现,是随着西方心理学和精神医学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和应用而产生的。[9][10]用西方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必然导致出现中国人高躯体化的现象。
四、高躯体化现象的实质:意识哲学之思维对身体哲学之行为的理解谬误
如果说传统西方哲学是一种“我思故我在”的意识哲学,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就是一种“即身而道在”的身体哲学。西方哲学范式是以主体的理性探寻为主,而中国哲学则是以主体的感性体验为主。中西方哲学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以各自哲学为基础的中西方文化对躯体症状的理解必然是不同的。为了更好地了解躯体化的来龙去脉,很有必要探究躯体化的哲学源头——西方的意识哲学。
意识哲学是由笛卡尔所开创,由黑格尔推到顶峰的认识论哲学。意识哲学的核心就是认识论是建立在批判以往西方文化贬低个人作用的基础之上。意识哲学对个人自身的理性意识能力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在于人的意识,人的本质就是理性思维的意识,而不是身体或其他。依靠这种理性的意识,人们摆脱了自身肉体的限制,可以追求永恒的真理。意识哲学把人的意识从身体中分离出来作为最高的主体,将身体体验等一切感性因素加以排斥。以此为基础的西方医学确立了这样的治疗原则:症状主诉与生理病变相对应,即患者对症状诉述应当与能证明的病理改变相称,用躯体用语报告躯体不适,用心理用语描述情绪苦恼。生理病变是导致身体症状的原因,但躯体化患者的身体症状却没有相对应的生理病变,找不到合理的病理原因,这就被看成是心理痛苦被压抑以器官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是一种非常态的病症。
但是,在中国哲学中,意识并不是主角。传统哲学从身体出发,通过体验、体悟等感性方式作为生命存在的方式。意识哲学将意识与身体对立起来,并将意识视为生命的本质。而身体哲学则反其道而行之,把身体看成是生命的基点、意识的起点。中国哲学并没有向外追求真理和知识,而是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力行来探讨个人安身立命之本与万物之源。体知以其与身体在认识论、修养论、本体论的密切关系而成为传统哲学身体性研究的重要内容。体知的体验性、关系性、实践性这三个特性进一步验证了身体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作用,身体既可以是认知的手段,也是表征与身体互补共生的事物的有效方式,更是实践各种认知、准则的行动主体。知识不需要如西方般通过观察、实验等摆脱个人主观感受的方式间接获取,而是通过把个体融入自然、社会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体味出来的。那么知识的出现既不是逻辑思辨、实验观察,也不是冥思苦想,本质上它是生活性的、社会性的,并且这些知识的传播也离不开日常生活的场景与个人身体的“亲在”。
那么,在身体如此全面地参与到世界、社会、生活的基础上,身体症状不再是压抑心理痛苦的病症。身体既然是以一种开放的方式连接到万事万物,那么对身体的诊断就不再需要如西方医学般运用各种医学检查得出,依靠身体症状的直观体验就可获得有关病症的认知。身体症状也不仅仅表明人体器官或组织的损伤,也可能是情志问题,也可能是个人发挥身体症状的社会功能,等等。“体知”不仅通过身体的感性体验进行认知,更重要的是经由身体对认知进行实践。在“体知”的映照下,个人通过述说躯体不适向他人表述着特定的意义,而在同一认知体系下的他人根据种种背景因素分析出其所要表达的含义。那么一方诉说身体症状,再加上倾听一方的心领神会,双方共同完成了体知的实践。总之,身体症状既显示了通过身体体验完成的认知,又体现了通过身体表达的实践。
归根结底,中国人的高躯体化报告率实际上就是用西方意识哲学的思维去理解中国身体哲学影响下的身体。意识哲学把身体看成是意识的对立面,是受压制的。因此,心理表达是正常的表达痛苦的方式,而躯体表达则是有问题的表达方式。意识哲学中的还原论思想把事物还原为最原始的状态,体现在医学中则表现为症状主诉与生理病变相对应。躯体症状如若找不到对应的生理病变就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而在中国身体哲学文化中则不存在上述两个条件。那么,用西方意识哲学的思维来界定中国身体哲学影响下报告病情的行为,必然导致中国人高躯体化这一有失偏颇的结论。
[1] 季建林,赵梅,王崇顺.抑郁症门诊患者躯体症状主诉及疗效比较[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10).
[2] 任清涛,李广,马秀青.内科门诊躯体形式障碍的临床特征和治疗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1,(4).
[3] 张再林,张云龙.试论中国古代“体知”的三个维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9).
[4] 张再林.中国古代“体知”的基本特征及时代意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9).
[5] Zhang. Depression and culture—a Chinese perspective. CanadianJournal of Counselling, 1995,(29).
[6] 刘雅芳.身体化的表达与诠释——中国古代精神疾患之历史文化考察[D].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09.
[7] 杨儒宾.儒家身体观[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
[8] 周瑾.多元文化视野中的身体——以早期中国身心思想为中心[D].杭州:浙江大学,2003.
[9] 翁玲玲.坐月子的人类学探讨:医疗功能与文化诠释的关系[J].妇女与两性学刊(台湾),1993,(4).
[10] 徐俊冕.躯体化与躯体形式障碍[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4,(3).
[11] 许又新.躯体化以及有关的诊断问题[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19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