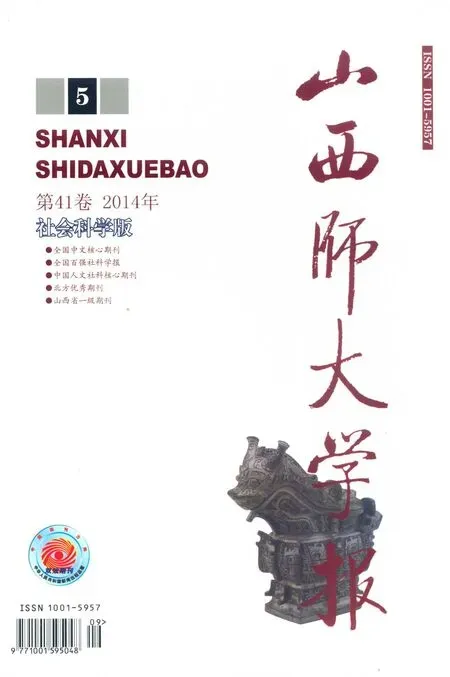行动者的鲁迅之“欲行动的思想”
胡 梅 仙
(广州大学 俗文化研究中心 , 广州 510006)
鲁迅一直崇尚一种可以让你动、你想动的思想。鲁迅“欲行动”的思想可从两个方面来追溯:走出象牙之塔和出路的“可笑”;呐喊和做泥土的工作。
一、走出与出路
鲁迅鼓励青年走出来,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早年写过《摩罗诗力说》,歌颂“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晚年谈到为什么要做小说,仍坚持早期的启蒙主义思想——“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526。鲁迅于1924年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走出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等作品。象牙塔在艺术领域一般专指脱离现实生活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小天地,比如大学、研究院等。鲁迅鼓励青年走出象牙之塔,他号召青年参与到社会中来,摒弃读死书,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他强调,看书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并且“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2]462—463。鲁迅反对死读书,赞成和社会现实相联系,使读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用社会实践丰富书籍内容,使书籍指导社会实践。实践能使所读的书活起来,读活书又可以使人想行动、想实践。正是因为鲁迅立足于现实,所以,他的语言行动都无一例外地具有与实际生活接触的意义,不发空言,不发对社会改革、个人改造无关的宏论。所以,我们很少看到鲁迅对于国家政策的宏文伟论,鲁迅的所有文章、行动的出发点即在于对社会、对个人劣根性的发掘和改造。
青年要走出象牙之塔,走出之后的路怎么走,鲁迅也不甚了然,不过,他还是鼓励人们向前走,至于走到什么地方,走的是什么路不重要,只要在走,在做就行。他说:“青年人要求出路,第一必须把眼光放远,着眼到社会的内部;另一方面又要抱有牺牲的精神。”[3]202关于怎么走路,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谈道:走人生长路有两大难关:一是歧路,一是穷途。遇见歧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4]15鲁迅说他“不问路”,因为他料定别人也不知道,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走。这条路是对是错,是成功失败,他不敢担保,但人是必须前行,必须寻找的。只有在寻找中才能找到一条渐渐通向正确的路。另一种是穷途,无路可走的时候,该怎么办?鲁迅主张“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4]16,说不定能走出一条崭新的路来,即使不能走出路来,说不定也可以收获到一些冒险的经历。不过鲁迅说:“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4]1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于行动的热衷,不管有路无路,反正就是要一直往前走。直到晚年,他还在告诫自己说要“赶快做”:“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5]633他曾说,睡在床上学游泳是永远也下不了水的,一个母亲不能因为怕婴儿摔跤就不让他学走路。这也体现了鲁迅的实践行动观。
此外,鲁迅特地谈到了对于社会的战斗。从《新青年》时代开始,鲁迅就反抗旧文化,针砭时弊,参与社会实践行动,参与到民族改革的大潮中,这是鲁迅一直在做也是一直在鼓励青年要做的事。所以,对于社会战斗的重视自是鲁迅作为启蒙思想家、革命者的最鲜明的特色。在鲁迅去世前几天,他还在一篇回忆章太炎先生的文章中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6]565
鲁迅是一个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现在、地上这是切实可感的,现在是时间,地上是当下,也就是执着于当下的切实可感的事物。所以鲁迅反对施蛰存提倡读《庄子》、《文选》,他担心国民会重新沉入读古书的死寂和专做修辞的文饰中去;反对林语堂谈性灵、幽默,和朱光潜论争静默之美和崇高之美,《新青年》时期反对胡适提倡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都是鲁迅执着于现在执着于地上的表现。郜元宝认为,20世纪中国最具现代性的问题应该是鲁迅提出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文艺与现在的关系。鲁迅是一个执着于现在的人,所以他对“生存”这些现实问题特别关注。同时,生存在鲁迅那里是以现实的关注和哲学的追究两者共存的,这使鲁迅的作品不仅仅留下历史的面貌和身影,更让他的作品达到了深层的探索人生、人性意义的高度。探索人生、人性、宇宙的意义是哲学家常做的事,鲁迅文学的价值在于把这些意义归之于对具体现实的描写、揭露、探讨之中。他的作品的长久价值即在于鲁迅自己一直在追求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的史的价值。现在是未来的历史,现在的时间是未来的桥梁。
对于现世的出路,鲁迅还没找到,也是怀疑不敢确信的,对于未来他又是坚信的。“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虽然有人指定我为没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状元么——的作者,‘毒笔’的文人,但我自信并未抹杀一切。”[1]98对于出路鲁迅虽不能确切地知道,但他知道决不是中状元的路,也不是一些正人君子和所谓青年革命家所指的道路,但鲁迅还是在努力寻求一条改革之路。对于现世出路的怀疑和对于未来的光明的坚信在鲁迅身上交织,使鲁迅既与绝望抗争,又为希望奋斗。而对绝望的抗争有时也是一种对希望的深沉的渴望。“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1]107对于当时的鲁迅来说,他已深受一些西方思潮的影响,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已经成为他的主导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鲁迅也愿把它当做一种中国的出路来探索。
对于出路的迷惘,对以往出路的否定,对未来出路的坚信,使鲁迅一直行批判之事业,一点一滴地创作,发议论,教书,亲自翻译,办杂志,编书,帮青年校对写序,提倡木刻版画,每一件事都是鲁迅一个小钉一块布片的建设工作,目的是在全社会唤醒沉睡的人们,驱除旧的习俗弊病,打破传统固化思维,创造一个不再有奴隶的新的时代。
二、“呐喊”和做“培养天才的泥土”
呐喊倾向于外部的有影响力的行动,做泥土倾向于内部的默默无闻的铺垫工作。鲁迅用文字和演讲呐喊,也用生命来做泥土的工作,并且也经常劝年轻人做泥土的工作。
在《〈呐喊〉自序》里鲁迅说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6]439在《〈奔流〉编校后记》中,鲁迅坦言热爱裴多菲是因为他的反抗俄皇亲临战场的爱国精神:“收到第一篇《彼得斐行状》时,很引起我青年时的回忆,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但他其实是一个爱国诗人,译者大约因为爱他,便不免有些掩护,将‘nation’译作‘民众’,我以为那是不必的。他生于那时,当然没有现代的见解,取长弃短,只要那‘斗志’能鼓动青年战士的心,就尽够了。”[7]197文艺虽不是直接行动,却是具有行动的意义。不过,鲁迅对于事物的看法最为尊崇的还是自己的实感和独立思考。他对于革命文学也有多重看法和一些不能确定的概念,创造社、太阳社对于革命的理解是政治活动,甚至连革命文艺都要服务于政治活动,而鲁迅更注重于国民文化、根性上的启蒙革命,所以不一定赞成流血的革命,他希望以最少的牺牲来换取最大的变革。
鲁迅说,既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但他遵循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1]469。呐喊不但是为了作前驱者,鲁迅经常会谈到自己的写作是为了慰藉那些流血的默默的隐痛的魂灵或者正在寂寞中前行的人们,也是对于自己过往光阴的纪念。由此我们既可以感受到鲁迅是用一颗人类文明中的诗人之心对于那些默默的前驱者的抚慰,同时也可以感受到鲁迅作为前驱者的孤独以及“未尝经验的无聊”。在昏睡和“大嚷”之间,鲁迅也有过困惑。是让熟睡的人们从昏睡中死灭,还是大嚷把他们叫醒去承受无可逃避的死亡和失败的苦楚?鲁迅仍希望对未来抱着希望。所以他又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6]441“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6]439叫喊于生人中无人回应,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寂寞。民众的愚昧和启蒙者的寂寞一直是中国改革、革命的首要问题。鲁迅一直都注重一种能产生社会效应的语言,这也是他所说的选择文艺改变国人精神的思想,也即是鲁迅一生都在坚持的启蒙文学。鲁迅一生都在呐喊,其言语昭示着一种行动的趋向,即使在无语的沉默以及无词的言语中,我们仍能感到那种用鲜血、阴影积成的沉默的爆发力。
鲁迅强调切近的人生选择,强调做泥土,做梯子,这都表明他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作者,是言与行结合的典范。他也可以像那些躲在研究室、实验室的人一样做自己宏伟的千年的事业,可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鲁迅更希望能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真正地做一个民族的呐喊者、启蒙者。这个启蒙者是用鲜血、生命来承担自己的忧患和理想的。特别是那种来自于生活、底层、最朴素的泥土里的艺术,这种艺术带着人的血性、体温、屈辱的泪水。只有把自己的鲜血浇铸在里面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像鲁迅那种把文学当作与刀和剑拼搏的血肉却又不乏文学性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
鲁迅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5]122可见,鲁迅对中国脊梁的定义是“干”的人,是用自己的“动”来显示自己的存在。特别是那些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更是鲁迅所尊崇的,而他一辈子也如他所称赞的中国的脊梁一样,拼命苦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鲁迅的眼光始终都是向下的,向着弱者的。
只有空洞洞的呐喊显然不足以承担鲁迅所要坚持的启蒙事业。办杂志,当编辑,翻译外国文学,讲演,扶持青年作者等,都是鲁迅启蒙行动的一部分。像柔石、叶紫、萧红、萧军等都是鲁迅扶持过的作家。鲁迅帮他们看稿子,推荐发表,写序言,引入文学圈子,甚至还在经济上帮助他们。
针对当时附和胡适等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整理国故”,“崇拜创作”等主张的人们所发的一些议论,鲁迅提出要做“培养天才的泥土”,他说:“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6]177“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6]174—175对“地底下”的中国脊梁的赞扬,对于人类文明的点滴累积意识也可看出鲁迅对于培育天才的泥土的重视。
鲁迅对于青年“则必退让,或默然甘受损失”,所以他一生为青年、为中国甘心做泥土、梯子的工作,但也不能否认一些青年人的堕落。他举例说:“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1]5。不过鲁迅此后还是“为最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1]5。在左联成立大会后,鲁迅写信给川岛说:“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8]226加入左联后他虽知道左联人员芜杂,但还是希望自己能为有一个共同目标的人做梯子。他说:“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敷药。”[1]645鲁迅认为,几个人处事,只要在大的方向上一致,于中国有利,就可以联合成战线。“梯子说”充分说明鲁迅并没有对一切抱着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希望,只是尽自己的一份力,为了一份目前自己还比较愿意相信的理想去做一些实事,而不是如苏雪林所说的“沽名钓利”。1936年3月18日鲁迅在《致欧阳山、草明》的信中说自己“数十年来,不肯给手和眼睛闲空,是真的,但早已成了习惯,不觉得什么了”,并说,“在中国要做的事很多,而我做得有限,真是不值得说的。不过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9]48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曾这样描述鲁迅:“孔子的‘栖栖遑遑’,是为的周游列国,想做官,来达到他改革社会的理想。而鲁迅也终日‘栖栖遑遑’地‘席不暇暖’,却为的是人手少,要急着做的事情正多,他以一当百还嫌不够,时常说:‘中国多几个像我一样的傻子就好了。’‘有一百个,中国不是这样了。’所以一面自己加紧工作,一面寻求精神的战士。”[10]161
鲁迅希望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改造中国,搅动中国这一潭死寂的静水,唤醒沉睡着的国人。怎样让中华民族不至于在与世界角逐中失去生存的资格,怎样吸收外来文化,怎样挖掘民族文化的精华,怎样发动民众,这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在考虑的问题。鲁迅深切地感知到,一个大的时代要来,这个大的时代一定是一个需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参与的时代,他宁愿做这样一个时代的行动的先锋。
[1] 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鲁迅演讲全集[M].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07.
[4] 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 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 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 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 鲁迅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 许广平.鲁迅的写作和生活[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