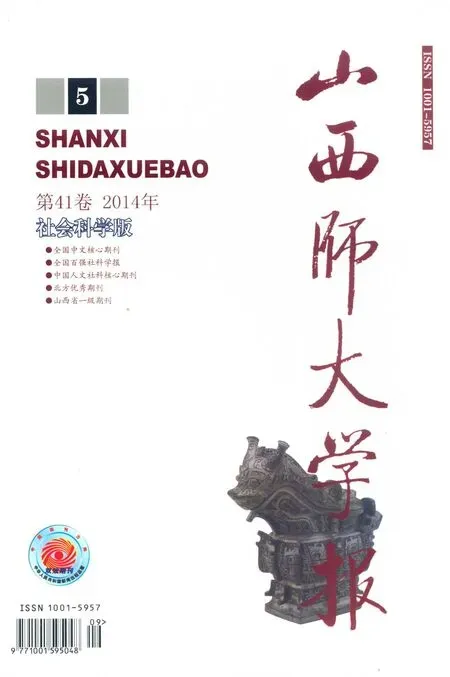知识分子的另类成长:从自由主义者到政治一分子
——从《围城》到《洗澡》
龚 郑 勇
(南通高等师范学校 人文系, 江苏 南通 226000)
钱钟书说杨绛的《干校六记》“记这,记那,都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1]3事实上,并不仅仅是杨绛的这本《干校六记》有这样的功能,所有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中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也都有这种充当点缀大历史背景作用的功能,读者可以通过这种“小点缀”、“小穿插”窥到一点大时代的秘密。
建国后,伴随着新政权建立的还有一系列的运动,这一系列运动的先后展开让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对传统中国进行了一番自上而下的改造,从而使得全国上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强势姿态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国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社会各阶层也被前所未有地通过被改造的方式,纳入了国家的体制中。这在当时代和后人描写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多有涉及,即便是向来喜欢穿“隐身衣”来观察社会人情、写作淡化时代背景的杨绛夫妇的文字中也同样有所反映。[2]102—108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他们夫妇各自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围城》和《洗澡》,就会发现,尽管两本小说描写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小说中的人物群体无论是在学历上,还是在生活习性上都有相似性,但仅仅因为人物生活的时代有所不同,《洗澡》中的系列知识分子较《围城》有着更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开始在各种不同人物的日常言谈举止中显现出来,成为一个时代的化石。
当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当时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单方面在国人的生活中的渗透,事实上,当时某些人物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也积极地利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来获得一种自我的保护和生存空间,这在杨绛的《洗澡》中并不少见;而在钱钟书的《围城》中却是一个空缺。
笔者想通过钱钟书的《围城》与杨绛的《洗澡》这两部风格主题较为接近的小说,对建国前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日常工作中的同事关系、师生关系、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变迁做一番简单的探讨,以窥到一点时代的痕迹。
一
政治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是由其学识贡献来决定”的常识。所以,当《围城》中李梅亭在大学课上有声有色地教授子虚乌有的《先秦小说史》[3]226时,作者不动声色地将李梅亭的不学无术揭示了出来,因为先秦时中国尚无小说,李梅亭课堂的热闹是建立在他的无知基础上的,但这种无知并不需要掩饰且强以为“知”。而在1950年代,由于政治第一、以苏联思想指导一切的原则的确立,传统对于知识分子的评价原则开始受到颠覆,一些极个别不学无术的政工、南下干部开始以真理自居,理直气壮地对传统知识分子发号施令。《洗澡》中施妮娜强词夺理要图书管理员找巴尔扎克的《红与黑》、会议上夸夸其谈《恶之花》是小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戏剧时,这里暴露出的不仅仅是她的无知,还有她的蛮横和周围诸人对于作为南下干部的阿谀奉承,姜敏说:“把《恶之花》说成小说,也没什么相干,反正是腐朽的嘛!”[4]98,余楠甚至恭维她把《人间喜剧》说成戏剧是“顶俏皮”[4]98的话,江滔滔说要研究“勃朗特姐”,余楠也奉承道:“咱们要的是姐,没要妹。”[4]99同样是一种不学无术,也同样是一种奉承,但由于施妮娜、江滔滔政工干部的身份,使得其政治色彩突出,硬寻找到一种牵强附会的理由,把一种不学无术包装起来,使“无知”成为了一种理直气壮的“有知”。更值得深思的是,李梅亭尚未对其他人的教学能力批评指责;而施妮娜、江滔滔凭借其政治身份,能够对其他人指手画脚:施妮娜开会指导别人的文学研究,“研究资产阶级的文学,必须有正确的观点,要有个纲领性的指导”[4]86,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无一丁点内心不安之感。由于各人身份的不同,各人对于政治话语的认识程度和依赖利用程度不同,这使得一些政工、南下干部一旦掌握了政治话语权便开始有了对知识分子重新评价的资格,反之,纯粹的知识分子因对政治的习惯性距离使其在当时的政治上自觉低人一等。政治生活改变了传统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方式,一切都重新开始了。
虽然在《围城》中,陆子潇在方鸿渐的房间里看到了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忙向校长高松年告密[3]291,高松年认为方有思想问题而予解聘;但《洗澡》中,姚宓的一篇尚未公开发表的文章,仅仅被同事私下借阅,便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在大学学刊上以《批判西洋文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的老一套》为题,不点名地批判,上纲上线。[4]153政治关系到个人的社会地位,也是各项研究成果是否为废品毒草的依据,连不是干部的姜敏也认为她的研究才是抓到了重点,只有她纲领性调子定下了,姚宓的研究才能进行:得等我先定下调子,她才能照着分析研究呀![4]117可见无论建国前还是后,政治一直渗透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成为一种衡量是否进步、甚至打压对手的重要工具。只是1950年代的政治至上的环境氛围开始严重干扰,甚至扭曲了正常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不安全感开始增强,敌对氛围加重,政治成了打击对手的最有力的致命武器。即便是知识分子的日常家庭和邻里关系也受到政治的有形无形影响,连向来不关心家庭以外的家庭妇女宛英在家里也听到丈夫他们反复提到 “观点不正确”、“阶级性不突出”、“人性论”等等具有时代尤其是具有政治内涵的词汇。[4]134在“三反”运动的高潮中,邻里间的正常串门也开始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所利用,许彦成喜欢到姚家去和姚老太太一起听音乐,结果姚老太太善意提醒他得小心,别到处串门儿,以免人家说他“摸底”或是进行“攻守同盟”[4]201,姚老太太是一个身体行动不便、不出大门的家庭老妇人,但也同样被笼罩在强烈的政治空气中,口吐政治术语,受到时代政治的熏陶。而在《围城》中,固然有诸如“从龙派”、“粤派”、“少壮派”、“留日派”[3]261的说法,但更多地依然停留在单纯的人际交往圈子层面,并不具有政治功能。
《围城》中,学生对教师的鄙夷往往体现在对其学术水平低下而产生的不满,钱钟书这样调侃说:学生的美德是“公道” 而非“悲慈”[3]279。三闾大学的学生将方鸿渐教错的试卷准备上交展示即是其对教师不满的一种反抗,虽然其间还有其他教师挑拨之故,但其反抗的方式还是未脱离传统的师生关系的正常轨道。但建国后由于政治的因素,学生对教师的反抗就不是简单地以教学水平为借口了。《洗澡》中许彦成告诫妻子大学里的教师在羡慕他们不用面对学生,因为学生的程度不一:“不是教书,是教学生啊。咱们够格吗?你这样的老师,不说你散布资产阶级毒素才怪!况且咱们教的是外国文学。学生问你学外国文学什么用,你说的好吗?”[4]180所以,后来许彦成夫妇从文学研究所离开到大学去教书,虽然姚老太太认为他们中了“头彩”,但许彦成的内心反而充满着不安,认为以后离文学越远越好,只打算教教外系的英文,或者本系的文法。[4]261这时,学生的“美德”成了“政治”。几十年后的杨绛写小说时将此情节设置在小说中,正说明其内心的不能释怀和心有余悸。事实上,杨绛的这段情节设置是有强烈的现实依据的,其师吴宓在课上随意举一个例子“三两犹不足,何况二两乎?”来说明文言句式,结果被学生告发为“反对党的粮食政策”[5]225;梁宗岱1950年代批评当时的学生素质差,认为有些人根本不应该入大学,结果被批判为“天才教育论”[6]291。大概也鉴于此,杨绛本人在当年的课堂上中规中矩,据她的学生回忆说:“她上课从不说任何过格的话,课又讲得不错,既不属于‘向上爬’的典型,也不属于‘混饭吃’的典型。”[7]175—177本来,课堂是师生互相交换信息、碰撞思想火花的地方,现在成了教师被监督和告发的审批席,成为教师恐惧的屠宰场,其间变味也隐含着时代的变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一个向来没有个人本位的国度里,家庭是抗拒外来力量(国家、社会)的最基层单位。但是,随着建国后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渗透,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父子相隐”的文化开始衰落,传统的家庭也开始变得有缝隙了,其与国家社会相抵抗的功能开始削弱了。余楠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读大学的儿子“思想都很进步,除了向家里要钱,和爸爸界限划得很清”[4]4。女儿开始学会用“糖衣炮弹”[4]57这样的政治术语来评价妈妈烧的菜。政治术语、政治文化开始进入日常的家庭生活,政治运动又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的分化。“三反”运动中,余楠建国前开玩笑说的卖五香花生豆儿的陈年琐事也被全身心投入运动的女儿余照所告发[4]218—219,成为一条不可告人的罪证,于是想到家中最近加入了青年团、开始和家里十分疏远的女儿和两个非常进步的儿子,余楠不知自己还有多少被上纲上线的家庭琐事被儿女告发,于是“顿时彻骨寒冷”。[4]219随着运动的进一步深入,他开始连自小青梅竹马、向来百依百顺的妻子也开始害怕,于是一向具有大男人主义色彩的余楠竟也感觉在妻子宛英面前“矮了半截”。[4]220传统的家庭观念与家庭氛围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开始土崩瓦解,家庭琐事在政治运动中被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赋予了各种不同的政治内涵,他们对此作出了有利于自己的解读。于是在政治运动中,传统的、温馨的、田园牧歌似的家庭面纱被撕破,与外界大社会一样成为一个政治斗争的场所而不是躲避社会风暴的避风港。而在《围城》中,旧式大家庭中的恩怨只能以一地鸡毛式的日常琐事来体现,这种家庭琐事只停留于家庭这个层面,并未被上升到政治的角度,更未被家庭成员援引外界的政治运动来获得有利于自身的政治资源,家庭依然是各个家庭成员至少是经济上守望相助的共同体。尽管旧式大家庭中存在着诸多的不尽如人意,但较建国后运动中的家庭氛围依然要温和得多。
二
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有一段关于“学校与教师有机体”的高论,学校与教师的关系可以像有机体与细胞的关系,但事实上,这种有机体理论在当时只存在于想象中并未有实现的条件。所以,后来方鸿渐在三闾大学的落聘并未断绝了他的一切生路,他依然可以在上海的报馆找到工作。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雇主也并非只有公立的学校机关一家,当时以方鸿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虽然也同样受到领导报复、同事排挤等诸多人为因素造成的失业困扰,但他依然可以在其他雇主那里寻觅到自己的生计和社会关系。但建国后,随着单位体制的建立,知识分子与单位才在真正意义上构成了细胞与有机体的关系,这固然解决了长期困扰知识分子的失业问题,但也同样阻碍了知识分子的正常流动,使他们一辈子身困于单位的体制格局和人事关系中,妨碍了他们的主动选择和积极性。只是,这种自古未有的大变局所造成的的利弊需在一段时间后才能显现,对于当时许多局内人而言尚未意识到这种时代变迁的真正意义。因此,在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恐怕是拥护“单位”这种模式的,丁宝桂在“洗澡”交心中讲自己现在“就像聘去做了媳妇一样”非常有安全感,而从前一直担心失业与生病。[4]237。
因此,当知识分子与单位体制真正有机结合时,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开始衰退与对单位体制依附性的增强。所以,文学研究所里的知识分子在重新填表等待分配的时候,大家认为这是买彩票等“开彩”,因为“配在什么机构,就是终身从属的机构”[4]257——这是知识分子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点”,这在杨绛1980年代写这本小说时看得很清楚,这段平实的语言几十年后读来依然显得如此的苍凉,这批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着被动与无奈。
所以,当自由流动成为一种可能时,方鸿渐们的未来才不会完全无路可走;而当自由流动的可能性丧失时,许彦成们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被动的等待,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彩票”一样的不可把握上。随着国家对整个社会改造的完成,新的意识形态开始进一步渗透,并参与到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使得他们与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同样被打上时代的痕迹:政治的纲领性文件指导着他们的一切,政治运动也左右着他们的一切,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参加会议、“交心”、汇报、检举揭发……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个性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知识分子残存的独立性多少有些抵触,杨绛借丁宝桂私下对老伴儿的话说:“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越丑越美,越臭越香。像我们这种人,有什么可检讨的呢。人越是作恶多端,越是不要脸,检讨起来才有话可说,说起来也有声有色,越显得觉悟高,检讨深刻。”[4]203—204但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一切血肉之躯都是那么微不足道。政治改造着社会各个个体成员,也改变着他们的日常一切,甚至是家庭生活,没有人能够置身于政治之外。“三反”运动中,朱千里自以为与己毫不相干,但是最终被折腾得自杀,躺在医院里还要面对着墙上打倒他的大标语。[4]234钱钟书引古罗马谚语“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8]333,可谓是对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表现的总结。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恐惧政治的,一部分先行者在掌握了政治秘诀后便成了真理的代言人,江滔滔告诫大家苏联文学要溶化在每项研究的重点里[4]87;负责政治工作的办公室主任范凡在无法区分知识分子水平高低时,觉得“也许该看他们的‘政治’了”[4]97。“政治第一”的原则用吴宓的说法:“阶级为帮赖斗争,是非汝合记分明。层层制度休言该,处处服从莫妄评。政治课先新知足,工农身贵老师轻。中原文史原当废,翘首苏联百事精。”[5]220
由于政治的渗透需要具体的“人”作为载体,所以,“人”的被政治化的进程就是政治的渗透影响加剧的进程。杨绛《洗澡》中三个篇章的小标题委婉地反映了这个历史进程:“采葑采菲”语出《诗经·邶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比喻取其所长,文学研究所广招各路人才;“如匪浣衣”语出《诗经·邶风·柏舟》:“心之忧矣,如匪浣衣。”比喻政治运动前夕,个人内心不同的紧张、焦虑与无奈;“沧浪之水清兮”语出《楚辞·渔父》,意为自取之也,暗喻政治的渗透作用与个人的价值取向密不可分。所以,政治需要一些“人”作载体,而一些“人”也需要借政治作东风,于是,一些人开始变得可怕起来,人际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钱钟书总结历史上在政治作用下的文字狱时说:“口戕口”可与武王《笔书》中‘陷水可脱,陷文不活’相印证”[8]855—866。
因此,钱钟书夫妇的两本小说——《围城》与《洗澡》,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构成了一个系列、一对互照的镜子、一种互补,反映出知识分子在特定年代里的成长变迁和时代在这个群体身上的投影。如果说方鸿渐因为缺乏人生的目标而使自己的生活不断在“围城”里漫无目的地穿梭,那么许彦成的未来目标则清晰得多,那就是在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缝隙中觅得有限的生存空间,达到“‘亦见亦隐’之境界”[8]246,至于能否做到“万人如海一身藏”的逍遥,则要看个人的造化了。由于两部小说创作的时代尤其是创作时的人生经历不同,它们的主题也由具有现代性的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转向了更具现实意义的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处境的揭示,这或许是他们夫妇作品略有不同的地方。
[1] 杨绛.杨绛作品精选——散文(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 陈佳璇,胡范铸.一九七二——一九七五时的社会批判:《管锥编》与撰述语境的互文性分析[J].苏州:东吴学术,2012,(3).
[3] 钱钟书.围城[M].北京:三联书店,2002.
[4] 杨绛.洗澡[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5] 傅宏星.吴宓评传[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M].北京:三联书店,2013.
[7] 孔庆茂.杨绛评传[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8] 钱钟书.管锥编 [M].北京:中华书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