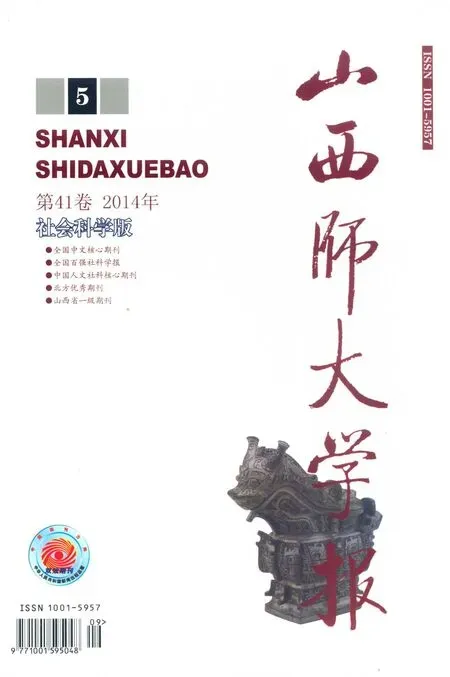反讽张力与小说审美空间的拓展
朱 斌,杨思涵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兰州 730070)
D·C米克曾说:“如果有谁觉得自己产生了一份雅兴,要让人思路混乱、语无伦次,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请他当场为‘反讽’做个界定。”[1]11不错,要界定反讽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它本身充满了自我悖论。所以,关于文学中的反讽,D·C米克避开了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而只总结出它的诸多基本特征:“自信而又无知(真正的或佯装的)、表象与事实的对照、喜剧因素、超然因素和美学因素。”[1]70在我们看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自信而又无知”以及“表象与事实的对照”。因为“在大多数批评术语中”,反讽都“保留了‘伪装’的基本意思,或与事实不同的意思”[2]135。而“伪装”以及“与事实不同”,其具体所指实际上都基本一致:事实真相与表象的对照。这种对照往往使蒙蔽于表象的被反讽者显得“自信而无知”。可见,表象与真相的对照,常常内含了“自信而又无知”的对比。所以,反讽必然要求表象与真相的对立统一,自信与无知的矛盾一体,因而往往能拓展出张力充盈的审美空间。
一、叙述的反讽张力与审美空间的拓展
“每一种反讽的基本特征都是事实与表象之间形成对照”,“反讽者似乎在说一件事,而实际上在说十分不同的某事”[1]43—44。这样,反讽者直接说出的,往往只是事实表象:一种假扮、佯装,或故意欺骗,但与此同时,事实真相又被他巧妙地透露了出来。所以,对叙述者而言,其反讽成功的关键既在于假扮、佯装,以事实表象故意欺骗人,又要在其中暗示出事实真相,让人知晓真相。这就要求在隐藏与显露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
如果叙述者对事实真相隐藏过深,没有足够的细节暗示,就难以让人体味到反讽,甚至会以假为真,错将表象看作真相,这就意味着反讽叙述的失败。这类失败的反讽叙述常常是不可靠叙述。所以,“运用不可靠叙述者这一技巧最难的,是如何实现从不可靠到可靠的连接和转化”[3]375。作者必须做出“许多有意识的精心安排”,使读者在不可靠叙述的含混中,获得必要而可靠的清晰判断,从而“与沉默的作者进行交流,宛如从后面来观察坐在前面的叙述者,观察他富于幽默的、或不光彩的、或滑稽可笑的、或不正当的冲动的行为举止”[4]300。可见,成功的不可靠叙述,总蕴藏着巧妙的可靠暗示和指引,总维持了不可靠叙述和可靠暗示之间的必要张力:叙述的不可靠导致了叙述者意图倾向的遮蔽和含混;而可靠暗示和指引则又促使了其意图倾向的显露和清晰。显露因而与隐藏交融,含混因而与清晰一体,这就拓展出了张力充盈的审美空间。
加缪的《局外人》,其叙述者由主人公莫尔索充当,这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但其不可靠叙述,却有诸多细节暴露了他的偏激与反常。比如:他对生活敷衍塞责,缺乏正常人的感情,对一切都作局外观;而对世界的冷漠,却反倒有“兄弟般的情意”。这样的细节,就成为其不可靠叙述中的可靠暗示,指引我们作出可靠判断:其思想情感和人生态度不能视为隐含作者的倾向。实际上,隐含作者对其局外人般的冷漠是有巧妙批判的。譬如,在小说结尾部分,叙述者指出,为了把一切做完善,也为了使他不感到孤独,他希望在被处决的那天,有很多人来围观,希望人们对他发出表示憎恶的喊叫声。这与他的一贯态度迥异,使得叙述似乎自相矛盾。而这正巧妙地表达了隐含作者的倾向:同“世界的冷漠”有着“兄弟般”情意的局外人,已对世界的冷漠有了认真的反思,且开始转向对它的批判了,因而他希望被处决那天,围观者不是局外人般的“温和的冷漠”,而是置身局内的积极参与,哪怕“对我报之以憎恶的喊叫声”。这样,可靠与不可靠彼此激荡,拓宽了叙述的审美空间,因而有效强化了叙述的反讽张力。
对可靠叙述者而言,其反讽张力的生成关键在于其意图倾向的含混化。可靠叙述者因其全知全能,常给读者过多指引,小说意义世界往往毫无遮拦,其又拥有直接评论的权威,往往过度发挥,说教味过浓,甚至粗暴生硬。这样,其反讽张力的匮乏,往往在于事实真相透露过多,让人一目了然,毫无回味的余地,无法促成表象与真相的“对照”。因此,其反讽叙述往往蜕变为肤浅而露骨的讥讽。可见,可靠叙述者要想强化其叙述的反讽张力、拓展审美空间,就必须促成其主观倾向的含混化,通常的情况是:表面上,他看起来似乎在表扬、肯定一个人,而实际上,他对人的褒扬里面所暗含的主要是对人的贬斥、批判与否定。这样,叙述者的否定倾向就披上了肯定的伪装,因而增添了几分含混。这其实是“反话正说”:表面看,似乎是肯定和称颂,但实际却是否定和批判。但其“反面”的否定和批判,却伪装成了“正面”的肯定和称颂,叙述者的意图倾向就添了几分含混,但又并不晦涩,以至促成了清晰与含混的矛盾统一,因而强化了叙述的反讽张力。
也有“正话反说”的反讽:表面看,似乎是批评和否定,但实际上却是肯定和褒扬。譬如《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叙述者说贾宝玉生来就有一种“下流痴病”,喜欢在女儿堆里混,因而自幼就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如今知了些许人事,又看了一些“邪书僻传”,所以“下流痴病”更加严重。这里,叙述者将宝玉对黛玉的情爱,视为一种“下流痴病”,把宝玉喜爱之书,视为“邪书僻传”,表面上,是对宝玉的批判与指责,但结合全书语境,我们却不难发觉,叙述者实际的态度正好相反:认同宝玉的痴情,赞赏他的喜好。这样,叙述者正面的肯定性评价,就披上了反面的否定性伪装,其可靠的主观倾向就获得了几分含混,不再那么清晰透明,因而促成了表象与真相的矛盾统一,从而被反讽化了。然而,叙述者意图倾向的反讽化,无论是“正话反说”,还是“反话正说”,他所说的一切其实都是一本正经的假话,是佯装真实的大胆谎言,因而总要披上表象的伪装。这就强化了可靠叙述中的不可靠力量,促成了表象与真相、含混与清晰、遮蔽与显露等诸多矛盾因素的彼此撞击,因而拓展出张力蕴藉的审美空间。
二、主题的反讽张力与审美空间的拓展
小说最常见的主题是命运反讽主题。命运反讽,常将消极低落的未来与积极高扬的现在矛盾交融:积极高扬的现在构成反讽的事实表象,而消极低落的未来则构成反讽的事实真相,这就促成了表象和真相的对立统一。虽然任何反讽的突出特征主要都是事实表象与真相之间的对照,但这种对照的存在,只有反讽者和旁观者才明了,被反讽者则往往是“自信而又无知”的,只陶醉于积极而高扬的事实表象,因而完全被各种表象所蒙蔽,而不知道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所以,命运反讽主题,其表象与真相的矛盾统一,又内蕴着自信与无知的对立一体。
曹文轩曾肯定地说:“预叙不能作为一种全局性的安排,因为倘若如此,它就会使小说丧失了使阅读者进行阅读的动力。阅读的动力是‘以后’。难以预测的、不确切的‘以后’总在前方诱惑着读者,……预叙过量了,甚至将‘以后’都和盘托出了,阅读再进行下去也就索然无味了。”[5]155这话大体正确,通常,预叙的魅力确实在于半透明性:不将“以后”和盘托出,以激起你看个究竟的欲望。但将“以后”——尤其是悲惨的、不幸的结局——和盘托出,虽丧失了对“以后”结局的悬念,却强化了另一种悬念——对过程的悬念:如此结局是怎样导致的?更关键的是,对悲惨结局的预叙,能给读者一种超越于人物之上的反讽视角让人洞察:人物沉溺于其中的一切,譬如欢笑或悲哀,奋斗或沉沦等,都毫无意义,最终等待他的只是悲惨和不幸。实际上,这正是命运反讽主题的一种经典表达。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其篇名就预告了事件的低落结局,这作为一种事实真相,高悬于情节发展的整个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人物却一直为种种高扬的事实表象所蒙蔽,不遗余力地追求着,满怀希望地期盼着,因而显得“自信而无知”。这样,作为结局的真相就与作为过程的表象矛盾统一,其中又内蕴了人物盲目自信与毫不自知的对立一体,这就拓展出极具张力的审美空间,也便有了深广的人生反讽意味:一切美好注定会化为乌有。
除预叙之外,反讽中的低落结局,也常以预言或预兆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中国古典小说中,预言结局的开端极其普遍,话本的“入话”或“得胜头回”,章回小说的“引首”或“楔子”,以及传奇的“开场”或“引子”,往往都是带有预言性的对未来的暗示。而在故事叙述中穿插诗词或韵文,以对未来结局做出暗示,则几乎成为古典小说的一种惯例。譬如,《金瓶梅》频繁采用“山坡羊”唱词,“这一曲牌演唱的频率之繁,不免使人感到它似乎是整部作品的主题歌,常讽刺挖苦西门庆庭院里的妇女中的那几只迷途的小绵羊”[6]109。而且,它明显发挥了预言结局的作用。比如第三十三回,当陈经济与潘金莲打得火热之际,那里的二支“山坡羊”唱词就满含着对未来的暗示:他们的乱伦,将毁灭自己。这样,唱词跨越了现在,预示了悲剧性未来,而这悲剧性未来又与人物此刻的执迷不悟形成了强烈反差,因而拓展出极具张力的审美空间,生发出浓郁的反讽意味。整部小说,几乎每一回出现的各种唱词中,都内蕴了这么一种相似的暗示:虚幻的热情终将冷却。这就于热烈欢快的沉溺中透示出一种浓郁的凄凉和空虚味道,因而能够使读者超越眼下的欢快场面,洞察到消极与低落的末日必将来临。
当然,低落结局的提前揭晓,不一定总在故事叙述的开端。其实,任何地方的披露,哪怕只是巧妙的暗示,都会促成未来真相和当下表象的对立统一,因而都能生发出耐人寻味的反讽张力。所以,俄狄浦斯发誓查惩凶手并诅咒凶手时,我们却知道:凶手正是他自己,等待他的,将是他的自我惩罚,这时,我们就会感受到一种命运反讽。当伊菲革涅亚被父亲带到奥利斯,以为自己将与阿喀琉斯成亲,对爸爸心存感激时,我们却知道:她父亲阿伽门农向她隐瞒了真相,他带她到那里,是要将她献祭给神灵的,这时,我们也能感受到一种命运反讽。因此,反讽无论出现在故事叙述的哪个地方,都能拓展出极具张力的审美空间,散发耐人回味的审美意味。
三、视角的反讽张力与审美空间的拓展
著名学者王国维有一句著名的话:“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7]31不错,“入乎其内”,所以能够移情观照,因而具有人间情怀;“出乎其外”,所以能够超然审视,因而具有天道精神。这反映到小说作品中,就促成了“入”与“出”的对立一体,也促成了移情卷入和超然反观的矛盾统一,同时也构成了内蕴着天人之道的张力视角。[8]这其实是一种“反讽观照”视角:以宏阔的宇宙视角、上帝眼光,对人间进行超然反观与审视;与此同时,又以真切而体贴的人道眼光、人间情怀,移情入世。那么,在小说文本中,这种内蕴了天人之道的反讽张力视角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呢?
在我们看来,其最常见的生成方式是通过如前所说的提前预示真相,将消极而低落结局提前叙述。这消极而低落的结局,其实就成了一种烛照真相的超然视角,一直高悬于情节展开的整个过程,而故事人物移情卷入的整个努力过程,便染上了突出的虚幻表象色彩:不过是一场白忙活而已。于是,作为结局的真相就与作为过程的表象彼此交融,洞悉真相的超然就同蒙蔽于表象的沉溺矛盾统一,这就形成了极富张力的反讽视角和审美空间。此外,通过最终发现让移情努力完全落空的事实真相,以促成表象与真相的对立统一,这也是小说文本构成反讽视角的一种常见方式。且看郑万隆的小说《狗头金》,它主要讲述一个名叫王结实的淘金人挖寻狗头金的故事:淘金人冒着危险,辛辛苦苦挖寻到一块狗头金,经过一番斗智斗勇,击败了贪婪的窥视者,其后又历尽艰辛,冒着风雪,满怀希望地回到家中,但最终却发现,这狗头金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而已。这样,王结实最终对事实真相的发现,便使其种种移情努力的艰辛过程成为一场徒劳,只是白忙活而已,因而染上了人生幻象的色彩。这样,人物移情卷入的努力过程就作为一种人生表象,与其最后超然洞悉的真相发现彼此交织、矛盾统一,从而形成了张力充盈的反讽视角和耐人回味的反讽空间。
在诸多小说文本中,反讽视角也常常通过对比性视角的并置来促成。马金莲的小说《父亲的雪》,主要采用叙述者阿舍的视角,但小说还常常借用其他人物的视角作为对其视角的修正与补充,因而形成了诸多不同视角的对比并置。例如,叙述者阿舍指出:她一进继父的家门,母亲就叫她把这当成自己的家,但她却固执地认为这不是自己的家,她自己的家在母亲改嫁那天就破碎了。这可以视为阿舍的视角与其母亲视角的对比并置。又如,当她母亲指着她的继父,让她“快叫新大”时,她动了动嘴,继父他们都以为她叫了,所以非常高兴,但他们不知道,她想说出的那个字是“不”。这是阿舍的视角和继父他们视角的对比并置。再如,她觉得母亲上了媒人的当,嫁给了一个没有男人模样的男人,但她母亲的心思却全扑在这个男人上头,“一心一意地”和他过日子。这又是阿舍的视角同其母亲视角的对比并置。又如,她认为她继父对她毫不关心,所以在送她回家的半道上扔下她走了,因而非常恨他。但她母亲却告诉她:继父时常牵挂她,那一回一直偷偷跟在她身后送她,直到她回家后,才冒着风雪连夜往回赶,差点冻死了,而且落下了严重的肺病。她大姐也责备她,说她太犟了,继父想听她叫一声“新大”,愣是到死都没有听到。这里,阿舍的视角与其母亲、与其大姐的视角,都形成了对比并置。这诸多不同视角的对比并置,巧妙地暗示出了事实真相:阿舍根本不理解其母亲,也根本不理解其继父,没有领会他们对她的深爱,这就使她显得盲目自信而又毫不自知,因而有了浓郁的反讽意味。
可见,小说仰仗于提前揭示真相,或通过最后发现真相,加之依靠种种对比性视角的并置来暗示真相,就有效地促成了事实表象与真相的有机一体,这就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反讽视角,并拓展出极具张力的审美空间。当然,反讽张力在小说中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难以一一例举,我们在此论及的,只是其大概。可以说,正是这种种反讽张力,拓展了小说的审美空间,强化了小说的艺术魅力,因而提升了小说的艺术品级。
四、中国当代文坛:逼仄的“反讽”空间
但是,让人觉得遗憾的是:中国当代文坛的诸多所谓“反讽”,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诸多小说“反讽”,却常常缺乏这样的审美张力,因而匮乏耐人回味的反讽空间。它们虽然都披上了“反讽”的外衣,也常常都自诩为“反讽”,可实质上,其绝大多数都只属于修辞层面的言语反讽,很少有文本总体格局上的叙述反讽、视角反讽和主题反讽,尤其缺少针对人类命运的本体反讽。其中,有许多甚至连言语反讽也谈不上,而多属王朔式毫无节制的随意调侃和毫无遮拦的嬉笑怒骂,以至于沦落为浅白露骨的讥讽了。反讽因而变得毫无遮拦,直接将意图倾向和盘托出,透明得像平板玻璃,丝毫没有含蓄、朦胧的意味,因而破坏了反讽所必需的表象与真相的矛盾统一、有机一体,也消解了言语反讽所必不可少的言内义与言外义之间的必要张力。[9]
在此,我们仅看看王朔笔下的几处所谓“反讽”。先看:“同志们啊,这是灵与肉的奉献呵!……我们就是受到万人唾骂、千夫所指、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是值得的,也可以笑慰平生。”(《你不是一个俗人》)再看:“要说全世界各民族让我挑,我还就挑中华民族,混饭吃再也没比中国更好的地方了。”(《一点正经没有》)又如:“综观世界历史,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通过吃世代相传地保存下来,我们还独此一家。这也是我们民族数千年绵延不绝、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根本原因。”(《千万别把我当人》)这些,大体可以代表王朔所谓“反讽”的基本特征,也大体可以体现我国当代文坛的所谓“反讽”的基本风貌:浅白直露,毫无含蓄蕴藉之美,匮乏表象与真相比照的张力空间,因而匮乏耐人回味的反讽意蕴。其实,如前所说,这并不是意味深长的反讽,而是肤浅而油滑的讥讽,因为“讥讽者的口吻如此明确无误地传达他真正的意思,以致几乎没有一点假装不知此事的样子”[1]75。
叙事学家华莱士·马丁曾指出:“反讽可以毫不动情地拉开距离,保持一种奥林匹斯神祇式的平静,注视着也许还同情着人类的弱点。”[10]180是的,“毫不动情地拉开距离”,保持一种“神祇式的平静”,超然反观“人类的弱点”,这才是小说反讽应有的真正品质。而我国当代小说的所谓“反讽”,却缺乏这样的品质:常激情难抑,沉醉在纯粹的语言快感之中,只擅长肤浅而任性的冷嘲热讽,对自我和自我所处的时代以及整个人类都无法“拉开距离”,也难以保持“神祇式的平静”,因而难以超然反观,也就难以看出“人类的弱点”。这样,小说反讽张力的匮乏,小说审美空间的狭隘,小说反讽意味的平淡,就不可避免。由此可见,真正的反讽作家应该跳出自我看自我,跳出时代看时代,跳出人类看人类,他就像上帝一样,总保持着一种超然的“神祇式的平静”:站在一旁,默默旁观,用心倾听,或躲在一边,悄悄窥视,仔细铭记,以能有效而准确地把握其反讽对象——自我与自我所处的时代,以及整个人类——的盲目自信而又毫不自知。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作家,“这一点很有趣:上帝被想象成戏剧家或小说家,反过来,作家又被想象成上帝”[1]56。这样,伟大的作家宛如上帝在天上俯视人间一样,其对自我与自我所处的时代以及整个人类的凝视,都是超然冷静的反讽式凝视。因为他拥有了上帝那样宏阔的宇宙精神和浩大的宇宙意识,所以总能以上帝那样宏阔而浩大的眼光审视自我、时代与人类,故而总能洞悉自我、时代与人类因盲目自信沉溺于人生表象而无所觉察的诸多事实真相:在人们盲目乐观、自以为是、毫不自知的时候,他却目光如炬、洞察秋毫、了然于胸,因而往往忍俊不禁,常常会发出米兰·昆德拉所说的“上帝的笑声”。所以,真正的反讽性作品,就应该始终充盈着这种洞悉一切真相的“上帝的笑声”,因而总能让人发现自我、时代以及人类的盲目自信而毫不自知,从而总能将人引向无限的宇宙境界——审美的极境空间。
[1] D·C·米克.论反讽[M].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
[2] MH Abrams.AGlossaryofLiteraryTerm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Thomson Learning, 2004.
[3] 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 Wayne C Booth.TheRhetoricofFic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5] 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6]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 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8] 朱兵.天人之道的张力空间[J].燕山大学学报,2010,(3).
[9] 朱兵.失败的小说:审美张力空间的匮乏[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6).
[10] Wallace Martin.RecentTheoriesofNarrativ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