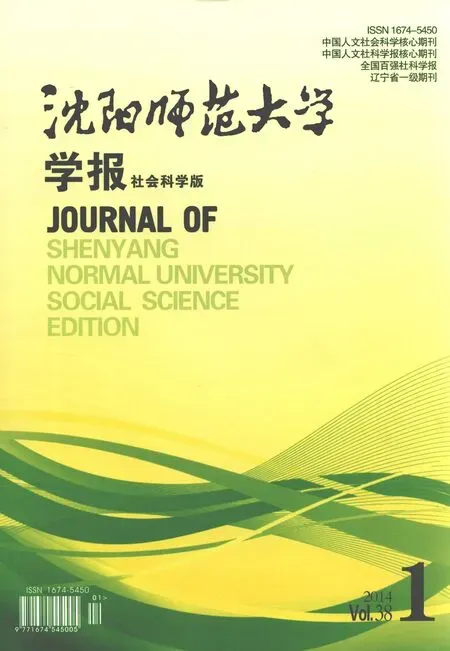论体系因素对联盟稳定的影响
鲁大东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89)
论体系因素对联盟稳定的影响
鲁大东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89)
在新现实主义者的论断中,两极体系意味着同盟的稳定,而多极体系则作为不利于同盟稳定的因素与之对立。然而在一定形态下的多极体系也包含有两极体系所具有的可促进联盟稳定的变量,而两极体系也存在被新现实主义者视为多极体系才拥有的不利于同盟稳定的因素。文章将借助格伦·施耐德的联盟困境概念定义联盟稳定,并通过神圣同盟与冷战中两大联盟体系的比较重新审视两极及多极体系对于联盟稳定的利弊影响。
同盟困境;联盟理论;联盟稳定;神圣同盟;冷战
缔造同盟是国家经常践行的一种维护自身安全的手段。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扩大和加强同盟被沃尔茨描述为外部均衡势力的主要方式[1]。鉴于此,同盟研究一直是现实主义研究的重点。文章将考查体系因素对联盟稳定的影响并试图解释多极体系是否完全无益于联盟的稳定以及两极体系是否有如新现实主义者所言那般利于同盟平稳运行。在美国权力优势逐渐下降,世界渐为多极化的今天,了解多极体系对于联盟稳定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依据本文研究框架,我们可将联盟的稳定定义为同盟安全困境较为温和,两种风险大致平衡,联盟的结构没有重大变化,相对完好。没有一个盟国退出同盟实际并不能表明联盟稳定,因为同盟有可能是在抛弃与牵连两种风险极不平衡的情况下运行的。由于联盟关系承受强烈的同盟困境的考验,同盟实际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将同盟困境与同盟结构都纳入稳定的定义之中是一种更为合适的做法。
一、细致划分的多极体系与联盟稳定—体系层面的能力分布
格伦·施耐德在其关于联盟的著作《联盟政治》阐述了多极体系下联盟运行的不稳定性,例如多极体系会促成盟友之间更多元化的利益,结盟的灵活性造成更多的盟友背叛情况发生,较高的相互依赖造成牵连(entrapment)的风险增高[6]。然而施耐德的观点是建立在对1879-1914年间联盟体系的研究之上的。此外,这些分析中还包含有一些需要被注意的逻辑问题。施耐德所指的多极的弊端:利益的多元化,结盟的灵活性与较高的相互依赖中前两个都会使抛弃的风险增高,后一个特性令牵连风险增高。虽然利益多元是多极体系普遍具有的特性,但是灵活结盟与高度相互依存同时存在这一点具有逻辑悖论,高度的相互依存已经否定了结盟灵活的可能性。因此多极体系应被更细致地划分为三种。前两种分别是具有较高灵活结盟特性及较低相互依赖的多极,以及盟国之间具有高度依赖性,较低结盟灵活性的多极。前者以1648-1789年的欧洲为典型,后者以1879-1914的欧洲体系为代表。而1814-1853年的欧洲体系是一种类似两者特点混合的产物,即第三种类型:具有一定的结盟灵活性,盟国之间又保持一定程度但并非很高的相互依赖。在这里可将第三种类型的多极体系定义为稳定型多极。一定程度的结盟灵活性有效地避免了牵连的发生风险,而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又降低了抛弃的风险。
有利的结构中的能力分布是温和型多极具有这种特点的重要原因。1815-1853年的国际体系较之前的国际体系最重要的变化是很多大国的相对衰落,西班牙和瑞典这些在17、18世纪初仍可叱咤欧陆的国家,其实力比18世纪之前大为弱化,荷兰的地位也远不如前。同时,德意志地区的邦国数量也进一步减少,并维持在德意志邦联的范围之内。这使得五大国的结盟选择较之前要降低很多。但总的来说,每个大国仍旧保有一定的选择余地。而在1870年代后德国的统一及强盛和奥匈帝国的进一步衰落使大国的结盟选择过少。
利益多元化是多极体系的一个弊端,但通过其他途径可减轻其影响程度。这一时期的体系内,东、西欧之间保持了实力安排恰到好处的缓冲区即德意志邦联的存在,这使得本地区既不会成为其他大国的角力场,也不会被视为其他大国的威胁。“东方问题”是19世纪国际体系中最为突出的大国争夺权力的舞台。然而在1815-1853年这段时间之内,土耳其对巴尔干半岛的各公国尚有一定的掌控力,因此没有产生足够的权力真空使矛盾不可调和。世界范围内,殖民地的分配被重新调整,加之英国海军的独霸地位,殖民地问题上的多元利益也无法通过武力实现。因此同盟中即使存在多元利益,也因缺乏权力真空使其对联盟稳定的影响大为降低。
多极体系下,各盟国彼此实力差距更小,很多利益与目标需要通过联合的手段才能实现。但一定的结盟灵活性使得这种依赖度保持在适当的程度。大国拥有次优的替代选项,可以有效避免牵连风险的增高,同时替代选项因不及现有同盟有利于自身利益,而且建立要花费更高的成本来达成,抛弃的风险得以被控制。例如神圣同盟,普、奥虽然有仅保持两者联盟的选项,同时英国也是一个虽然可能但是较难争取过来的盟友,但是与俄国的联盟无疑极大增加他们应对法国革命挑战的实力并且通过结盟也可以限制俄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同时俄国虽然有与法国结盟的选项,然而尤其是在1830年革命之后,与东方另外两个君主国的联盟始终是基准国策。1833年签订的柏林协定规定三国合力保障欧洲的旧秩序,并且遇有第四国卷入干涉时共同应对,矛头直指法国[7]。
有赖于此,这一时期内复杂的东方问题对神圣同盟稳定的不利影响被抑制住。1822年初,梅特涅的游说成功地使俄国放弃了干涉希腊革命的企图。俄国在1828年的俄土战争中没有因为奥地利的反对而与盟国决裂,因为这样会使俄国单独面对日后法国以及革命的威胁,奥地利虽因为实力上的缺陷无法阻止盟友的行动但因为利益差异和替代选择的存在也不会被牵连其中。此外,1832年到1833年的近东危机中,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缔结温凯尔·斯凯莱西条约(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引起英法强烈反对之时,该举动因未与奥地利产生严重利益冲突而没有引起神圣同盟内部的争论。1833年,俄、奥签订蒙申格莱茨条约(Treaty of Munchengratz),进一步明确要求双方在近东和波兰事务中彼此合作,并且在1840-1841年的近东危机中联手与英国合力阻止现状改变[8]。此时期,俄国在与土耳其签订条约之时都会注意避免或减少损害奥地利之利益,以保全同盟的存在,降低抛弃的风险[9]。这是神圣同盟可以存在长达近33年的重要基础,其存在期间联盟的安全困境一直维持在稳定的范围内。
新现实主义者指出的多极体系的缺陷也存在于两极体系之中。两极中并非没有利益多元化问题,而且其程度也比较严重。在第二次中东战争及第二次柏林危机中,西方盟国都显示出了严重的利益分歧。尤其是第二次中东战争和殖民地独立问题上,英法与美国分歧严重,这为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埋下了隐患。西德在发展核武器问题上也与美国存在分歧,最后是阿登纳的下台才彻底解决这一问题[10]。而社会主义阵营里,中、苏和南斯拉夫、苏联的利益分歧都极为严重,最后造成联盟关系破裂的事实。苏联则是始终依靠高压政策才压制了东欧一些国家与它的政治分歧。
归根结底,两极相对温和型多极最主要优势在于沃尔茨所说的超级大国对于同盟的控制力和讨价还价的能力。但是多极体系也有可能形成有利的联盟内部能力分布,从而使联盟中较强国家具有一定的讨价还价能力的优势。
二、相对权力优势与控制力——联盟内部的能力分布
联盟内部的能力分布对联盟的管理和稳定同样具有重要影响。盟国所拥有的相对权力优势的多寡是依赖性的重要决定因素,相对权力越大,对盟友的依赖性就越小。格伦·施耐德通过对讨价还价的权力的分析,进一步解释了该变量对联盟管理的作用。施耐德将联盟中一国的讨价还价权力的影响因素归结为三点:即利益、承诺和依赖性。该国在讨价还价所涉及问题上的利益越多,讨价还价的权力越大。该国对盟国的承诺越多,讨价还价的权力越小。而依赖性则与讨价还价的权力大小也成反比。当这三者水平相当时,妥协是最可能的结果[11]。在联盟双方在该问题上都有着重要的利益关切且承诺程度相当时,依赖性是讨价还价权力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前两者相当的情况经常发生在危机中,因此依赖性这一变量与讨价还价权力的大小具有强因果关系。
依赖趋向对等的情况会使联盟决策更多倾向于集体讨论而非压迫。妥协与协商是1815-1853年间同盟内部处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这种方式也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缺陷:成功的前提是有一定的谈判基础,即在会议开始之前利益冲突的攸关方已经先取得某种解决问题的共识。因此这种妥协与协商在处理涉及盟国直接冲突(即并非是某一其他地区的危机)时很难奏效①关于会议外交的问题与终结可见RoyBridge,“Allied Diplomacyin Peacetime:the Failure of the Congress‘System’,1815-1823”.载于 Alan Sked ed,Europe’s Balance of Power1815-1848,London:Macmillan Press,1979,pp34-53.。如上所述,妥协会出现在盟国利益、承诺、依赖三者相当的情况之下,达成难度较大。
因此仅有协商与妥协作为管理联盟的主要手段往往不够,一定程度的强制具有必要性。控制力上的优势即讨价还价权力的非对等性在多极体系下也有存在的可能,有利的同盟内部能力分布可以促成这种情况的出现。多极并不意味着实力在大国间的完全平均的分配。在温和型多极的体系内五大国实力的分配是不均等的。英、俄的实力要超出其他三个大国一定程度。英国依靠强大的海权和殖民帝国,而俄国仰赖其最庞大的欧洲陆上军事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二者都拥有极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享受较其他三国低的多的易受攻击性。普、奥实力较其他几国更弱。奥地利面临诸多的内部问题和财政困扰,而普鲁士则拥有狭长且难以防御的边境以及资源的稀缺。两者也是受拿破仑战争影响最深的国家,有鉴于此,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认为二者的地位甚至不如战前①。这使得神圣同盟中,俄国拥有可以调解同盟内部争端与纠纷的能力,例如,1850年7月普鲁士从丹麦撤军和11月的奥尔缪茨协定的达成,俄国就利用了自己的相对实力的优势使普鲁士放弃了有违“联盟精神”的行动并解决了普、奥的严重纠纷。同时这种优势又赋予俄国在近东的一定的行动自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侵犯盟国的利益而不引起盟友的强烈反对,如1828年的俄土战争和1832-1833年的近东危机。因为普、奥则更为依靠这一联盟,他们与俄国结盟所带来安全收益远大于可能的替代联盟。另一方面,在多极下这种优势弱于两极体系中联盟领袖所拥有的巨大的相对权力优势。俄国仍然需要两国的支持来维持欧洲的政治现状。如前所述,俄国在外交中需要考虑与盟国的利益差异并避免增高联盟安全困境烈度,协商与妥协需要经常使用。
压迫的手段在两极联盟中出现的次数更多。因为依赖的较大的不对等性,两极中联盟领袖可借助巨大的讨价还价权力优势进行压迫式的同盟管理。但在冷战两大阵营中也同时存在着压迫程度的差异。霍尔斯蒂依据联盟结构的不同将联盟分为两种:整体式的联盟(Monolithic Alliance) 和 多 元 式 的 联 盟(Pluralistic Alliance)[12]。前者与后者的差别在于其联盟决策权更为集中(即他国缺乏讨价还价的权力),以及前者的联盟涉及更广的议题(即不单纯局限于国际安全)。这意味着联盟的主导国在整体式的联盟中更为专断,管理范围及事物更多。盟国的讨价还价极少奏效并且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造成这种差别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同盟内部的相对实力的分布状态。东方阵营在形式上更接近整体式的同盟,压迫的手段更为经常地被使用。
单纯采用压制的管理方式存在诸多隐患,最为直接和严重的结果就是盟友退出联盟。当所争议问题涉及被较弱盟国视为是最重要的利益,且该国较联盟中其他国家拥有更少的对联盟领袖的依赖度时,退出联盟的情况就可能会发生。中国和法国就分别在这种情况下退出了中苏同盟和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中苏之间的争论问题涉及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即独立自主。而美法之间则涉及殖民地问题和核问题。南斯拉夫也由于不满苏联的管理方式而在冷战伊始就与苏联决裂。另一方面,这种控制力在超级大国与“外围”国家,如伊拉克、埃及等国的联盟中也没有起到严格控制盟友的作用,联盟的崩溃与较高的牵连和抛弃的风险并没有被避免,盟友的转换阵营及联盟解散时有发生。与在欧洲地区表现不同的是,两极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在与这些次要国家建立联盟时却并没有显示出强大的控制力。
三、体系对联盟次困境的影响
联盟的稳定程度不仅受到内部因素的操控,也要受到联盟——对手关系的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的极为紧密的关系类似于“一个硬币的两面”[13]。因此,施耐德认为联盟内部很多试图平衡联盟困境的手段会产生副效应。例如,试图通过加强对盟友的支持而减轻抛弃风险的行为会对缓和联盟与对手之间关系的做法产生不利影响。同样,试图减少支持,限制盟友以弱化牵连风险的行为会使对手感到同盟内部出现分裂并采取强势立场。这两种情况是由副效应所创造出的从属于联盟困境的次困境(Subdilemmas):“支持-缓和”困境(support versus conciliate dilemma)和“威慑-限制”困境 (deter versus restrain dilemma)。这些困境在危机之中会更为严重。
施耐德强调多极体系中存在的会强化这些次困境进而影响联盟稳定的因素在两极体系中较少出现。特别是“支持-缓和”这一困境是多极体系的特点。原因是多极中盟友的忠诚度较不可靠,因此采取缓和同盟间关系的做法会加剧同盟内部的抛弃风险,掣肘颇多。而两极体系中因为缺乏代替联盟,因此忠诚问题几乎没有影响。同样,肯尼思·沃尔茨认为盟国除了忠诚以外“几乎别无选择”,而即使变节,联盟领袖也可以经受住这种损失,因此联盟领袖大可放心地执行自己的战略而无需考虑盟友的意见。
虽然有利的联盟内部实力分配可以减轻次困境的影响,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次困境的消失,次困境并不是多极体系的专利。两极体系之中,联盟领袖实际上仍然要考虑变节问题,其盟国也并非没有选择。通过对外交史的考察,两极体系下的联盟仍受次困境的影响,两极联盟中的联盟领袖并不能如沃尔茨所言为所欲为地执行自己的政策。北约建立以来,美国始终在执行政策时总会遇到来自盟友的阻力。1950年后的杜鲁门政府以及之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都极为重视同盟团结的重要性,对苏采取强硬立场以团结西方联盟和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盟[14]。在将西德纳入北约的过程中,美国就面临了来自法国的极为强大的反对意见,并致使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EDC)失败。而柏林危机后期,为了与苏联达成协议,安抚苏联对西德可能拥有核武器而产生的不安全感,肯尼迪政府对阿登纳政府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这使阿登纳拉近了与法国的距离,疏离美国并严重威胁到联盟团结。最终阿登纳的下台才使问题得以彻底解决[15]。虽然美国利用自己强大的相对实力优势和西德对于北约的依赖成功处理了这次危机,但是在此之前因为担忧对盟国区别对待而造成西德不满以及试图防止其他盟国拥有核武刺激苏联,美国采取了同时限制英、法、西德三国发展自身核武器的态度。这与1963年初美国再次拒绝修正多边核力量计划共同促成了对北约依赖小于西德的法国彻底断绝在核武方面与美国合作的意愿,并在1966年退出了军事一体化组织。
东方阵营同样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随着替代选项的增多及联盟领袖影响力的下降,同盟的解体和抛弃在这一阵营更为常见。苏联试图避免激化与西方联盟关系而减少对阿拉伯国家支持的做法直接导致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后苏埃联盟的解体。赫鲁晓夫上台后试图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行为也是中苏同盟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两极下一些不满的盟国并不是没有选择。苏联在东亚、巴尔干半岛和北非最重要,实力最强的三个盟国,南斯拉夫、中国和埃及均摆脱了与苏联的联盟关系。西方联盟中,法国自身脱离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而阿登纳也曾尝试与法国建立紧密的联系。一些国家还选择与敌对的联盟保持密切关系或加入敌对阵营,如中国在70、80年代就与美国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而埃及则与美国实质上结成了联盟。因此盟国忠诚与否也是两极体系下联盟领袖需要考虑的问题。关于即使盟国抛弃同盟,超级大国仍能承受这种损失并继续执行其政策这一点也需要更细致的考察。法国脱离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或许是美国可以承受的,但是法国和西德同时退出北约必然会对美国的遏制战略产生重大且难于弥补的损失。很难想象美国在丧失了在欧洲大陆的前沿阵地之后如何寻找替代盟国。苏联也同样难以承受其欧洲盟国的类似行为。不利影响不亚于多极体下的欧洲大国失去盟友。苏联在失去埃及和中国之后对于这两个地区的影响力也大为降低。而美国亦需通过寻找新的盟友来弥补失去伊朗的损失。
两极体系下还存在另外一种施耐德所提到的次困境,这就是威慑-支持困境。这根源于两极体系下同样存在的利益多样性及威慑会造成的牵连风险。当超级大国在危机中试图威慑对手,而这一事件或危机并非涉及其他盟国切身利益时,会遇到次要盟国的反对。柏林危机中,当美国试图使用核力量优势威慑苏联时,明确地遇到了法国和英国的反对。英、法都不想因为德国问题而被牵连进核大战之中,英国甚至背离了盟友单独与苏联进行了接触。这为美国执行自己的战略带来很大困难[16]。冷战中,英、法始终都存有这种担忧。
两极体系下的联盟虽然也面临次困境,但其有利的联盟内部能力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一问题。然而,温和型多极体系下的联盟实际上也可以通过这一方式改善次困境的影响。多极联盟中的背叛问题也并不是无处不在。沃尔茨和施耐德的论断是建立在多极体系下同盟内部实力分配平均的基础之上的。如前所述,多极体系下联盟内部的能力分配也可能存在差异。温和型多极就具有这样的特征。此时期的五大国实力分配较之前以及之后都更不平衡。神圣同盟之中,俄国高出另外两国的实力使普、奥更为依赖联盟,而且获益良多。代替同盟对于这两国来说缺乏足够诱惑力。这使得俄国在1820年代后期试图改善与法国关系并在希腊危机中开展合作时不必过分担忧神圣同盟的稳固问题。
结语
两极体系下的联盟可以凭借有利的能力分布提升联盟的稳定性,降低联盟安全困境。但是如果细致地辨别各种不同的多极体系也会发现温和型多极这种多极体系可形成有利于同盟稳定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有利的能力分配形成的对利益多样化的和结盟灵活性的限制;合适的大国数量使诸国拥有次优的代替联盟,形成对依赖程度的限制;不均等的大国实力分配造成的非均衡的联盟内部能力分配,由此产生联盟中依赖的不均等及控制力差异和次困境的缓和。同时,两极中的联盟也存在其他多极中的联盟所面临的问题。超级大国的盟国并非没有选择而只能留存于联盟之中。同时两极联盟也受到次困境和一定程度利益多样化的影响。因此单一地认为多极之下的联盟一定不稳定或两极之下的联盟牢不可破的观点都是片面的。多极体系形成有利于联盟稳定的条件更为复杂,但这不等于在任何条件下两极体系的同盟都要比多极体系牢固,温和型多极也同样拥有很多有利于联盟稳定的特点,值得受到更多关注。
[1]肯尼斯·沃尔茨.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125.
[2]Thomas J.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Chain Gangsand Passed Bucks: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2(Spring,1990),pp.137-168;StephanWalt,“Testing 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2(Spring,1988),pp.275-316,“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9,No.4(Spring,1985),pp.3-43。沃尔特.联盟的起源[M].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
[4]Glenn H.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World Politics,Vol.36,No.4(Jul.,1984):461-495.
[5]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180-186,307-308.
[6]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181-183,184,307-308.
[7]F.R.Bridge and Roger Bullen,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uropean States System 1814-1914(Second Edtion)[M].Edinburgh:Pearson 2005:92-93.
[8]Matthew Anderson,“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1821-41”,p91-92载 于 Alan Sked ed,Europe’s Balance of Power 1815-1848[M].London:Macmillan Press,1979:79-97.
[9]F.R.Bridge and Roger Bullen,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uropean States System 1814-1914(Second Edtion)[M].Edinburgh:Pearson,2005:56,87,92.
[10]Marc Trachtenberg,AConstructed Peac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370-379.
[11]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175-176.
[12]Ole R.Holsti,P.Terrence Hopmann and John D.Sullivan,Unity and dis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s:comparative studies,New York:JohnWiley&Sons,Inc.,1973:166-169.
[13]Glenn H.Snyder,Alliance Politics[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192.
[14]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107,114-115,140-143.
[15]Marc Trachtenberg,AConstructed Peac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302-314,328-329,340-349,355-357,367-379.
[16]Henry A.Kissinger,Diplomacy[M].New York:Simon&Schuster Paperbacks,1994:598-599.
D813.1
A
1674-5450(2014)01-0054-04
2013-10-03
鲁大东,男,辽宁东港人,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杨抱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