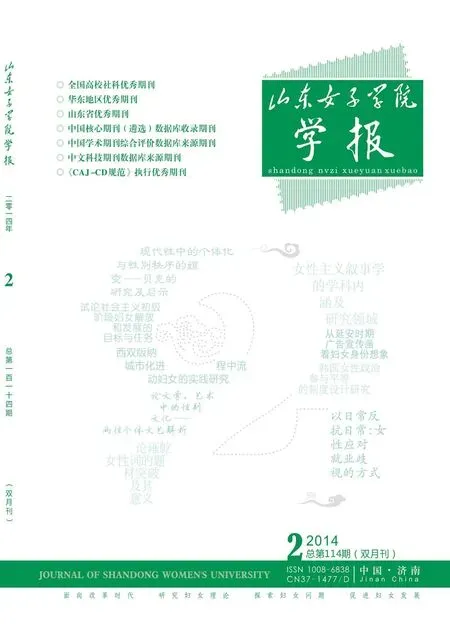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学科内涵及研究领域
杨永忠,周 庆
(云南财经大学,云南 昆明 650221;云南民族大学,云南 昆明 650031)
一、引言
自本世纪初以来,国内学者就开始关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积极从学科发展高度探讨叙事学与女性主义的关系,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建构进行了有益的思考和探索,并由此产生了一批具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如申丹(2004)[1]、唐伟胜(2007)[2]、郑大群(2007)[3]、杨永忠、周庆(2012)[4]等。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女性学研究者对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个学科的了解较为模糊,致使目前国内对于这个新生事物缺乏必要的理解和关注。国内学者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基本概念、研究范围和学科属性等问题都存在一定的误区和偏见,甚至有研究者提出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之说,或者将女性主义叙事学等同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因此,要从根本上厘清认识上的误区,就必须梳理女性主义叙事学从学科创立、成长到成熟发展的历史轨迹,分析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学科定位、学科内涵和研究领域,探讨女性主义叙事学进一步发展所需的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
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历史渊源
女性主义叙事学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美国,其时经典叙事学界和女性主义学界都遇到了一系列涉及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女性主义叙事学以人本主义和实用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以现实主义和多元主义为其社会学基础,以结构主义为其叙事学基础,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性别平等思想为其女性学基础。无论其动因如何,女性主义叙事学都是以问题为导向,以女性主义意识为出发点,核心是研究叙事中的女性意识,目的是揭示文本的叙事形式、叙事特征和叙事结构与性别主体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女性主义叙事学旨在探察女性叙事权威和女性叙事者身份及女性主体意识的构建方式,评价文本生成者或叙事者和文本阐释者的性别角色与叙事形式、叙事特征和叙事结构的互动关系[4][5]。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者是一批关注并研究叙事中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学者,代表人物有兰瑟(Lanser)[6][7][8]、普林斯(Prince)[9]、沃霍尔(Warhol)[10]、梅齐(Mezei)[11]等。其中最杰出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者和实践者为兰瑟。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学科就是她提出来的。她于1981年出版的《叙事行为:散文化小说的视角》[6],率先探讨了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986年发表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7],首次使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在这篇具有宣言性质的论文中,兰瑟提出,经典叙事学都是以男性作者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因此,如果要对女性作家的文本和女性读者的阐释经验加以考虑,就必须修改叙事学甚至整个文学历史[2]。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在美国出版的沃霍尔的《性别化的干预》[10]和兰瑟的《虚构的权威》[8],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目标、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做了进一步阐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批评实践。之后,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成果纷纷在《叙事》《文体》《PMLA》等杂志上发表,标志着女性主义叙事学已成为叙事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1]。
当然,这里所说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还是比较笼统的概念。事实上,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几大各具特色的学派,主要有美国学派、英国学派和法国学派。
以兰瑟为代表的美国学派具有研究领域宽广而多样的特点。它以经典叙事学的知识为基础,借鉴并采用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声音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的作用,将对叙事声音的技术探讨与女性主义的政治探讨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研究叙事声音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内涵,考察文本生成者或叙事者的特定叙事声音选择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内在联系[1],揭示女性叙事声音赖以生成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学土壤[2],探察叙事过程中女性权威、女性气质、女性身体、女性生活等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方式和过程[3]。就方法论而言,美国女性主义叙事学采用的是文本分析模式,注重对叙事方式的研究[12]。
以劳拉·马尔维(Laura Mulvey)为代表的英国学派重视叙事学的基础地位和核心作用,将精神分析方法运用于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其认为,电影的父权制与传统电影所惯用的叙事手法之间存在联系。在整个电影叙事过程中,女性始终是叙事的客体,处于被审美的地位,这无疑是父权制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在电影叙事中的再现。与旨在检视电视作为机制而发挥功用的方式的美国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不同,马尔维的叙事研究力图揭示研究对象的性别权力结构[3]。可以说,英国女性主义叙事学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强调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女性所遭受的社会不平等[12]。
以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的“女性写作”(écriture feminine)、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女性主义符号学”为代表的法国学派采用的是精神分析学模式,探索女性文本、女性气质、女性书写与女性解放,强调女性的精神和性压抑,反抗西方白人历史中心论、男性中心论和逻格斯主义中心论。通过对语言结构的分析,质疑真实与虚构间的所谓必然联系,进而揭示文本中蕴含的组合与分裂[12]。法国女性主义叙事学将性别问题等同于语言问题,注重语言或写作上的革命,强调对女性语言的塑造[1]。
三、女性主义叙事学学科定位的主要观点及评述
目前,学界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学科定位有以下三种观点:(1)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女性学与叙事学两个学科结缘的交界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2)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女性学、叙事学、民族学、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相互融合的多界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3)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以叙事学为主导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第一种观点是将女性学和叙事学直接结合在一起,主张凡是涉及叙事学理论与叙事行为分析的女性学研究与实践,或者凡是涉及女性学理论与女性行为分析的叙事学研究与实践,都属于女性主义叙事学。这种观点涉及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核心课题,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然而,这种交界学科论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混淆了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叙事学女性主义的界限。我们既可以说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是叙事行为中的女性主义问题,同样也可以说研究的是女性的叙事行为问题。其落脚点可以是叙事,也可是女性主义。显然,这样的界定具有模棱两可性,因而不可取。
第二种观点排除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双学科性质,强调女性主义叙事学多学科相交的属性。这种观点同样涉及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核心课题,因而具有很大的学科覆盖面。但是,这种多界学科论的问题在于其陷入了多界即无界的悖论[13],导致女性主义叙事学学科界限不明,学科目标不清,研究领域驳杂,研究方法呈现随机性特征。结果是,女性主义叙事学像任何一个与其相关的学科,但又什么学科都不像,而且还容易沦为“自由开放的教堂”(broad church)或无所不纳的“垃圾场”(dustbin category)[14][15][16]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因此,这样的学科界定同样不可取。
第三种观点将女性主义叙事学等同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甚至认为它是文学批评的一个分支。虽然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政治目标相同,但是二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上仍然差异显著[1]。因此,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可等同,前者更不可成为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女性主义叙事学学科的独立地位与核心内涵
本文关于女性主义叙事学学科定位的观点是: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女性主义与叙事学的整合,具有“超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y)特征。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是基于实践性研究需要,通过博采众家之长,从整体上把握研究主题。它并不是从两个或多个学科的认识论出发,而是以某一学科(如叙事学)作为学科起点,利用相关学科的方法论和分析工具(如文本阐释、叙事分析、话语分析)开展调查和研究,将一种理论逻辑在另一种理论逻辑中加以丰富和扩展[17-18]。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核心是女性的叙事权利和叙事策略,它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作为叙事者和被叙事者的女性意识问题。因而,女性主义叙事学始终是以女性意识问题为旨归,即使是研究叙事问题,也必须以女性的权利和策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女性主义叙事学形式上是研究叙事问题,实质上是研究女性的权利、策略、生存和发展问题,或者说,是研究女性的现实生存状态和发展问题。
女性主义叙事学源于女性主义和叙事学,因此,其学科基础就是女性主义和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边界是与其结缘学科的相关课题,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课题包括三大类:(1)基于女性主义的叙事权利和叙事策略问题;(2)叙事权利和叙事策略与性别的关系问题;(3)女性在叙事文本生成和解读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
显然,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一门具有明确研究课题的独立学科,具有鲜明的学科目标和学科界限。诚然,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其他学科结缘的特质决定了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往往带有多学科的色彩,呈现多样性的特征,但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并不表明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一门既无目标又无核心、既无边界又无内涵、既无理论又无实践的附庸学科。虽然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问题极其繁杂,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呈现多元性特征,但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与女性密切相关的叙事权利和叙事策略问题。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范畴及其与各相关学科结缘的特征和性质决定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领域的广度和研究层次的深度。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者在研究工作中,针对不同的叙事文本,会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既有宏观视角,亦有微观处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然而,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抑或是综观,其研究的出发点、立足点和聚焦点,都是女性的叙事权利和叙事策略以及女性在文本与现实中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从根本上说,女性主义叙事学始终关注作为现实社会延伸的叙事文本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权利的问题,也就是女性在非现实环境中的社会发展问题。
如前所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哲学、语言学、民族学、文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这种兼容多学科的研究路径无疑为女性主义叙事学开创新的学科范式和研究方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旨在解决女性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反过来,现实问题的解决则可以促进理论的深化和研究方法的提升。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理论问题或增加学术知识,更是为了解决女性在现实社会以及作为现实社会延伸的文本和超文本这类虚拟现实中的权利和生存状态等这样一些实际问题。实际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理论指导,而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同样离不开来自实践的直接经验反馈。可以说,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基于并源于女性生存现实问题,其终极目标是改变女性生存现实状态,探寻女性作为一个社会主体(包括行为主体、叙事主体、审美主体)的发展可行性问题。作为一种偏重问题研究的学科类型,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五、基于女性主义叙事学学科内涵的研究领域及课题展望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起点是叙事学中的女性性别话语问题,尤其是关注女性作为叙事者和被叙事者的权利和策略问题,学科领域已经突破叙事学本身,推广至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哲学等学科,并试图从这些学科中探寻问题的解决途径。女性主义叙事学以性别作为切入点,通过融合经典叙事学中的叙事声音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感性认识和理性分析,分析女性文本生成者或叙事者的叙事策略及构建其叙事权威的基础。诚然,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和原则借鉴自经典叙事学,但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是其研究的立足点[19][20],其突出的“批评客观性”特征显而易见[3][4]。
沃霍尔指出,女性主义叙事学就是对性别建构语境中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的研究,换言之,通过对女性文本的“外科手术式”解读,发现叙事形式、叙事特征、叙事结构、叙事策略与性别意识之间的互动关系[4]。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文本的结构、声音、视角、时间和内涵,尤其关注叙事特征、叙事形式、叙事策略、叙事结构与文本生成者或叙事者的性别和文本阐释者的性别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叙事结构、叙事形式、叙事特征、叙事策略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察文本生成者或叙事者和文本阐释者的性别差异与叙事结构等因素差异之间的本质联系[2][19][20]。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研究女性的叙事权利和叙事策略以及与叙事相关的女性问题的学科,它的学科内涵决定了女性叙事必然成为其主要研究领域。女性主义叙事学所涉及的领域包括:(1)女性叙事的权利和策略;(2)女性叙事与女性发展;(3)女性叙事与女性身份认同;(4)女性叙事与女性权利和女性主体意识。
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包括:(1)叙事系统与叙事多样模态性的关系;(2)叙事多样性发展与女性作为叙事主体和叙事客体的关系;(3)叙事过程中的女性话语分析与女性性别主体的构建;(4)女性叙事者和被叙事者与男性叙事者和被叙事者的相互关系和地位;(5)女性叙事者的叙事能力的评估。
这些研究领域及课题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例如:叙事系统与叙事多样模态性的关系涉及叙事声音模式、叙事者的显性/隐性特征和身份、叙事的层级与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叙事多样性发展与女性作为叙事主体和叙事客体的关系涉及女性作为叙事主体和叙事客体的叙事模式、叙事语法与叙事结构等问题;叙事过程中的女性话语分析与女性性别主体的构建涉及女性叙事话语模式的呈现方式、女性叙事主体意识及其构建过程等问题;女性叙事者和女性被叙事者与男性叙事者与被叙事者的相互关系和地位涉及女性与男性分别作为叙事者和被叙事者的身份与地位,以及二者在叙事过程中的互动与影响等问题;女性叙事者的叙事能力的评估涉及女性叙事者的能力评价标准和评估体系的构建等问题。
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在国内已经有所开展,但是与国外相比,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国内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都极为薄弱。为此,我们对新时期我国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课题提出以下展望:(1)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女性学研究和女性学人才培养国际化进程;(2)我国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开展及其与国际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接轨;(3)我国女性主义学者的叙事学意识、叙事学知识和叙事能力框架构建等;(4)我国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实践及其与我国女性社会现实生存状态的联系;(5)叙事学研究对我国女性的社会权利的获取、社会身份的确立等方面的指导。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可以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并为其提供新思想、新观念,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当代社会实际出发,在理论创新中突出原创性,努力实现本土化。中国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应当具有强烈的学科意识,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为出发点,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拓展视野,改进研究思路,实现中国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法和对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研究方法相一致,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特色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才能合理地产生并健康地发展,进而为中国妇女解放的事业提供切实可行的思想指导[21]。中国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应当具有如同黑格尔哲学那样“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理论探讨方能深入、完善[22],中国本土的叙事学理论才能与国外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实现融合,进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苏珊·兰瑟式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23]。
六、结语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一门融女性学和叙事学为一体、与多学科结缘的独立学科,具有明确的研究主体、研究课题和研究范式。其以女性为本,立足于女性的全面发展,基于女性的叙事权利和叙事策略,以问题为导向,关注具体问题和具体过程,以跨学科的视角,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面对各种叙事实例,解决女性的叙事权利和叙事策略问题以及叙事的性别取向问题。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视域来看,叙事既是权利,也是资源;女性既是叙事的主体,也是叙事的客体,具有二重性特征。
女性主义叙事学重视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其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学术知识或社会知识,而是为了研究和解决叙事实践中女性某个方面的实际问题。由于研究和实践具有双向性特征,因此,叙事实践往往也可以促进科学研究。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中,研究的主题不是研究者大脑中的产物,研究课题也不是空对空模式。女性主叙事学的研究课题源于研究者的叙事实践分析,是基于社会现实的理论研究,因而具有现实意义[13]。
与其他学科的紧密联系无疑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核心特征,着手解决女性叙事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也从其他相关学科寻求解决问题的指导理论和具体方法,但是女性主义叙事学尚未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统一协调的知识体系。虽然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者具有共同的研究目标和明确的社会责任,但是,就整体而言,女性主义叙事学仍旧缺乏明确的行动路线,尚未在宏观、微观或综观层面就女性与叙事、女性与社会、女性与权利等关键课题及其关系建立一个自成体系、完全自洽的整体和学科范式。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生态学理论研究成果可以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研究范式和新的学科增长点。生态学理论主张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以生态平衡、均衡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3],这样的学科理念与女性主义叙事学集经验、体验、立场和文本意义于知识论建构之中的整体观正好契合[4][24]。
因此,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中,我们应当将女性和男性在叙事过程中的身份、地位、作用和特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对各种复杂因素和复杂情境加以分析,既要基于叙事文本和叙事过程本身,又要超越叙事文本和叙事过程本身,以整体观的视野解决与女性叙事相关的各种问题,进而提出女性摆脱现实困境的对策,并指明女性未来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J].北京大学学报,2004,(1):136-146.
[2] 唐伟胜. 性别、身份与叙事话语: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流研究方法[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5):73-80.
[3] 郑大群.女性主义美国学派——女性主义叙事学简论[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50-54.
[4] 杨永忠,周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目标、原则与方法[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4):5-10;妇女研究(人大复印资料),2012,(6):10-15.
[5] 张继英.《使女的故事》的女性主义叙事技巧[J].文学教育,2009,(10):92-94.
[6] Lanser, S. S.TheNarrativeAct:PointofViewinProseFiction[M].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7] Lanser, S.TowardsaFeministNarratology[J]. Style, 1986,(3):341-363.
[8] Lanser, S. S.FictionsofAuthority:WomenWritersandNarrativeVoice[M].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9] Prince, G.OnNarratology:Criteria,Corpus,Context[J].Dialogue, 1995,(3):73-84.
[10] Warhol, Robyn R.GenderedInterventions:NarrativeDiscourseIntheVictorianNovel[M].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9.
[11] Mezei, K.AmbiguousDiscourse:FeministNarratologyandBritishWomenWriters[C].Chapel Hill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6.
[12] 马红英.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多元格局检视[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4):59-62.
[13] 梅德明.教育语言学的学科内涵及研究领域[J].当代外语研究,2012,(11):32-37.
[14] D. Cameron.RepresentingSociolinguistics?[J].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1998,(2):421-431.
[15] 杨永林,张彩霞.社会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跨学科视野下的对比研究[J].现代外语,2007,(3):239-250.
[16] 杨永忠,周庆.女性学的学科地位及其发展[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1,(4):69-74.
[17] Fairclough, N.Discourse,SocialTheory,andSocialResearch:TheDiscourseofWelfareReform[J].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0,(4):163-195.
[18] 沈骑.教育语言学何为?——教育语言学的学科特性及其启示[J].当代外语研究,2012,(11):38-42.
[19] 王海红.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看《理智与情感》[J].绥化学院学报,2008,(6):88-89.
[20] 罗宾·沃霍尔—唐.形式与情感/行为:性别对叙述以及叙述对性别的影响[J].王丽亚,译.江西社会科学,2008,(1):27-31.
[21] 王宏维.中国特色妇女理论的后现代主义方法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3,(5):11-16.
[22] 杨永忠,周庆.女性学研究——反思与展望[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6,(4):8-13.
[23] 凌逾.女性主义叙事学及其中国本土化推进[J].学术研究,2006,(11):132-136.
[24] 谢淑海. 论后现代女性主义课程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