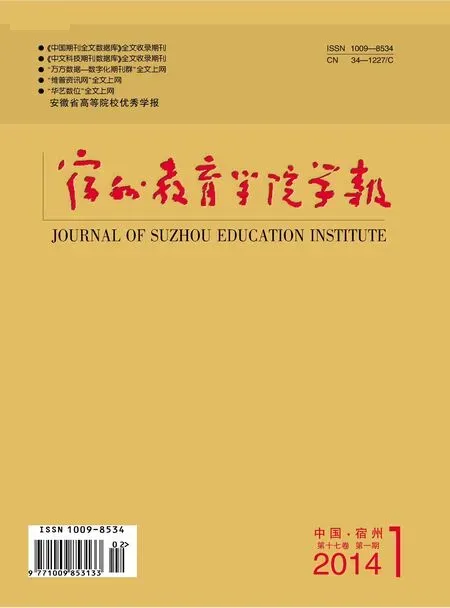从饮食观念看《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与其他人的思想文化内涵
郭欣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青岛266100)
从饮食观念看《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与其他人的思想文化内涵
郭欣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青岛266100)
在王蒙先生的《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所代表的处于二十世纪变动中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形象颇具典型意义,一面向往现代文明,一面又由于自身或外界原因无法从旧传统社会中脱身。与他相对比,家庭中的另外一些成员——静宜、静珍、姜赵氏和两个孩子,则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思想文化性格形象和发展可能。在倪吾诚的生命中有两件大事,一是洗澡,另一则是吃饭。饮食对倪吾诚来说是精神享受和力量源泉,注重营养搭配;对静珍来说是精神消遣,甚至是无聊时的精神支撑;对静宜、姜赵氏和两个孩子而言,温饱足矣。王蒙先生在小说中精细、生动、入骨地描写了很多有关吃饭的片段,饮食既是我们窥见每个人所代表的不同思想文化内涵的一个窗口,它本身也揭示了由于缺乏追求理想的行动力而耽溺于日常事务的众人的精神苦难。
饮食思想文化内涵精神苦难
1983年,陆文夫先生专门描写苏州饮食文化的小说《美食家》发表于《收获》杂志并获奖,深受中外读者喜爱,时隔三年后,王蒙先生的《活动变人形》发表,并被冠名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变形记’和‘心灵历程的缩影’”①而广受关注。然而,在《活动变人形》中同样有大量描写北京市民饮食习惯的片段,不仅通过作品人物对待饮食的不同观念和态度传达了他们代表的不同思想文化内涵,饮食描写的大量出现本身也揭示了由于缺乏追求理想的行动力而耽溺于日常事务的众人的精神苦难。与其他人的饮食观念不同,在对美食的热衷和美食带来的力量面前,集中西文化影响于一身的倪吾诚堪称是一个“美食家”。
一、“民以食为天”——静宜、姜赵氏以及孩子倪萍、倪藻
在小说中,没落后的姜家和收入微薄的倪吾诚给静宜娘几个带来的影响是对温饱的最低要求。生活的压力、理想的平庸,把静宜和姜赵氏打磨成了极端现实主义者,每日纠缠于下一顿饭吃什么,是否吃得饱这样的问题中,对炉子里放多少柴多少煤球精打细算。即使是对自己最爱的“好孩子”倪藻,也只能无奈地叹息“吃什么呢?吃什么,有什么可吃的呢”②,最后只能做了为倪吾诚所不以为然的糨子,并把自己爱吃糨子的现实主义观念灌输给为饥饿所驱使的倪藻。当静珍不顾家境窘迫坚持喝酒就花生米,以及单独做饭以飨胃口的时候,静宜和姜赵氏甚至两个孩子就会跳出来指责她的不是,原因不外乎是静珍不知节俭,在无法确保温饱的情况下自顾享受,威胁到了整个家庭的饮食保障,而这恰是最令静宜他们感到恐慌的事情。
静宜是一个曾经接触过现代文明的皮毛却在现实物质的匮乏面前一路败退的女性,就像她非天非人、亦天亦人的脚,趋向于新还是趋向于旧全部取决于她的现实需要。革命前的姜静宜与母亲、姐姐同流并肩,解放后的姜迎之与她们拉开距离,避免了与她们、与封建主义一道灭亡。姜赵氏是典型的没落地主阶级,收租收利,坐吃山空,吃饭穿衣混日子是生存的全部,所以到了晚年,她跟别人说:“我一点也不怕死了。我现在活着一点意思也没有。”③童年的倪萍、倪藻跟随妈妈和姥姥的脚步,恐惧明天的没有着落,对爸爸姨姨的奢侈行为苦大仇深。从根源上看,静宜、姜赵氏和孩子们眼里没有传统和现代之分,只有生存和无法生存、生活得好和生活得差的区别。是长久的传统生活环境和习惯性的伦理道德自我约束使她们对靠拢现代文明需要支付的代价惶惶终日。静宜、姜赵氏无疑是社会底层任由生活摆布的小人物,她们的精神苦痛在于把物质生活当做最高理想,时刻被现实左右,没有依凭。
二、吃是无聊消遣——静珍
《活动变人形》中的静珍这一角色极具有性格色彩,她是一个精通封建没落文化、严守封建道德的年青寡妇。丈夫早死、膝下无儿无女的静珍,被守志的决心和清苦守寡生活的矛盾所累,全力投入生活中一切可以激起她的激情的事情,并以此为生活的重心和支撑。因为不是儿子亦不是母亲,不被依靠又无所依靠,静珍在精神上是独立的,对家庭团结甚至是和母亲妹妹的团结不以为意。当倪吾诚离开那个小四合院或者倪吾诚和静宜和好的时候,静珍失去了战斗对象,她把精神寄托在做饭和吃饭上,即使在热汤杂面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为了酒可以与妹妹恶言相向。静宜和丈夫和解之后,静珍每天为了做什么饭而苦恼。“我今天做什么呢?她永远答不上来,她永远害怕回答这样的问题,她永远为这样的问题而痛苦,甚至是羞愧。一个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事可做的人是多么羞愧啊!”然而当做起饭、吃起饭来,她又是勇往直前,神魔无阻的,“从宣布吃肉饼到做出肉饼来,她的表情是决绝的、排除万难的、无笑容的。要一直吃到快饱的时候,丝里哈拉了一阵子以后,她才会由衷地笑起来。”④但是读书、吃饭都只是静珍无所事事的消遣,当她觉得做饭吃饭没意思了之后,又和“热乎”热乎起来了。
静珍精通封建文化,同时对现代文明保持兴趣。她会背很多古诗,还会背新诗,既读闲书,也读新式小说和外国作品。封建社会传统观念提前在她身上、心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内化成她与生俱来般的坚定信念,但她并不拒斥所有后来的文明因素,与倪吾诚身上中西交汇的矛盾不同,现代和传统在静珍这里汇聚成流,共同为打发时间,解闷逗笑服务,彼此相安无事。静珍的精神世界无疑是最强悍、最果敢、最坚定的一个,她所坚持的事情不会因外界的作用而改变,可是她的强悍、果敢、坚定都是环境造就的盔甲,她的精神世界里没有支撑,除了偶尔对小丈夫的思念外一片荒芜。所以她喜欢虾酱饼、羊肉这些带刺激性气味的食物,对生活中的波澜的反应总是一马当先,无所畏惧,当她在某一刻发现了使她兴奋的事物,那件事物就是她那一刻的精神支撑。当生活中没有了能激起她的热情的东西,她的结局可想而知。
三、“食以味为先”——倪吾诚
小说中倪吾诚正式以现实个人姿态登场,是请杜公到沙锅居吃饭。本来请客的宏大愿望变成了便宜实惠的沙锅居,顶着伙计施加的压力点了几个便宜实惠的菜,因为现实条件不允许,美好理想退而求其次,但是沙锅居的菜肴同样也赐予了他活力。喝了两口酒,吃了两筷子猪肠之后,“他的两眼大放光芒,他的面孔喜形于色,他的声音也洪亮了许多。‘请吃,请用一点,杜公,不要客气!’他优雅地摊开手掌,让着菜,倒像桌面上已经布满了仨盘俩碗,山珍海味。”“你看他两口酒三口菜下肚以后,是何等地精神焕发,神采奕奕,那样子简直像是突然做了皇帝!”饮食居然能改变他进沙锅居时的寒酸样子,并且只是一份沙锅白肉就可以让他对“世界的未来、国家的未来、朋友的未来与自己的未来”⑤充满信心。一个靠饮食给予力量的人,如何能经受得住他口口声声追求的理想和现代文明所不可避免的考验和磨难,令人怀疑。
倪吾诚爱孩子,尤其在意孩子们的营养搭配。他愿意向自己的孩子介绍西方文明,让他们远离传统文化里束缚他自己的东西。但是他的愿望是自私和偶然的,就像他带倪藻去吃西餐,却只顾和“密斯刘”交流,以致回家以后腿被冻得冰凉的倪藻觉得并不懂得享受的妈妈“比爸爸好一千倍”。病前为孩子们买的鱼肝油在被孩子们拒绝之后,倪吾诚用对西方科学文化的盲目崇拜克服了东方人身体对鱼肝油腥味的自然排斥把它成了自己营养和康复的源泉。面对大葱抹黄酱和红薯粘粥,“他兴致勃勃地出声地吃着,连说话都改了腔调,完全恢复了童年时期孟官屯——陶村一带的乡音,连笑声也变成乡下式的了,绝对没有任何一点欧罗巴的影响。”⑥在饮食面前,倪吾诚身上的东西方文化矛盾消失了,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追求也淡化了,家庭似乎也变得可亲可爱可交流了。然而在厌烦了千篇一律的大葱抹黄酱和菜粥之后,他对孩子们表现得津津有味感到心寒,以往他所批判的,在病后曾经一段时间的甘之如饴之后,又真正弃之如敝屣了,健康、营养、美味,现代文明重新占据了他的思想,他又变成了一个有追求有理想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仅在饮食一面,倪吾诚就步步印证了小说主题“活动变人形”的深刻性。
即使是在下定决心与静宜离婚之后,在静宜揭发他策划离婚恶行的宴会上,倪吾诚仍然沉浸在体面的地方请客吃饭的物质和精神双重享受中而乐不思蜀。他“咂嘴舐唇,谈笑风生,其神采为数月来所未有”,“倪吾诚正在喝汤,喝得太香,沉醉了,他在头几秒钟竟没有察觉到餐桌上的风云突变”⑦,美食取代了他数月为之烦恼奔波的缘由,成为他此刻注意力的全部中心,是莫大的讽刺。在他自杀未遂与家庭决裂又迫于生计不得不回来后,倪萍对他嗤之以鼻:“您在外边吃喝玩乐够了吧?没有饭吃了吧?所以您回来了。”⑧倪吾诚响应大跃进下乡参加劳动,只会休息,去农家喝酒吃狗肉;食品供应困难时期,“见到每样能入口的东西他都瞪起大眼睛来”;看到稿费的希望后,见人就发出邀请,想的是得到稿费后请各位朋友吃饭……倪藻当面对他说“一顿好饭就能改变您的世界观”,倪吾诚不但不以为杵,反而点头称是,并说那符合唯物论,为自己的好吃懒做安上一个无懈可击的借口,是可鄙,也是可悲。
倪吾诚对西方现代文明当然是向往的,他甚至对革命也是真诚地支持的,但是他真正企盼的不是追求和革命的奋斗过程,而是现代文明和革命所带来的理想生活: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精神追求不受道德约束。对于极其缺乏行动力的倪吾诚来说,留洋经历和西式教育不仅没有解救他和祖国,反而让他看清了内外差距而陷入更大的痛苦中。他试图改造静宜和孩子,但是既未脱离传统土壤又只得到了现代文明的皮毛的困境使他自己都找不到出路,他所夸夸其谈的理论被他自己验证了是荒唐的。每当被问及有关追求和抗日革命的现实问题,倪吾诚的精神便退缩回孟官屯——陶村人的世界中,麻木、迷茫、无所适从。他与全家人的矛盾除了他自以为文明的优越感带给其他人的不适之外,还集中在物质利益冲突尤其是饮食问题上。他的苦痛、挣扎是因为他自以为是的智慧和能力没有机会发挥出来,从而无法回报给他相当的物质享受。从这一方面看,与静宜、姜赵氏相比,倪吾诚只是不满足于温饱,尚且肖想些美味,中间多了作为留洋知识分子而堂而皇之的理想和追求作为幌子罢了。
饮食作为生存必需,是观察和分析一个人的性格和思想文化内涵的窗口。倪吾诚一家对待饮食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分处在传统和现代及它们的交界上的众生情态。他们各自的精神苦痛是个人的苦痛也代表了集体和社会的苦痛。王蒙先生对现代与传统的碰撞的描写尖锐、深刻又不乏希望。倪萍、倪藻、倪荷不可避免地也具有活动变人形的特性,但是他们代表的是一代有反抗精神、有行动力的新生群体,他们或许没有接触过西方文明,但是他们通过行动参加并真正融入了现代文明。
注释:
①王蒙.活动变人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封皮.
②王蒙.活动变人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75.
③王蒙.活动变人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35.
④王蒙.活动变人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16.
⑤王蒙.活动变人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3.
⑥王蒙.活动变人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78.
⑦王蒙.活动变人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89.
⑧王蒙.活动变人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18.
[1]王蒙.活动变人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温奉桥.王蒙·革命·文学——王蒙文艺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王蒙.王蒙、王干对话录·《活动变人形》与长篇小说[A].王蒙文存(二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4]朱希祥.江南俗食与美食——陆文夫笔下的饮食文化[J].食品与生活,2000(1).
[5]冯维娜.邯郸学步与学以致用——评王蒙小说《活动变人形》[J].作家杂志,2010(2).
[6]夏义生.倪吾诚:文化与政治革命的双重“零余者”——重读王蒙的《活动变人形》[J].当代文坛,2011(1).
[7]谷熠.无处倾泻的力比多——简析《活动变人形》中的静珍[J].语文学刊,2012(9).
[8]付品晶,徐其超.由倪家人的文化个性透视中西文化关系变迁——评王蒙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8).
I207.4
A
1009-8534(2014)01-0020-03
2013-07-19
郭欣(1990.11-),女,山东省临沂市费县人,中国海洋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