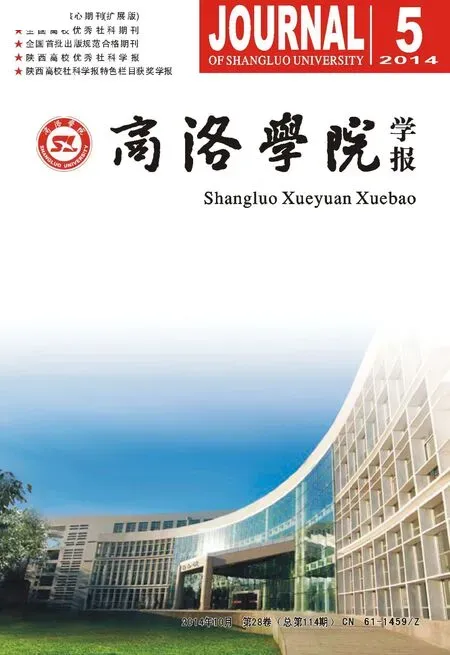论电影《归来》的改编策略
杨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24)
论电影《归来》的改编策略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24)
张艺谋从小说《陆犯焉识》改编的电影《归来》作为今年最重要的电影改编案例,因涉及“文革”背景和改编者对原著的“大幅削减”引起争议。通过对电影文本与小说文本的细读,对小说内容进行细致比较分析,得出电影《归来》的改编主要采取了淡化政治影响、淡化个人与时代关系、简化家庭人物关系等策略,投射了当下社会的文化特征及创作者的文化心理。
《归来》;改编策略;个体与时代;愈合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电影受“影以载道”的艺术原则、审查制度等多因素的影响,成为受政治影响最大的一种艺术形式。电影文本如何表现时代历史及其“隐蔽”的政治,不仅体现了创作者个体的世界观与历史观,更投射了整个时代大众群体的主流心理,好作品因创作者个体与官方意志的博弈,促成一份反映时代“症候”的绝佳文本。张艺谋要改编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引来学界各方猜测。如何在当今政治文化环境处理小说中的特殊历史时期,应该是影视界和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电影公映之后,对比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不难发现导演张艺谋的改编策略就在于对“愈合”主题的精心强调。本次改编案例也极能体现电影作为当代媒介所发挥的维持社团与亲族感的作用,具体到本片来说就是缝合政治历史裂缝,治疗社会伤痛,抚慰群体心理的作用。本文拟分析电影《归来》的改编策略,即创作者是如何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与电影审查制度、市场因素博弈,并平衡自身创作欲望的,以求还原导演改编的缘由与初衷。
一、淡化政治,时代后置为背景
《陆犯焉识》是一部把知识分子的灵魂放在火上炙烤的小说。小说用贯穿始终的现在和过去两条时空线索,前后约五六十年的时间跨度讲述了陆焉识的悲喜人生,从少年赴美留学开始,依次经历了回国任教的学界争论,抗战随校迁至重庆后物资贫乏的生活困境,两年牢狱之灾,抗战胜利后的物价飞涨、房产接收闹剧、再次失业,建国初期的再次执教与信仰学术自由的1955年“反革命”,从此才开始小说的重点叙述时空——西北荒漠上的20年劳改生涯。小说用倒叙手法展开故事,小说开头写1963年陆焉识已经是熟谙农场监牢生存法则,伪装口吃保护自己的老犯人了。后半部分才写到焉识1955年被作为“反革命”抓捕后经历的种种真正的荒诞和精神幻灭:无定论的减刑和加刑,从刑场被通知死刑改无期的孰幸孰哀。严歌苓是这样描述这种恐惧下的梦游的:“灵魂看着自己的肉体自行其是,无法去控制它。经历了巨大心理恐惧的人以这种方式逃避恐惧。”[1]即是说,小说里那一代知识分子遭受的苦难是从1955年“肃反”开始一直贯穿到“文革”的。带出的监狱里的其他形象亦是那个时代某个侧面的缩影:因饥饿与仇恨杀死不忠母亲的梁葫芦设法搞到各种吃的;对抓捕任务产生过怀疑的前国民党警察老刘吞药自杀;出身书香门第的中学生被裹挟进上山下乡的命运,学英语搞学术的梦想如梦幻泡影,所有理想彻底被毁灭……
由于电影容量远小于小说,无法承载过于漫长的时间跨度,《归来》只选取了《陆犯焉识》的最后二十页进行改编,这使得时间跨度必然大大缩减,本无可厚非。但成功的文学改编电影,一定会在电影有限的文本有限的时空中浓缩原小说的整体韵味,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相比《色戒》《赎罪》这类同样改编自小说并成功处理时代风云与小儿女故事的作品,《归来》和原著《陆犯焉识》已无紧密关系,甚至可以说是风格迥异,独自存在的两部艺术作品。
在现有的电影审查制度下,直接处理“反右”和“文革”题材极难通过,对比《归来》,会发现时代已完全后置为背景,历史政治作了完全淡化处理,一些历史问题也被置换,导演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腾挪转移。电影开始时字幕说明是“文革”时期,而整部电影中也从未提过焉识是何时被抓捕入狱的,“文革”结束后区委干部对婉瑜说,文革结束了,焉识被释放回家了,这是在提示观众,焉识只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电影这样表现,焉识所代表的知识分子1966年之前所遭受的苦难就被淡然抹去,建国后从“反右”开始的一系列历史错误与问题被置换成“文革”问题。
显然,在电影中亦是关于历史少有的提及之一。关于历史与时代,电影集中在焉识逃跑这场戏中有所体现,女儿因为想跳《红色娘子军》里的吴清华而向邓指告了密,这本是那个时代的经典叙事之一,在许多人物传记中即可见到。最终的演出中,舞台中的暴力叙事和影片中的历史叙事形成一种文本内的呼应,红色灯光下吴清华被簇拥在人群中,而女儿丹丹扮演的配角战士只能在边沿擦泪,也是一种很明显的伤痛暗示。随着这场戏之后的字幕“‘文革’结束”,整部电影的主要情节才拉开大幕,而这之后的所有情节和场景,都明显是一种淡化时代的处理。婉瑜的失忆如果没有后来浮出水面的方师傅的存在,没有读信、修钢琴这些情节中透露出的细节,基本上类似于一个当代的普通家庭悲剧。结尾处“很多年后”,焉识依然推着婉瑜的轮椅去接“5号到”的爱人,那时车站、办公人员制服已换了新装,提示时代流转,伤痛依然存在,但疗治愈合的努力始终不曾放弃。
张艺谋的这种“营造的愈合”和谢晋导演的“以家喻国”回避政治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果说谢晋是用道德置换政治,用女性和家庭缝合政治创伤,那张艺谋的《归来》就是试图在淡化政治的背景下,用失忆喻创痛,用温情愈合创伤。
汪晖的《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谢晋电影分析》一文曾引发了关于政治与艺术关系的再度讨论。文中有段话对《归来》依然适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故事的道德化的叙事方式恰恰表明了谢晋电影的政治性质。甚至可以说,较之西方那些直接以上层政治为对象的影片,谢晋电影才是真正政治性的,因为将政治隐于背景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策略。换言之,‘展现影片政治意义的东西并非是直接政治话语:它是一种道德化的话语’,而这种道德化的话语却试图重写中国的历史,塑造中国的未来,创造适合于中国社会的永恒价值。”[2]显然,《归来》就是这样一个用爱情道德话语隐蔽政治,重写历史的文本典型,但相比谢晋从“反思三部曲”开始的强烈的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认同,再对比他于1994年执导的颇为直露批判的《活着》,张艺谋的“将政治隐于背景”更多体现出一个体制内导演经历岁月洗礼后的某种妥协。
二、只见小儿女,不见大时代——历史记忆的留白
《归来》体现出历史记忆的留白,对个人与时代关系的淡化处理。关于电影中的时代与个人,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山教授有过非常精彩浓缩的总结:“讲述历史中的人的电影必须既有大时代又有小儿女,像《一江春水向东流》。只有大时代没有小儿女,不叫电影;只有小儿女没有大时代,也不是好的电影。”用陈山教授的观点分析,《归来》似乎属于后者——只见小儿女不见大时代。电影静心呈现的是一场乱世之恋,是“右派”知识分子陆焉识和他忍辱负重的妻子冯婉瑜之间不离不弃相伴一生,用不懈努力愈合伤痛的感人传奇。历史就在这传奇之中悄然散去,不为人关注。这也许是电影媒介的大众性和敏感性使然,却不得不让人惋惜。
对比其他表现时代与个人的电影,会发现,这类将个人情感与时代悲剧连接在一起的故事成功的叙事关键便在于以小见大,由浅入深。横向比较如2007年上映的《色戒》,通过王佳芝个人的悲剧,国恨家仇前形形色色人物的表现来展现抗日时代的悲剧,由小开始,以大收尾。纵向比较像1937年沈西苓的《十字街头》和1947年蔡楚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青年人在乱世中的遭遇,前者通过四个青年的不同选择透视战前社会境况,后者则用一个大家庭从战前到战后的遭际折射整整十余年的社会变迁。再比较同样表现政治运动对个体影响的1994年俄罗斯导演米哈尔科夫的《烈日灼人》,相似的“故人回归”情节,主要情节是没落贵族、将军和将军之妻三个人的命运悲剧,可渐往深处得见的是整个斯大林时代的悲剧。反观《归来》,焉识的归来似乎只见证了他与婉瑜爱情、家庭的悲剧,整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被避而不谈,只在一些细节处仔细咂摸方可意会,如对话中得知大卫的自杀。难怪戴锦华在访谈中提出:“若说现实主义就是一套营造‘透明’叙事的成规、惯例,那么,《霸王别姬》《活着》始终不失为出色的现实主义情节剧。《归来》是大踏步倒退。”[3]
只见小儿女不见大时代和历史记忆的留白简直互为因果。历史记忆的留白体现在人物记忆中,就是一种空白化处理。无论是焉识归来后政策的迅速落实、组织的尽心安排,还是对焉识在狱中苦难的毫不提及,都是一种或乐观化或空白的处理。
电影将时代带给人物的隐性创痛埋在人物心底深处,用婉瑜的失忆来隐喻普通人的历史创伤,她始终记得自己爱人的所有信息,保留着学生时代的回忆,对女儿丹丹“出卖”父亲始终耿耿于怀,遭欺侮的经历更是她心底不能磨灭的梦魇,但她却对历经沧桑站在面前的爱人相见不识。婉瑜个人对耻辱经历的失忆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时代的记忆。
电影中对婉瑜的伤痛记忆用方师傅这个人物来具体化。方师傅对应的是小说里利用职权占有婉喻的个别丑恶的政府干部,在电影里简化成了工人,始终未曾露面的方师傅却是盘踞在婉瑜心中的最大恶魔。此处的留白大有其妙处,人内心的伤痛虽是无形却绵长难驱。婉瑜的屈辱记忆浮出水面,导演对方师傅的悬念做足后,前去算账的焉识却被其家属咆哮告知,“老方”被专案组带走至今未归。这个处理避免了普通个体成为家庭乃至历史替罪羊的陋处,这传达出这样一个暗示:任何人都逃不出悲剧历史规则的捉弄。
三、简化家庭人物关系,弱化反思
家庭人物关系的简化处理也是电影的一个巨大改动,对情节的集中确实行之有效。小说里焉识和婉喻有一儿一女,焉识归来之后家庭矛盾随之升级。儿子对父亲带给自己的敌属身份及随之衍生的苦痛记忆耿耿于怀,女儿在母亲逝后默许丈夫一家完成了对父女二人家庭的“殖民”,甚至焉识教小孩英语时说的“毛主席也不是英文专家”也让儿子大惊失色,历史的伤痛就此复发,焉识在婉瑜去世后再次成了“多余的人”。电影里父女关系的简化有助于将情感主线专注于焉识婉瑜二人,父女关系也是为主线服务的。集中主线故事,剪掉枝蔓的同时,陆焉识释放回家后融入社会群体的艰难也随之烟消云散,新旧时代的碰撞、遭遇历史创痛的个体如何努力适应新时代的脚步,这些极有意义的问题也无法在银幕中得到表现。
这种简化在突出主线的同时,也简化了丹丹对待父亲从仇恨陌生到理解并产生悔意的过程,使得对父亲的道歉也显得突兀。这一方面是电影没有足够容量来铺垫情感和关系,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是导演创作“愈合”主题的需要而降低了对人性的探索。
当然,这样的改编策略与《归来》的电影类型——家庭伦理剧关系甚深。家庭伦理剧这种中国传统的电影类型,在近年的主流的关于时代历史的剧情片中,承担起愈合历史伤痛的时代功能,不论是2010年上映的《唐山大地震》还是如今引起讨论的《归来》,都采用了消隐大时代描摹小儿女传奇的策略,都是在弱化真实时代背景的前提下,用真挚亲情关系带来的巨大情感冲击力来感动观众,达到国家族群对创痛经验的整体疗治。这不同于《一江春水向东流》赤裸裸地揭开一个大家庭在时代巨变中的伤口,也不同于文艺探索之作《团圆》所表达的伤痕对三代人的影响。看完电影以后,观众的意识被焉识和婉瑜的感人爱情故事所占据,将原著小说里的历史反思和对知识分子群体灵魂的审视扫荡得干干净净。对比张艺谋1994年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如果说《归来》是回避历史或曲笔写实,那《活着》则是一首民国到“文革”后以笑代哭发人深省的时代悲歌,片中对知识分子“文革”中遭遇的黑色幽默式表现,直接导致电影的禁映(也许这也是张艺谋此次策略的一个原因),由此亦可见审查制度随时代变迁产生的变化。
四、结语
张艺谋的《归来》是在历史语境和当代语境的夹缝中腾挪,是政治表达和个人情感以及市场因素的综合妥协作用下的一个时代作品。它专注于描摹特殊政治背景下的言情剧却对时代反思甚少,但同时又满足了主流观众对温情的需求,让我看见导演那一代人在现实语境下试图愈合历史创伤的努力。这是这个时代难以言说的悖论,也是“文革”题材电影面对市场和审查制度行之有效的“妥协”手段。这部电影也是一个文化范本,从中可以窥见我们时代的许多特性。
[1]严歌苓.陆犯焉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296.
[2]汪晖.政治与道德及其置换的秘密——谢晋电影分析[J].电影艺术,1990(2):33.
[3]刘功虎,戴锦华.《归来》是一部烂片跌出了下限[EB/OL].共识网,2014-07-30.
(责任编辑:李继高)
On Adaptation Strategy of the Film Com ing Home
YANG Yi
(lnstitute of Art,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24)
The film Coming Home,this year′s most important adaptation case from the novel The Prisoner Called Lu Yanshi,caused argument for the background of the″cultural revolution″and the excessive cut of the original.Comparing flim text with fition text carefully,the author has elaborated on the analysis of fiction content.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simplification of politic influenc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age,and the family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exert a projection of current social cultures and writers'cultural phychology.
Coming Home;adaptation strategy;the individual and the time;heal
J905
:A
:1674-0033(2014)05-0042-04
10.13440/j.slxy.1674-0033.2014.05.009
2014-07-22
杨祎,女,陕西商州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