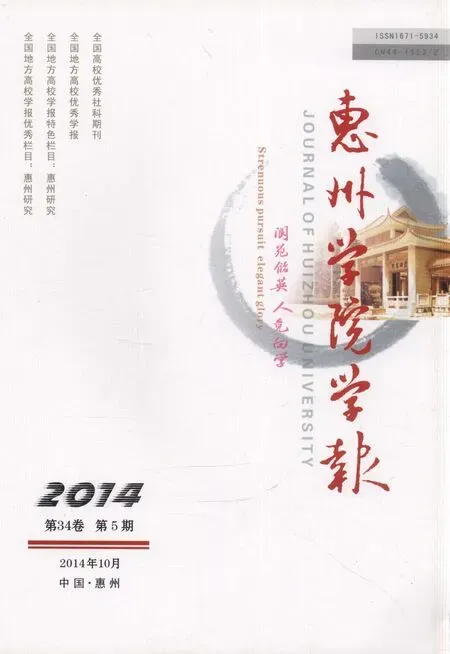惠州文化的“后客家文化”性质定位
柯汉琳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东江文化”概念的提出很有意义,相对于“惠州文化”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但“东江文化”是否可以等同于“惠州文化”,“惠州文化”是否“东江文化”的“缩影”或“中心”、“代表”?如何理解“惠州文化”的性质定位和特殊性?等等,笔者试就此作一些粗浅思考。
一、东江文化:客家“文化圈”四大“文化区”之一
提出“东江文化”的概念,主要是用以替代“惠州文化”的概念,使原先的“惠州文化”概念具有更大的外延和更丰富的内涵。鉴于现今惠州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少学者又强调惠州是“东江文化”的代表、中心或缩影。还有学者进而提出“东江文化”是与习惯所说的岭南文化三大谱系——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并举的一种具有自己特质的文化。
这些描述似已获得大多学者的认同。笔者非常赞成“东江文化”的概念,赞成把东江流域的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进行研究。但是,如果把东江文化视为与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并列的一种文化,则仍缺乏充分的说服力和必要性。
成晓军先生曾指出,“东江文化”的要质是客家文化,但不是纯客家文化。反过来说,“东江文化”不是纯客家文化,但要质是客家文化。就是说,“东江文化”虽然不能笼统说是纯客家文化,但其“内核”是客家文化。一种文化的“内核”决定了该文化的根本性质和从属。语言、历史、文物、风俗才是文化的“内核”,而无论对作为“东江文化”的语言、历史、文物、风俗的考证还是生活现状的考察,都足以证明,“东江文化”总体属于客家文化。对此,时人已多有论说。
那么,东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的性质应该如何定位呢?这是给惠州文化作性质定位的前提。这里必须先谈谈文化的区域性问题。
文化具有区域性,因为人类各种不同的文化都是在一定的区域产生、发展、成熟并形成区域的特色的。因此,对文化进行区域的划分、对某一区域的文化进行研究,必然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区域一般所指是地理空间,某一区域的文化就是指占有某一地理空间的文化,如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等和今天讨论的东江文化,都是区域文化,规范说法是“文化区域”(cultural area)。“文化区域”作为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对文化分布描述的概念之一,固然强调地理空间性,但又不是一个纯地理空间的概念,它必须是体现一定文化特征的地区,即具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语言、语言心理、行为方式、居住形式、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等[1]414。其次,“文化区域”也不是一个与时间无关的概念,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时空中运动的,区域文化必须有历史,有传统。一个“文化区域”内部也可以划分为若干小区,一般称为“文化区”。“客家文化”的概念显然强调的是一个人群的基本相同或相似的语言、语言心理、行为方式、居住形式、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及其传统,而不是以地理空间命名,它当然具有区域性。但由于其分布的地理空间不完全相连(不仅分布于广东、江西、福建,还有湖南、广西、四川等一些不完全相连的地区),所以可以用“文化圈”名之。文化圈概念是由德国文化人类学家莱奥·弗罗贝纽斯(Leo.Frobennius,1873—1938)在对非洲文化进行划分时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文化圈都是以一定的物质文化为特征的,但其内涵尚不够明确。其后德国民族学家R·F·格雷布纳(Robert FritzGraebner,1877—1934)于1904年在柏林一次学术会议上发表了论文《大洋洲的文化圈和文化层》,对文化圈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理论阐述,由此文化圈的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而被正式确认。格雷布纳认为“文化圈”指一个地理空间范围;但1911年他在《民族学方法论》中进一步指出,不论分布在什么地方,只要拥有同一种文化的,就属于同一个文化圈。这样,文化圈就不一定指一个独立自足形成整体的地理空间。后来奥地利民族学家W·施密特(Schmidt,Wilhelm,1868—1954)也强调“文化圈”不限于一个地理空间范围,地理空间不完全相连而主要文化元素相同或相似的就属于同一文化圈①。这样说来,“文化圈”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文化区域”,常常用以指某种跨国文化,但笔者认为也可以用以指一国之内的某种跨空间文化(因为从历史看,许多“国”的空间也是变化的,所以文化圈的跨国研究与就一国研究并不矛盾)。如果赞成这一说法,那么,可以认为“客家文化”是存在于一个“文化圈”中体现着客家人特色的文化,即“客家文化圈”。“客家文化圈”又可以划分为若干“文化区”、“文化小区”。
“客家文化圈”的区域,从客家人世居聚集的角度说,人所共知,主要是闽西南、赣南、粤东等地区。但以往一般认为以汀江流域、赣江流域、梅江流域三个地区为主要。这一表述的缺陷是没有充分认识到东江流域作为客家人世居聚集地的相对独立性和重要性。实际上,东江流域应与汀江流域、赣江流域、梅江流域并列为客家人世居聚集的四个地区,而“客家文化圈”就形成了以梅州为代表的梅江流域客家文化,以赣州为代表的赣江流域客家文化,以汀州为代表的汀江流域客家文化和以河源为代表的东江流域客家文化四个“文化区”。理由非常充足,因为全国有“纯客住县”44 个(“纯”不是绝对的,一般指客家人在95%以上),其中江西16个,广东18个,共26个,超出了全国总数的一半;而穿越江西、广东两省的东江上中游的江西赣南(赣县、南康市、大余、崇义、上犹等)和广东粤北(龙川、东源、紫金、和平、连平、翁源、新丰、始兴、陆河等)就共有10 多个;[2]4中下游的惠州、博罗、东莞、宝安(今深圳)等既然不是“纯客住”市县,也是以客家文化为“内核”的“文化小区”。就是说,粤境内的东江区域客家住地范围比梅江流域客家住地范围还广大,所以,讲客家人世居聚集的大区域,理所当然应该把东江流域列为主要区域之一,东江文化也毫无疑问属于客家文化。强将东江文化从客家文化分离出来,与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并举的就显得牵强附会。
二、惠州文化:东江文化历史迁移中诞生的“后客家文化区”代表
处于东江中游区域的惠州,早自一千四百多年前的隋唐已是“粤东重镇”;中国近现代史以来,惠州更是东江地区的首府,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惠州也是客家人世居聚集的重镇,其文化内核是客家文化。但是,从客家族群诞生、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惠州既不是东江地区客家形成的源头,也不是最具典型性的纯客住地。
据各种历史资料综合分析,东江地区客家族群形成的源头可以认为有三个重要源头,即福建汀州、江西赣州和广东古龙川(今属河源)。就是说,河源才是粤境内东江流域最早最成熟的纯客住地。理由有两点:第一,据有关历史学家介绍考证,河源是最早客家先民的涉足地和落居地。早于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前已有秦军驻守在古龙川,后便成为古龙川第一批客家先民;东晋战乱时,河南、山东等地区的中原汉族相继南迁,也部分成为河源客家人。现在,广东79个县市全部都有客家人居住,而今属河源的龙川是全省客家人最为集中的县之一。第二,作为一种文化的代表地,一般应较集中地拥有体现该文化的古文明遗迹,而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显示,整个东江水系的考古调查,发现代表东江文明的古遗址数量是:河源地区138 处、惠州地区10 余处、东莞10 余处、深圳10 余处,其中从属于河源的和平县的代表性古遗址就有116处,占标识东江文明起源的早期古代遗址(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战国)95%。事实表明,河源是客家文化始源地之一,又是粤境内东江流域客家文化的代表或缩影。
与河源比较,惠州显然不是传统的客家文化区即不是纯客家文化区。理由是:惠州的客家移民较河源晚,据记载,唐末才有中原先民约5 万人入惠定居,南宋之后才有大批中原先民入惠定居,约20 万人;又据《惠州市志·人口》载:宋末,北方汉人为躲避战乱再次大量南迁,自宋至明中叶、清初,惠州的客家移民从梅州、赣州、吉安、抚州、龙岩、河源、韶关等地相继迁徙而来,才使惠州市境容纳了大量“客户”。但当时的惠州“客户”仍少于“主户”[3]439(《太平寰宇记》记载是:原籍6115户、客籍2224户)。至当代,根据侯国隆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惠州全市户籍人口中客家人口只占41%左右。[4]另一方面,惠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又使其长期明显受广府文化的影响和一定程度受潮汕文化渗透。这种特殊情况,使惠州文化不同于传统的客家文化。所以把惠州文化定位为东江流域客家文化的代表或缩影是不妥的。
但是,人们又说惠州文化的内核是客家文化,与上面的说法是否矛盾?笔者以为不矛盾。中原先民入惠定居的时间相对较晚和人口比例不过半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和确保惠州原生的本地文化占绝对优势。一般来说,一个地区在一种外来相对先进的文化介入之后,会引起质的变化。特别是这种外来文化不仅先进而且强势时,就更明显。据记载,秦朝时期,秦始皇派50万大军南攻岭南,在东江以东,赵佗的军队并没有受到太顽强的抵抗,南下汉人的势力迅速壮大,再加上经江西、福建而来的汉人势力的源源不断的补充,北方和中原汉人很快同化了当地的越族,本土居民很快就被汉文化同化。这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同化现象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并不鲜见。广东传统的客家人居住地如梅州、河源等是如此,惠州也不例外。秦军入惠,灭了“缚娄”国(春秋战国时期,惠州地区属于百越范围,曾建立过一个叫作“缚娄”小国)之后,本地文化更大程度上被汉文化同化;同时中原先民入惠,又带来了当时明显优越于惠州本地文化的中原文化,在千百年的磨合过程中改造了惠州本地文化的存在形态,慢慢地形成了以中原文化演变而成的以客家文化为内核的惠州文化。所以,从大的方面着眼,惠州文化应该属于客家“文化圈”的文化。
但是,正如上文指出的,惠州不是纯客住地,惠州文化与传统客家文化不同。那么,如何对它的性质定位呢?笔者认为,可以把惠州文化定位为一种“后客家文化”;惠州可以视为东江流域乃至广东“后客家文化区”的代表。“后客家文化”和“后客家文化区”的提法虽受“现代”、“后现代”一类术语的启发,但主要源于两点考虑:第一,如上所述,从客家族群迁徙和形成过程的先后来说,相对于梅州、赣州、龙岩、河源等客家而言,惠州客家是“后来者”,可称为“后客家”。第二,从文化变迁和特点看,惠州文化虽然内核是客家文化,但必须看到,惠州客家文化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较明显体现了对传统客家文化的离析与对广府文化、潮汕文化的吸纳,并与本土文化整合,整合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与传统的纯客家文化有别的客家文化,就是“后客家文化”。“后客家文化”所在地包括惠州(惠阳、惠东、博罗等),也包括增城、东莞、宝安等(今之深圳),即东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称为“后客家文化区”。如果说,赣州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摇篮”,汀州是客家“首府”,梅州是世界“客都”,那么,惠州就是“后客家文化区”的代表或中心。
“后客家文化区”受广府文化、潮汕文化的渗透(当然反过来也有客家文化包括“后客家文化区”对广府文化、潮汕文化的渗透),但渗透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很明显,靠近潮汕文化区的惠东更多受到潮汕文化的渗透,靠近广府文化区的惠阳、博罗、增城、东莞、宝安更多受到广府文化的渗透,特别是增城、东莞、宝安等甚至受到广府文化不同程度地同化。所以,对东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后客家文化区”仍要作具体分析。但整个“后客家文化区”都受到其中心惠州文化的辐射则是没有疑问的。因此“后客家文化区”研究的重心必然是惠州文化。
三、惠州文化:作为“后客家文化”的特征
如果认同惠州文化作为“后客家文化”的代表和中心的说法,那么,认识“后客家文化”的性质特征,便成为深入研究和把握惠州文化的重要课题之一。
上面提到惠州文化的“离析”与“整合”问题,实际关系着如何正确把握惠州文化的特征问题。这里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一)关于文化“离析”问题
和一切区域文化一样,客家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不论什么区域文化,随着时代的推移,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文化“离析”与“整合”。所谓“离析”,指的是一种文化从其母体分化出来的过程和现象。这里说的“母体”是相对的,例如我国各民族的文化母体是华夏文化或炎黄文化,客家文化也是从这个母体中分化出来的,当然具体说是从汉文化母体中分化出来的。而客家文化一旦形成稳定的传统,就称之为传统客家文化,即客家文化的母体。随着传统的客家文化的发展,又必然衍生出新的客家文化,这个过程和现象就是客家文化的“离析”。实际上,客家文化的母体存在于整个客家文化区域中,即客家文化圈中,而各客家文化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客家文化母体的“离析”现象,这种“离析”并不是对传统客家文化的消解,而是促进了客家文化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客家文化区都保持着“原生态”的传统客家文化,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个客家文化区都保持着“原生态”的纯之又纯的传统客家文化。惠州文化就是从客家文化母体“离析”出来的新的客家区域文化。
(二)关于文化“整合”问题
一种区域文化在其从母体“离析”的过程中,也是演进、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定也是吸纳、融合其他文化——时代文化和周边文化的过程。时代文化是历时性的,是超越民族的反映时代精神或趋势的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或区域文化能游离于时代文化而自我封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世界的文学”时所说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5]27”周边文化是共时性的,指的是周边地理空间的异质文化。文化史证明,没有一种区域文化能够与周边文化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而不互相吸纳、渗透的。惠州,其特定的地理位置,恰恰就处于广府文化、潮汕福佬文化之间的地带。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广府文化、潮汕福佬文化等周边文化的辐射、渗透、影响,这就是所谓文化发展的“外缘”。在此情况下,惠州文化自然而然要吸纳、融合这些异质文化(当然是异质文化中的先进成分),进行文化整合,即以传统客家文化为内核,吸纳、融合广府文化、潮汕福佬文化的先进元素,根据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需要建构一个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新的文化整体。
惠州文化就是在对本土文化和传统客家文化的继承与变异、“离析”与“整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后客家文化的特征。
那么,惠州文化作为后客家文化具有什么特征呢?成晓军等学者概括为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和创新性等。笔者以为,还应该注意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后客家族群的居住地多靠近海洋(纯客家族群的居住地多在山区),具有海洋文化的进取性、开拓性特征;二是靠近香港,较早通过香港受到西方异质文化的先进因素的渗透而具有更多的现代性特征。特别是近代以来,这两个因素相辅相成并形成一种力量促使以惠州文化为代表的后客家文化的进取性、开拓性和现代性特征更为鲜明突出。这几个特点与传统客家文化的相对保守性、自足性(与传统客家或纯客家的居住地多为山区有关)明显不同。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惠州区域的整体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些特征,而作为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的深圳诞生于后客家文化区也不是偶然的。深圳作为一个新兴城市,其人口来源于全国各种文化区域,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共生城市。但它毕竟诞生于后客家文化区,以后客家文化为根基,后客家文化的进取性、开拓性和现代性特质对深圳整体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深圳的发展也反过来证明了后客家文化的现代活力。
四、余论
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存在于流动发展的过程中。一种文化的起源及其原生态所确立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形态,总是在规定、影响着该文化的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态势,这就是所谓历史文化的“在场”现象,因此,对文化传统和历史形态的研究,不仅研究该文化的性质特征的根基,也是把握该文化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根据,就是说,对该文化的起源及其原生态所确立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形态的发掘、梳理和阐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文化研究的深层意义不只在于从中发现过去的辉煌,也不能把一种文化“部落化”和过分强调稳定性,而应该充分注意文化的流动发展,注意文化发展过程的离析、选择与整合及由此形成的新的文化形态,重视文化的现代化,重视文化与现代价值体系的吻合,这才是文化研究的重心。
注释:
①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页;《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0页。但上述百科全书说文化圈由格雷布纳首次提出。根据其他资料考证,应是弗罗贝纽斯首次提出。
[1]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414.
[2]丘桓兴.客家人与客家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4.
[3]惠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惠州市志·人口[M].北京:中华书局,2008:439.
[4]侯国隆.关于广东客家人分布情况的调查[M]∥程志远.客家源流与分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4.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7.
——粤语·女独·伴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