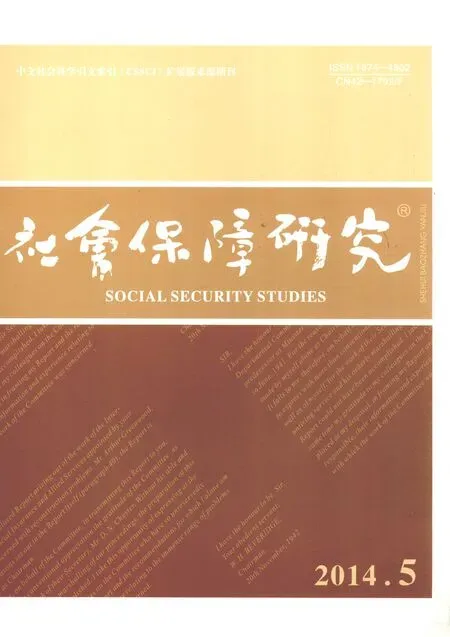子女赡养责任政策与立法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杨翠迎 马 涛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433)
子女赡养责任政策与立法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杨翠迎 马 涛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433)
由于受文化、经济与政治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对子女赡养老年人的政策立法及其理念各不相同。本文在比较借鉴国外相关制度立法规定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试图从立法层面寻求对规范和完善我国子女赡养老年人责任的政策启示与建议。重点进行了三方面的研究:一是基于立法层面对典型国家关于子女赡养义务的相关政策与法规进行梳理和概述;二是对各国子女赡养责任立法及其实践进行多角度的比较,总结其普遍性的做法及理念;三是在对我国子女赡养责任立法现状概述的基础上,结合国际经验,提出对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建议与设想。
养老保障;赡养义务;政策法规;国际比较
在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问题上,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与中国经历着正好相反的路径。发达国家一直以来是以社会化养老为主,但是近年来因为社会化养老的负担越来越重,开始提倡和强调子女的赡养义务,有回归家庭养老的趋势。而与之相反,近年来我国在致力于建立健全社会化养老体系过程中,反而有些忽视家庭养老资源,低估了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能力。
世界上各个国家普遍存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现象,随着老年人口数的增多,养老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在美国,退休人数和在职人数的比例,2000年为25%,预计2020年将达到33%,照此速度发展,每年养老金缺口额会占到工薪税总额的2%。[1]德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据世界银行的科尔海因斯预测,[2]德国需要把工薪税调到工资总额的32%左右,才能保持住目前的福利水准。这意味着大多数中等收入家庭的整体边际税率会达到80%以上。日本的老龄化情况更甚,受益人与纳税人之间的比例增加,从1976年的8%直增到1990年的23%,2000年达到37%。[3]奥地利60到64岁的老年人中领取政府养老金的比例为74%,为世界之最。瑞士、法国、美国、日本对应的这一受益人和纳税人的比例分别是17%、60%、44%、24%。[4]面对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子女赡养责任问题也越来越频繁地被重新提及。
针对养老回归家庭的现象,有学者对此做出相关研究。如鲁恩艾尔维克、英格丽海尔格伊[5]通过对挪威、英国这两个国家重新重视家庭养老的做法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英国对老年人生活、就业等全方位的从家庭得到支持进行制度设计,挪威为老年人推行优先就业路线等,都属于一种积极的养老政策。翟芳[6]对国外近年来推崇的精神赡养理论、制度与实践进行了经验总结,并为如何完善我国老年人精神赡养制度和法律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研究,对强化子女赡养责任、推进家庭养老和确保老年人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典型国家关于子女赡养义务的政策与立法实践
(一)美国:通过减税鼓励子女赡养父母
一直以来,美国年轻人在成年以后其父母就不再提供生活费等费用,他们也没有承担赡养老年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老年父母通常是和朋友或者配偶共度晚年。但是近年来,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如通过为赡养老年父母的纳税人减免税收的方法鼓励子女承担赡养责任。美国财政部下面的国内税务局是主要分管税务的机构,其借助在《医疗保健法》、《税法》等法律中的列举条款,规定只要纳税人进行申报证明其在赡养父母,就可以减免税收,由此减轻尽孝人的负担,并提倡更多人效仿。[7]
美国是以家庭作为基本纳税单位,国内税务局在计算出一个家庭的总收入后,会为这个家庭扣减掉因为赡养老人的那部分减免额度。一种情况是,如果家庭里的纳税人在赡养父母、配偶的父母或者两人的祖父母,并和他们同住,那么他们可以在年终的纳税表里申报减免额度,以此享受退税待遇;另一种情况是,虽然纳税人没有和父母等老年人住在一起,但只要纳税人能提供其承担了超过一半的父母赡养支出证明,也可以获得退税。在2010年的税务年度,赡养父母可以得到的税收减免额度是每位老人3650美元,在2011年,这一数字为3700美元。
(二)新加坡:激励与惩罚兼具,让老年人成为家庭的“宝贵财富”
受儒家孝道文化熏陶,新加坡大力弘扬孝道,也为此出台了很多具有倾向性的鼓励和惩罚性政策法规。新加坡在1995年颁布了《赡养父母法令》,因此是世界上最先为“赡养父母”制定专门法律的国家,据此法令,要是子女被控不遵守该法令的罪名成立,可能会面临高额罚款或者一年的有期徒刑的惩罚。
因为该法令中有许多在经济方面的鼓励性条款,在新加坡,老年人不但不会是家庭里面的负担,反而成为一个家庭的“宝贵财富”。比如和购房政策相结合,单身的年轻人若不愿意和父母同住,则不能购买或者租赁组屋,相反,如果愿意同住还能享受政府津贴。从2008年4月开始,新加坡政府规定,达35周岁的单身者如果购买组屋时和父母同住,可以得到2万新元的专门住房补贴;若子女愿意和丧偶的老人同住,那么在继承该房产时可以享受遗产税减免待遇。[8]
(三)韩国:鼓励三代同住
韩国也尊崇儒家的孝道文化,推行“家庭照顾为主,公共照顾为辅”的养老政策,所以也制定了比较细致完善的税收优惠、房产优惠等政策,以此鼓励子女赡养父母,进而推动家庭养老的发展。首先,专门为老年人养老制定法律。比如1981年6月制定了《老年人福利法》,1992年出台了《老年人就业促进法》和《遗产法》。其中,在《老年人福利法》中规定,“要保持和发展以敬老孝老为核心的家族制度”;其次,把政府提倡子女赡养父母的理念贯穿于住房、遗产继承的相关政策中。又如韩国建设交通部在2006年8月公布的《住房认购制度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那些赡养父母、岳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家庭将优先获得购房权,”[9]此规定在减轻孝顺子女的买房压力的同时,还在社会上弘扬了赡养老人的良好风气。
(四)日本:强化“家庭纽带”,提倡“一碗汤的距离”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在老年人养老的理念和政策上开始做出一些调整,逐步减轻国家的养老负担,让养老回归家庭。借助家庭和企业的力量,提倡国民自立和自助,提倡家庭成员互相扶持。上述改革和调整有如下具体的特点:第一,国家只为老年人提供社会机构难以提供的养老服务,就是说国家要承担的养老责任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第二,进一步明确地方和中央的作用分工,发挥都、道、县、市、盯、村各级政府提供养老服务的积极性,为国家减轻财政负担;第三,提高企业和个人保险缴费的额度,促使个人自立。[10]
在这些大力提倡“个人自立”、“加强家庭纽带”的法律原则指引下,“一碗汤距离”的养老理念在全日本兴起。就是说为了子女更便利地照顾老人,和老人居住地离得不能太远,以送过去一碗汤还不会凉为宜。这样,子女既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又能够方便照顾老年父母。政府在考虑城市规划和楼盘建设时,也把这一理念运用到设计当中,将适于年轻人居住的户型和适于老年人居住的户型结合到一个小区内, 从而通过建设规划“一碗汤距离”小区的方式,让“一碗汤距离”居住模式更加普及。
(五)法国:在物质保障的基础上逐渐强调子女精神赡养
一直以来,法国成年人没有赡养父母义务的观念,主要因为法国有比较完善和发达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就算是那些收入很低或者没有收入的老人,法国政府也会发放低保给他们,一般是每人每月650欧元,每对夫妻每月1000欧元(2010年),这些领取低保的人可以100%报销医疗费用,而且法国人都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个最偏爱的私人医生,以长期照料和保健自己的健康状况。总之,法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至少在经济上能为每个老人养老送终。[11]
这套制度最大的缺陷就是阻隔了父母和子女的关爱和亲情,按约定俗成的惯例,法国子女回家看望老人的频率就是一年一度的圣诞节,甚至可能吃完圣诞节晚饭的当晚就驾车离开父母,除此外,子女看望父母的次数实在屈指可数。也因此,法国对法律进行了重新修订,要求子女要更多地从精神上关爱和赡养父母,据新修订的法律规定,如果子女不和父母住在一起,则子女有义务让父母随时掌握自己的行踪,还要随时了解父母的身体状况,否则就是违法。从而通过制度约束,提倡和鼓励子女与父母之间相互照顾、相互探视和相互关怀。
(六)瑞典:更多地要求子女承担对父母的“精神赡养”责任
欧洲特别是北欧国家,由于社会养老体系比较完善,国家要求子女承担的养老责任,在经济赡养方面比较少,在“精神赡养”方面相对较多。在这些福利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中,都对子女“精神赡养”父母的内容做出了具体要求,以此最大限度地保证老年父母们晚年的幸福生活。
比如瑞典的《养老金法》中,以量化的方式具体规定子女与其父母居住的距离,每年、每月、每周甚至每日应该和父母接触的次数和时间;甚至对子女和父母交谈的忌语都做出了一定限制,这样从立法上以最大限度地来保障精神赡养的质量。[12]
二、典型国家有关子女赡养责任的政策与立法比较
(一)政策与立法的共同点:以实惠、可执行的措施鼓励子女承担赡养责任
典型国家子女赡养责任的政策与立法,普遍比较务实。一方面是多用实惠性的鼓励性措施。在这些国家关于子女赡养立法的显著特色是,他们出台了很多鼓励子女更多地赡养老人的鼓励性法规,如从购房、遗产继承等方面,来引导子女主动承担更多的赡养老人的责任;另一方面是法律的可操作性强。比如涉及精神赡养内容的规定,要求以量化的方式规定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每年、每月、每周乃至每日应当与父母接触的时间和次数;最后,还通过规定惩罚措施来保证实施效果。像新加坡在1995年颁布了《赡养父母法令》,要是子女被控不遵守该法令的罪名成立,可能会面临高额罚款或者一年的有期徒刑的惩罚。
(二)日、韩、新的理念:基于儒家“孝道文化”,一贯地注重子女赡养责任
日本在1998年修订和出台了较多的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政策和法规,最重要的新改革点在于要“加强家庭纽带”,即在个人自立的原则上,鼓励家庭成员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和保障能力,所以以本次法案为标志,子女和家庭将在日本的养老保障中被要求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从韩国、新加坡这两个近邻的养老立法情况看,他们的立法理念和动态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受儒家孝道文化影响,他们一直以来就有重视家庭养老的传统。
其实这几个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保障制度也比较完善和充实,对老年人的保障水平也是比较高的,社会和政府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支持老年人养老,所以实际上老年父母对子女赡养的依赖在减弱,但这些国家的政策法规还是很推崇子女对父母更多的赡养。而且,在这些法律条文中,也并没有强制要求子女更多地承担生活照料和精神赡养的义务,他们更多的是依据于“孝道”儒家文化传统,看重的是这一优良传统在养老保障中的天然优势和无限潜力。
(三)西方发达国家理念:在对精神赡养的追求下也开始强调子女的责任
美国《老年人法》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经历了多次修改,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次修改是1995年,美国白宫的一次老龄会议之后,确定了关于美国老年人养老保障政策的“优先项目”:“从养老社会保障、老年人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方面继续肯定并加强针对老年人的福利保障政策”,同时“鼓励子女对其父母的赡养义务和责任” 。[13]
法国的物质保障程度极高,但是近年来在老龄化的压力下逐渐暴露出社会保障成为子女和父母间亲情和关爱沟通的阻力,一般情况下,子女们仅在每年的圣诞节回去看望老年人,老年人得不到应有的家庭温暖。所以法国对相关法律做了新的修订,希望能从制度上强化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精神赡养。
(四)共同趋势:传统理念和精神需求,让子女赡养成为必然
通过对东亚、西方国家养老政策整体框架的概览,可以发现其养老保障的发展历程普遍是从“济贫救助”到“社保制度和机构照料”再到“居家和社区养老”的转变过程。东亚国家历来重视家庭保障作用,与子女赡养责任的政策目标保持了一致性。相比较,西方发达国家却经历了较大的转变,他们早期的法律多数是以大力发展社会医疗和养老保障制度为赡养老人确立可靠的经济来源为立法目标,通过实行社会共同承担的养老模式以化解老年人的养老风险,但是近年来他们逐渐发现,即使这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完全建立起来,也难以满足老人日益加剧的精神养老的要求,为此,不少国家开始在政策上进行调整,逐渐强调家庭赡养的作用,鼓励子女和老年人同住,要求子女自觉地承担对老年父母精神赡养的责任,从而使得传统家庭养老有重新回归并被逐渐重视的趋势。
三、我国关于子女赡养责任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法律历来都明文规定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新中国成立后,在1950年发布的《婚姻法》中,就有明确规定子女赡养义务的条款,第十三条写道:“父母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双方均不得虐待或遗弃;养父母和养子女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前规定” ,[14]这可以算是我国关于赡养制度最早的立法。
2001年再次修订的《婚姻法》,对子女的赡养义务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第三十条规定:“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以此表明子女赡养义务的法定地位,子女不能逃避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也能看出我国越来越重视对于老年人的赡养。
2012年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更加系统地对赡养制度做出了规定。本法明确了家庭养老的法律地位,而且规定了赡养义务人的范围、赡养包含的内容和若不履行赡养义务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也有涉及关于子女赡养义务的条款。[15]
这些法律法规对规范和约束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如都普遍存在太多的空泛词语,例如“提倡”、“政府鼓励”、“更加重视”等,这些原则性、抽象性的词语缺乏操作性,除了上述技术层面的问题外,还存在如下一些立法理念和内容方面的问题。
(一)立法理念:养老“主要依靠谁”仍没有达成共识
中国老年人的养老主要得依靠谁?其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这方面有一些规定:主要是靠家庭,赡养父母是子女的义务,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人。赡养人应当履行的义务包括对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顾和精神关照等。当然,这和我国源远流长的孝文化相呼应,自古以来,老人由子女赡养,天经地义。
但是,在如今我国所处的特殊社会历史时期,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和子女还是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现在有很多“四二一”家庭模式,一对夫妻需要对四位老人尽养老责任,不管是经济能力方面还是护理照料的质量方面,都面临着较大的压力,也产生了很多子女没有能力赡养老人的情况。当子女没有能力承担这一义务时,大家就提出政府和社会机构应该全力帮助解决,起到主要赡养作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才是“和谐社会”应有之义。所以我们的立法及修订不可避免的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子女到底应不应该承担父母养老的主要责任?
(二)法律内容:可操作性不强,精神赡养内容模糊
1.相关法律在家庭赡养部分的可操作性不强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婚姻法》虽然也有一些具体可行、目标明确、能对老年人权益保障起到促进作用的规定,例如地方政府在旧房危房改造或者公租房、廉租房分配的过程中,可以考虑给予条件合适的老年人予以优先照顾。
但是对家庭赡养的许多规定比较粗略宽泛,实际操作性不强,按此执法时不能很好地落实到位。像《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规定,子女对老年人有“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等义务,但这里面,经济供养具体是指哪些内容?是子女对老年人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仅涉及日常的衣食住行还是包含其他?具体的标准又是什么,是每月按照子女的能力还是老人的需求提供一定数额的赡养费?
2.法律在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方面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一方面,我国目前法律关于精神赡养的界定还不够清晰明确,还比较粗略。虽然《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和义务,甚至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还明确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照料老年人生活、慰藉他们精神的义务” 。[1]然而,更为具体细致的内容,比如要履行精神赡养义务的法律主体类别、履行该责任时子女的顺序、具体履行该义务的方式,都没有做出相关规定。
另一方面,精神赡养的执法难,因为很难去准确地量化子女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量或者程度,一般的物质性赡养内容比如赡养费还比较好衡量,但是诸如子女对老年人的关心慰藉、排解老年人孤独的情感抚慰,难以衡量,也就难以对子女尽精神赡养义务做一个公正的评判。所以前面我们提到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要求子女尽精神赡养责任,也很难用一个明确的标尺去衡量和惩戒子女的行为,从而法律的可执行性和权威性难以得到保证,法律在保障老年人应享有权益的效力也会打折扣。
(三)法律执行:赡养纠纷增多,老年人诉诸法律解决的却很少
在老人维权案件中,赡养纠纷等问题是一直难以解决的难题。根据《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关于老年人赡养纠纷的案件现在大约以11%的比例逐年增加,赡养纠纷的案件占到了全部涉老民事案件的13%左右,高居第一” 。[16]
即使家庭的赡养纠纷产生了,老年人的正当权益受到损害,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也很少选择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更多还是选择默默忍受。有的是出于不想和自己的子女关系搞得太僵,而不愿意采用法律手段;有的老年人是因为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认为和子女对簿公堂是件丢人的事;因为亲情这道关系,老年人维权有了很大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这些侵害老年人权益的事件不断发生。
四、发达国家子女赡养责任的政策与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尽管东亚和西方国家赡养老人的政策法规有较大差异,但是从他们的立法理念、政策规定以及改革动态中可以寻觅到许多宝贵经验,对完善我国子女赡养义务立法及有效保障老年人权益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一)在立法理念和原则方面
1.明确“三位一体”的养老责任原则
我国的养老立法首先要回答的是老年人的养老主要依靠谁的问题。目前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这方面的规定是赡养父母是子女的义务,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受两千多年的农耕经济影响,长久以来我们确实也是家庭和子女承担了主要的养老责任。但是近十多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并且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规模和结构日益小型化,加之分工的细化,家庭养老保障的功能日益弱化,迫切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来填补家庭养老的不足。养老,确实不能只依靠子女来承担责任。针对目前中国的养老现状,中国老龄学会近些年在充分地调查研究后提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养老模式来应对养老问题,即构建家庭养老、社区养老、社会养老“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居家养老新模式,在该模式体系中,家庭养老处于核心和基础地位、社区养老作为重要补充、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作为最后的保障。这种“三位一体”的养老体系,既尊重了我国注重亲情和家庭保障的传统,又适应了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新需求。这就迫切需要在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时,进一步强化立法原则和理念,注重体现多元主体的养老责任原则。
2.明确家庭赡养在养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确定“三位一体”养老责任原则,构建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辅助,政府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兜底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适时地满足新的养老需求,是我们养老的目标。但要明确的是,即使在目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政府会继续承担养老责任,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家庭仍然是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子女仍是最重要的养老主体,只是不再是唯一主体。今后的养老立法建设,要继续完善和加强家庭和子女对老年人养老保障的责任。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是大势所趋。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要求子女对老年人尽赡养责任,更多是从“精神赡养”的角度出发,我们国家立法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我们更多还是因为“未富先老”、“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的存在,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保障力度有限,因此需要家庭养老起到最核心和基础的作用,需要子女不仅仅在精神赡养方面发挥作用,也需要子女在经济赡养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3.立法建设要强化“孝”文化思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四二一”家庭结构不断强化,子女履行赡养义务,每况愈下,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在现代社会,子女赡养老人,更加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促进,甚至道德约束的作用更加重要。这样一来,可否将道德的作用法律化,也就是说,在法律条款中可以注入更多的孝文化元素。为此,建议在完善我国相关法律条款时,增加体现孝文化思想的法律条款。如可以学习新加坡的做法,若子女愿意和老人同住,那么在继承该房产时可以享受遗产税减免待遇;还可以明确规定老年人有权要求子女探望、照料等。
(二)在立法内容方面
1.进一步提升法律内容的可操作性
可以借助国外经验,对我国现有的有关子女赡养老年人法律条款进行细化研究,出台较为具体、可行的且具有直接的可操作性的法律条文,以增强法律的可执行力和实施效果。我国目前关于子女赡养的相关法律分散于不同的法律中,如《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都有相关条文,建议对这些法律按照同质性进行梳理和整合,要么归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并对之具体化,要么重新出台一部更细更具体的《子女赡养义务法》,以强化子女赡养责任的细节内容。比如,就子女的物质赡养责任,可以规定“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责任是指为维持老年人的基本的、必需的人权和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经济费用和服务内容,包括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必要需求”等。
2.增强“鼓励性条款”内容
鼓励子女承担养老责任的措施,考虑到中国最现实的住房问题,可以学习韩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在保障性住房中,对于赡养老人的子女有住房优先认购权,既可以缓解那些孝顺子女在住房问题上的压力,又可以弘扬和提倡子女多承担赡养责任的良好社会风气。另外,在税法的相关规定中做出鼓励子女多承担赡养责任的条款,应该会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如在税制改革中,可否综合多方面因素评判纳税个体的应纳税基数,而不单单看收入这一单一因素,建议综合考虑子女数、家庭开支、需要赡养老年人的个数、日常赡养老人支出等因素,对赡养老人的子女进行适当的税收减免或者税收返还。
3.提高“法律责任”及“违反事项”内容的针对性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1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这属于法律范畴中的强制性条款,但赡养人是否履行到位,是否违反了规定,法律上并没有相应的界定标准来予以判定,也没有明确的惩罚措施予以保障。为此,建议法律条款明确“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明确界定法律责任内容,明确违反事项的标准,设置更加切实可行的惩罚措施和鼓励性措施,增强法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在法律执行方面
1.明确专门的管理机构集中执法管理
我国法律体系中并没有明确地对哪个机构授予权力来保护老年人权益,即使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里也并未具体写明主要负责单位或机关,所以行使执法权的主体不明确,碰到赡养纠纷,机关之间经常就会互相“踢皮球”,这对于保障老年人权益是非常不利的。为了防止“踢皮球”现象频繁发生,建议明确执行主体,比如民政部,赋予其成为中央集权式的总揽老年人权益相关保障的权力机构,统一分管协调下面各级机关,搭建一个通畅高效的管理体制,加强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执法体系。
2.建立赡养法律援助制度
老年人因体力智力的下降、法律知识欠缺等原因,面对赡养纠纷,即使寻求法律途径,也会时常面临诸多困难,除了街道、居委会或者村居委会的协助帮忙以外,还需要我们积极建设对老年人法律援助的长效机制。首先,要把老年人常见的赡养纠纷事项设为常态化法律援助事项,一旦发生,可以简化受理流程,及时有效地为老年人提供帮助;其次,在各个居住村、街道合理规划,建立老年人法律维权联络点,并依托残联、老龄委合作设置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为老年人寻求法律援助提供方便的通道,也为开展各项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对于一些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为他们设置专门的便捷、利民法律绿色援助通道,比如为他们提供上门服务,上门了解情况,代为填写申请、代为诉讼,减少他们的来回奔波之苦。
3.充分发挥基层居委会和村委会的作用
要较好地维护《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对老年人赋予的被赡养等权益,基层居委会、村委会等组织具有天然的优势,而且还有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首先应该给予基层居、村委会资金支持,鼓励他们多对本地住家老年人的赡养情况进行关注和及时了解情况,出现不赡养老人、或者出现赡养纠纷的情况,应积极主动为其进行劝解、调解、甚至帮其代理诉讼;其次,要赋予基层居、村委会一定的赡养监督权力,增强其调解的权威性,就是说子女对于居、村委会就赡养事宜的调解结果,要充分遵从并严格执行,否则居、村委会可以向当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居、村委会也可以及时和相关司法部门联系,为老年人父母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
[1]Jacob.“Americasagingpopulation”.http://www.prb.org/pdf11/aging-in-america.2013-06-27
[2]沈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评析》,100~108页,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
[3]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相关数据,http://www.ipss.go.jp,2010- 03。
[4]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8 Revision.New York,2009:48-52,184。
[5]鲁恩艾尔维克等:《挪威和英国的积极养老观念与政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6]翟芳:《老年人精神赡养的法律问题研究》,55-6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7]杨冠琼:《当代美国社会保障制度》,37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8]代山:《新加坡:子女与父母同住可获政府津贴》,载《人民政坛》,2013(8)。
[9]凌寒之:《韩国赡养老人可获买房优惠 并可获得优先购房权》, http://tj.house.sina.com.cn/n/2006-09-15/112541203.html。
[10]孟双见、吴海涛:《日本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影响》,载《日本问题研究》,2005(4)。
[11]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2009 Ageing Report: Underlying Assumptions and Projection Methodologies, p.19. http://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publications/publication_summary14911_en.htm,2014年4月30日访问。
[12]魏知:《国外也鼓励“常回家看看”》,载《中国社会工作》,2012(23)。
[13]马歇尔·卡特等:《信守诺言——美国养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思路》,李珍等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年版),第十三条。
[15]《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一章(第二条);第二章(第十四条)。
[16]《北京法制报》,2012-11-08。
TheComparisonofOffspringSupportingobligationsPolicyandLegislationandtheEnlightenmenttoChina
YANG Cuiying MA Tao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economy and politics, different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have their own policies, legislation and ideas for offspring supporting obligation.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foreign Legisl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relevant system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mprove our offspring supporting legislation from policies, regulations and other aspects.
old-age security,offspring supporting obligation,regulations,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H)
*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12JZD035)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居家养老服务筹资模式创新与调查实证研究——基于规范子女赡养责任与义务的视角”(13PJC054)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