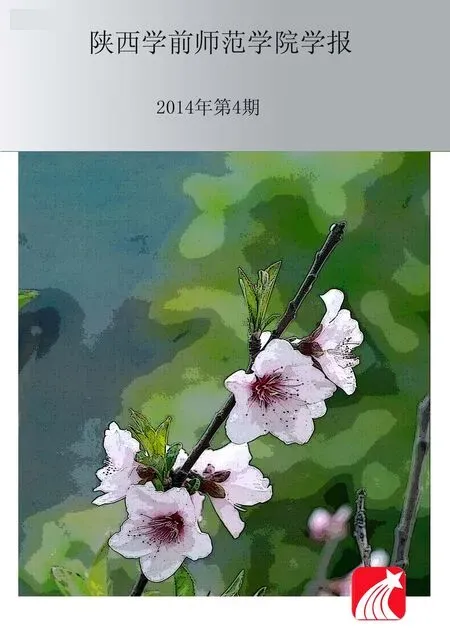“人欲”因素对小说功能的影响
崔明明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一、小说对“人欲”的关注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8人性的本质是什么?向来是中国哲学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2]60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直至明清,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中, 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未曾间断。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人性问题,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人欲是人性的组成部分,“人性善”与“人性恶”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人欲的讨论。
文学界对“人欲”的评判不一,理欲之说肇端于先秦,诸子多有论及。其中,尤以儒道两家言说居多。但当时所论多以欲为中心议题,或言节欲,或言导欲,或言寡欲。[3]14而何为人欲?人欲即人作为生命个体为生存、发展所有的希望、盼望及想得到某种东西或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人欲是人本能的释放,构成人类行为最内在与最基本的根据和必要条件,能否得到合理引导关系重大,叔本华曾指出欲望过于剧烈和强烈,就不再仅仅是对自己存在的肯定,相反会进而否定或取消别人的生存,因此人欲需要科学的调控,而这离不开文学的引导与反映。
小说是一种特定的本文。“本文”二字并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云遮雾罩”,相反,它倒是最“形而下”的。在语言学中,“本文”指的是构成一定话语的一系列词或者也可以说是这一话语的文献。[4]78小说比诗歌散文晚熟,略早于戏曲,最初出现之时属于底层文学,对文化的观察视角较为局限,但作为街头巷语,娱乐性较强,极少有国家道义的负担,能较为真实的反映它所选取的文化精神和涉及的社会内容,有较强的自主性,且并未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与限制。
小说对人欲的关注是主动的,这是小说文体特征所决定的。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写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虽说小说有虚构成分,但也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扎根于民族文化最深处的文学体裁,小说对社会生活有很强的依赖性,随着题材的不断丰富和观察视角的不断多样化,尤其是对人的关注,促使小说功能不断发生着变化。
二、先秦至唐朝时期人欲因素对小说功能的影响
受农耕经济形成的宗亲思想影响,中国自古就有压抑人欲的传统理念,古有“三从四德”,后有朱熹“存天理,灭人欲”,从道德的打压到文学的制衡,古代对人欲的正视、肯定经过了漫长的过程,而随着“人欲”得到肯定,“人欲”对小说的功能转变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中国,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成为古典小说叙事的源头,孕育着小说的艺术因素,为小说的形成准备了条件。细致地分析,史学对小说的强势渗透,一方面与中国发达的史官文化颇有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历史与小说客观发展的产物。[5]22“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先秦诸子重道而菲薄小说,认为小说是琐屑浅薄的言论与小道理,这就定义了小说的“小”,也点出了这个文体的最初特征。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最早的小说形式,如《山海经》和一些寓言。
秦帝国时法家压倒诸子,法家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漠视以及对个体人格的鄙夷,决定了它根本无力承担其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的重任[1]3汉武帝时,儒家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的王权相结合,儒家价值观念转化成具体的政治操作模式,个体势必重新寻找其生存的意义和价值。魏晋时期士人放浪形骸,有独特的精神风度,玄学盛行,使人生价值在玄风中回归,确定生命的价值。汉代时期小说地位有所提高。班固《汉书·艺文志》提到“列九流十家,小说家附列于诸子之末”。《史记》开创了我国的纪传体史学,它关注人,并以人物为中心,通过人物的活动说明历史,为小说在情节书写和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提供经验。小说包括《淮南子》、《列女传》、《越绝书》等,已关注人及情节,人欲在小说中渐渐萌发。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小说的雏形: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这个时期,小说与“史”在理论上虽然可以区分,摆脱了史家的附庸地位,但未获得文体上的独立,艺术上“粗陈梗概”,缺少写作技巧,更多的还是实录,只能说是一个准文体概念。
这段时间,小说主要具有补正史阙、伦理教化和娱乐功能,在文学中的地位有所提高,摆脱了坊间传说的范围,开始具有初步文体特征,并确定了主要的发展方向,即注重以人为关注主体。
(二)魏晋南北朝至唐时期
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初具规模,关注人及其性格描写,确定了人在小说中的主体地位。曹植在《与杨祖德书》中写到:“街谈巷语,必有可采。”刘勰《文心雕龙》谈到小说时指出“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虽指出小说是稗官所收集整理,但正视了小说的功能。而《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相对于前一发展时期,它更多的表达了个人的情感。在唐朝,小说才真正的具备了小说要素,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古典文言小说的成熟。
“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 唐代经济较为繁荣,文学较快发展,尤其是唐传奇的盛行。人们开始有意创作小说,出现虚构技巧,传奇体小说促使小说趋于成熟,形成了独立的文学形式,使小说创作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艺术活动。除了补正史之阙和崇艳猎奇外, 从唐传奇开始, 小说的劝戒功能开始被重视。唐传奇最大的特色就是虚幻,而佛道文化的发展,为唐传奇提供了很好文化题材。唐传奇创作出了很多在当时列为大胆前卫的作品,如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歌颂了对爱情的追求,作者对人欲的肯定,赞扬了人的主动性,出现了如《柳毅传》之类的人仙恋,将主人公设置为神仙,神通广大,且无人间的道德束缚,表达了将人欲从重重束缚中解脱,并加以正视的欲求,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人欲的探视,使小说除了娱乐功能外,更有启蒙意义,但受到时代和小说交流过程中的社会制约,人欲因素并未引起思想小说界的革命。
三、宋朝至清朝时期人欲因素对小说功能的影响
《世界日报》曾报道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人类所有行动是受十五种基本欲望和价值观驱使,包括好奇心独立等。宋朝至清朝期间,随着白话小说的增多、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过渡及章回体小说出现和兴盛,人欲作为小说的因素对小说功能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一)宋元时期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期,理想主义和历史主义盛行,理学家自觉地将个体生命的意义纳入到人类整体命运的视野中考察。[1]4宋代是小说的发展转折期,特征就是出现了白话小说。从宋代开始,以文言短篇小说为主流逐渐转为以白话小说为主流,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市民阶层的崛起,使小说越来越关注人,并使写作重心下移,渐渐转变了小说的社会功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井文化的兴起,宋元时期出现了话本小说和演绎小说,话本的诞生更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以《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为例,它是追求美好爱情并展现妇女民主意识觉醒的话本,通过塑造为追求爱情而极具个性的周胜仙形象,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并具有更多的世俗性,更容易打动读者,增强教化功能,延续了唐传奇的文学精神,并有所拓宽。宋结束了晚唐五代的分割与战争,新朝带来的和平与安定,使人们更注重追求人生价值。面对历史教训和内忧外患的形势,宋代人表现更多的是理性主义,朱熹的程朱理学出现并盛行,理学勃兴归根到底是探索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寻求自身价值中营造了浓郁的人文氛围。
唐代的俗讲和宋元的说话向大众传输了文学,而随着文化市场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已形成规模,重商思潮和尚利好货的倾向促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发展和满足,市民文化的普及与文化娱乐使文人走向市场,接受并创作通俗文艺来迎合市场。以宋元白话形式写成的话本,以平民生活为主要对象,促使小说的关注中心发生转移,丰富了小说的题材,扩大了写作的视野,为明清小说的繁荣打下了基础。随着话本的发展、兴盛,元朝时期更加肯定文学的世俗性,而元朝以后,对人欲世俗性的认可和肯定进一步深化,并走向以通俗小说为主体的新阶段,创作主体也由群众为主转变成以文人和群众创作相结合,提高了话本的文学性和艺术性。[6]17
元摆脱了宋文学以理智态度自我敛约的特点,走向情感的活跃和解放,更加肯定人的欲望的世俗性,并通过对人欲的注重,增强自身的说教、认知和娱乐功能,以《娇红记》为例,作者以自然情性排斥非人性教条压迫的作品,展现出深层心理上的自我觉醒,强调了小说的形象感染力和实用性,突出文本的说教和娱乐功能,促使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
(二)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以“权”为核心标志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念逐渐走向崩溃。明清之际的政权更迭,反对专制独裁与反对压抑情感形成了强烈的启蒙倾向。嘉靖时期《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流行,标志了小说的再度兴盛。[7]261明末至清初,再次受到封建正统文化的反拨和压制。清代,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思想家都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抛弃了晚明文学的表现自我、个性解放、率真浅俗的理论观念。在清中叶,文学领域也呈现出类似晚明的一股思潮,反传统,尊情,求变,思想解放。[8]203这些思潮使得俗文学得到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诗文等获得同样的重视,也使小说的题材不断增多,出现世情小说、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讽刺小说、侠义公案小说等。明清小说批评家对小说游戏娱乐作用的认识大致有三种:其一是寄托情思,发抒郁积;二是自娱娱人;三是另备一格,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欣赏要求和审美需要。[9]63这种分类充分显示了人欲因素对小说的影响。
明前期一百年受到专制文化压制,明中期解放个性,明朝中期以后,中国社会正孕育着巨大的变化,在思想领域表现为反抗思潮和极端情绪,徐渭提出“本色论”,喜爱民间文学,创作了《四声猿》表现反抗精神,而李贽也倡导、宣扬俗文学,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并提出“童心说”,鼓励文学创作的人文意义。小说理论家与小说作家为了抬高小说的地位, 更加关注生活中人们的需求与抗拒,通过对人的多方面观察,将人的特性带到小说中,有意识地刻画立体的人物形象,有意识地加强了小说的劝惩功能。积极表现自我的创造精神在晚明达到顶峰,尤其是阳明文学把内在的良知并和外在的天理,在理论形式上把确认真理的权利交还给自我,更突出审美功能。明代掀起“拟话本”的高潮,以“三言”、“二拍”、“一醒”为代表,也促使古代白话小说的第一个高峰出现。而人欲的复杂性大大提高了小说的思辨功能,也对小说提出了新的要求。冯梦龙“三言”把“情”与“欲”放在“理”或“礼”之上,要求“礼顺人情”;《金瓶梅》是世情小说的顶峰之作,在《金瓶梅》中,作者以清河县为例,运用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平凡却不普通的世俗生活画面,通过对官宦、商人、平民等各阶层人们生活场景的描写,正面描绘了人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把人欲作为主要描写对象,肯定人欲并将它放在社会操控者的高度,对读者进行劝诫,除此之外还有《醒世姻缘传》。
清代由蒙古族统治,文化粗狂外向,减少了封建文化对人欲的压制,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增大了作者的能动性,把人欲正式的加到文学因素中,并对人欲进行不同层次的阐释,促使小说不仅具有叙事、补充历史、思辨功能,还具有审美、教育功能,启人心智,协调欲望,使小说的启蒙、教育功能走在了文学的前端,如《歧路灯》、《玉娇梨》等。清代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高潮,其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代表着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的第三个高峰。作者将人物形象仙鬼化,扩大了人物的刻画空间,赋予形象更多的人情欲望,在仙鬼的背后展现人性。除此之外,受各种思想潮流的影响,有些小说未能正确把握人欲因素,如清末侠邪小说《品花宝鉴》、《海上花列转》等,在宣传人欲方面具有一定的极端倾向,走入了误区。
总之,“小说”由概括故事性的传闻到真正具有文本意义的小说作品,从集体编纂到个人独立的案牍创作,从借史演绎到关注人生,随着文人创作高水平的自我要求与小说发展的内在规律,小说对人物及其人性欲望的挖掘更深一层,人物形象也越来越趋于个性化,突出了对人欲的张扬与正视,使作品更有深度,更有意蕴,从而推进古代小说不断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2]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 卞良君,李宝龙,张振亭著.道德视角下的明清小说[M] .长春市: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
[4] 孟悦.小说功能内外观[J] .上海文学,1986(08).
[5] 梁爱民.小说观念与文化精神[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
[6] 纪云华,杨纪国主编.中国文化简史-元明清卷[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7]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8]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9] 范道济.古代小说功能论概观[J].嘉兴学院学报,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