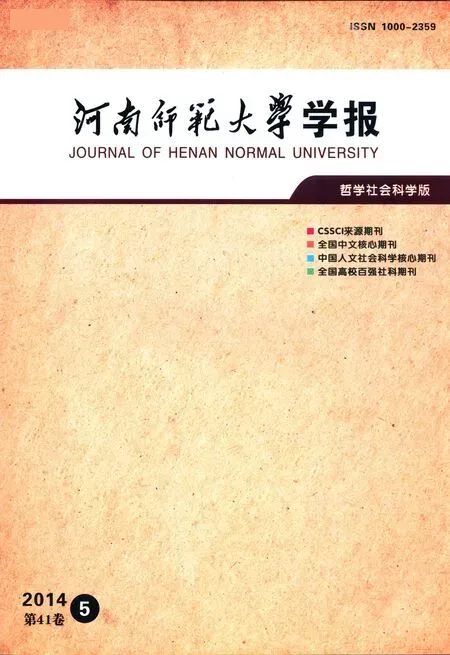从创作角度看清代至民初文人对元稹诗歌的接受
周相录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二十年之后,明崇祯九年,也就是清崇德元年(1636),清太宗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清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一举攻占明朝首都北京,明朝宣告灭亡。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大举入关,打败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同年,清顺治帝迁都北京,清王朝取代明王朝,成为新一轮的天下霸主。入关后的二十年里,清朝先后灭掉了大顺政权、大西政权与南明政权等,基本统一了全国。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清帝宣布退位,清朝结束自己的统治,整个清朝递传十二帝,历时296年。在清朝政权灭亡之后,仍有一些清朝遗老活跃在民国初年的文坛上,政治上他们已难有所作为,文学上却能假往日之余威,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当时的新文学发展虽然已经如火如荼,但旧文学仍有余烬散发着微弱的温热。为体现历史的延续性,我们将民国初年的一二十年时间与整个清代划分在一个时段之内。在约一千年的元稹诗歌接受史上,清代至民初是最后一个时代,也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时代。这一时代,如明代王世懋“生平闭目摇手,不道《长庆集》”[1]一样对元稹作品的偏激批评声相对少了,喜欢在创作过程中模仿追和元稹作品的人多了,向元稹诗歌学习的面广了,元稹诗歌对清代至民初的诗歌产生的影响大了。由于距今年代甚近,清代至民初存世文献浩如烟海,分藏天下,清理出相关文献极为困难,梳理相关文献也相当不易,而且,元稹接受史至今尚未得到根本的重视,清代至民初元稹诗歌接受史至今尚是一个没有人专门涉足的研究领域。没有相关研究成果可资借鉴,绝对全面的搜罗相关文献又有些不太现实,我们只能在尽可能多地占有相关文献的条件下,勉力讨论有关清代至民初元稹诗歌接受史上的一些问题。为使讨论的问题相对集中,本文仅从清代至民初诗歌创作的角度,探讨清代文人(包括皇帝)对元稹诗歌的接受问题。
一、文人接受元稹诗歌的方式
后世文人接受前代作家作品的影响,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选择与再创造的过程。在这个主动选择与再创造的过程中,接受者的审美趣味、文坛的潮流动向甚至所属时代政治经济的风云变幻,都有可能影响到后世文人对前代作家作品的接受。这正因此,不同时代的文人,对前代作家作品的接受方式、接受特点等都有可能存在差异。清代至民初文人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接受元稹诗歌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用元稹诗歌之典
用典,也就是用事,是古代诗歌写作中一种常用的重要修辞手法,即引用前代典籍中的故事或词句,以丰富而含蓄地表达有关的情感或思想,有时也具有炫耀写作者自己学养的作用。这是一种最直接、最外在的对前人诗歌的接受方式,也是最浅层次的对前人诗歌的接受方式。用元稹诗歌之语(词语或句子),如黄之雋《无题代答(其三)》云:“谁能夜夜立清江?暂寄华筵倒玉缸。晓色入楼红霭霭,残灯无焰影幢幢。同心梔子徒夸艳,並蒂芙蓉本自双。不为旁人羞不起,日高方始出纱窗。”[2]卷10该诗第四句用元稹《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之首句:“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3]606该诗第七句用《会真记》中崔莺莺诗之第三句:“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3]1519用元稹诗歌之事典,如乾隆《蕴真堂》云:“乐善远刘苍,奉诚近礼王。”其自注云:“乐善园旧为康亲王别墅,乾隆戊戌,复王封号为礼亲王。是园盖取汉东平王苍‘为善最乐’语意名之,岁久日就荒圮,亭榭无存。王以其地临长河岸傍,为御舟往来所必经,奏进求充御园。按《唐书·马燧传》载纳其安邑里旧宅为奉诚园之事,故元微之《奉诚园》诗有云:‘萧相深诚奉至尊,旧居求作奉诚园。’”[4]五集卷32引其词语,用其事典,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引用者对被引用者作品熟悉与喜爱之程度。在清代之前的诗歌创作中,用元稹诗歌之典的例子就已较多地出现;在清代至民初的诗歌中,用元稹诗歌之典的例子更是触处可见。
(二)续元稹之诗
所谓续其诗,就是指后世文人喜爱元稹的诗歌而又不满意或以为元稹原作意犹未尽,或另可做其他之演绎以申述己意,而另行接续以抒写自己之体悟或认识。与陈子龙、李雯并称为“云间三子”的宋征舆《酒后续元微之句》云:“除却巫山不是云,落花时候每思君。沙盆潭水流春色,红泪偏沾白雪裙。”[5]卷14元稹《离思诗五首》(其四)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3]1436宋征舆诗之首句即元稹诗之第二句。元稹之诗乃其与自寓性小说《莺莺传》女主角“崔莺莺”分手之后而写,主要表达自己经历一场“思想深处的革命”之后,对一般的诱惑具备了一定的“抗干扰”能力,一般的诱惑不再能够让自己失守“原来的阵地”。钱钟书先生曾云:不见可欲,不可谓贞。吃过山珍海味、深明养生之道之后,不会再一见美食就垂涎三尺了。而宋征舆之诗,则直喻所写之“君”,乃巫山之云,令人一见即难以释怀。一得道语,一深情语,黑白雅郑,迥然不同。宋征舆之诗,虽然也引用了元稹的一句诗,但与一般的引用明显不同,重在接续元稹原诗句而申述自己之新意。再一种情况,是不用元稹之诗句,直接在元稹原作之基础上,接续演绎。如毛奇龄等有《联续元稹诗三十韵一首》,毛奇龄序云:“汝南蒋亭阅唐元稹《会真诗》,深鄙其事,並笑樊川所续不足,因谓元稹非续诗也,即其诗耳,杜则真貂之末矣。拟晚食外重戏续之。”[6]卷150不满元稹之旧作而再续之之意甚明,无须再赘言之。此类诗作虽然数量不甚多,却是清代至民初出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接受形式,它表明对元稹诗作的接受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三)效元稹之诗体
效前人诗作之诗体,是后人对其眼中的前人成功之作或特异之作进行有意识的效法与模仿,是后人学习前人诗歌的一种重要方式。前代成功的作家,往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特色,如杜甫之“沉郁顿挫”,孟郊之寒瘦,韩愈之怪奇等。元稹之诗,以工致密丽见长,没有白居易诗歌那么平易,但后人往往将元稹与白居易并称,而通谓通俗晓畅之诗人。清代至民初拟元稹之体的作品也不甚少,如乾隆《古筑城曲效元微之体亦反其意也兼用其韵》与《拟元白诗二首并用其韵·元拾遗微之(种竹)》、顾景星《除夕效元微之体》、王世禛《代赠戏仿元白体》、王文治《拟元微之体二首》、王昶《秋夜寄晓征于京师效元白体》等。元稹《种竹》诗云:“昔公怜我直,比之秋竹竿。秋来苦相忆,种竹厅前看。失地颜色改,伤根枝叶残。清风犹淅淅,高节空团团。鸣蝉聒暮景,跳蛙集幽栏。尘土复昼夜,梢云良独难。丹丘信云远,安得临仙坛?瘴江冬草绿,何人惊岁寒?可怜亭亭干,一一青琅玕。孤凤竟不至,坐伤时节阑。”[3]47乾隆《拟元白诗二首并用其韵·元拾遗微之(种竹)》云:“堂下有竹埭,尚缺五六竿。却嫌少清听,岂虑碍远看。趁此膏雨足,兼之暑未残。移來青山曲,随见绿阴团。斜拂凌云松,低临溘露栏。汀芦与池苇,欲效良云难。不肯裁为箫,空期凤下坛。不肯持作钓,富春江上寒。愿学兰田上,种出千琅玕。劲节从此申,生机实未阑。”[4]二集卷10虽然元稹与乾隆之作存在其他方面的明显不同,但用语的浅易明白与用韵的高度一致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再考虑到乾隆的许多诗作滞涩难通,喜“掉书袋”,更易看出由于该诗是“效”元稹之作,所以风格比较质朴流畅明白。
(四)和元稹诗之韵
唱和诗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形式的诗歌,它由一唱一和、一唱多和及酬和他人原唱、酬和自己旧作几种形式。如果从原唱与酬和用韵之关系看,唱和又可分为和意不和韵的一般唱和(和意不和韵)、依韵唱和(原唱与酬和同在一韵)、用韵唱和(原唱与酬和不仅同在一韵,而且韵字相同)、次韵唱和(原唱与酬和同韵部、同韵字、同顺序)。中唐时期的元稹与白居易,是中国古代唱和诗发展史上两个最为关键的人物,唱和诗发展至元白,在体制上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原来的主要和意不和韵发展到以和韵为主。元白之后的唱和诗,又演化出追和古人诗作的一种新形式。清代追和元稹之诗作,和韵追和占据了其中绝大多数。而在和韵追和之中,次韵追和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在追和元稹《生春二十首》时,我们发现,清代至民初十八人二十二次酬和,其中十三人十六次采用次韵追和的形式。尤其是乾隆皇帝,更是一人四次追和元稹《生春二十首》,每次都是次韵追和二十首。有些诗歌,如乐钧《山居野兴用元微之放言韵五首》、彭昕《除夕感怀用元微之放言诗韵》等,因其与元稹原诗之内容基本没有联系,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唱和诗,而只是借用了元稹诗歌的用韵而已,但仍采取次韵追和的形式。文人编纂诗选,往往重视所选作品内容上的雅正,相对忽视艺术技巧的考量,而追和前人诗作,则考虑更多的是诗歌的艺术技巧,因为唱和这种创作方式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原唱者与追和者之间相互竞赛的性质。
(五)反元稹诗歌之意
所谓“反其意”,就是不赞同元稹在诗歌中表达的对某事物的看法,有意在追和元稹作品时与元稹唱反调,以显示自己较元稹的高明之处。续元稹之诗,也表达与元稹原作不同的情感或思想,但重在接续原作基础上的“异”,而反元稹诗歌之意的作品,则一开始便与元稹原作“分道扬镳”。此类作品,清代至民初的诗歌中,数量并不太多,我们只发现了顾景星的《改元稹将进酒歌有序》,但在乾隆的追和诗中则出现得比较多。乾隆反元稹诗歌之意的作品有《反元稹将进酒乐府》《古筑城曲效元微之体亦反其意也兼用其韵》。除此之外,乾隆还有反其他唐代诗人的一些作品,如《反白乐天放言句》《反白居易阴山道乐府》《再反白居易阴山道乐府仍用其韵》《反韩偓斗鸡诗》《反李白丁都护歌》《反韦应物采玉行即用其句二首》《咏金廷标四皓图反杜牧诗意》。作为皇帝——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裁判者,特殊的身份往往带来盲目的自信,自以为作为一般文人,识见不如自己高明,故多有与前人“唱反调”之作。如元稹《古筑城曲五解》:“年年塞下丁,长作出塞兵。自从冒顿强,官筑遮虏城。”“筑城须努力,城高遮得贼。但恐贼路多,有城遮不得。”“丁口传父口,莫问城坚不?平城被虏围,汉斫城墙走。”“因兹请休和,虏往骑来过。半疑兼半信,筑城犹嵯峨。”“筑城安敢烦,愿听丁一言。请筑鸿胪寺,兼愁虏出关。”[3]699乾隆反元稹原作之意而创作的诗歌云:“伊犁无绰罗,驻我镇抚兵。耕牧有余闲,命之坚筑城。”“守望不可阚,其实非防贼。何曾捉民丁,事半功倍得。”“游辞惯腾口,问汝复能否?哈萨及布鲁,岁岁请安走。”“贡马敢称和,往来城下过。将军坐令拜,虎帐高峨峨。”“抱杵事颇烦,加赐颁德言。室家有恒产,东望玉门关。”[4]三集卷33元稹谓辛苦“塞下丁”以筑城,其实不是消除边患的根本措施,治标不治本,根本措施是修明政治,增强内力,不筑城而国防自安。这种认识,虽然不能算错,但确实是老生常谈,有些空洞,不能有效解决某个当下面临的迫切问题。而乾隆之追和,则是基于皇帝之立场,为边塞筑城进行辩护,谓新疆边地筑城,乃利用“镇抚兵”之“余闲”,并没有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反而保证了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定。
当然,在极为复杂的现实面前,理论的概括梳理往往捉襟见肘,很难完全与纷繁的事实若合符契。虽然如此,理论的概括梳理仍是必要的,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缤纷的现实。在清代至民初文人的实际创作中,对元稹诗歌的接受并不是这五种方式都相对独立的存在,而是存在着在效其体的同时又与元稹诗歌存在唱和关系,存在着续其诗作的同时也受元稹诗歌影响等相交叉的情况。这种接收方式的多样性存在,表明清代至民初文人对元稹诗歌的接受,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又从一个侧面标志着清代至民初对元稹诗歌接受达到了历史上的高潮时期。
二、文人接受元稹诗歌的三个时段
清代至民初的历史,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第一时期即清前期,自清朝建国至康熙退位,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个皇帝,是清帝国自建国走向兴盛的时期;第二时期即清中期,自乾隆登基至嘉庆退位,历经两朝,是清帝国自兴盛走向衰落的时期;第三时期即清晚期至民初,自道光登基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个皇帝与民国,是清帝国衰落并最终走向灭亡的时期。每一时期的时间跨度相差不大,都在八十五年至一百年之间。
(一)清前期
清代最早对元稹诗歌表现出较大兴趣、较多地模仿效法元稹诗歌的诗人是降清名臣钱谦益。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苏州常熟县(今江苏常熟市)人,明末清初文坛领袖,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其诗歌作于明朝者收入《初学集》一百一十卷之中,入清之后所作诗歌收入《有学集》五十卷之中,晚年所作诗歌另收入《投笔集》二卷之中。乾隆时,钱谦益之诗文集曾一度遭到禁毁。钱谦益模仿效法元稹诗歌之作,主要有《仿元微之何处生春早二十首》《和元微之杂忆诗十二首》。元稹《生春二十首》描绘了不同时空背景(云色、漫雪、霁色、曙火、晓禁、江路、野墅、冰岸、柳眼、梅援、鸟思、池榭、稚戏、人意、半睡、晓镜、绮户、老病、客思、濛雨)下的烂漫春色,取材较为广泛,触及到了现实生活的诸多方面,从社会下层到社会上层,从晴日到雪天,从户内到户外,从闺房到旅途,分层设色,极力描摹,为读者呈现出了一幅春日的多彩画卷。而钱谦益的效仿之作,则将笔触集中在了一个狭小空间的上层女性身上,刻画其美目、巧笑、眉黛、鬓发、靥辅、好口、皓腕、素足、翠袖、罗带、穷袴、锦被、宝镜、角枕、帘幕、画舫、小院及睡起、新浴、刺绣时之神态举止,给读者勾画出了一幅上层社会女性生活的百态图,刻画细腻,虽无梁陈宫体之色情暗示,但风格工致而绮艳,具有元稹诗歌的部分神韵。《和元微之杂忆诗十二首》与元稹《杂忆诗五首》一样,每首第三句均以“忆得”开头,而且用语、格调都与元稹诗极似,是清代至民初学元稹而深得其神髓之作。
钱谦益《仿元微之何处生春早二十首》,田甘霖写有酬和十章。田甘霖是明末清初湖北容美土司最为知名的诗人,田玄第三子,字特云,号铁峰,1657年袭容美宣慰使职,康熙十四年病逝。田甘霖之十章和诗,与钱谦益诗中的十首所写对象完全相同,只是规模稍小而已。表面上看,田甘霖只是酬和钱谦益之诗而已,但钱谦益之作既然为追和元稹而作,田甘霖之酬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追和元稹,只是田甘霖对元稹诗歌之接受,有赖于钱谦益之文坛影响而已。钱谦益追和元稹诗作,同用一东韵而韵字及其次序俱有不同;田甘霖酬和钱谦益之作,亦采取同样的唱和方式。钱谦益与田甘霖都把写作的重点放在了描绘的细腻与工致上,而在用韵上并未着意用力(采用一东韵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元稹原作每首俱以“何处生春早,春生□□中”开篇,必须押一东韵)。
追和元稹《生春二十首》者,还有归庄。归庄字尔礼,昆山(今属江苏)人,明代散文家归有光之曾孙,明末诸生,诗多奇气。归庄《和元微之生春二十首》,分咏亭馆、田野、漁艇、佛屋、紫陌、绣户、宫禁、边塞、大海、深谷、远眺、独坐、书幌、染翰、半醉、残梦、花信、鸟语、棋局、诗句,所写对象或大或小,或远或近,无不牢笼笔下。而且,归庄之追和,亦全部依次用“中”、“风”、“融”、“丛”,属于次韵追和。无论是题材还是用韵,在清代追和元稹《生春二十首》的作品中,都最得元稹原唱之遗韵。
除《生春二十首》之外,清初诗人追和最多的元稹诗歌,应是《表夏十首》。严熊有《追和元微之表夏十首》、高士奇有《记夏初景物用元微之表夏十首韵》。严熊与高士奇之追和,俱次元稹原唱之韵,但对仗不如元稹工稳,绘景不如元稹原唱之工细,二人酬和之作之着力点或在用韵之讲究上。元稹《生春二十首》,用二十首五律刻画春天之景,工致密丽,穷形尽象,而且全部依次用相同的四个韵脚,写作难度很大;元稹《表夏十首》,用十首五律刻画夏天之景,亦细密铺排,多角度描摹,而且全部用相同的四个韵字。严熊、高士奇等人追和此类诗作,显然有与元稹一较诗艺高下之用意在。
清代追和元稹诗歌,出现了一个前代未曾有过的新现象,那就是对元稹乐府诗的追和。如顾景星《改元稹将进酒歌》《花鸟使拟元稹体上家吏部尚书张受先员外》。乐府诗的酬和或拟作,作者的着力点主要不在诗艺的锻炼上,而在识见的高下优劣上。如《改元稹将进酒歌》序云:“元稹《将进酒》云云,愿主回恩以下,托言不纯,非风人忠厚之旨,因改之。”[7]卷2当然,那只是后代文人自以为识见超越了元稹,至于是否真的超越了元稹,那倒未必。
钱谦益、田甘霖、严熊、高士奇、顾景星等对元稹诗歌的接受,属于较为显明的接受,除此之外,还有虽不甚言明而实际对元稹诗歌却存在潜在的继承或效仿的例子。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崇祯间进士,明末清初的诗坛巨匠之一,娄东诗派开创者。吴伟业长于七言歌行,初学“长庆体”,后自成一家,后人称为“梅村体”。吴伟业曾谦虚地说:“一编我尚惭长庆”[8]卷10,表达自己对元稹、白居易及其长庆体的仰慕与服膺。吴伟业《永和宫词》《圆圆曲》《楚两生歌》等,与元稹《连昌宫词》、白居易《长恨歌》颇属同调。清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之九)曾云:“草堂乐府擅惊奇,杜老衰时托兴微。元白张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学妃豨。”[9]卷五元白张王乐府不求外表与古乐府相似,而追求内里与古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基本创作精神的汇通。不亦步亦趋的模仿,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学习,因此,清初最得元稹之真传而能变而通之者应是吴伟业。
(二)清中期
清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是清代第六位皇帝,掌控清朝六十余年,开创了所谓的“盛世”。虽然是皇帝,却有那么点儿“不务正业”,喜欢诗歌创作,在《题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自豪地宣称“平生结习最于诗”[3]四集卷25,在《题玉澜堂》中自谦地说:“笑予结习未忘诗”[3]五集卷70。乾隆一生创作宏富,登基之前创作的诗歌收录在《御制乐善堂全集》(卷14-卷30)之中,登基之后创作的诗歌收录在《御制诗集》(初集44卷、二集90卷、三集100卷、四集100卷、五集100卷)之中,退位之后创作的诗歌收录在《御制诗集》(余集20卷)之中。乾隆一生创作的诗歌作品的数量,历来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大约总数有四万三千多首,这个数字是不会有大问题的。在这数量众多的诗歌中,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即是模仿、追和唐代诗人的作品。而在对唐代诗人的模仿、追和中,对元稹诗作的模仿追和又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点。
清代中期对元稹诗歌的接受主要集中在乾隆时期,乾隆时期对元稹诗歌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乾隆对元稹诗歌的特别偏好与乾隆君臣间以唱和形式对元稹诗歌的追和上。除用元稹之语典、事典之类的作品外,能够直接体现乾隆对元稹诗歌接受的模仿、追和之作,主要有:《反元稹将进酒乐府》《夜合用元微之韵》《生秋诗用元微之生春诗韵有序》《杂和唐元稹东川诗四首有序》《拟元白诗二首并用其韵·元拾遗微之种竹》《古筑城曲效元微之体亦反其意也兼用其韵》《生春二十首用元微之韵有序》《生夏二十首仍用元微之生春诗韵有序》《生冬二十首仍用元微之生春诗韵有序》《有鸟二十章》等。在乾隆的这些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元稹《生春二十首》的反复追和,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乾隆各创作二十首,模仿元稹之诗歌体式,学习元稹之写作技法,步趋元稹之用韵。与元稹原作不同之处,主要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帝王身份与为文造情带来的生涩之感。如此大规模地模仿、追和元稹之诗歌,不但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创造了元稹接受史上一个辉煌的记录。
不但乾隆模仿、追和元稹诗作创造了一个记录,而且乾隆朝大臣酬和乾隆模仿、追和元稹之诗作,也创作了一个历史记录。在此之前,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有出现过君臣唱和同时也是共同追和元稹的例子。清代乾隆时大臣彭元瑞有《恭和御制生春诗元韵》、钱陈群有《恭和御制生春诗二十首元韵》及《恭和御制生夏二十首仍用元微之生春诗韵元韵》。彭元瑞的酬和是一种选择性酬和,只写了八首,而钱陈群的酬和则规模宏大,两次酬和各创作二十首诗歌。《清史列传》卷一九《钱陈群传》载:“三十九年,卒。谕曰:‘在藉加刑部尚书钱陈群,老成端谨,学问渊醇。自康熙年间通藉词垣以后,久直內廷,……并时以御制诗章,寄令赓和。儒臣老辈中,能以诗文结恩遇、备商榷者,沈德潜故后,惟陈群一人而已。’”[10]1446《清史列传》卷二六《彭元瑞传》载:“元瑞少负隽才,多读书,工词翰。通藉后,以文字受知两朝,入直南书房,垂四十年。……所为文章,自敷陈典礼,歌颂功德,恭和宸章,申谢恩命,及奉敕跋题内府珍藏卷轴。……其恩遇优渥,罕有伦比。”[10]2004乾隆是皇帝,作诗免不了带有君主的口气;彭元瑞、钱陈群是叨陪圣上、仰人鼻息的臣子,多少有些唱颂歌的意味,尤其是精于谄媚、常常谄媚的钱陈群,这方面的气息明显要浓得多。国家“全盛”之时,皇帝以诗润色鸿业,臣下以诗希求恩宠,各取所需,而少关感发,写诗至此,就很难产生鼓动读者心旌的作品了。
君臣唱和之外,值得关注的地方是追和元稹组诗成为一种风气。程梦星《解秋次元微之韵十首》、刘墉《效白香山何处春深好二十首》、刘秉恬《生春诗八首》、洪亮吉《消寒七集招同人集朝华阁分赋长庆集生春诗四首》、庄述祖《生春诗咏纸墨笔砚》、尹嘉铨《生春四首》、汪学金《生春分韵五首》及程晋芳《效元微之解秋十首》《效元微之表夏十首》《效元微之遣春十首》。虽然刘秉恬、尹嘉铨与乾隆君臣之所作,俱受元稹诗作之启发,但刘、尹之作似与乾隆、彭元瑞、钱陈群君臣无甚关联,因为刘、尹之作不仅用韵与乾隆君臣之作无任何关系,体式内容上也无多大关联。至于程梦星、刘墉、程晋芳所作,不在乾隆君臣感兴趣的范围之内。这些诗人对元稹的接受,应该代表在野诗人对元稹的接受。
(三)清代后期至民初
道光及其以后,清代诸多社会矛盾日渐激化,国势日衰,再也没有出现如乾隆一样的“好文”之君,而且又面临着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瓜分大清帝国疆土的危险,朝廷君臣之间通过唱和活动模仿追和元稹诗作的现象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模仿追和元稹诗作的活动并没有停止,而是表现为零星的、小范围的、私密性的模仿追和。邓廷桢《和钱心壶给谏生春诗十二首用元微之韵》是为酬和朋友钱陈群曾孙钱仪吉(心壶)《生春诗二十首》而写作的,顾春《纫兰寄到阖家共赋春生诗数十首且约同赋遂用元微之原韵仅成十章以诗代柬》是为酬和“闺蜜”纫兰及其家人而写作的。这就是说,对元稹诗歌的模仿追和是在亲戚朋友之间进行的,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如果说朝堂或其他公共场合,由于种种顾虑或其他原因,不易显露自己的真正的喜好,那么,私密场合更能体现写作者的真实趣味。另外,还有李星沅《生春诗》与《续和》、俞越《何处春深好四首仿元白体不用其韵》、彭昕《除夕感怀用元微之放言诗韵》、宝廷《拟元白放言》、李希圣《乱离一首仿元白体》等。
民间追和元稹诗作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民国初期超社组织的一次文学雅集活动上的诗歌唱酬。超社即超然吟社,是民国初期在上海租界中出现的一个遗民诗社。诗社成员主要是前清的一些遗老,在清朝灭亡之后,陆续聚居于上海租界,一时闲淡无事,遂效前人结社之习而于1913年年初组织成超然吟社。超然吟社主要成员有:瞿鸿禨、沈曾植、陈三立、缪荃孙、梁鼎芬、沈瑜庆、吴庆坻、吴士鉴、王仁东、林开謩、周树模、左绍佐、樊增祥,杨钟羲、张彬二人是后来加入的。虽然超然吟社的成员在政治上已“靠边站”,不再是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但因其多为清末民初古典诗坛上的重量级人物,有身份,有地位,交游广,从者众,在古典诗文创作领域的重要性与影响无论如何是不可小觑的。
超然吟社集会之时,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唱和。唱和之时,采用“即席分韵,下期纳卷”的方式,即在本次集会上“分题”,下次集会时各出所作,相互观览,切磋相长。超然吟社与元稹密切相关的一次集会活动,是在1914年的立春,地点是沈瑜庆在上海的寓所涛园,参加者有沈瑜庆、樊增祥、吴庆坻、沈曾植、王仁东、周树模、陈三立、林开謩、吴士鉴、缪荃孙、左绍佐、梁鼎芬,共十二人,共同模仿追和元稹《生春二十首》。由于至少是在半月之内分别撰写而成,非一时一地之作,而且并未限韵,所以,无论题材还是用韵,都相对宽泛而自由。有的主要吟咏自身人生阅历,如吴庆坻《甲寅立春社集涛园拈元微之何处生春早句仿效其体……重念生平行脚万里旧游历历如梦如影因就辄迹所至各系一诗其虽尝涉足非当春时者皆不及焉……用质方雅毋诮詅痴》;有的主要吟咏他人及自身之事迹以赠人与自述行迹,如沈瑜庆《甲寅立春超社第十九集赋得何处春生早用元微之韵赠同社诸公以止相冠首余以齿为序后八首自述》;有的则与自身之经历等关联不甚密切,只是一般描绘春景,如沈曾植《立春日超社第十八集会于涛园斋中赋何处生春早诗》。至于用韵,由于不约而同在每首诗开篇袭取了元稹“何处生春早,春生□□中”,吟社中人之追和都采用了一东韵,虽非次元稹之韵,但亦在一韵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此一阶段没有了“续”元稹之诗与“改”元稹之诗的作品。
三、文人接受元稹诗歌的特点
白居易《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并序》云:“公著文一百卷,题为《元氏长庆集》。”[11]1468但至北宋时,元稹集已严重散佚,刘麟父子已感慨“其文虽盛传一时,厥后浸亦不显,惟嗜书者时时传录”[12]卷首。刘麟父子收拾当时存世的元稹作品,重新编纂,辑成六十卷本,现存的各种版本的元稹集都是从此六十卷本而来,只是明代马元调刊刻元集时又做了补遗6卷。在最初的六十卷浙本元集中,卷一至卷九为古体诗与挽歌伤悼诗(挽歌伤悼诗占一卷余),卷十至卷二十二为律诗,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六为乐府诗,其余为文。马元调所辑补之作品,后人涉及不多;现代人所辑之元稹作品,因清代至民初文人无从寓目,故无须顾及。单从元稹别集中不同诗体所占篇幅大小看,元稹诗作中的古体诗与律诗几乎相等。如果后人对元稹的古体诗与律诗一视同仁,无别爱憎,那么,后人接受元稹古体诗与律诗的比例也应该是相差不多的。但是,清代至民初的文人,追和模仿元稹诗作,主要学习元稹的律诗,是一个至为明显的事实。据本人所做不完全统计,清代至民初学习元稹律诗的作品,约占全部作品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相对于中国古代属于“自由体”的古体诗,律诗是一种规则更严更多、语言更凝练典雅的诗体,它不仅务求平仄不能随意,用典雅致细密,用韵有严格的限制(押平声韵,押本韵,一韵到底),而且还要求运用尽可能工稳的对仗。因此,律诗的写作难度无疑较古体诗为大。清代至民初,模仿效法元稹之诗作,以律诗为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写作技巧的学习、竞赛是清代至民初接受元稹诗歌的一个重要取向。
这一取向在清代至民初文人追和元稹诗歌上得到了更鲜明的体现。在清代至民初文人追和元稹诗歌的作品中,次韵是其中最主要的追和形式。不仅有律诗,而且有古体诗,有乐府诗。清代至民初文人追和元稹的古体诗与乐府诗,如程梦星《解秋次元微之韵十首》,与元稹之原唱一样,十首分别依次押“轻生茎萌”、“鹰惩鹏能”、“乡行霜黄”、“多何罗跎”、“云文焚氛”、“竹熟曲局”、“落萼恶索”、“秋头忧休”、“茵尘亲人”、“烟然年诠”。另外,次韵追和元稹古体诗的,还有严熊《追和元微之竞渡诗》(较元稹原唱误落一韵)与《追和元微之表夏十首》、高士奇《记夏初景物用元微之表夏十首韵》、乾隆《拟元白诗二首并用其韵·元拾遗微之种竹》与《古筑城曲效元微之体亦反其意也兼用其韵》,约占全部古体诗与乐府诗追和作品的一半。古体诗与乐府诗用韵自由,平仄可通押,且中间可自由换韵,作者一般不在用韵上刻意为之,以逞其奇技;酬和者一般也不有意次原唱之韵,不在用韵上因难见巧。而清代至民初的文人,在追和元稹诗作时,对“自由体”的古体诗与乐府诗也次韵追和,表现出在次韵追和上的浓厚兴趣,表现出在技巧上的刻意追求。
在元稹的诗歌作品中,清代至民初文人学习最多的,是元稹的《生春二十首》《放言五首》。尤其是《生春二十首》,追和者有钱谦益、归庄、田甘霖、徐简、徐骏、钱陈群、邓廷桢、顾春、李星沅、彭元瑞、刘秉恬、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尹嘉铨、洪亮吉、庄述祖、沈曾植、沈瑜庆、吴庆坻、董元度、谭莹、汪学金、刘崇如等。这些人中,既有如钱谦益、归庄这样在文坛上很有号召力的文坛宿将,也有如徐简、顾春这样的较为远离文坛中心的闺中女性;既有权重天下因而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的皇帝,也有因朝代更迭而被迫靠边站的清代遗老,各色人等,几乎应有尽有。这说明,元稹《生春二十首》在清代至民初得到了广泛的喜爱。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李星沅更是先后两次追和元稹《生春二十首》,追和数量多达三十首;乾隆更是四次追和元稹《生春二十首》,追和数量多达八十首。这种反复的追和,表明追和者对元稹《生春二十首》的喜爱程度无以复加。以愚所见,没有一首(组)唐诗被后人如此广泛、如此被一个诗人多次的追和。也许可以说,元稹《生春二十首》是清代至民初诗坛上最受欢迎的唐代诗歌之一。
在对元稹《生春二十首》的追和诗歌中,次韵追和是其中的主角。除超然吟社诗人的追和之外,只有尹嘉铨《生春四首》、洪亮吉《消寒七集招同人集朝华阁分赋〈长庆集〉生春诗四首》、汪学金《生春分韵五首》、刘崇如《何处生春早》四位诗人的追和诗歌没有采取次韵追和的酬和方式。超然吟社诸诗人,如沈曾植、沈瑜庆、吴庆坻等人,虽未采用次韵追和的形式,但很多首诗作与元稹原唱选择了同一韵部——即一东韵,只是有些韵字不同而已。
元稹《生春二十首》,全部作品都用“中”、“风”、“融”、“丛”四个韵字。二十首作品全部写初春景象,又完全依次用相同的韵字,这本身就有相当的难度。打一个也许不甚恰当的比喻,这就好像二十个长相差不多的孪生兄弟或姐妹,又穿了款式、颜色、质料近似的衣服,而能画出各自细微的差别,对画家的绘画技巧是一个相当高甚至有些苛刻的要求。也就是说,写作此类诗作,主要需要的不是细敏的感受、浓郁的深情,而是较为渊博的学问与较为娴熟的技巧。作为追和者,利用元稹提供的现成的“形式”,表达或描绘相同或相近的题材,用韵完全相同且次序一致,而能在同中求异,与数百年前的原唱作者一较高下优劣,无疑在诗艺的运用上有很高的要求。
当然,要写出价值高的好诗歌,不仅要掌握一定的“作诗之法”,还要有敏锐而深邃的感悟。只有娴熟的诗艺,写出来的只是“匠人”之诗,而不是诗人之诗,因此,就不是艺术价值很高的成功之作。如乾隆用元稹《生春二十首》之韵,写作了八十首追和之作,分别咏春、夏、秋、冬之景,极铺排与用韵之能事,是着意为之,炫耀技巧,争奇斗胜之意图甚为明显。乾隆《生春二十首用元微之韵》序云:“无须频拈梅柳(微之廿首诗中‘梅’、‘柳’对句者凡三见,而‘柳眼’、‘梅援’又各成一律),殊称自具体裁。”[3]三集卷69《生秋诗用元微之〈生春〉诗韵》序云:“云光霁色,不妨大同;柳眼梅心,亦云小異。”[3]初集卷33《生夏二十首仍用元微之〈生春〉诗韵》序云:“选旧题于长庆,翻新亦既先秋。”[3]四集卷5《生冬二十首仍用元微之〈生春〉诗韵》序云:“翻元和之旧体,还如举一例余;效玉局之叠赓,时复因难见巧。”[3]四集卷8凡此种种,均透露出个中消息。不同的只是,元稹之原唱迤逦而详尽,细腻而工致,而乾隆之追和,少了清新,多了学究之气;少了自然,多了凑泊之嫌。
元稹在诗歌用韵上,有着意求新求险之癖。写作一组或十首、或二十首的诗歌,同用一韵,用相同的韵字,次序也追求相同,仿佛后诗次前诗之韵,以追求“用尽”之难。《生春二十首》即是如此。又喜用险韵,如《江边四十韵》,用三爻韵,《痁卧闻幕中诸公征乐会饮因有戏呈三十韵》用九佳韵,《春深二十首》(拟题,已佚)用“家、花、车、斜”韵,《三月三十日四十韵》(拟题,已佚)用六御韵,都是如此。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曾云:“微之又以近作四十三首寄來,命仆继和。其间‘瘀’、‘絮’、‘敕’、‘虑’四百字,‘车’、‘斜’二十篇者流,皆韵剧辞殚,瑰奇怪谲。又題云:‘奉烦只此一度,乞不见辞。’意欲定霸取威,置仆于穷地耳。大凡依次用韵,韵同而意殊;约体为文,文成而理胜:此足下素所长者,仆何有焉?”[11]477险韵之为险韵,正在其“险”。使用上难度的增加,为作者炫奇斗巧留下了空间。元白唱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炫奇斗巧的过程。元稹的主动挑战与白居易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说明在用韵的争奇斗巧上,元稹是非常喜欢与非常擅长的。清代至民初的文人喜欢元稹的律诗,喜欢追和元稹的诗,特别喜欢次韵追和元稹的诗,很大程度上与他在用韵的争奇斗巧上有不小的关系。
元稹《生春二十首》与相类似的《春深二十首》之所以受白居易、刘禹锡及清代至民初文人的广泛喜爱,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程式化的结构。《生春二十首》每首诗开篇均用“何处生春早?春生□□中”,每首诗均依次用“中”、“风”、“融”、“丛”四韵字;《春深二十首》每首诗开篇均用“何处春深好?春深□□家”,每首诗均依次用“家”、“花”、“车”、“斜”四韵字。每首诗用相同的结构,相同的用韵,而又要同中求异,细腻铺写不同的情景,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后人效仿追和颇多的元稹《杂忆诗五首》也是如此,每首第三句均用“忆得”开头,“忆得”之前写眼下之情景,“忆得”之后写由眼前情景所回忆起的过去的情景。显然,学习效仿此类诗作,易于凑泊拼接成诗,但要写得很成功,又非常困难。应该说,清代至民初的文人学写的此类作品,失败得多,成功的则极少,大有邯郸学步而失却自家步伐之嫌。
当然,我们也没有忘记古代文人在自己的文章中曾表达出来的某些诗学主张。如乾隆《杜子美诗序》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孰谓诗仅缘情绮靡而无关于学识哉?然三百篇之诗,不拘格律而音响中度,所谓太羹不和而有至味也。汉变四言为五言,间亦有七言之体,至魏晋而音韵愈盛,入唐而格律益精。盐梅之设,太羹之害也;七窍之凿,混沌之贼也。至有不言性情而华靡是务,无劝惩之实,有淫慝之声,于诗教之温柔敦厚,不大相剌谬乎?”[13]卷7虽然乾隆在《鉴始斋题句识语》中标榜自己“予少时即喜作诗,不屑为风云月露之词”,“寻常题咏,亦必因文见道”[14]余集卷2,在《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序》中又称“离忠孝而言诗,吾不知其为诗也。”[14]初集卷12但是,他的 创 作 中却有相当 多 的 作品正务技巧而落性情,务声韵而离“忠孝”。理性的宣示是一回儿事,实际的诗歌创作又是一回儿事。乾隆如此,很多文人也是如此。
元稹即使不是唐代遭后人非议最多的文人,那也一定是遭后人非议最多的文人之一。细观后人对元稹的诸多非议,就不难发现,后人非议元稹,谈论最多、批评最激烈的,不是元稹写作的那些作品,而是元稹的人品——讥评元稹谄媚宦官以求仕途升迁与“始乱之,终弃之”以投机婚姻。而对元稹的作品,后人给予了较多的肯定。这种肯定有时不是表现在批评评点上,而是表现在对元稹作品的学习模仿上。清代至民初,是元稹接受史上的一个高潮,不仅学习模仿者人数多,学习模仿的作品多,而且学习模仿的形式多样,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过了以前的任一时期。清代至民初对元稹作品的学习模仿,主要表现在艺术技巧的心仪与效法上。在有些时候,考察文学的发展动向,不能仅看后人堂而皇之地提倡什么,标榜什么,更要看那些文人实际在做什么、学习什么。提倡标榜什么,有时是出于现实的功利的考虑,如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而学习效法什么,则往往更能体现出当事人真正的兴趣爱好。元稹作品在后世被肯定、被追捧、被效仿,足以表明,在清代至民初的历史上,元稹及其作品重塑着此一阶段文学的生态景观,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研究清代至民初的文学发展,甚至文学思想,元稹及其诗歌作品是一个忽视的影响因素。
[1]王世懋.历代诗话·艺圃撷余[M].北京:中华书局,1981:783.
[2]黄之雋.香屑集[M].同治辛未重刻本.
[3]周相录.元稹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乾隆.御制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宋征舆.林屋诗文稿[M].清康熙九籥楼刻本.
[6]毛奇龄.西河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顾景星.白茅堂集[M].清康熙刻本.
[8]吴伟业.梅村集[M].董氏诵芬室刻本.1911(清宣统三年).
[9]王士禛.精华录[M].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10]佚名.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1]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刘麟.元氏长庆集序[G]//元氏长庆集.明杨循吉影钞宋本,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
[13]乾隆.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4]乾隆.御制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