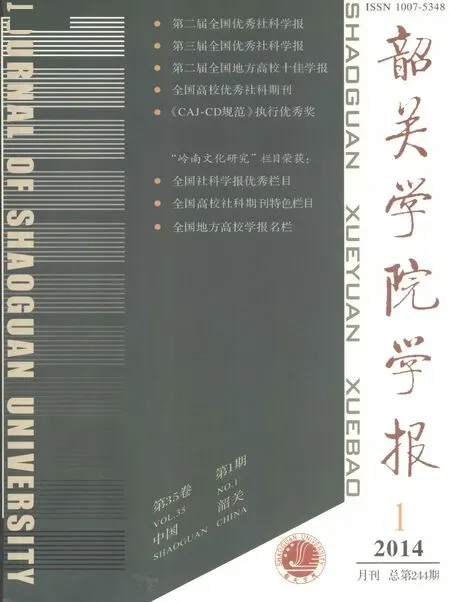关于音乐抽象本质的若干思考
邓 青
(韶关学院 音乐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一直以来,对于音乐究竟是抽象的艺术还是具体的艺术这个问题,从未停止过争论,各有各的理论依据。许多鼎鼎大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在论及艺术或美学问题时,都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艺术是具体的、紧密反映生活的。如贺拉斯的“艺术摹仿生活”理论,狄德罗的“美在关系”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即生活”理论……这些观点具有合理的成份。
但另一大批先贤,如柏拉图、席勒、黑格尔等,却认为艺术是抽象的(即理念的、先验的、纯粹的等观点)!如席勒说:“在一件艺术品里,材料必须消融在形式里,躯体必须消融在意象里,现实必须消融在形象显现里。”[1]100又说 “表现上的纯粹客观性是好的风格的特质,是艺术的最高原则。”[1]78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它符合人们的天然情感,排斥了过多的“意义价值”的功利色彩与沉重的哲学思辩,还原了音乐艺术本身的单纯优美与精神属性。
我们认为音乐由于其无形无踪的声波作为物质形态,一直是抽象性最强最彻底的艺术。虽以物质形态为基础并作用于人的物质器官,有不容置疑的物质具体性,但在起源、创作、心理过程、审美及意义指向方面,只能且必然是抽象性的,否则就失去了音乐的本质美与大部分的存在价值,从一种纯粹美感的精神活动与产物变成科技或实用性的东西。
为了更好地说明音乐的抽象本质,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详细论述。
一、从音乐起源及历史角度看音乐的抽象本质
从音乐的起源来看,其起源与目的并非预设,只为人类的精神愉悦而来,是人类的精神放出的火花。当人类第一次有了闲暇,不用为了填饱肚子整天奔波于丛林、草原,即在满足直接生活需要而有余力时,才会进行自由的艺术活动。吹骨笛、在岩壁上画出一只牛或在头发上插上一朵花,都是无关于生存的活动之一,可算是人类精神活动或审美的第一朵花。原始人在吹响第一声骨笛时,并没有学习过所谓的理论、意义与音乐技巧,自然无法想像这骨笛声会有什么意义;只是以有规律(间或无规律)的乐声,以人类创造的区别于大自然的声音,来愉悦自己、愉悦别人,这应是音乐的本原。所以从德谟克利特认为音乐并不产生于需要而产生于正在发展的奢侈(或余力),到近代类似的(席勒和斯宾塞)余力说,都明确指出音乐是超功利性与精神审美的结果。音乐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具备了天然的抽象性。
从人类历史角度来看,各种古代文明都曾将音乐放在极高地位,与巫术并列,是国之重器,参与重要的政治决策,就是利用了音乐的天然抽象性与神秘性所具有的力量,其原因有:第一,对音乐无形无踪的形态不可捉摸与不能理解,且音乐的感受因人因时各有不同,呈现出极强的神秘主义色彩,非常符合当时对事物的神秘主义解释,因此音乐被认为是上天或神的启示,成为统治者有力的统治工具。第二,对音乐具有的能量的敬畏。音乐由于能与人的心理契合,能给予人愉快、悲伤、紧张、愤怒等感觉,能让人安静冥想,又能让人激昂奋发。
音乐从诞生时的娱乐到巫到教化,随着音乐社会功能的扩展,音乐从纯粹的东西一步步变成复杂的载体,其实质是人的社会化程度的加深,是人的复杂化。
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走过了原始天真的阶段步向文明,而文明的后果是复杂化、功利化与思辩色彩的浓重,离艺术的本原与魅力却越来越远。柏拉图是西方最早主张管制音乐的思想家,这种主张曲折地反映了柏拉图社会理想模式与秩序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与其师相同:“节奏与乐调不过是些声音,为什么它们能表现道德品质而色香味不行呢?……因为节奏与乐调是些运动,而人的动作也是些运动。……音乐的节奏与和谐之所以反映人的道德品质,是因为两者同是运动。音乐的运动形式直接摹仿人的动作(包括内心情绪活动)的运动形式,例如高亢的音调直接摹仿激昂的心情,低沉的音调直接摹仿抑郁的心情,不像其他艺术要绕一个弯从意义与表象上间接去摹仿,……从此可见,音乐的节奏与和谐不能单从形式去看,而要与它所表现的道德品质或心情联系在一起来看的。”[1]221
正因为音乐的抽象性,先贤们意识到其解释的近乎无限的可能性,才天然地最适合用于阐释“道德品质”或“心情”此类抽象的概念。而为防止不合规矩的一切思想,必然且必须管制音乐。
需要指出,音乐具有很强的历史时代特性,当然这并非音乐的本性,而是反映了该时代社会的好恶等情绪。例如得到全世界普遍好感的《蓝色多瑙河》,在一战前的中、东欧斯拉夫民族中就受到排斥。因为这些民族当时处于奥匈帝国的统治下,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与民族主义浪潮高涨,厌恶痛恨与奥匈帝国有关的一切事物,连本无国界民族之分的音乐也无法例外。又如,进行曲通常给人以奋发向上、斗志昂扬的感受,也常用来描写年青人的朝气与活力。一些优秀的进行曲都曾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重大的激励人心的作用,如《马赛曲》、《义勇军进行曲》等。但在二战后的欧洲,基于对战争的厌恶与惨痛记忆,很长时间内社会都非常排斥进行曲及类似进行曲的二拍子节奏。
人类历史的积累与丰富,影响到每个时代每一个人。出生时纯粹的个体,被高度复杂的社会所包裹、浸染,已不可能以单纯或素朴的心态去聆听音乐,自觉不自觉而被越来越丰富的意义、联想所淹没。以一个复杂的底印去面对音乐时,自然会认为音乐本身具备了各种各样的意义与具体指向,而忘记了音乐本身的抽象性。
二、从音乐欣赏主体(即人)的角度看音乐的抽象本质
赫拉克利特认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强调世界的变化与更新。面对艺术(包括音乐)没有绝对永恒的美或评判标准,视不同历史时期而有变化;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同一社会里,不同的个体也会造成审美口味与标准的千变万化,所以休谟说:“美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它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每一个人心见出一种不同的美,这个人觉得丑,另一个人可能觉得美。”[1]440人的复杂,导致即使面对一个单纯的事物,也会搞得复杂无比。音乐不过成了人的情感转移与寄托物,起一种联想的媒介作用,并不是音乐有什么具体性。
正是基于对人的复杂性的了解及音乐抽象性的清楚认识,才在不同历史时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大量主张艺术(包括音乐)是抽象本质的思想家,并一直占据西方文艺思想的主流地位:以柏拉图开创的理念说为渊源,历经新柏拉图的普洛丁(灵感说)——康德的美不带概念的形式主义学说——德国狂飙运动的天才说(歌德、席勒等人为代表)——尼采的酒神说——柏格森的直觉说和艺术的催眠状态说——佛洛伊德的艺术起源下意识说——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萨特的存在主义说等,这些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从中可以看出,面对复杂的人、神秘的心理与头脑、无法解释的种种文艺现象与事实,他们也无法得出一个具体化的、可精确度量的理论,只能诉之于抽象的近乎神秘主义的解释,其中音乐因其无形无踪的物质形态,表现得最为突出!
古代中国人常用音乐来表现与阐释 “天道”、“禅机”,而领悟的多少与深浅,一切全取决于个人的修为与灵性,在形式与内容上也达到神秘、空玄与唯美的极致。这正是基于对音乐的抽象本质的深切领悟与运用。
终极的思考与哲理的冥想或许太高远了,人们回归音乐的抽象本质,就是为了回归音乐的最初目的——娱乐(或游戏)!席勒说:“只有当人是充分的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1]139他明确指出了音乐所带来的美的欣赏与愉悦,超越了低级本能与利害计较,产生游戏冲动,让人手舞足蹈、放声高歌或浅斟低唱,释放精神与自由,纵情欢笑或落泪。
因此,从欣赏者的角度看,音乐的本质也是抽象的。
三、从审美的角度看音乐的抽象本质
社会越发展,人们的联想越丰富;个人的水平学识越高,感受越复杂越丰富,但却离理解与欣赏艺术之道越远。就像老子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也印证了佛所说的“着了形迹”或“着了相”。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是最糟糕的现象。科技化与理性主义对艺术的侵蚀,让人们忘却了音乐的抽象本质。
古希腊的艺术成就达到人类史上的高峰绝非偶然,它所追求的“古典的静穆”的理想境界与文艺审美观,一直深受追捧与信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思想家认为“凝神观照”是人生的最高幸福!无所为而为,在平静中欣赏文艺自身所产生的乐趣,在静观默想中得到最高的快乐,文艺应表现出神的庄严、恬淡、静穆,才能真正达到最高的风格与成就。
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认为艺术属于审美范畴,要以直觉作为对待艺术的正确方法与态度。音乐作为一门艺术,须以不带任何利害计较的心态去面对,追寻心灵的直觉与颤栗,获得源自灵魂而非单纯的感官满足的审美快感。康德说:“审美趣味是对审判心境的普遍可传达性的估计,它不是推理的结果,只是一种朦胧的舒适的感觉,具体表现为意识可察觉到的快感。”[1]78又认为“……自由的美是事物本身固有的美,不以对象的究竟是什么的概念为前提。”[1]而英国哈奇生说得更清楚:“(音乐)在本原美项下可以列入和谐或声音的美,因为和谐通常不是看作另一事物的摹本。和谐往往产生快感,而感到快感的人却不懂得这快感是如何起来的,但是人们知道,这快感的基础在于某种一致性。”[1]95
艺术需要摆脱一切才能获得一切。摆脱的是日常繁杂的实用世界,获得的是单纯的意象世界。主张音乐的抽象本质才是正确的审美态度与方式。
以上从多方面阐明了音乐的抽象本质。主张并坚持音乐的抽象性,并非仅仅满足于理论的争辩,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有正确的态度与方式去创作音乐、欣赏音乐,专注于音乐形式本身的审美,忘记功利主义,获取纯粹的审美愉悦与心灵净化。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