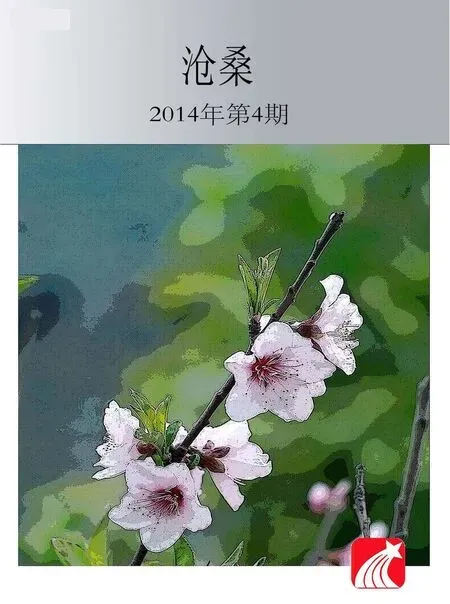海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浅析
罗澄洋
海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浅析
罗澄洋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离不开其时新近的研究方法,譬如区域研究、计量史学和跨学科交叉方法等等。本文将以几部海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代表著作为例,对是类方法加以具体探究,冀对国内近代史研究有所裨益。
海外中国学 社会文化史 研究方法 研究特色
恰当的治史方法,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特定时期、特定史学流派的方法,不仅会助益于读者厘清其研究路径的经纬,而且对于深化理解其独特的研究取向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本文拟对国外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兴盛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加以考察,以孔飞力著《叫魂》[1]、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2]、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3]、王笛著《茶馆》[4]、韦斯谛主编《中国大众宗教》[5]等论著为例,以期管窥西方史学家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具体研究时,如何剖析和阐述的某些侧面。
一、史学承转
20世纪50年代中期伊始,西方历史学向社会科学化转向的趋势逐渐增强。1961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E·H·卡尔曾积极肯定并推动是类潮流,他说“历史学变得越来越社会学化,社会学变得越来越历史学化,这样对两者都有更多的益处。让社会学、历史学之间的边界保持更加广阔的开放态势,以便双方沟通”[1](P162)。
美国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趋势为典型的代表。60、70年代以来,社会史已经超越政治史成为历史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1978年美国社会史领域的博士论文数量是1958年的4倍,已经超过了政治史[1](导论P1)。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相互交融的背景之下产生的社会史,使得史学研究的对象大为扩展,研究领域突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范畴,而扩展到劳工史、妇女史、儿童史、人口史、家庭史、社区史、少数民族史等众多领域。社会史的兴起不仅扩展了历史学家的学术视野,而且也使历史学从一门描述性的人文学科转换成为一门分析性的社会学科,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史学研究方式的落后面貌[1](P318)。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肇始,“新文化史”出现在历史学的舞台。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文化人类学的影响,社会史领域也出现了“文化转向”[7](导论P5),即越来越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对社会现象加以阐述,史学家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描述下层人民生活的状况,而是更加关注和期待了解文化体系是如何塑造民众的身份认同、感情和日常生活的历史面貌。
“中国研究”是美国历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上世纪40年代,费正清创立了不同于欧洲传统汉学的中国研究,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日渐成为一门“显学”[1]。60、70年代,美国中国学研究呈现出繁荣局面,中国近代社会史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以孔飞力、史景迁、周锡瑞、杜赞奇等学者为代表的美国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国学家们已经不再局限于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相关研究,而是更倾向于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广大群众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加以考察,这推动了海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勃兴。此外,中国政府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亦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些许便利条件。
二、方法探析
古语有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任何学术成果的铸成都离不开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史家继承了先贤者严谨细致的搜集、鉴别、归纳分析史料的方法,以及高超的叙事路径。同时,他们亦创造性地运用了些许新方法,如计量史学方法、区域研究以及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1.区域研究的创新视角。
倡导区域研究,是费正清开创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与传统欧洲汉学研究范式所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点。区域研究又称为地域史研究,将研究的范围专门固定于某一特定地区,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其内在的自然环境、社会阶层、人口数量、经济水平、交通状况、政治制度等。施坚雅提出了宏观区域理论,将中国横向分为9个大区,运用区位理论、“中心地”的原则以及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考察区域的内部结构与外界联系[1](P60)。
王笛的《茶馆》书著,运用区域研究方法,描绘了近代中国大众生活的侧面。王氏将研究视角投放于成都,冀通过对该区茶馆的叙事,窥探当时中国“市民社会”的相关状况。王氏将成都的茶馆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的样本范例,对茶馆的社会地位、经济运作以及政治斗争等相关历史面貌做出详实的叙述,生动地刻画出成都市民斑驳陆离的生活百态,且透过微观研究和宏大叙事有机结合,解读了国家政权和组织在现代化建设过程当中,是如何向下层渗透的大命题。
学者在民间文化和大众宗教领域,也倾向于区域研究方式。譬如,万至英曾就民间信仰形象的历史沿革研究时,强调区域视角为切入,对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面貌、民间文学与信仰、女性地位及财富、家庭观念等多重维度的研究[5](P143-196)。华森亦选取了两个富有代表性村落为案例,通过分析区域内特殊的道义经济体系、地方精英统治、社会分层、祭祀庆典等侧面,披露出“天后”正统化的过程[5](P57-92)。总而言之,区域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可克服“通史”重广博而轻精深之瑕疵,为研究者提供一条深入解剖历史真相的渠道路径。
2.计量史学的运用。
计量史学是指利用数学和推论分析方法,根据实际数据统计,对历史进行定量分析,再把定量结果用于历史验证。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为数据分析和信息存储提供便利,计量史学运用于社会史等史学研究领域。
这一段关于“行侠仗义”的探讨,发生在金庸先生所著的《倚天屠龙记》第五章末尾,便是谢逊大闹天鹰教的场子,意图抢夺屠龙刀之时。众所周知,张翠山是武当七侠之一,而谢逊是臭名昭著的金毛狮王,按江湖中的话来说,乃是“正邪不两立”。
计量史学对“美国中国学”研究贡献颇大。施坚雅分析四川农村社会的经济数据,提出了“市场层级理论”[1](P7);黄宗智在《华北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中通过定量分析“满铁”调查的数据,提出了“小农经济过密化”理论。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成功之处也得益于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
周锡瑞独辟蹊径,以定量和定性区分史料。定性史料主要是19世纪旅行家们讲述的故事以及县志,定量史料以及以此为依托的资料库构成了周氏本书分析和写作的基础[2](P6)。周氏创建了一个包括山东省内各县的人口数量、县级人口密度、各县士绅力量、自然灾害的频次及各地盗匪案件数量的数据库,他根据特定的公式将这些史料信息换算成量化数字。周锡瑞在具体分析山东地区自然灾害时,统计了各县自然灾害发生频率、严重程度及因自然灾害而获免税特权的次数,综合换算出“灾害指数”。另则,根据各项目中独特的运算法则,周氏对山东各县的人口密度、地主所有制程度、士绅力量等也进行了换算,按照相似性原则将程度相近的县城划归到同一地区,是故将山东省划分成六片内部社会经济状况相似的区域,这又为他的区域研究奠定了基础。
总之,计量史学可助研究论点及论证更加精确化。计量史学的宗旨就是用“数据”说话,它所呈现出来的“数字语言”所具有的精确性,是传统史学中常用的定性分析难以比拟的,因而能使史学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当然,计量史学也带有其不可规避的局限。有论者指出它受史料的依附程度太深,只有在数据资料比较充分的前提下,方才有施展的空间,而且数据中的误差和错讹有可能导致结果的偏差。所以,学者绝不能忽视鉴别史料真伪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先科学评估后的数据,方可助益于学者正确探求历史的真相。
3.跨学科方法的实践尝试。
随着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大举进军历史研究领域,社会文化史领域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特色。
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也吸收了社会学科的成果。此书中的核心概念“国家政权建设”是社会学领域的概念,杜赞奇将其指代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官僚化及向基层乡村社会渗透的过程。为了克服单一运用“国家政权建设”的弊端,杜赞奇提出“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杜赞奇藉此分析国家财政收入和政府机构数量增加,但政府职能却未有相应增强的根源。杜赞奇根据“后现代主义”思潮,提出了“文化的权力网络”[3](中文版序P2),他认为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在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充满了政治博弈。
三、研究特色
以区域研究、计量史学及多学科交叉为代表的新的研究方法的应用,使海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体现出了新的特色。
首先,微观史学异军突起,以小见大的描述成为史家叙述历史的新途径。在区域研究的指引下,研究者可以将研究的范围缩小到某一地区,甚至集中到某一事件的发生发展、某一人物的命运或者某一个场所的变迁层面。王笛的《茶馆》将成都的茶馆当作解读社会文化和历史变迁的一个文本,通过解读茶馆作为一个日常的休闲场所、一个经济实体以及政治角色所具有的作用和在社会中的地位,不仅描绘了成都的地方文化、社会生活和经济状况,而且也展现出了20世纪上半叶国家机器向下渗透的过程中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间的冲突和妥协。
其次,将叙事与分析有机结合,并且突出文化在权力的运作和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与传统的历史叙事不同的是,社会文化史的叙事不仅仅满足于告诉读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更是将叙事和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读者解释历史事件背后文化的作用。
《叫魂》凭借其流畅的文笔和生动的情节被公认为叙事史的佳作,孔飞力先生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就是边叙事边分析的。例如,在描述了妖术大恐慌的兴起和蔓延之后,孔飞力先生通过解读清代的碑刻和小说来了解民众心中的鬼神观念,从而分析妖术大恐慌的由来;又如在描述完全国大清剿的失败和叫魂闹剧的草草收场,孔飞力又从制度层面对官僚君主制中的非常规权力的运作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并且揭示出在这个事件中君主、各级官僚和下层民众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博弈。这种分析和叙事相结合的特点在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周锡瑞在讲述山东各地反洋教斗争的具体过程时,也总是细致分析当地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民间文化和外来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考察这些群众运动是否与1899—1900年间的“义和团运动”有着相同的仪式。从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周锡瑞先生对文化因素的重视。
第三,突破西方中心观,注重从中国自身寻求社会发展的力量。费正清开创的现代中国研究是以“冲击—反应”模式为导向,这种研究取向须有“假定预设”,即19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左右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最重要的影响来自于西方的冲击。这种模式夸大了西方的影响,后来的史家逐渐察觉其弊端,并在新的社会文化史中加以修正,将探寻历史发展动因的视角转移到中国的本位社会。例如,周锡瑞虽然指出西方的经济渗透给山东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造成了冲击,而且洋教的肆虐也是直接造成教民反抗的原因,但是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发展和壮大根本还是要从中国社会自身内部寻找原因,一方面它跟清政府对外软弱妥协、对内剿抚不定的态度有关,清廷不明朗的放任态度实际上促使了拳民势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它也离不开山东的地方文化,正是山东习武传统中的“刀枪不入”的招式和民间戏曲小说中“降神附体”的仪式,使得义和团运动便于传播,因而迅速蔓延。是故,周锡瑞认为推动是次社会运动发展的根源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
四、结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自从上世纪60、70年代兴起以来,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涌现出许多受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优秀著作[7]。作为西方学术的重要一环,虽然它在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上与我国国内的近代史研究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依然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以期为开拓国内历史学视野增添色彩。
[1](英)E·H·卡尔.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林·亨特.姜进译.新文化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张广智.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4]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陈倩.区域研究在美国中国学中的兴起.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5).
[6]刘照成.美国中国学研究,以施坚雅模式社会科学化趋向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7]刘毓庆.文史研究突围与历史大循环的发现.晋阳学刊,2003,(1).
罗澄洋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硕士研究生
(责编 樊 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