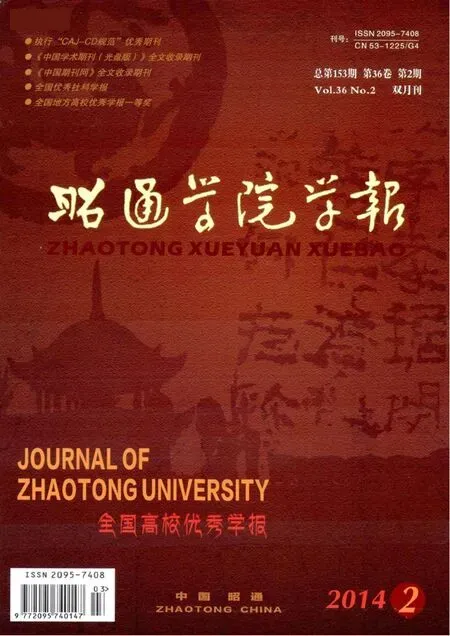论离魂文学发展以《阿宝》为代表之巅峰时期
龙柯廷, 魏 刚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作为母题之离魂故事“可以转换出无数作品并能组合入其他文学体载和文化形态之中。表现了人类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集体意识,并常常成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标示。”[1]由此可晓离魂故事之巨大艺术魅力。六朝时期,离魂主题尚处萌芽阶段,其用意唯于“及其著述,亦足以发神明之不巫也……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2]此为其第一阶段;唐宋时期,诸传奇作品“始有意为小说”,[3]离魂作品亦属其内,以爱情为媒介,真正触及封建礼教及世俗婚姻等社会问题,始于此期,遂至成熟时期,故为第二发展演变阶段;元杂剧繁盛之期,离魂主题亦引入戏剧,其文体于此期得以扩展,以致离魂主题“盛传不辍,且成词曲典实”,[4]作出主题之创新及推进,即:反映门第观念及科举弊端,此为第三阶段;至《聊斋志异》时期,离魂文学已具先作诸采,且艺术特色颇丰,男女间生死不渝之情爱,得以借离魂故事宣扬,离魂文学遂至顶峰,此为第四阶段。由此可见,离魂文学以其独特之故事情节,而颇具艺术感染力,各时文坛之上,皆能彰显其特定艺术魅力及社会内涵。虽“借神怪以言情,以情胜”,或“借神怪以言志,以理胜”,[5]离魂文学于不同时代之不同历史环境中,体现相异之艺术表现,且呈历史继承关系,成辩证发展之轨迹,离魂故事之巨大艺术包容性、再造性,得以深刻展现。
一、离魂及离魂文学概念
离魂者,若论其思想渊源,当本属我国起源甚早之灵魂观念也。若欲晓其意,逐解“离”“魂”二字,后合其意以释此词,即字源追溯,以求其真。离,《说文》曰:“黄苍庚也,鸣则蚕生。从隹、离声。”[6]段玉裁注云:“葢今之黄雀也。方言云:黄或谓之黄鸟。此方俗语言之偶同耳”、“借离为离别也”[7]。案:此“离别”一语,即可为解。魂,《说文》曰:“阳气也。从鬼、云声。”[6]段玉裁注云:“阳当作昜。《白虎通》曰: 者,沄也,犹沄沄行不休也。《淮南子》曰:天气为 。《左传》:子产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 ,用物精多,则 魄强”[7]。案:此处“魂”与“魄”相连,而诚如“魂魄”一说,可知“气”为“魂”之大意。然此意尚不能明,若借朱子之说,似可深明其意矣。朱子言:“生则魂载其魄,魄检其魂。死则魂游散而归于天也,魄沦堕而归于地也”[8],又云:“人所以生,精气聚也。人只有许多气,须有个尽时。尽则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而死矣。人将死时,热气上出,所谓魂升也;下体游冷,所谓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也。夫聚散者,气也。”[8]案:朱语之中,将“魂气”与“形魄”连用,已有合理之解释,且切合古说。综合朱、段之说,可知魂实为阳气,魄即为形体者也,二者可发生分离,即为阳气之魂离别为形体之魄也。
然笔者意为,此非离魂之真意也,乃因其有二分:一者,魂离魄后,无可再聚,即死亡之意,此不可谓离魂,殊因其魂不可再回附形体;另者,魂虽离魄,仍有聚合之时。其间或有形死,然之中有魂可回附形体,此若与死亡相别,皆因其有魂回附形体之现象,即死而离魂之意也;其间或有形体未灭,呈现假死之态,可谓魂游与体外,即生而离魂之说矣。对于后者,西学亦有其解。如言“这些居住于人类体内的灵魂能够离开且迁居到他人身上……在某一个范围内可离开它们的身体而独立。”[9]此乃离魂得现之形态,即真正意义上区别于死亡概念之离魂。立于故事之文学角度而言,若可称为离魂文学者,须以此之离魂概念为其理论依据,且亦有情节虚设,此所谓情节,其必以离魂(离魂之始与回魂之终)情节为其一,如此即可谓离魂作品。此些作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重新面临那种在漫长的时间中曾经帮助建立起原始意象的特殊情境,这种情形”[10],亦即“当符合某种特质原型的情景出现时,那个原形状就复活过来”[10],若离魂诸作皆如此式,且成系统,即为离魂文学。
二 、《聊斋志异》中离魂故事之文学表现
魏晋至元明,其间数百年,离魂文学之发展演变,已颇具艺术,主题演化,亦至熟境。如此历程,可见离魂文学之运未有衰落,皆因其极具艺术发展潜力。遂于原有高度再次思变,或艺术成就,或人物情节塑造,或思想蕴含等,如诸方面,蒲松龄之《聊斋志异》,皆至新高。蒲松龄总结晋宋以来之离魂故事,以其为基,创造运用,将离魂故事之艺术魅力推至顶峰。如《王桂庵》与《寄生》两作,虽设有离魂故事,然其仅为情节所需,以显志怪特点,未有大效;《凤阳士人》一作,仅以离魂入梦为构,非魂离生躯而独有行举,另如《长青僧》、《促织》等篇,虽可视为离魂故事,然非以离魂述爱情之作。除此之外,另有一作,可赞为离魂文学巅峰之作,名为《阿宝》,较之于诸多离魂作品,其卓然异色;往之离魂先作,皆有其弊,行文以彰故事之怪奇为主,且情节胜于人物描写。《阿宝》之人物,刻画细腻,形体生动,风采鲜明;复杂性格之刻画,遵简设繁,繁处显形,简处率情;其情节,蒲翁匠心求离奇,曲折如流,兼收并蓄,皆有新创。基于此,笔者以《阿宝》为代表,力阐离魂文学第四次发展演变之卓越表现。?
三、以《阿宝》为代表的离魂文学艺术成就
首先,于情节结构而言。《阿宝》既承往作波澜起伏之情节系统,亦外加新创。以往诸作,以离魂为主要情节,或以丰富离魂内容为取胜妙法,如此格局,遂为《阿宝》所破:除离魂外,新造其余主要情节,虽为先作未具,然与文意紧联,逻辑互依,更显曲折多变,格局完整。试从以下几方面析之:
第一,真幻互补结构。《阿宝》之文中世界,虽为艺术设造,然其皆源于现实,足具现实社会生活底蕴,而与幻界和谐统一。现实所不能之愿,亦以幻界得偿,二者相辅相成,离魂与现实两界得以和融,此乃先作所不具之特。如:主人公孙子楚首见阿宝之后,魂魄难由自主,随阿宝而去;对于离魂后之孙子楚,蒲翁又奇想崛起,离魂与肉体,分而述描。如此真幻两界,实有相异,亦和谐共存。孙子楚之离魂,随阿宝“坐卧依之,夜辄与狎”,却又“腹中奇馁”,如此离魂,依需饮食,实与常人无异。可见斯文,亦真亦幻,真幻互补。
第二,双线并行结构。与往作相比,其最突出之情节结构,乃于离魂故事外另构断指、附魂、还魂三情节,翻先作而是为独创之处;换言之,此乃斯文于离魂文学之最大创新。四情节之设,皆随孙子楚之情感变化,故而跌宕起伏,行文发展之主要线索,亦由其构。另外,孙子楚为得阿宝之爱,其所行相异之诸举,阿宝之内心情感亦与其相应,即:无心—动心—生情—痴情,如此心理历程,乃故事情节发展之另一线索。两条线索,互相并行,相辅相成,共促文章结构行曲折之径,终酿张阿真爱。如此结构,可于以下四情节析之:
首先断指情节。对于孙子楚之主动追求,阿宝无所动心。因别人怂恿,孙子楚“殊不自揣,果从其教”,托媒人向阿宝求婚,对此,阿宝两次“戏言”,以示无心。第一次戏言“去其枝指”,第二次戏言“我请再去其痴”。若第一次戏言乃随意而无心,则第二次当属故意刁难,以证其完全无意于此门亲事。其次离魂情节。蒲翁有意构建三“骇”及两“祝曰”,以示阿宝动心之历。细析三“骇”,方晓阿宝于孙子楚感情之转折及升华。第一次“骇极”。孙子楚之魂与阿宝“坐卧依之,夜辄与狎”,而答名“我孙子楚也”,如此情况,阿宝定颇感“骇极”;第二次“益骇”,发生于孙子楚家人至阿宝闺房招魂成功之后,孙子楚能“何色何名,厉言不爽”,阿宝听之“益骇”,且“阴感其情之深”。若第一次“骇极”仅觉事之怪奇而发,则第二次可言其心已生情,故言“益骇”,着一“益”字足知此意。第三次“大骇”,发生于孙子楚第二次离魂出窍时。此时之阿宝,实知孙子楚情意,为了追求自己竟不惜舍身变鸟,故而对如此行径而感之“大骇”,故“解其缚”。相较之,此骇已异于前两骇,阿宝接受孙子楚之感情,亦由此始。再次附魂情节。阿宝对于孙子楚之感情,渐深以致相爱。经上所析,阿宝生情于孙子楚已由离魂始之。后继附魂而巧构两次“祝曰”,可为阿宝续情之过程,若言三“骇”为阿宝感情变化之转折,两次“祝曰”则可为其结果。一者,阿宝知孙子楚化身为鹦鹉后,阿宝即祝曰:“深情已篆心中,今己人禽异类,姻好何复圆”,阿宝之深情此“祝”足晓,只因“人禽异类”,虽觉“姻好”而不能“复圆”。遂有第二次“祝曰”:“君能复为人,当誓死相从”,可见阿宝之爱已至深境,此语实源于其心非有虚情。然孙子楚因前戏而难信之,阿宝唯有“女乃自矢再昭其心。至此,阿宝对孙子楚感情之转变,足以知晓。最后还魂情节。二人感情已达痴情境界,经前三情节遂推至极境;然其爱之真纯否,亦由此检而验之。经努力,孙子楚与阿宝终究相爱。然此情历三载后,孙子楚“忽病消渴卒”,而阿宝则为之“泪眼不晴,至绝眠食”。曾有人言:“正因为有此一波折,才显出阿宝的痴情……因为先有了孙子楚的痴于情不顾生死,才有后面阿宝的痴于情起死回生”,[11]如此观点甚同。二人之爱,其虽历曲折离奇,然合情乎理,其果乃孙子楚所愿,亦阿宝所求“日择良匹”之果。
第三,与离魂文学之先作相比,于结构关系上《阿宝》有意设“男悦女”、“人化鸟”之双重拓展,可谓于传统离魂文学结构颠覆也。“人化鸟”之设,使以往单一离魂情节得以转变,其深遂增,故其所表爱情,较之先作,甚挚甚深。既如此,蒲翁选鹦鹉以附魂,乃匠心之作,会言之鹦鹉,与阿宝日夜厮守,将孙子楚之真情实意,一一昭示,可为最有效之表达方式。先作“女悦男”之模式,为斯文“男悦女”之新构所转。之所以如此,乃因以男子为灵魂形象,可使阅者觉其真实可信,而倍感其情;改变妇女地位之先进意识,亦或蕴其中;另“痴爱”意念,斯文亦有其收,如:据《庄子骈拇》“骈拇枝指,出手性哉,而侈于德”之言,[12]取“枝指”多于常人之所得之意,而将其与“痴情”之性相联系,以“枝指”为形寄“情痴”之性,独有孙子楚,其情痴之性甚深,故生出断指情节。如此情节,虽为蒲翁于离魂文学之拓,然其皆基于以往作品可用之素材及典故,而附于己之艺术成其形。
其次,与以往离魂诸作之形象相较,《阿宝》之人物形象,亦有其特异之处。以往之至爱精神,《阿宝》之男女主人公,虽有其承,然亦以此为基另有新造,可如言:“《聊斋志异》的人物形象,不仅在主导性格上各有差异,而且在次要性格的各个侧面也同样存在着差异。”[13]为此,《阿宝》中形象塑造之“先进之处”,亦即离魂文学第四次发展演变之期,其鲜明特点之一也。《阿宝》中,蒲翁力塑主人公之情痴特点,以其贯穿全文,经系列跌宕起伏之情节,有意设其离奇之采,遂升华为文章之旨。如言:“蒲松龄以痴笔写痴人,从而把情痴形象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使情痴这种艺术审美形象成为后世爱情故事的典范。”[14]至此时期,离魂文学之人物塑造,得其全新形式,超先作而增色。
孙子楚与阿宝,二人之性格有其相似之处。试析之:孙子楚虽为“孙痴”,然其不痴为实,反为大智若愚之类。断指情节中,其痴情难渝。托媒人求婚于阿宝,难料阿宝无心且为戏言所弄,戏其:“渠去其枝指”,此言固为玩笑之语,然孙子楚无所顾虑,说出“不难”二字,遂“以斧断其指,大痛彻心”。由此可见,此乃果敢之举,其虽为书生,然具些许侠士风范,豪爽而多情。对于爱情,其执着之性亦何等热烈。后知阿宝“揶揄”,遂弃其念,亦可见其理性。离魂情节中,浴佛节当天为再睹阿宝芳容,孙子楚竟“早旦往候道左,目眩晴劳”,直至中午,得见阿宝现身于车中,可见其沉着冷静之心;然附魂情节中,为与阿宝朝夕相处,竟不惜化身鹦鹉,却“他人饲之,不食;女自饲之,则食”,终动阿宝恻隐之心,亦无过分之求,唯愿“得近芳泽”。当阿宝第二次说:“君能复为人,当誓死相从”,此时变为鹦鹉之孙子楚,略显老练,为不再上当受骗,乃言“诳我”,以致阿宝“自矢”,随之“衔履而去”,且以其为阿宝之信物,又逼其“不忘金诺”。终得与阿宝“亦迎成礼,相逢如隔世欢”,此时之孙子楚,真诚与机智足显,执着而老练顿生。
另析阿宝之形象。《聊斋》之中,多数女情痴所获之爱,皆有一见而钟情之缘,然阿宝其异。其巧设常人难为之要求,而欲晓孙子楚品行,后常感于孙子楚真诚执着之性而与之渐生爱情。随情节发展,其对孙子楚之情感亦获渐深,终至痴情境地。文始先于侧面写阿宝之境况:“邑大贾某翁,与王侯莩富,姻戚皆贵。有女阿宝,绝色也。日择良匹,大家儿争委禽状,皆不当翁意。”阅此可知,其貌“绝色”,“大家儿”争相求娶,生于财势两富之家,着一闺秀也。后“媒媪”登门,其来由已不言而喻,阿宝亦主动相问,且无羞涩之态,知求亲者为孙子楚后以戏言敷之。说出“渠去其枝指,”一语后,阿宝为孙子楚“以斧断其指”之情所“奇之”,则显其心己有所触,故第二次“戏请再去其痴”,此可为缓计,对一素味平生之男子,自不能因一戏言而真以身相许,故“再戏”以求应付。痴为本性,何可去之,如此不实之由,足绝孙子楚之求,此亦可见阿宝之随机聪明,见其之纯真率直,顽皮中隐含于礼教之不屑。阿宝“每楚与人交”、“心异之,而不可以告人”,尚未出嫁之少女,阿宝并未因此有所惊恐,而唯感好奇。孙子楚离魂三日后,阿宝知其性命垂危,竟毫不避嫌,“不听他往,直导入室,任招呼而去”,率直、坦诚、善良诸性,进一步突显。自此,阿宝“阴感其情之深”,知其已然生情。浴佛节降香路上,突见路旁候其之孙子楚,不由“以掺于幕帘,凝睇不转”。经与孙子楚几番非常接触,阿宝遂晓其为人,知其秉性及用情之挚,以此为基,遂萌其爱。后“女以履故,失不他”,可见阿宝动情之深,倔强、执拗之性,亦获尽显。阿宝之卓越,其非常见识人皆叹赞!亦昭其“不易及”之至情至性,一旦倾心相爱,宁愿“处篷茚而甘藜藿”,如言“蒲松龄对人物刻画最大的特色就是能抓住一个人身上最本质的地方加以描绘,落笔不多,而形象生动逼真。”[15]
经上述可知,阿宝及孙子楚之情性,既存共性,为其主导性格,即情痴。然相异之次要性格,二人亦具,其相似之主导性格及相异之次要性格得以和融,同谱爱之真言。甚可言,孙子楚之形为扁,阿宝之形为圆;各自性格,皆源其心,确有人之灵性,如言:“多具人情,和易可亲”。[3]较之离魂先作,其人物形象模糊、乏实,受控于作者,此等不足,皆为《阿宝》所超。
再次,于思想内容而言,以《阿宝》为代表之离魂诸作,其思想多较之以往先进。《阿宝》之蕴含,固有其深:其一,蒲翁所塑之情痴形象,是为其理想形象而颂扬,显受晚明思潮影响,诚可谓于宗法专制之反叛。其于《聊斋》所塑之人物昭彰此思,如言:“在他的作品中多少保留了晚明那种叛经离道、嘲圣骂贤的气象”、“但他的思想主要受王守仁心学特别是王学左派主张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16];并以痴性为重,阿宝与孙子楚皆是也,“他把它(痴)上升为人生观的高度来认识,他笔下的痴是把人性中最纯净,纯粹的部分提炼出来,凝聚成一种美,其核心是真。”[17]细品之后方可皆晓,蒲翁于其作力唤人性返璞归真,寄寓自我崇高之人格理想;亦可知,阿宝及孙子楚等形象,即是作者所求,此二人所昭示之情性,其真其诚,皆合人性。如此思想,乃离魂文学之思想呈深变之标志也,已于先作之世俗性脱离,足以其证。其二,孙子楚求爱于阿宝,以其执着终感阿宝,阿宝亦“誓死相从”,迫其父母认可婚事。二人成婚“居三年”,孙子楚“忽病消渴卒”,致使阿宝“哭之痛,泪眼不睛”,其痴情得感冥王“姑赐再生”。由此情节,可知晓二人同痴于情。原先孙子楚痴于阿宝,不顾生死而求之,故后有阿宝痴于情,得救丈夫起死回生,如此挚爱,鬼神亦为之所感,此乃于封建婚姻之有形反抗。其三,以往先作其离魂者皆为女性,然《阿宝》却如前文所论,乃男性为爱而离魂,诚可谓离魂文学之大开创也。男性不仅离魂,且甘愿断指、甘愿化鸟,以求真情,似于封建男尊女卑观念之颠覆,不论男女之分,皆应为己爱所付出。
最后,《阿宝》之艺术技巧,甚促离魂文学之叙事及描写技巧。首先,情节行进时,主动态、重神似,以精湛叙事技巧造离奇曲折之故事情节;然如此巧设情节之同时,亦有意于形象之塑造;或言人物形象之产生与变化,皆伴于情节之所变及其新构,如言:“从故事情节的发展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揭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反过来,又从生动逼真、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的雕塑中来加强小说的故事性和行动性”,[15]如为显阿宝之绝色容貌,蒲翁遂设三次重点渲染,以求衬托阿宝之美。其一当为“绝色也”之语,此三字可谓惜墨如金,总括阿宝之美,置其美呈若隐若现之妙,出于阅者视野,此为直接描写;其二“众情颠倒,品头题足,纷纷若狂”,蒲翁以恶少之颠倒狂态,反衬阿宝之美,亦于前文“娟丽无双”之描成对比。遂可知,蒲翁复避人物形象之正面传达。其三者,乃如言“群成之曰:魂随阿宝去耶?”,孙子楚反应亦衬阿宝“美如天人”。此三次重点渲染处,即有直描亦有间写,且其笔法由隐到显,得塑完美形象,此乃《阿宝》于离魂文学描写手法之突破也。其次,行为描写,多简笔而用力于细节,然其所写实为精选,甚能现出人物形象之言行及细节,以蕴诸多内涵。如“女戏曰:‘渠去其枝指,余当归之’”,乍看随意之嫌经细品亦颇有意蕴,字简而意传神,仅一言一行即现丰满人物;亦将孙子楚托媒求婚之事,及阿宝戏之以拒之事清晰写出。除此之外,此等艺术用笔,于斯文俯拾皆是,概无赘述。
总而言之,《聊斋志异》中之《阿宝》,以其艺术创新之独特,复创离魂文学又一次发展演变,可概为第四次;早已成熟之离魂主题,复至新高,若言《阿宝》为离魂文学之巅峰,经上文所述,概不为过。虽如此,其由招魂而映射出之神怪思想;乃至后文孙子楚得以还魂之因果观念;或因痴情而“誓死相从”之婚姻观念,可谓愚痴;此些“一系列唯心论的思想倾向”,[18]若批评继之,方可见《阿宝》之全妙,得离魂文学其精。
[1]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M].郑海,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499.
[2]汪绍楹注.搜神记(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0:9.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32,117.
[4]冯俊杰.郑光祖杂剧本事汇编.北京: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515.
[5]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9:196.
[6]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国书店影印,2010.
[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四川:成都古籍书店影印,1981:149,435.
[8]黎靖德.朱子语类: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9:47,37.
[9]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杨庸,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10]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121,101.
[11]王海宁.从《阿宝》看蒲松龄心目中理想的夫妻模式[J].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3):42—43.
[1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7.
[13]吴九成.聊斋美学[M].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18.
[14]杨萍.浅析《聊斋志异》中的情痴形象的审美情趣[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3):61—63.
[15]杨柳.聊斋志异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92,99.
[16]何天杰.晚明启蒙思潮在《聊斋志异》中的回响[J].学术研究,1992,(5):127—131.
[17]左勇慧.浅谈《阿宝》孙子楚形象的“痴”[J].安徽文学,2008,(11):165—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