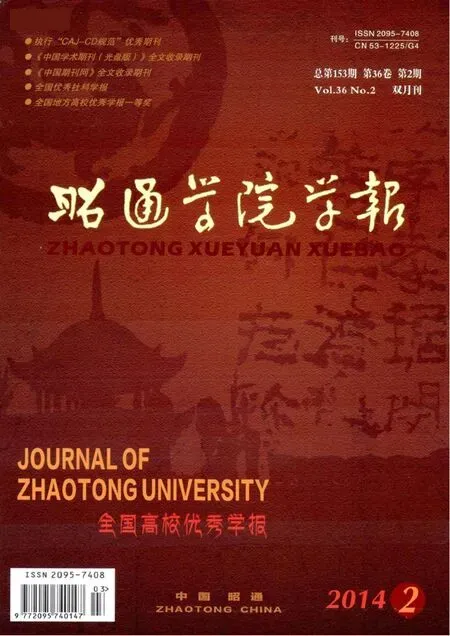曹丕《典论·论文》中的文学观浅析
付 芮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P.177)。就在这一玄学兴盛和精 神自由 的时期,出现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第一部作家论专篇——曹丕《典论·论文》。它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宏观地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问题的专著,冲击了汉代后期统治文坛的陈腐观念,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和新经验,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例。
《典论·论文》以“文”为题,实际上探讨的是“文人”。才性论是魏晋清谈的主要话题之一,《典论·论文》受魏晋玄学影响,深入探讨了作家气质、个性与文学文体及风格的关系,在讨论文体的同时也评论作家,在阐释文气之论的同时也强调文学的价值和社会功用,其独特的理论观点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经国之大业”说
著名的辞赋家杨雄早年热衷于辞赋创作,后来却在《法言·吾子》中称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而在曹丕的《典论·论文》里,对文章的价值和作用给了从未有过的崇高评价:“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谓是开启了文学自觉的先声。“经国之大业”,将文章提高到与事功并立的地位,前所未有;而“不朽之盛事”,则侧重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不懈追寻。关于儒家的“三不朽”,早在春秋时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叔孙豹就说过:“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2](P.1919)按照儒家“三不朽”的原则,“立功”次于“立德”,“立言”居于最末,文学只是教化的工具,“立言”是为“立德”、“立功”服务的。关于这点,早在《毛诗序》中就记载了诗“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作用,正所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3](P.107)。
但是不同于儒家的文学观,曹丕把文章提到了比“立功”、“立德”更为重要的地位,“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只有文章比个人的生死寿命和现实生活的荣耀与欢乐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他把对文章价值和作用的认识,最终落实到个体生命的成就和声名的不朽长存,落脚到个体人格的完善和认识价值的彰显。作为个体的生命,人生的价值不再是追求富贵安乐,而是“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其人格和名声的不朽“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是将身心投入到著书之中,借“文章之无穷”,最终实现“声名自传于后”。
著书如此重要,其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所以他鼓励文人珍惜时光,不为饥寒所迫,不为富贵所惑,“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全身心地投入到发愤而著书中,更有先辈“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我们要努力实现他们一样的卓越成就,永垂后世。曹丕自己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却以文才为重,不仅说明对文学的重视,还说明他的文学观已突破了儒家传统文学观的禁锢。
二、“文气”说
关于“文气”说,曹丕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作为《典论·论文》的核心范畴,“文气”说的本质就是“作家才性论”,正如朱东润先生指出:“子桓之所谓气,指才性而言……又《典论》称‘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与吴质书》言‘公幹有逸气’,其所指者,皆不外才性也。”[4](P.23-24)同时,王瑶先生也赞同这种观点,他在《中古文学史论》中说到:“这种禀赋之气底表现,就是人的才性;而文即才性底表现。才性因了赋受的多寡清浊而有昏明,则文之‘引气不齐,巧拙有素’,也是不可‘力强而致的’”[5](P.65)。
作家的才性,也就是“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和个性气质,从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风。有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清逸奔放,就有老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沉痛哀吟,有李商隐“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的缠绵婉约,就有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引吭高歌。这些不同的风格,就是作者精神气质在诗文中的体现。文气的形成与作者的生活体验、个性禀赋、思想修养、艺术修养的等密不可分,从而不同的作家也展示出不同的文气。
作家“才性异区”、“各师成心”、“其异如面”,那么文气自然也是不尽相同的,曹丕便将文气主要归结为“气之清浊有体”,即“清气”和“浊气”。以“建安七子”为例,曹丕一方面肯定建安七子各有特长,王粲“善于辞赋”,陈琳、阮瑀“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认识到文学创作需要特殊的才能;另一方面,则以“清”、“浊”为标准对七子的才性进行划分,指出他们不同才性特征显示出的不同风格。如徐幹“时有齐气”,代表了舒缓阴柔的风格,反映在作品上就是“辞意典雅”,同样带有阴柔的还有“和而不壮”的应玚。与之文风相反的则是“壮而不密”的刘祯,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公幹有逸气”,代表了一种高逸雄健的风格,虽刚健洒脱但文辞粗糙。
此外,曹丕还强调了文气的独特性和不可改变性,“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最鲜明的莫过于曹氏父子三人,虽为父子兄弟,但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文风,“曹公忙忙,古直悲凉”的英雄之诗,曹丕哀婉淡逸的文士之诗,曹植“天下才有一石,独占八斗”的才子之诗。父子三人,气质个性各异,诗歌作品的体貌风格亦别,而三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正是他们各自不同的创作个性和诗歌风格所决定的。
三、文本同而末异
“文本同而末异”又是《典论·论文》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唐开元时五臣共注之《文选》中,吕向说:“有此篇,论文章之体也。”曹丕“论文章之体”是其批评论逻辑的展开,他在《典论·论文》中提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里所指的“本”与“末”,分别就文学的本质特征和文体特征而言的,属于曹丕的“文体论”。任何文体,都是通过语言文字来传达自己的情感思想,“本”是相同的;同时,不同的问题在表达方式、语言风格、体貌情性方面又有各有千秋,其“末”就是相异的。
他据此概括了各种问题写作的原则和要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也可称之为“四科八体”。大体上说,奏议书论属于无韵之笔,銘诔诗赋属有韵之文,而“末异”中的“雅”、“丽”、“实”、“理”,是对不同文章展现出来的体貌风格的综合概括。奏议之类的公文,讨论的多是朝廷和军国大事,所以语言应侧重于典雅大气。子书和论文的写作,辨命析理,在言辞适宜的前提下,更要注重道理的阐释。铭文、诔文向来夸张其词,曹丕反对这种谀墓风气,认为碑诔之作也应当朴实无华、实事求是。值得一提的是曹丕对于诗赋特征的的概括,一个“丽”字,则标示出文学作品与应用型文体的区别所在,表明他对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有了初步的认识。曹丕之前,杨雄提出过“诗人之赋丽以则”,便是抹杀了作品的艺术性而只看到了“则”的社会功用。曹丕的“诗赋欲丽”将文学从“诗言志”的附庸下解脱出来,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从而实现了文学的独立和文学的自觉意识。
综上所述,曹丕的《典论·论文》中对很多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全新的看法,其中的某些观点对于后来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都有重要的影响。鲁迅先生曾说过:“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6](P.504),《典论·论文》的诞生,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到来的象征,为后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生命情趣。
[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朱东润.中国批评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6]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8]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9]周振甫.文心雕龙译注[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0]袁济喜.六朝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