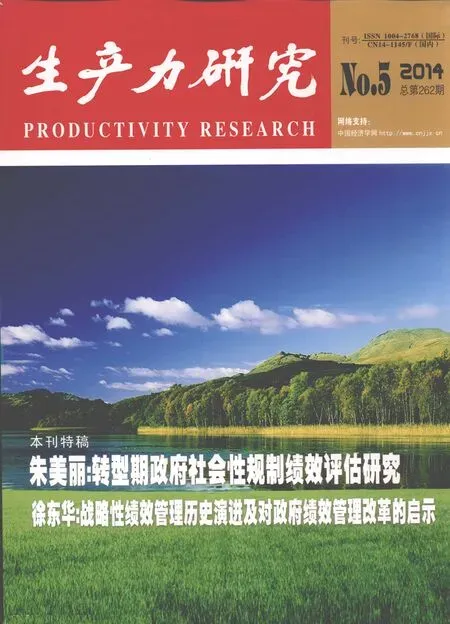战略性绩效管理历史演进及对政府绩效管理改革的启示
徐东华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陆续召开,不仅描绘了中国梦的伟大愿景及其实施路线图,也进一步吹响了深化改革的“号角”。中国梦的实现程度,关键取决于各级政府率领全国人民所能干出的实绩水平高低。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那么,当前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发展现状如何?应该运用什么管理理论来指导、推动政府绩效管理改革实践?本文根据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先探讨战略性绩效管理的历史演进及思想本质,再据此梳理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思路及对策。
一、绩效管理在管理中的地位
自1911年“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泰勒因提出科学管理理论而标志着管理学诞生以来,管理思想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管理实践的不断推进迅猛发展,各种管理学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至今,管理理论“丛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而各种管理流派无一不与绩效管理密切相关,都涉及到绩效管理及提升问题。可以说,一部百余年管理思想的发展史,也是一部绩效管理思想的演变史。
现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明确阐释了管理、绩效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1]管理之所以会产生、存在并发展,就是因为它专注于绩效。而且,管理具有三项同等重要的任务:(1)达成组织特定的使命及目标;(2)使工作富有生产力,并使员工取得成就;(3)增强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责任。[2]可见,绩效管理在管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特殊地位。而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绩效管理属于人力资源管理范畴,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职能,而人力资源管理又是现代管理的核心内容。由此,绩效管理是现代管理的重中之重、核心之“核心”。管理者几乎所有活动,都是围绕如何提高组织及员工绩效而展开的。
二、战略性绩效管理的历史演进
绩效是指组织及个人的履职表现和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是组织期望的为实现其目标而展现在组织不同层面上的工作行为及其结果,它是组织的使命、核心价值观、愿景及战略的重要表现形式。绩效是分层次的,根据被衡量行为主体,绩效可划分为组织绩效、群体绩效和个人绩效。这三种绩效至上而下是层层分解的,而从下往上是逐层支撑的。组织绩效必须通过部门及个人绩效才能完全实现,个人绩效虽然最容易实现,但是组织绩效的战略价值最高,因此是管理追求的最终目标。随着管理实践与理论的发展,组织绩效实践与思想经历了从绩效评价、到绩效管理、再到战略性绩效管理的发展演变过程。
1.绩效评价阶段(20世纪70年代之前)。绩效评价(performance appraisal,PA)通常也称作绩效考核,绩效评估,是评价主体应用一定的方法对评价对象在一定时期内的绩效进行评判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漫长时期,都是绩效评价的主导时期。绩效评价自古有之,不过早期主要应用于军队和政府组织中,那是因为军队和政府组织规模庞大、地理位置分散,具有官僚科层制结构,必须通过绩效评价把那些工作表现出色的官员甄别出来,将之提拔到高层岗位上。例如,我国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采用“上计制”考核官员政绩,即地方官员定期向朝廷呈送上计文书,报告辖区内的治理状况。古代组织的绩效评价基本都是非正规性评价,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有规律的常规绩效评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已经蔚然成风。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勒及其追随者、“动作研究之父”弗兰克·B·吉尔布雷思等人对绩效评价进行了有目的、有计划的探索和实践。为了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他们对工人的工作及动作进行细致、科学地分析,获得“最佳唯一的”(one best way)工作方法,并将之固化下来,形成规范的工作制度,要求工人严格遵照执行;而且,重视评价工人的工作产量,实施“计件工资制”,以加强员工激励,根据工人经绩效评价后的实际工作表现,而不是按工作类别来支付工资。[3]早期绩效评价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一味追求工作效率的做法,最后导致了工人的不满和厌烦,罢工此起彼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及管理实践的发展,绩效评价也迅速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有规律实施绩效评价的组织大幅增加。研究数据表明,到50年代早期,美国已经有61%的组织有规律地实施绩效评价,远远地超过二战刚结束时的15%的比例,而且有50%~75%的大公司实施了绩效评价;而在欧洲,实施绩效评价的大公司的比例也于60年代达到了50%~75%。[4]其二,绩效评价的对象也从仅重视员工评价向同时重视员工和组织两方面评价方向发展,组织绩效评价成为绩效评价的另一个重点。例如,美国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颁布总统令,要求所有联邦政府部门实行“计划——项目——预算制度”(PPBS),以加强总统对联邦政府各部门行政活动和预算的绩效控制。[5]部门预算控制及效果评价一直主导着60年代前后时期美国政府的绩效评价。该时期绩效评价仍以效率评价为主线,而且侧重于财务指标的考核。这种片面、狭隘的绩效评价越来越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
而事实上,早期绩效评价“见钱不见人”的做法及其危害已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尤其是管理学家和心理学家一直在探寻解决问题的良方。也正是这种探索过程,促使绩效管理思想逐渐萌芽和产生,并推动绩效评价向绩效管理转变。因此,绩效评价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正是绩效管理的孕育与成熟过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籍澳大利亚人乔治·埃尔顿·梅奥主持了著名的“霍桑实验”,揭开了组织中人的行为研究的序幕,并据此提出人际关系学说,奠定了行为科学的根基。人际关系学说注重人的因素和非正式组织的影响,强调满足员工各种社会需求,并通过内在激励驱使员工好好工作,以提升员工绩效。人际关系学说和行为科学突破了科学管理理论单纯重视员工效率评价的思维定势,延伸和拓宽了绩效评价的视野、充实了绩效评价的思想内容,再加上受美籍奥地利学者L.V.贝塔朗菲(L.Von.Bertalanffy)于40年代所创立的系统论思想的影响,促使绩效管理思想发酵和萌芽。而且,德鲁克于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一书,提出了目标管理思想。目标管理融合了科学管理理论与人际关系学说两者的优点,既“重视物”,也“重视人”,强调员工自我管理,支持员工参与目标制定,并通过监控和评价目标实现程度以优化管理过程,从而从思想和工具准备上进一步支撑与推动了绩效管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2.绩效管理阶段(20世纪70—90年代)。不容置疑的是,在早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社会环境比较稳定和明了的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传统的绩效评价对于促进组织管理和发展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7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全面复苏与繁荣,世界开始转型和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环境也日益复杂,仅侧重于财务指标的“秋后算账式”的传统绩效评价已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绩效管理日益受到管理研究者及实践者们的重视,并开始取代绩效评价。绩效管理时代已经到来。
绩效管理(performance management,PM)是指识别、衡量及开发个人、团队和组织绩效,并使之与组织组织目标保持一致的一个持续性过程。[6]显然,绩效管理是在绩效评价的基础上产生的,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绩效管理是一个完整的管理过程,注重信息的沟通和绩效目标的达成,伴随管理活动的全过程;而绩效评价只是绩效管理中的一个环节,重视评价考核,只出现在特定的时期,只是事后评价。可见,在绩效管理阶段,绩效评价不仅没有被抛弃,反而得到了发展,这主要体现为:一是在保留财务指标评价的同时,开始引入非财务指标评价;二是探索与组织战略建立联系,比如80年代出现的关键绩效指标就是尝试以战略为导向,通过承接和分解依次构建组织、部门及个人绩效指标,以实现绩效评价与组织战略之间的协同。
从绩效评价发展到绩效管理,是组织绩效实践及思想的重大进步,但是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及管理理念及工具的制约,绩效管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它虽然已经开始尝试与组织战略建立联系,以提高自身战略地位,但是由于当时缺乏科学、合适的配套理念及工具,还不能实现与组织战略之间的“无缝”联接,仍局限在运营管理范围之内,主要还是侧重于事务性管理或任务管理,因此对组织的价值贡献仍比较有限。
3.战略性绩效管理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信息网络广泛应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无形资产的作用日渐凸显,不确定复杂因素持续增多,人们对以财务指标为主的传统绩效评价模式提出了质疑。为适应新形势下新的发展要求,组织必须高度关注战略管理,统筹、协调人、财、物、时间及信息等各种资源,聚焦并服务于核心战略的实施,持续提升组织竞争优势。因此,基于组织战略的绩效管理,即战略性绩效管理应运而生。
1990年,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罗伯特·卡普兰教授和诺兰诺顿的执行总裁戴维·诺顿带领一个研究小组对12家公司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以探求一种新的绩效评价方法。1992年,他们将研究结果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提炼,并在《哈佛商业评论》(1—2月号)上发表了《平衡计分卡——驱动业绩的衡量体系》一文,标志着平衡计分卡(the Balanced Scorecard,BSC)正式问世。平衡计分卡从客户、内部业务流程以及学习与成长等几个层面丰富和拓展了绩效评价指标,弥补了传统财务指标的不足,促使企业在了解财务结果的同时,能对自己在增强未来发展能力方面取得的进展进行监督。[7]此后,两位大师不断完善和发展平衡计分卡理论,陆续出版了五部专著,促使其从最初只用于绩效评价,后来用于绩效管理,至今再发展成为一套能够将战略与运营有效联系起来的综合战略管理体系。[8]平衡计分卡理论及工具的产生与发展,使得绩效管理与组织战略之间的“无缝”对接成为必然趋势,促进了战略性绩效管理的产生与发展。
从绩效评价、到绩效管理,再到现在的战略性绩效管理,组织绩效实践及思想经历了从非正规到正规、从经验到科学、从封闭到开放、从片面到全面、从分化到融合的蜕变过程。今后,战略性绩效管理将进一步向科学化、可操作化方向发展。
三、战略性绩效管理的思想本质
战略性绩效管理(strategic performance management,SPM)是指组织及其管理者在组织的使命与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为达成愿景和战略目标而进行绩效计划、绩效实施(含绩效监控与辅导)、绩效评价(含绩效审计)、绩效报告以及绩效反馈的循环过程,其目的是为了确保组织成员的工作行为和工作结果与组织期望的目标保持一致,通过持续提升个人、部门以及组织的绩效水平,最终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战略性绩效管理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随着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不断发展,绩效管理思想也获得了“解放”,不再拘泥于自身,而是把注意力转向并集中于组织战略,以及与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其他各项管理职能的相互协调上。战略性绩效管理与绩效管理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侧重于推进战略管理,而后者侧重于推进运营管理。
战略性绩效管理既不是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也不是时间管理,不过包含有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它要求管理者在过程前就关注质量,否则到过程结束再重视质量则为时已晚;要求管理者制定并明确目标,并采取一系列行动确保目标的达成;促使管理者行为过程的时间管理,准确把握推进每个环节的最佳时机。战略性绩效管理与战略管理之间关系尤为密切,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管理一般包括战略分析、战略制定、战略实施以及战略评估与控制四个过程,而战略性绩效管理的几个主要环节,至少与战略管理的“后端”即战略实施、战略评估与控制两个过程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是这两个过程的具体执行和落实活动。因此,战略性绩效管理是有效实施组织战略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及手段。
四、对我国政府绩效管理改革的相关启示
(一)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实践探索及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政府仅重视绩效评价实践探索及制度建设。这种状况一直到2008年才有所改变,绩效管理开始进入政府工作的视野,出现在中央文件之中。2008年,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提到“绩效管理”这一术语。至此,政府绩效管理制度上升为国家政策,成为政府关注的问题。为进一步指导、协调和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工作,2011年3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政府绩效管理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监察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务员局)、审计署、统计局、法制办等9个部门组成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监察部。不久后,监察部印发了《关于开展政府绩效管理试点工作的意见》,并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北京市、吉林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杭州市、深圳市等8个地区进行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绩效管理试点,国土资源部、农业部、质检总局进行国务院机构绩效管理试点,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进行节能减排专项工作绩效管理试点,财政部进行财政预算资金绩效管理试点,为全面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探索积累经验。按照国家关于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要求,各地各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府绩效管理政策,以规范政府绩效管理工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的精神,促进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2013年12月,中央组织部出台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要求,“政绩考核要突出科学发展导向”,“对限制开发区域不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而且,“选人用人不能简单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论英雄”。可见,我国政府绩效管理不断向科学化、规范化及常态化方向发展。
然而,当前我国政府绩效管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理念滞后。尽管中央出台的相关政策提出,推进政府绩效管理,但是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多数组织仍以绩效评价及传统的绩效管理为主,战略性绩效管理不仅在思想上尚未受到真正重视,实践中也未得到充分落实。二是与政府愿景及战略脱节。许多组织仍缺乏清晰的使命、核心价值观、愿景与战略陈述,致使绩效管理与之脱节,从而还停留在事务性管理水平上,无法回应和“服务”于组织愿景及战略实施。三是体系与法律不健全。许多组织仍缺乏系统性思考,采取“设定目标——秋后算账”片面管理方式,仅重视绩效评价而忽视绩效管理;而且,绩效管理法治化水平不高,缺乏专项法律支撑,从而难以形成良好的绩效管理长效机制。四是工具与技术落后。绩效管理缺乏先进、科学的工具与技术支撑,习惯于按往常惯例与经验进行管理,工具比较落后。此外,绩效文化、管理机构与队伍建设也比较滞后,诸如“四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政出多门、队伍专业素养薄弱等问题,也制约着政府绩效管理实施及绩效改进。
(二)我国政府绩效管理改革的主要思路及对策
我国政府应该应用战略性绩效管理理论及工具,大力推进绩效管理改革与创新。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创新管理理念。政府不仅要由单纯重视经济增长的片面政绩观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理念转变,也要由片面重视绩效评价的传统管理理念向全面重视战略性绩效管理的先进管理理念转变。管理实践表明,绩效不是“考”出来的,而是“管”出来的。只关注“秋后算账式”的绩效评价难以真正提升政府绩效,只有重视绩效计划、绩效实施、绩效评价、绩效反馈及绩效沟通的循环管理,才能确保政府绩效产出与组织愿景及战略目标高度一致。
第二,健全管理体系与法律。政府要改变单纯重视绩效评价的不良做法,构建并实施完整的战略性绩效管理系统,通过依次确定组织使命、核心价值观、愿景和战略,再开展绩效计划、绩效实施、绩效评价、绩效反馈、绩效沟通的循环式管理,确保政府绩效从一开始就维持在较高水平状态。而且,重视绩效管理立法,提高其法制化水平。可借鉴美国联邦政府的相关经验。早在1993年,美国联邦政府就颁布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PRA),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制度。2010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政府绩效与结果修正法案》(GPRAMA),对《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修正与完善,要求各联邦机构向美国管理和预算署(OMB)与国会提交至少向后覆盖四年的战略规划,同时规定至少每三年对战略规划修订一次,并将之发布在部门网站上,接受社会各届监督;[9]与之配套的是,每个财政年度之初各机构必须向总统和国会提交一份年度绩效计划,明确年度绩效目标和考核指标,年后提交一份年度绩效报告,陈述年度绩效计划中确立的绩效指标、特定工作完成及相应责任落实及追究情况。
第三,导入科学的管理工具。政府绩效管理不仅要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制度基础,也要有科学的管理工具与技术支撑。仅凭既有惯例及经验来管理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管理的新要求,政府应该选用并导入当前世界上先进的,且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绩效管理工具。建议积极推进平衡计分卡的中国化模式研究及实践,以破解当下政府绩效管理工具缺失及本领“恐慌”问题。平衡计分卡自1992年诞生起就显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1 000强公司中,有70%的公司使用了平衡计分卡系统;《哈佛商业评论》更是将平衡计分卡评为75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战略管理工具。鉴于其在理念上的先进性和应用上的有效性,许多政府组织将之应用到各自的战略性绩效管理体系中。研究表明,2004年美国约8%的地方议会、11个州政府以及10个联邦政府机构已采用平衡计分卡;[10]2007年澳大利亚约11%的地方政府已推行平衡计分卡,约44%的地方政府正考虑采用该工具。[11]各级政府应该探索应用像平衡计分卡这种科学的管理工具,以推进政府绩效管理工作。
第四,加强绩效文化及队伍建设。政府绩效管理不应仅停留在制度及技术层面上,更应升华并深入到精神及意识层面,并解决管理队伍存在的专业素养薄弱问题。政府不仅要努力创建高绩效文化,优化绩效管理的“软”环境,克服官僚文化、“人治”文化及特权意识,强化“顾客至上”的公共服务理念、廉洁高效的管理价值取向、注重实绩和责任的行政氛围;而且,优先培养和打造一支掌握战略性绩效管理基本理论与实务能力的高素质专家队伍,为政府绩效管理工作提供坚强可靠的人才支撑。
[1]Peter F.Drucker.Management:Tasks,Responsibilities,Practices.New York:Truman Talley Books.E.P.Dutton,1986:P6.
[2]彼得·德鲁克.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使命篇)[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39-40.
[3]方振邦,徐东华.管理思想百年脉络[M].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
[4]Individual Performance in History.http://www.integrating performance.com/pages/individual-level/profile-and-evolution/individual-perforance-in-history-13.html.
[5]朱立言,张强.美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历史演变[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4.
[6]赫尔曼·阿吉斯.绩效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
[7]罗伯特·卡普兰,戴维·诺顿.平衡计分卡:化战略为行动[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13-14.
[8]罗伯特·卡普兰,戴维·诺顿.平衡计分卡战略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6.
[9]何文盛,蔡明君,王轰,等.美国联邦政府绩效立法演变分析:从GPRA到GPRAM[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94-96.
[10]Holmes S.H.,S.A.G.de Pineres,L.D.Kiel.Reforming Government Agencies Internationally:Is There a Role for the Balanced Scorecard[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6(29):1125-1145.
[11]Perera S.,Schoch H.P.,Sabaratnam.Adoption of the Balanced Scorecard in Local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An Exploratory Study[J].Asia-Pacific Management Accounting Journal,2007(1):5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