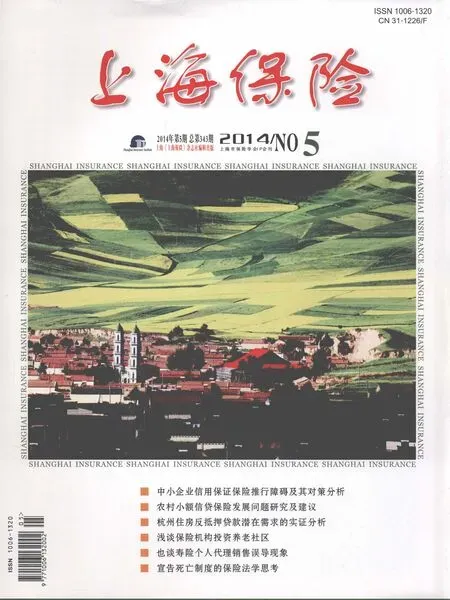宣告死亡制度的保险法学思考
段宏磊
宣告死亡制度的保险法学思考
段宏磊
近年来,伴随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的自我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加强。与此相应地,我国商业保险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据有关数据,我国商业保险机构的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一家发展到现在的一百余家;保费收入从1980年的4.6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72万亿元。与这种蓬勃发展态势相对应的,却是我国保险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尽管2009年开始实施的新《保险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但不可否认,仍有相当数量的保险法学疑难问题急需解决。宣告死亡制度与保险法律制度的衔接问题即是其中比较棘手的一个。宣告死亡制度是我国民法自然人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国《民法通则》第23条规定,公民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下落不明满四年的;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二年的。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时间从战争结束之日起计算。我国宣告死亡制度与《保险法》的若干规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在制度的制定上,二者又缺乏有效的疏通和联系,这直接导致我国宣告死亡制度在保险法范畴内的适用上出现了若干疑问。本文从保险法学角度进行思考,对我国的宣告死亡制度进行解构和探讨,从而为该制度的改革提供若干建议。
一、宣告死亡后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问题
(一)《保险法》中的“死亡”是否包含宣告死亡
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并没有明确把民法中的宣告死亡归入《保险法》中“死亡”一词。但是,从学理上来分析,我国是民商法统一的国家,作为商法单行法的《保险法》与《民法通则》属于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从法律调整的对象来看,《保险法》调整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应属于民法的特别法”。在特别法没有其他规定的情况下,当然应适用普通法中做出的规定,因此,《保险法》中的“死亡”一词应包含宣告死亡。在司法实务中,宣告死亡也通常被法院认定为《保险法》中“死亡”,从而判决保险公司向受益人支付保险金。
(二)宣告死亡后保险公司在何种情况下承担保险责任
在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中,是否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后,保险公司就一定会承担保险责任?笔者认为并不尽然,这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分析。从我国《民法通则》第23条的规定来看,宣告死亡分三种情形:一般情况下的宣告死亡、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所造成的宣告死亡、战争期间下落不明所造成的宣告死亡。笔者认为,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必承担保险责任的,因为这种情形完全可以等同于因战争导致的死亡。众所周知,这是可以归为我国保险业通用的免责事项的。根据保险原理及行业惯例,对于因战争导致的被保险人死亡,各保险公司都是作为免责事项而不予承担保险责任的。
至于一般情况下的宣告死亡和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所造成的宣告死亡,笔者认为,它们原则上都应该进行理赔,除非保险公司在与被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时进行了明确的免责约定,并尽到了审慎的提醒和说明义务。然而,有学者从保险安全性的角度认为,一般情况下的宣告死亡不应该进行理赔。这部分学者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一般情形的宣告死亡缺乏死亡的直接动因(如意外事故或战争),宣告死亡制度的启动仅依赖于四年的下落不明,这存在极大的人为操纵因素,被保险人可以故意隐匿四年时间从而骗取保险金。有学者形象地将此问题概括为“宣告死亡的道德危险问题”,并指出,在这种情形下,保险公司若仍要承担保险责任的话,当事人骗保则是轻而易举的事。为了防止大量骗保事件的产生,从整体上维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这一类保险责任。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失偏颇:其一,它没有把保险公司与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的意思自治考虑在内。尽管对一般情形下的宣告死亡的被保险人进行理赔确实有可能会发生道德风险问题,但保险公司完全可以通过缔约时的免责条款对此进行免责。如果保险公司没有与投保人进行此项免责约定,那么保险公司当然应就其因意思自治所带来的风险承担责任。其二,在保险合同中,保险公司是真正“强势”的一方,保险法律制度的制定应主要致力于限制保险公司的权利而不是相反。与一般合同相比,保险合同表现出了明显的缔约人能力的不平等性。相对于保险公司一方,投保人一方无论是在资本、信息、行动性等各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新修订的《保险法》在更多方面体现出了对投保人一方权利的维护。虽然在实务中,骗保确实是保险业界深恶痛绝的事,其对保险公司和社会秩序的恶劣影响有目共睹,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毕竟是小概率事件。与此相对地,保险人恶意利用信息不对称侵犯被保险人利益的事反而更值得关注。
综上所述,无论是一般情形下的宣告死亡还是因意外事故所造成的宣告死亡,只要在保险合同中没有作出有关免责事项的约定,保险公司即应承担保险责任;而对于因战争期间下落不明所造成的死亡,由于战争致人死亡的免责事项已经存在,则无须单独作出约定,保险公司不必承担理赔责任。如果保险公司在与投保人缔约时,直接约定“宣告死亡”为免责事项,则应尊重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宣告死亡的全体三种情形均不承担保险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保险法》第17条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由此可知,保险公司还负有向投保人做出提示和说明的义务。具体到宣告死亡的相关免责条款,保险公司更负有大于一般免责条款的详尽说明义务。毕竟“宣告死亡”一词属于专业词汇,有相当一部分投保人对此并不了解。如果保险公司的解释不够详尽,将来可能因此引起法律纠纷。
二、宣告死亡申请人顺位制度的存废问题
(一)现行法律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并没有对宣告死亡的申请人进行顺位上的限制,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25条则规定:“申请宣告死亡的利害关系人的顺序是:(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四)其他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还规定,“申请撤销死亡宣告不受上列顺序限制”。根据本条规定,失踪人的配偶因此获得了排他的第一顺位申请权,为配偶滥用申请权打开了法律缺口;而与失踪人具有权利义务关系的非近亲属则需要在排除上述顺序的前三位之后才具备申请权,实质上几乎排除了其申请权。
我国《民通意见》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一方面与贯彻婚姻自主原则相关。如果没有顺序的限制,就可能出现父母要求宣告死亡,但配偶不希望宣告死亡而愿意继续维持婚姻关系的情形。如果满足父母的请求,就会干涉配偶的婚姻自主。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身份利益的维护。由于宣告有配偶的失踪人死亡,不仅关涉财产利益,而且还关涉身份利益,特别是婚姻利益。此项婚姻利益,不仅较财产利益优先,而且也较其他身份利益优先。故而应将配偶列入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之内,且应列为第一顺序。父母与子女,其身份利益仅次于配偶,故而应列为第二顺位。其他亲属,则统统列为第三顺位。亲属之外而有债务关系的人,则列为末位。
(二)主张废除申请人顺位制度的原因
在司法实务中,已经发生了多起配偶或其他近亲属滥用申请权顺位或怠于行使申请权从而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案例。具体到保险法领域,宣告死亡申请人顺位制度的存废则与保险受益人的身份休戚相关。我国《保险法》第39条的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由此可知,受益人既可能是被保险人的配偶或其他近亲属,也可能是其他人,而这些人又分别处于我国《民通意见》第25条所规定的不同顺位之中。在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如果前一顺位受益人恶意怠于申请宣告死亡,处于后一顺位的受益人则无法获得保险金,这显然是极为不公平的。因此,笔者建议废除我国《民通意见》第25条的规定,不对宣告死亡的申请人进行任何顺位上的限制,各利害关系人均享有申请宣告死亡的权利。如此,不仅保险法领域中的疑难问题会得到解决,实务中常见的配偶或其他近亲属怠于行使申请权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案件也能得到公正处理。
三、宣告死亡后死亡推定时间的改革问题
(一)现行死亡推定时间的规定所造成的保险法难题
下落不明的人在被法院宣告死亡后,必然会产生死亡时间的推定问题。我国《民法通则》对此没有进行规定,而《民通意见》第36条的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判决宣告之日为其死亡的日期”。学界则对本条规定存在异议:判决宣告之日是一个不稳定的、可人为操纵的日期,以此为被宣告死亡人的死亡日期,实不合理。
以判决宣告之日为死亡日期的做法,会造成保险法上的若干难题。其一,会使短期身故保险合同在事实上不能理赔。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宣告死亡不但要有一定时间的下落不明,而且还要权利人申请,并经法律诉讼程序,待法官宣判之时,下落不明人才真正被宣告死亡。这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在事实上否定了宣告死亡判决的溯及力,使其仅从判决宣告当日起生效。这便直接造成了短期保险合同的期间不可能包容得下整个法律程序,下落不明人在合同期间内不可能被宣告死亡,致使保险公司不能理赔。其二,会造成各种定期身故保险合同出现一定的“尴尬”期。由于死亡推定时间设置于判决宣告之日,在保险合同期限内发生意外事故的被保险人经常无法在合同期限内被宣告死亡,意外事故的发生日和判决的宣告日之间的这段时间成了保险合同的“尴尬期”。保险公司因此与理赔责任“擦肩而过”,不必支付保险金,这极大地侵害了受益人的利益。其三,会使终身保险的投保人支付保险费的期限被不合理地延长。在终身险情形下,不会发生保险公司不能理赔的状况,但会发生另外一个矛盾:在因意外事故或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下落不明人通常已经不可能生还,但投保人不得不在法定下落不明期间和诉讼程序期间继续支付保险费,直至法院作出最终的判决宣告,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赔。
(二)死亡推定时间的立法选择
通观国际上对宣告死亡后死亡推定时间的立法例,概括起来有四种:第一种是以失踪人的失踪日或意外事故遭遇日为死亡日期,该立法例以瑞士、土耳其为代表;第二种即以判决宣告日为死亡日期,除我国外,奥地利也采用此种立法例;第三种是以法定期满日为死亡日期,代表者为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第四种则是以法官认定日为死亡日期,以法国为代表。
依笔者观点,在这四种立法例中,无论是第二种还是第四种,都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且赋予了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也没有考虑被宣告死亡人的具体失踪情况。如法国所采取的“法官认定日”立法例中,由法官依自由裁量权,根据被宣告死亡人的具体情况确定死亡日期,但这种做法显然不适合中国国情。而采取第一种与第三种相结合的做法,既符合学理,也能解决保险法上的难题。由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的第48条即采取了此种做法:依本条规定,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死亡时间为意外事故结束之日;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死亡时间为战争结束之日;除此之外的情形,则以法定期间届满之日为死亡之日。此规定的合理性在于:对于因意外事故或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事故或战争本身的作用通常直接造成了被宣告人的死亡,被宣告人在下落不明期间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将死亡推定期间提前至事故发生日或战争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