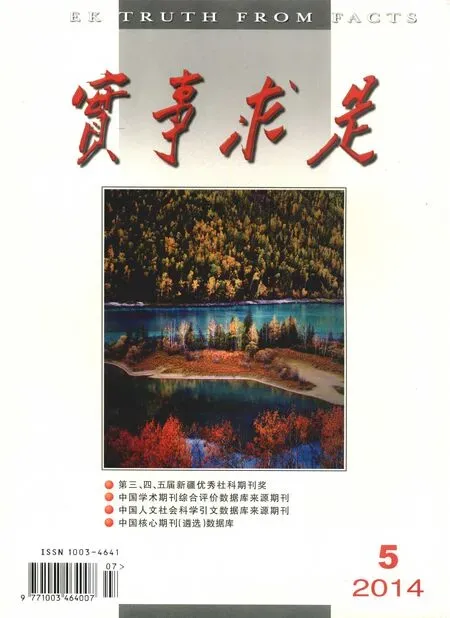论先行调解制度
徐 晨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重庆 401120)
法学
论先行调解制度
徐 晨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重庆 401120)
《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增加的先行调解制度性质上应定位为司法ADR。先行调解宜以法院为主导,融合委托调解形成新的纠纷解决方式,对于适宜先行调解的纠纷,法院从纠纷解决主体变为整合纠纷解决力量的平台。通过先行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具备有限的既判力,且无需经过司法确认程序即具有执行力。
先行调解 司法AD R委托调解 有限既判力
根据程序相适应原理,并非所有的纠纷都适宜通过诉讼程序加以解决,诉讼爆炸的现实情况也决定所有的纠纷通过法院解决不现实。为了缓解司法资源紧缺的现状同时便利公众救济私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在2012年修改后增添了先行调解制度。根据条文解释和体系解释,先行调解属于起诉之后立案受理之前的调解,但仅止步于此尚无法解释法院何以介入尚未系属的纠纷,此种调解制度与其他调解有何区别,在缓解法院压力同时便利公众救济私权上有何独到之处等问题。因此,还需进一步探索先行调解的性质并在此基础上探析该制度运行方式和制度效力。
一、性质定位:司法ADR
根据调解主持者性质的不同,可以将调解分为两类,一是法院调解。该种调解具有司法性质,如诉讼中的调解。第二类可以称之为非司法性质的调解。主持该类调解的组织并非司法机关,如人民调解委员会、行政机关、行业组织等其他组织甚至是个人,可以归入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两种调解最本质的区别就是所达成的调解协议效力不同,非司法性质的组织和机构所主持的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不直接具有强制执行力,不具有既判力,不能从本质上定纷止争;而诉讼中的调解作为结案的法定方式之一,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并能排斥当事人对同一纠纷再行争议。出现这种差别的关键在于诉讼中的调解有审判权作用其中,而调解主持权是法院审判权作用的具体形态之一。
从这一层面来讲,可以通过判断是否有审判权的参与来确定调解是否具有司法属性。一般认为,案件系属于法院后产生法院“必须对事件进行审理的”效果,[1](P149)即审判权开始作用于纠纷解决中。我国实行立案审查制度,立案受理之前,因案件尚未系属,原则上法院并不能通过审判权的运作对纠纷进行处理。因此,如果以审判权是否作用其中为参考标准,存在于此段时间的先行调解显然与诉讼中的调解性质不同,它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司法属性。然而是否不属于司法调解就应当归属于ADR的范畴,这种非此即彼的定位是否恰当还需进一步探讨。
单纯从法条对先行调解的程序性质进行解读恐难以更进一步,不过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实务中就进行了大量的立案之前调解的实践,分析实务中类似实践如何操作对理解该制度的性质大有启发。如陕西省丹凤县法院龙驹法庭进行的立案之前的“诉调对接”模式,对于起诉到法院且未经调解的民间纠纷,法院引导当事人自愿选择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调解人员主要由社区主任或村干部组成,法官对调解员进行指导,调解无法成功的才进入诉讼程序。[2]再如上海浦东法院将法院调解与社会调解结合起来,聘请符合一定条件的街道司法干部、律师、仲裁员甚至退休法官来从事诉前调解工作。当事人达成调解的,可以由法院出具调解书,达不成调解协议的可以直接进入立案程序。[3]分析这些实践可以发现,这些先于立案进行的调解突破了立案对法院审判权作用时间的限制,法院以指导者或引导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这种做法有融合司法和ADR资源的意味。
从域外经验来看,实践中的这种融合是ADR发展与司法适应社会纠纷解决需要的必然趋势。
笔者认为,将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增的先行调解定位司法ADR的理由是:
第一,立法应当是司法实践的总结和高度抽象。自2008年明确提出“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后,法院进行了大量的属于“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范畴”的实践,引导当事人于立案之前通过调解解决纠纷。[4]由于2009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引导法院对立案前的调解进行了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效果,《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亦有学者提出在诉前程序中引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意见。[5](P171)第122条的规定与实践中的做法在整体框架上基本一致,因此先行调解制度应当是实践中的“诉前调解”的立法化。保持一致性有利于以法律的形式统一各地细节上不尽相同的“诉前调解”,也有利于维护司法制度的稳定。
第二,从制度价值性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先行调解必须具备司法ADR的属性。法律规定的原则化与模糊化是为了给实践更多灵活操作的空间。根据第122条的规定,先行调解以当事人自愿为适用前提条件,而适用对象又是当事人起诉到法院、适宜调解的纠纷。说服以寻求司法救济为目的而起诉的当事人自愿选择调解作为纠纷的解决方式,那么替代性制度除了便捷、高效之外还需满足以下两个要求:一具有可以媲美司法救济的终局性和权威性,这需要审判权适当介入弥补ADR终局性的不足;二不因纠纷通过该制度无法解决而额外增加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成本,调解协议无法达成时应能够顺畅转入诉讼程序。这均要求先行调解具备司法ADR之属性,兼具ADR与司法救济之优势互补,否则若还需经过额外的程序才能获得与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的相同效果则必然得不到当事人的青睐,那么先行调解制度必然被现有的其他调解制度架空,立法者设立先行调解之目的亦无法实现。
二、运行方式:各方参与者在先行调解中的角色和地位
1.法院在先行调解中的主导地位。不可否认的是,为达到缓解司法资源紧缺的现实局面,将一些纠纷分流出去不进入审判程序是先行调解制度设计的思路之一。但是分流不能等同于“拒绝”,法院不能拒绝对当事人已经起诉到法院的纠纷的责任。作为司法权的唯一拥有者,法院以“减负”为理由而拒绝行使司法权不具有正当性。先行调解制度的设计不是为了使法院对于一些纠纷“置身事外”,而是尝试转换法院角色,以新的方式高效、便捷地解决纠纷。
在英美法系“司法社会化”运动的第三波浪潮中,西方学者认为“接近正义”的思路是“改变对法院在纠纷解决中的功能的狭隘认识”,法院在纠纷解决中不再仅仅扮演裁判者的传统角色,而是通过为纠纷的解决提供规则或基础,引导社会纠纷中的绝大部分借由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加以解决。[6](P168)
基于上述思路,我国先行调解制度的运行中,法院可以通过选择、融合社会纠纷解决资源形成调解主持力量,引导当事人选择该程序,管理和监督程序运行,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调解不成立即为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
2.社会纠纷解决资源在先行调解中的受委托者地位。法院通过选择、融合社会纠纷解决资源形成先行调解主持力量的设想需要解决法院与社会纠纷解决资源关系的问题,即是法院通过怎样的模式引入社会纠纷解决力量。
如果把法院通过司法权解决纠纷作为一种国家资源,则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属于社会资源,司法ADR可以理解为将两种纠纷解决资源重新整合分配后形成的一种纠纷解决力量。面临现代社会爆炸式的纠纷数量和很多专业性极强的纠纷,以法院审判为主导的传统纠纷解决方式不可能独当一面。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社会转型的结果是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和自治性都大为增加,把一部分纠纷解决资源从国家体制中剥离出来交给社会,对减轻司法压力和促进市民社会的构建都是极有意义的转变。”[7](P3)最能体现社会主体在纠纷解决方面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同时又与司法权联系在一起的方式是委托调解。
首先,由于可以委托不同的组织进行调解,因此委托调解面对种类繁多的纠纷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对于行业、家庭纠纷尤其如此,这一点非常契合先行调解高效便捷解决纠纷的要求。
其次,委托并不是推脱,法院可以挑选有资格的调解组织供当事人选择,监督调节进行过程、审查调解协议等方式主导先行调解程序。
最后,以委托调解为方式进行的先行调解已有实践基础。因此,在先行调解定位为具有司法ADR属性,将大大降低先行调解制度的司法成本。
三、程序效力:调解协议之既判力与执行力
1.既判力。既判力本是作为确定判决的一种拘束力而使用的概念,但是随着既判力理论的发展,学者开始追问除了判决之外,法院做出的其他法律文书如裁定书、调解书等是否具有既判力。同时由于既判力与纠纷解决的终局性和确定性紧密联系,先行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方式之一,就不得不追问,其能否终局确定的解决纠纷,即调解协议是否具有既判力。
既判力的作用具体来讲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禁止当事人就已作出过确定判决的同一纠纷再次起诉或在后诉中就既判力所确定的诉讼标的提出矛盾主张,并且禁止法院受理该重复起诉或接受矛盾主张,此为既判力的消极作用;第二,当本案判决所确定的诉讼标的成为后诉的先决问题时,后诉法院裁判应以前诉为基础,此为既判力的积极作用。[8(]P483)
判断法律文书能否产生既判力归根结底是要探讨既判力产生的根据。判决既判力产生的原因在于诉讼制度的效力要求和程序保障及自我责任。[9]作为法院纠纷解决方式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终结纠纷的能力就无法实现其分流案件减轻法院负担和便利当事人接近正义的设立目的。但是由于调解过程不可能适用严格的诉讼规则,当事人无法获得充足的程序保障,且调解结果可以不严格适用实体法,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多或少的进行让步和妥协,那么调解协议所确定的事实和法律关系极有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种情况下,不能忽略先行调解协议具备既判力积极效力的正当性严重缺失的事实。
为保证先行调解制度能真正发挥其设立目的,同时兼顾因制度特点带来的程序保障缺失和难以符合纠纷真实情况的特点,先行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应以具有有限既判力为宜:即通过先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终结纠纷的效果,但是当该调解协议所确定的法律关系成为另一诉讼的先决条件时,该诉法院可以对此作出相反判断,但该判断的效力不及于先前达成的调解协议。
2.执行力。主要是该调解协议是否还需要司法确认程序才能具有强制执行力的问题。《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新增加的司法确认程序是诉讼与ADR调解进一步对接的产物,反应了国家司法权对ADR的管理和指导。而先行调解具有法院附设诉前调解属性,司法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介入到了调解之中,无需当事人另行申请司法确认程序,法院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直接进行形式审查即可。这也是司法ADR与一般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区别点所在。
四、结语
如果将先行调解制度定义为司法ADR,进而推动我国的司法社会化进程,重新思考法院在现代化的纠纷解决中扮演的角色,进而整合优化解决纠纷的社会资源,可能会对我国司法系统在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一些问题有所益处。
[1] [日]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M].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 李政.对新民事诉讼法“先行调解”的理解与适用——以陕西丹凤县法院“诉调对接”为例.http://www.civilprocedure⁃law.cn/html/fytj_1178_3038.html,2014-03-03.
[3] 唐力,毋爱斌.法院附设诉前调解的实践与模式选择——司法ADR在中国的兴起[J].学海,2012(04).
[4] 奚晓明.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5]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释解[Z].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6] 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7] [澳]娜嘉·亚历山大.全球调解趋势[M].王福华等译,北京:中国法治出版社,2011.
[8] [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9] 许少波.论民事裁定的既判力[J].法律科学,2006(06).
责任编辑:哈丽云
D925.1
A
10.3969/j.issn.1003-4641.2014.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