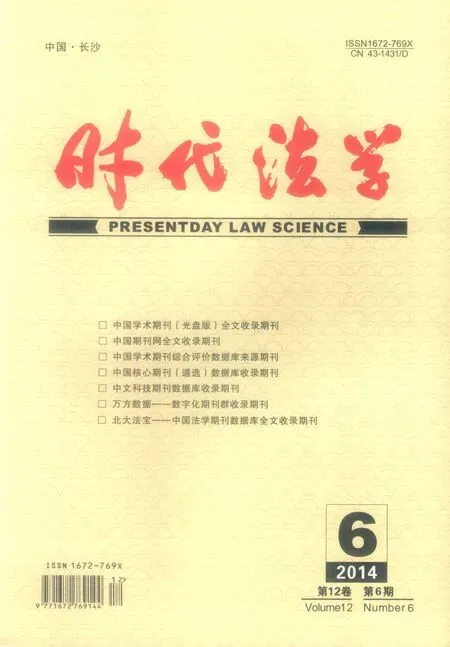诉讼诈骗罪的刑法立法*
马荣春,李 红
(1.扬州大学法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2.上海协力律师事务所,上海 200120)
诉讼诈骗罪的刑法立法*
马荣春1,李 红2
(1.扬州大学法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2.上海协力律师事务所,上海 200120)
诉讼诈骗行为在国外刑法立法中已经被规定为犯罪。社会危害性与现有的规制效果,说明诉讼诈骗行为在我国犯罪化的必要性。在犯罪化之后,诉讼诈骗罪应被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的“妨害司法罪”一节,并可考虑单位犯罪和身份犯等方面而作出具有罪刑阶梯的条文设计。
诉讼诈骗罪;犯罪化;社会危害性;道德风险;妨害司法罪
一、 诉讼诈骗罪的国外立法例
毫无疑问的是,诉讼诈骗这种犯罪现象在国内外都存在着。而国外对诉讼诈骗这种犯罪现象的处置有三种态度:一是按照诈骗罪这一既定罪名予以定罪量刑,二是分不同类型作出区别性规定,三是专设罪名。按照诈骗罪这一既定罪名予以定罪量刑的做法以德国和日本为典型代表,而这一做法与刑法理论界普遍奉行的如下认识有关,即诉讼诈欺先使得法院作出错误判决,再凭借判决来取得财产性利益*[日]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M].顾肖荣等译.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713.。具言之,在传统诈骗罪中,被害人会因为行为人的行为而陷于错误的认识,但在诉讼诈骗中,法官控制了财产的处分权,同时法官由于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像、伪造证据而陷于错误认识,故从二者的行为构造上来看,诉讼诈骗行为与传统的诈骗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故对诉讼诈骗犯罪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刑*张明楷.论三角诈骗[J].法学研究,2004,(2):32.。而分不同类型作出区别性规定的例子如西班牙。西班牙刑法将诉讼诈骗分为侵财型和非侵财型两类。对于侵财型的诉讼诈骗,明确规定按诈骗罪定罪量刑;而对于非侵财性的诉讼诈骗,可分别以伪造公共、官方、商业及电讯文书罪和伪造私人文书罪论处*西班牙刑法典[M].潘灯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94-95.。西班牙刑法所采取的也是那种不专设罪名的做法,但其现有的“区别性规定”却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司法不统一”,因为诉讼诈骗毕竟是一种完整的即具有独立个性的犯罪现象。至于对诉讼诈骗这种犯罪专设罪名的做法,则以意大利和新加坡为代表。意大利刑法第374条规定,在民事或行政诉讼中,行为人有意使用欺诈手段,以欺骗进行调查或取证的法官,使相关的情况包括地点、物品或者人身状况发生改变,或者对鉴定人进行欺诈而使鉴定结果出现错误,对于这些行为,在没有其他法律进行规制时,应当判处6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这一规定不仅适用于刑事诉讼中的非法欺诈行为,也适用于刑事诉讼前的行为*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51.252.。而新加坡刑法第208条规定,采取欺诈性的手段,使法院作出判决,或者使一项法令或命令通过,该法令或命令使起诉者获取了额外的不恰当的利益,这项利益可能大于其本应该获得的数额,或者本没有资格获得却最后额外获得财产及利息,或者使已经被履行的债务再次被执行,则最高可判处2年的有期徒刑,或者处以罚金,或两者并处。该条的罪名是“采用欺骗手段接受非应得数额的判决罪”,并被设置在“伪证及破坏公正司法罪”一章之中*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51.252.。在我们看来,德日按照诈骗罪这一既定罪名来处置诉讼诈骗这一犯罪现象,正如其所奉行的刑法理论所表明的那样,是“类型化解释”即“类型化司法”的一种结果,亦即“三角诈骗”最终是诈骗犯罪的一种类型;而无论是西班牙的“区别性规定”的做法,还是意大利和新加坡专设罪名的做法,正如其刑法立法本身所表明的那样,是“类型化立法”的一种结果,即诉讼诈骗毕竟因可能侵害其他法益或因可能侵害司法公正而不能再被视为纯粹的财产性犯罪。可以这么看问题,专设罪名的做法对于我们更好地解决诉讼诈骗问题或许将提供正面的借鉴,而按照诈骗罪定罪量刑的“传统性”做法或作出“区别性规定”的做法,则或许将提供反面的启示,因为“类型化思维”首先是立法思维,而后才是司法思维包括刑法司法解释思维。另外,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虽然对诉讼诈骗按诈骗罪定罪处罚是日本的传统做法,但主张对诉讼诈骗单独立法的呼声一直未断。这对我们审视诉讼诈骗犯罪的处置问题,或许有所启发。
二、诉讼诈骗犯罪化问题的争论与结论
(一)诉讼诈骗犯罪化问题的缘起
按照最高检《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行为如何适用法律的答复》,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而占有他人财物所侵害的主要是法院的正常审判,即便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也不论以诈骗罪而可由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这便引发了“诉讼诈骗”的定性讨论。有人认为,诉讼诈骗不但骗了法院,而且也骗了被害人,故无论从哪一方,其都具有诈骗罪之结构,即其主张诉讼诈骗这种违法行为应按诈骗罪予以定罪量刑*董玉庭.论诉讼诈骗及其刑法评价[J].中国法学,2004,(2):136.135-140.。但有人认为,诉讼诈骗不构成诈骗罪,或有这样的理由,即由于民事诉讼采取形式真实主义,故利用民事诉讼本身尚非欺诈行为。而在诉讼诈欺中,被害人并非基于错误而是基于对法院判决的不得已服从才交付财物,且被欺骗人与交付财物者并非同一人,亦即欺诈行为与交付财物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不成立诈骗罪*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633.;或有这样的理由,即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毁灭、伪造证据以谋取非法利益,其犯罪化问题只能通过修改刑法完成*董玉庭.论诉讼诈骗及其刑法评价[J].中国法学,2004,(2):136.135-140.。而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说法则是,诈骗罪与“三角欺诈”异形同质,诈骗罪包括“三角诈骗”与诉讼欺诈同形质异,故诉讼欺诈应归入妨碍司法罪*吴玉萍.诉讼欺诈行为定性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4):47-55.。在对诉讼诈骗这种违法行为形成是否应定诈骗罪的认识对立的同时,又形成了是否应定敲诈勒索罪的认识对立,即有人指出,以恶意诉讼为手段而占有他人财物不具有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而应论以敲诈勒索罪*王作富.恶意诉讼侵财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特征[N].检察日报,2003-02-10(3).,即其基本主张对诉讼诈骗可按敲诈勒索罪予以定罪量刑。但有人认为,当事人提供虚假证据向法院起诉,对方败诉而被迫交付财物是基于公权力的强制而非恐惧或精神强制,故不成立敲诈勒索罪*李林.“诉讼诈骗”定性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2010,(4):64.62.68.。是否成立诈骗罪的认识对立和定敲诈勒索罪的不经推敲,使得诉讼诈骗犯罪化的倾向似乎占了“上风”,以至于快要“喊破喉咙”,即有人提出,虽不成立诈骗罪,但在民事诉讼中自行毁灭、伪造证据以谋取非法利益的,应由伪证罪突破刑事诉讼的范围限制予以应对*董玉庭.诉讼诈骗及其刑法评价[J].中国法学,2004,(2):135-140.。如果试图通过“伪证罪”来寻求突破,则“诉讼诈骗”恐怕连其本身的称谓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针对诉讼诈骗必须予以罪刑处置的认识或主张,至于是按既定罪名处置,还是予以专门的犯罪化处置,则先撇之一边,却有一种似显更加“守旧”的声音“逆流而来”,即我国一些学者以外国法律制度作为知识背景,没有把诉讼诈骗放在民事诉讼制度之中而有坐井观天、画地为牢之嫌*李林.“诉讼诈骗”定性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2010,(4):64.62.68.。由于诉讼诈骗的定性主要围绕诈骗罪、三角诈骗罪展开,故按现行法律,诉讼诈骗不应构成犯罪,即最高检《答复》具有合理性*李林.“诉讼诈骗”定性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2010,(4):64.62.68.。
由上交代可见,从是否应该作为犯罪处置,到是否按照现有罪名予以处置,再到是否应形成新的罪刑规定即予以专门的犯罪化,诉讼诈骗的犯罪化问题便构成了我们的直接面对。
(二)诉讼诈骗犯罪化的必要性
必要性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建构一项制度的重要内容,对诉讼诈骗的犯罪化问题亦是如此。之所以对诉讼诈骗是按照既有罪名处置还是增设新的罪条还存有较大争议,甚至还有人主张诉讼诈骗根本就不能视为犯罪,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是对诉讼诈骗犯罪化必要性的认识分歧。在我们看来,诉讼诈骗犯罪化的必要性应从两个层面予以把握:一是诉讼诈骗本身的社会危害性,二是对诉讼诈骗现有规制的效果状况。对于诉讼诈骗的社会危害性,我们很容易想到财产秩序等社会秩序和司法秩序,即诉讼诈骗能够产生财产秩序等社会秩序和司法秩序的多重危害。实际上,如果诉讼诈骗的利益谋求被看成是既包括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则在司法秩序的危害之外,诉讼诈骗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仅体现在财产秩序上,还会体现在其他社会秩序上。只有这样看问题,我们对诉讼诈骗的社会危害性才能“视域”更广。由于“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故在诉讼诈骗中司法正义的受害将被其他社会秩序的受害“烘托”得更加明显。易言之,诉讼诈骗对司法秩序及其所隐含的司法正义的危害与对其他方面社会秩序的危害在一种“交相辉映”之中“膨胀”着诉讼诈骗整体的社会危害性。那就是说,其社会危害性不能仅仅视为诉讼诈骗对司法秩序的危害性和对其他社会秩序包括财产秩序的危害性的简单相加,而可能是一种“相乘”,其更加有力地体现了边沁所提出的“混合型犯罪比单一型犯罪要严重”的犯罪轻重比较规则*[英]吉米·边沁.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M].孙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7-9.。而最为可悲或最令人担忧的是,在此“交相辉映”和“膨胀”之中,人们的法感情会逐步钝化乃至荡然无存,以致于一提起“法律”二字,人们将表现为“嗤之以鼻”或“不屑一顾”,亦即司法正义的受害最终将远远大于财产秩序等其他法益的受害,正如有人指出,诉讼欺诈在扰乱公私财产所有权和正常的诉讼秩序的同时,还损害司法裁判的公正性与权威性,甚至其对司法秩序即司法正义的危害性大大超出普通诈骗侵财行为*李翔,黄京平.论诉讼欺诈的可罚性及其立法完善[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6):28.,因为诉讼诈骗通过使法庭变成非法交易甚至犯罪的场所等负面影响而使得诉讼这一保障社会安定的最后救济手段面临着巨大冲击。正因如此,诉讼欺诈行为应当作出刑法上的否定评价*李翔,黄京平.论诉讼欺诈的可罚性及其立法完善[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6):28.。只有这样看问题,我们对诉讼诈骗的社会危害性才能“视透”更深。
但对诉讼诈骗的社会危害性,我们还不能就这样“浅尝辄止”。江苏某法院在2005年曾经同时受理了两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两个案件的原告分别以100万元和120万元的贷款事由起诉同一被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偿还贷款本息。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事实本身和偿还本息问题很快达成共识并形成调解协议。案件处理之顺利竟让法官都感到有点奇怪,但在进一步调查了解中发现:被告已经在另一起借贷诉讼中败诉,且已进入执行程序。而已经达成的调解协议却掩盖着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虚构事实以图转移财产,进而逃避债务的行为事实*赵秉志.刑法分则要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454.。由于受害人对案件知情,故其尚可提起上诉或申诉,以对挽回自己的不应有的损失而作“最后一搏”,但前述案件中的受害人,如果不是法院在好奇中的偶然发现,或许将永远被蒙在鼓里,即吃一个永远无法“昭雪”的“哑巴亏”。那么,诉讼诈骗这种悄无声息的欺骗性或蒙蔽性,能否使得我们对诉讼诈骗的社会危害性获得一种更新或更深的认识呢?边沁所提出的犯罪轻重比较规则对我们极有启发,即越是隐蔽而不容易被揭露的犯罪,其社会危害性越重,因为其带给人们的恐慌因越隐蔽而越大*[英]吉米·边沁.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M].孙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7-9.。那么,当我们对诉讼诈骗的社会危害性有了更加全面且深入的认识,则我们对诉讼诈骗的犯罪化的接受便当然会相对容易一些。
再就诉讼诈骗的现有规制效果而言,诉讼诈骗这种违法现象呈现出一种上升趋势,尤其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等沿海省份,其常见类型有通过纯粹地虚构事实而使他人遭受损失,或歪曲事实而使他人重复履行已经履行过的债务等。这些诉讼诈骗现象不仅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包括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还严重地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介晓宇.诉讼诈骗的定性及其法律规制[D].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15-16.。诉讼诈骗这种违法现象有增无减说明对诉讼诈骗的现有规制是乏力或效果微弱的。那么,对诉讼诈骗的规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伪造重要证据或者虚假陈述而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或拘留,而若构成犯罪的,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4条,对妨害民事诉讼的个人的最高罚款限额是1万元,对单位则是30万元,拘留的最高期限是15日。首先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而言,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实施伪造证据等诉讼诈骗行为,尚无相应的罪条与之对应,亦即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民事诉讼当事人实施的伪造证据等诉讼诈骗行为只能论以无罪;再就对妨碍民事诉讼的罚款和拘留规定而言,乍看上去其惩罚力度委实不小,但在诉讼诈骗可能获得的利益面前,那只是有可能付出的代价便不足挂齿或大可值得去冒险。而在司法实践中,包括诉讼诈骗这种情形在内的妨碍民事诉讼的程序性责任追究,也较少被落实到位。那么,诉讼诈骗规制现状所存在的问题,或许正如有人指出,诉讼诈骗的行为方式,或是行为人(当事人)自己毁灭、伪造证据,或是行为人(当事人)通过其他人包括证人等向法院提供虚假证据。而第二种行为类型,刑法其实已有规定*董玉庭.论诉讼诈骗及其刑法评价[J].中国法学,2004,(2):139.。那么,针对刑法还没有规定的情形,考虑到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协调,刑法自应作出相应的规定。否则,民事诉讼法上的规定就变成了空文,导致法条虚置,无法保证法律横向之间的配套协调,刑法也因而失去了其后盾法和保障法应有的作用和地位*李翔,黄京平.论诉讼欺诈的可罚性及其立法完善[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6):28.。此种状况,正如有人指出,诉讼欺诈行为之所以高发,一方面因为一些人受到利益驱动,一方面也因为法院判决的效力对行为人的极强吸引力,但更因为现行刑法对诉讼欺诈行为的“盲视”*曲艳红.论诉讼欺诈[D].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14-15.。
其实,对包括诉讼诈骗在内的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仅有的程序性规定及其很不到位的落实,使得我们可以联系违法收益与违法成本来考察问题。具言之,罚款或拘留这样的程序性制裁相当于包括诉讼诈骗在内的妨碍民事诉讼行为的违法成本,而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利益所在便相当于违法收益。于是,当违法收益与违法成本的比值即违法效益具有相当的诱惑力时,则包括诉讼诈骗在内的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实施便在“按奈不住”之中。当某起事实上的诉讼诈骗收获了行为人预期的利益即犯罪收益,其竟然没有受到刑事制裁即没有付出犯罪成本,则其诉讼诈骗的犯罪效益便大得无法再大,即其诉讼诈骗的犯罪诱惑力便达到极致。显然,在目前规制状态下所发生的诉讼诈骗,便可用以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命题的“新古典经济学”即“标准经济学”予以解释。那么,回过头来,诉讼诈骗这种违法现象的有增无减便不足为怪或在情理之中了。
社会危害性与规制效果的现实态势两相结合,使得诉讼诈骗确有犯罪化即增设罪刑条文的必要。有人强调,对社会控制来说,没有什么比造就一个法律权威更有效和更经济,因为一旦树立起权威,便意味着人们的行为不需要太多的社会压力而取向于理性的社会合作*[英]洛克.政府论(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那就让我们从中体味诉讼诈骗犯罪化即予以罪刑增设的必要性吧。
(三)对诉讼诈骗非罪化主张的辩驳
有人立于民事诉讼制度本身而不主张将诉讼诈骗犯罪化。如其指出,在我国,审查证据材料、查证案件事实是法院的义务。如果再赋予当事人提供真实证据的义务,便意味着法院把相应的义务转嫁给当事人。而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制度要求当事人必须如实提供陈述和证据,即禁止当事人作假证。这是当事人主义模式所决定的。论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诉讼诈骗”在我国的犯罪化缺少制度基础。易言之,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中“诉讼诈骗”犯罪化存在着制度基础,但在我国,审查证据、查证案件事实是我国法院的义务,故诉讼诈骗犯罪化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存在的制度土壤*李林.“诉讼诈骗”定性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2010,(4):63-64.66-67.。在我们看来,论者总体上是立于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区分来对待诉讼诈骗应否在我国予以犯罪化的问题。现今看来,以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区分作为否认诉讼诈骗在我国当下应予以犯罪化的理由,已经明显是站不住脚了,因为即便我国法院仍然负有审查证据乃至有条件的取证义务(在当事人提供证据线索的情形下),不能说明我国的民事诉讼仍然停留在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阶段,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诉讼理论,还是诉讼实践,都证明着“谁主张,谁举证”早已将我国的民事诉讼推进到了当事人主义阶段。仅以审查证据来断言我国的民事诉讼仍然停留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阶段,在形式逻辑上犯了“推不出”的错误,因为在被视为典型的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模式中,法院也肩负着审查证据的责任,否则“举证”将有何意义呢?或曰法院径行按照“举证”一方的“举证”及其所对应的诉求直接作出有利于“举证”一方的裁判罢了。
有人立于“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区分而否认在诉讼诈骗中法院“被骗”的事实,并指出,由于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代替“法律事实”,故直接导致把诉讼诈骗定性为诈骗罪的错误结论。论者还从所谓“程序正义”的角度指出,虽然原告提供虚假的证据材料,但法院基于“法律事实”和程序规则作出判决,故法院并没有被骗。否认在诉讼诈骗中法院被骗意在否认诉讼诈骗的最终犯罪化。在我们看来,进一步地,“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区分根本不能作为否认诉讼诈骗犯罪化的理由,或曰“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区分问题与诉讼诈骗应否犯罪化,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退一步讲,不仅“客观真实”要求诉讼当事人实施诚实的诉讼行为,而且“法律真实”也要求诉讼当事人实施诚实的诉讼行为,因为仅与证据相联系,“法律真实”要求证据的来源合法和证据的形式合法,而通过证据做文章的诉讼诈骗首先是在证据的来源和形式上实施“不合法”的勾当。
有人还从所谓“道德风险”来否定诉讼诈骗的犯罪化。如其指出,诉讼诈骗犯罪化将产生深度的道德风险。如A向好友B借款数十万元。出于对A赖账之无奈,B诉至法院。在明知B没有借据而只会败诉之余,A到公安机关报案,声称B提供虚假证据向法院起诉以达其非法占有目的。由于过度的形式有时被认为有损个人感情,故口头合同在我国大量存在。但这种合同一旦引起纠纷,便往往难有证据支持,如果有心怀恶意之人的“点拨”,则合同事实更难证明。那么,当事人起诉往往只能败诉而遭受利益损失。而这却被遮盖在“法治的合理化牺牲”的美名之下。如果“诉讼诈骗”犯罪化,则不法之徒又正好声称已经败诉了的可怜当事人触犯“某罪”。当事人岂非“雪上加霜”甚至“祸不单行”?“诉讼诈骗”被犯罪化将会引发极严重的道德风险,对“诉讼诈骗”定性时,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李林.“诉讼诈骗”定性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2010,(4):63-64.66-67.。在我们看来,在诉讼诈骗犯罪化的道德风险问题上,论者多少有点言过其实或危言耸听,因为在其所举的例子中,乙或者苦于没有证据而自认倒霉,干脆作罢,或可以借据之外的其他证据如证人证言或对甲的录音等作为起诉证据。而如果乙所作出的是后一种选择,则其或因为证据确凿充分而胜诉,或证据不足而败诉,但两种结局都不能反推乙实施了一起诉讼诈骗。乙何有“牢狱之灾”?恰恰相反,如果对诉讼诈骗这种违法行为不予以犯罪化,才真正会出现有论者所担忧的“道德风险”。
有人还从“诉讼诈骗”难以按照现有的罪名予以处置来肯定诉讼诈骗的非罪性。如其指出,民事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瞒证据的,不构成伪证罪,因为伪证罪的主体只能是刑事诉讼中的前述“四种人”。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当事人必须真实陈述,故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提供虚假陈述也不构成伪证罪。诈骗罪重于伪证罪。根据举重以明轻的解释原则,当事人提供虚假陈述不构成伪证罪,当然也不构成诈骗罪。因此,诉讼诈骗犯罪化将直接导致与《民事诉讼法》第71条、《刑法》第305条相矛盾。总之,从法律体系解释的角度,诉讼诈骗不应构成犯罪*李林.“诉讼诈骗”定性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2010,(4):66.64-66.。论者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但我们发现,论者一直是出于“实然”的心态来看待诉讼诈骗,而诉讼诈骗应作为一个“应然”的问题予以对待。当伪证罪的已有刑法立法将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排斥在犯罪主体之外,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即便伪造有利于自己的非法证据,也不成立犯罪,或曰不能将其视为“刑事诉讼诈骗”,因为刑事责任的严厉性消解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不实施非法证据行为的期待可能性,或曰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非法证据行为的无罪对待体现了对刑事诉讼当事人的人性弱点的一种关照,而只有在刑事诉讼中的这种人性弱点才值得予以关照。然而,在民事诉讼中,民事利益所驱使的虚假诉讼行为便不值得予以人性弱点的关照了,或曰再予以关照便显得过分了或太“纵容”了,甚或“偏爱”过度了。易言之,民事利益的诱惑性难以消解诈骗性诉讼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其实,《民事诉讼法》对法院审查证据责任的规定隐含着对违法证据行为以及由之上升的诉讼诈骗行为的一种“提防”,而《民事诉讼法》关于对诉讼违法行为可以采取程序制裁的规定,正说明着《民事诉讼法》对诉讼违法行为包括或特别是诉讼诈骗行为的不予容忍。而我们正在讨论的正是应否突破以往的容忍而令诉讼诈骗 “适得其所”或干脆曰“罪有应得”的问题。这样看来,将诉讼诈骗予以犯罪化对待,不仅与《民事诉讼法》和《刑法》不相矛盾,反而构成一种“呼应”,而这种“呼应”甚至是《民事诉讼法》和《刑法》所等待甚或期盼的。
论者还从更为细微的或曰“微观的”层面来论证诉讼诈骗不应予以犯罪化。如其指出,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行为必须以当事人被骗为前提,即在诈骗罪中,被骗人基于认识错误“自愿”处分财物,但在诉讼诈骗中,法院根据程序规则作出裁判结果。这种裁判结果不是法院的“自愿行为”,而是程序规则的必然选择。既然法院没有意思瑕疵,法院判决处分财产的行为就不是诈骗罪意义的财产处分行为*李林.“诉讼诈骗”定性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2010,(4):66.64-66.。另外,无论普通诈骗抑或三角诈骗,被骗人至少应当占有被害人财物。否则,谈何处分财物。被骗人占有被害人财物是被骗人处分财物的前提。然而,诉讼诈骗中,“被骗人”法院并不占有被害人财物。相反,裁判生效后,法院基于公权力处分当事人财物。既然如此,这种处分行为就不是诈骗罪处分财物的类型化行为*李林.“诉讼诈骗”定性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2010,(4):66.64-66.。应该肯定的是,论者对诉讼诈骗中法院是否出于“自愿”和法院是否实际占有最终被处分的财产的强调,是符合事实的,但这只能说明诉讼诈骗不同于一般的诈骗犯罪,而不同于一般的诈骗犯罪便一定要以“无罪”或“非犯罪化”为问题走向吗?其实,当诉讼诈骗不能按照既有的伪证罪、敲诈勒索罪和诈骗罪予以定罪量刑的时候,其特殊的行为构造及其所对应的特殊的犯罪客体或法益侵害,正是将其推向独立犯罪化的境地。
三、诉讼诈骗罪立法增设的章节安排与条文设计
(一)诉讼诈骗罪立法增设的章节安排
所谓诉讼诈骗罪立法增设的章节安排,亦即刑法分则应在何处对诉讼诈骗罪作出罪刑规定或设置罪刑条文。具言之,诉讼诈骗罪的立法增设是安排在“侵犯财产罪”一章,还是安排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在我们看来,诉讼诈骗罪立法增设的章节安排,如果既能对应诉讼诈骗罪的刑法理论本身,又能照应已然的相关罪刑规定,则或许显得最为妥当。在理论层面上,正如前文所论,诉讼诈骗罪是侵害财产犯罪和妨害司法犯罪的一种竞合性犯罪,或曰诉讼诈骗罪是一种竞合犯,而正是在竞合之中的妨害司法属性使得诉讼诈骗罪才有着不同于作为财产犯罪的一般诈骗犯罪的特殊性。那么,如果将诉讼诈骗罪仍然增设在“侵犯财产罪”一章,将难以或不能更好地体现诉讼诈骗罪之于一般诈骗犯罪的特殊性。那就是说,诉讼诈骗罪增设在其他章即“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便显得相对为宜。因此,如果将诉讼诈骗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无疑将体现“客体特殊立法特殊”这种立法思维。当现行刑法没有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作出“金融诈骗罪”的专节规定,则“金融诈骗罪”无疑是要按照一般诈骗罪的规定予以定罪量刑的,即“金融诈骗罪”仍然是属于“侵犯财产罪”一章的。而当市场经济的发展“烘托”出“金融秩序”的重要性,则“金融诈骗罪”因犯罪客体或侵害法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而被作出了特殊的立法对待,即体现为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作专节规定。那么秉承“客体特殊立法特殊”这一立法思维,如果说“司法秩序”这一客体的意义大于乃至远远大于“金融秩序”这一客体,则诉讼诈骗罪的规定更应突破“侵犯财产罪”的“框定”,而将其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则更显“适得其所”。实际上,仅从诉讼诈骗罪包括侵财型和非侵财型这种犯罪实际出发,将诉讼诈骗罪的罪条归属安排在“侵犯财产罪”一章便也显见不妥。而如果将前述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结合起来看问题,则将诉讼诈骗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其所将显示出的便是刑法分则体系的一种相对的结构和谐性。那么,当我们能够接受诉讼诈骗罪应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则其便毫无疑问地应被安插到“妨害司法罪”一节中了。
那么,诉讼诈骗罪的罪刑条文安排在“妨害司法罪”一节中的什么具体位置上呢?有人提出,应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第305条伪证罪后设定第305条之一“诉讼诈骗罪”*赵晶.诉讼欺作问题研究[D].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31.。论者显然是立于诉讼诈骗罪也具有广义的伪证的属性而提出其看法或主张的,但考虑到诉讼诈骗罪的犯罪客体的复杂性,将其置于“妨害司法罪”一节最后一个罪条的位置上显得更为妥当。
(二)诉讼诈骗罪立法增设的条文设计
在解决了诉讼诈骗罪在“妨害司法罪”一节中的具体位置之后,其法条内容该如何设计或予以表述呢?有人对诉讼欺诈罪的法条提出如下设计:
第×××条 为了达到非法的目的,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提供虚假的陈述,提出伪造的证据,或串通证人提出伪造的证据,从而破坏人民法院正常司法活动,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法院一审作出胜诉判决,诉讼相对人因而遭受较大损失的,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法院二审作出胜诉判决,诉讼相对人的财产因而被执行的,处5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犯前款罪,又构成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或者妨害作证罪的,实行数罪并罚。
单位犯第一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该款的规定处罚*刘远,景年红.诉讼欺诈罪立法构想[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2):23.。
以上条文设计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正如前文论述的那样,将行政诉讼排斥在诉讼诈骗罪发生空间范围之外已显不妥,且有放纵犯罪或法网疏漏之嫌;二是一审胜诉判决也可导致诉讼相对人的财产被执行,因为即便是在诉讼诈骗的场合,也存在着诉讼相对人因觉得上诉无望或其他原因延误上诉而导致一审裁判生效的情形;三是既然把“情节严重”作为诉讼诈骗罪的基本犯的构罪要件,则诉讼诈骗罪的第二级罪刑梯级应以“情节特别严重”作出罪状描述,即以情节加重犯与基本犯构筑诉讼诈骗罪的罪刑阶梯。同时,既然由于“非法的目的”包括非财产性目的,则在诉讼诈骗罪的基本犯之上的罪刑梯级中仅局限于财产损失,也显见不妥;四是将作为诉讼诈骗罪手段行为触犯其他罪名的情形拿来与诉讼诈骗罪予以数罪并罚,不符合牵连犯的刑法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罪刑均衡原则;五是“没收财产”存在仍然存在“合宪性”问题。
另有人对诉讼欺诈罪提出如下设计:
当事人以虚假陈述、伪造证据等手段,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当事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督促程序的申请人、公示催告程序的申请人、破产程序的申请人、强制执行程序的申请人以虚假陈述、伪造证据等手段向法院提出申请,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曲艳红.论诉讼欺诈[D].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42.。
以上条文设计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作为诉讼诈骗罪基本犯构罪要件的“情节严重”在逻辑上包含着作为其加重犯的“数额较大”乃至“数额巨大”;二是对诉讼诈骗罪的基本犯规定可以“单处罚金”显得过于偏重诉讼诈骗罪对财产秩序的侵害而使得司法秩序这一犯罪客体的地位被不当对待;三是诉讼诈骗罪基本犯的法定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与第一级加重犯的法定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存在着重叠关系。
还有人对诉讼欺诈罪提出如下法条设计:
第×××条 民事诉讼当事人以提供虚假陈述并伪造证据,使审判机关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从而使自己或他人得到财物、财产性利益或其他非法利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实际造成诉讼相对人财产损失,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司法工作人员犯该款罪的,从重处罚。
单位犯第一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该款的规定处罚*初攀东.诊诉讼欺作的刑法规制[D].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22.。
以上条文设计也需要完善:一是将诉讼诈骗罪的发生空间局限在民事诉讼领域,同样显得不妥;一是未将“情节严重”作为诉讼诈骗罪基本犯的构罪要件;三是“没收财产”同样存在着“合宪性”问题。
在我们看来,对诉讼诈骗罪的条文设计或罪刑内容表述应兼顾诸多因素或方面,以求得一种立法平衡,而这其中包含着应在横向上兼顾与作为财产犯罪的诈骗罪和同样作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招摇撞骗罪的立法平衡,同时应在纵向上即在“妨害司法罪”内部兼顾与其他具体类型的妨害司法罪的立法平衡。具言之,在横向上,既然诉讼诈骗罪以其复杂犯罪客体显示出较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整体上相对为重的社会危害性,则其法定刑应相应地高于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当然,诉讼诈骗罪的最高法定刑也要因其社会危害性不同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暴力型侵犯人身权利罪而受到死刑的限制。而在纵向上,诉讼诈骗罪同样因其犯罪客体的复杂性而令其法定刑应适当高于其他具体类型的妨害司法罪,但同时必须低于暴动越狱罪和持械聚众越狱罪。那么,在汲取前述法条设计值得肯定之处的基础上,本文提出诉讼诈骗罪的法条如下:
第×××条 为了达到占有他人财物或其他不法目的,以伪造证据等手段而实施虚假的民事讼诉或行政诉讼行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督促程序的申请人、公示催告程序的申请人、破产程序的申请人、强制执行程序的申请人以虚假陈述、伪造证据等手段向法院提出申请,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司法工作人员犯前两款罪的,从重处罚*此规定符合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理论和刑罚个别化理论。。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条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The Criminal Legislation of Crime of Litigation Fraud
MA Rong-chun1, LI Hong2
(1.SchooloflawYangzhouUnivertity,Yangzhou,Jiangsu225127,China;2.ShanghaiXieliLawFirm,Shanghai200120,China)
Litigation fraud has already been crimized in forgein criminal legislation.The social harmfulness of litigation itself and the controlling effect of it shows that the crimination of litigation fraud in our country is necessary.After crimination,crime of litigation fraud shoud be arranged in the Section “crimes of impairing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aper“crimes of obstruct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public order”.Meanwhile,the article of crime of litigation fraud can be design to be the ladder of crime and penalty after considering unit crime and status crime and so on.
crime of litigation; criminization; social harmfulness; moral risks; crimes of impairing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2014-08-27
1.马荣春,男,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2.李红,上海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律硕士。
DF626
:A
:1672-769X(2014)06-004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