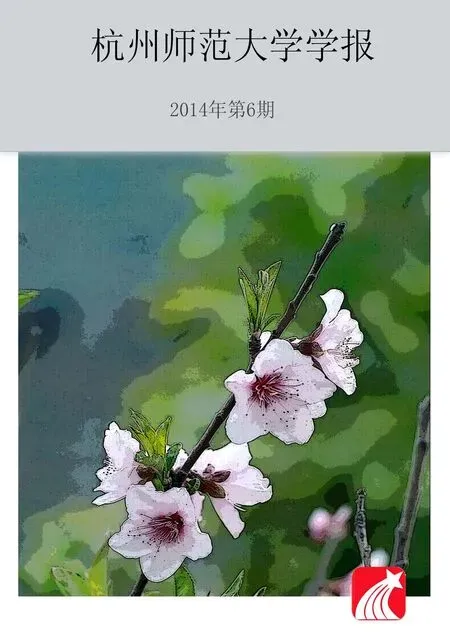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
——钱锺书与英国古典主义诗学
许丽青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钱锺书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中较早肯定中西文艺理论比较研究(即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的一位。他强调中西文论的相互阐发与对话,并将其视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最基本的途径。《谈艺录》中论李贺,曾谈及文艺创作中的模仿自然与润饰自然。他由李贺“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引申开来:“夫天理流行,天工造化,无所谓道术学艺也。学与术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也”;“顾天一而已,纯乎自然,艺由人为,乃生分别”。[1](P.154)对此,古今中外很多批评家都有过自己的思考,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以及继承希腊罗马批评传统的英国古典主义批评家,如菲利普·锡德尼(Philip Sidney)、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和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钱锺书根据中西文学史和批评史的实际,把创作分为两大宗:一为师法造化,以模写自然为主;二为功夺造化,以润饰自然为主。从钱锺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所谓师法自然与润饰自然并非泾渭分明,两者其实是存有内在相通性的。
一
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看似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方法,有关此两者的论述古今中外已有许多。钱锺书对中西文学批评非常熟悉,也很了解模仿说的渊源。他申明,在西方,模仿说始于柏拉图,发扬于亚里士多德,重申于西塞罗,其焰至今不衰。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影响深远,其有关艺术模写自然的观点也为西方很多作家和批评家接受,如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便言“持镜照自然”。钱锺书认为莎士比亚此言通于韩愈《赠东野》诗“文字觑天巧”一语。他在谈诗论画的时候也注意到模仿的问题,常常由此及彼,将诗画并行论述,时有共性的揣摩和差异的提醒。《管锥编》中,他引谢赫《画品》论“六法”,指出“传移,模写是也”;盖“写”与“传移”同义,移于彼而不异于此之谓。移物之貌曰“写”,拟肖是也;移物之体亦然,转运是也。[2](P.256)艺术模仿自然其实是很复杂的,模仿的方法可以分为多种,钱锺书提出绘画的“拟肖”可分为两种:同材曰复制(copy),殊材曰摹类(imitation),凡“象”者莫不可曰“写”。他注意到复制和摹仿是不一样的,所以用英语中对应的copy与imitation两词来做区分,说明两者功能有别。类似于画,钱锺书注意到模写自然的方法在中西诗文中也多有运用,常见的一种手法即是信景直叙法:
苏轼《上巳日与二三子携酒出游、随所见辄作数句》,纪昀批为“信景直叙法”者,可以相参。后世院本中角色一路行来,指点物色,且演且唱;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一节相似,特陶辞叙将来而若现在,更一重一掩矣。绘画有长卷、横批,其行布亦资契悟。……经生拘迂,以为谑浪调情之际,无闲工夫作诗,诗必赋于事后,而“尔”、“我”之称,则类当时面语,故曲解为追溯之记言。夫诗之成章,洵在事后,境已迁而迹已陈,而诗之词气,则自若应机当面,脱口答应,故西方论师常以现在时态为抒情诗之特色。[2](PP.1226-1227)
钱锺书注意到,中西诗歌中写景无论过去将来用的都是现在时态,生动活泼,已成为抒情诗的一个特色。《谈艺录》中他分析陆游的诗作,归纳出陆游的诗歌擅长模山范水,专务眼处生心,景随眼现,工于写景叙事;但他又指出陆游诗夺于“外象”,而颇缺“内景”。[1](P.329)模写自然的同时,是不能遗忘“内景”的,但“内景”介入了,势必会逾越“模写自然”和“润饰自然”的界线。在钱锺书的眼中,创作一味追求细致真实描摹“外象”,而疏于“内景”也是一种缺失。其实他的潜台词是在强调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的密切关联。
英国古典主义诗学批评家中提倡模仿论者颇多,如锡德尼、德莱顿、蒲伯和约翰逊等。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沿用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阐明自己的诗学观点,他把诗视为一种“模仿的艺术”,认为“模仿不是搬借过去现在或将来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是在渊博见识的控制之下进入神明的思考,思考那可然的和当然的事物”。[3](PP.11-12)他强调模仿不是对客观事物依样画葫芦,而是要求人把“渊博的见识”和“神明的思考”结合起来,把诗教的目的(教育与怡情悦性)同创造性手段结合起来。锡德尼所言的模仿,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模仿。他肯定自然之于人类的重大意义,意识到没有哪一种传授给人类的技艺不是以大自然的作品为其主要对象,但也看到了模仿中人类的创造性才能。
蒲伯的《论批评》(AnEssayonCriticism)主要论题也是阐述自然与艺术的关系:(一)自然是艺术模仿的对象。他认为诗“应该追随自然,依照他的永恒、公正的标准,建立你的判断”。[4](P.33)把自然视为文艺批评的至高无上的准则。(二)自然与荷马是一致的,古时的创作规律是发现而非发明自然,自然是条理化的自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文学模仿的是自然或人生。蒲伯虽也承认文学是模仿的艺术,但他把模仿的对象确定为古人的作品,认为模仿自然就是模仿古代准则。他重视继承古代的文艺传统,并将此视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因而蒲伯的模仿说不可避免地带有形式主义的成分。蒲伯更多看到的是自然的秩序井然,所以他所信奉的“自然”是一种永恒的自然法则(natural law),包括古人立下的艺术创作和批评的规则。蒲伯的这种模仿论可能是最僵化的一种,最终被塞缪尔·约翰逊批评为盲目崇拜古代遗产。在《漫游者》中约翰逊谈及时人模仿斯宾塞的弊端时也说:“虽然后人可以通过不懈努力接近斯宾塞的风格,但是新的生活赋予我们更高的目标,而不仅仅是收集古人已经废弃的,或者学习那些毫无价值已经被人遗忘的东西。”[5](第121辑,P.226)新的生活赋予文学更高的目标,文学应该反映当代的生活,文学批评也应该切合当下的实际。
持模仿论的英国古典主义批评家并非都提倡机械被动的模仿自然之法。锡德尼强调“渊博见识”和“神明思考”相结合,约翰逊强调反映当代人的生活和现实。而钱锺书则在前人实践和理论总结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细节,他注意到模仿可以有很多种,可以copy或者imitation,进而发现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两者之间的相反相成貌异心同,偏重于写景必然有失于抒写内心。
钱锺书交代,润饰自然之说在西方萌芽于克利索斯当,近世培根《学术的进展》、波德莱尔和惠斯勒也作如是观。其实,蒲伯《论批评》中也强调过润饰自然的必要,并提出“巧智”(wit)“是将自然精心装扮,平常的思想,绝妙的表达”。[6](P.40)蒲伯强调文辞技巧需要依赖人的主观才能。钱锺书认为李贺的“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可加以提要勾玄:
此派论者不特以为艺术中造境之美,非天然境界所及;至谓自然界无现成之美,只有资料,经艺术驱遣陶镕,方得佳观。此所以“天无功”而有待于“补”也。窃以为二说若反而实相成,貌异而心则同。夫模写自然,而曰“选择”,则有陶甄矫改之意。自出心裁,而曰“修补”,顺其性而扩充之曰“补”,删削之而不伤其性曰“修”,亦何尝能尽离自然哉。[1](P.155)
即是说,没有哪一部作品可以完全脱离作者的主观因素,创作受启于自然,也需要人为的加工,天工与人艺都是不可或缺的。莎士比亚既明白模仿自然的必要,也懂得后天润饰的重要,《冬天的神话》便言“人艺足补天工,然而人艺即天工也”。在《管锥编》中,钱锺书再次谈及天工与人艺的关系:“画形则神式凭之,故妙绘通灵能活,拟像而成实物真人。言虽幻诞,而寓旨则谓人能竞天,巧艺不亚于造化,即艺术家为‘第二造物主’(a second maker*“Such a poet is indeed a second maker; a just Prometheus under Jove.” See Shaftsbury’s Characters, Grant Richards,1900,p.136.)之西土常谈也。”[2](P.716)夏夫兹伯里在其特写随笔集中所言之“第二造物主”,类似于位居上帝之后的普罗米修斯。在创作中,作家的潜能是巨大的,他是作品的造物主,他的巧艺不仅可以补天工,甚至可夺天工。钱锺书深刻意识到了人在模仿自然时润饰自然的重要性,在他眼中,匠心跟天工都是不可缺少的。
由上可知,其实不少提倡模仿论者也非常强调依靠人力润饰自然的必要性。德莱顿把模仿视为戏剧创作的最基本原则,他认为,戏剧舞台是现实世界和人类行动的再现场所,而人类生活的场面是无法依赖想象达致精确的,唯有模仿生活本身。在论及喜剧的时候,他说“如果诗可以模仿,那么这种模仿中一定需要这样一种描摹,对于人类行动、激情、美德和罪恶、愚蠢和陋癖的描摹”。[7](P.139)从《论戏剧诗》中尼安德对莎士比亚的称赞,也可以看出德莱顿对莎士比亚式模仿的推崇,高度评价其真实展现现实人性的广度和深度:“在所有的现代诗人当中,或许在所有的古代诗人们的行列里,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具有最伟大的和最广阔的心灵。当他描写一件事情,你不仅看见这件事情,而且也在心里感觉到这件事情。”[8](P.637)模仿生活、描摹人性,不仅需要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精准的观察力,更需要洞悉人性的智慧,这显然离不开人的审美创造力。
约翰逊在论及人艺和自然的关系上也竭力赞扬莎士比亚,说很少作家像他那样描写生活的本来面貌。他在《漫游者》第4期开头说:“模仿自然,大家名正言顺,视为艺术无比伟大的卓绝境界;但是有必要从自然中区别看待,筛选出最适宜模仿的部分:表现生活时,需要倍加小心,因为激情经常改变生活的本色,邪恶往往使生活变得丑陋。”[5](第4辑,P.20)约翰逊所说的现实主义是指“描绘一般,普遍,典型”;他所说的模仿也是有条件的,有时候尊奉自然会偶然占上风,更多情形下他是高举道德的标尺。现实世界纷繁芜杂,模写自然要避免流水账,所以需要剪裁。和钱锺书一样,约翰逊意识到人工筛选和修补的必要,但他主要依据的却是道德准则。
钱锺书和多数英国古典主义批评家都看到了润饰自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如何润饰自然,各人所思却不一样。蒲伯强调的是一种绝妙表达的巧智,德莱顿强调的是洞悉生活和人性的智慧,约翰逊强调更多的则是道德层面的人工筛选。钱锺书则较多地肯认诗中抒情和写内景的重要性,同时也肯定了艺术中造境的价值。
二
人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涉及艺术起源的重要问题,也是中西文艺批评所绕不开的一个基点。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韦勒克指出,“模仿自然”是新古典主义诗学的核心概念,“模仿”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摹拟(mimesis),不是照相式的自然主义,而是一种“再现”。“自然”也不意味着“无生命的自然”——静物或户外景色,而是指一般的现实,也包括人性。[9](P.1)其实,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模仿”和“自然”是两个众说纷纭的术语,不同的人对此的理解完全迥异。自然可以是一般的普遍的现实,也可以是一种规则(Natural Law);模仿可以是一种带有目的的筛选。模仿自然并不意味着不可以介入主观,不意味着完全的被动模仿。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之间不是泾渭分明的,其实有内在关联,只是主观介入的程度不一样而已。所以,“模仿自然”也可以掺有一些主观的因素,甚至某些时候人艺就是一种天工。
钱锺书关心的既不是“模仿自然”与“润饰自然”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也不是两种方法的差异,而是把这个问题推衍深化,进而涉及写实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模仿”与“润饰”自然的分寸如何把握,把握不好会有怎样的后果,钱锺书都有论述。写实模仿或人艺造境都需要把握分寸,不可走极端。他提醒道:“写实者固牛溲马勃,拉杂可笑;造境者亦牛鬼蛇神,奇诞无趣。”[1](P.156)润饰自然不仅仅指依靠人工虚构造境,其实描摹自然时也有赖于人类的想象力。钱锺书发现,中西方人对想象问题的思考有相通之处:
《正义》“实象”、“假象”之辨,殊适谈艺之用。古希腊人言想象(imagination),谓幻想事物有可能者(things that can be),亦有不可能者(those that can not be),例如神话中人生羽翼、三首三身……非即“实象”与“假象”乎?[2](P.15)
古希腊人所言的想象其实是一种幻象,也是一种假象。17、18世纪的英国人对想象的认识也与此类似,认识比较混乱,多为经验主义的理解。大部分英国古典主义批评家既肯定润饰自然的必要,也承认虚构和想象的价值。
锡德尼把诗人的模仿看得更高,他认为诗人的模仿更能见出创造力,诗人善于通过创造光辉的形象来阐明德行,“只有诗人不屑为这种服从所束缚,为自己的创新气魄所鼓舞,在其造出比自然所产生的更好的事物中,或者完全崭新的、自然中所从来没有的形象,如那些英雄、半神、独眼巨人、怪兽、复仇神等等,实际上,升入了另一种自然,因而他与自然携手并进,不局限于它所赐予所许可的狭窄范围,而自由地在自己才智的黄道带中游行”。[3](P.9)锡德尼的这段话意思非常明确:自然不一定是客观的大自然,也可以是人们想象中的世界;人类若想描摹想象中的“另一种自然”,必须借助想象力去虚构。德莱顿承认创作中想象和虚构的意义:“因为诗人有描绘现实中并不真实存在的事物的自由,这种世界中有精灵、侏儒以及其他一些魔幻的超乎现实的东西。这也是一种模仿,不过是对于想象世界的模仿。”[7](P.140)很明显,德莱顿也认为诗人是可以模仿超现实的世界的,这种模仿仍需要借助想象。
在蒲伯和约翰逊的理解中,巧智都和想象力有关。蒲伯认为想象力的运用是有限制的,他担心一味追求奇幻会使诗人受到迷惑而误入歧途,运用巧智要以不破坏艺术规范为前提。约翰逊对创造性想象力缺少兴趣,在《拉塞勒斯》第43章中提出“想象力的危险盛行”的议论,不赞成做白日梦和逃避现实的态度,反对写感官的形象和松散的思想。约翰逊多次表达了他对想象力的怀疑态度,称之为一种“无拘无碍,飘忽不定的才能,弃尽町畦,不容驾驭”。[5](第25辑,P.345)不过,在纯文学的语境内,约翰逊承认想象力是诗人资质的组成部分。他曾如此评论蒲伯:“他具有想象力,它在作家的头脑里留下了强烈的印记,所以五光十色的自然形态,日常生活事件,激情的能量,这些他都能传达给读者。”[10](P.299)模仿自然决不意味着照相式的记录,大到虚构的人物、情境等,小到遣词造句都需要借助智力和想象力。因此模仿自然与润饰自然其实不存在分明的界线,这两种看似迥异的创作方法原本就存在关联。
钱锺书也肯定想象力之于艺术表达的意义,他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谈到想象力之于情感表达的意义时,引休谟《情感论》中的观点进行论述:“他(指休谟)认为情感受‘想象’的支配,‘把对象的一部分隐藏不露,最能强烈地激发情感’;对象蔽亏不明,欠缺不全,就留下余地,‘让想象有事可做’,而‘想象为了完成那个观念所作的努力又能增添情感的强度’。”[11](P.13)这段话很像莱辛《拉奥孔》中讲绘画该挑选富有生发余地的瞬间,“好让想象力自由游戏”。钱锺书认为,西方学者的这些观点,都与中国古人所言“得意忘言”相通。
对艺术模仿自然,或者说人艺参照天工造化,中国人有自己的思考,但是人与天并非如西方人所以为的主客那样分得清楚。钱锺书意识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维特征:“人出于天,故人之补天,即天之假手自补,天之自补,则必人巧能泯。造化之祕,与心匠之运,沆瀣融会,无分彼此。”[1](P.156)这一点,刘若愚在中西诗学比较中也发现:“在西方的模仿理论中,诗人或被认为有意识地模仿自然或人类社会,如亚里士多德派和新古典派的理论,或被认为是神灵附体,而不自觉地吐出神谕,一如柏拉图在《伊安篇》中所描述的。可是,在中国的形而上理论中,诗人被认为既非有意识地模仿自然,亦非以纯粹无意识的方式反映‘道’——而是在他所达到的主客观的区别已不存在的‘化境’中自然地显示出‘道’。”[14](P.73)
三
对模写自然追求真实这个问题的深入追究,势必要涉及文学的真实与虚构问题,但这需要辩证的理解。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多次阐述了这种微妙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作品中的虚构也会营造一种真实的诗境:
据实构虚,以想象与怀忆融会而造诗境,无异乎《陟岵》焉。分身以自省,推己以忖他;写心行则我思人乃想人必思我,如《陟岵》是,写景状则我视人乃见人适视我……[2](P.114)
模写自然旨在追求真实,但忠实客观世界并非唯一标准;因为除了外在世界的真实之外,还有一个内在世界的真实问题。文学还追求意境,虚构人物,虚拟时空,可以渲染真实诗境。虚构类作品追求离奇,然而情节的荒诞中也要讲究真实合理:
拟之三段论法,情节之离奇荒诞,比于大前提;然离奇荒诞之情节亦须贯串谐合,诞而成理,奇而有法。如既具此大前提,则小前提与结论必本之因之,循规矩以作推演。……盖无稽而未尝不经,乱道亦自有道……更进而知荒诞须蕴情理。[2](PP.594-595)
在这里,钱锺书仔细分析了虚构的必要,以及情节的荒诞离奇与和谐成理的辩证不违。他指出,情节的荒诞要合情合理,合乎逻辑。不过,约翰逊否定虚构,强调创作中的真实,认为文学是对现实存在的事物和活动的一种公正再现;虚构文学的宗旨在于传达真理;小说家应该是人类风尚的公正复制者。由于过分看重真实,约翰逊的论述中贯穿着对一切虚构艺术的深刻怀疑。正是基于这种态度,约翰逊不喜欢古代神话,他怀疑古代神话的真实性。
不是文学中描摹的一切都可以绝对区分出真伪,譬如诗歌中的情感。约翰逊非常强调诗歌情感的真实,他挑剔过很多诗作中的情感。他怀疑考莱艳情诗中情感的真实性,并讥嘲说:“他(指考莱)赞叹从未见过的娉婷,诉说他从未感到过的妒忌,设想自己时而受到眷顾,时而又遭抛弃;绞尽脑汁地去想象,搜索枯肠去回忆,为的是找到那些表现希望的欢乐或绝望的忧郁的意象;他在打扮想象中的齐罗丽思或菲利丝时,时而用鲜花喻其红颜易逝的美丽,忽而用珠宝喻其永世长存的美德。”[10](PP.4-5)同样,他也不喜欢弥尔顿《利西达斯》(Lycidas),因为“这篇作品不能视为真实感情的倾诉,因为感情所追求的,不是古老的典故和深奥的见解”。[10](P.94)约翰逊并非一个胸襟狭隘的批评家,但是他在此问题上的态度确实显得比较武断、偏执。如果按约翰逊的标准去衡量,大部分文学作品都要被打入冷宫。
钱锺书注意到,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不仅体现在情节和情感的真与伪,还体现在诗文措辞和场景设计方面。首先,他指出诗文之词的虚真而非伪:
夫世法视诗为华言绮语,作者姑妄言之,读者亦姑妄听之。……一言以蔽之,诗而尽信,则诗不如无耳。……盖诗歌虽可招文字之祸,尚万一得托“诗人之言”,“虚”而非“实”,罪疑惟轻。散文相形,更信而有徴,凿而可据,遂愈不为罗织者所宽假也。[1](PP.170-171)
诗文之词虚真而非伪,最常见的一种就是诗文中常用的比喻修辞:
“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虽曰河、汉广狭之异乎,无乃示愿欲强弱之殊耶?盖人有心则事无难,情思深切则视河水清浅;歧以望宋,觉洋洋者若不能容刀、可以苇杭……苟有人焉,据诗语以考订方舆,丈量幅面,益举汉广于河之证,则痴人耳,不可向之说梦者也。不可与说梦者,亦不足与言诗,惜乎不能劝其毋读诗也……述事抒情,是处皆有“实可稽”与“虚不可执”者……盖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语之虚实与语之诚伪,相连而不相等,一而二焉。是以文而无害,夸或非诬……诚伪系乎旨,征夫言者之心意,孟子所谓“志”也;虚实系乎指,验夫所言之事物,墨《经》所谓“合”也。所指失真,故不“信”;其旨非欺,故无“害”……高文何绮,好句如珠,现梦里之悲欢,幻空中之楼阁,镜内映花,灯边生影,言之虚者也,非言之伪者也,叩之物而不实者也,非本之心之不诚者也……皆泥华词为质言,视运典为纪事,认虚成实,盖不学之失也。[2](PP.95-97)
钱锺书指出,言词虚妄并不代表作者本心不诚,此乃诗文创作中追求绮丽效果而虚拟措辞表征之,诗中典故纪事都不足信实。亚里士多德有言,诗文语句非同逻辑命题,无所谓真伪。在这一点上,锡德尼认为“诗人不确语,故不诳语”。*参看锡德尼《为诗辩护》:“在白日之下的一切作者中,诗人最不是说谎者;即使他想说谎,作为诗人就难做说谎者”,“至于诗人,他不肯定什么,因此他是永不说谎的。因为我认为,说谎就是肯定虚伪的为真实的”,“因此他虽然不叙述真实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并不当它真实的来叙述,所以他并不撒谎。”见锡德尼著、钱学熙译《为诗辩护》,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45-46页。约翰逊出于对想象和虚构的极端怀疑,因而对于隐喻和象征等修辞艺术均不信任。而文学表达一旦排除了隐喻、象征等修辞,又该如何去表达?
关于诗文言词的虚而非伪,钱锺书的考察要比锡德尼更加细致全面,对修辞多有深入浅出的解析。
在模写自然和润饰自然过程中应当忠实于外还是内,到底该追求一种怎样的真实?对此钱锺书自有看法,他提出形容譬喻之辞的“情感价值”与“观感价值”是有所区别的:
夫诗文刻划风貌,假喻设譬,约略仿佛,无大剌谬即中。侔色揣称,初非毫发无差,亦不容锱铢必较。使坐实当真,则铢铢而称,至石必忒,寸寸而度,至丈必爽矣……作者乃极言其人之美丽可爱,非谓一睹其面而绥山之桃、蓬莱之杏、蓝田之玉、梁园之雪宛然纷然都呈眼底也……皆当领会其“情感价值”,勿宜执着其“观感价值”。绘画雕塑不能按照诗文比喻依样葫芦,即缘此理。[2](P.106)
“情感价值”与“观感价值”未必会是百分百对应的。在钱锺书看来,描摹可以虚夸,观感上不够信实的其情感未必有假,关键是读者能够领会诗中情感。18世纪伯克《论崇高与美》中对此有过类似剖析,钱锺书认为伯克的解释“切理餍心,无以加之矣”。正是因为描摹的虚夸性,他提醒诗中景物不尽信而可征:“窃谓诗文风景物色,有得之当时目验者,有出于一时兴到者。出于兴到,固属凭空向壁,未宜缘木求鱼;得之目验,或因世变事迁,亦不可守株待兔。”[2](P.90)他指出,淇奥之竹、溱洧之芍药与弥尔顿笔下写地狱沼面秋叶委积都不可尽信。
其次,诗文中还常常依附真人构造虚事,并设计虚假场景。钱锺书认为对此不必苛责,皆可理解:“词章凭空,异乎文献徵信,未宜刻舟求剑……依附真人,构造虚事,虚虚复须实实,假假要亦真真……盖谓经有‘假设之词’,而诸子、词赋师法焉,真六通四僻之论矣……顾谓不可苛责词赋之有背史实,刘谓不宜轻信词赋之可补史实……不徒庄子然也,诸子书中所道,每实有其人而未必实有此事,自同摩空作赋,非资凿空考史。”[2](PP.1296-1298)西方说理常设计主客交谈(指对话体)场景,如柏拉图的对话录,古代学者将年辈悬殊之哲人置于一堂,上下议论,场面几近于戏剧。他发现,“设论”之体便于使异代殊域之古人促膝抵掌,这在我国子书中也常见。锡德尼也注意到这种“设论”之体的巧妙,《为诗辩护》中他说柏拉图的作品在内容和力量上是哲学的,可是外表却是诗的,因为全部依靠对话,其中富有诗意的会谈细节的描写。17、18世纪欧洲经典诗论多为对话体,如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批评家布瓦洛《诗的艺术》和18世纪英国诗人兼批评家约翰·德莱顿的《论戏剧诗》均采用的是对话体。诗论用对话,别有一番生动妙趣,说理却不枯燥。
通过钱锺书的分析可见,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看似截然不同,实则相反相成、貌异心同。这两个概念不像人们字面理解的那般泾渭分明。钱锺书关心的不是两个概念的区分,也不是两种方法的差异。“模仿”不是照相式的精确记录,“自然”也不一定单指无生命的自然。钱锺书在前人实践和理论总结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细节与深层机理。他和多数英国古典主义批评家一样,重视润饰自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如何润饰自然,所思却不一样。并且,他把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的问题推衍开去,延伸论及许多相关的重要问题,如写实与想象、真实与虚构。对写实与想象、真实与虚构需要辩证理解,不可偏执一端。钱锺书指出诗文之词虚而非伪,文学修辞的“情感价值”与“观感价值”也是有所区别的,不可执著于“观感价值”。笔者认为,钱锺书在文艺美学的范畴层面拓展与深化了“自然”的主客观内涵,进而揭示了相应的表征方式与审美价值,因而具有独到的思想启示。
[1]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1.
[2]钱锺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锡德尼.为诗辩护[M].钱学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4]A. Pope.TheRapeofLockandOtherPoems[M]. Thomas Marc Parrott. Halley Court Jordan Hill:Oxford, Ginn and Company,1906.
[5]Samuel Johnson.TheRambler[M]. F.P. Walesby. S. and R. Bentley, Dorset Street,1823.
[6]A. Pope. Essays on Criticism[C]//TheRapeofLockandOtherPoems, Thomas Marc Parrott. Halley Court Jordan Hill: Oxford, Ginn and Company,1906.
[7]James Kingsley, ed.JohnDryden:SelectedCriticism[C]. Gloucestershire: Clarendon Press,1970.
[8]John Dryden. An Essay of Dramatic Poesy[C]//LiteraryCriticismfromPlatotoDryden. Allan H. Gilbert.Tennessee: American Book Company,1940.
[9]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卷1[M].杨自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10]J. P. Hardy, ed.John’sLivesofthePoet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11]钱锺书.七缀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2.
[12]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M].杜国清,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