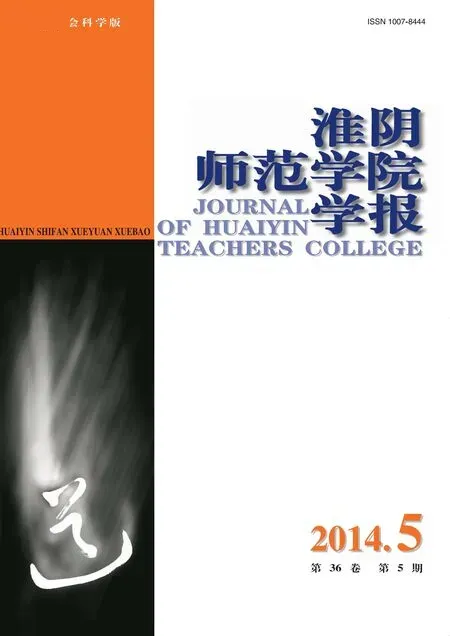女性主义视野中《福》的女性形象探析
傅守祥, 高 捷
(1.华东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上海 201620; 2.浙江大学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女性主义视野中《福》的女性形象探析
傅守祥1,2, 高 捷1
(1.华东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上海 201620; 2.浙江大学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库切在小说《福》中以苏珊·巴顿作为小说的第一叙述者,创造了一个女性叙述者形象,对西方经典《鲁滨逊漂流记》中的荒岛英雄故事进行了创造性还原。苏珊·巴顿不仅因其女性叙述主体的身份而给男性文本《鲁滨逊漂流记》平添了女性视野和女性话语,而且不同于传统女性,是一个具有女性主义自觉意识的独特形象。苏珊·巴顿面对命运作出自由选择,身处荒岛困境不断质疑传统观念,最后从渴望言说到自觉发声,实现了对男权秩序与绝对价值观的跃起反叛。因此,苏珊·巴顿是一个具有超越性的女性形象和自觉的女性话语者。
女性主义;《福》;女性形象;苏珊·巴顿
《福》(Foe,1986)是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第五部小说,这部作品是对西方经典文本《鲁滨逊漂流记》的颠覆性改写。目前,学界对库切的研究“多是以某一部小说为蓝本进行寓言性、隐喻性的解读”[1],即从内容、主题方面切入来阐释文本意义。在对《福》的研究中,学者们亦从创作主题和创作形式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学者在创作主题方面对小说进行了后殖民文学研究(张德明:《从〈福〉看后殖民文学的表述困境》,《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4期)、互文性研究(王旸:《库切对现实主义小说的质疑——〈福〉与〈鲁滨逊漂流记〉互文性分析》,中国地质大学硕士论文,2012)、二元性研究(王洁欣、张书红:《库切小说〈福〉二元性解读》,《作家》2011年24期)等。学者在小说创作形式方面的研究主要从叙述语言角度切入,如段枫:《〈福〉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3期);王成宇:《试析〈福〉的语言策略》,《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5期;Michael Marais,Reading/Colonizing Coetzee’s" Foe",English in Africa,Vol.16,No.1(May,1989),pp.9-16.等。。诸多研究当中,对于小说中苏珊·巴顿人物形象的批评有所涉及。譬如学者们对苏珊·巴顿的研究主要围绕她的第一叙述人身份,探讨其边缘人形象和女性话语权等问题*学者从边缘人形象切入的研究有:高文惠:《边缘处境中的自由言说——J.M.库切与压迫性权威的对抗》,《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2期;Spivak,Theory in the Margin:Coetzee’s Foe Reading Defoe’s "Crusoe/Roxana",English in Africa, Vol. 17, No.2(Oct.,1990),pp.1-23.等;学者对其有关女性话语权的研究有如韩瑞辉:《库切小说〈敌手〉中的女性主义叙事视角》,《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4期;高敬,石云龙:《试论后殖民语境下库切小说〈福〉中的话语权》,《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10期等。;将苏珊·巴顿视为女性群体的代表,探讨叙述主体的不稳定性,突出女性在面对独立发声时的恐惧与自我怀疑,认为她“呈现了一个女性克服了‘写作的焦虑’*“写作的焦虑”(anxiety of authorship)出自女性主义批评代表作《阁楼上的疯女人》。书中提出,女性作家焦虑的首先是自己是否有能力成为作家掌握话语权进行写作。这是“对于她没有能力进行创作的极端恐惧。由于她无法成为后世的‘先人’,她害怕写作的行为会令她与世隔离或者会导致她的毁灭”。这种焦虑来自对作者权威的恐惧,因为作者权威从根本上说是父性的,话语本身是男性的(转引自任海燕:《探索殖民语境中再现与权力的关系——库切小说〈福〉对鲁滨逊神话的改写》,《外国文学》2009年第3期)。的过程”[2];然而,对于人物形象的全面研究尤其是对苏珊·巴顿这个女性形象的价值研究还远远不够。
其实,苏珊·巴顿并非一个由未摆脱附属于男权的传统女性形象向具有完整女性话语权建构的自觉意识转变的处在变化过程中的女性形象*认为苏珊·巴顿是一个从传统女性形象到具有自觉意识的女性形象的转变的观点在以下研究中有所提及:如黄晖:《〈福〉:重构帝国文学经典》,《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3期,高敬、石云龙:《试论后殖民语境下库切小说〈福〉中的话语权》,《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10期等。。小说家库切将苏珊·巴顿作为叙述主体不仅仅是将女性引入了叙述视野,更表现出她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传统女性的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独特形象。苏珊·巴顿面对命运玩弄作出自由选择,面对落难荒岛的困难境遇对传统观念不断质疑,最后从渴望言说到自觉发声,实现了对男权秩序与绝对价值观的跃起反叛。借助成熟的“文本细读”法,我们试图“还原”苏珊·巴顿这个女性形象的心理与现实处境,发现苏珊·巴顿身上体现出明显的“女性自觉”意识,因此说她是一个具有超越性的女性形象。
一、荒岛体验与自由选择
库切的小说《福》对“鲁滨逊神话”的改写是彻底的、颠覆性的。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塑造了一位具有进取精神的殖民主义男性开拓者的形象,而在《福》中,库切将主人公设定为名为苏珊·巴顿的女性,她为寻找女儿历经艰险,意外地流落荒岛并在那里遇见鲁滨逊与星期五。整部小说以苏珊·巴顿为叙述视角,库切将《鲁滨逊漂流记》的原文本通过仿写的形式镶嵌在苏珊·巴顿的叙述中,通过书信、自述与对话的方式呈现了苏珊·巴顿与作家福的交流过程。
“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女性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甚至是被忽略不计的:她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名字,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属品,扮演着母亲、妻子、女儿或寡妇的角色。”[3]如鲁滨逊伦敦朋友的遗孀,笛福对她进行着墨不多的侧面描写。“我的恩人,那个忠实的寡妇仍然活着,我曾把钱交给她保管,但她遭受了很大的不幸,第二次做了寡妇,穷困潦倒,无以为生。”[4]164笛福甚至没有给这位无名的寡妇话语权,寥寥几句便刻画出她作为男性附属的被动的、依附的内在性形象。与《鲁滨逊漂流记》中“失声的群体”*“失声的群体”理论认为,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是“失声”的群体,她们的声音被强大的男性话语淹没了,女性只有在占支配地位的男性系统之外建立属于女性自己的表达手段,才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信函、日记以及其他的传播形式就是具体的抗争手段。——(Kramarae,C.(1981).Women and men speaking: Frameworks for analysis.Rowley MA: Newbury House. pp34-35,转引自刘蒙之《从批判的理论到理论的批判——失声的群体理论研究四十年回顾》,《学术界》2009年1期。不同,库切在《福》中创造了一个女性叙述者形象,苏珊·巴顿作为小说的第一叙述者,对《鲁滨逊漂流记》中的荒岛英雄故事进行了创造性还原。库切借此对《鲁滨逊漂流记》进行了反讽式的戏仿,此番改写不仅瓦解了荒岛生存的英雄故事,还对原小说中女性形象进行重现与声讨。
小说开篇采用插叙手法描述了苏珊借由小船艰难划至海岛的过程,她的一切遭遇从寻找被拐的女儿开始。由此作为小说始端,苏珊·巴顿在一开始便体现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对女性处境的分析中,总结出女性的所谓“特性”,即她“沉迷于内在性”。她提出女性的处境之一便是“女人从未构成一个封闭的、独立的社会;她们是人类群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群体受男性支配,她们在群体中受支配地位”[5]673。由于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以及缺乏支配事物的技术训练,使女性带有听天由命、妥协忍耐等特性,这些特性是女性在男性世界的框架内将自己内化成的角色,她们将男性社会的这种要求内化为女性自己的要求。同时,女性被封闭在她的家庭或家务活动的有限范围里,“她被剥夺了所有与他人具体沟通的可能性……人们几乎不可能指望她可以超越自己,朝着一般性的福利迈进。她固守于她所熟悉的那个领域,她在那里能够控制一些物件,并且在它们中间拥有一种靠不住的主权”[5]682。小说中,苏珊·巴顿与传统忍气吞声、自困闺房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她为寻找女儿来到巴依亚,忍受粗暴与威胁。为了生存她在出租屋内接揽缝纫的活计维持生活,最终踏上商船,在船上受尽欺凌后被水手放逐荒岛。她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勇敢出走,对遭遇作出反抗,对未知进行探索。苏珊·巴顿的所有遭遇都是她主动选择的,她没有遁入安宁、没有安于现状,而是跨越自己的内在性,通过自由选择和自己的行动努力改变现实。
流落荒岛的生存体验,使苏珊·巴顿走出传统女性的生活空间,获得顽强的生命力与广袤的视野。苏珊·巴顿在荒岛上生活了近两年的时间,她与克鲁索及星期五过着海难漂流者的自足生活。他们捕猎耕种,环岛探险,经历致命的暴风雨,体验被海浪吞噬的恐惧。她不是那个固守领地,受人规劝的传统女性角色,她通过自己的体验来感受这个世界。在获救的“约翰·霍巴特”号商船上,斯密斯船长怂恿她将故事写下来交给出版商,这个建议引发了苏珊·巴顿之后的有关写作的一系列思考和行为变化,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详述。在此首先提及有关苏珊·巴顿的写作的想法,意在解释她的荒岛体验为其写作作了前提性的、关键性的铺垫。同时这种生存体验也为之后的思考与自为的行动提供潜在的鼓动因素。
女性主义思想家吴尔夫曾提出女性要写作必须拥有两个条件:五百万英磅的年金和一间自己的房间。她认为这笔钱让女人可以不必敌视男人,可以去旅游拓宽眼界,去思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她在对19世纪初的几位女性作家的评析中指出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的缺陷,即女性作家通常在足不出户的生活状态下创作。以夏洛蒂·勃朗特为例,吴尔夫认为由于缺少人生经验,女作家容易将自己的激愤和个人情绪带入小说写作中,把自己与小说人物混淆,将本该写得机智的部分变得呆板扭曲。由此她猜想,如果夏洛蒂·勃朗特能够拥有年金,“如果她对那个繁忙的世界,那些充满了生活的换了的城镇和郡县有更多的了解,有比现在更多的人生经验,与和她一样的人有更多交往,结识更多的秉性不同的人,结果又会如何呢?”[6]吴尔夫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与提出女性要写小说必须有钱和一间屋子的构想,其关键就在于她看见生存空间和经济等社会因素的阻碍对女性的自由创作产生影响,因此她认为女性应该去体验、交往和旅行,在与世界的接触中使天赋得以发挥。因而,苏珊·巴顿的荒岛体验,于无形中为她视野开阔和开放性的思维提供了潜在的支持,让她得以切实地感受生活,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在小说中,由于福篡改了苏珊·巴顿最初的想法,苏珊·巴顿极力反抗,同时她意识到岛上生活的枯燥和千篇一律使得故事显得愚蠢乏味——福虚构故事的缘由。由此她发现使故事总保持沉默的原因在于星期五,在她发现故事缺乏的部分便是星期五失去舌头后有关星期五故事的那段空白之后,她试图作出努力恢复星期五说话的能力。在对星期五的思考中,苏珊·巴顿慢慢产生有关话语权与身份建构等问题的思考。通过荒岛体验,苏珊·巴顿对克鲁索与星期五的观察、思考和对生活的感受,刺激了她想象力和洞察力的提升,为之后的书信及自传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
二、不断怀疑与自我反思
从苏珊·巴顿的心理切入,对她超越性的行为背后潜藏的活跃思考能力与问题意识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苏珊·巴顿是“有意识”地对自己的生存进行自由选择并积极行动,与甘于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并且困囿于自己活动范围中的传统女性不同,她是一个“自为”存在的角色。
《福》以苏珊·巴顿的第一人称叙述手法构建了前三章的内容,其中大量的对话和引号的运用成为小说一大特色。“库切曾经将《福》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主题技巧归结为‘声音’。”*Coetzee,Doubling the point 143.转引自段枫:《历史话语的挑战者——库切四部开放性和对话性的小说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小说中的对话和声音是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意识的全方位展现,为人物的行为提供阐释性依据,同时也为构建立体的人物形象提供了鲜活生动的补充信息。由此,苏珊·巴顿的叙述话语将她变化的思维过程呈现出来,其中,不论是在海岛、与福的通信或是与福的对话当中,我们都能从中看到她不断提问、反问及设问的具有怀疑精神与问题意识的行为。这种问题意识与对自我及世界的思考,体现出一个跨越女性内在性的反叛过程。
苏珊·巴顿自始至终对写作问题进行的思考体现出她作为女性渴望发声的意识。苏珊·巴顿流落至小岛之后,她在克鲁索(Cruso)的棚屋中一直想找到克鲁索的日记,但最终无果。她猜想克鲁索没有写日记的打算。苏珊·巴顿不断对克鲁索有关写作问题提出疑问,并且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进行了多次有关写作问题的思考,她将渴望发声的心理展露无遗,成为一个具有反抗意识的“失声的群体”的代表。在与《鲁滨逊漂流记》的对照中,我们发现,克鲁索(Crusoe)在安顿好住处之后便开始记日记。“我打算把所有的日记展现给你们,尽管日记里把已讲过的事又复述了一遍。一直到墨水用尽,我才被迫停止日记。”[4]39而在《福》中当苏珊·巴顿问克鲁索(Cruso)*原小说中的英文名,在《福》中库切将克鲁索的原名改为Cruso.——J.M.Coetzee:Foe.New York:Penguin,1986.:“假设有一天我们获救,你难道不会后悔没有在遭遇海难的这几年留下一些记录,没有让你所遭遇的一切留在记忆里?就算我们永远未能获救,在我们相继去世之后,你难道不希望在死后留下一些纪念品,或许下一波旅人漂流到这里,无论是谁,他们都有可能读到我们的故事,也许还会在读后潸然泪下?……”[7]13对此克鲁索不为所动。库切对克鲁索(Crusoe)的改写亦是颠覆性的,《福》中的克鲁索(Cruso)乏善可陈、消极被动*也有学者认为改写后的克鲁索(Cruso)仍是一个具有抗争精神的存在主义者形象。如武娜《存在主义视域下对库切〈福〉之解读》,《电影文学》2009年第24期。。库切将克鲁索(Crusoe)的形象改写成克鲁索(Cruso)后为人们留下的印象,正如有学者指出:“我们可以将Cruso缺失的那个字母e,理解为主人公情感(emotion)的缺失、生命活力(energy)的缺失和人格魅力(enchantment)的缺失。”[8]笔者认为此番改写与苏珊·巴顿对写作问题的反问,既突出了她作为一位女性渴望言说的心理*另有戈蒂埃认为,库切对原著中的克鲁索形象作如此颠覆性改写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说明殖民主义者已经失去早年的开拓精神和活力,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且还在提醒读者,殖民主义者已经成了一种老朽的古物,甚至丧失了记忆能力,只能等待像苏珊那样的历史学家或考古学者来使之开口说话。,也将苏珊·巴顿这位女性形象与《鲁滨逊漂流记》中具有超越性的开拓者男性形象作了平行对照。
苏珊·巴顿对女儿问题的质疑体现出她对看似合理的现实进行的自我思考,对男性世界任意篡改果敢提出反抗与质疑,为自己言说的权利与还原历史真相努力抗争。苏珊·巴顿欲将自己的探险经历记录下来,她将自己的故事告知认为能比自己更好地将其作为小说呈现出来的作家福。而福却为了迎合读者及出版市场肆意篡改她的小说,他在原设想的女落荒者在小岛上的经历中虚构了一条主线,即母亲寻女与母女重逢的故事。苏珊·巴顿对此十分不满,她不希望将她的出生与寻找女儿的故事曝光于众。“我之所以选择不说,是因为对于你或是其他任何人来说,我都没有必要用一长串的历史证明我曾经存在过。我宁可选择我在岛上与克鲁索和星期五共度的时光,因为我是一个自由的女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希望选择说出自己要讲的故事,这是我的自由。”[7]119在小说的第二章中,出现了一个自称是苏珊·巴顿的陌生女人,这个女人与随后出现的爱米女仆是福为使小说情节完整而特意安排的角色。当这个同样名为苏珊·巴顿的女儿第一次出现时,她并未直接相认,纵使女儿将自己的身份与来由设计得近乎完备。面对这位陌生的女儿,她提出了种种质疑。“是福派你来监视我的吗?”“你来见我的目的是什么?”[7]64按照自己的记忆和经历,她对陌生的女儿的种种身份描述进行一一反驳。在对女儿问题的质疑与对福的质询中,她不断提出疑问,开始对这个世界的构建的真实性产生思考。从福设计这个女儿和女仆的角色来干预苏珊·巴顿的真实人生开始,她觉得整个人生都要成为别人笔下故事的内容,她自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我的心中充满了疑惑。除了疑惑还是疑惑。我在质疑:谁在说我?我是不是也是一个鬼魂?我属于何种秩序?还有你,你又是谁?”[7]121由此生发出苏珊·巴顿对女性在男权秩序下生存的进一步思考。
苏珊·巴顿对自身处境问题进行了反复思考,这种自觉意识为她的反抗提供了清醒的判断。苏珊·巴顿来到克鲁索(Cruso)的海岛,作为女性,她进入了一个由主仆关系构成的男性世界中。初到海岛,她受到克鲁索的警告,海岛上有猿猴出没,猿猴不会像怕他和星期五一样地怕女人。克鲁索的警告引起苏珊·巴顿的思考:“对于猿猴来说,女人和男人有何不同?”[7]11作为一个外来者,这个小岛对于苏珊·巴顿来说更像男权社会的简化缩影。男性带着偏见思考女性问题,对女性的保护行为实则借由隐性意识的灌输制造控制与被控制的权力关系,使女性将传统观念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与思想。在克鲁索建造的权力社会当中,苏珊·巴顿很有可能会成为第二个星期五。而我们却看到,她不断对权力关系提出质疑与思考,“如果我们继续像兄妹、主客、主仆或是其他什么身份生活在一起,那样会更好吗?”[7]25“单说我们之间在这个岛上相安无事地生存着,就可以确定: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规矩。”[7]32苏珊·巴顿对女性处境的思考和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通过她的写作进行抗争,对男性社会控制的话语权提出挑战。
苏珊·巴顿对种种问题的思考,正体现出她自觉地对现存秩序和传统观念的质疑。对传统女性而言,“她不但对什么是能改变世界面貌的真正行动一无所知,而且迷失于世界中间……由于她在男人世界上一无所为,她的思想没有流入任何设计,和做白日梦差不多。她缺乏观察能力,对事实真相没有判断力”[5]676。与此相比,在男权社会的制度中,苏珊·巴顿没有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内化,通过对男性世界绝对性的质疑,产生超越的自我意识。这个世界的概念在苏珊·巴顿的脑中不是含混的,她没有接受男性的权威而是通过自己的逻辑思维和判断对现实事物提出质疑,对现存秩序进行思考,对自身处境采取行动。
三、拒绝屈从与渴望自由
由上可见,苏珊·巴顿的自由选择反抗命运的性格以及颠覆传统观念的反思意识,是苏珊·巴顿与传统女性内在性差异的一大表征。除此之外,受到这种意识的潜在支配,她对自我身份的构建与虚构的独立判断等皆通过写作体现了行动上的超越性表现。
苏珊·巴顿对写作的迟疑经过了一个心理变化的过程。对于最初史密斯船长书写荒岛经历的建议,苏珊·巴顿认为自己不懂得写作技巧,会掩盖迷人内容的鲜活性,对艺术一窍不通,因此有过放弃写作的想法。对此有学者指出,“作者并没有将苏珊刻画成一个女性话语的自我觉悟者”,认为其最初放弃写作的想法是屈从于传统女性地位的表现[9]。然而,苏珊·巴顿这种想法是清醒且经过深思后的决定,当船长劝她不妨试试,提出“出版商自然会雇人对其加以调整,在各处润色一番”的建议后,她十分坚定地说:“我不想里面有任何谎言……如果我不能以作者的身份出现,发誓自己的故事是真实的,那还有什么可以值得读的?”[7]35可见这并非是屈从传统女性地位的表现,而是经过自我审视和清晰判断后作出的具有自我认知性的决定,她认为福拥有能够传达出真正的实质感的一切外在条件,而她不具有。苏珊·巴顿发现福将她的故事大幅度改写,并且充斥谎言后,产生了自己写作的想法。到了小说的第三章,苏珊·巴顿与福对小说的内容进行梳理,在这个过程当中,福把故事的主要线索大幅度更改,凭空虚构出一条故事主线。对此,苏珊·巴顿意识到自己被夺取的实质。通过自己对故事的亲自言说反抗了女性身份建构的被动性及由男性建构的话语权威。
为了迎合读者,福将真相掩盖,对原有故事进行虚构加工。认识到这点,苏珊·巴顿认为故事的空洞与枯燥是由于星期五的沉默造成了他的那部分历史故事的缺失。因此苏珊·巴顿和福费力教授星期五读书写字,试图让星期五开口言说,还原他的真实历史。可惜一切只是徒劳,星期五已失去学习或言说的能力,他只会随意地在石板上涂画。库切借由星期五设计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图形。“当我走近一看,才发现叶子其实是眼睛,睁开的眼睛,每一只眼睛都长在一只人脚的上面:一排排的眼睛下面都长着脚,成了会走路的眼睛。”[7]136有学者认为这个图像描绘的是将读者作为一个旅行者的隐喻*Friday’s design is a graphic depiction of the metaphor of the reader as a traveler.——Michael Marais ,Reading/Colonizing Coetzee’s" Foe",English in Africa, Vol.16,No.1(May,1989),pp.9-16.。而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有关身份与话语权建构的隐喻。叶子上的眼睛是我们用于凝视世界的目光,我们在凝视他者的同时也在被他者所凝视,整个世界正是由无数目光交织而成的网。萨特认为“人的身份本身就是凝视的产物”[10]。在凝视的目光构建的网中,似乎我们只有通过别人才能看清自己是谁,在别人的注视下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图形中眼睛下面的脚则是人行动的象征,凝视与行动是一个彼此互动的过程,而失去言语能力的星期五画出这样一个图形,则暗示着其渴望通过言说行为建构自己身份的处境。小说中,苏珊·巴顿说星期五像她的影子一般,星期五失去了语言的能力,他在他者的凝视中被建构了自己的身份,与此相像的是,他可被视为一个被剥夺话语权时女性的象征。如此对照,苏珊·巴顿通过写作反抗男性对女性形象的歪曲,她是一个渴望自由言说的女性形象,渴望成为自己故事的创造者。
苏珊·巴顿绝不屈从于他者对真相的虚假改写,她时刻关注话语权的问题,体现出她对自由的渴望。福先生曾对苏珊·巴顿说过一个寓言:一个女人被判犯了偷窃罪,上绞刑架之前,要求牧师听她忏悔,因为她从前说的都是谎言。女人讲述了她一生犯下的诸多罪行,成为十足的罪人,倘若她说的不是实话,则犯下亵渎神灵的更重的罪。于是女人就不断地忏悔,然后再质疑自己的忏悔。最后牧师赦免了她的罪。福先生在其中看到的隐喻是总有一个时刻,我们要对世界有个交代,一次获得永恒的平静。而苏珊·巴顿关注的则是牧师拥有的权力。“在她看来那位牧师比最强的力量还厉害,决定着最后的定论。”[7]112牧师是宗教话语的传递者与代表,他们的话语拥有主导女性自由的决定性力量。在现代文明中,宗教是欺骗女性的工具,“当强迫一个性别或一个阶级出于内在性状态时,就必须为它提供一个进行某种超越的海市蜃楼”,“女人不再被否认有超越性,因为她要把自己的内在性奉献给上帝”[5]700。苏珊·巴顿意识到了宗教话语的强大力量,宗教将女人的反抗与劣等地位都在其营造的平等的幻想中被扼制住。从苏珊·巴顿关注的问题上,我们发现,在对问题提出质疑、思考过后,她清晰地看到那些掌控话语、为女性安于内在性而制造幻境的对象。她通过自由地掌控自己的话语权,对男性霸权进行反抗,实现自我的超越。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诺奖授奖辞中这样评价库切:“在人类反对野蛮愚昧的历史中,库切通过写作表达了对脆弱个人斗争经验的坚定支持。”库切在《福》中借由对笛福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多角度改写与多声部对话,反省了边缘群体的身份认同和生存处境等问题,并将这些问题讨论的焦点自然地汇聚到苏珊·巴顿这个女性形象身上。库切通过女性叙述视角和对女性形象的多维度刻画,还原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声势浩大的男性“英雄神话”背后脆弱个体微弱但有力的脉搏颤动,这种反叛和渴望自由的斗争成为小说的潜在力量。
[1] 蔡圣勤.孤岛意识——库切的创作与批评思想研究[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17.
[2] 任海燕.探索殖民语境中再现与权力的关系——库切小说《福》对鲁滨逊神话的改写[J].外国文学,2009(3).
[3] 黄晖.叙事主体的衰落与置换——库切小说《福》的后现代、后殖民解读[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4).
[4] 笛福.鲁滨逊漂流记[M].张蕾芳,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164.
[5]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下册[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673.
[6] [英]弗吉尼亚·吴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贾辉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49.
[7] [南非]J.M库切.福[M].王敬慧,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
[8] 张德明.从《福》看后殖民文学的表述困境[J].当代外国文学,2010(4).
[9] 高敬,石云龙.试论后殖民语境下库切小说《福》中的话语权[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2(10).
[10] [英]丹尼·卡拉瓦罗.文化理论关键词研究[M].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31.
责任编辑:刘海宁
I47.095
A
1007-8444(2014)05-0639-06
2014-07-31
2010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的生成与传播研究”(10&ZD135)。
傅守祥(1970-),教授,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所兼任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哲学、艺术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艺术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