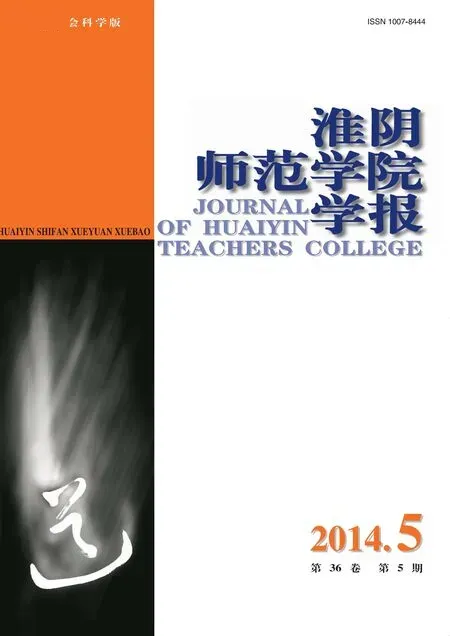萧一山与“新史学”
刘永祥, 魏 蔚
(1.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2.山东英才学院,山东济南250104)
近年来,学界对萧一山(1902—1978年)的史学成就颇为关注,发表了不少相关论著。已有成果尽管不乏创新之见,但似乎未能真正把握其史学主旨,对其代表作《清代通史》的学术特色也未能给予透彻分析。实质上,萧一山是梁启超“新史学”的承继者和开拓者,不仅在理论上展开进一步探索,而且将其运用到清史编纂的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本文拟对此略申己见,以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
一、“新史学”流派的承继者和开拓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史学是对乾嘉考史的反动,尤其是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借助西方新学理,以突出的忧患意识、深刻的批判精神和浓厚的爱国情怀,对传统史学展开全面检讨,并在吸收其精华的基础上建构了新的史学理论体系,主张从宏观上对历史加以解释。“五四”前后,在新文化运动、新史料的发现和西方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等因素影响下,接续而高于传统考据学的新历史考证学逐渐兴盛,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的局面。以往认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兴起令新史学迅速走向消亡,实则不然。这一时期,不仅梁启超本人对原有体系加以深化、完善,而且还有一大批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在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萧一山正是新史学的重要承继者和开拓者,与梁启超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在学术上深受其影响,形成了博通的治史风格。他曾明言:
余一生所钦佩者二人:一、孙中山先生,二、蔡孑民先生……除此则感恩知遇者,梁任公先生一人而已。梁先生之精神伟大,非一般人所能喻,余面承教诲,身体力行,一生行事,绝不敢违背孙、蔡、梁三公之精神,此余敢以自誓者。[1]586
萧一山自幼酷爱史学,对《史记》《史通》《通志》《资治通鉴》《日知录》《文史通义》等均“用过功夫”[2],并在父亲影响下熟知公羊学要义。上述知识积累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其学术品性,后来他“极力提倡通史通儒通才”[3]卷十《悼张荫麟君》60,与中国史学讲求通识、致用的优良传统不无关系。故而,当他接触到以进化史观、爱国主义等改造这一传统的新史学时,迅速引起思想上的共鸣,并将其作为清史编纂的理论指导,同时又继承章学诚、梁启超等在史书体裁上的综合创新意识,把新式章节体与传统体裁熔于一炉,撰成了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气象博大的“新式”清史。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当蒋百里把《清代通史》上卷书稿拿给梁启超时,会得到梁的激赏并亲为之序,称:“萧子之于史,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遵斯志也,岂惟《清史》?渔仲、实斋所怀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将于萧子焉有望也!”[4]梁启超序编纂符合新史学宗旨的中国通史,是梁启超始终未能完成的宏愿,而萧一山的勇于实践显然让他倍感欣慰,遂推荐萧氏到清华任教。
作为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能得到当时史学泰斗的高度评价,萧一山所受鼓舞可想而知。他窥得学术门径,并渐次登堂入室,显然都与梁启超的指导和提携密不可分。他回忆说:“年十九,由晋转学北雍,得阅京师藏书,于清史尤致力,成书约五十余万言。受知于新会梁先生,介而教授清华,与共朝夕,始窥学术藩篱,续成清史乾嘉道三朝事,约六十万言。”[3]自序而晚年对清史编纂进行自我评价时又谓:“《清代通史》系余一生事业之总结……顷四十余年之心力,写四百一十万言之通史,仿浹漈实斋之义例,贯中外史学之通则,自信尚能‘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愧梁任公先生之期许也。”[1]《非宇馆五十自述》586凭一己之力,耗时 40 年,践行恩师的史学主张,成就修史大业,堪称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新历史考证学与新史学的核心差异,就在于前者本着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致力于考证历史真相,而后者则出于强烈的现实关怀致力于解释历史进程,颇近似于古代史学的“专”与“通”、“求真”与“致用”。当时,鉴于“破”的目的已经达到,新史学的首倡者梁启超遂将重心转移到史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上,表现之一就是,在坚持以历史解释为史学终极目标的基础上,强调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从事部分考据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考史”风气的弥漫起到推波助澜作用。不过,梁的考据却被时人批评为“非稗贩东人,则错误纷出,几于无一篇无可议者”[5],并就此贬低其史学贡献。对此,萧一山给予严词批评,极力维护恩师的学术地位,明确揭示出其史学主旨,并大力倡导广博、通贯的史学方法论,“以破支离分裂之考征,辟饾饤补苴之功力为事”,认为历史研究可以划分为“考据与史学”两个不同层次,直斥“今之人受所谓整理国故者之影响,以考订破碎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此梁任公先生之所以见轻于人,而弟之所为深痛者也”,又谓“汉学足以亡清,国故亦足以亡中国”[3]卷九32。这从他所撰《悼张荫麟君》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自己有一套理论,就是极力提倡通史通儒通才……反对当时饾饤琐碎风靡一世的考据派史学……任公先生说我有胆量有见识,但他不愿公开提倡,因为他受了“新汉学”派的歧视,颇欲争一日之长,实则他老先生的成就,已远绍亭林,近逼实斋,绝非“新汉学”家所比拟,而荫麟兄今日对于学术界最大之贡献,亦即在此。可以说是任公先生的薪传,荫麟兄实为接承之第一人,使二人地下有知,必当含笑谓余知言也……须知宏博不难,而坚实为难,宏博而不坚实,则有疏浅之弊,“新汉学”家之攻击通儒通才,常以此为口实。任公先生之见訾于人,即由此故,实则任公先生能谓之疏浅乎?乃别派不明学术之源流,有意有此谬说,荫麟兄所谓任公先生之贡献于史学全不在考据,而在史才,其识见固已超越恒流。[3]卷十《悼张荫麟君》59-61
从研究范式和学术风气上讲,梁启超和胡适分别开辟了以历史解释和历史考证为中心的史学科学化道路。很显然,在萧一山的学术体认中,他和张荫麟同属梁启超新史学一脉,以疏通为史学旨归,极力反对史学走入史料整理一途。在他看来,“史学本为一综合科学,必广览洽闻,得博约之旨,而后始能无偏执固陋之弊,是史学又以贯通为务,殊非仄深之士所能喻也”[3]卷四《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134,因此批评胡适“以‘家世汉学’走入支离破碎之途,号曰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实他所用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是一种演绎法,清代的汉学家,已有此弊。又不能真正抉发‘国故’的精华,仅是些抱残守缺的考据事业,所以与科学的距离,一天一天的远了”[1]《蔡元培》499,认为这一派“只可以说是考据家,如果也称他们是历史学家,那就不对了”[3]卷二《历史上几个重要的问题》131。上 述 批 评 言 辞 犀利,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烦琐考据的危害,但也因心存门户之见而未免抹杀太甚,未能理性看待新、旧历史考证学之间的本质区别①参见陈其泰《新历史考证学与史观指导》,《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不过却充分折射出他在梁、胡之争中的鲜明立场,而两种学风之间的巨大张力,更由此可见一斑。
二、中西交融下史学理论的新探索
20世纪初,梁启超首倡新史学,以鲜明的立场对两千年旧史展开激烈批判,并围绕什么是史学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可以概括为:主张在史观统摄下对历史加以解释,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坚持“求真”前提下的史学致用观,主张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崇尚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并讲求史书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主张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人类社会生活全貌;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倡导跨学科的治史方法等,初步建构起与中国传统史学相区别,与西方现代史学相接轨的理论范式,吹响了中国史学转型的号角,并引起人们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的深刻变革。五四以后,除了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崛起外,新史学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发展。有的学者将理论付诸实践,编纂出许多有影响的新式史书;有的学者充分把握西方史学理论大量涌入的契机,积极进行理论的二次提升;有的学者则于上述两方面同时用力。萧一山属于第三类。
事实上,新史学这一概念在民国学术界的使用存在明显的泛化趋势,几乎所有史家都以此看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所怀有的目标也并无二致,即:融合中西以成新的史学话语体系,只是在实现途径上却往往大异其趣。与新历史考证派不同,萧一山认为,一个合格的史学家,绝不应止步于事实真相,必须考察史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从整体上解释人类历史进程,并总结出带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发展规律,这才是史学的根本任务和终极目标。他明确指出:
历史既包罗万象,如何能贯串得法,措置合宜,始综合文化政治经济三方面的事态,可得历久常新颠扑不破之理则呢?这才是史家所蕲求的……研究历史的人,必先懂得史律史法,不可以小学的专家自限。[1]《清代档案之整理与研究》432-433
史学者,钩稽史实之真象,为有统系有组织之研究,以阐明其事变演进之迹,并推求其因果相互之关系者也。[4]导言
至于他所运用的解释工具,则是进化论。经过新史学思潮的涤荡,进化史观逐渐取代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循环史观、倒退史观等,成为一般人认识历史的基本观念,更内化为史家的学术自觉。萧一山就认为:“社会是进化的,历史是积累的,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必然的内在的密切关联的,必顺其自然的发展,而后能形成一种自然的进化史律”[1]《民族革命运动之厄运》48,“世界进化为人类颠扑不破的真理”[1]《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211。不过,线性进化论虽然在唯物史观兴盛以前一直主导着史学界,但于内涵和运用上都表现出简单化和机械化的弊端,已经无法满足解释人类社会复杂历史进程的需要,引来不少学人的批评或重新思考。比如,章太炎就曾撰写《俱分进化论》加以驳斥[6];梁启超本人也曾予以部分修正[7]。而萧一山在综合中西史学、文化的基础上,勇于独立思考,并大胆提出新的见解。他设想说:“世界上所谓进化论者,也不是说一往直前,有进无退的。有人以为进化如波涛起伏,有人以为进化如螺旋上升。我的想象是大小循环,双重进化,如地球之自转与公转然。”[1]《中国近代文化政治之演变》267试图将传统史学常用的盛衰循环观纳入进化论范畴,以解释变幻莫测的历史现象。
同时,他又紧跟时代步伐,用辩证法的三大定律丰富其历史哲学。只是,他在本体论上持折中态度,进而认为历史解释上的唯心和唯物倾向“皆不免各有所偏颇,唯用‘社会的方法’以研究之,则无是弊。即愚所谓普通史之社会一般现象也。盖用此法,则两观并用,心物兼摄,而以时间空间为枢纽,无挂一漏万之弊”①见萧一山《史学之研究》。此文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出处不详,文末标注写作日期为1922年1月10日。。再者,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他将辩证法视为中国文化所固有,认为“我国在二千年以前即已发明,且为中国文化之精华”,即孔子的中庸之道,而且认为它“以精神与物质并重,实在比他们(指黑格尔和马克思)更进一步”[3]卷一8,并将其称为“不变之通则”[1]《论物质与精神》528,“用在历史方面,叫做‘历史定律’,用在社会方面,叫做‘进化法则’,用在科学方面,叫做‘宇宙真理’,用在哲理方面,也可称‘辩证逻辑’”[1]218-219。赋予传统概念以近代内涵,表面看来抹杀了两者间的根本区别,实则折射出他急切的民族文化复兴心理,而在历史解释上兼顾心、物的“综合史观”,相较单线进化论而言,无疑是较大的进步,并且这一学术取向不单单表现在他一人身上,张荫麟、杨鸿烈、陆懋德等都有类似主张,反映了新史学在史观领域所达到的理论高度,而这与唯物史观的日渐兴盛不无关系。当时,他们一般将唯物史观界定为“经济史观”,萧一山就称“此说为历史之经济的解释……故比较言之以‘经济的历史观’一辞为妥”①见萧一山《史学之研究》。,故而在肯定其合理性的同时,指出它与其他史观一样失之偏颇,无法给出一个完满的解释,遂力倡综合考察政治、经济、文化等之间的关系。对此,胡秋原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萧一山在当时学界以史料为史学的风气下,“肯定史学要研究历史的因果关系,说唯物史观值得注意,但是,历史必须是文化、政治、经济的历史,必须注意三者及三者之关系……真是难能可贵的”[1]《我所知道的萧一山先生》765-766。
除进化史观外,萧一山还在继承经世传统的基础上,将新史学有关史学功能的理论推进到新的层面。他认为,中国学术的本源,“只是‘经世’两个字,引而申之,可谓‘经世致用’之学”,但汉学“驱使一般聪明才智之士,竭其毕生精力,往‘故纸堆里’钻”[3]卷三《经世释义》7,宋学则“让一般聪明才智之士,竭其毕生精力,往‘鬼狐禅’路上走”[3]卷三《这一年》17,均失其精义,民国以来,“有些人埋首研究,‘为学问而治学问’,成绩亦颇斐然,但褊鄙自是,忽视一切,不知指导社会,照顾人生,和现实联为一气,仍受经学家襞续补苴之遗毒”[3]卷二《近代社会之症结》97,而这种学风“致使史学人才不能负荷时代所赋予之使命”[3]卷四《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134。因此,他大力倡导经世之学,并将史学置于所有学科之首,指出:“而今文化革新,国运衰替,士子多瞩目瘁心于事变之哲理,与夫实用之科学;于史学之綦要,乃鲜有注意及之者。不知增进文明,浚疏人智,史学之在今日,较他学科为尤要焉。”[4]导言在他看来,“史学为基本学科,人之求学,为扩充经验增智识也,史学即经验之宝库,智识之锁钥也,不有史学常识,而大言精诣于某学科,是犹矗立之柱而无础也,植愈高则危险愈甚”[3]卷五《中国通史大纲序》10,继而指出:“人类为什么需要历史?就是因为人类需要将过去所发生的现象,以及现在所演成的局势得到一个综合的认识,而人类可以利用这宝贵的经验,来促成社会的进步!支配社会,创造社会,才能使社会调和而不至冲突倒演。”[3]卷二130与早期新史学从政治视角出发将史学视为爱国心之源泉不同,萧一山乃从知识、经验的角度立论,并将过去、现在、将来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因而史学就成为关乎整个人类社会走向的学问,显然更为理性、丰富、深刻。
值得一提的是,史学与文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不能脱离史实向壁虚造,因此史料的搜集、鉴别实为治史的基本手段。早期新史学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对此确实有所忽略,五四以后则着意弥补。萧一山也明确指出文、史学科的性质差异,认为“历史虽不能全真,也要近真,才有价值。否则,‘满纸荒唐言’,那不成为小说了么”[1]《怎样研究历史》469,并强调说:“考信的功夫,是治史者应有的精神……最好是‘小心求证’,不要‘大胆假设’。”[1]467因此,他“并不反对合乎‘经世’之旨的义理考据与词章……却反对静坐空谈的义理,饾饤琐碎的考据和吟风弄月的词章……提倡合乎‘经世’之旨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却不提倡以读书空谈写作为能事而实际受了汉宋学遗毒的目前国人之所谓科学”[3]卷三《经世第四年代》26-27。
新史学之治史鹄的在于寻求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法则,进而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这要求对长时段历史具有高度的宏观掌控力,而往往借助于大规模的“著史”来实现,并在史学范围上力求突破政治史范畴而描述社会整体情状,因此这一派的学术成就在实践层面大都体现于历史编纂领域。萧一山在努力推进新史学理论建设的同时,以此为指导开展清史纂修工作,以非凡的气魄和毅力完成一部410余万字的《清代通史》。他曾自言:“四十余年来,孜孜矻矻,惟以读书著史为业,真不知老之将至。”[2]583这部皇皇巨著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是新史学在断代史领域的成功范例!
三、《清代通史》的编纂特色
事、文、义,是中国传统史著的基本元素,优秀史家无不融三者于一炉,而以史义为灵魂统摄全书,包括对历史进程的把握、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对历史事件的判定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等,这是西方史学所谓史观能够传入并生根发芽的文化土壤。《清代通史》的最大特色,也是核心价值,就体现在史义的贯彻上,而非细密的考据或华丽的词章。张其昀的评价可谓切中肯綮:“考据义理与辞章三者,虽性质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譬之人身,考据其骨干,辞章其肌肤,义例其灵魂也。必须断之以义,始尽史之能事。三者之中,孔子自谓有取于义,一山通史,亦以义为全书之精神所在。”[1]《介绍萧一山清代通史》675-676
萧一山深受传统经世精神和近代民族主义影响,又对中国所遭受的压迫有切身体会,因此努力探寻文化复兴之路,尤其看重史学的功用,而刚刚过去的清代历史特别是晚清部分,无疑最具参考价值,这是他将清史作为研究志向的思想动因。当然,他的治史路数与重在考证史实的孟森等人存在很大差异,不将清史视为众多历史事件的堆积,而是看作环环相扣、紧密联系的整体,力求通过深入分析史实间的因果关系,得出有规律和有价值的认识,因此绝非那些编纂史书只知“条列史实,缺乏见解”[8]者可比。他明确指出:
夫历史事变,具有因果,首尾相承,累代一贯;吾人既不能于其间有所绠断,则历史亦不当于彼此有所分割。且社会演进之象,又属“有渐无顿”;而人类旧习之保存,亦为人性自然之倾向,其结果即成历史上所谓“历史之继续”……盖以人类习惯无骤变之迹,亦无骤变之理;此语殆成史学上最重要之原理。[4]导言
历史的发展是前后一贯、不可分割的,因此任何历史现象的产生都不能一蹴而就,必然有长期的积累。故而,他编纂清史时特别注重连续性和整体性,力求做到丝丝入扣,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历史的断裂感。包遵彭曾评价说:“根据中外史料,以阐明其事变演进之迹,并推求其因果相互之关系,斯真可达渔仲实斋所谓圆通之旨,而尽新史学有系统有组织之能事矣。”[1]《读萧一山先生清代通史》683
上述思想贯穿全书,最突出的表现无疑在于提出了“民族革命史观”,并以此为中心展开对近三百年清史复杂进程的解释。对于这一产生深远影响并引起广泛争议的史观,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首先,它是新史学讲求历史法则在清史领域结出的硕果,具有重要的学术示范意义,为民国学风的多样化贡献力量,并且充分反映出萧一山的独立创新能力,可谓成一家之言。其次,它的产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遭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必然结果,是符合历史潮流、具有突出时代意义和进步性的史学思想。第三,萧一山的目的,在于唤醒国人的自信心,团结人心以挽救危局,同时也隐含着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复兴理想。第四,切不可忽视这一史观的局限性,应作两段式评论。就晚清历史而言,将民族革命视为基本线索之一自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若将之前的历史演进主线也归结为民族革命,认为政治、经济、文化“之所以能互为影响,则又以异民族之统治压迫造其因”[4]导言,不仅有失偏颇,而且混淆了民族内部矛盾与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革命之间的性质,并非科学的民族观点。
近代以来,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趋于瓦解,与之相适应的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模式也逐渐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则是新史学对“民史”的倡导。他们强调历史是“整个的”,史家的职责在于写出社会全貌,叙述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历史演进的影响,而尤为重视发掘和记述普通大众的社会生活。《清代通史》的另一大特色,正在于采取政治、经济、文化均衡铨叙的编纂原则。
萧一山具有创造精神,在史著结构和风格上有明确追求,在“叙例”中鲜明地标示其编纂主旨:
本书所述,为清代社会之事变,而非爱新一朝之兴亡……近世唯物史观之学说兴起,谓……历史之因革,尤以经济为转枢……吾人既不能不认生计为历史上最重要之问题,亦不能认文化政治纯受经济之支配。盖普通史之内容的评价,为文化、政治、生计三者:文化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导一切;政治握社会上最大权力,故能支配一切;而个人之生存,社会之维持,又端赖生计,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者也。本书取普通史例,故三者亦均衡诠叙之。
他借鉴西方史学中“普通史”的做法,纵的方面,要考察清代历史的变迁过程,清代与其之前的明代史、其后来的民国史之间的联系;横的方面,要叙述清代社会各环节以及各地区、民间的情状和相互影响。换言之,其所记述的乃是涵盖清代社会方方面面的一代全史,而非简单的皇朝兴亡史,亦即突破旧史偏重政治记载的束缚,展开全方位的探索和论述。本书虽为断代史而命名为通史,原因即在于此。故而,他在梳理清代政治盛衰大势的同时,对清代社会的经济如土地、人口、农业、工业、商业、税收、国际贸易等各项,无不一一详细阐述。而且,他还充分重视各族人民的生活状况,对于汉族以及南方、北方各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宗教、习俗等内容,也详加记载,阐述其形成与流变,提出诸多有见识的看法。相较以往史著而言,这些无疑具有首创价值。据粗略统计,萧氏专论和涉及经济、人民生计的论述,达到全书的五分之一,无疑是写史未曾有见的新创制,无怪乎李大钊称其为“有清一代之中国国民史”[4]李大钊序。
任何史学著述都离不开一定的体裁形式,其运用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到史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中国史学历来有重视体裁的优良传统,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编纂形式,先后产生了编年、纪传、典志和纪事本末等几种主要体裁。“17世纪以后,在历史编纂上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9],其主要特点,在于突破单一体裁的限制,糅合几大体裁之长,创造出既能反映历史演进大势,又能涵括社会丰富内容的综合体裁。步入20世纪以后,随着新史学的兴起,西方章节体迅速风靡全国,成为最流行的史书编纂形式。与此同时,新综合体的趋势也在延续,并有了新的内涵,即: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章节体之中。《清代通史》正是章节体在大型史书编纂中的首次成功运用,但同时又广泛吸收了传统体裁的优点,从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全书共分3卷17篇,每一篇下再细分章、节、目,并且连续编号以突出历史的连续性,层层统摄,前后连贯,浑然一体,大致按照清初、康雍、乾嘉、晚清的时间顺序展开叙述,在内容上则兼顾政治、经济、文化等,将章节体层次清晰、逻辑严密、容量宏富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当时学界多将章节体运用到中国通史编纂中,而习惯于划分历史为上古、中古、近世等几大时期,每个时期中先用较多章节叙述政治演进,再用一到两章叙述社会组织、制度、经济、文化等。对此,萧一山批评说:
今之治普通史者,多以文明史附丽于每期之后;是不啻以一史划割为两部,而为政治史文明史之混合物也……今拟力矫此弊,统摄诸种现象于一小时期中而并述之。[4]叙例
他把“通”的精神贯彻到章节体中,不把清史分为政治、文明两大部分,而是细分为几个小时期,从多个视角对每个小时期进行综合叙述,分析彼此间的内在联系,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历史的完整性。
值得注意的是,纪事本末体与章节体之间存在共通性,都便于体现历史演进大势,符合新史学的要求,章节体顺利传入中国的内在基础正在于此。萧一山对旧史体裁的优劣了然于胸,他说:“纪传之属,详于状个人,而疏于谈群治;编年之作,便于检日月,而难于寻终始。其间虽纪事本末一体,略有合于新史学之义,然其体创始于袁枢,特为便读《通鉴》者之寻览。即后之继此而作者,亦不能有深识别裁,以斟酌乎其中。故皆史实散漫,略无系统,可以为史料,不足以为史学。”[4]导言因此,他高悬深识别裁和系统性的目标而在体裁上下尽功夫,一言以蔽之,即发挥章节体的优势,弥补纪事本末体记载范围狭窄、彼此互不统属的缺陷。全书在风格上已呈现由叙事向研究的转型趋势,但无论是篇目设置,抑或历史叙述,仍带有突出的纪事本末风格,将因“事”命篇、不为常格的方法运用得恰到好处。包遵彭评价说:“普通史是一种综合的组织,近于吾国之纪事本末体,尤与东西洋近代史学之分篇章节者相同。然本末一分,西史二三分之体材,均未免简略,此书分卷篇章节目,系统尤为详密。”[1]《读萧一山先生清代通史》681此外,萧一山在有关社会、经济、生活等章节借鉴了典志体的长处,而于清代学术大致采取以人为纲的方式,以及史表的设置则又是吸纳纪传体的优点。
结语
易代修史是中国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然清朝灭亡近10年后,官、私领域的清史修纂仍是一片沉寂。萧一山继承、发展了梁启超首倡的新史学理论,并将其贯彻到清史撰写中,又在体裁上极尽创新之能事,成功编纂出气象博大、新意迭出、风格独特的《清代通史》,不仅为清史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而且为历史编纂的现代转型作出卓越贡献,更为人们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演进路径提供了重要参照,同时又提醒学者应对“新史学在民国时期的演进”这一命题给予高度重视!
[1] 萧一山文集编辑委员会.萧一山先生文集[M].台北:经世书社,1979.
[2] 江地.萧一山传略[J].社会科学战线,1987(2):227.
[3] 萧一山.非宇馆文存[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4] 萧一山.清代通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 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M]//李红岩.素痴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194-195.
[6]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7]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
[8]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77.
[9] 陈其泰.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