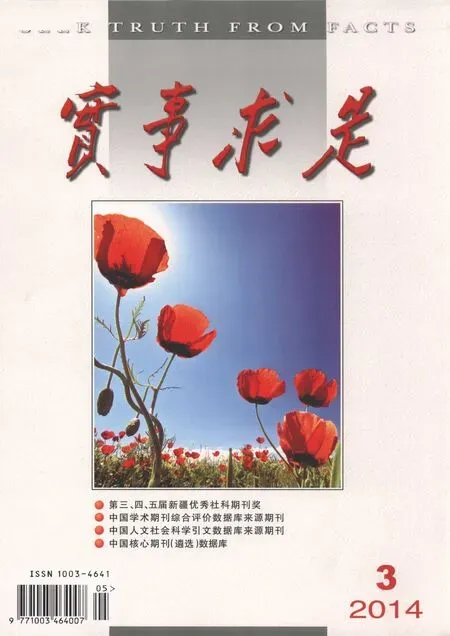美国对朝政策的文化透视以美国的东方主义为例
李东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美国对朝政策的文化透视以美国的东方主义为例
李东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与美国惯有的“优越”传统文化使得美国的意识形态表现出了浓厚的东方主义,其基本特征是人为地构建了美国与东方的二元对立。某种程度上,这种东方主义文化也影响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其典型表现之一就是美国对朝政策的“单边主义”。中国与朝鲜同属于东方国家,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美国对朝政策的文化意蕴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
美国 东方主义 朝鲜
本文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范式来分析和研究美国视朝鲜为“邪恶国家”的文化根源以及美国对朝政策的文化意蕴。笔者并无意于将美国对朝政策的制定全部归于东方主义的影响,更多地是想考察美国对朝政策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因素。某种程度上,正是依据美国文化中所蕴含的“优越性”,美国东方主义者们人为地构建了美国与东方的二元对立。这在美国对朝政策上也有着显著的表现,即美国试图利用单边主义的方式在朝鲜和中国等东方国家推行美国式的民主与自由。因此,考察和分析美国对朝政策所表现出来的东方主义文化,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换以及国际政治思维的创新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的东方主义者人为地构建了美国与东方的二元对立
“东方主义”一词来自于阿拉伯裔的美国人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其基本特征是创造西方的“自我”与东方的“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按照爱德华·萨义德的话来讲,“东方学假定了一个一成不变的、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东方(其理由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1](P311)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的东方主义者大都通过一种批判性的话语,根据语言、肤色、种族、气质、文化等类型的划分标准,对事物进行整体性的概括与归类,把东、西方简单地构建成“我们”与“你们”之间的截然对立。在这种思想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美国政治精英们,其政治思维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文化的烙印,因此,对美国东方主义文化的考察与分析,是我们透视美国对朝政策的一种全新视角。
一方面,美国人的东方主义来自于对西方中心主义思想遗产的继承。在西方理论界,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观点:西方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的文明,世界上的其他文明不是软弱无力,就是被西方文明所同化。西方文明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适文明”,西方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指出:“欧洲人自视为传授文化的正统,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在欧洲以外的,有了文化的发展,有了独立思想,便视为反叛。所以用欧洲的文化与东洋的文化相比较。他们自然是以欧洲的文化是合乎正义人道的文化,以亚洲的文化是不符合正义人道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优越感的驱使下,西方中心主义者们否定任何文化类型的发展都是根据自身不同的背景、条件、道路和需要而做出选择和创造的结果,坚持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的价值取向、判断标准、道路模式才是契合于文明精神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有意或无意地不去倾听东方的声音和诉求,而是以站在高处的姿态来打量东方的一举一动。而美国则是一直以来,特别是从20世纪开始进入国际权力角逐的舞台以来,承担的经常是西方传统文化代理人和捍卫者的角色,因此,美国社会同样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其外交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受这个思想意识的影响。
另一方面,美国独特的价值信仰与其特有的“天赋使命”、个人主义等文化传统,滋养了其东方主义的文化。作为美国最基本的国家意识形态,“美国优越”的概念被反复强调。美国人认为,美国是被上帝选中的国家,自己是“山巅之城”的居民,这就要求美国承担起“救世主”的角色和充当自由与民主的楷模。基于此,既然美国是民主自由的传播者和人权事业的捍卫者,那么其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了。我们就此不难看出,美国对其“优越”、“例外”的宣扬在客观上也就造成了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及其文化、价值、模式、道路之间的对立。为了证明其“优越性”和“例外性”,就需要一个负面的“对立者”来加以衬托,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就是在外部世界寻求一个“丑恶”或者“邪恶”的对手来美化自己。正如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美国清教徒的“山巅之城”的神话,导致了美国在看待外交冲突的时候有一种把对手“妖魔化”的倾向,而且这种神话使得美国人深信自己有一种责任把民主和自由传播到整个世界。他说:“清教徒把他们的社区看做善的所在地,而把世界的其余部分看做是邪恶的。后来的清教徒们一直是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美国,并认为美国有一种责任用上述形象来改造世界。”[2](P15)美国著名外交史专家亨特在其著述里也特别提到,美国的国家使命感以及美国对“东方人”的文化和种族偏见对于美国对非西方的态度与外交政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容易把非西方民族贬低和丑化为非人性的。[3](P176)就此而论,这也是美国提出“朝鲜邪恶论”、“中国威胁论”的原因之一。
那么,作为朝鲜等东方国家方面,面临着美国文化以及在外交政策上咄咄逼人的态势,不能不有所反应,只不过是反映的程度和策略不同罢了。我们知道,朝鲜是属于东方的国家,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所不同的是,朝鲜的政治精英选择了较为超前的意识形态,其国家行为与政治发展都对意识形态有着很大的依赖性,这就在某种方面加重了意识形态的教条化倾向。因而朝鲜对美国的文化攻势和批评指责,就比其他东方国家更容易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来加以解释,朝鲜的反应也就比其他东方国家显得更为激烈些,同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朝鲜意识形态的刚性特征。据此,美国更加确认,朝鲜这个“桀骜不驯”的国家总是在跟美国“对着干”,于是找各种借口尤其是抓住朝鲜的核开发问题不断向朝鲜施加各种压力,这更使得被美国视为“邪恶轴心”的朝鲜感到安全上始终受到威胁,觉得只有进行核开发才能维护其安全利益。基于这种恶性循环的逻辑推理,美国与朝鲜的二元对立性也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典型。
二、美国对朝的“单边主义”政策是东方主义的典型表现
关于“单边主义”的政策,专家学者从各种不同的理解角度对其有着不同的认识与看法,因此,单边主义并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定义。但有一点比较确定的是,美国对朝的单边主义政策与美国的东方主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谋而合。正如我国著名学者王辑思在其《美国霸权的逻辑》一文中所指出,美国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就是“美国式‘个人英雄主义’灵魂深处所固有的特征在国际舞台上的自然表现”。[4]也有学者同样指出,美国对单边主义外交的追求就是对美国在世界上自由意志、自由行动、自我霸权的追求。与其说单边主义是布什的作风,不如说它所代表的是美国风格。[5]在这里,“美国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美国的文化特征。这些表述都直接或间接揭示了美国外交政策与美国东方主义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即当美国实现自我价值或彰显自我需要的时候,美国的这种东方主义文化就可以为其提供坚实的营养根基和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纵观美国的外交历史,单边主义是其外交政策的主线,只不过是“有的时候单边主义表现强烈一点,有的时候表现的弱一点;合作程度大一点或者弱一点都是可能的,但始终是围绕这根主线上下波动。”[6]因此,美国对朝鲜政策的主线也是单边主义,同时也表现出了围绕着这根主线上下波动的特点。如在美国国内,在对朝鲜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是强硬派,也称意识形态派,该派主张采取高压政策压垮朝鲜或更替朝鲜政权;另一种是务实派,也称理性现实主义派,该派主张采取接触政策使得朝鲜发生有利于美方的变化。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在两派之间左右摇摆,时而强硬,时而缓和,但不管如何摇摆,美国的对朝政策都始终围绕着“单边主义”这根主线上下波动。2005年9月,第四轮朝鲜六方会谈签署“共同声明”之后,美国对朝的强硬派一度占了上风,他们以参与洗钱、制造假币以及贩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朝鲜的八家金融公司进行了经济上的制裁,冻结其在美国等地的财产,致使朝鲜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这引起了朝鲜的巨大反弹,朝鲜并没有屈服于美国的有关压制,反而表现得更加强硬。基于此,美国的务实派又对朝鲜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表示美国可以与朝鲜就签订和平协议等进行会谈,但前提是朝鲜必须重新回到六方会谈等等。2007年7月,朝鲜试射导弹之后,再次刺激了美国的敏感神经。美国强硬派的声音又一次在对朝政策上占到了上风。美国开始恢复自1999年克林顿政府时期解除的对朝制裁措施,开始集中强调朝鲜的人权问题和金融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攻击。
当然,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遭到了东方国家甚至也遭到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反对。后来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以及美国国内外政治环境的转换,布什在第二个任期内似乎在单边与多边之间寻求到了某种平衡,走了一条较为折中的道路。不管美国的对朝政策如何变换,但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即美国在全球推进民主、追求安全与霸权的根本宗旨并未改变。换句话来说,美国依然会不失时机地抛出各种理论,打出各种“民主”、“自由”以及“人权”的旗帜,来促使朝鲜等尚未实现民主与自由的东方国家实现所谓的“民主”与“自由”。如布什在第二期总统就职演说中着重陈述这样一种理念:美国今后将支持所有国家的民主运动及在那里建立民主制度,最终在世界上“结束暴政”。[7]这也就是说,美国对朝政策的有关转变没有根本改变美国的“东方主义”性格,美国在利用多边框架来规制朝鲜的同时,仍不时地来实现自己的单边主义利益。继布什之后的奥巴马政府,虽然在对朝鲜的政策上表现出了更多的弹性,将朝鲜从“支恐”的名单中删除,但是对朝鲜的敌视态度并没有根本改变。
总而言之,美国在对朝政策上始终表现出其浓重的东方主义文化特征。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优越感很强的国家,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国家,它对朝政策的宗旨就是要向其渗透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和制度,促其“和平演变”。正如诺姆·乔姆斯基在评论美国外交时所指出:“美国总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攻势,这种攻势是先树立一个幻想出来的恶魔,然后对他发动进攻,将它粉碎。”[8](P204)而朝鲜是坚持走“朝鲜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对美国“和平演变”的渗透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敌意。实际上,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对立与纠葛,并不简单是国与国之间的纷争,更多的是两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就未来发展走向来看,只要朝鲜坚持走“朝鲜式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美国就还会找各种理由和借口向朝鲜施压,即便是朝核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美国仍会利用所谓的人权问题、武器出口等问题继续向朝鲜施压。
三、美国对朝政策的文化意蕴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事实上,作为东方国家的中国也时常被美国基于“东方是野蛮的”这个东方主义的老调子而赋予了很多的负面性。例如,“中国威胁论”、“黄祸论”等论点的提出便是美国东方主义文化在对中国态度上的显著表现。在这样的文化前提下,中国被视为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相对立的东方。朝鲜与中国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东方国家,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美国对朝政策所蕴含的东方主义文化因素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
首先,应当适时地、适度地转换国家安全战略,以攻防相结合的战略取代应对性防御战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庸“和合”的文化,并不是“中国威胁论”者所谓的好战文化,加之囿于自身国力的有限,中国在对美关系上更多地表现出隐忍的那一面,在安全战略的选择上也往往是应对性防御战略。所谓应对性防御战略,是指国家无法控制或阻止即将发生的威胁,只能等到威胁到来之时去仓促的应对。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是基于东方主义的文化偏见大肆渲染中国发展的威胁性,不仅强调“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是个决心要获得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9](P421)而且以此为基点作以理论上的推演,敌视北京政权。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敌视并不是简单地指武装颠覆或者军事入侵,而更多的是通过政治、经济、外交以及文化手段来影响中国的意识形态,以此达到使中国认同西方民主观念、资本主义观念的目的,进而促使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有利于美方的变化。如同美国与朝鲜的关系一样,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并不简单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多时候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此而论,只要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美国敌视中国、演变中国的初衷就不会改变,只是在有些时候基于国家利益和战略考量,其敌视的程度和策略会有所不同而已。面对这样的处境,中国应该转变过去以应对性防御为主的国家安全战略,转而采取攻防相结合的国家安全战略,把防御与进攻辩证地结合起来,在防御中有进攻,攻防结合,交替运用。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的经济、文化等安全利益以及应对未来发展中的各种挑战。
其次,应当避免陷入“中国威胁论”的理论陷阱,革新国际关系思维和创新国际政治理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顾名思义,就是一套关于“中国构成威胁”的话语或者解读体系,是对中国未来走向的主观臆想和猜测。如我国著名学者时殷弘教授在其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美国将“美国利益真实或臆造的威胁想象为单一性的,或在本质上单一性的”。具体而言,这种想象中的单一性威胁起初是所谓的整体的“好斗的共产主义”,后来是“造就‘顽固好战’的中国以及北京为指挥中心的‘亚洲共产主义’”。[10]所以,“中国威胁论”实际上就是美国对中国的东方主义化的理解和肆意猜测,是美国强加于中国的“话语霸权”,“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威胁”之间并不能直接划等号。对中国学者来说,“中国威胁论”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否定中国构成威胁或者批驳美国对我们的污蔑,而不充分研究这个命题的真伪,势必会陷入“中国威胁论“的理论陷阱。由此,我们应当跳出关于“中国构不构成威胁”的争论,而提出“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顺应时代潮流的国际关系新思维来回应美国的有关污蔑。当前,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与世界一体化是难以阻挡的历史潮流,而东方主义的文化偏见在其中只是一股细微的逆流。我们要克服东方主义文化的消极影响,在创新国际政治理论的基础上,实现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平等化,促进人类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霸权威胁始终存在着,其外交政策仍会受到东方主义文化偏见的影响。美国不仅会千方百计制造出各种理由以及舆论来丑化中国、牵制中国,而且会不失时机地寻求各种机会来消耗中国的实力、消磨中国的意志。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就是极其典型的例子,即美国借用朝鲜核问题成功介入到东北亚地区的事务中来,对朝鲜及周边大国、尤其是对中国形成了战略压制。因此,中国应该致力于积极稳妥地处理好朝鲜问题,化解危机以抵消美国的战略压力。此外,中国要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世界各国一道反对霸权,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M]. Knopf Grouppress,1979.
[2] Stephen W. Twing. Myths, Models & U.S. foreign Policy: The Cultural Shaping of Three Cold Warrios[M].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1998.
[3] Michael H. Hunt. Ideologyand U.S. Foreign Policy[M].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
[4] 王辑思.美国霸权的逻辑[J].美国研究,2007(02).
[5] 储昭根.布什“单边主义”的文化传统[J].史学月刊,2007(11).
[6] 储昭根.单边主义是美国外交的一种传统[J].国际论坛, 2008(01).
[7] 张晓慧.新布什主义[J].国际资料信息,2005(05).
[8] 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9]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0] 时殷弘.与复杂局势相违的简单化政策[J].美国研究,1997(02).
编辑:李月明
D801
A
10.3969/j.issn.1003-4641.2014.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