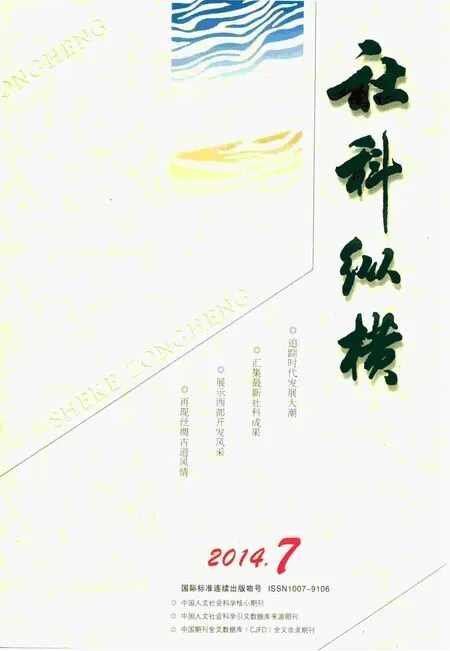唐才常的日本观
刘国习
(韩山师范学院思政部 广东 潮州 521041)
唐才常(1867-1900),字伯平,号佛尘,湖南浏阳人,清末著名政治活动家,与谭嗣同并称“浏阳二杰”。曾先后在岳麓书院和两湖书院肄业,自1897年起,参与湖南维新运动,先后担任《湘学报》主笔、时务学堂教习、南学会会友以及《湘报》总撰述,创办浏阳算学馆和群萌学会。维新失败后,辗转上海、香港、南洋、日本等地,接洽康有为、孙中山诸人,并联络两湖地区的哥老会组织。1900年,在武汉建立自立军,策划勤王起义,事泄被捕,英勇就义。纵观唐才常一生,其言论和行动中有诸多涉及日本之处,除了散见各处的涉日言论外,他注重研究中外史地,深入了解日本维新历史,有多篇涉日专题论文发表;在其策划自立军起义期间,也曾在日本开展活动。因为英年早逝,唐才常的日本观未能呈现较长时段的演变轨迹,但就戊戌维新时期中国人的日本观及中日关系的复杂面相而言,却具有较好的研究价值。
一、唐才常日本观的渊源
作为传统型知识分子,唐才常的学问之路始于科场,并取得很大成功,曾以小三元及第名闻三湘学界。但他终究能不为章句所束缚,在传统学问之外,更专著于经济实用之学,“尤娴于中西史乘”[1](P203)。他认为,除传统中国史学外,中国知识界尚无“通知泰西泰东各国治乱兴衰之由者”[2](P40),为此需加强东西各国历史的研究,“首宜揭古今各国政术异同,以知强弱存亡之本;次考立国源流,种类迁徙;次列帝王人物,中西比较;次明各教派别善否,知将来环球大地,不能越素王改制精心;次表各国合战机要,有关全局者;次详各国古时土番,与中国僮、黎、蛮、苗渐次消灭之理”,主张“合中西之古以为鉴”[2](P41)。此外,他还注意到“泰西不立史馆,盖报馆即其史馆也”[2](P41),提倡国人“广阅西报,以为通人之津”[2](P43)。正是在所谓“通人”的自我要求之下,唐才常在求学于岳麓书院和两湖书院时期,即注重收集和阅读有关日本的各种书籍报章,广泛涉猎日本历史尤其是日本近代维新时期的历史、人物以及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知识。他还在《湘学报》发表《日本宽永以来大事述叙》一文,指出“世罕知日本,罕知日本变法之难”[2](P97),向国内知识界提出要加强日本研究和介绍。可以说,唐才常早年虽不像黄遵宪等人那样直接游历和观察日本,但在中国内地知识分子中,唐才常对日本的了解是深入的,在其关于湖南维新时期的各种评论中,日本经验是最重要的镜鉴,并在各种场合不断被提及。
在唐才常的观察中,日本维新志士的卓厉敢死之气给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才常为此发表专文《论热力》,讨论中国士夫如何振刷精神,维新图强。他说:“若夫日本与我,国同洲,书同文;其痛疾外人连构奇殃,统绪垂绝,又与我同病。全恃二三侠士仁人,出死力,排众议,以成今日维新之治。”[2](P142)他列举日本开国之前的启蒙人物林子平、吉田矩方、高山彦九郎、蒲生君平、赖襄诸人以及维新志士木户孝允、岩仓具视、伊藤博文、井上馨、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万死一生、肝脑涂地的事迹,指出维新时期日本虽然也有新旧之争,但其两派“一则愤其国之不强而生横逆,一则求其国之必强而亡躯命,其致力殊而用心则一。故变法只三十年,而人才之贲溢,心力之勇猛,局势之雄奇,为五洲所仅见。”[2](P143)借此反观中国,唐才常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反差,“悲夫!悲夫!吾四百兆神州之遗民,轩辕之遗种,素忘之教徒,曾无一人剖心泣血,屠腹剐肠,痛陈不变之祸于君父之前者;又无一人痡手堵足,摩顶放踵,力任合群之责于士民之间者……然而谈科名则热,谋仕进则热,工钻营则热,逐锱铢蝇头之利则热,甚至昏夜乞怜,屏气匍匐则仍热;门户争歧,灭顶濡尾则仍热。”[2](P142)他明确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对待国家民族的淡漠情绪,“尤可异者,人而不知种教之危则已,乃既已知之,而仍太息痛恨于时势之无可为,而曰吾心实灰,弗能强焉,则太古之殭石,已陨之流星而已,直谓之非生人类可也。”[2](P142)但他认为,只要有热血之人能站出来进行鼓动,中国的消极民气是可以渐进扭转的,“如磨电机器然,不磨则不热,不热则电不生耳。”[2](P141)对唐才常而言,“热力”一词不仅是一种言论发明,也是其整个政治活动的动力源泉,“夫求新者既洞悉十九周以后之地球,必文明大启,又灼知孔教杀身成仁,佛氏大雄大无畏之旨,与夫意大里、奥斯马加、日本之变法,俱一二奇人侠士为之,遂毅然决然,舍身度世,以扞天下之危难,无所于涂。”[2](P165)正气会的建立以及自立军起义的发动正是这种信念的实现。
唐才常的各种舆论宣传与鼓动多以湖南知识分子为对象,其宣传工具主要包括《湘学报》、《湘报》,南学会和时务学堂则是其维新宣传的主要场所。他对湖南寄予厚望,希望湖南维新党人能效法日本萨摩维新志士,救湖南而救天下,他说:“今夫湖南于十八行省中,以守旧闻天下也,今乃遽然大觉,焕然改观……何前后之歧异至于如此?曰:昔之守旧也,非有他也,愤吾国之不强,而张脉偾兴也。今之求新也,亦非有他也,求吾国之必强,而赤诚相与忠爱缠绵也……惟有热力者,愈变愈新愈文明耳。故以吾湘,方之日本萨摩党,庶几近之,而尤愿其热力所充,直充至于救世同仁,以为文明太平之起点,则中国其庶几乎?”[2](P145)又说:“其有毅然舍身命、度众生者,伊何人也?其有坦然披肝胆、剖肺肠,而爱力缠绵者,伊何人也?吾遍索之幽幽九州而不得,乃还而求之吾湘……语战绩则曰湘军,语忠义则曰湘士,语以民权而参官权,则亦曰湘人。古所谓燕赵慷慨悲歌之地,今所谓日本萨摩坚忍悍劲之风,其庶几焉?”[2](P170)他的这种以湖南比喻日本萨摩的言论也得到其他湘省维新派人物的认同,如江标就说:“余尝至日本,见其人民聪秀,而性强悍,乡曲豪(士)举游侠之雄,遍于八洲三岛……夫其桀悍若此,以云变更,难乎难矣。然自迭遭挫辱以来,瞿然于闭关锁港之非,而一意开通,大修学制,为亚东雄国。吾之以日本望湘人士也,久矣,今其气象,庶几近之。”[2](P159-160)正因为有唐才常等人的热力宣传,湖南维新人物中较为普遍地产生了一种以湖南自比“小日本”的观念。正如谭嗣同所言,他与唐才常、熊希龄等湘籍志士“平日相互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3](P474),正是对这一情况的注解。
二、师日观
在唐才常的观察中,中日两国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其政其学甚至其教其种都源出一脉。在西力东渐的过程中,反应也基本相同。正如他所说:“善夫日本古贺侗菴,于其国未变法以前,痛陈攘夷之妄、锁国之失、夜郎自尊之谬,与专言兰学而萎靡颓丧之非,颜其书曰《海防臆测》,以扞当世之文网而不恤。吾党治史学者,诚取而证中国海禁既开情事,有不哑然自笑其自尊自局自沮之不谋而合者哉!”[2](P97)唐才常强调,“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因为日本“能师中国以并师泰西,故变法只三十年,而修慧修福,遂积成阿僧只无量之功力,为亚东雄国。”[2](P97)故中国同样应学习日本经验,变法求强,“如再不变法,亦万无复存之理”[2](P229)。在唐才常所论及的诸多维新话题中,诸如工务、商务、交涉、军事、政治、法律等方面,他都注重借鉴日本经验。
工务方面,唐才常主张设立赛工艺会,并拟定赛工艺会条例;同时主张自造各种机器以遏洋货利权。他记叙日本在此方面的情况说,“近日日本又步武西人,二十余年,称雄亚东。”[2](P39)他引用英国报纸对日本的评价,称其在学习西方工艺方面“乖巧疾速”,“且将以十万人,跳刀拍张于大海中”[2](P39)。对于日本在工艺方面全面学习西方的迅猛势头,唐才常深以为然,他提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安见中国之心思才力,远出西人下耶?”[2](P39)针对西方国家在日本的工艺专利垄断,他表现了强烈的危机感,他说,“况今日本已有遍地设机器之条款,而西人动以利益均沾为词,则将来遍中国皆外洋机器,不十年间,无可措手矣。”[2](P39)
商务方面,唐才常在《历代商政与欧洲各国同异考》一文指出,自唐虞三代至秦汉,中国人重视士农工商,四民平等。但自暴秦变法,“商政无一存焉”,而西人则“雅重商民,多方扶持”,以至“上下一心,竭精殚虑,强甲五州”,“日本起而效之,遂骎骎不可制。”[2](P3)同时日本也重视在通商过程中维护其经济自主权,“惟通商只许在海口而不许入国,阴柔有谋,视西人为更挚”,反观中国,则“但有各国商埠,而无立埠他国之利,漏厄所出,尾闾不足壅其流。”[2](P6)所以唐才常主张中国应当实力研求近代商政,而在向西方学习商政方面,日本的成功经验是可资参考的。
对外交涉方面,唐才常主张国家重臣应当亲赴海外,了解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具体情势。他说:“若夫亲王大臣,出洋学习俄、日,以建维新之治,尤为今日策时之第一义。”[2](P29)又说:“西国百年来,以交涉名家者,若意之加孚尔、普之毕士马…日本之伊藤博文,之数君者,先皆游列国,或充公使,或入学堂,一旦身登机府,各国情状,瞭如数掌纹,索米盐室中。”他反观中国在此方面的不足之处,“中国居机府者,鲜身历重瀛之人”[2](P106-107)。唐才常注意到近代外交中的实力因素,也深知西方列强炮舰外交的实质,他借鉴古贺侗菴的观点:“近代泰西吞噬邻邦,大都以兵不以教”,并称其为真知灼见。他也重视交涉学的作用:“今之君子,与其鸣孤愤,奋空拳,贻君父羞,何如请求交涉应付之宜,折冲樽俎,使君父享无穷之益也?”[2](P44-45)他主张抛弃闭关自守的外交政策,与西方列强展开实用主义外交。他在《外交论》一文中说:“中国通亦通,不通亦通,与其通于人而塞自主之权,何如通于己而扩小民之利。”[2](P49)在此问题上,他也提到日本的经验:“昔日本未变法之前,亦建议锁国者也,逮为荷兰学者极力通之,以有今日。然近律法更而约章改,利权横溢于五洲,外船绝迹于港汊,则是通塞塞通也”[2](P49)。他广泛阅读中西各报纸,深入了解日本外交的大局和细节。如日美关系,他指出美国在甲午战争期间对日本所持的偏袒立场,“中日之役,不闻弥兵会之言,且贷款于日,以资之战”[2](P72);但他也能注意到美日两国的猜忌实情,“美人思合檀香山为一国,原出檀岛太后之意,而日报毒诋,至无完肤。”[2](P120)他还注意到日本与泰国的双边关系,指出两国从前政俗悬殊,但都力图变法,且两国王公大臣相互交游,故能“联袂牵裳,相视莫逆”。[2](P116)他也指出甲午战后日本外交面临的国际压力,“于法则法诟之,于波斯则波斯疑之,其尤眦賧相向者,莫如俄人。”[2](P73)具有启发性的是,他能注意到中日战争期间日方对中方发动的舆论战,“前年日人无礼于我,普天同愤,然乃先以中国不直之说,饶舌五洲,至英德诸国,周章观望,欲鹬蚌两国而收其利,甚至有调人出,而德先梗议,日人益毫无忌惮,以肆其阴谋。”[2](P117)①
军事方面,《湘学报》4-6号刊载唐才常《兵学余谈》的长文,借鉴各国经验,从选将、选兵、海军、陆军四方面论述军事改革问题。他介绍德日两国军事近代化历程,指出两国在走向军事强国道路之初所处的困境,但两国终于以弱变强,“德之制于法也,养兵无许逾七百,更番训练,以复法仇。日本之见逼三国也,危如累卵,痛改兵制,卒雄亚东。”[2](P55)他提出其“寓武事于四民教养之中”的军事改革思想,尤其详细考察日本陆海军经营过程与军制改革历程,并指明:“日与我近,又参酌西法,已著有成效,故详称之,以资考镜”。[2](P49)他提出,无论王公大臣,贵戚子弟,均须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天皇)睦仁之弟,与其太子,与兵民齿。大臣若山县有朋、嗄本武扬诸人,皆昔在欧洲充黑衣之职者。”同时,统兵大员须接受正规军事教育并亲赴国外留学,学习近代军事理论,“(日军)统兵大员,无不由学校出身,学既成又航海至泰西,隶名军籍,如是一二十年,然后回国,予以大将之任。”[2](P58)他就此对中国公卿世爵之家提出批评:“中国重文轻武,往往小视海军将牟,故世禄之家,不喜入军籍,此实三十年办理海军之病源”。[2](P58)在海军军制方面,他借鉴日本海军经验,批评清朝海军分立三军的做法,提出:“今再立海军,当有一知兵大臣总理南北粤闽海权,毋受各督抚牵制。”[2](P65)他还借鉴日本海军战胜中国海军的经验,“中国铁舰,虽大于日本,而行驶不及日本。日本吉野舰所发快炮,络绎不绝,定远、镇远两舰,仅发一炮,而吉野之炮已约有四十弹”,提出“舰不必取其大,以便利为要;炮不必震其名,以灵活为要。”[2](P64)在建立近代军事抚恤制度方面,他首先介绍西方国家的相关制度,“凡役兵十余年以老归者,给饷终身;死王事者,官为给其父母妻子。”随后,他进一步介绍日本在此方面仿效西方国家的做法:“日本近亦仿行此例。凡战殁者由官给其家,月非银十两,子女由官养,至十六岁止。”最后,他指出中国军事抚恤制度的现状,“中国无给饷归田之例,其战殁虽间有恤银,然往往无从领取。”[2](P56)
政治方面,唐才常发表长文《各国政教公理总论》,介绍并比较西方各国的国会制度。他指出欧美各国遍设国会,“无国不会,无会不国”,而实施情况则各有分别,就国会权力而言,“以法意奥为至悍,以德日为至劲,英美瑞士为至纯”[2](P87)。他尤其关注日本政党与国会制度的运作情况,他说:“日本维新以来,会党林立,而国日强。其迟之又久,始设立国会,尤得西法之精。”[2](P87)虽然日本政党与国会制度在具体运作中,也出现各种党派纷争的情况,但其与“专为身家执法营私者,不可道里计。”[2](P87)此外,他还着重介绍日本的近代君主立宪制度,他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历史说,“日本大权旁落,民思其君,藩幕篡政千余年,而不克窃其位;及尊攘议起,大将军徒步就邸,无敢异言,非民气固结之效乎?自兹而后,去浮谈,求实学,开设元老院,比于欧洲。”[2](P94)他就此评论道:“夫国者非一人之国,君者非一人之君。吾能使吾君公权于国,公国于天,赫然如俄之大彼得,日本之睦仁,尽变祖宗之成法,与天下更始,则吾虽犯天下之不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所忻慕焉”[2](P164-165)。唐才常的多数政治活动都是围绕上述目标展开,其参与南学会、保卫局运作以及其领导自立军起义的各种活动,皆是如此。
法律方面,唐才常注重向国人介绍日本改订条约的历史。唐才常指出,日本在明治初年的情况同中国如出一辙,其关税以及司法皆尽丧失自主之权。其维新志士如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诸人为此不懈努力,多年以来,不断遣使于欧美诸国,商讨更订约章。自1896年起,“各大国终与更约,视平等例”[2](P157)。他就此对中国的相关情况提出深刻批评,指出中国在教务、商务、军务、税务、界务各个方面受制于人,“处处有违公法者,难缕指述。”[2](P36)他将其归因于公法知识的缺乏,“无深谙公法之人,据理与争。”[2](P27)他主张中国应当借重公法与列强交涉,他说:“日本维新以来,于大学中设立文科,使诸生研求律例,一经考录,充作律师,榜其门曰代言事务人。由是遇与西人交涉案件,每能援东西律例,断断与之争辩,故近来美国与日本订约,许复其自主之权。”[2](P46)他为此创立公法学会,并提倡赴日留学。
三、联日观
甲午战败,唐才常在上欧阳中鹄书中引用薛福成的话评价日本“阴而有谋,固属可虑,其穷而无赖,则更可忧”[2](P227),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日本的警惕。但和中国知识界多数人一样,唐才常仍然未能祛除传统中国人对日本的轻视态度,习惯性地称日本为“倭”;也仍然不能直面战败,对马关条约的认识似乎也还停留在传统中国人的“抚”与“和”的概念上。受此影响,他未能认真对待日本民族性中的某些危险倾向和特征。对他来说,虽刚经历对日战争的失败,日本也只是与英俄法德一起并列的列强之一,并不需特别对待。他对战后寻仇日本的议论,颇为不以为然。他认为中日两国的对峙,即如“两盲相遇,而仇道不休”[2](P49),“吾见排解者之援以为功,而所丧滋多矣”[2](P49),显然这是对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的批评。
他具备广阔的世界视野,习惯于将中、日、俄三国关系放在宏大的时空坐标中进行比较研究,使得他对中日战后关系的评价超越了简单仇日的见解。他研究俄国历史,尤其注重研究俄国在东西两面的扩张史,指出:“今夫俄之蓄而谋亚欧也,自其彼得大帝临终之言,已犼狂狮吼淆乱天下也……其阴谋狡毒,券我支那者,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俄而东三省铁路归其掌握也,俄而一纸索大连湾、旅顺,扰乱全球矣……方日本如入高,亟欲改纪其政,使图富强,而俄使威喇君则阴搆其背日而仍旧……故其欲波兰、高丽我也,驾轻就熟……又闻俄之亡人国也,曰杀人愈多者,服之愈久”[2](P150)。从这种宏观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待甲午战后的中日俄三国关系,他认为日本的扩张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都不比俄国的威胁更严重。因此,他选择提出了联日联英以拒俄的主张,他说:“英属地遍五洲,商埠环瀛海,举事一不当,则鞭长莫及,全局瓦解,故持盈保泰其本心……日本席新胜之威,而购船置械,如穷人入市,惶惶贳米贳刀,惟敌德则有余,敌俄则不足。牛瘠偾豚,唇亡齿寒,谥曰至愚,尚犹知之,况乃聪明洞瞩如日人者乎?”[2](P153)他主张中国知识界讲求实学,向日本学习近代农、工、商、矿务,兴办近代交通,积极整军御侮,“以通学者通日,通日者通英,合中日英之力,纵横海上,强俄虽狡,必不敢遽肆其冬封之志。”[2](P153)
当然,唐才常对中日俄三国关系的这种认识,除了在反专制、求维新方面与英日有相通之处外,一定程度上也同日本的拉拢分不开。因为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日本政学两界极为震动,有人承认“辽东半岛归还一事,几乎支配了我一生的命运”[4](P52);加之对李鸿章访俄和中俄密约的猜疑,抵御俄国的威胁成为日本比瓜分掠夺中国更为紧迫的战略任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方面主动采取措施,缓和中日关系,拉拢中国国内的维新志士。正如唐才常在南学会演讲中透露的那样,1897年初,日本派遣参谋部神尾光臣等三人来华进行秘密联络活动,在汉口和谭嗣同进行交谈。日本参谋部人员颇能掌握中国知识界的地域文化心理以及省界路界之分,提出:“侧闻湘省风气大开,钻研政学,无任钦迟,尤愿纳交,相为指臂。且振兴中国,当于湖南起点”。这种联络沟通工作立即取得效果,唐才常公开承认,“日人既愿联盟我,且愿秘联中英相犄角,且愿性命死生相扶持,千载一遇,何幸如之,何快如之!”[2](P151)在《论兴亚议会》一文中,他提出了湖南与日本加强合作的十条建议。当然,唐才常也主张以日联英的同时,还须与其展开商战。只是他认为,商战之祸不及兵战之祸,“联俄则燃眉噬脐,旦夕即成异类;联日以联英,则皮肤之癣,犹可补救于将来。”[2](P153)他进而指出,“不此之务,而以四万万人之身家性命,委之蓄诈行贿、贪饞狡虐、权压兵勒之无道俄,而欲延残喘于须臾,乞余生于虎口。此三尺之童,所惊疑诫愕,而志士仁人之抚膺顿足,悲不自胜者也。”[2](P153)作为联日论的重要补充,他强烈主张中国青年学子赴日留学,“学通而政通,政通而国通”[2](P153)。他强调这是甲午战后中国国际战略的关键,并多方宣传其主张。
维新失败后,唐才常继续奔走各地,联络同志。日本则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维新派的争取工作,“东人之奔走喘汗,乃心中国者,不下百十人”。[2](P183)日方举动对国内的维新派产生重大影响,唐才常在送别日人安阳藤州时即称:“嗟夫阳州,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吾之于二三子游,非独不知有国界,即形骸之界且忘之矣。异日亚东有事,吾知息壤之盟,辅车之助,必有践言于存亡呼吸之间者,阳州其人哉!阳州其人哉!”[2](P184)在开展自立军运动的过程中,唐才常也积极争取日本方面的支持。他将时务学堂多名学生送到日本留学,向其宣传民主维新的理论,培养了一批自立军运动的基本干部。唐才常也亲赴日本,联络康有为孙中山等人,并与日本政界人物如犬养毅等沟通交流,争取各方力量支持,扩大自立军运动的力量基础。在国内,唐才常积极争取日本人士加入自立军运动,自立会《会章》规定“日本志士愿入本会者,一律列名会籍”,一些日本人士如甲斐靖、田野桔茨等人在自立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作为日本进步党领袖的犬养毅曾亲自致电张之洞,“求其保全,以睦邻德”。[5](P199)由此可见,就中国维新派而言,中日联盟已经不仅停留在言论层面,而是有了实质性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百日维新失败后,唐才常等维新志士处境艰难,对日本方面的示好之举产生强烈认同,在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上,也呈现出重大偏误。在《日人实心保华论》一文中,唐才常称:“甲午以来,时局益棘,西力东渐,势甚燎原,自非至愚极闇,懵于中外情形者,靡不以亟联日支为词”[2](P192);甚至称:“若大日本志士所欲饷遗于中国者,则专以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为汲汲,而又于中国二千余年之教宗,毫无窒碍,舍末图本,弃短取长,斯乃天所以成将来二国合邦之局,而杜欧势东渐之关折也。”[2](P193)②对明朝抗倭,他则认为“不过野蛮争斗之为”③;对于甲午战争,则“适以启亚东文明之渐”,甚至称:“诡激之子,观于变法之难,至有诟日本甲午之役,不直捣京师,荡除瑕秽,以成中国南迁之局”[2](P185)。这种偏激言论说明唐才常此一时刻的孤立孱弱的心态,似乎正好说明他自己也是惧于变法之难的“诡激之子”了。
四、几点评价
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历程中,甲午战争是一个转折点。战前,中国在某些具体器物上向西方学习,但整体制度和知识体系仍沿袭传统。战后,特别到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时期,中国社会终于开始了知识、制度与文化体系的近代转型。④由此出发,观察此一时期的中国知识界,会发现他们身上承载了这种古与今、中与外、东与西的转折点上的诸多印记。就唐才常的日本观而言,首先,是中国传统国际观的深刻烙印。在对日本的称呼上,“倭”“寇”“小”等话语仍经常使用,特别是在论及日本对中国的诸多恶举时更是如此。这种千年以来形成的传统话语体系妨碍了中国人对日本的正常认识,成为中国人在认识日本时的一种难以跨越的障碍。⑤其次,在唐才常的话语中,中性的“日本”、“日本国”等称呼也在逐渐使用,这也表明知识分子终于开始摆脱传统封贡体制(费正清语)下自我中心论的国际关系认知,开始强化中日关系上的中与外的差别。在日本观问题上,战胜国、强国、与外国的认识三者合一,催生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民族自强成为时代主旋律。受此影响,战败带来两种情绪与认知,一是憎恶感,日本通过卑劣的战争手段剥夺了中国的土地、人民、财产,更重要的还有尊严;一是危机感,即中国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上述认知的推动之下,中国知识精英认识到我们必须像日本学习,“以强敌为师资”(康有为语)成为这一时期国人的共识。甚至随着中国留日青年的不断增加,日本对中国的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西方,引入中国的新知识甚至被指“名为西学,实倭学也”[6](P23)。再次是唐才常的日本观还受到东西观念的影响,即中日同文同种,近代以来的国情遭遇也相同,在白种西方文化的强势威胁前,中国人对日本又有强烈的认同感。这就造成了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的某种复杂情况,日本也正是在此问题上找到可资利用的空间,在甲午战后中日关系的大格局中展开某种类似于春秋合纵之术的外交攻势。最典型的是,在日本刚刚战胜并大肆掠夺中国的情况下,却到中国的决策圈和知识界开展游说,话语之中颇多中日两国本为兄弟之国,应当共同兴亚以及对甲午战争深为愧悔的言论,最典型的当属唐才常引日本参谋本部神尾光臣等三人面见谭嗣同所讲的一段话:“彼我本兄弟国,贵国遇我良厚,不意朝鲜一役,遂成仇釁。又不意贵国竟不能一战,挫衄不可收拾。嗣兹以来,启各国心,危若朝露,每一回首,悔恨何及。然贵国亡必及我,我不联贵国,将谁联?”[2](P151)并且唐才常是在南学会的演讲中面对湖南的知识精英公开转述上述谈话的,却未见有人特别针对日方这种言不由衷的合纵之词进行批判,足见东西之别在时人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唐才常的日本观时必须要注意到的一个重大背景。⑥
当然,今人评价唐才常的日本观时另外一个背景更不能忽视,即其对日本的所有评价实际上不是一种简单的日本观,更大程度上却是一种中国文化反思。一方面,他对日本与西方的文化体系作出近乎完美的评价,实际上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批判,这也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做法。许多知日派如薛福成、黄遵宪、梁启超等也熟知日本社会的诸多弊端,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还没有产生诸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类的文化批判运动,传统文化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他们有意识地回避日本的负面形象,其目的也是借助战胜国日本的心理高位优势文化来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另一方面,在所有舆论批评的矛头都指向满清王朝的情况下,日本对中国的伤害似乎得到了选择性遗忘。这种情况在唐才常挚友谭嗣同身上尤其明显。马关之约成,谭嗣同在上欧阳中鹄书中全面道出其心路历程。他说:“睹和议条款,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大为爽然自失。”他谴责马关条约为“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7](P155),并揭露“倭之蓄谋,当在二十年前,储峙钱粟,缮治甲兵,久为外人侧目”。[7](P222)但对清政府的极度失望情绪淹没了其对日本的痛恨,他列举中国官吏“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以及西人所谓“秽、贿、讳”之种种怪现状,说:“君以民为天,民心之涣散,天心之去留也。”他还神秘地说:“往年威海冰膠,不能进船。去冬严寒胜往年,而倭进攻时,独不合冻。倭固万无蒙天佑之理,而以我之所为,又岂能望有偏佑哉!”[7](P155)他甚至提到:“民间有号泣留倭者,且言倭一去,则官又来虐我矣。从而迁者数百户,无告之民,其惨痛乃尔乎?亦将何词以责之?”[7](P155)故当听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藉免华官妄辱冤杀”时,他致信汪康年了解情况,表示“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我辈皆可免被人横诬为会匪而冤杀之矣”。[3](P492-493)所谓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谭嗣同、唐才常对自辱之清政府的痛恨远远超过其对辱人之日本的痛恨,恨日本更“恨中国”。这似乎也成为一种未经宣示的普泛情感。⑦只是对于唐才常而言,他对日本的膜拜到底是属于一种文化自卑还是一种基于中国文化批判的工具理性亦或是二者的某种结合,需要进一步分析。以谭、唐二人人格特征而言,谭嗣同是属于张扬豪放的,唐才常则属沉稳有谋。如果说谭嗣同的对日膜拜有二种情绪综合的可能,那么,对唐才常而言,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基于中国文化批判的有意识的工具性的价值选择。举例来说,唐才常将其书房自名为“觉癫冥斋”,依照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命名习惯,实际上正是其保持理性的一种表现。又如,在白种人与黄种人通婚的问题上,唐才常进行严肃学术研究并认可通婚的人种改良作用的。但因为该问题过于敏感,他并未在公开场所宣传该问题,只是进行一些比较私密的讨论,其刊登于《湘学报》的相关论文也只有《各国种类考》一篇,内容也是相对中性的。更重要的是,百日维新失败,挚友谭嗣同牺牲之后,唐才常忍痛继续秘密运动,与康有为、孙中山、南洋与日本同情革命诸友人以及两湖会党甚至湖广总督张之洞相联络,最终组织起规模达十多万人的自立军队伍,足以推断唐才常的理性思考与运作的能力。
一般认为,在甲午战后约二十年时间内,中国知识界在对日态度上和一般战败国的反应大为不同,在本应仇视日本的战败情形下,却产生了联日甚至亲日论。但就唐才常而言,我们须注意到与这种“另一种面相”不同的另一种面相,即对日本的批判。这种批判集中体现在他在1896年就中日通商条约所做的批评中。他认为,中日同文同种,近代以来又经历同样遭遇,但日本在中日关税税则问题上却“一则曰现行之税则,再则曰现行之税则”,“不为我中国延一线生机”,“语于不仁之者甚者也”。对于日俄在东亚的交涉,他尖锐指出日本外交的卑怯:“旧者之岁,闻有创兴亚会者,与俄人兴东会遥遥相峙,西人固已目笑存之。未几,瞰俄铁路未成,乘乱朝鲜,破吾空气球而裂之,栩栩鸣于各国曰:吾为天下雄,于是兴亚转成亡亚之祸。欲割辽东,则俄阻之;欲改朝鲜政法,则俄煽之,而彼终亦蒙面吞声,莫之与抗。”他揭露中日条约的不平等的实质:“凡日本人在中国所沾之利益,一则曰照最优之国,再则曰照最优之国,而中国人在日本利益几何,约中均未载明。”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他仍然不能超越所谓的东西之辩,“脱竟瘠我中国而亡之,日本又能孓然国于太平洋中耶?”他对日本的幻想仍然是相当强烈而具体的,“则岂若于战胜中国时,布告全球,仿柏林、维也纳会议之例,公订条约,俾朝鲜为万国公保之国,并退还辽东,寡索兵费,与中国酌改交涉之律例税则,为万国倡,且力以广学堂、改科目、兴制造、重农商,恳切敦劝,则吾四万万人感之不暇,何暇仇之,行见义声所倡,吾国奉为师资。俄德消其狡计,而密约之谣,瓜分之议,乌自来矣。不特此也,凡国于亚洲,若暹罗,若朝鲜,若南洋群岛,稍有自立之机者,即以公法平权之议,与之交涉,且开通其政学,为兴亚资,岂不廓然大公也哉!”[2](P129-134)这种亲近日本、抨击日本与对日幻想相互纠结的情况,也是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日本观问题上的一种普遍现象。
注释:
①这种输掉战争,同时输掉国际同情的情况值得今天的中日关系研究者和决策者重视。
②这种“大日本志士”的称呼以及“二国合邦”的言论相当危险,似乎已经是某种早期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论调了,足见日本参谋本部各种政治争取工作在中国维新知识界产生的重大影响。
③薛福成甚至评论明朝抗倭斗争为“有明中叶,内政不修,奸民冒倭人旗帜,群起为寇”。
④此处受到中山大学桑兵教授和关晓红教授的启发。
⑤日本利用中国人的这种落后的国际观做文章,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舆论与外交工作中赢得了支持。如何对待日本的弱国牌和悲情牌,这也是我们在处理与中日关系相关的舆论问题时须斟酌的问题。
⑥这种情况类似于毛泽东时代,基于其三个世界论的基本判断,中国对日外交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当时一般中国人的认知与觉悟水平。
⑦就其目的而言,并无太多非常之处;就其方法而言,则颇为值得商榷。由此足见中日关系问题的敏感,极易由外交问题转化为内政问题。
[1]杜迈之,刘泱泱,李如龙.自立会史料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3.
[2]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德富苏峰.苏峰自传[M].昭和十年版,第310页,转引自郑匡民.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5]宋梧刚,潘信之.唐才常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6]王代功.清王湘绮先生闓运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7]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