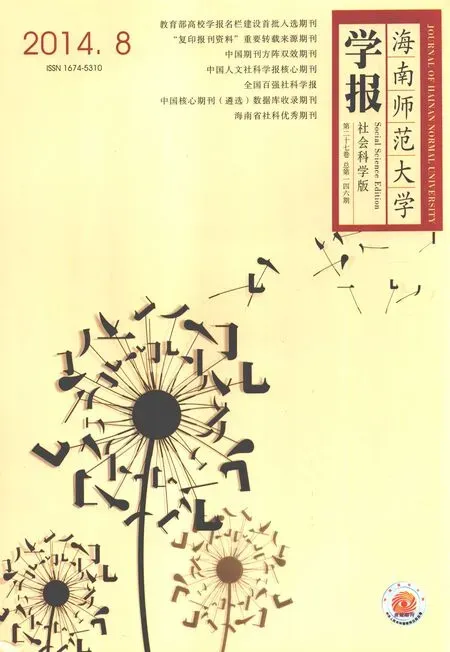庞大的躯体,隐形的主体
——《神谕女士》的肥胖隐喻及叙事策略
张 雯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311121)
庞大的躯体,隐形的主体
——《神谕女士》的肥胖隐喻及叙事策略
张 雯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311121)
肥胖是阿特伍德的长篇小说《神谕女士》的中心意象,女主人公琼先胖后瘦的过程是小说的叙事主线与焦点。事实上,琼的“增肥”与“减肥”两种行为的背后都隐含了心理与文化层面的寓意:“增肥”的实质是出于自我身份的危机感而来增加存在感;“减肥”则是西方主流审美观主导下的“自我消灭”。而琼成功减肥以后依然无法摆脱的“胖女人” 幽灵,其实是她另一个自我的化身。这是阿特伍德“双胞胎”主题的又一次体现。
阿特伍德;《神谕女士》;肥胖;身份危机;双胞胎主题
《神谕女士》(LadyOracle)是加拿大当代最有成就的女作家之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追述了女主人公琼的人生经历。琼天生体形肥胖,因而失爱于严厉的母亲。她成年以后成功减肥并与马克思主义者亚瑟结婚。婚后的琼同时保持着诸多不同的身份:亚瑟的妻子、不善家务的家庭主妇;神秘的哥特小说写手;行为艺术家“皇家刺猬”的情妇以及畅销书《神谕女士》①小说中女主人公琼所创作的诗集名也是《神谕女士》。的作者。最后,当琼的多重身份面临被揭穿的危险时,她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假溺水身亡事件而脱身,从多伦多逃到了意大利。
《神谕女士》台湾译本的导读撰写者伍轩宏把这部小说总结为:“这是个胖女孩变身的故事。”[1]的确,肥胖是贯穿小说自始至终的主题意象。那么,《神谕女士》中的肥胖意象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呢?琼的减肥行为有什么样的隐喻?她又为什么始终无法摆脱“胖女人”的阴影?本文将结合琼由胖而瘦的过程来分别解读“增肥”与“减肥”的背后所隐含的精神分析学和身份问题以及“胖女人”的隐喻。
一 增肥:身份危机中的自我养育
《神谕女士》的女主人公琼是一个异常肥胖的女性。对于她的躯体,琼自己是这样描述的:“我通常不通过镜子或其它的方式看自己的身躯;我只是经常偷眼看身体的某个部位,但全身的模样实在令人震撼。在那里大剌剌瞪视我的,是我的大腿。它巨大无比,臃肿、像病肢,像丛林原住民照片上的大腿。它无止境地延伸,像从飞机上拍摄的草原照片,腿肉不绿,青青白白,静脉蜿蜿蜒埏其间如河流。它的尺寸相当于三条正常大腿。”[2]117琼的肥胖是她少年时代与自己的母亲抗争的结果。她把吃当成对母亲的反抗:“我与母亲之间的战争开始白热化,争议的领地是我的身体。”[2]65-66当母亲采用各种方法诱逼琼减肥时,她的反应是“再多吃一样玛氏巧克力,或来双份炸薯条。”[2]66琼将自己“领地”的扩张看成是对母亲的胜利:“在餐桌上,我的身体一寸寸向她逼近,至少我在这方面所向无敌”[2]66。最终,琼以自己245磅的体重宣告了这场母女之战的胜利。
根据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的观点,母亲经常会倾向于把自己的女儿当成自己的延伸物,试图把女儿塑造成与自己一样的人。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南茜·丘得罗(Nancy Chodorow)在她的代表作《母性的繁殖》(TheReproductionofMothering)一书里说:“早期母女关系比母子关系更容易发生他们所描述的这种融合、投射与自恋的延伸以及拒绝分离这些模式……母亲没有意识到或否认女儿做为一个独立的的人存在。”[3]在丘得罗看来,母亲极易把女儿当成自我形象的投射,使女儿成为她自恋的延伸和自我的镜像。这种母女关系在《神谕女士》中得到了印证:琼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西方中产阶级主妇,优雅、美丽、苗条、井然有序;她不遗余力地试图将琼变成和她一样的人,让琼观看她化妆,给她买漂亮的衣服,最重要的是,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她减肥。
与此相对应的,阿特伍德笔下的女性都普遍地患有“惧母症”(matrophobia),即害怕成为与自己母亲一样的人,比如《人类以前的生活》(LifeBeforeMan)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肉体伤害》(BodilyHarm)中的雷妮和《强盗新娘》(TheRobberBride)中的三个女主人公托尼、查丽丝和洛兹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为对母亲的反感、反抗与逃离,琼是这一系列“惧母症”女性形象的先驱。她处处与母亲为敌,甚至把让母亲哭泣当成乐事。而琼最为典型的“惧母症”表现是努力让自己向着与母亲相反的方向发展:肥胖、粗俗、丑陋、不修边幅。她说:“我绝不会让她把我变成她的样子:瘦而美丽。”[2]78琼一方面认为母亲试图同化她的行为是“自恋和本质上自私的”[4],另一方面,她不愿意作母亲的延伸或者替代物,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肥胖来证明自己是与母亲完全不一样的人,换言之,是为了获得自己存在的独立性。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琼的内心深处其实潜藏着十分严重的生存危机感。这要从琼的出身说起。琼是所谓的战争婴儿,即在二战期间因特殊的历史环境而出生的婴儿。在阿特伍德的人物画廊里,战争婴儿除了琼,还有《强盗新娘》的三个女主人公。战争婴儿不可避免地都有自我身份危机。因为她们的出身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就像琼的母亲说琼的出身是一个“意外”。她们知道自己其实并不是自己父母本来就打算要的孩子,如果不是刚好遇上了人类社会的特殊状态——战争,她们就不可能出生。同样由于战争的原因,战争婴儿的父亲们都是在外打仗,有的甚至永远不能回来了。一个冷酷的母亲和一个不在场的父亲,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战争婴儿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质疑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进而产生身份危机。正如《胖小姐之舞:阿特伍德的〈神谕女士〉》(TheFatLadyDances:MargaretAtwood’sLadyOracle)的作者玛格丽·费(Margery Fee)所说的“阿特伍德的女主人们普遍地被身份危机所困扰”[5]。
出于对自身存在不确定性的恐慌感,琼疯狂地进食:“吃也是因为惊慌。有时候我很害怕我不是真实的存在,我只是个意外;……我是不是想变成坚固的实体,一个像石头的实体,好让她无法摆脱我?”[2]74她试图以自己庞大的躯体向企图抹杀她存在合法性的母亲宣告自己是“有形”、“可见”的,是实实在在、无可否认的“存在”。再进一步讲,与其说琼是为了向母亲证明自己的存在,不如说她其实是试图说服自己的不安感,以对抗内心深处的身份危机。
琼的名字很值得玩味,她的姓氏是“福斯特”,英文原文是“Foster”,这个词是“养育”的意思。而琼给自己增肥可以看成是一种另类的“生长”,那么这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自我养育”。这种自我养育似乎在表明这样一种理念:既然母亲不愿意生育她,她就自己“生育”自己;既然母亲是迫不得已才成为她的母亲,她就自己充当自己的“母亲”。于是,琼以她一贯的假想的方式解构了与母亲之间生产者与被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她自己充当自己的母亲。琼以这种自我增肥的“刻意性”来对抗自己出身的“偶然性”和“随意性”。
再来看“琼”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母亲根据一个电影明星琼·克劳馥给她命名,这让她怀疑:“母亲赋予我别人名字,是要我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名字吗?”[2]38名字是身份的象征,母亲没有给她一个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名字,从某种意义来说是没有给她一个真正的身份。也正因为此,她不断地给自己创造以新名字命名的新身份。在现实世界中,琼既是一个笨拙而本分的家庭主妇,同时也是另一个男人的秘密情妇。私底下,琼又是创作通俗哥特小说的露薏莎·K·德拉寇。而在另一个世界中,她又以高雅诗歌《神谕女士》的作者的身份出现。如果说给自己“减肥”是为了突显体形上的自我,那么编造各种身份是在社会价值观的层面为自己创设多重自我。琼给自己创造了诸多的身份,其实是想证明自我的存在。简言之,正是因为对自己身份的不确定,她才会不断地给自己制造身份。
这样说来,琼在减肥以后为自己创设的多重身份其实是她已并不存在的肥胖身躯的替代品。内心深处的身份危机促使她不断地使用各种方式进行“自我养育”或“自我生产”。琼让自己的身体无限制地生长和不断地给自己建造新身份这两种行为,都是源于内心深处最初的那种自我身份危机。琼为自己增肥的深层目的是为了突显自身的存在,而为自己制造多重不同的身份是一种减肥以后对自己的补偿心理。所以说,不管是自我增肥还是自我建构自份,实质上都是一种“自我养育”行为,其深层原因都是琼对自己身份的危机感。
二 减肥:主流审美意识下的自我摧毁
如果说“增肥”的实质是琼出于内心深处的身份危机而“增加”自己的存在感,那么,“减肥”又具有什么心理与文化上的寓意呢?琼少年时代的肥胖使她成为与母亲的战争中的胜利者,可是也让她成年以后在男女交往中屡屡受挫:在巨大的肉体中,她没有年龄也没有性别。胖子似乎超越了年龄的变化,“所有的胖女人都是42岁”,同时也是独立于男人和女人之外的第三种人。他们被认为是没有性欲的人:“尽管浑身是肉,但超脱了肉体的欲望。”[2]91琼作为年青女性的魅力和吸引力完全被她的肥胖淹没:“体积庞大,却几乎隐形。”超重的她既不会被同性嫉妒,也没有来自异性的青睐和骚扰。“肥胖是一种绝缘体”[2]139,肥胖掩盖了琼的女性体征,导致她像小说多次提到的关在塔楼里的拉普索(Rapunzel)*即《格林童话》中的“长发姑娘”。一样,被禁闭一个封闭的世界里而失去了与英俊王子浪漫相遇的机会。也就是说,颇具反讽意味的,在当代“以瘦为美”的主流审美意识主导下的欧美社会,琼的肉身不但没有体现出,反而是淹没了她的主体性。她本寄希望强调自己身份的肥胖,反而使她丧失了身份。
直到琼成功减肥以后,女性的生理特征才显现出来,这时她才从“第三种人”变成女人:“以前我是局外人,备受限制;如今我是普通人。”[2]142琼这一胖一瘦的过程折射了阿特伍德本人对社会观念给予女性身体的精神暴力这一问题的思考与焦虑。自我增肥本是为了突显自己的存在,结果却因为太过肥胖而在男性面前“几乎隐形”。同时,琼为了迎合西方社会主流审美观而成功瘦身,却又始终无法摆脱作为肥胖者的自卑感。胖瘦导论背后隐含着的其实是当代女性的生存与自我定位困境。就像第一部小说《可能吃的女人》(TheEdibleWoman)所暗示的,在消费主义社会,女性身体也成了被消费的对象,以至于象征性地成了男性口中的食物。女性身体被赋予了过多的社会审美暗示与消费主义主张的解构式诠释,以至于女性自己无法成为自己身体的主宰。
西方以瘦为美的审美观念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与传统的贵族阶级之间的权利斗争有很大的关系。当时,资产阶级开始在财富上超过原先的贵族阶级,他们形象的代表是肥胖的身体和隆起的腹部,而传统的贵族阶级为了使自己与这些“粗俗的暴发户”们有所区别,则尽量保持着身材的苗条和行为的优雅。到了上世纪,随着西方社会财富的进一步积累,肥胖越来越不为主流社会价值观所接受,苏珊·博尔多说:“超标的体重被视为反映了道德和人格的缺陷,或缺乏意志。”[6]194无疑,这种价值观与审美标准更多地是制约女性的身体,无数女性将之内化为自己的“身体美”的标准。阿特伍德在一次访谈中说:“西方社会迷漫着关于女性身体胖瘦问题的困扰。我的意思是,告诉我三个认为她们的身材是好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不存在,身材永远没有‘好’。”[7]于是,女性的身体成了革命、改造甚至是消灭的对象:“‘现在,’一则典型的广告说道,‘摆脱这些尴尬肿块、肿胀、肥胖的肚子、松驰的胸部和臀部……远离臀部和腿部的脂肪团……拥有一个没有肚子的好体形。’要实现这些目标(通常就被想象为完全消除身体,就像‘没有肚子’所表明的好样),就需要对敌人发动猛烈攻击;必须‘攻击’并‘毁掉’肿胀,‘烧毁’脂肪,‘毁坏’并‘消除’肚子。”[6]191
从博尔多的话来看,这场盛行于整个西方社会的减肥运动的实质已远远超出了健身的范围,而是旨在消除和毁灭自己的身体。女性似乎是在将身体当作万恶不赦的敌人来进行毁灭性袭击。此时,身体早已不再是身体,身体成为身份与其它社会价值的辨识物,不再是与“主体”一体的事物,而是演变成了主体的他者甚至是敌人。在当今这个以瘦为美的社会里,主体与身体似乎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身体越苗条体积越小,主体便能越突出;相反,如果像琼一样因为肥胖而体积庞大,则反而是隐形的。正如阿特伍德在《女体》(“FemaleBody”)里所说的:“我这争议重重的话题,我这包罗成万象的话题。”[8]女性身体被承载了过多的审美和社会价值评判,她被赋予了包括生育在内的太多的义务,所以往往会被与主体割裂开来履行各种各样的责任,而女性的自我与身体也很难达成统一。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大众审美双重标准之下,女性的身体很容易成为自我的他者、敌人,甚至是自我(主体)试图消灭的对象。
三 “减不掉的肥”:无法逃避的过去
《神谕女士》这部小说中颇耐人寻味的情节是:琼虽然成年以后成功减肥,彻底告别了胖女人的形象,但始终无法摆脱过去那个“胖女人”的影子:她无数次梦见过去那个胖女人;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并不存在的肥胖的躯壳……最为不可思议的是,在小说的结尾处,琼正在创作的哥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也幻化成了她本人过去的胖女人形象。种种迹象表明,曾经的那个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而是一直潜伏在琼的身上,伺机出现。所以当琼遇见自己童年时曾经欺侮过她的玩伴时,突然间感觉到自己似乎又变成了胖女人:“一团团脂肪从我的大腿和肩膀冒出,我的腹部鼓凸如筍瓜,一顶褐色毛料的贝蕾帽咻地穿过我的颅骨出现在头上……我蛰伏的过去瞬间恢复生命力。”[2]228小说多次将肥胖称之为自己的双胞胎:“我那如影随形的双胞胎在我肥胖时瘦削,在我瘦削时肥胖。”[2]245“我的黑暗双胞胎,我的哈哈镜影像。”[2]250阿特伍德在《作家谈写作:与死者协商》(NegotiatingwiththeDead:AWriteronWriting)一书里详细谈到了她对双胞胎主题的关注以及对她的创作的影响,她说:“同卵双胞胎——与化身并不完全一样——总是能引起人的注意。”[9]双胞胎是阿特伍德的作品中几个反复出现的母题之一,通常都表现为一个看不见的黑暗的神秘影像,行踪不定,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悄然出现。很显然,这是一种心理层面的意象:与其说是外在影像,不如说存在于主人公的内心深处。简言之,是人物心理上的恐慌与呼唤的外化。
与胖女人的幽灵一样挥之不去的是母亲的鬼魂:琼的母亲死后也是一路追随着她。在小说中,母亲的鬼魂一共出现了三次,最后一次是在琼逃到意大利以后,这终于迫使她明白自己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躲不过母亲鬼魂的追踪,也终于使她意识到母亲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她:“镜子里站在我后面的是她,她是那个在每个拐角等待的人,她轻声低语。她是那位船上的姑娘,死亡之舟,那有着飘逸长发和忧郁眼睛的悲剧女子,塔中的女子。她无法面对窗外的风景,生命是她的诅咒,我如何能绝弃她呢?”[2]331上文说到琼的肥胖是她反抗母亲的结果,琼离开母亲以后便通过减肥变成了瘦女人,其实,过去的胖女人与母亲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两者都是“过去”的象征,而在阿特伍德的理念体系中,过去、母亲和自我这三者是一体的:母亲代表了自己的过去,而过去其实是另一个自我。厌恶母亲相当于否定自己的过去,而否定过去就是否定自我。所以,“惧母症”的实质是逃避自我。而自我是永远逃避不掉的。被压抑的黑暗自我总会以各种方式来寻找你、纠缠你,直到你学会与她和平共处。琼也与阿特伍德作品中的其他女主人公一样,经历了由“惧母”到接受母亲的过程。接受自己的母亲就等于接受自己的过去,而接受过去又意味着接受自我。
加拿大著名后现代主义批评家琳达·哈琴说: “‘自我’在我们的文化中被定义为连贯、统一和理性的,而阿特伍德的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促使人们追问自我的本义到底是什么。”[10]“自我”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分离的,那被压抑的另一半自我通常都用双胞胎、化身、镜像、梦境和鬼魂等意象来表现。为了达到自我的再次重合,阿特伍德的女主人公们都必须面对过去、接受母亲。而接受过去和母亲就是接受自我。
众所周知,阿特伍德作为“加拿大文学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加拿大民族意识。如果我们站在加拿大民族主义立场来审视《神谕女士》的话,琼的命运可以看成是整个加拿大在寻找自我定位道路上的一个缩影。加拿大同样经历着与琼相似的身份危机:长期以为来被诟病缺乏历史与文化积淀以及自身的民族特色。加拿大受制于它的“母亲”——优雅的欧洲和“父亲”——强大的邻国美利坚,而难以找到自身的民族定位。琼与母亲的关系相当于加拿大与英国的关系:就像琼拒绝成为和母亲一样的人一样,加拿大也一直试图证明自己具备有别于英国或欧洲的属于自身的特性。为了表明自己既不同于欧洲母亲,也有别于美国父亲,20世纪的加拿大一直致力于各种自我定位,可事实上过多的自我定位正是没有真正自我定位的表现。因此,要想真正建立加拿大的民族身份,首先要停止这种反复的自我定位,而应该从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中去寻找其真正的属性。
[1] 伍轩宏.“红头发与绿蜥蜴”( 《女祭司》导读)[M]//[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女祭司.谢佳真,译.台北:天培文化有限公司,2009:3.
[2] Margaret Atwood.LadyOracle[M].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8.
[3] Chodorow, Nancy.TheReproductionofMothering,BerkeleyandLosAngeles[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03.
[4] Tolan, Fiona.MargaretAtwood:feminismandfiction[M]. Amsterdam, New York : Rodopi, 2007: 80.
[5] Fee, Margery.TheFatLadyDances:MargaretAtwood’sLadyOracle[M]. Toronto: ECW Press, 1993: 35.
[6] Bordo, Susan.TheFlighttoObjectivity:EssaysonCartesannismandCulture[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194.
[7] Atwood, Margaret. “Using Other People’s Dreadful Childhoods”. interviewed by Bonnie Lyons. Convers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Ontario Review Press, 1990: 225.
[8] Atwood,Margaret.BonesandMurder[M]. London: Virago Press, 1995: 78.
[9] Atwood, Margaret.NegotiatingwiththeDead:AWriteronWriting[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9.
[10] Hutcheon, Linda.TheCanadianPostmodern:AStudyofContemporaryEnglish-CanadianFi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44.
(责任编辑:王学振)
HugeBodyandInvisibleSubject:MetaphorofObesityandNarrativeStrategiesinLadyOracle
ZHANG Wen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HangzhouNormalUniversity,Hangzhou311121,China)
Obesity is a principal image in Atwood’s novelLadyOracle. The protagonist Joan’s transformation from a fat lady to a medium-size person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plot. In fact, both “gaining weight” and “losing weight” imply some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meaning. Gaining weight arises in substance from a sense of self-identity crisis while losing weight is actually an act of self-destruction in the Western culture. Nevertheless, that Joan is still haunted by the image of a fat lady even after she has lost weight is an embodiment of her another ego as well as a representation of Atwood’s “twin” motif.
Atwood;LadyOracle; obesity; identity crisis; twins
2012年浙江省教育厅项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加拿大土壤中的后现代主义”(编号:Y201223054);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后现代主义观照下的加拿大民族性研究”(编号:13YJC752037)
2014-04-16
张雯(1979-),女,浙江金华人,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I106.4
A
1674-5310(2014)-08-008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