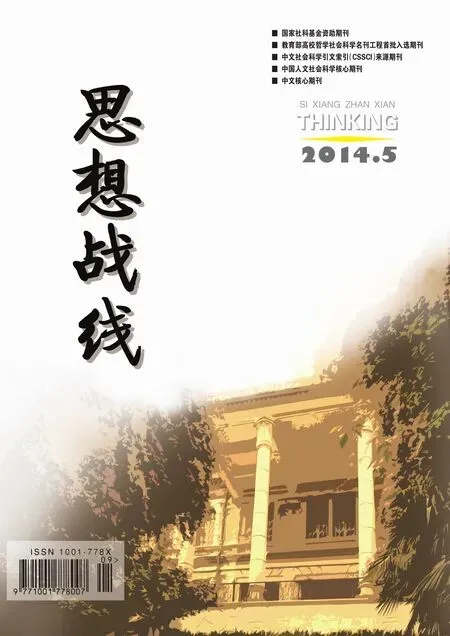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器”与“道”
王建民
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艺术,已经成为当代诸多中国大陆学者的共识,并进而引发了艺术学、美学等学科研究者对于艺术人类学这一重要学术研究倾向的兴趣。然而,由于对理论和方法论范式的认识不足,对于应当怎样以人类学的观点来理解和阐释艺术品或工艺品,开展对艺术品或工艺品的人类学研究,却依然较为模糊。为了追寻本土认识论源流,我们用“器”、“道”两词来作为核心词,钩沉中国古代对于“器”与“道”关系的探索,更关注人类学对被视为艺术的承载物或艺术本体的艺术品或工艺品的研究,力求重新链接以往被割裂的知识脉络和社会文化关联性,以飨对此问题有兴趣探讨的学者,进而促进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有效拓展。
一
《周易·系辞上》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一论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易学和哲学的重要命题。乾坤和阴阳变易的法则从诸多有形中概括、领悟、凝练和思辨成无形,因此是形而上的;器则是有形、有象、可以致用之物,是形而下的。
尽管出于对礼制的重视,自先秦以降,庙堂之器一直被视为朝廷之根本,四裔来朝贡献器物也被朝廷视为归附的荣威,甚至“器”在古汉语里有了如今我们所说的“重视”之意,但在汉代官僚选任体系确立之后,识文断字在中原地区变得越发重要,科举制实施之后,“道”又得到了更多强调。
中国经学与易学释经者们对于道与器的关系提出了个人的见解,但却莫衷一是。如唐初著名经学家孔颖达认为:
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谓之器”也。[注]王 弼:《周易正义》卷7·系辞上,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内府刊本。
崔憬则主张:
凡天下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言有妙理之用,以扶其体,则是道也。其体比用,若器之于物。则是体为形之下,谓之为器也。[注]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8,潘雨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11页。崔憬,又作崔觐,唐代稍晚于孔颖达时易学家。
强调道与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道必须依赖于器。他在注重玄理的同时,也兼采象数,主张《易》以象为本,象尽意,辞尽言,反对重道轻器或将道与器对立的认识。
此后,宋、明、清各朝诸家多有争论,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焦点。譬如,宋代理学大师朱熹认为: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秉此理然后有性,必秉此气然后有形。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者也。[注]朱 熹:《朱文公问答全集》卷29·答黄道夫,载朱 玉辑《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册6·问答,雍正八年(1730年)紫阳书院刊本。
不仅道先于器而存在,而且道、器相隔;明清之际王夫之则主张:
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注]王夫之:《周易二种·周易外传》卷5·系辞上传·第12章,同治四年(1865年)刻本。
道是以器的存在为前提的,有器方可有道。双方据理论辩,后人主张各异,或道理而器具,或道本而器末,或无器则无道。时至今日,这一关系依然有待于放置在新的时代学术语境中重新梳理和辨析。
人类学家认为,不同文化制度(cultural institution)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制度的性质,因形式的来源不同,而有种种之别:有的是自然生长的,谓之生长的制度;也有人为规定的,谓之规定的制度。生长的制度系从风俗(民风、习俗、惯例、共同习惯等)及标准(民仪、民德、礼教、行为规则等)中发展出来的,如自然家庭及天伦关系。规定的制度,乃由人类充分运用理性与意志的结果,法律与政治是最好的例子。”[注][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9页。吴文藻先生参照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观点,对于器物(物质底层)、制度(社会组织)和语言(精神)三个文化因子和经济、教育、政治、法律与秩序、知识、巫术宗教、艺术、娱乐八个文化的方面(有时加上技术成为九个方面)。“三因子大致上代表了文化的结构,而八方面代表了文化的功能,二者是由相对而组成的。”[注]吴文藻:《文化表格说明》,《社会学界》第10卷,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8年,第207~246页。文化的每个方面都与三因子彼此关联,三因子同时并存,发生交互作用。
因此,在人类学的立场上来看,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表现在物质对象、社会制度、精神观念三个层面,既体现出人们对于周围自然的适应,又反映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人们的主观行为。概括来说,按照人类学的基本认识,对于艺术的研究就不仅要关注与艺术相关的器物和技艺,也要考察和分析生产艺术品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社会结构,认识和理解艺术生产的美学观,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观、空间观、道德观、伦理观和宇宙观。照说这个道理似乎并不难理解,但艺术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三个主要的相关学科各自更多地停留在其中一个层次之上,学科的边界成为了阻断“器”与“道”关系联结的篱笆。因此,要特别强调的是,从三个层次(即吴文藻先生所说的三因子)去观察和分析艺术,需要克服将彼此相割裂的倾向,实现三个层次的紧密联系。
这样的认识是以人类学学科的整体论(holism)研究范式作为方法论基础的。按照这样的观念,只有把艺术放置在艺术所在的社会文化之中才可以得到理解。艺术是嵌合在社会文化之中的,与特定的社会场景直接关联。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说明,艺术并不是一种可以和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等文化制度切开来进行研究和认识的孤立现象,在许多文化中,艺术也不是像现代社会那样作为一个专门化的领域存在的。人类学家认为,艺术生产并非仅仅是美学的,更是嵌合在作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丛的艺术世界之中的活动。不能只关注艺术品,而忽视了为生产艺术品做出贡献的社会关系丛,不能忽视了社会群体成员彼此之间的存在与实践、观念及阐释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学研究艺术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艺术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关注文化观念和社会条件是如何制约着艺术的发展。这一特征可以说是以往人类学与艺术学在艺术研究上的最大区别。
以往很多学者常用“嵌入”或者“镶嵌”表述艺术与社会文化的这种关系。其实,人们所说的“艺术”本身与社会文化的其他部分原本就是浑然一体的,所以,在传统文化中才不会刻意区分到底什么是仪式用品,什么是艺术品,什么时候是做仪式,什么时候是在表演。只是到了近代科学发展起来以后,研究者才按照现代科学的结构原则,把“艺术”刻意地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特别行当“分”了出来,以利于更深入、更清晰地运用“科学”手段来研究和说明这种现象。艺术和政治、经济相分离,甚至和社会、文化相割裂,彼此之间因而有了更为明确的界限。遗憾的是,不少学者以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分割的,或者只有这样被切分开来之后才能够加以认识,然而却正是因为这种切分一成不变地持续延展,使得人们的认识和理解出现了偏差。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科学主义的人类学研究范式进行反思,这种思考也表现在艺术研究之中。以往被加以特别强调的那种制约艺术存在的结构(structure),也就是以往所重视的社会性、集体性因素被重新加以考量,结构对于艺术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结构的影响和制约究竟是怎样作用的?当代人类学家对于艺术的研究力求将结构与能动性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更多地涉及情绪情感(emotion)和行动者的能动性(agency),在文化的再生产和再创造的建构论立场上,能动性得到了更多地强调。
与此同时,人们认识到,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传统的社会关系、市场结构及文化观念的整体瓦解了,不同利益群体的差异化诉求及社会文化构成成分成为彼此断裂的碎片。面对现代社会中文化碎片化的状况,有人认为整体论已经失去了魅力,应当摒弃作为人类学基本观念的整体论。一些人类学家虽然不再把整体论作为一个总括性的研究课题加以强调,但却依然会把它当做一个世界构成策略(world-making strategies)探究必不可少的工具箱。
当代人类学家多强调场景(context),这是在地化的研究资料搜集方式,是方法论的、文学的和政治的审慎处理,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理解。场景是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中对特殊现象的在地性描述,是将观察到的现象与更大的经验、意义、文化、功能或社会整体联系起来的理解。简而言之,场景是整体论的,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田野工作和跨文化比较的标志之一。[注]Nils Bubandt and Ton Otto,“Anthropology and the Predicaments of Holism”,in Ton Otto and Nils Bubandt eds.,Experiments in Ho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Malden, MA: Wiley-Blackwell,2010,p.1.对于场景的多样化理解的新观点,表现出人类学理论取向的多样化。
作为和语言一样很早就成为人类表达观念与情绪情感的方式,艺术本身有其特定的表述规则、有其自身的结构要素与结构关系,具有一套相关的概念,通过具有特定族群和时代特征的艺术语言和结构表达其特定的意义。因为艺术符号系统具有独特的自我指涉性(self-referentiality),[注]有关艺术符号系统自我指涉性的讨论,参见王建民《人类学艺术研究对于人类学学科的价值与意义》,《思想战线》2013年第1期。通过艺术语汇和日常生活语言的重新组合、简化、反复、叠加、变形、挪用、盗用、扭曲和倒置等手法,构成了一个不断再生的文化表达体系。艺术可能由此会作为现实的异在而呈现,构成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性认识,法兰克福学派审美的乌托邦思路即是由此建立起来。正是因为艺术对现存世界的否定与超越,艺术才在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的眼中具有了革命性的、批判性的力量。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自我指涉体系造成了艺术与社会其他各界的隔膜,这一专门领域被不断地魅化了(magicalized),其魔力在不断扩张和加强。在艺术行业专门化日益加深、艺术产品市场化日益加强的场景中,表征的方式盖过了表征的对象,艺术形式、风格、样式盖过了艺术主题,人们的注意力无条件地付诸于外在参照物和艺术形式。艺术生产者们越来越关注器物的形制和技艺的标准或完美程度,在公共媒体的蛊惑下,社会公众对于艺术的鉴赏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拜物教性质的文化现象。因此,英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吉尔(Alfred Gell)强调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首先应当“去魅”。不过,我认为去魅之法不一定要回避,而可以运用破解策略。通过人类学对于当代文化现象的批评、反思及其实践,揭露“魅”(magic)的形成与强化过程,才可能避免艺术在自我指涉的道路上走得过远,而失去了与社会文化的联系,沦落为少数人孤芳自赏的游戏。
二
以器物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常常被判定为文化之中最易明白、最易捉摸的部分,其实却需要基于更为深入的理论追寻和反思,才能够对此有新的认识和理解。物质文化是一系列围绕着物质的人类日常活动——包括使用、分享、谈论物质,为物取名,以及制造物品的方法。[注][英]Tim Dent:《物质文化》,龚永慧译,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第19页。围绕着物的人类的行为模式和观念体系,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就是关于物质文化研究。艺术品或工艺品在物质文化研究视域中被认为是“物”,围绕着它们的行为模式或者观念体系的研究也应当放置在物质文化研究理论脉络之内。
早期人类学家通过“物”研究文化的进化、传播与变迁,借由文化残存物的“物”来考察新旧文化之间的历时性关系,用从原始部落收集来的器物在博物馆中说明西方文明的存在和辉煌。传播论者则将文化与社会的变化与差异归因于物质文化的传播。美国历史特殊论学派在文化地理学的基础上强调文化的特殊历史,物成为“文化区”建构的重要尺度。法国社会学年刊派主张把社会事实转化为物质实在来研究。早期的人类学家虽然对物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与考察,但更侧重于利用“物”在时间与空间中建构文化的进化、传播与变迁图景。在最初的这些研究范式中,物和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脱离的,人类学家在那个时代关注的主要是物本身。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库拉”交换研究中开创了对于物的功能研究,在社会整体的彼此联系中看待在“物”,强调物质对象作为制度的基础和观念的载体而存在,他也注意到了纯粹的物物交换与关乎声望的“库拉”交易的区别。[注]参见[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开创了对礼物交换的研究,通过礼物馈赠与回报的不同原则来观察作为礼物之物的交换过程,说明道德与经济的紧密关联,契约与交换被视为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混融。[注]参见[法]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 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将文化视为社会区隔和再生产的资本,他关注物的象征意义,文化资本包括可以被制度化为证书等社会承认的资质,但也被客体化成为绘画、书籍、事典、道具、器械等物质。他强调艺术是某种艺术意向的产物,文化鉴赏并非天然禀赋,而是文化实践的产物。[注]参见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人类学对于物的研究从大的文明、文化的时空比较逐渐转向更为细致的功能、认知、分类、符号、象征意义等层面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文学批评和哲学等学科对于“物”(thingness)和物质性(materiality)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学术探索。在新的物质文化研究中,人们开始关注在社会文化视野下以物为切入点探讨社会生活方式,透过物来折射出地方性的“人观”。
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在其著作《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TheSocialLifeofThings:CommoditiesinCulturalPerspective)把马克思对物的商品化的强调转向了物的流通的整个生命过程,通过对于人们在过去和现在的社会文化场景中如何销售和交易物品的考察,聚焦于文化是如何定义交换各个方面、社会是怎样规定流通过程的,说明人们如何发现物的价值,以及物怎样赋予社会关系以价值。[注]参见Arjun Appadurai ed.,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阿帕杜莱和其他几位英美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将物视为社会生命,倡导“物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ings)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物的价值如何外化,以及怎样找寻的研究方式,在物的研究领域架起了社会史、文化人类学、经济学、考古学和艺术史等学科之间的桥梁。
这类新探索颠覆了长期以来在物的研究中对于人们如何制造物(how people make things)的研究模式,而去诘问物是如何制造人(how things make people)的、客观之物是怎样影响到人的社会关系的、没有生命的物何以具有了其自身的能动性。作为主观和客观之物、礼物和商品、艺术品和人工制品,具有可让度性和不可让度性的“物”,前后两者之间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难以区分。由此学术转换获得新的启发成为当代艺术人类学研究者面临的新挑战。
从人类不同社会文化群体来看,为了在所在群体与他者之间做出区分,就需要显示自我的独特性或差异性,由此去寻求其自身的目的和意义。在寻找共同意义与方向的过程中,人们为了说明其意义的重要性,为了与所在文化场景中其他族群相区别,就会对表达性的手段对某些物品进行更加特别的处理,使之更加明显、更加独特、给人能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人们对那些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物品更加用心地去制作,创造出了艺术品或工艺品这种独特的不寻常之物。正如达文波特(William H. Davenport)所言,仪式中的物品通过装饰与日常生活之物相区别,艺术附加值成为了物品分类为圣与俗的标志。[注]Davenport, William H,“Two Kinds of Value in the Eastern Solomon Islands”,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95~108.为了满足表明存在、彰显认同、展现自我的需要,与一般的物品相较,艺术品或工艺品时常具有独树一帜的表现性。苏珊·朗格认为,“所谓艺术,就是‘创造出来的表现性形式’或‘表现人类情感的外观形式’”。作为被创造出来的“生命的形式”的“创造物”,“一件艺术品就是一件表现性的形式,这样创造出来的形式是供我们的感官去知觉或供我们想象的”。她认为,这并非艺术形式的全部含义,不同于指事物形状的那种形式,“抽象的形式是指某种结构、关系或是通过互相依存的因素形成的整体。更准确地说,它是指形成整体的某种排列方式”。[注][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05页、第13~14页。
以器物形式呈现的艺术品和工艺品基于具有与特定时代联系的社会、文化差异的特定语汇和表达结构,才能够建立起对于器物的基本认识和理解,了解器物所能够表达的意义。有些人借用“文以载道”之辞,衍生出“物以载道”的说法,来表述器物与观念之间的关系。不过,何以辨析这种关系则多语焉不详。
按照器物研究的新思路,应当认识到,器物有其社会文化属性,体现着物与天、物与地、物与人的关系,也还有着心与物、文与质、形与神、材与艺、用与美的关系。所以,用人类学的眼光来审视艺术品和工艺品,就需要认识其原材料和制作工艺(器之体)、艺术形式和形制(器之形)、社会功用(器之用,从不同器物的生产、生活用途,到各种形式的收藏、作为个人馈赠亲友的礼物,再到国家交往的国礼),但从人类学的立场上看,要探求其表征和多重意涵。从器之形和器之用,延展到器之性(器物的社会文化属性,诸如文化认同、历史记忆与表述、使用器物区隔社会等级、体现文化精神、建构民族国家,乃至宣传世界和平)、器之礼(器物的生产、交换、占有、使用、转让和继承的规则、制度、仪式和秩序)、器之神(器物本身及其与器物有关的信仰崇拜)、器之品(器物的格调)、器之美(器物的审美)、器之韵(器物的精神意涵)、器之情(器物蕴含的情绪情感)等不同方面,以及与器物打交道的人在不同场景中如何处理和变通这样的,这些,也许是未来可以进一步去探讨的方向。
我们所列举的器之体、形、用、性、礼、神、品、美、韵、情本身就是相互联系的:天成地就的原料关乎器的独特品和韵,人们在特定的规制中,以不断琢磨和提升的精湛技艺制作出器之体、形、创造了美、伴随着情,在器物产生之后的生命史过程中,器之用、性、礼不断塑造着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器之神作为人们的信仰和观念在实践中得以产生和重塑,又通过品、美、韵、情的赋予,使这种器成为一种非“常器”的艺术品。因为这种重要性,艺术品的上述诸方面在一种彼此交通(traffic)、互渗、共融的关系里彼此相互纠缠,同时处于被再生产、再创造的周而复始、延续承继的过程中。认识到这样的联系性,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器物与观念以及情绪情感(emotion)之间的关系, “道”的复杂性、变化性、多样性也才能够真正呈现出来,“道”就有可能得到认识、理解和阐释。在每项器物的人类学研究所面对的具体场景中从事研究时,重视彼此之间的关联,就有可能实现对器物的人类学研究和探索。
唐卡是当代许多人关注的宗教器物和艺术品,但画师心目中的唐卡、供奉和观瞻者心目中的唐卡,以及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中的作为收藏品和艺术品的唐卡、旅游者们作为具有某种神秘宗教色彩的旅游纪念品的唐卡,却可能有着多重具有差异但又相互交织和纠缠的概念系统、意义体系和情绪情感。按照藏传佛教造像的观念,在西藏昌都县嘎玛乡唐卡画师艺术实践的个案中,画师们将唐卡绘制与宗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视之为修行的一种方式,运用多感官来感知和体悟佛法的密义。藏传佛教造像至今依然保持着严谨的造像量度,画师们依循各画派略有差异的造像量度经,作为观瞻和体认佛法的基础,熟记于心,并在唐卡绘制实践中对量度法则加以阐释和运用。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画师们也存在着身居何处的焦虑,面临着与外部世界有关的唐卡签名、唐卡形式、颜料和技法改变等不同挑战,他们在宗教、经济、艺术之间、在画师个体创造力与绘画形式之间的张力中进行着认识和实践略有差异的选择、平衡和化解。因“发心”这一看不见的画师绘制唐卡时的内心活动,使这种佛教造像的唐卡既是艺术,又有别于普通的艺术。在唐卡成为艺术市场交易品、收藏品的时代,在商业性唐卡博览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传承人认定等事件的冲击下,优秀画师们正是坚持唐卡的宗教神圣性发心,在绘制一遍遍、一幅幅唐卡的过程中,延续和增强着作为佛教造像的唐卡的价值,也呈现出画师们在遭遇艺术、商品化时的自我审视,以及对于唐卡的未来的探索。[注]参见刘冬梅《造像的法度与创造力——西藏昌都嘎玛乡唐卡画师的艺术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
川北仪陇县大木偶的选材与制作由专门的雕刻艺人完成,而演戏却是由专门的木偶戏班来操作。传统大木偶的制作材料以当地的麻柳树为主,这种材质轻便、质地坚硬、不易起裂、色如肤色的树材被誉为“神树”,并凭借三国英雄张飞的地方神话传说而获得了特有的品性。当地木偶的神话传说与地方社会紧密相关,在仪式场景和过程中更易被当地人们所接受。大木偶人物制作精良、机关巧妙,造型以写实为主,眼、眉、口、头、耳、鼻、手、腰以及关节均可以活动,表演时能取物握物、穿衣解衣、戴帽脱帽、穿靴脱靴、吹火点蜡、拂袖掸尘、变脸下腰,并能展现出翎子功、扇子功、水袖功等,神乎其技,宛若真人。木偶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社会丧葬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借由木偶表演具有了神圣性的社会文化意义。过去,当地大木偶艺人们依靠演戏、说书、看风水、治病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游走于川北、陕南和甘南一带谋生。在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中,大木偶艺术承受着家族、师徒、同宗、同乡等亲密关系所结成的社会组织与民间信仰体系、共同价值观念的共同滋养、分享和维护。通过大木偶的制作和表演,可以进一步认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艺人们生计方式的选择、地方政治历史过程的变迁,以及中国汉人社会神灵信仰模式的结构与行为,在相互关联的“纵式”与“横式”的研究框架与元素匹配中去阐释各种关系及其对木偶、木偶戏、木偶艺人的生活与内心世界的演化过程及结果。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和旅游开发热潮中,川北大木偶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又经历了新的生命史。[注]参见张猷猷《求偶纪——“李木脑壳”的人类学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
湘西苗族巴岱卓还傩愿等10多项仪式中法师的法杖上系着36条绺巾,由法师的36位姊妹亲手绣制,每人1片,在法师立坛仪式上启用,成为法器。绺巾长约40厘米,上端宽3厘米,下端宽7厘米,用彩色丝线绣上昆虫、植物、人物以及文字,表现出当地民众对所在自然环境的在地化认知及特有的造型、色彩美学观。绺巾是一种民间艺术品,更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法物,还是体现社会关系的礼物。绺巾作为信仰仪式中的一件礼物,不仅与社会生活中的人情往来有关,也是信仰层面的见证。人与神虽然处于两个空间,但是在信仰仪式中,通过绺巾上打“三十三重天”,下打“十八层地狱”,打通神、人、鬼三界,请来五方神明护佑百姓。由其姊妹完成的绺巾从不同的女红能手们流向新巴岱,帮助他获得合法化的神职身份。巴岱卓做法时常以左手舞动着绺巾,呼唤和借用神明法力,绺巾伴随巴岱经历一生的仪式活动,而绣制绺巾的姊妹们也将获得这位巴岱终身免费的法事服务。赋予地方性美学价值的器物与社会关系、与神圣性之间的联系在这一个案中得到了充分彰显。由于当代家庭结构和亲属关系的变迁,原本由家姊妹、堂姊妹就可以完成的绺巾绣制,现在绣制者需要扩大到更大的亲族,甚至是那些不太能够清晰计算的同姓姊妹。不仅有文化的传承,而且也能够体会出当代社会的变化。[注]参见邹宇灵《巴岱仪式中的绺巾与审美——湖南湘西苗族信仰仪式法器的人类学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在物的新研究范式之下,不同学科的学者开始通过器物的田野民族志研究进行物的探讨。在每项器物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所面对的具体场景中从事兼顾文化法则与激情、情感的民族志研究时,重视器的性质和观念之间的关联,重视器的各个方面彼此之间的关联,重视器对于人的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制约。在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研究和探索之中,作为艺术品的器物不再是静止的、单向的客观之物,而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变得生动起来,人们依循和创造性地运用着一套与器相关的特殊语法和语用体系,使器具有了能动性,具有了生命力,在人们的面前呈现出深奥而多变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