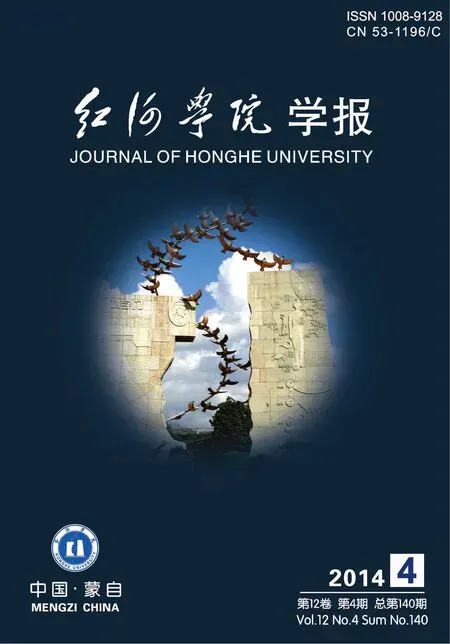韦伯与福柯现代性理论的比较
刘梦阳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昆明 650000)
韦伯与福柯现代性理论的比较
刘梦阳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昆明 650000)
韦伯与福柯都是研究现代性的集大成者,韦伯将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比作“理性的铁笼”,而福柯将现代性对人们的监控看做是“全景监狱”。他们的思想的差异性建立在其亲和性和继承性的基础上。他们各自的理论有其显著的特点。从韦伯与福柯的著作中发掘二者在现代性思想方面的差别,其主要集中在方法论、分析视角、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和关注焦点这四个方面。然而殊途同归,二者都关注现代性社会的权力与身体议题,同时又都对现代性进行了有逻辑、有价值、有深度的批判。然而二者虽都剑指现代性的症结却都没有提出超越的方案和设想。
马克斯•韦伯;米歇尔•福柯;现代性理论
提到现代性理论,学者们一般会把福柯与马克思、福柯与哈贝马斯、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进行比较,但将韦伯与福柯二者放在一起比较的却很少,通过检索文献仅发现有将韦伯与福柯权力观进行比较的研究[1]。他们一个是经典社会理论家,一个是后现代理论家(虽然福柯本人不认同这个说法);一个中规中矩,一个剑走偏锋。乍看上去二者的理论、思想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韦伯和福柯都是研究现代性的集大成者,比较二者的现代性思想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二者理论既截然不同,又殊途同归,使其现代性理论碰撞,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火花。下面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 福柯与韦伯现代性思想的差异
(一)方法论的差异:理想类型与系谱学
韦伯的学术研究都是在他的理想类型的方法论的指导下展开的。他的理想类型意味着“每一种定义都不是要穷尽性地描述推理和社会的特殊情形,而是要提供一个概念框架。[2]”然而,理想类型是研究的“工具”,而非社会“模型”。
“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是韦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也是韦伯现代性思想的核心术语。[3]”韦伯将现代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他强调现代社会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恰恰与非理性(新教伦理)产生了契合效果,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即理性化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基础。但在一片繁华中,韦伯还是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负面:工具理性蔓延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目的让步于手段,客观与主观的分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凸显。于是他提出现代理性导致“致命的自负”。可以看出,韦伯的理想类型不是仅仅止步于对类型的划分,而是作为进一步推进理论的基石,在类型的背后蕴涵着深远的意义。
福柯的方法论指导思想是谱系学。谱系学源于福柯的独特历史观,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尼采的思想的影响。尼采的思想促使福柯进行反思那些“想当然”的事情是否真正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的理所当然。谱系学在李猛看来是这样一种方法论:在某一时期某一概念被赋予全新的意义,而随着新的意义的跨代传播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于是这部分被认为是必然的、无害的、可敬的。但是福柯的谱系学试图通过历史考察证明某一概念的不整自明性从基础上受到损害,关注偶然事件和微小的偏差,反对历史决定论,揭露意义与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信念与伦理体系极为深刻地牵涉到权力斗争[11]。因此福柯的理论建立在历史特殊性的基础上,意图揭示常规现象或制度的形成的特殊机制和背后的策略安排。
比如,论述惩罚方式。福柯考察了从酷刑到温和的惩罚方式的历史,因此福柯的著作也常常被当做法制史来阅读和研究。当然,他的思想并不止于此,而是在于更进一步发掘出这样一种观点:看似更仁慈更人道的制度在历史的细致考察下却并非如宣传的那样。福柯说:“(惩罚)不再是通过公开处决中制造过度痛苦和公开羞辱的仪式游戏运用于肉体,而是运用于精神,更确切地说运用于在一切人脑海中谨慎地但也是必然地和明显地传播着表象和符号的游戏。”[4]所以可以看出这些仁慈和温和的转变的实质不过是从一种残酷走向另一种残酷。
再比如分析疯癫,福柯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疯癫其实是是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是一种布迪厄所谓“符号暴力”。《疯癫与文明》表面上讲述的是对待疯癫的人的治理术,从隔离到禁闭再到精神病院的产生。但实际上福柯撕开了表面上看似对疯癫人似乎越来越人道的对待,他真正的目的是向人们展示疯癫的人是怎样遭到理性的排挤和控制的历史。
(二)分析视角的差异:现代性的概述与现代性的“深描”
正如上文所说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论贯穿其理论的始终,他的理论框架都是在类型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所谓理想类型就是忽略细枝末节的差异将某一现象或者领域抽象为几个类型从而进行研究。因此韦伯的现代性理论是抽象的,是对现代性的概述。
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是抽象的,他考察的并不是工具理性的微观表现。韦伯的大体思路是:生活中的理性化和理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带来的副作用是“让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能够通过合理的计算来把握任何事物”[2]。可以说韦伯的观点是由于我们对人类的理性盲目的自信导致了现代性的“非预期后果。”
韦伯的现代性思想也提到了“自由的丧失”。韦伯看到,理性化会导致自由的丧失,即人的独立价值的丧失。因为现代社会强调效率,而要提高效率就要不断加强工具理性的程度,如管理体系的广泛应用,但官僚制度使社会成为机器,在这样的制度中,每个人都成为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或螺丝钉,个人按照自己信仰、理想的价值而行动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压制[3]。人们整齐划一却态度冷漠。之后,哈贝马斯发展了这一思路指出工具理性已经向我们的生活世界殖民。
我们看到韦伯的论述保持在较为宏观的抽象层次,他没有具体到分析工具理性是怎样、通过什么来控制人们,人们又是怎样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螺丝钉为社会大机器而存在。可以说,韦伯的思想是具有吸引力的,但是有失精致,是一种概述性的论述。而福柯则认为现代理性并不是同质的,在不同领域(疯癫、性欲、惩罚等)的支配理性有其特殊性,这点与布迪厄倡导的场域关系论有相似之处。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微观的权力分析,对现代性进行“深描”。
福柯对现代性的分析集中体现于《规训与惩罚》一书,展现了现代权力的无孔不入,对身体进行各方面监控的图景。书中他细腻地分析了现代微观治理术的策略。这些技术都是很精细的,甚至往往是些细枝末节,但正是这些细节规定了某种对人体进行具体的政治干预模式,一种新的权力“微观物理学”[5]。这些“狡猾伎俩表面上正大光明而实际上居心叵测”福柯也将它称为“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这些治理术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管理者分割和利用封闭的空间,每个位置都安置不同的人,建立有用的联系,打断其他联系。比如场所、座次、班级的排列。福柯说:“纪律是一种等级排列艺术,一种改变安排的技术[5]”这便是所谓的分配的艺术。
其二,对活动的控制体现在制定详细而精准的时间表、规定动作习惯的方向、力度、时间、特定的姿势。“使时间渗透进肉体之中”。除此之外,纪律还操作肉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比如士兵不断操练拿枪的姿势,工人不断练习如何给一个零件拧上螺丝钉,以此达到熟练 的状态、达到肉体和武器、工具、机器的复合。还有榨取时间,福柯在这里用了“榨取”,这跟韦伯对“时间就是金钱”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赞扬恰好相反。
其三,更经济地利用时间,将一切序列化,规定好人生某一段时间应该完成哪些任务。人们将这种训练内化,逐渐形成“进化”的时间观念,人们按照指定好的大纲进行着自己的人生。
其四,是福柯所谓“力量的安排”。是这样一种权力的艺术,将每个肉体变成一种可以被安置、移动及与其它肉体结合的因素,然后按照年龄或者其他因素组合起来,以发挥最大的力量获得最佳的效果。
于是自动驯顺的肉体便培养成功,但是规训的手段远不止这些,福柯接着论述了层级监视技术,即在边沁所谓“全景式监狱” ,典型的包括军营、学校、工厂等,在这些建筑物之中进行可见又无法确定的监视。福柯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感觉:你知道自己被监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被监视的什么时候是自由的,这种控制技术是精神对精神的监控,比持续的监视给人以更大的心理压力,“未知”是这种恐惧的核心。
还有是规范化裁决,这种裁决方式标示出差距,并按统一标准制定奖惩。人们对比这些所谓标准可以明显看到自己同别人的差距,并会按照这些求自己,却没有人追问这些标准是怎样制定的?我们凭什么要由标准裁决自己?
此外,检查(examination)也是监控的策略。检查进一步引导人们进入规范的符码世界,不断强化人们遵守规范的意识。
以上这些微观的,并不为人所察觉的规训从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管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而人们的行动又不断强化这些规范,不知不觉将其完全内化,从而自觉成为驯服的人,成为“监狱”中合格的却麻木的一员,人们丧失了主体性。
当然这样思想的差异与二人所处的时代有莫大的关系。(由于不同社会背景并非二者理论本身的差异,所以笔者并没有将这一点差异提出来进行详细的论述。)韦伯(1864—1920)处于现代理性和技术的黄金时期,人们享受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丰硕成果。福柯(1926—1984)生活的时代则看到更多现代社会贝克所谓“自反性”。因此,韦伯的现代性理论是较抽象的,具有启发意义,而福柯的现代性理论是具体的、特殊的、细致的。
(三)对思想和身体的控制:理性铁笼与全景监狱
韦伯论述的现代性的副作用集中于现代工具理性对人的精神或者说对“意义”的侵蚀。韦伯提出的现代性的后果是形式合理性占领了现代性的高地,而价值合理性被压制、被忽视、被抛弃。人们热衷利用各种手段和精心的计算以提高效率,却深陷在工具的泥沼,忘记了最初的目的。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轮回着重复的工作,却丢掉了意义。理性的崛起,宗教信仰衰落,信仰体系像是突然被抽空, 于是“诸神不和”,人们的思想受到了冲击。于是“工具价值观的蔓延,终极价值受到忽视”。[2]可见,韦伯论述的一系列现代性的后果都与意义、精神有关。韦伯将现代性诊断为“理性的铁笼”。他说道“对圣徒来说,对物质财货的关注只应是‘披在肩上的一件随时可以甩掉的轻飘飘的外套’。然而命运却注定从这一外套锻造出一件钢铁般坚硬的外壳(铁笼)①”[6]可以说,人被工具理性“异化”了。
福柯关注的是现代性对身体的监控。他的著作《规训与惩罚》的副标题叫做“监狱的诞生”,无独有偶,他的《疯癫与文明》也以“精神病院的诞生”作为全书的收尾。细细想来,福柯不仅仅在叙述监狱和精神病院的诞生历史,而是以监狱和精神病院的封闭、监视、惩罚、规训来隐喻“现代性”,历史是外壳,现代性批判才是其著作的实质。福柯自己也明确指出“本书(《规训与惩罚》)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这才是我的兴趣所在。[7]”如果同样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福柯对现代性的诊断的话,那么笔者认为“全景监狱”较能突出福柯的观点。它关乎身体自由的丧失,自我沦陷于现代性的“圆形监狱”中,这便是福柯描绘的“现在的历史”。
(四)对待现代性态度的差异:纠结矛盾与态度鲜明
韦伯对于现代理性又爱又恨,一方面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理性”成为他分析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现代理性的限制。即现代性的典型现象如祛魅、生活的理性化、科层制等都具有正面和负面双重的性质。负面的影响在于人们因追求效率而丧失了意义,这样的世界无异于困于“理性的铁笼”。但韦伯又认为“理性的铁笼”又无法抗拒,是现代性必经的阶段。“现代性将走向何处”这个问题韦伯也是纠结的,一方面他对此感到绝望和悲伤,但另一方面他心中又有无法熄灭的星星希望之火。他始终在肯定理性化的结果和意义丧失的忧虑之间徘徊。纠结的韦伯陷入矛盾困境无法自拔,甚至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备受煎熬。笔者看来,韦伯的纠结源于他的辩证思维,他总能看到事物的两面性,因此无法朝着一个单一的方向行进,而是困在现代性十字路口踌躇不前。不过这也正是辩证思维的魅力所在。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达尼洛•马尔图切利所说“他的著作的丰富内容就来自其回答的含糊性本身。[8]”
福柯则没有纠结,他坚决地批判现代理性,甚至到走到了全盘否定的极端,他将“解构”之路一条道走到黑,不顾辩证思维,义无反顾,头也不回。也正是这样的态度鲜明使他的思想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他解构话语体系,认为知识是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是一种符号。他认为陈述得以实施,它需要“参照(这种参照不一定是事实,事物的状态,甚至也不是对象,而是一种区分的原则)。[9]”在《文明与疯癫》中认为疯癫的知识是理性建构起来的,是理性给非理性贴的标签。所谓“疯癫”的人甚至比理性的人更正常。这里理性与否成为划分正常人与疯癫人的原则,疯癫可能根本不是事实,也不是非理性人的真实状态,而只是一种排挤的策略和原则。“非理性被置于审判之外,从而被武断地引渡给理性的权威[10]”
当然他没有停留在语言、知识阶段,而是将权力引入分析框架,接着解构人类的规范体系。如上文提到的,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将现代性的典型场景描述成边沁的圆形监狱,现代性的人时时刻刻生活在权力的监控下,各种规训的治理术使人成为驯服的肉体。而规范体系将功利主义观念掩藏起来。不拨开这层迷雾,打破现代性的幻象,我们无法认清自己,无法反思到“温和”又“残酷”的规训体系,无法看透这个监狱般的世界。
韦伯既肯定现代性的成果批判现代性的后果,表现出他悲天悯人的情怀。福柯眼光独到狠辣,态度鲜明,研究角度又匪夷所思不走寻常路。
二 韦伯与福柯现代性思想的继承性和亲和性
(一)韦伯思想对福柯的启发性
权力是韦伯探讨的重要主题之一。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11]并且延续理想类型思路将权力(权威)分为法理型、传统型、卡里斯马型,韦伯的权力分析基本属于“合法化—权威模式”,韦伯将权力作为社会分层的三个维度之一,可见权力分析在韦伯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对于权力的分析更是福柯的中心主题之一,集中体现于其《规训与惩罚》一书。正如前文“现代性概述与现代性深描”这一部分所说,福柯主要对现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即微观的治理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因此,现代社会的权力问题是韦伯与福柯共同关注的问题。韦伯的思想是社会学领域古典权力理论的滥觞,福柯继承了这一主题,将权力理论推向前进。他对权力理论的发展包括认为权力是多形态的而不是同质的,权力是作为关系出现的策略,而不是所有物,权力首先是生产性的时间,而不仅仅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和关注权力的微观运作。[4]从现代性权力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与福柯思想的亲和性和继承性。
此外,韦伯和福柯都将对身体的控制和对性的压抑视为现代性的突出特征。其实韦伯论述的新教徒的苦行、勤俭、工作为荣耀上帝、证明自己的上帝的选民而辛勤努力工作,最终成为理性的精于计算的人跟福柯所谓“规训的身体过程”是如出一辙的。我们不妨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看作是新教练伦理对新教徒进行“规训”的描述。所以他们的关注点是类似的,体现了二者思想的亲和性。
(二)现代性批判的勇士
韦伯和福柯都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理性化或者说现代性这一主题,阐述了对启蒙运动大力赞扬的人的现代理性产生的负面影响。两位社会学家如上文的分析,存在着诸多方面的不同。但是殊途同归,不同的支流都汇聚到现代性批判的洪流之中。二者都是敢于批判并且有深刻洞见的勇士。
韦伯生活的年代已经久远,但是他的思想是敏锐、有预见性的。他没有盲目地赞扬资本主义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没有沉溺于理性化带来的发展中而沾沾自喜,而是深刻地洞见了现代理性的限制方面及其严重的后果。虽然理论家们一般不把韦伯放到批判理论家的队伍中,但是韦伯的理论确实具有深刻的批判意涵。正如雷蒙•阿隆所说:“韦伯,我们同时代的人”[12]张旅平亦认为“尽管韦伯是古典社会理论家,但其意识和方法确实是超前的......蕴涵了某些后现代思想并富于启发性[13]”他指出了现代性工具理性的泛滥导致的意义丧失,人们置身于自己亲手建造的理性的铁笼里且无计可施。
福柯赞同韦伯理性化的延伸或者说扩展这一观点,他更具体地分析了理性化在惩罚、疯癫等领域的扩展的细节,阐述了知识——权力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进行统治。他以毒辣的眼光和冷峻的思维揭示现代知识和权力的运作策略。福柯继承了韦伯的现代性批判思想的衣钵,现代性批判之于韦伯是现代性的一方面,而福柯将这一方面发展成了自己理论的全部倾向和逻辑。可以说福柯的理论是韦伯理论传统的极端化、激进化和微观化。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福柯强硬地坚持韦伯理性化的描述。”[14]
(三)没有提出超越方案的悲观者
韦伯与福柯都是现代性的诊断师,却不是治疗师。他们剑指现代性的症结,却没有像哈贝马斯那样提出“沟通理性”这种类似的超越的可能性。他们对现代性的走向基本持悲观态度,他们没有设法改进现代社会,只是停留在批判的阶段。
韦伯试图从政治场域找出超越的可能,他将卡里斯马统治视为超越的动力,“只有卡里斯马的激情才能打破旧有的传统。[15]”但同时又将卡里斯马囿于传统时代。同时,韦伯也将价值理性作为革命性的力量,但是没有进一步阐述价值理性如何战胜工具理性。
福柯同样在探讨监狱的形成、现代精神病院的形成之后再无他话。虽然他将疯癫作为解放的可能性。主张将理性祛除,给非理性留出足够的空间。但这只是福柯个人略为天马行空的愿望,而非有逻辑,有系统的阐述分析。(此处与哈贝马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者都将超越的可能性的目光投向了怀旧。但发展至今,世界无法倒退,让理性退出历史舞台让带有传统意味的卡里斯马型统治或者是个人化的疯癫粉墨登场是不现实的。理性化建立了一种以系统理性的方式不断反传统的‘传统’”[16],也就是说理性已逐渐固化为一种传统。
当然我们不应过分苛责,因为批判思想、批判意识是超越的提前,如果没有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超越也就无从谈起。清醒的批判意识本身就已弥足珍贵。
三 小结
韦伯与福柯的思想存在诸多差异,笔者从较为深层次的方法论层次和研究视角层次对二者的理论做了区分,即类型学与系谱学的差异、现代性概述与现代性“深描”的差异。当然在具体内容上二者也是有区别的,韦伯更倾向于分析现代社会对人们精神的侵蚀,而福柯注重现代社会对身体的规训。对现代性的态度韦伯表现出犹豫徘徊,而福柯表现出的是坚决地批判。
韦伯与福柯思想的联系是十分微妙的,在内容上二者都关注权力和身体这两项议题,都意识到了现代性的负面影响进而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二者都没有提出超越或者克服现代性悲剧的替代方案。
当然作为思想深邃丰富的理论家,韦伯与福柯的思想的联系与区别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二者思想的区别是建立在联系的基础上的,即他们相当多的思想是在同一主题下,从不同视角或者方法来进行探讨的。比如福柯权力和身体的叙述是在韦伯理论的基础上的同向的或是反向的推进,也就是说二者思想的共性与个性关系是辩证的。因此,在本文很多地方的分析都体现为福柯的思想是韦伯思想的具体化、微观化。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社会理论正是遵循此路径发展的,即在联系与区别、概述与“深描”中日益丰富,日益推向前进的。
注释:
①此处苏国勋将“stahlhartes Gehause”译为钢铁般坚硬的外壳。这个单词更普遍的译法为“铁笼”。关于翻译的问题参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克斯伯第三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87页的129条注释
[1]张毓薇,韦伯与福柯之权力观比较,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J].2008,(12):34—36.
[2]尼格尔•多德著,陶传进译.社会理论与现代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3-43.
[3]毕天云,韦伯的现代性思想[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11), 10—15.
[4]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235-251
[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2012:157-165.
[6]马克斯•韦伯著,苏国勋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8,117.
[7]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2012:封底页.
[8]达尼洛•马尔图切利著,姜志辉译.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7,168.
[9]刘永谋,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64.
[10]米歇尔•福柯著,刘北城,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M].北京:三联书店,1999:248.
[11]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上卷),81.
[12]雷蒙•阿隆著,葛志强,胡秉诚,王沪宁 译.社会学主要思潮[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3,454.
[13]张旅平,马克斯•韦伯.基于社会动力学的思考[J].社会,2013, (5),53.
[14]达尼洛•马尔图切利著 姜志辉译,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7):147.
[15]张旅平,马克斯•韦伯.基于社会动力学的思考[J].社会, 2013,(5),51.
[16]李猛.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J].社会学研究, 2010,(5):213-243.
[责任编辑龙倮贵]
A Comparison between Max Weber’s and Michel Foucault’s Modernity Theories
LIU Meng-y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00,China)
Max Weber and Michel Foucault are two grand masters in the academic field of modernity theory.Weber explain the negative aspect of modernity by analogy with “iron cages of rationality”,while Foucault regard the supervision of modern society as a kind of “Panopticon”.Their theories have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and the main divergences exist in the methodology,the perspective,the attitude to the modernity and the main focus of attention.But at last,all roads lead to Rome.They both criticize the modern society logically and profoundly.Although they both point out the crux of modernity ,but they haven’t brought about new plans to exceed them.
Max Weber; Michel Foucault; modernity theory
C91
:A
:1008-9128(2014)04-0058-05
2013-11-04
刘梦阳(1989—),女,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方向:社会理论和发展社会学。